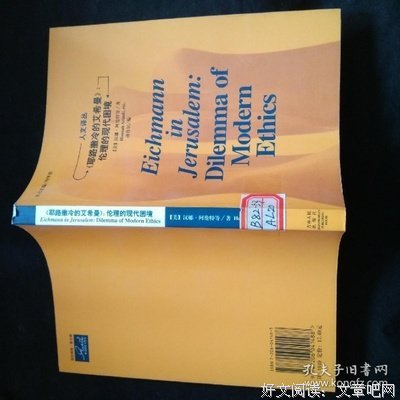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是一本由(美)汉娜·阿伦特著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4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精选点评:
●看书的前言简介何其装逼,生生把个汉娜糟蹋
●选篇不错,翻译捉急
●翻译的超级垃圾,估计是用电脑翻的。
●不需要背景的平庸之恶
●翻译实在是不敢恭维。
●好像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一样
●基于独立人格上的独立思考和质疑权威的能力是如此宝贵。这种能力让我们在他人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大声说:“这不是真的!”
●啃
●还要重新读 反思
●她的书都很晦涩,但若不知道“平庸的恶”,那么所有我们在他者的眼中就都是恶魔。这本书本应是5星,但翻译实在太烂,很多句子都不通顺,不符合中文语法与阅读习惯。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读后感(一):《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1、胜利者的法庭是否缺少公正
2、对人道的罪的有效定义
3、对犯这种罪是新的类型的犯罪者要有清醒认识
(在去病院途中)在车中恢复知觉,开始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试图动动自己的手和脚,身体也没瘫痪,两眼也能看见东西——一一确认了。于是,开始记忆,以十年为一单位回忆往事,还有背诗歌,用希腊语、德语、英语。接着又背电话号码,都正常。重要的是在那瞬间我感受到了一个人求生还是盼死。我并不以为死可怕,生确实是很美好,两者之间若要做出选择的话,还是喜欢生。
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这是我真正的观点。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况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读后感(二):平庸的恶: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
平庸的恶: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
文/魏英杰
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并据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
这本书有着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 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旨在审视艾希曼这类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作用。她关心的是,在第三帝国极权体制下,人的良知是如何一步步泯灭的。这是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中提出“极端的恶”之后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如今,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成为一个经典论断。
经典即权威,而这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伴随着“平庸的恶”一词的流传,误读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在国内,这一术语首先遭遇的是误译。目力所及,国内各种译作除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还有平庸的邪恶、平庸之罪、恶的平庸性、罪恶之浮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不同的译法,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包括误读。例如,恶与罪恶、邪恶,其内涵显然有所不同。平庸的恶与恶的平庸性或者平庸之罪,说的也不见得是一回事。
到底哪一种译法更符合阿伦特原意?阿伦特在致犹太学者肖莱姆信中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阿伦特对恶的重新定义,来源于她对艾希曼的近距离观察。在她看来,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并且缺少这种想象力。他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从这里可看出,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固然不算错,但究其内涵而论,更准确的翻译是“恶的平庸性”。正是这种恶的平庸性,让一个平淡无奇、乏味无趣的人沦为恶魔一般的罪犯。当一个人丧失思考的能力,在强权面前停止思想,就很容易沦为服从权威的傀儡。这一点,已被上世纪60年代一个叫作“米尔格兰姆实验”所验证。这场实验表明,只要条件合适,人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这场实验的主持者称:阿伦特的“恶的平庸”的观点,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接近真理。
但时下有些人,似乎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导致这一概念被不加节制地滥用。比如不久前,某报社员工家人遭遇车祸,在当地寻求媒体报道,记者一获悉对方身份,立即作出不报道的决定,并在网上公开羞辱对方。这场车祸适不适合报道,媒体记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但仅凭身份而不是事件本身作出选择,这无疑是极其荒谬的做法。没想到许多人竟然赞同这么做,有人甚至这么认为:由于这家报社名声不甚光彩,在这家报社任职可说是一种“平庸的恶”,活该被拒绝。
这简直是一个让人膛目结舌的说法。且不说这位报社职员的家人遭遇车祸与他本人身份完全无涉,论者何以见得他的职务行为就是一种“平庸的恶”?很难想象,如果连一个人的行为思想都不去了解,仅凭其职务身份就下这种论断,这种泛道德化的“指控”会把整个社会带入何种境地。这和当年流行一时的“血统论”、“出身论”,又有多少不同?显而易见,在这里使用的“平庸的恶”一词,已全然背离了阿伦特的概念本义,滑向了危险的民粹化思维。
阿伦特当年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这种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这其中,“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阿伦特在这部著作中也谈到审判涉及的法律与政治问题,比如该以什么罪名审判艾希曼,以及以色列对这场审判的政治考量。但她提出“平庸的恶”,思考的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指向的是人类的心灵,即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如何才不至于丧失良知。
这就为“平庸的恶”划出了一圈边界。一旦逾越这个边界,就可能是对阿伦特的误读,从而造成对这一概念的误用或滥用。道理应当如此,法律问题该由法院裁决,人们不能擅自作出审判,替代法律实施惩罚;道德问题,考问的是个人良知,也最好由个人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社会化的道德劝说,极易演化成为一场道德审判。这是在现代社会中不该出现的一幕公共场景。当然,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艾希曼在这场大屠杀中负有责任,在于他不仅参与其中,而且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参加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万湖会议,负责把犹太人组织与运送到集中营,他亲耳聆听来自上司的“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指令,亲眼看见死亡集中营中的惨烈场面。这就够了。他的平庸(这多少出自于阿伦特的片面观察),并不能消解他所干下的罪行,不能减轻他所应承担的罪责。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作恶”,仅凭他的身份而言,无论如何不能够判定他“有罪”。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当年就掀起了一场激烈论战,因此导致她与许多朋友决裂。这一方面在于阿伦特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比同时代人想得更远,当人们还在关注艾希曼本人的罪责,她思考的是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平庸的恶”作为政治伦理上的思考,不乏洞见与远见。遗憾的是,这个概念在当时便已遭遇功利化的解读(为纳粹分子辩护)与道德化的指责(缺乏对犹太人的爱)。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却又被矮化为对“平常的人们”的一种道德绑架工具。这大概是阿伦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种后果。
2013年6月11日
参考书目: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2版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
《责任与判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正义是否可能?》,张汝伦,《读书》1996年第6期
《平庸的邪恶》,徐贲,《读书》2002年第8期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读后感(三):艾希曼带来的是什么困境?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起的争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阿伦特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忠于职守的公务员,而非是一个极端邪恶的恐怖魔头,这与对纳粹官员的想象有极大的出入;另一方面,阿伦特提出了在大屠杀过程中,犹太管理委员会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这引起了的犹太人相当强的反弹。一些人会主张,上述的两个方面实际上都被阿伦特纳入到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之下,是这种独特的政治结构的产物。这种看法我并不想加以讨论,我所关心的乃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伦理难题?换言之,阿伦特使用“平庸的恶”所捕捉到的究竟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此处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应当服从邪恶的法律。战后一些德国法学家主张,如果法律过分邪恶,或者在制定的时候刻意违背正义,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服从,甚至这些规范本身就不是法律。撇开复杂的合法性判准的争议,至少可以承认,我们没有理由遵守过分邪恶的法律。而艾希曼本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难题,相反他缺乏基本的道德敏感,只是关心自己的升迁和“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无论其所执行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他就不能抗辩说自己在“执行法律”,进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解决方案似乎颇为完美,艾希曼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道德义务,最终必须付出代价。
但上述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真正的困难。真正的难题是,如果艾希曼生活在一个基本良序的国家,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公务员:忠于职守,对上司布置的任务兢兢业业等等。这些都是当代官僚体系所鼓励的美德。因此我们似乎很难说,艾希曼本人对道德完全丧失敏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的确接受了一些道德观点。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接受的这些道德观念都是消极的价值,在一些积极价值上,他并没有保持同样的敏感,比方说具有“不可妥协性”的正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不正义的,那么忠诚、法治这些价值就会丧失其意义:它们只是具有工具性,只有在服务一个内在价值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如果艾希曼能够对纳粹体制作出根本性的政治哲学反思,就应该发现,纳粹所宣传的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此时偏离法律的要求,消极怠工可能才是道德真正的要求。
上述的观点自然不错,我们需要时刻对政治生活和法律实践保持高度的道德反思态度。但人们要开始这个反思,需要一定的契机。如果我坚持我自己的确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那么我就不会开始我的反思之旅。反思的契机总是一些困惑和不安。有人可以主张,艾希曼刻意忽略了这些反思契机,比方说他在执行“最后解决方案”时,将大量的犹太人送入死亡营,似乎并没有对这些同样作为人的犹太人的命运保持道德敏感。相反,此时似乎应该追问,是否有正当理由如此行动?不过,如果你如此问艾希曼,他的回答可能是“有”,并且提出一整套纳粹的意识形态。换言之,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在艾希曼看来,可能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足够分量的反思契机。当然我会承认,如果艾希曼真的追问下去,可能会拆穿整个纳粹的意识形态,但我相信即使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如此高度思辨能力的人,也不会是多数。
一些人会质问我,大量的犹太人被送入死亡营,难道这不是一个强烈的道德刺激吗?的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道德刺激,但作出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我们承认一切人的生命具有平等且高度的伦理重要性。这是一个基点。但艾希曼的问题恰恰是,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瓦解了某些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伦理观念,或否定它们,或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因此,艾希曼似乎找不到一个支点,作为起始位置开始反思。
另一方面,这一方面格外重要,某种版本的康德式的道德哲学似乎给艾希曼了某种道德上的安慰。中世纪之后,道德深受神圣命令模式的影响,着力讨论规范化的道德戒律。康德将这种命令的来源,从外在的上帝,转移到了内在的实践理性,但命令模式依然如故。这似乎意味着,只要我们坚持了某种诫命,就已经做到了道德要求之事。艾希曼可以主张,自己已经在自己的范围内,按原则行动,而谴责那些对原则的折中。例如,当希姆莱下令暂时停止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的“最终解决方案”时,艾希曼居然依然忠实地执行着之前的命令,并将这个暂停的命令视为对原则的侵犯而刻意地置之不理。将道德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与个人和社群的伦理生活,与诸种美德的实现没有之间的关联,最终导致人们以德沃金所谓“规则手册”式的方式看待道德命令:它们是机械而又严厉的道德诫命,我们却无法说清尊重它们的深层理由,反而给了艾希曼虚幻的道德安慰。
一些康德主义者会强调,如果按照康德的道德哲学,应当将人视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显然公开地屠杀犹太人并不满足康德道德哲学要求。但这句话究竟在此处如何发挥作用则是不清楚的。或许我们可以主张艾希曼将犹太人当作了使得自己升迁的工具,但如果我们这么主张,现代良序社会的很多现象同时会被纳入谴责的范畴,比方说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买卖。值得认真对待的版本是说,即使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将别人视为手段,但其必须在根本上能获得“平等对待”的辩护,否则就是错误的。当然,一些人能主张,屠杀犹太人在根本上无法获得“平等对待”原则的辩护。此处我倒想起了一个例子:在一次事故中,有一个黑人受伤了,但种族主义的包工头在向上司汇报的时候说“没有人受伤,只有一个黑鬼流了一些血”。这个包工头显然没有将黑人纳入到“人”的范畴中。你可以主张说,他的行为显然也没有做到平等观切,但这个主张的前提是,我们拥有一个人的较为充分的实质性看法。这个看法是说,人就是理性行动的动物,只要他有运用理性能力的可能性,那就是一个人等等。这个观念并非是一个自然事实,永恒地存在在那里,相反它的确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主张。对艾希曼来说,犹太人只是不属于人的范畴罢了,他们是蚊子、苍蝇,或者种族细菌。
因此艾希曼带来的问题,是深层次的。艾希曼所缺乏的,并非是工具理性的推理能力,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价值和目标的理解和把握上。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对话、想象和换位思考来获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这种规范性现象的出现本身,就预设了很多深层次的条件。抽离这些深层次的条件,道德这项诠释性事业本身也会枯萎。纳粹德国的问题,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乃在于整个国家和法体系系统性地违背道德原则,这反而是的遵守道德的行为成为“例外”而受到法律内在原则的谴责。这个国家构筑了一种整体性的虚假道德实践,对人类深层基本价值缺乏敏感的人,显然无力突破这个困局。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读后感(四):平庸的恶从何而来?如何根治?
一、阿伦特对审判的质疑
(1)绑架秘密押送回以色列,蔑视阿根廷的国家主权。
(2)法庭事实上是胜利者的法庭。“加廷惨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两颗原子弹、战争中无辜平民的伤亡。
(3)艾希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罪”(反人道罪),而不是“反犹太罪”,因此耶路撒冷的法庭不具有审判资格,而应该由国际法庭来进行审判。
(4)耶路撒冷审判更多地表现为复仇,而不是伸张正义。阿伦特认为审判的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复仇。首先,以色列人一开始就将艾希曼作为一个象征来审判,而不是作为一个人。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当时曾说:“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如此这般的言论在阿伦特看来背后存在着一些阴谋:1、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的命运,以俘获世界各国的良心作为保卫以色列国家的一种手段;2、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表明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悲惨;3、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对于恢复犹太英雄主义的有效性。以上的这三个动机是外在于审判之外,与“正义”无涉,反而是出于以色列国家生存的考虑。
(5)“犹太人评议会”在最后阶段之前是帮凶。佩戴黄色六角星——集中在指定居住地——强制遣送“再定居”——死亡集中营;奥斯卡最佳电影《钢琴师》(罗曼•波兰斯基)。阿伦特认为在纳粹驱逐和肉体消灭犹太人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被送往死亡集中营之前,“不是艾希曼而是犹太人评议会制作提供了名单”, 要是不提供协助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关于这一条有学者通过调查进而反驳阿伦特的判断:“在东欧大屠杀这个最终事实上,犹太人参与放逐还是没有参与放逐——无论如何——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6)无思想的“平庸的恶”。这是阿伦特最为关心的问题,晚年一直到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这也是汉娜•阿伦特反被别人质疑最重的一条。阿伦特在目睹了审判过程中艾希曼的种种表现之后说艾希曼“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艾希曼是一个普通人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犯了反人类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
最后结论:我们看到阿伦特的种种质疑看上去似乎有在为艾希曼做无罪辩护的感觉,但是在下结论的时候,阿伦特还是说:“这里引起我们关心的只是你所干的事情……政治不是儿戏场所,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何况,拒绝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你和你的上司有决定谁能或者谁不能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正是因为你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必须处以绞刑的理由,而且是唯一的理由!”
口诛笔伐:反犹分子,一个纳粹的支持者,艾希曼无耻的辩护者。
美国学者沃林在《新共和》杂志上说“阿伦特以平庸来为艾希曼开脱其实也是在为海德格尔清洗过去犯下的错误。”
很多好朋友跟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布鲁门费尔德。而雅斯贝尔斯相对能够理解阿伦特的想法。
二、从“极端的恶”到“平庸的恶”
极端的恶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阐述的关键概念。它指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纳粹统治下的种族大屠杀,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极端邪恶的最集中体现。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极端的恶有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徐贲教授认为这三个特征不在同一个层次,前两者是“我们如何对待极端的恶”;第三个是“邪恶是什么?”极端的恶的不可罚并不是指不能在法律上给予惩罚,而是说罪恶深重,无论怎样的惩罚都不能抵消,“死有余辜、死不足惜”。极恶不可知并不等于“善恶不可知论”,不等于价值相对主义,而是说极权主义这种极端的恶植根于超越人类理解程度的卑劣的动机之中,它超过了人类的认知和理解程度。
艾希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之后阿伦特改变了原先对于邪恶是什么(邪恶不可知)的特征的看法,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即从极端的恶过渡到平庸的恶。摩尼教式“善恶二元论”,善与恶都是根本的;恶只是善的缺乏,魔鬼撒旦并不是天生的邪恶,而是堕落的天使。
三、“平庸的恶”从何而来?
平庸的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极权主义下或者说官僚体制中的个人为什么会丧失思考的能力?”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说:“极权主义的本质或者说所有官僚制度的性质都会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的一只简单的齿轮——非人类化。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是理解大屠杀的重要视角:追求效率的同时消解了道德在政治中的空间。”
倒转这个表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原本在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之前,道德是存在于政治之中的。
道德是什么?某某某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是在评价那个人的个人品质,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更多地与个人品性和素质相关,而与政治没有多大关联。其实在古希腊,个人的道德(美德、德行)只有在公共领域(政治空间)才有可能呈现,换句话说就是道德和政治是紧密相关的。
阿伦特划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对应家庭、家务(经济)、专制,同时为个人进入公共领域提供物质上的保障;而公共领域对应城邦、政治、平等,是个人形成和展示个人优秀品质(德性)的空间:节制、勇敢、正义、友爱、慷慨等等。私人领域是无价值的,私人(private)即来源于贫乏(privation),相反,公共领域是古希腊人“人之为人”的可能性空间。由此可以看出,个人的道德(德性)主要在政治中呈现,道德存在于政治之中。
只是到了西方近代,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认为国王应该兼具狮子和狐狸的性格,为了达成最终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治国术。政治沦为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不再像古希腊时期,政治本身就自成目的性,政治参与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近代之后的政治参与也沦为保护个人权利的手段之一。政治工具化、无意义之后,道德也开始从政治领域退场,成为私人领域的一种属性。
在阿伦特看来近代之后出现了社会领域(市民社会):古代限制在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在近代扩张到公共领域的产物。随着西方近代“个人”的出现,私人领域地位上扬超过了公共领域,政治成为保障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工具。古代的人是从公共领域出发,终点是公共领域中的个人德性、共同体的良善;而近代的人是从私人领域出发,终点是私人领域的个人利益和欲望。
鲍曼的观点:科学的理性计算;技术道德中立;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使得道德从政治的空间退场,随之出现了极权主义大屠杀。
:伯林和施特劳斯之争。
三“平庸的恶”如何根治?
阿伦特看到了现代人的无思想性——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是一种很可悲同时又是一种很可怕的症状,如何根治这种“现代病”成为阿伦特晚年回归哲学思辨的重要问题。她把人的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三个部分,认为“无思想”不是说人没有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指没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因此她认为必须提高人的判断力,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两分:判断力是横跨这两个领域的能力。
鲍曼的拯救之途:个人无条件地承担起道德责任。
鲍曼和阿伦特开出的处方能够根治“平庸的恶”吗?我的判断是没有办法根治。“平庸的恶”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世界的去魅之后理性化趋势使道德保持缄默,法律(规范)没有办法完全取代道德对于个人或者共同体的功能;道德成为个人的事情,而自律不仅对自己不具有强制力的,同时还没有办法推及他人。康德形式主义的伦理学。
没有办法根治,那么是不是还有出现极权主义的可能?电影《浪潮》反映的是当下西方仍然具有再次出现极权主义的可能——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去反映的。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是现代西方的一体两面,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