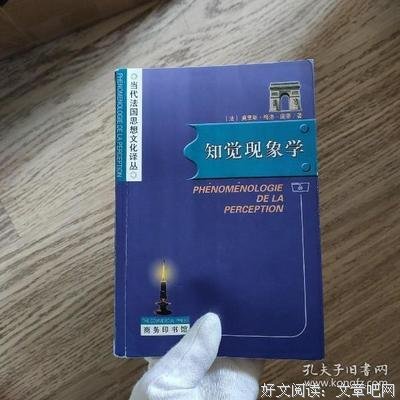
《知觉现象学》是一本由[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5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觉现象学》精选点评:
●译本太差了
●这翻译……天人之姿啊……我要肝原版了。
●虽然翻译并不流畅,有的词语有些模棱两可,但是对于法文并不熟悉的读者来说,有这样一本书去接近梅洛庞蒂已经很不错了,自己在期待好的译本的同时也要多加强语言的学习,这样才能再走近思想家。
●英译本对照之下,这中译简直天坑!特此标记,见此译者绕道。
●一半。实在不想再翻一遍。
●花了近二十天吧,一个字一个字读完的。过程真是痛苦不堪,但仅仅理解了十分之四也是痛快的。
●姜志辉果然是毁书不倦的译界奇葩。
●艰涩难啃
●代表作
●原来翻译跟写德勒兹身体美学的不是一个人啊我去
《知觉现象学》读后感(一):給2星純粹是因為翻譯~~
這個譯本還是我大學時候讀的,毫無印象。讀了一點colin smith的英譯本後,才發現這個中文版翻譯問題的嚴重。2星有一星是因為梅洛龐蒂的名字,另外一星是因為無法打零星。
英譯本五星,毫無疑問。
《知觉现象学》读后感(二):翻译醉了
这本书的翻译,看得真是要疯了,字都认识,但是好像不是人话,真是看不懂,不知道读了个啥,刚看了半个引论,不知道还能否坚持下去,难道是要我去读英文版的吗!!!!!!!!!!!!!!!!!!!!!!!!!!!!!!!!!!!!!!!!!!!!!!!!!!!!!!!!!!!!!!!!!!!!!!!!!!!!!!!!!!!!!!!!
《知觉现象学》读后感(三):真的建议学完法语,读过笛卡尔,再念。。
看到有的短评里面说:对照了中英本,觉得姜黑很过分,这本还不错,云云。。。。我想说,学过法语、学过哲学再来评价好咩。。
其实我没什么评价。只是,就在,终于快动笔开始写merleau的博士论文前,感慨读这本书的历程 一丢丢。
这本书首次见到是本科四年级,方向红老师开知觉现象学的课,第一次系统念。基本读的是中文和英语。而当时因为那个课是开放给其他院系,很多文学、外语系的学生来,方老师详细讲了avant-propos,之后为了激发大家的阅读,每章都是采取同学报告然后他点评的形式。(结果更加导致本来就杂多的内容被多学科背景的同学阅读以后,我更找不到哲学线索了
说实话我当时的法语能力远远不能直接读原文;而且此书的introduction部分(说是introduction,其实那部分很厚)涉及好多心理学实验——当时我却缺乏法国哲学身心关系问题的背景,导致有点迷失在各种具体材料里,而没有一条理解思路。。总之,没读懂~
后来研二要开始构思硕士论文了。复旦没老师上这个课,只能自己念。光念完introduction和第一部分corps就花了半年整。呵呵,姜译本能不黑吗?——几乎到每一页都要我自己重译一遍才能读懂的程度,可惜现在这本中文本丢我家了,不然好想晒几百页被彻底涂改的页面的图片出来。前前后后大约念了有三遍才开始写projet de thèse,给法国导师,然后根据博士计划的一部分写了硕士论文。
当然,依然非常难懂,但是甚至不是语言上的——merleau的语言非常优美有力,是可以引人进入哲学迷宫的。而是哲学背景上的:
merleau的起点是知觉,是身心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如果没读过法国哲学的笛卡尔传统(甚至其中涉及到中世纪阿奎那-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体系的知觉问题)、不熟悉近代英法所谓经验论-唯理论就很难进入其语境的问题;
可是最终的这本书的落脚点是人的自由,是一个与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自由”相关又相对立的命题。
= = 拿我法国导师的话说,前者是le scénario cartésien(第一个笛卡尔式的剧本背景),后者是rupture avec Sartre(与萨特的决裂)。
在我的硕士阶段,前者于我根本就是一个空白;后者,非常幸运地是在写博士计划前听到刘国英老师来复旦做的一个系列讲座,主题竟然就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关系,算是提供了一个基本入口吧。
而可惜,很多人往往误解merleau最大的背景是husserl现象学——这条路当然不算彻底的南辕北辙,但实在也偏离了太多。知觉-现象学,在处理知觉的过程里(merleau 26岁时候(1934年)写的博士论文计划书,就叫做la nature de la perception(论知觉的本性),这是他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彼时现象学和心理学都只是他借鉴处理这一核心问题的背景资源),最后所得到的对现象学的理解,其实也改变了德国“现象学”的定义。——最明确的宣言便是avant-propos了。
最近在导师的催命下,终于准备开始落笔写thèse。整理材料的时候又一次读到avant-propos的一段引文。这个前言在读博之前也是念了不少次了,读博后有一次还给一个同学几乎以口译般详细的形式讲过一遍。可是哪怕就这一段长引文,还是觉得写的简直好到极致(虽然可能,毕竟大多数书写的最好的就是前言。。)。
当然也更想感慨一下我的幸运,除了遇到一群学笛卡尔的小伙伴带我用最仔细的方式进入了scénario cartésien乃至往上延续中世纪的perception问题使得最终能够更好地去阅读merleau——结果,此生何等有幸,因为今年法国的agrégation(高等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的哲学史主题之一竟然就是梅洛庞蒂,。。天哪,简直不能想象就在我读博期间、在恰好要开始写论文的这一年、在Benoist的思考状态牛逼到顶点的情况下,恰好就,我眼里神一般的jocelyn Benoist用整整一个学期完整讲解了我眼里神一般的这本书!!
哈哈
《知觉现象学》读后感(四):《知觉现象学》第一部分第五章释读
[半年前写的论文,引文是自己从英文版译的,出处就不标了。译文没考证过,应该很多错。其实没懂梅洛庞蒂。]
他解开了著名的谜题,是个了不起的伟人。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 哲学仅宣示了从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入手解决该问题是可能的。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自从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著作在世纪之交出版,与主体共生的性的维度便给“19世纪80年代的欢愉启示录”划定了终止符;光与影交织的新时代也正如弗洛伊德所期盼地到来:“光”指称的是启蒙神话传承至今的火种,更深入地说,是在共时性的意识维度中透视人性的狂想;“影”则是人性中被压抑的底层枝干,它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实践中被拉入个体的意识,在作为整体的精神分析运动中被烙进历史的脉络。与其说弗洛伊德证明了(后)工业时代的中产阶级其内心有多么龌龊不堪,倒不如说他发现了众多内心的某个角落被阴霾所笼罩的脆弱病患是如何把自己装点为文明人的——直到人性中光与影的二维被视为人的一体二面时,历史才翻开了新的篇章。
结构主义运动前夕,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其名著《知觉现象学》中,专辟一章谈论身体与性的关系,即第一部分第五章“身体作为性化的存在”(The Body as a Sexed Being)。他称该章所要探究的内容是“情感化的背景”(Affective Milieu),即“只对自己有意义(sense)和实在性的那部分经验”。与此同时,正如英文版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性(sex)并非只是身体的可分离的一个属性,而是在“自身身体的综合”(The synthesis of one’s own body)中、在“活的意义的纽结”(a knot of living significations)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自身身体”、“活的意义”这些词语提醒着我们:梅洛-庞蒂要在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的基础上对性的话题展开研究,“回到实事(the things)本身就是回到先于知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知识总是在言说(speaks)”,这意味着梅洛-庞蒂的哲学致力于光复人(哲学家/哲学家笔下的人)与世界的原初联系,在生存的维度上揭开斯芬克斯的暧昧(ambiguous)面纱。
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尽管梅洛-庞蒂也乐于拥抱人性中的背阴面,但他仅是选择性地吸纳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对之进行了批判与重建。下面的文章将以问题为导向,对梅洛-庞蒂的控方陈词进行阐明。
Ⅰ
1. 1 反经验主义:知觉—性欲图式
在章节开头对于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关于性欲的观念的批判过后,梅洛-庞蒂认为他的洞见与精神分析中“最能历经时间考验的成果”不谋而合,这更多是因为他们都把性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固着维度。他们的不同点在于,梅洛-庞蒂秉承着德国先驱们的现象学方法,认为意向性活动在性的生活(sexual life)中无处不在,关键之处在于对性欲图式(Sexual schema)的知觉: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一个身体不仅仅被感知(perceived)为另一个客体,这种对客体的知觉(perception)根植在另一种更为隐匿的知觉当中:可见之身躯之下是一副彻底个人化的性欲图式,它凸显了快感区(erogenous zones),勾勒出了性欲地形,唤出了融贯在情感化的整体之中的男性姿态。假如一个人缺乏唤起性行为的意向性,那么他便无法捕捉性欲图式,从而引起性生活本身的退位(an alteration of sexual life itself)——这即是梅洛-庞蒂对于性冷淡(sexual inertia)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可以回头审察经验主义性欲观的偏颇何在:性欲不仅仅是一种反射,身体—知觉也不能被简化为物理学模型,性欲的运作是对性欲图式的知觉。下一部分,我将通过对梅洛-庞蒂反理智主义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包括“知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概念。
1. 2 反理智主义:生存分析
理智主义的性欲观,一言以蔽之便是把性欲作为表象(representation),作为纯粹的意识活动。但梅洛-庞蒂指出,“爱欲知觉(erotic perception)不是指向对象(cogitatum)的我思(cogitatio)”。弗洛伊德对心身二元论(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的不满也与此近似,这种简化的风险在于把身体形式主义化,实际上“(爱欲知觉)通过一个身体靶向另一个身体,这个过程是在世界,而非在意识中完成的。”性欲靶向的作用机制与视觉场相类似:它们都通过掩映把某物 [视觉对象/性欲图式] 相对于背景明朗化,而并不是把它作为意识的特定对象来捕捉。
更深一层的讨论涉及到身体与生存(existence)的关系。在此,梅洛-庞蒂把二者与话语—思想相类比,即原初话语的含义(signification)/思想并不外在于它自身,同理,身体作为一种原初的生存状态,它并不外在于生存。下述这段话很好地揭示了生存和身体之间的关系:
如果身体能象征生存,这是因为身体使生存现实化,并且身体就是生存的现实(actuality)。在一方面,我的身体是使得生存摆脱它自身、摆脱匿名和消极的状态、摆脱陷入纯粹形式主义的可能性。即理智主义对身体的讨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不存在作为纯粹对象的身体,它与经验主义一同遮蔽了我们对生存的真实理解之可能。身体是“跃动的虚无”(active nothingness),即它一方面附带着种种感受器官使我们与世界不至于断绝联系,一方面又浸染在它之为“生命的匿藏地”(life’s hiding place)的事实当中,使得事物的(在自然时间中的)确定性转化为(沉湎于静默中的)永恒性,使得海德格尔式的“栖息—无家可归”之间的神话性张力在此被定格为与彼时知觉同外延的生存论建构。
Ⅱ
上文通过考察梅洛-庞蒂对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批评引入了他的一些关键概念,而这一部分我们将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参照系,阐明梅洛庞蒂的生存论建构。
按照梅洛-庞蒂的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在于…在‘纯粹身体的’运作中发现辩证法运动,并把性整合至人类的生存中。”这显然与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纲要不符:
认为精神本身是无意识的观点,则使心理学能够取得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地位。它所关注的过程本身就像其他科学,例如化学和物理学所涉及的过程一样是不可知的,但却有可能建立支配这些过程的规律,并有可能去追寻这些过程的长期持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总之,有可能像所描述的那样,获得对正谈及的自然现象领域的“理解”。弗洛伊德竭力把精神分析的定位与科学靠拢,他把“肉体伴随现象”,即症状(symptom),看作是“某个结构的功能”,这甚至与梅洛-庞蒂所批判的经验主义暗合。按照梅洛-庞蒂的措辞,“弗洛伊德的作品不是一幅有关人类生存的图画,而是一幅有关各种非常频繁地出现的反常现象的图画”,实际上,精神分析跟现象学合流的可能性在于前者认为一切人类行动(包括症状)都具备意义,并尝试去理解它们——这是一种哲学的姿态,以苏格拉底的诘问面对一切存在之谜:
造就一个哲学家的是不停地从知识导向无知,又从无知导向知识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的某种宁静。我们隐约地能发现存在于弗洛伊德思想—人格中的深邃与断裂: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科学巨人,他发现了支配心灵过程的规律并引以自豪;另一方面,虽然他有意识地将作为心理学的精神分析与“哲学”区分开,精神分析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却启迪了整个哲学领域:哲学从纯粹的理性域下降到流变的生活世界,人文(humanity)关怀与理性主义传统互渗,为消费社会中的游荡灵魂奏响最后的挽歌。
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揭示出自我(the Ego)和他人(the Alter)之间的辩证法,即“正是在‘他的’欲望中,通过‘他的’欲望,更确切地说,作为‘他的’欲望,人才成为人,并且——向自己和他人——显现为一个自我”。梅洛-庞蒂在这一章中的论述对其借鉴甚多:“辩证法不是相互矛盾而又相互绞合的思想间的关系:它是从一个存在朝向另一个存在的张力。前者否认后者,然而前者并不能在缺乏后者的状况下持存。”比如,害羞和无耻不是心灵世界中的孤独情感,恰恰相反,主奴辩证法表明了“他者”填充着情感投射方向的对岸空缺,更为重要的是,凝视(gaze)与被凝视是向他人身体的、是向世界的开放。梅洛-庞蒂对主奴辩证法的认可在于它指向一条拒斥自闭(self- enclosed)的道路,指向他人也指向世界。《知觉现象学》著名的“序”(Preface)中有言:
世界……是我的所有思想和所有清晰知觉的背景和场域。真理不仅仅“寓居”(dwell)在“内在的人”(inner man)之中,而应该说,根本没有“内在的人”,人是在世界之中并且面向世界的,他在世界之中认识自己。人对自己的认识便是对身处世界之中的开放可能性之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实践立足于“治愈”神经官能症——即使得“患者”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重新协调,能够重新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生存(coexistence),神经官能症的发端始于创伤经验、始于性冲动的历时性发展障碍,即在共同生存的过程中遭遇失败。然而,精神分析的弊端在于,它虽然揭示了性作为生命的底层结构,但也把生存的所有维度都整合到性欲的维度当中。于是我们被引诱进了一个二难抉择:要么承认生存归根结底具有性的意义,要么承认每种性欲现象都具有生存论上的意义。其结果是把生存抽象化,并且成为了对性的生活的同义反复(tautology),也就是说,性成为生活动力学的第一因;而梅洛-庞蒂指出,性只是情境化(situated)的,同时,“性欲不能被浸没在生存中,仿佛它只是一种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性欲是无法被抹除的背景,它“和生活是同外延的”:
性欲既不超越于人类生存,也不将它的内核展现在无意识的呈现中。它在人类生活中永续不断地作为氛围(atmosphere)而呈现。性没有涵盖生活的全部,而是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反映的是我们的实存;共同生存不意味着患者从臆想下降到现实,而是指示着他走出了永恒的第一人称视角,重新“在世界之中”(being in the world):在此,光与影的二分透视法被整合进了暧昧(ambiguous)的生存歌剧当中。假如我们得以进入共同生存域,那性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精神分析的临床诊断已表明了答案:个体的性欲历史通过症状显现出来,精神分析的伟大洞见就在于“我之所是”的答案要通过对过往历史的回溯才得以展开:
力比多(Libido)不是一种自然地朝向给定结局的活动。相反,它是主体附着于不同背景上的一般力量,它确定了主体的经历,使他获取行为的结构:力比多就是保证主体具有历史的东西。这否认的是两种生活态度:一是“活在当下”。崇尚这类心灵鸡汤疗法的人祈祷在现代性大潮中能随波逐流,但往往在其最深层的静滞和无节律中无暇反顾自身,反倒被资本拜物教缚入了(后)现代性的牢笼;二是理想主义,机械化的时日进程使得人们开始幻想诗和远方,但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却被弃之不顾,只剩由一个个假设句式堆砌而成的翡翠梦境。最好的结局便是若干年后躺在养老椅上哀叹“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偷得听众的朵朵泪花。
他们所不知的是,力比多历史是发源于过去的、作用在当下的,并且影响到未来的:现在的每一刻都是过去的未来,都是未来的过去,主体的性欲地图便由此具有了时间性:这不是线性铺开的物理时间,而是经过对开放/拒斥的回溯而形成的逻辑时间轴。
我们总会遭遇到这样的艰难时刻:当真诚的呼救被世界的黑洞吞噬时,人对世界的拒斥便以症状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至关重要的洞见是,症状是影响(effect),而非原因(cause);抗拒(resistance)不是对某物的抗拒,而是对开放与共存的意向性抗拒:可能性场域(field of possibilities)崩溃了,逻辑时间轴上的奇点引爆了。梅洛-庞蒂区分了两种虚伪(hypocrisy),以便更好地说明这种抗拒作用的独特性:
前者(心理学上的虚伪)通过隐瞒主体明确已知的想法来欺骗他人,这是易于避免的偶发事件。后者(形而上学上的虚伪)通过普遍性的方法欺骗自己,它的终点不是命定的,但也不是(主体)曾设想的、曾欲望的;这种情况在“真诚的”、“可靠的”人想要假装成为无剩余的他所是(pretends to be what he is without remainder)之时也可能发生。这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梅洛-庞蒂在这一基础洞见上与弗洛伊德相契合。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抗拒作用将主体带离他所熟悉的悲惨世界——这是形而上学的而非心理学的抗拒(显然弗洛伊德不会同意这样的用词),是主体既知又不知的,却不是被意识到的。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比作考古学的意蕴便在于此:深藏的岩层不会自己破土而出,这种无可逃避的虚伪与自欺所代表的人类境况正是在幻象中所建立起的文明:
幸福必须服从作为全日制职业的工作纪律,服从一夫一妻制生育的约束,服从现存的法律和现存的秩序制度。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而哲学—现象学的任务则是“回到实事本身”,那么它所绘画的身体辩证法揭示的是被掩埋的“存在的步伐”(existential step),它“把观念转变为事物”,跃动的身体使人类闪回真实生存。物化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意义缺失体,它与理智主义一般,使主体和客体变得虚无;而哲学关涉人对世界的理解,主体对意义(sense)链条的构建应当通过生存,因为生存是对具体境况(a de facto situation)的拾起(taking up),它赋予某物以意义,赋予只有性的意义的某物以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各样的戏剧在我们面前纷呈: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呼吸着性的氛围。我们不能把意识中的某个单一组成认作“纯粹是性的”或不可能有性的,同理,经济和社会的戏剧给每个意识提供了予以自我解码的背景或意象(imago),在这种含义上,这类戏剧与历史是同外延的(coextensive)。性、社会、经济等等都是戏剧式的,“自由在‘沉积的’历史背景中突现出来”,凡人在其中饰演着他们自己——饰演一词的全部意思是,我们被位居自我之外的剧本所驱动(motivated),但我们又投入(engage)到世界当中,宏大背景下的偶然性被人类转化为具备意义的必然性。
梅洛-庞蒂在最后一章“自由”(Freedom)中述说道:“主体的突然现身(appear)使得意义和价值在物之中显现(appear),无物能不被他赋予意义和价值而触及(reach)他”,主体的自由只有在世界中才能实现,他的行动、选择孕育了意义,“拾起”一词意味着意义是零或全的游戏,当主体下决心跳入生活的冒险中后,他便源源不断地吸纳外部世界,并通过自由的选择开辟下一步行动,比如在生活的苦难面前选择饰演一个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意义”一词应作此解。
意义域总是待填充的,规避“瞬间的幽灵”(specter of the instant)意指着,每一个瞬间总是向下一个瞬间开放。生存既不是超越的(transcended),人类无法盼望无条件的自由;但生存也不是自闭的,人类对世界的介入注定了他能开拓无限可能:“无人彻底得救,也无人完全迷失(no one is fully saved, and no one is fully lost)”。
《知觉现象学》读后感(五):深度视觉理论演进及梅洛-庞蒂的本体论读解
在哲学传统中,深度(depth)现象因其复杂的意涵,被称为“视觉之谜”。对这种现象最朴素和流行的解读莫过于“照相机”比喻,即将人的双眼比作相机,外部世界以一定比例精确映现在视网膜上,从而人类得以观察和把握到外在对象。然而,照相机的比喻性阐释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常见的“两可图”(ambiguous figure),这种图形在视网膜上的映像是单一的,却能给出不同解读;其次,外部空间是带有深度的三维世界,但由于视网膜是一个平面,对象在其上只能以二维形式展开,在这种对象与视知觉的呈现并不完全对等的鸿沟中,面对画在平面上的立体几何形状,视知觉向身体释放着“错误”的信号,从而平面上的对象以三维方式呈现给身体,原本并不存在的深度,却以“在场”方式出现了。面对这些疑难,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做出了诸种不同尝试。鉴于如何诠释“深度”问题,牵扯到“空间”、“视觉”、“身体”、“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核心哲学论调,因而,以深度为契机能够切入到唯理论与经验论、康德的批判体系、格式塔心理学以及梅洛-庞蒂现象学等流派塑造视觉和空间学说的历史脉络中,更加明晰地窥探到深度视觉的理论嬗变及其所携带的哲学内蕴。
一、传统深度理论及其困境
(一)笛卡尔的几何学深度观
在《屈光学》[1](152-176)中,笛卡尔从心智分析的几何学角度处理深度视觉。他认为,距离(深度)判断是通过从眼睛发出想象的直线在物体上交会的角的大小实现的;眼底所对的角度越小则与物体的距离越大(深度越深),我们借助各个角的综合知觉(perception)到对象的大小和距离。传递方式是通过对象,经由眼睛再到思想。这意味着,是否“直接”知觉(看)到对象并不在认识中占据核心位置,对笛卡尔来说,天生性盲者通过触觉和数学解释也能明了视觉学说。
然而笛卡尔的问题在于,就“知觉”和“观看”这个整体系统来说,我们不能将知觉分割成各个部分,或者看做各种感觉和器官功能的简单拼合,因为被综合的整体在功能上总是大于部分之和。这样一个整体并非观念和运算的整体,知觉所发现的意义(meaning)也不属于笛卡尔式的概念范畴。如图一所示,两个图形在理智推断或运算的几何学上,以及在直接视看的知觉上所带来的意义完全不同。
图一更进一步,触觉和视觉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天生性盲者能够通过触摸和思维运算得到对类似广延物体的认知,但这不同于“看见”此物。假设他一直以来被教授利用触觉和心智运算顺利区别出圆形和方形,那么当他忽然获得视觉能力,重新通过“看”而不“触摸”能否准确区分出这些图形呢?事实上,经过英国医生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2]和研究者玛利乌斯·冯·森丹(Marius von Senden)[3]实验验证,答案是否定的。[4]①因此,就知觉本身来说,视觉很难与触觉或心智思维通约,即便经由心智或逻辑思维认知到的是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与“眼中”的世界带来的意义却截然不同。越过体验直接抵达观念世界、施行智性行为,而不分析知觉事实,这样的理论是否具备“视觉理论”的资格?
由视觉对象到思维观念转化的笛卡尔式解决方案,被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等学者归结为“一种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转化”,[5](6-9)在他看来,这种方式将“深度”这个三维问题转化成了二维问题,这与朴素的照相机譬喻并没有本质区别。符号化推论模式在现代科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科学家已经研发出能够进行“视觉识别”的机器:接收器以符号方式捕捉外部对象,将其转化为可识别的信息,再经过内部运算,而后执行各种外部命令。 但这与直接经验的根源性区别在于,一种以“智性(智能)思维”的推论为手段,把经验对象直接地还原为智性元素;而另一种则以“身体的知觉体验”作为视觉的意义核心。在这种符号化的唯理论视野之下,客观思维造就的一个宏大而精深的客观主义世界图景,但却扭曲了知觉世界的原初结构。
(二)贝克莱的经验论深度观及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
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乔治·贝克莱在《视觉新论》[6]一书中,对笛卡尔的深度视觉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深度纯粹是一个视觉问题,不能用不可通约的触觉语料替代解决。笛卡尔视觉学说的致命之处在于其“可解证性”(Solvability),实在的光学只研究直接经验的视觉问题。贝克莱将生理学和几何学抛开,试图单纯根据视觉材料建立一种新的视觉学说。
按照贝克莱的理论,由于视网膜是二维的,不能直接反映第三维度,所以深度本身并不可见。外在对象反射的光线以若干直线呈现给眼睛,不管距离远近,能见的只是光线各端或多或少的“点子”。由于光线只能“纵落”在视网膜上,而不是“横落”,所以眼睛能看见的只有一个个点组成的长和宽;深和厚,即视线中的距离根本无法通过这些点被看见。外在的广袤性并不是凭借视觉本身被识别,而更多地借助于知觉与对象中间的物体获得。归根结底,深度不过是从侧面看的宽度。
贝克莱的深度学说建基在其时代的知识背景和经验论传统之中,但方法并不是科学实验,而是用一种经验自省的方式对当时的视觉学说进行了整理。他认为,类似《屈光学》中所言的“线”和“角”本身在现实中用肉眼是看不到的,数学家以这样的概念来解释距离,但对不精通光学的人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知识,又如何在经验中经由两条光轴的夹角判断深度?笛卡尔的学说可以解释深度视觉,甚至在科学实践中应用,但却有悖于最常规的知觉经验。既然线和角并不真实,他们在自然中也就不是实在的存在,要知觉深度只能以实在的存在和其他观念作为媒介。如果知觉诸因素都是不相属的可感观念,那么不预设空间也就无法解释空间知觉。固然不能从视觉观念得到空间,触觉观念也一样得不到空间。
虽然视觉和触觉存在着根本差异,但对象的“可见属性”和“可触属性”却有一种实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至少在空间中是一致的。按照贝克莱的理论,所见深度是借由经验得出的假象(侧面看的宽度),而所触深度则是实在的。即便所触深度和实在的深度是两回事,但它们都是实在深度的“标识”。触觉和视觉所给予的感觉材料,以及关于情境中各种关系的经验与判断,都只能作为构造深度时的根据。因而,要点在于厘清何种观念或感觉伴随视觉而来,与深度观念相关联,并将其引入心灵之中。贝克莱的方案是:1.物象离我或近或远的位置变化带来了两眼位置的变化,眼睛的这种排列和运动能够引起一种“筋肉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心灵产生距离长短的观念原因之一;2.筋肉的感觉与距离之间的联系并不必然,因而天生性盲者无法在复明后突然从视觉上把握到深度。人们通过恒常的经验发现这种筋肉感觉经常伴随物象的不同距离出现,这两种观念便因为习惯联系起来。贝克莱由此断定,深度判断只是经验的结果。
在《视觉新论》的译者序言中,关文运指出,贝克莱的问题在于,假设V(vision)表示所见深度,T(touch)表示所触深度,D(depth)表示实在深度,J(judgment)表示心灵构造中所含的判断成分,那么实在深度D作为一个复合的统一体,既可以借助[JV],也可以借助[JT]表现出来。触觉所感之深度和视觉深度都不是实在深度,我们很难抛开意识中的反省/沉思(reflective)判断成分,直接将深度知觉视为只包含可感语料的经验习惯的结果。[7]但贝克莱对笛卡尔深度观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切中了要害:一方面在距离判断中,没有人敢于声称能够直接观察到光线之间的夹角;另一方面,笛卡尔无法解释动物、儿童以及没有几何学知识的人何以凭借几何解证知觉深度。
(三)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综合
笛卡尔的论证预设了一种心灵所固有的“天赋观念”能力;霍布斯和康德等哲学家也主张,如果没有一种先天地分开空间中的事物和时间上先后的先验观念,单纯凭借经验习惯,人们其实无法从知觉中获得有效材料。在康德看来,空间不是一个由外部对象抽象得出的经验性概念。空间关系要以已有的空间表象(Vorstellung)作为基础,即便可以设想空间中没有对象,但没有空间却存在的对象是不可设想的。空间作为现象存在的可能性条件,是外部表象基础的先天表象。[8](47-52)康德的时空观是在“先验感性论”中回答“纯粹数学何以可能”问题时提出的。感性是通过被对象作用的方式而接受表象的能力,空间和时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感性纯直观——起作用。感性不是消极接收,它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认识形式,把给予的感性材料组织为有条理和可被认识的经验。其过程是:物自体提供刺激对象;感性直观接收表象;作为先决条件的感性直观纯形式(空间和时间)提供感性得以综合感觉材料的能动性、弹性和限度。康蒲·斯密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空间之所以能够承担感性纯直观的功能基于以下原因和特征:1.空间是外部事物位置关系的先决条件;2.空间的先天性不依赖于外部对象和外部经验;3.空间关系不是概念之间的推理和概括,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空间的观念是单一的整体,先于部分并决定部分的性质,空间整体与部分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差别;(4)空间可以无特定外延地无限延展。[9](37-199)
在康德看来,空间的先验性在于它并不依赖于经验,相反经验对象只有预设空间才能被思维和表象。他的先验论证不同于笛卡尔的地方在于,后者认为空间的明晰和确定性始终是一种“观念”抑或“概念”意义上的实在性;而对康德来说,空间绝不是概念。空间之作为整体并非从部分抽象出来,它在思想上先于概念。既然空间不是概念,康德便抛出了其作为一种“直观”的论证,这一论证和唯理论的“天赋观念”论证如出一辙:说空间是一种纯直观,是因为当我们关注一个三角形的内角时,其内角和为180°的必然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经验和思考。
二、格式塔学派深度视觉理论
笛卡尔和贝克莱深度理论的显著特征是,认为触觉和视觉等诸感官能力与观念生成的直接程度,以及具体的知觉方式存在着差异,因此各种感觉在本质上是分离的。而以知觉的组织性为核心论证的格式塔(Gestalt)学派认为,各种感觉尽管在逻辑上分离,但感知到的却是一个完整的、有组织的知觉世界。以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为代表的格式塔主义强调以知觉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非知觉元素本身或感觉能力本身作为其他知觉的基础。知觉元素之间的关系面对不断变化的外界刺激,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特性对知觉中的恒常性[10]②、两可性和深度错觉等等,能够做出合理解释。
德文“Gestalt”与英文“form”相当,译为“形”或“形式”。所有知觉对象,作为 “格式塔”都是知觉进行积极组织和构建的结果,每一个都能作为独立的全新整体存在。例如,一首乐曲作为整体具有完整和稳定的格式塔结构,无论这首乐曲以钢琴、小提琴或哼唱等何种方式表现,曲调的内部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听众仍然能够辨识出这是同一首乐曲。而在识别过程中,知觉积极、主动的组织能力通过其能动的自我调节倾向达到内在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知觉中占优势的力量便会倾向于简化。例如,在艾恩海姆的实验和分析中,将某图形呈现在被试眼前一瞬间后迅速移开,若干天后,让被试将他所见的图形画下来。此时,原有刺激的印象因为时间关系大大削弱,被试对图形进行了大量改造,但改造后的图形相比原图会更加简单和对称,有断裂和缺口,倾斜和不规则的地方都会被纠正过来。反过来,面对简单、规则的格式塔,知觉主体会因为符合知觉追求简化的原则而感到轻松和愉悦。当被试画出他们认为能表现优美和愉快的线条时,他们画出的一般都是规律性很强、简洁、流畅或平直的线条。[11](80)
如果知觉简化原则成立,那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理论,面对深度等带有复杂空间层次的多重格式塔知觉对象时,首先需要做出“图形”(Figur)和“背景”(Hintergrund)的区分,确定“图-底”关系。所谓“图-底”关系是指哪些“形”从背景中突出构成“图”,哪些保留在背景中作为“底”,目的是为了定位三度空间或平面空间中的三度错觉空间的视觉中心。视觉中心决定了知觉式样在经验中以何种样态呈现。
图二如图二所示的三幅图中,A一般被视作六边形;B既可视为六边形,又可视为侧棱正对观者的立方体;C则被视为立方体。按照格式塔理论,三幅图都是正方体格式塔的变形,但根据简化原则,将A视为六边形而不是某一角正对观者的立方体对知觉本身来说更清晰和简便;而将C视为正方体也更符合知觉简化的规律,这个立方体并不是一个物理立方体在视网膜上的简单投影,而是对象在三度空间中的最简化的结构等同物。
格式塔学派的深度视觉理论区别于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处在于,它认为三维形状和二维形状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组织问题,原因在于“组织之力”[12](113)③,这些“力”既可能与其他力合作,也可能相互冲突。图B就发生了二维力量和三维力量的冲突,当冲突的两种力量达成平衡,处于优势的力就是视觉倾向于知觉到的形式。显然,在A中,二维力量占有优势,C则正相反。
格式塔学派的理论与笛卡尔类似,都认为视觉加工过程最关键的步骤不是发生在视网膜上,而是身体的整个系统当中。姑且不考虑这个系统的生理机制如何运作,它都起到了活动“场域“(Präsenzfeld)的作用,由刺激引发的各种“力”在这个“场”中相互角逐。而相比传统理论,格式塔学派认为,身体对刺激图式的处理不是机械的,而是按照诸种力量自身的倾向性,最大限度地把图式转化为最简单的整体性结构,对这种整体性结构特征的把握和组织是作为知觉和其他所有智性行为的基本前提。基于这种前提,如何确定物体在三维空间内的位置取决于某些先天因素提供的线索,人出生后能够学会利用附加的线索,对已有线索进行更精确的解释。但刺激的输入往往有模棱两可的多重解释,无论知觉系统在组织过程中到底偏好哪一个,在选择之后只发生一种知觉,即“知觉不允许混乱”。
图三如图三所示,四组弧形之间并没有实在的图形,但知觉会倾向于主动在四个弧形之间构造一个正方形,即“虚形”出来。同样,观看只有线条构架的立方体(图二C)时,虽然这个立方体四周并没有墙壁,但在知觉中,它四周似乎包裹着明晰可辨的面。这是知觉在解决自我矛盾现象时达到某种妥协的结果。人们知道(wissen)它们是不存在的,但看上去(sehen)却存在;这便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笛卡尔面对的“可解证性”几何学深度理论是非视觉学说的质疑。格式塔学派认为,在说明深度视觉之前不能混淆“知识性事实”和“知觉事实”。线条画之所以能够成功再现物体得益于知觉的“完型”(Gestalt)效果④。在知觉完型作用下,对象所处的环境一直都被当做一个整体,从而在物体的内部和外部、正面和反面互相暗示、相互统一。这种统一性使意识不再局限于物体表面,而是深入到对象内部和不可见的“潜在空间”。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论证,感知深度——特别是平面深度带来的错觉——与其说是某些可确定的刺激线索在“图-底”关系的系统中直接作用的结果,不如说是心理构造的直接结果。物体投射的阴影、视大小的变化以及重叠的数目等现象暗示心理,这是一个由许多物体居于其中或其上的面,心理于是就构造这样一个能够包罗这些物体的平面,而其他的透视线索和方法则加强了这种构造,使之更加生动有力。因而,包括格式塔心理学在内的深度理论,特别是传统的物理主义和内省式心理学,始终在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认识框架之内寻求一种“非具身性”(disembodiment)[13](124-140)倾向的融贯性,以“刺激-反应”模式来解读空间和知觉问题。梅洛-庞蒂认为,虽然格式塔理论提醒我们从整体和组织关系角度把握知觉,并作出了知觉事实(知觉主体)和知识性事实(思维主体)的区分,但其所依赖的实在论和反省的因果思维,要么把心理活动看做物理实在世界的一个区域,要么极力将思维和意识还原为一种生产性原因,[14](16)终究无法逃脱二元论的窠臼,因而并未给深度视觉理论的解读带来全新的面貌。
三、梅洛-庞蒂的深度视觉理论
(一)知觉的首要性与整体性及身体的实践综合
梅洛-庞蒂借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和“背景”概念以及知觉的整体性观念,并吸收了康德在论证空间的先验特征时所用的方法。他认为,我们首先不能将知觉分割成视觉和触觉等各个部分,或者看做各种感觉的简单拼合,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知觉的整体总是先于部分;这个整体不是观念的整体,被知觉发现的意义世界也不属于概念范畴。如若知觉带来的意义属于概念范畴,那么我们必须要在感性知觉和概念之间设置一个能够联结彼此的中介,以及中介的中介,由此便会陷入循环往复。[15](10-11)
知觉的整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主体将知觉对象及其周边背景视为整体,并赋予所知觉的感性材料以意义的“综合”行为。在知觉内部,每一个心理活动都彰显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在这个“作为意识对象的结构”[14](219)⑤中各部分的内容都根据它们在特定时刻带给整体的意义显现,但并不脱离整体的框架。正如格式塔心理学所秉持的,作为知觉对象的空间结构形式不是一种物理实在或物理世界的一个事物,而应当被定义为一个被知觉的整体;同样,知觉对象所寓居的空间也不是欧几里得和笛卡尔式的几何空间。被感知的对象随着场所和情境的变化,属性也在改变,并能够不断延伸到一个可以被称作“完型空间”的抽象空间中。理智主义,包括康德式的“智性综合”依赖逻辑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来把握物体,但物体却是触手可及的“真实”。在视知觉过程中,视野之内的部分以在场的方式表象出来,而对于不在场和在场却“不可见”[16](35-40)⑥的部分来说,物体显现为一系列并不完全确定的视角,每个视角与它的整体关联,又都不是物体的全部;而为了使物体以特定方式显现其意义,我们只能借由身体的运动[17]⑦变化来实现空间的完型。因此,这个过程不可能是线性因果链条中的“非具身性”的智性综合,而只能是一种“具身性的”(embodiment)“实践”综合行为。[18](267-272)
(二)“身体-主体”的确立
这意味着在对空间的知觉中,主动的实践综合主体除了能够在物体中确定对象的呈现角度和透视变形的已知状态之外,还需要超越这种已知状态进行整体性和情境性的把握。这样的主体承担者不可能是“非具身性”的“我思”,而只能是作为“知觉场”和“实践场”的身体[19](173-174)。身体发出主体所及范围之内的实践动作,并将周围熟知的物体划入到其领域之内。和诸知觉要素对应,整个身体也不是并列在空间中的器官的集聚,主体在一种不可分割当中拥有身体。经由“身体图式”(body image/schema)[18](113,163)的筹划[20](275-286),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能被假定或者将它的意义用反思因果思维抽象出来,因为抽象出的纯粹概念性的身体无法进行空间方位的确定,只是对空间方位确定的解释,在知觉理论中没有具体的意义。与“实在空间”和外在对象相互交织(interweave)的“身体-主体”空间,非但不属于“实在空间”中的一个部分,恰恰相反,身体与空间相互构造,没有身体也就没有空间。[5](34-36)⑧
梅洛-庞蒂的空间观通过强调身体知觉对空间的交互性、原初性和直接把握,试图克服思辨的空间哲学耽于从外部物体关系,抑或对空间的感觉层面处理深度问题时塑造的一种的位置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position)窠臼,而将身体的空间性理解为情境中的、“处境”(situation)的空间性[18](115)。正如汤姆·洛克摩尔所言,知觉的现象学仅仅通过描述而履行“面相事物本身”的职责,在“强调把知觉经验当做知识终极来源的过程中,瓦解了康德在感觉、知觉与经验之间的细致区分。”[17](30)
承担这一救赎功能的“身体-主体”概念,在根基上导源于梅洛-庞蒂的存在论立场。由于笛卡尔主义的传统,我们习惯借助因果思维的反省态度把身体定义为部分之和,将身体的普遍概念纯化;而将意识定义为向其本身呈现的存在,同样净化了意识的普遍概念。“存在”依此则被赋予两种仅存的意义:人,作为物体而存在;或作为意识而存在。但身体的体验恰揭示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方式。由于其动态的实践性综合取向,身体始终处于一种“是其所是,又有别于其所是”的暧昧、含混的统一性中。如果在康德意义上,身体可以作为一种使对象客观化的条件或中介,但它并非一般对象,它为每一种行为得以实施提供了一种类型的空间,其意义是在先的,一旦试图将身体空间的意义抽象化,就只能发掘出纯粹概念性和逻辑意义上的空间。因此,对空间的解读也必须上升到存在论层面,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存在方式的展开。此时,空间性和存在在梅洛-庞蒂哲学中变成了一个问题。
(三)“动机-情境-决定”深度理论
基于这种存在论的立场,梅洛-庞蒂在讨论其称为“最具存在特征的空间维度”——深度过程中,秉持胡塞尔树立的“现象学态度”,通过Stratton和Wertheimer[18](284-287,289-290)的经典实验,检视了在把握空间的非常态特例中,唯理论、经验论和传统心理学的反省式因果分析态度的不足之处,从而确立了他的“动机-情境-决定”(Motivation-Situation-Decision)深度视觉理论。
rattond的实验大致过程是:基于视网膜映像倒置的特点,被试佩戴特殊镜片使视网膜映像变正,起初被试看到的整个景象会变得颠倒和不真实;第二天开始被试逐渐感觉到景象开始变正,但身体是颠倒的;在随后持续八天的第二阶段实验中,第二天景象不再颠倒而是感觉身体处在不正常的位置;从三天到第七天,身体逐渐恢复正常,特别是被试如果在活动中,则身体会重新占据正常位置。实验结束被试摘下眼镜后,除了运动反应颠倒(即要求被试伸出右手,却给出右手),物体看起来并不是颠倒的。Wertheimer的实验大致内容与Stratton的设计相似,使被试通过镜子观看所处的房间,镜中所见房间与垂直方向倾斜45°,整个房间和走动的人看起来都是倾斜的,沿门框掉落的纸板也是倾斜的,但几分钟后,在被试眼中墙壁和房间中走动的人以及坠落的纸板都变回垂直了。
如前所述,贝克莱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倾向于将深度体验归结为习惯的结果,深度空间始终是外部世界的关系内容,等同于从侧面观看的宽度,而知觉只起到被动体验的作用。然而诉诸于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经验主义,无法解释Stratton和Wertheimer实验中为何身体“有能力”迅速地将倒置和倾斜的视像摆正的问题。与此相对,理智主义者声称深度经验由主体能力构造,并在内部先验地规定了空间关系的具体形式。但正因为这种主体内部的非具身性筹划,使得“视像倒置”实验在理智主义的视野中毫无意义,因为正如本文图一指示,对“思维主体”来说,视像的方位和角度对主体如何运用几何解证思维认知空间理应没有任何影响,显然,实验过程中身体和视知觉的往复变化和适应已将这种说法直接否证。格式塔心理学派虽然通过“图-底”原理的整体性动态原则超越了传统深度观,但诉诸“组织之力”在思维内部的角逐实际上将对象的视大小、重叠等深度线索与知觉构造还原为“材料”与“形式”的对立二分,并把深度体验的线索理解为产生深度的原因,最终放弃了直接性生存体验(live experience)回归到内省分析的因果思维。
梅洛-庞蒂认为,Stratton和Wertheimer的实验确证了身体和世界之间一种动态的、有机的关联,在此关联之下,深度既不属于物与物的关系,也不是思维主体的非具身性构造。为了纠偏格式塔心理学将深度线索混淆为深度原因的主张,梅洛-庞蒂引入了“动机”(motivation)[18](301)概念,试图通过非因果性序列的“动机-情境-决定”理论来重释深度主导的现象领域诸种概念关系。在他看来,行为或现象的驱动不能被简单还原为某种独立的第三人称因果关系,也不是意识构造出的理性决定。它们的动因根植于以过去、身体和世界相互交织并作为推进和重塑各种可能性的关系背景之中。[21](132-133)形成动机的事实要素作为溯源的依据之一,不是因为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引发现象或行为,而是为现象的呈现提供担保。当汽车渐行渐远,身体与车之间的距离增大,对这段距离的把握表面上看是通过物体所呈现的大小变化表现出来的。现代心理学聚焦于诸如此类的视大小、目光会聚、对象的重叠、双目视差、阴影和透视法的运用等深度线索,但这些线索不足以产生深度。它们在深度体验中出现,就像“动机”出现在“决定”中。梅洛-庞蒂举例说,受邀参加一个葬礼时,举行仪式和需要安慰的家属这样的事实线索为参加葬礼提供了一个动机,而“去参加”的这个“决定”才使得这种行为的意义得以生效。换句话说,事实作为动机产生的理由,是意义起作用的前件(antecedent)。整个情境包含着动机和决定这两个因素,前者可称为事实的情境(the situation as a fact);而后者是允诺的情境(the situation undertaken)。在深度视觉中,由于“知觉不允许混乱”(图三及相关论述),当身体通过运动捕捉作为情境出现的深度线索时,这些线索已经将 “含混的”(implicit)意义(动机)给予了身体,而视知觉的目光(决定)才使得这些意义清晰化(explicit),构成深度表现出来。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依赖于刻意地“忽略含混性”,而含混性恰恰是生活世界经验的来源和核心基础。事物的显现在“图-底”关系和身体与含混世界的互动关系背景下角力、争执,通过彼此的差异性而获得一种动态身份;一个事物是可见的,只有在其他事物不可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22](336-351)深度于是成为事物保持自身并与他物区别开的手段。
梅洛-庞蒂以其知觉现象学的深度理论扬弃了笛卡尔以来确立的沉思式因果思维,将深度视觉归结为前反省(pre-reflective)式综合行为的结果,而且他认为这种实践综合所产生的并不单单是空间关系,也包括时间关系。他认为,传统哲学对“时间性”(temporality)和“空间性”(spatiality)的区分太过严格,深度知觉所提供的“呈现场”(field of presence)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扩展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即“此处和彼处”的维度以及“过去-当下-未来”的维度。
空间性必须要通过时间性要素才能得到阐明。[18](309)具体来说,深度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将身体“放置”在空间“之中”,而不是预设一种主体与外部世界面对面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时间性则担保了以身体运动为基础的深度知觉的可能性。如在图二C所示的立方体呈现过程中,除了要求有感知深度的“动机-情境-决定”和身体导向等要素之外,目光还必须沿着立方体的侧棱向后运动,在这个时间流动中,静态的观看只能在一个瞬间捕获到某个点,而只有时间性的、动态的观看才能确保从点到面再到立方体,从一维到二维、三维实现的可能。因而,深度的形成要求一种知觉和时空的同时性,这种同时性正包含在知觉意义本身中;对空间的定义并不外在于时间,被感知的物体和我的知觉在时间和空间之内同时进行。[23](139-157)
(四)以深度空间为契机建构肉身本体论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梅洛-庞蒂之所以将“深度”称为“最具存在特征的维度”,甚至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因为不仅经由深度视觉,杂乱无章的世界向我们显现出明确清晰的意义,并且,时间性视阈的引入将深度的现象学功能提升到了更始源性和本体的层次上。将深度理解为时空性(spatiotemporal)维度的意义在于,有距离地捕捉到某物,就意味着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同时性(simultaneity),以及空间的共存性(coexistence)的双重维度中把握到它。[24](23-50)因而在后期著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梅洛-庞蒂通过再度聚焦于深度,试图构造一种本体论学说,他说:“没有深度就没有一个世界或存在,就只能有一个区别性的移动带……深度使事物有一个肉身(flesh),也就是说它使事物抵制我对各种障碍的探究,它是一种抵抗,但这种抵抗恰恰是事物的实在、事物的开放、事物的当下现实。……在被我的纯粹观看当作现在之持留的东西中,深度就是源始……”[25](277-278)
由此可见,在《知觉现象学》中,深度理论作为统筹身体与世界关系矩阵中的交汇性轴心概念是经由传统空间哲学的演进脉络得出的;而到了其思想后期,特别是《眼与心》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梅洛-庞蒂则用存在论色彩浓厚的原创性概念“肉身”代替了“深度”作为其未竟本体论的内核。就此而论,“深度-肉身”概念作为理论契机承担的哲学使命和意义远不止重塑空间哲学和纠偏心物二元论。身体-主体的确立将传统哲学的先验自我(transcendental ego)扭转为肉身主体性(incarnate subjectivity)并开启了一个包罗情绪、梦、神秘和癫狂等非理性、非常态世界以及反省式世界的“人的空间”(human space);对这一空间的现象学描述颠覆了传统哲学对形式与内容,清晰性和含混性,实在与表象的区分,进而为哲学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带来了新的变革。[26](79-87)
注释:
①“天生性盲者忽然获得视力能否用双眼识别复明前依靠触觉顺利判别的几何物体”的假设被称为“莫利纽克斯问题”,来源于爱尔兰哲学家威廉·莫利纽克斯(William Molyneux)1692年3月2日给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书信,对这个问题源流的讨论详见:John W. Davis的The Molyneux Problem一文。否定性结论随后分别在1728和1932年得到英国医生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转引自Sender L. Gilman的The Figure of the Black in German Aesthetic Theory一文)和研究者玛利乌斯·冯·森丹(Marius von Senden)的证实(详见:Marius von Senden的Space and Sight: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and Shape in the Congenitally Blind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一书)。
②“恒常性”(constancy)作为复杂的心理学和哲学命题涉及到知识的确定性等基本问题,其中“视大小恒常性”是现代视觉学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即如何确定渐行渐远的物体,虽然视像不断变小,但仍然是同一物体。格式塔心理学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第六章的讨论。
③“我们心物情形中有两种力,一种存在于分布本身的过程中,而且倾向于在这种分布上印刻最简单的可能形状;还有一种力存在于这种分布和刺激的模式之间,它们限制朝着简单化方向发展的应力。我们把后面这种力称为组织的外力(external forces of organization),而把前面的这种力称为组织的内力(internal forces of organization)。”
④“完型(补足)效果”可以通过“隧道效应”说明:当知觉判断一列经过隧道、车身被隧道截断的火车时,会倾向于将其视作一列完整的火车,而不是两个火车的片段。隧道效应面对的质疑是:究竟这种完型效果是长期经验引发的,还是知觉固有的。在社会生活中,这一倾向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简化和补足倾向会影响我们对固有陈规和习俗的准确判断。
⑤“……而结构则是意识的一种对象。只是为了思考被知觉的世界,它们才有其意义。”
⑥深度视觉仰赖于对象“可见的”和“不可见”相互依存的辩证存在方式,当我们可以从全部视角,如上帝一般观看世界,深度也就不见了。
⑦刘胜利在“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关于一种原初空间性的考古学的初步反思对身体运动与空间之间的构造关系”一文中指出 “在具体运动的每一瞬间,身体将各种结构维度及运动的可能性赋予空间,并将运动情境的空间关系纳入自身以重新进行身体的综合;空间结构的起源及其瞬时重构则对应于世界对身体运动所作出的回应。身体与世界的对话过程既是双方的交互构造过程,同时也是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过程。”
⑧作为现象学意义上身体图式概念吸收了格式塔心理学中对整体综合性的强调,克服了“我思”的唯我论倾向,梅洛-庞蒂将其理解为身体性经验的概括以及给予一种内在表达和身体动作以意义的含混概念。对这个概念的一些澄清参见David Morris的The Fold and The Body Schema in Merleay-Ponty and Dynamic Systems Theor一文,以及作者的The Sense of Space,一书第34-36页.
参考文献:
[1]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1, 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and Dugald Murdo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52-176.
[2] John W. Davis, The Molyneux Probl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1, No. 3(Jul.-Sep., 1960):392-408.
[3] Marius von Senden, Space and Sight: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and Shape in the Congenitally Blind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Tans. By Peter Heath.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60.
[4] Sender L. Gilman,The Figure of the Black in German Aesthetic Theor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8, No. (Summer, 1975):373-391.
[5] David Morris, The Sense of Spa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6-9.
[6] George Berkeley, An Essay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Vis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1732.
[7]贝克莱.视觉新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xxii-xxiii.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7-52.
[9]康浦·斯密.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义[M], 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37-199.
[10]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李维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艾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80.
[12]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
[13]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24-140.
[14]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
[15]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行及其哲学结论[M],王东亮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10-11.
[16]Sue L. Cataldi, Emotion, Depth, and Flesh: A Study of Sensitive Space Reflections on 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Embodiment, SUNG Press, 1993:35-40.
[17]刘胜利. 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关于一种原初空间性的考古学的初步反思对身体运动与空间之间的构造关系[A];汤姆·洛克摩尔. 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性以及知识的历史限度[A].理解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在当代[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9,30.
[18]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Con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267-272.
[19] Stephen Priest: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the body-subject, Blackwell Science Ltd 2000 Nursing Philosophy, (1):173-174.
[20] David Morris, The Fold and The Body Schema in Merleay-Ponty and Dynamic Systems Theory, Chiasmi International: Trilingual Studies Concerning Merleau-Ponty’s Thought 1 (1999):275-286.
[21] Donald A. Landes, Merleau-Ponty Dictionary,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132-133.
[22] Anthony J. Steinbock, Merleau-Ponty’s Concept of Depth, Philosophy Today, 1987:31:336-351.
[23] George J. Marshall, A Guide to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08:139-157.
[24] Françoise Dastur, World, Flesh, Vision, Chiasms: Merleay-Ponty’s Notion of Flesh, edited by Fred Evans and Leonard Lawlo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23-50.
[25] 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277-278.
[26] Monika M. Langer,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acmillan Press, 1989:7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