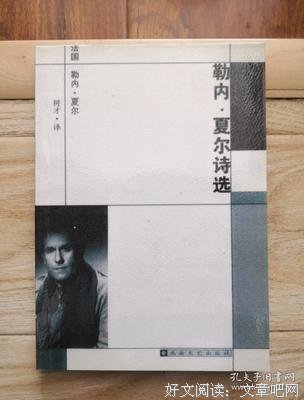
《勒内·夏尔诗选》是一本由[法] 勒内·夏尔著作,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元,页数:1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勒内·夏尔诗选》精选点评:
●和加缪的语感颇有共通之处
●你在本质上始终是诗人,始终在爱的顶点,始终渴望真理和正义。这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你在意识里无法始终是这种恶。
●树才念叨译诗有点热情过剩,不过想想他对博纳富瓦说中国现代诗时的期望,又觉得合乎情理。“你出走得好,兰波!”真是振聋发聩啊,Rene Char。《夜的升起》:我烘暖的花朵,我让它的花瓣成双,我使它的花冠黯然。/时间撕碎并修剪。一道闪光远去:我们的刀。/春天逮住你,冬天释放你,爱的蹦跳的国度。/星星把躲在它身上的胡蜂的螫针还给了我。/守护,脸侧着,你在山巅上浇灌绵羊的心。《拉开的有裂缝的百合窗》也很美。“群狗冲着天使狂吠。我们也是。”“我们折射什么?我们没有翅膀。”《依靠一间枯瘦的房屋》是变形的奇特。最喜欢的《刺》:——为什么如此热烈,青春的脸庞?/——我走了,夏天消失。/我的不安粗线条地跟我说,/比灰色的水和枝条要好。/——跪在地上,天使驾临;/在你的翅翼上我的鞭子呼呼响。
●阴翳的闪电
●打四星是因为翻译实在太差了,作者本来就写得艰涩,这么译就更生疏了
●翻译硬伤较多,有些错误近乎不可饶恕,例如将我只与火炬起舞译成我只与乌龟跳舞,将凝血染上朝霞的淡红译做卵石染上朝霞的淡红,将烛台译成日历,等等,彻底摧毁中文读者正确理解的可能,并且在译文中存在对原文的删减。但作为第一本对夏尔广泛译介的诗集,依然有历史意义。
●从福柯开始关注此人。而今终于找到足本,却未找到当初那句梦之至深处
●不懂翻译。对诗歌节奏的把握确实惊人。
●好诗。
●“一粒灰尘落在忙于写诗的手上,把诗篇和手,双双击倒。”
《勒内·夏尔诗选》读后感(一):我们将不再让大地痛苦
即使是越过了翻译的背后,即使是通过文化背景的消减
《为什么前去》还是一首保留了夏尔超想象以及赤裸生命力的呈现
《为什么前去》
啊!会合,我们的翅膀并肩飞翔
蓝天是忠于它们的。
但是什么东西仍在我们之上闪耀?
我们的胆量,那濒死的反光
一旦我们穿越了它
我们将不再让大地痛苦
我们彼此凝视
《勒内·夏尔诗选》读后感(二):愤怒与神秘
——欢喜陀完成于2004年5月,那是我第一次写诗歌评论
勒内夏尔(法国,1907—1988)
我是在Barre Phillips粗糙而发出金属磨擦般贝司的引导下进入到勒内夏尔的超现实世界的。音乐所营造出的神秘色彩是阴暗的,不论是从远处传来的Paul Bley断续的钢琴,还是忽然在嘶鸣贝司声中将空间骤然破坏的Evan Parker低沉的萨克斯。神秘,因为断裂的愤怒而疯狂,恐惧或是屈服,迷失或是清醒,紧张或是惊悚,抽象或是迷离。一支溺水的手伸出水面,胡乱的挥舞,与音乐中沉重的喘息交融在一齐,被突兀的贝司猛的割断:
《四种迷人的动物》
4云雀
天空绝对的炭,白昼最初的激情
它镶嵌在清晨,歌唱起伏的大地
报时的钟声,它呼唤主人,它途中的自由
太迷人了!人们赞叹着,射杀它
勒内夏尔的象征的形式是简约的,但支离于其后的精神空间却是极其晦涩的,至今仍有大多数作品是未被认知与理解的。质朴偏离的后现代哲学在异奇的暗喻下变得疯狂而隐藏了揭示。将自己的内心包裹起来的诗人往往有着超越常人不堪忍受的痛苦经历。
理论是法国人的专长,但实施者却往往是美国人,此时耳中一阵慌乱的贝司将我的心陡然从胸腔掀至喉咙,自然而然地被眼前相互搏杀的人群所震撼,像被一种残忍之美所放射出来的迷咒所催眠。迷乱抽象的暗喻隐射着诗人本身与人类社会最不愿启及的原罪:
《四种迷人的动物》
1公牛
你死时,夜不再降临
被嘶喊的黑暗所包围
太阳在两个相似的尖点上
爱的猛兽,剑中真理
互相刺杀的一对在众人中独一无二
与博纳富瓦睿智而理性的思索不同,勒内夏尔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是愤怒与封闭的,他渴望保持一种清醒与昭然的旁观者角色,却无意识地进入到了混沌与迷失的在场状态。争吵,与自己文字背后的灵魂口舌,莫名的恐惧在生活的盲区和混乱的情欲之间的徘徊让这种自罚的赎罪感超越了正常的思考模式而支配了文字。晦涩,勒内夏尔的晦涩是一种形式透彻与思想混乱的矛盾,这在他所有情感直白、但不经意遗忘在诗句中令人费解的象征得到了某种潜意识的暗示:你泡在其中的黑暗受你的太阳般上升的淫荡所支配。人生是悖谬性存在的。拒绝,因为害怕拒绝而主动拒绝的内心躁动被诗人的文字所影射:“我不是单独的,因为我是被抛弃的。我单独,因为我是单独的,园圃隔墙间的杏仁核。”这不是一种建立在自信与独立基础上的骄傲,而是致极自卑的反面:拒绝,因为被烙上了卑微的印记变得无助与晕眩。得不到寄托的心灵永远只可能离散于个体的灵魂愈来愈空……
在选择拒绝之前,为什么不先尝试着接受呢……
《空间中的房间》
这就是树枝的歌,当暴雨逼近——风用雨,用重返的太阳,给自己搽粉——我浅浅的醒来,我飞升着融化;我收获未成熟的天空。
靠着你,躺着,我移动你的自由。我是喷吐花朵的一坨泥土。
难道劈开的喉咙比你更绚丽?要求即死。
你叹息的翅膀把一根绒毛放在叶片上。我爱的箭矢闭合你的果子,渴饮它。
我在你脸庞的恩惠中,我的黑暗用欢乐盖住它。
你的喊叫多么美,它把你的寂静给了我!
《勒内·夏尔诗选》读后感(三):转帖:花神的梯子(作者:蓝蓝)
一
在你枝条的风中,你能保住那些根本的朋友。——勒内·夏尔
赵君晓阳,山西人士,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忠直仗义,博览群书,有极好的文学判断力。
2001年,山西诗人潞潞、姚江平邀我参加“太行金秋诗会”,自太原到黎城颠簸的路上,身后一直有人不断愤世嫉俗地评判当下丑陋的世风和读物的庸俗,颇合我心。当我扭头看他时,却只见到一顶棒球帽遮了脸,此君已开始打瞌睡。
这位便是赵晓阳。
潞潞悄悄告诉我,赵晓阳是赵树理的亲外孙,作为一个有眼光的编辑,他编辑出版过很多好书。潞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2000年北岳文艺出过一套“黑皮诗丛”,里面收入了我喜欢的诗人多多、潞潞、宋琳等人的诗集。这套诗丛的责任编辑就是赵晓阳。
这次诗会,诗人、翻译家树才也来了。赵晓阳当时就和他谈定要出版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博纳夫瓦、勒韦尔第这三人的诗集,另外拙作《蓝蓝的童话》也被他约了去。
赵晓阳喜酒,三杯下肚,一浇心头块垒,郁积在胸的苦闷便滔滔不绝地。其率真和单纯,闻者无不动容。除了对一位有判断力的编辑的尊敬外,我对他是赵树理的外孙的身份也有些好奇。他却说得不多,只是说赵树理当年被揪出去批斗,抬回家来已经被打得几乎奄奄一息,只能托人找车拉到医院救治。
“我姥爷……唉!”
他摇头叹息,那种说不出的痛苦,只能令我沉默无言。我曾在太原街头见到过赵树理先生的一尊站身塑像,问起赵晓阳,他赶紧摆摆手:“别提啦!那怎么会是赵树理?整个一夹着账本的大队会计。”
赵晓阳的父亲因为受赵树理牵连,为躲灾祸而出国。赵树理平反昭雪后,赵晓阳到俄罗斯探望多年音信皆无的父亲,回国后常挂在嘴边的却是一桩趣事:一日他喝得高了,走在大街上,对面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俄罗斯陌生的哥儿们,看到他就大张双臂,亲密地拥抱在一起,举起手里的酒瓶子请他畅饮。“多好的同志啊!” 赵晓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就是这位性情中人,在那次山西诗会后一年,给读者送来了一架勒内·夏尔的“花神的梯子”,使我不仅拥有了三本一模一样的《勒内·夏尔诗选》,还能借助这架诗歌之梯,望词语和创造的辽远之美。
二
说吧,是什么,让我们喷吐出花束?——勒内·夏尔
“你喜欢谁的诗?最近在读谁的诗?”“勒内•夏尔。佩索阿……”“哦,夏尔!写得真是太好了!”
一头白发、狮子一般的诗人多多听我说到勒内·夏尔时,眼睛登时亮了,“是北岳文艺出的那本诗集吧?”
我点头。身边参加2005年“三月三诗会”的诗人们也加入进来,谈论起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诗人。
勒内·夏尔,1907年出生在法国南方沃克吕兹省索尔格河畔,在乡间长大。他有着192公分的高大身材,是个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1927年,他在法国的炮兵部队服完兵役。23岁时接触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初期的作品便赢得了布勒东和艾吕雅的赞赏和器重,并与其出版了诗歌合集《施工缓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法国被德军占领,夏尔英勇参战,加入抵抗运动,并成为下阿尔卑斯地区的游击队领袖。在当地,很多人不知道他就是诗人夏尔,但是,很多人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尉”,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法国光复后,夏尔继续诗歌创作,经历过苦难和死亡威胁后的诗人,虽然他后来脱离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然而其创作手法依旧是超现实主义式的,他对现实的关注也愈加强烈。他的诗歌奇崛神秘,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复杂难解,但仍然影响了包括福科在内的众多大家,被誉为法国最好的隐秘主义诗歌大师。
《勒内·夏尔诗选》的译者树才曾对我说:“‘我歌唱新生儿脸上的热烈’,这样的句子惟有夏尔才能写出来。”树才翻译夏尔的诗作极其认真,在这本诗集的附录后记中他写道:“我译得吃力,缓慢,……正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我的译诗,在为‘可能’而战。”
这本诗集连同树才翻译的另外两本博纳夫瓦、勒韦尔第诗选的封面设计者,恰好也是拙作《蓝蓝的童话》的设计者。赵晓阳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每道环节事必亲躬,和我多次就封面、纸张、版式、字号等具体问题电话来往,让我也了解到树才翻译的三本诗集的进展。由此,我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诗集印出上市的时间,并很快在郑州的书店买到了《勒内·夏尔诗选》。那是2002年秋天,几个月后,便有了和多多等诗人在太湖边谈论夏尔诗歌的机缘。
有一次我偶尔在网上读到何家炜翻译的夏尔的一首诗《宣告其名》,在树才的译文中翻译为《宣告他的名字》。有一个挺大的异译是,何译:“那时我十岁,索尔格河将我镶嵌。”而树才的译文是:“我十岁,索尔格插入我。”
“镶嵌”与“插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我不懂法语,心存疑惑,一直想找机会向树才请教,但一见面却又总是忘记。
三
棕色蜜蜂,在这醒来的薰衣草中,你们在寻找谁?——勒内·夏尔
拿到《勒内·夏尔诗选》后的一段日子,我几乎整日沉湎于诗集中那些令人着迷的诗句。以往的阅读习惯开始接受着又一轮的挑战。我记得在翻过整本诗集后的某一天,当我顺手再次翻开书的时候,一行字跳进眼睛:“倾翻的船上没有恶毒的影子。”我记得我读过这句诗。但为什么我又一次读到它的时候,醍醐灌顶般就打了一个寒颤?是的,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任何对于人的诅咒都会为死亡来临时对生命的怜悯所取代。这样的阅读令我心仪不已,这是因为它证实了肤浅而匆忙的阅读几乎完全无效,而夏尔的诗带给了我再次认识并开拓自己理解力的机会。
没过多久,赵晓阳把一整套崭新的三本译诗集和《陈独秀传》寄到了我手中,于是我有了第二本《勒内·夏尔》诗选。我打电话向他道谢,但同时表示,像这样的诗集再多一套也不算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去读多少次。
勒内·夏尔有一首诗《红色的饥饿》,我印象极深。我记不清在这本诗集出版前是不是已经读到过这首诗。因为树才当年不断地在翻译法国诗人的作品,我们通信时常会接到他打印在纸上的一些翻译诗歌,诸如勒韦尔第的作品,雅姆的作品,我都是很早就从树才的惠寄中读到了。因为市场的原因,一般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诗集,他们忘了那些杰出的诗篇不仅仅像夏尔所说“诗,从身上盗走了我的死”,。
回到夏尔的诗——《红色的饥饿》,是写给一个死去的女人的诗,作者营造了一种她仍然活在人间的氛围—像往常一样,在餐桌旁坐下,和诗人一起吃饭,或者被她爱的男人紧紧搂在怀中。然而,“你疯了”,诗人的疑问和肯定都是针对自己的,他知道借用诗歌的魔力能让爱人复活,活在自己的膝盖上和双臂间,或在视力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你太美了,没有人意识到你会死。”夏尔这句诗像迎面撞过来的一口大钟,让读者清醒,并为美的殁亡而痛心疾首。诗人接下来写道:“确定无疑的赤裸,/乳房在心脏旁腐烂”,令人毛骨悚然的具体的描写推进着悲哀绝望的前行。然而,死去的女人并不孤独,诗人深情地说:“过一会儿,就是夜。你和我一起上路。”因为这是一个跨越了生死的“重合的世界”,“一个男人,他曾把你紧搂在怀里。/坐下来,吃饭。”
这是一首让人潸然泪下的诗。一首你读到以后再也不会忘记的诗。对于一个合格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诗篇就像芬芳的薰衣草,吸引着我们蜜蜂般寻找真情的翅膀前往。
四
为什么众人中最活生生的生者,难道你只是生者中花朵的黑暗?——勒内·夏尔
法国老牌的伽里马出版社有一个在全球威名赫赫的“七星文库”,它和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文库一同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典文学系列丛书。能够入选七星文库的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至名归的经典大师。截至2009年,仅有198位作家成为该文库的入选者。对于很多诗人作家来说,被七星文库看中,意味着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和莫大的荣誉。勒内·夏尔是唯一一个在世入选文库的诗人。他于1988年在巴黎去世,20年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百岁时由七星文库推出了他的七本文集,成为了另一个入选七星文库的“七星活人”。
2003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和几位诗友见面时,诗人树才又送了我由他翻译的《勒内·夏尔诗选》。至此,我的《勒内·夏尔诗选》达到了三本。我并未推辞,而是快乐地感谢并接受—有谁能够不要自己喜欢的书呢?哪怕你已经有了。
我从不隐瞒对夏尔诗歌的喜爱,正如我也非常喜欢另一个法国诗人—极为朴素晓畅的雅姆。两位诗人在表达形式上完全不同:夏尔的诗,用树才的话来说是 “陡坡”,有险峻有意外,也有高崖之下山谷的幽深;而雅姆则宁静澄明,质朴如憨厚的农夫。我渐渐地发现,这两位风格迥异的诗人却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内在的一致。夏尔的诗句在看似抽象中处处布满具象,而雅姆邻家老叔般低声的喃喃诉说却也似一把直抵心胸的精神刀子。两位诗人都在探索人类的痛苦、希望和命运,他们关注的都是人的本质和心灵中最隐秘的那些颤动。虽然他们挥舞的是不同样式的镰刀,但收割的却是完全一样的沉甸甸的精神稻谷。
去年仲夏初到的一天,很久没有联系的赵晓阳忽然打来电话,问:“你忙吗?”我说我不忙。他说:“我今天给很多人打了电话,人人都在忙。”我说我不忙,然后就沉默,听着他话筒里的叹息。我知道,在一些人的记忆里,会有某些个难以遗忘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像毒针一样深深扎进人的大脑中,时常来刺痛你。从他几乎要哽咽的声音里,我听到的是痛苦,也是一个人高贵的性情。感谢赵晓阳,给我们出版了这么多好诗集;感谢树才,翻译了这么好的诗句。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动人的诗歌绝不是点缀“浪漫”生活的花边,它们如沉重的锤头,依旧在不停锻打着诗歌这架引领我们上升的梯子,把我们送往更接近正直高尚的精神领空。
《勒内·夏尔诗选》读后感(四):转帖:花神的梯子(作者:蓝蓝)
一
在你枝条的风中,你能保住那些根本的朋友。——勒内·夏尔
赵君晓阳,山西人士,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忠直仗义,博览群书,有极好的文学判断力。
2001年,山西诗人潞潞、姚江平邀我参加“太行金秋诗会”,自太原到黎城颠簸的路上,身后一直有人不断愤世嫉俗地评判当下丑陋的世风和读物的庸俗,颇合我心。当我扭头看他时,却只见到一顶棒球帽遮了脸,此君已开始打瞌睡。
这位便是赵晓阳。
潞潞悄悄告诉我,赵晓阳是赵树理的亲外孙,作为一个有眼光的编辑,他编辑出版过很多好书。潞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2000年北岳文艺出过一套“黑皮诗丛”,里面收入了我喜欢的诗人多多、潞潞、宋琳等人的诗集。这套诗丛的责任编辑就是赵晓阳。
这次诗会,诗人、翻译家树才也来了。赵晓阳当时就和他谈定要出版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博纳夫瓦、勒韦尔第这三人的诗集,另外拙作《蓝蓝的童话》也被他约了去。
赵晓阳喜酒,三杯下肚,一浇心头块垒,郁积在胸的苦闷便滔滔不绝地。其率真和单纯,闻者无不动容。除了对一位有判断力的编辑的尊敬外,我对他是赵树理的外孙的身份也有些好奇。他却说得不多,只是说赵树理当年被揪出去批斗,抬回家来已经被打得几乎奄奄一息,只能托人找车拉到医院救治。
“我姥爷……唉!”
他摇头叹息,那种说不出的痛苦,只能令我沉默无言。我曾在太原街头见到过赵树理先生的一尊站身塑像,问起赵晓阳,他赶紧摆摆手:“别提啦!那怎么会是赵树理?整个一夹着账本的大队会计。”
赵晓阳的父亲因为受赵树理牵连,为躲灾祸而出国。赵树理平反昭雪后,赵晓阳到俄罗斯探望多年音信皆无的父亲,回国后常挂在嘴边的却是一桩趣事:一日他喝得高了,走在大街上,对面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俄罗斯陌生的哥儿们,看到他就大张双臂,亲密地拥抱在一起,举起手里的酒瓶子请他畅饮。“多好的同志啊!” 赵晓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就是这位性情中人,在那次山西诗会后一年,给读者送来了一架勒内·夏尔的“花神的梯子”,使我不仅拥有了三本一模一样的《勒内·夏尔诗选》,还能借助这架诗歌之梯,望词语和创造的辽远之美。
二
说吧,是什么,让我们喷吐出花束?——勒内·夏尔
“你喜欢谁的诗?最近在读谁的诗?”“勒内•夏尔。佩索阿……”“哦,夏尔!写得真是太好了!”
一头白发、狮子一般的诗人多多听我说到勒内·夏尔时,眼睛登时亮了,“是北岳文艺出的那本诗集吧?”
我点头。身边参加2005年“三月三诗会”的诗人们也加入进来,谈论起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诗人。
勒内·夏尔,1907年出生在法国南方沃克吕兹省索尔格河畔,在乡间长大。他有着192公分的高大身材,是个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1927年,他在法国的炮兵部队服完兵役。23岁时接触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初期的作品便赢得了布勒东和艾吕雅的赞赏和器重,并与其出版了诗歌合集《施工缓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法国被德军占领,夏尔英勇参战,加入抵抗运动,并成为下阿尔卑斯地区的游击队领袖。在当地,很多人不知道他就是诗人夏尔,但是,很多人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尉”,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法国光复后,夏尔继续诗歌创作,经历过苦难和死亡威胁后的诗人,虽然他后来脱离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然而其创作手法依旧是超现实主义式的,他对现实的关注也愈加强烈。他的诗歌奇崛神秘,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复杂难解,但仍然影响了包括福科在内的众多大家,被誉为法国最好的隐秘主义诗歌大师。
《勒内·夏尔诗选》的译者树才曾对我说:“‘我歌唱新生儿脸上的热烈’,这样的句子惟有夏尔才能写出来。”树才翻译夏尔的诗作极其认真,在这本诗集的附录后记中他写道:“我译得吃力,缓慢,……正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我的译诗,在为‘可能’而战。”
这本诗集连同树才翻译的另外两本博纳夫瓦、勒韦尔第诗选的封面设计者,恰好也是拙作《蓝蓝的童话》的设计者。赵晓阳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每道环节事必亲躬,和我多次就封面、纸张、版式、字号等具体问题电话来往,让我也了解到树才翻译的三本诗集的进展。由此,我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诗集印出上市的时间,并很快在郑州的书店买到了《勒内·夏尔诗选》。那是2002年秋天,几个月后,便有了和多多等诗人在太湖边谈论夏尔诗歌的机缘。
有一次我偶尔在网上读到何家炜翻译的夏尔的一首诗《宣告其名》,在树才的译文中翻译为《宣告他的名字》。有一个挺大的异译是,何译:“那时我十岁,索尔格河将我镶嵌。”而树才的译文是:“我十岁,索尔格插入我。”
“镶嵌”与“插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我不懂法语,心存疑惑,一直想找机会向树才请教,但一见面却又总是忘记。
三
棕色蜜蜂,在这醒来的薰衣草中,你们在寻找谁?——勒内·夏尔
拿到《勒内·夏尔诗选》后的一段日子,我几乎整日沉湎于诗集中那些令人着迷的诗句。以往的阅读习惯开始接受着又一轮的挑战。我记得在翻过整本诗集后的某一天,当我顺手再次翻开书的时候,一行字跳进眼睛:“倾翻的船上没有恶毒的影子。”我记得我读过这句诗。但为什么我又一次读到它的时候,醍醐灌顶般就打了一个寒颤?是的,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任何对于人的诅咒都会为死亡来临时对生命的怜悯所取代。这样的阅读令我心仪不已,这是因为它证实了肤浅而匆忙的阅读几乎完全无效,而夏尔的诗带给了我再次认识并开拓自己理解力的机会。
没过多久,赵晓阳把一整套崭新的三本译诗集和《陈独秀传》寄到了我手中,于是我有了第二本《勒内·夏尔》诗选。我打电话向他道谢,但同时表示,像这样的诗集再多一套也不算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去读多少次。
勒内·夏尔有一首诗《红色的饥饿》,我印象极深。我记不清在这本诗集出版前是不是已经读到过这首诗。因为树才当年不断地在翻译法国诗人的作品,我们通信时常会接到他打印在纸上的一些翻译诗歌,诸如勒韦尔第的作品,雅姆的作品,我都是很早就从树才的惠寄中读到了。因为市场的原因,一般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诗集,他们忘了那些杰出的诗篇不仅仅像夏尔所说“诗,从身上盗走了我的死”,。
回到夏尔的诗——《红色的饥饿》,是写给一个死去的女人的诗,作者营造了一种她仍然活在人间的氛围—像往常一样,在餐桌旁坐下,和诗人一起吃饭,或者被她爱的男人紧紧搂在怀中。然而,“你疯了”,诗人的疑问和肯定都是针对自己的,他知道借用诗歌的魔力能让爱人复活,活在自己的膝盖上和双臂间,或在视力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你太美了,没有人意识到你会死。”夏尔这句诗像迎面撞过来的一口大钟,让读者清醒,并为美的殁亡而痛心疾首。诗人接下来写道:“确定无疑的赤裸,/乳房在心脏旁腐烂”,令人毛骨悚然的具体的描写推进着悲哀绝望的前行。然而,死去的女人并不孤独,诗人深情地说:“过一会儿,就是夜。你和我一起上路。”因为这是一个跨越了生死的“重合的世界”,“一个男人,他曾把你紧搂在怀里。/坐下来,吃饭。”
这是一首让人潸然泪下的诗。一首你读到以后再也不会忘记的诗。对于一个合格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诗篇就像芬芳的薰衣草,吸引着我们蜜蜂般寻找真情的翅膀前往。
四
为什么众人中最活生生的生者,难道你只是生者中花朵的黑暗?——勒内·夏尔
法国老牌的伽里马出版社有一个在全球威名赫赫的“七星文库”,它和日本的岩波文库、英国的企鹅文库一同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典文学系列丛书。能够入选七星文库的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至名归的经典大师。截至2009年,仅有198位作家成为该文库的入选者。对于很多诗人作家来说,被七星文库看中,意味着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和莫大的荣誉。勒内·夏尔是唯一一个在世入选文库的诗人。他于1988年在巴黎去世,20年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百岁时由七星文库推出了他的七本文集,成为了另一个入选七星文库的“七星活人”。
2003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和几位诗友见面时,诗人树才又送了我由他翻译的《勒内·夏尔诗选》。至此,我的《勒内·夏尔诗选》达到了三本。我并未推辞,而是快乐地感谢并接受—有谁能够不要自己喜欢的书呢?哪怕你已经有了。
我从不隐瞒对夏尔诗歌的喜爱,正如我也非常喜欢另一个法国诗人—极为朴素晓畅的雅姆。两位诗人在表达形式上完全不同:夏尔的诗,用树才的话来说是 “陡坡”,有险峻有意外,也有高崖之下山谷的幽深;而雅姆则宁静澄明,质朴如憨厚的农夫。我渐渐地发现,这两位风格迥异的诗人却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内在的一致。夏尔的诗句在看似抽象中处处布满具象,而雅姆邻家老叔般低声的喃喃诉说却也似一把直抵心胸的精神刀子。两位诗人都在探索人类的痛苦、希望和命运,他们关注的都是人的本质和心灵中最隐秘的那些颤动。虽然他们挥舞的是不同样式的镰刀,但收割的却是完全一样的沉甸甸的精神稻谷。
去年仲夏初到的一天,很久没有联系的赵晓阳忽然打来电话,问:“你忙吗?”我说我不忙。他说:“我今天给很多人打了电话,人人都在忙。”我说我不忙,然后就沉默,听着他话筒里的叹息。我知道,在一些人的记忆里,会有某些个难以遗忘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像毒针一样深深扎进人的大脑中,时常来刺痛你。从他几乎要哽咽的声音里,我听到的是痛苦,也是一个人高贵的性情。感谢赵晓阳,给我们出版了这么多好诗集;感谢树才,翻译了这么好的诗句。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动人的诗歌绝不是点缀“浪漫”生活的花边,它们如沉重的锤头,依旧在不停锻打着诗歌这架引领我们上升的梯子,把我们送往更接近正直高尚的精神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