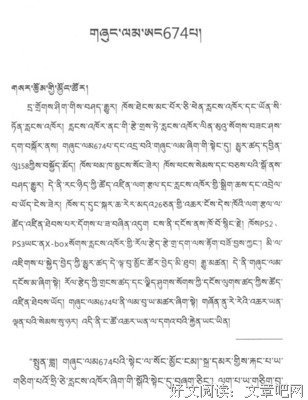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是一本由吴岩 主编 / 郭凯 副主编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4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精选点评:
●这封面蛮应景~
●蝴蝶效应很萌,开窍蛮有意思的
●有一部分之前没看过,有的是重温了,不管何时读来,总能感受到科幻的力量,直达人心。
●最最喜歡何夕的《人生不相见》
●看的有点烦啊
●第一篇那个数学史害我去研究了好久倍立方问题,但是其实不太好看,有些什么自助烤肉那样的完全就是优秀的搞笑作品,有的还不错,开窍以前在豆瓣看过,很棒,再生砖人性多,热岛播种和深海鱼这样的就是能看看。
●每年的编选都用心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韩松的《再生砖》,笔力很好,由浅入深,把局限于个人的生活提高到宇宙哲学的层次,文学性和科幻性俱佳。
●能看到自己的小说在著名的科幻年选中出现异常激动,今天看到,更加激动了!呃。。。。另,汪元元写的点评相当专业且精道。
●科幻让世界变得纯洁。
●每天一短篇走起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读后感(一):什么时候能买到啊?
问一下,光看译文版了。年底回头关注下中国科幻。:)问一下,光看译文版了。年底回头关注下中国科幻。:)问一下,光看译文版了。年底回头关注下中国科幻。:)问一下,光看译文版了。年底回头关注下中国科幻。:)问一下,光看译文版了。年底回头关注下中国科幻。:)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读后感(二):简评,略刻薄
昔日玫瑰:白富美高大上类型,作为开篇显得有气场,不作为科幻来看挺好。
人生不相见:中规中矩的文明存在探讨,缺少新意。
蝴蝶效应 :没看懂,思想太跳跃,内容太“丰富”。
再生砖:韩氏一贯的神神叨叨,不看名号也知道谁是作者,这也是一种成功,还挺喜欢这种灵异飘逸的风格的。
深海鱼:没有经过验证,但隐约觉得内核存在硬伤,真能“跳”上太空?作为一种探索精神也就罢了。
弦歌:音乐部分写得很唯美,科幻部分就显得单薄了。
开窍:很赞这种开放式的充满惊悚意味的文章,回味无穷。
喷薄欲出:总感觉怪怪的,星河本身是在碳排放相关工作吗,也在科研圈吗,几年前我还在校园内,但变化已经那么大了?这就是所谓的新校园科幻?
星海彼岸:很有电影感,笔法也很成熟。
热岛:这样的小说也填充到最佳集册里?难道就因为作者是美女?
播种:创意很好,漫天的火车的意象很美,灾难片+平行空间写出了新气象。
去记住他们:看完就忘了说啥的故事,写评论还要翻回小说。
山民纪事:这是赛博朋克类型吗?写得不知所云。
烤肉自助星:儿童科幻水平。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读后感(三):也可能是我品位下降了
分篇短评:
昔日玫瑰:野心不小,有些地方解释地不太明白。
人生不相见:强说愁。
蝴蝶效应:禁止酒后写作。
再生砖:情节?
深海鱼:单薄无力。
弦歌:毫无逻辑的战争。
开窍:自命不凡,爱蹦小众名词,主题不明,典型陈楸帆。
喷薄欲出:散发着科研生活一般的无聊。
星海彼岸:没劲。
热岛:美女搞科研也还是无聊啊。
播种:开篇挺好,后面开始凑字数。
去记住他们:暧昧不清。
山民纪事:凑字数。
烤肉自助星:吃顿饭聊出来的文章就能入年度最佳上哪说理。
不知道是有什么潜规则在限制这种选集收入的文章,还是真就是打心眼里评出来的年度最佳科幻,还是为了增加多样性,就说最后一篇,作者自己就招认是吃饭聊天聊出来的东西,这样信手拈来就进了年度最佳……连同其他文章带来的感受,我又控制不住把问题上升了。
觉得中国目前的科幻写作者还是一群会写点东西的科幻爱好者而已,从他们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内心里的高潮迭起,大家拜读过之后,那些幸运地能和作者心灵相通的读者沾到了高潮的余韵,其他人没有撕破脸皮说“这什么玩意儿”,可能是潜意识里还不愿放弃科幻爱好者这个身份,毕竟科幻文学在国内还是很小众的东西,好不容易有几个高产和中产的作家,再不捧着点,怎么都于心不忍。
可我还是觉得,有些东西写出来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2011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读后感(四):序言完整版
序言:中国科幻的革命与循环之年
郭凯
一本理想的年选也许应该像一个时代的博物馆,把一年里各种类型的作品做一个综述,无论是点子还是故事,逻辑的还是情感的,个人的还是大众的,面向市场的还是学术的,有出众之处,皆应汇集于此。遗憾的是,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们没有时间机器,无法从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溯今天,去判断哪些作品最终能经历时间的筛选,面对时间,无人能做裁决者。我们都是筛选者的一员,无论是此书的编者还是读者,无论是读过或未读过此书的人。
2011年是和“革命”这个词绑定在一起的,人们纪念和讨论着90或100年前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们并不吝啬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历史的河流也许是一个圆而不是条直线,曾经发生过的也许还在发生,如同在很多中国科幻人眼里,变化从未停止,这一年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年。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销量也许不及三十年前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十分之一,但已经足以改变一切,让科幻重新回到大众和学术界的视野。写此文时,刚刚在成都借星云奖召开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擅长将科幻与政治联系的韩松简称为“一大”,不能不让人联想起这个词汇遥远的最初含义。这一年中国最重要的一本科幻理论著作大约是吴岩的《科幻文学论纲》,吴岩在这本书里开始探讨科幻的权力结构问题,他认为科幻的作者和读者们,都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他们借助科幻这种边缘文化向权力的中心挑战,如果成功,他们将成为中心,而新的边缘将产生,以新的科幻重新向中心挑战,于是科幻的定义和形式永远在变化。
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革命,一切又如一个不断循环的圆。
“革命”一词,在西方,其实最早就是圆的意思,和科学与科幻,也并非没有联系。
“革命”一词在英语里是“revolution”,这个词的拉丁语形式在中世纪时,其实是一个科学词汇,最早用于天文学,指天体的圆周运动。当时的欧洲人相信一切天体镶嵌在水晶天球中,绕地球旋转,恒星背景固定不动,太阳在诸星座中每日移动一度,一年中经过黄道十二宫,走过一周,回到原点,完成一个循环的周期,即是一个revolution。文艺复兴时代,这个词汇借星占学向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拓展,欧洲人相信王朝的更替和社会的变革,如同天体的循环一样,随看不见的时光之轮转动,一切终将回到原点。逐渐,revolution一词中,循环的意思被逐渐遗忘,变化的细节被逐渐强调,它被用于代指直线性的,积累和进步的,不再回头的重大变革,现代性的观念被建立,这个词的意思走向了它原意的反面。哥白尼为了用更简单的数学方法解释天体的运转,希望恢复古希腊柏拉图思想中对于正圆的推崇,他提出了日心说,认为这种设想更能体现古希腊人的某种观念,他的那本《天体运行论》的英文名是On the Revolution,意指循环,在今天的人看来,他却是一场科学革命的发动者,改变了人们眼中世界的面貌:地球不再是特殊的,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一棵普通的星球,其他的星球也有可能居住着生命。当时的欧洲小说和诗歌中开始出现外星文明的踪迹,亚当•罗伯茨在其《科幻小说史》中,将那个时代称为科幻文学真正的开端。
古人曾以为脚下的大地是平坦的,因为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圆的一小部分,如果时间的河流也是一个巨大的圆,我们会被迷惑吗?科幻会将我们送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还是一个曾被丢失和被遗忘的世界?要把握这一切,需要从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作品开始,这就是这本年选的意义。
沿着学术这道门,走得更远的是韩松的《地铁》。韩松的作品风格本来就与主流文学十分趋近,对于科幻与现实政治、社会间的关系,思考也更加深入,8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今日批评家”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主流文学界批评家们对韩松近年来以《地铁》为代表的科幻作品进行讨论,从意象风格,叙事结构,词汇使用等各个角度进行细致剖析,这些角度是科幻文学内部讨论很少遇到的,并且是在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讨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的认识来说,意义深远。而沿着商业这道门,最典型的事件则是专业商业图书公司围绕钱莉芳《天命》所做出的一系列宣传,《天命》和作者几年前的作品《天意》一样,试图在中国开创一条“历史科幻”路径,以严密的历史考证和大胆的猜想去取代传统科幻中技术细节和未来设计,转而走向对历史的重新解释。这种路径似乎趋近于大众文化中流行的“穿越”题材,但科学解释所提供的故事大框架又保证了两类故事性质的不同。“历史科幻”的路径显然是要发挥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特色,创造一类对中国大众市场有足够吸引力的新型科幻,但这种创新也是有代价的:科学解释和历史文化间的衔接有着明显的断裂,传统科幻的读者们对这种科幻的风格也并不完全适应。
另一些作品却是完全拒绝商业化的,景芳的《流浪玛厄斯》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商业宣传,这部作品中设计了一对相互观察的未来社会:完全被商业化控制的地球,和完全没有商业化,所有知识产品和艺术免费分享的,精英文化的火星。景芳以诗人般优美的语言和建筑师般的精巧手法延续着比科幻本身更加古老的乌托邦传统,让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们相互观察,每一个世界都是中国与外界在不同时代的投影。这一年的长篇科幻作品还有王晋康的《与吾同在》,赵海虹的《水晶的天空》,谭剑的《人形软件》,墨熊的《红蚀》等,相比去年来说,国内科幻长篇的出版稳中有升,在“三体”系列的影响力笼罩下,作者们依然按照自己不同的风格在创作着。
而对于中短篇科幻来说,多样性则表现地更为明显。
《九州幻想》依然在上海高举着他们“大幻想”的旗帜,试图把一切幻想文学类型打通,在商业化和艺术化间寻找个性解放的道路。在其作品中寻找哪些是“科幻”,显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区分这些东西对他们本身来说并不重要,“科幻”一词的定义都需要重置。万象丰年的《播种》是去年“城市毁灭”专题的延续,不同的是,前两年选集中所收录的此选集的作品,被毁灭的都是大型城市如西安,上海等,这次被毁灭的是相对小的柳州,这座城市昔日铁路枢纽的地位被强调,来自平行宇宙的火车穿越时空,一次次地撞向这座城市,更深一层的中国在新一轮的毁灭中被揭示。苏学军的《星海彼岸》讲述一群失去记忆,历史和技术的人类后裔在新世界的探索,苏学军一贯重视人类最本质的奋斗和创造力量,让新的世界图景和过去的历史一点点在讲述中展现,浑然天成。
作为一份网络刊物,《新幻界》逐渐在中国的科幻界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一个有分量的新作品发表平台,它也开始将其中的作品汇集成实体书出版。梁清散的《烤肉自助星》几乎没有任何想要讲述哲理的宏大欲望,它仅仅是为了有趣而写的,当一位穿着密封宇航服的饥肠辘辘的探险者来到满是烤肉的星球上会遇到什么?这篇作品的每一个文字似乎都在刺激人最原始的生理欲望,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写科幻了。
《新幻界》不是唯一的科幻网络载体,一家新兴的网站在这一年里吸引到了更多的目光,不仅仅是关于科幻的,也是所有涉及科学相关内容的。一直关心科幻发展的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在2010年底建立了一个商业化的分身:果壳网。在其众多颇受欢迎的版块中,支持短篇科幻发表的“果壳微科幻”栏目成了原创网络科幻新的聚集地。果壳网是一个科学青年聚集的场所,这里最文艺的科幻作品往往也有着很强的技术背景,半夏大魔王的《去记住他们》是一个机器人讲述的末日童话,人类从世界上如气泡般一个个消失,机器人踏上旅途记录人类最后的痕迹,并最终似乎发现了人类消失的线索,他们如同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一个周期总是减少一半,却不知具体的个体谁会先离去,又如蜻蜓的幼虫,化作成虫前无暇告知同伴,几个简单的科学比喻,隐藏着人类的命运。
选集中最为特殊的一篇,大约是飞氘的《蝴蝶效应》,从作品的构成到发表的途径,都充满着实验性,它由几十个小章节构成,分三部分发表在不同类型的刊物上。飞氘套用西方科幻电影的主题,重写中国的历史,远航的郑和,成为了《星际迷航》的船长,不知道如何安置手下梁山好汉的宋江,陷入了X战警分阵营的迷茫,被贬远方的苏东坡,来到了《月球》上,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民国时鲁迅感时伤神,西方科幻中关于未来的一切,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中都发生过了,历史是一个循环吗?三种类型的刊物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大约也宣告了这样的历史描写,不同的读者都可以接受,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西方人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飞氘自己也在寻找答案。
所有人都在找。
这一年,科幻界的活动很多。以上海为例,上海高校科幻协会联盟——科幻苹果核于今年6月和8月,分别举办了上海高校幻想节和第二届科幻星空奖颁奖礼,江浙地区与科幻相关的作家和科幻迷都参与了这两次活动,既有九州幻想这样的纯幻想迷群体,也有上海科协这样的官方科学组织,甚至包括了一些在8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的老作者。华南,华中和西北地区也出现了科幻迷群体并组织了一些活动,各个地方开始整合当地的科幻资源,去年在北京创办的民间科幻奖项星空奖的举办今年转到了在上海举办。而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创办的科幻星云奖规模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年不仅举办了之前提到的韩松所谓“一大”,也开设了扶植科幻作家实体出版和新媒体出版的“星计划”和对科幻进行学术探讨的“云论坛”,一大批科幻作者在此次活动中签约,可想而知下一年也许会是中国长篇科幻出版集中的一年,本次“云论坛”以“三体时代的科幻文学”为主题,来自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日本各地的学者,作家和出版者就科幻文学的历史境遇,当下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多方面交流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这是科幻文学在中国新一轮崛起。
但中国科幻这一年与世界的接触更是前所未有的频繁,与科学,与文学,与官方,与大众,与学术,与商业,与地方,与国外,与现实,与网络,如果说前几年科幻界与这些领域只是试探性的接触,探讨合作的意向和可能的话,这一年在许多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实质性的合作,这方面的例子已经数不胜数,就在写此文的这一天,“三体”系列的中文数字版权刚刚与一家相关公司签约,宣布将于年底在新的媒体平台与读者见面,而韩松则刚刚抵达挪威,他将与安妮宝贝、汪晖等中国作家和学者一起,参加当地举办的“中国文学周”,向世界讲述近年来中国科幻所发生的一切。“三体”系列只是一个契机,它的背后,是中国科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积累的力量的爆发,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例如中国当今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在《天南》的科幻专辑中,困困发表了一篇报道《依然有人仰望星空》,他引用韩松的话说,很奇怪,中国的科幻作家大多来自偏远闭塞的城镇,那里充溢着工业幻想和郊县文化,这样的地方分化出两类人,或出于对工业化的羡慕,激发改变命运的野心,现实而投机,或是内向的,希望用想象去跨过这个阶段,到达一个遥远的乌托。因为中国的这片土壤,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漫长过渡中,科幻站在了一个醒目的位置。毫无疑问,中国科幻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前景,未来还未到来,过于乐观或悲观,都言之过早,中国科幻可以做的,是思考自身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回到“revolution”一词的原意,它最早确实是一个科学词汇,指天体周年循环的运转。但正是在天文学家无数代人的观察中,他们发现了天体并不是简单地匀速圆周运动,而是快慢不定,顺逆无常,他们建立了各种精密的模型试图说明这种变化,并不断修改这些模型,最终形成了今天科学意义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的面貌,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revolution”。世界真实的运转不会随着我们的意愿去重复循环,它逼迫我们的思想远离过去的圆形轨道,走上一条远离中心的切线,这是近代科学从以往人类知识中分离出来的道路,而科幻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指出,按科学哲学的前沿,费耶阿本德的结论,科学的创新需要完全的自由,而任何现实条件都会制约这种自由,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大约在十年前,刘慈欣发表了一篇小说,讲述一个中国农民如何从社会的最底层来到大城市,来到星空,最后作为整个人类的先驱,离开地球的那条圆形轨道,带着理想主义一去不复返地飞向群星。十年之后,刘慈欣笔下的宇宙深处已经残酷无比,但那位农民已经不可能回头,他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在天堂和地狱间,他需要首先杀出一片血海,这是作为科幻作者和读者的边缘人群的宿命,也是中国科幻和整个未来中国的宿命。
2011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