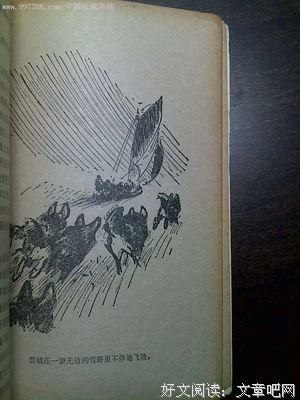
《草莽艺人》是一本由田川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草莽艺人》精选点评:
●觉得应该是近年新书里相当好的一本。走南闯北说戏曲,@newquantum 兄应该喜欢。其中印象深的是皮影戏那一段。文章贯穿着冷幽默,也不过分。“梆子是农村生活的一种节奏,该听戏就像该播种、收割了一样。”“我觉得自己一年来的生活就是跟着一群陌生人走很多路去认识另一群陌生人...”
●中国传统戏曲的小人物群像
●纸上苍生
●难得一见的好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当举国上下都只知道追逐名利的时候,这些民间的宝藏就只有末路一条了。
●叙事风格有意思,题材很好,但是有点杂有点跑题
●当然有瑕疵,但田川最宝贵的特质在于他丝毫没有修饰自己的欲望,既不掩盖城市资产阶级的眼光,也不试图从短暂的在地观察中挖掘以小见大的真理,而这些诚实并未妨碍他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带着热气的人味儿。好想和作者约会啊!!
●我曾一度以为作者试图大声疾呼让我们奔走相告,去啊!去拯救那些即将死去的民间艺术!却逐渐发现铺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 “喜好只会使人走出第一步时兴奋地抬起脚,而当这只脚确实落到了坚硬的地面、开始了征程,更多地,我想需要的是别的东西。”
●书做得太漂亮了
●乡土戏文能热闹地充满人心,但莫名地又让人倍感凄凉,这凄凉不知道来自何方。
●很有《读库》风格的一本书,前面晋、陕、冀的部分让我回忆起自己家乡和童年乡村看戏的经历,但二人转的那篇就让人感到工业质感的悲凉落寞了。初版是2002年,采风年代在更早,感谢有这么一份记录。
《草莽艺人》读后感(一):文化中国的“纪录片”
《草莽艺人》读后感(二):三星半
田川记录的是2000年黄河以北部分艺人的生活状态,距今又过去了十五年。我或多或少地有些想法,比如,那些艺人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否有所改变之类。
其实并不重要。我真正关心的,与此无关。
事实上,我本来是抱着读一本报告文学的心思买了这本书,掀开看,才发现是本杂感。当然也没什么不好,田川的文字挺地道,读起来顺溜,不亏。啼笑皆非就是人生,没啥没啥。
我这心态跟田川出门采访时的状态总是有点像的吧。我猜。
读书随感性质的文字,我有差不多快两个月没写了。这不大对头。虽然忙,但也不对头。我的记性一般,读了书不写点什么,就觉得跟忘了没两样。
我是为什么买了这本书?一个可能是,《读库》。但好像也不是。不记下来,就会纠结。活该。
开头几篇我不喜欢,里头有淡淡的优越感。甚至可能不怎么淡。在豆瓣看书评,一篇采访文字里头说田川的老师也不喜欢这本书,认为有嘲讽的成分。田川解释道:我是在嘲讽所有人。所有中国人。而这嘲讽里头有宽容与自信的意思。
这话我觉得别扭。
再想想,还是别扭。
优越感也好,嘲讽也罢,这些味道在后几篇里不太能找得见踪影,也许我是适应了。可确实觉得后几篇比前几篇漂亮,像是心思和身段都更沉了些。
述而不著,是圣贤的一个状态。田川当然不可能是圣贤。这等境界,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反倒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心思诚实地记下来,就挺好。从这一点上看,田川的这本书,颇有价值。
于是,在读《草莽艺人》的时候,我是在读田川吗?
嗯,是的。
《草莽艺人》读后感(三):“草莽艺术”中远去的乡土
文/严杰夫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鲁迅在《社戏》里对旧中国农村戏曲的这段描写,一定令很多人难以忘怀。而民间艺术在旧乡土社会里的繁荣,应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农业社会里的民众,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家族中发生大事时,才会放下劳作寻得片刻休憩,这种“忙里偷闲”的生活节奏,不仅维持着古老帝国日常生活的运作,而且滋养出了形式各样、百花齐放的地方民间艺术。
随着近代以来,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再加上新娱乐形式层出不穷地侵入到民众生活中,维持民间艺术的土壤开始瓦解,曾经活跃于农村广阔天地里的草根艺术逐渐式微,继而终于成为旧乡土社会在现代社会留下的少数几片阴影。不过,“阴影”毕竟还在某个角落中顽强地生长。田川的《草莽艺人》正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阴影”的生命力。
《草莽艺人》,田川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很“水浒”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记录的那些人物,多少都有些“草寇”的味道。无论是平遥的瞽书人,还是石家庄的丝弦艺人,抑或是华阴的皮影雕刻师,再到河北“老梆子”和东北的“二人转”演员,他们似乎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只因为偶尔的不如意才不得不藏身于县乡的文化馆或某个偏远的剧团里,不然就是混迹于充斥着三教九流的草根剧场中。这些“草莽”们自然不同于现代社会里的“多数人”,他们似乎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遥远却又异常丰富清明的世界里,所以田川会说,“我始终有一种不成熟的认识:人一老,就像孩子一样,喜欢胡闹、喜欢说没意义的话;但少数人老了,却像成精了一样,所有的事情做得太有分寸,举手投足成了一种气质。”
不过,“草莽们”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他们也不得不与柴米油盐打交道。于是,在田川的笔下,他们多少还是有些“烟火气”:对平遥的瞽书盲人来说,赶回家过年比为一个来自遥远北京的旅人表演更重要;名扬海外的侯马皮影雕刻师也会为了生活而担心;拥有三位梅花奖演员的运城蒲剧团更是如同多数社会组织一样,深受团员互相拆台的困扰。这一切一切发生在舞台下面的真实细节,却是展现了草莽艺人们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是如何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草莽艺人们在褪去戏服、卸掉戏妆后,当然不过是个普通人,但这种“烟火气”并没有削弱艺人们的魅力,却为他们的生活多少平添了一些真实。
事实上,在读完《草莽艺人》后,我们很难描述田川写作这本作品的目的。它并不是一个收集仍然存在的传统民间艺术的汇编,但它确实列出了北中国大部分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而它又很难说在记录民间艺人所面临的困境,因为对于这些艺人,作者笔端流露出的敬佩并不少于同情。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看,《草莽艺人》记录的其实就是一个都市人眼中民间艺术的生存现状。
这样来看,《草莽艺人》提供了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草莽艺人身上交杂的骄傲、迷惘、窘迫、期待等复杂情绪,更是让我们从民间艺术这个独特的角度,来理解“乡土社会正经历着怎样的变迁”这个宏大的题目吧!
《草莽艺人》读后感(四):田川:在艺人身上发现“文化中国”(from<南方都市报>)
(这种复制粘贴没问题的吧(⊙_⊙))
日期:[2013年8月18日] 版次:[GB19] 版名:[人物] 稿源:[南方都市报]
田川
北京人。纪录片工作者,曾制作《回望梁启超》、《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等纪录片。出版了《四季日光》、《寻找英雄》、《草莽艺人》、《东京记》等。
十年前,因为出版了《草莽艺人》,田川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拍纪录片,今年,《草莽艺人》一书再版,田川离开了央视,忙于自己的工作室。他说,这是一个巧合的轮回。“田川的《草莽艺人》以平实的态度讲述了北中国数省艺人们的生活,他把寻找艺人、观看艺人在台前台后的言行等过程写了出来,二人转、丝弦、瞽书、皮影、河北梆子等等,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复调式中国生活图景”,这是余世存对《草莽艺人》的概括。
《东京记》、《草莽艺人》是田川最初的两部作品,“它就代表那时期我的认识,做修改就不伦不类了。”再版,除了增加一篇余世存的序言《农民中国里的艺人命运》,没什么太大的变动。
2006年,田川出版过一本《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这是因为2005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套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录片,“我做了很长时间,很多采访人在之后一两年之内就故去了。而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不能播。”田川觉得很可惜,于是把电视里没呈现的部分公之于众,这样就有了《寻找英雄》。“尽量文字少用形容词,用最简单的话把你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是田川写作时对自己的要求。
《草莽艺人》的因缘
南都:你从日本回来不久,什么契机促使2002年《草莽艺人》的出版?
田川:当时国内很流行说“看图时代”,很多以摄影、图片为主的杂志出来。编辑杨全强在南京做一个叫《光与影》的杂志,我刚从日本回国,也没工作,我把在日本拍的照片投稿到《光与影》杂志,杨全强对我有了印象,后来他进出版社了,先邀我写《东京记》。这时我已经去过两个地拍过艺人,先是北京湖广会馆的“北昆”,后来又去了一趟山西。所以《草莽艺人》和《东京记》两本书是同时写的,《东京记》写得靠前一点,写闷了,就想出去转转,没什么目的地去找那些艺人。
所以拍草莽艺人的时候,没想过出书。《草莽艺人》和《东京记》是一个钢镚儿的两面。两本书都是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过去几年在异域的生活要记录下来,未来怎么重新适应祖国和社会,我希望通过一个不同于出国之前的视点去找自己,我找的人都是我曾经忽视的、完全没关系的那些人。
南都:《草莽艺人》其实挺难在图书种类中进行归类,是吧?
田川:当时我是想把它弄一个小说似的东西。《草莽艺人》我相信比《东京记》要小众多了。看的人一定是很感兴趣,所以你怎么让他能进入得快一点,前几篇是比较好玩、轻松一点的,进去以后就是那些沉重的东西、活色生香的东西。
最早给《光与影》杂志投稿的时候,我是想做纯摄影,但2000年回国以后,我发现大家没时间拿着一张照片好好看。都要求你写很多照片说明,讲背后的故事,要不然就看不懂似的。文字恰恰又是我很擅长的,最后《草莽艺人》就有点喧宾夺主了,照片成配图了。
南都:有没有书作为你写作的一个参考?
田川:我觉得写作的时候还真没有一个参考的东西,给我个人影响比较大可能有两种类型的书。我第一本书起名叫《东京记》,是跟中国古籍《东京梦华录》有关,还包括《扬州画舫录》、《海上花列传》、《儒林外史》这类的书。我喜欢古籍中记述社会生活百态的杂记类著作,好像没有一个完整情节,其实,生活的日常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另外一类就是日本的私小说,很像随笔,有很强烈的个人感在里面,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波澜壮阔的情节,很散漫,但是给你的冲击很大。
另外,我在日本看了大量的片子,当时国内根本看不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国的经典电影,日本全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视训练,看了这些后,我突然发现,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都是电影和纪录片的作者,小说已经成为一个古董了,它能影响的人很少,满足感也很小,反而是那些话很少的东西更有意思。潜移默化,我当时就想怎么拿影像来表达。
南都:触发你去寻找乡村艺人原因是什么?
田川: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日本看过一张照片,摄影师在一个日本的歌舞伎的舞台的上面,透过木地板的缝,拍下面一个艺人在化妆。那张照片对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的父辈来自于农村,血液里有北方曲艺的因素,那张照片可能就把血液里的那种因素激发了。所以我就很痴迷于那舞台后面的东西。回国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们的传统在哪?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现在在干什么?反正闲着也没事,就去找他们吧!这样就开始。
接触艺人不容易
南都:网上的简历说,你去日本的三年是学习刷碗、搬报纸和纪录片?
田川:我在日本大学艺术学院学的是纪录片。但只限于理论层面,没有机会摸摄像机的。在日本生活艰辛,我自己赚钱买了个相机,没时间休息,所有照片都是来回打工、上学的路上拍的。那时候日本有很多中文报纸,此前我在国内没发表过作品,我给日本的报纸写过几篇小文章,却发现一篇小文就够我累死累活干一天的工资。那不如多写几篇,后来基本百发百中,就有信心了。如果生活不那么逼,我可能还永远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2000年回国之后,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有一种悲愤的情绪。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在国外很孤寂,回国后看到很多现实。就想拍点什么,写点什么发泄一下。
《草莽艺人》在2002年出版以后,央视一个编导找我,想拍里面的一个素材,我就提供了线索;后来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拍一下试试,我就拍了《台口》,还得了奖。就这样,我就进央视拍纪录片了。
第二次去跟拍丝弦,我是以中央电视台编导的身份去的。跟石家庄丝弦剧团跑了半年,到处跑台口,这个感触就更深了。因为第一次我是作为普通人的身份去的,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戏曲爱好者;下面的演员们很自然地对待你,领导们也不把你当回事。有人说,摄像机就是权力,等我有了一个央视的身份,扛着摄像机再去时,变化来了。剧团的领导们都出来了。他们不停地开会,希望你去拍他们主持会议。他们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我在后来的片子里剪了一段会议:领导在煞有介事地说官话,下面的演员扣指甲的、烦闷抽烟的、挤眉弄眼的、调情的;片子放出来,剧团领导很不满意,因为没有突出他的“业绩”。但我只拍忠于我感受的东西。
南都:书中的草莽艺人十年以后还有联系吗?
田川:很少了,因为有很多艺人可能都不记得我是谁了,匆匆而过。我到一个地方目的性不是很强,我是先设定一条路线,比如说我沿着黄河,进陕西,目的地也不知道。觉得累了就回北京。我找艺人基本上是见谁问谁,一路打听一路走,找不到也无所谓。
后来某报纸的一位朋友说,你太不了解中国现实了,容易出问题。于是弄了一张介绍信,但是地方文化部门的同志们一眼就看出来,单位跟单位之间不是这么联系的,提前不打招呼是不可能的。我在山西运城的宾馆里苦苦等了三天,他们说文化局局长会回复我,但根本没人理你。当时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痛苦,后来才发现这个过程甚至比寻找艺人本身还有意思,因为它反映了你在中国生存的现实。
南都:这也是《草莽艺人》对比《东京记》最大的特点?
田川:对,我写《东京记》比较冷静的,写《草莽艺人》就投入了情感。句子也会长。你写别人的事总是尽量客观,但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我觉得就是家里人,有很多这种嘲讽和幽默。
我的大学老师当时看了《草莽艺人》,不喜欢。觉得里面有歧视农民的倾向,有来自城市人的嘲讽。他理解错了,嘲讽是针对我作为中国人这个存在的,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嘲讽,也是自嘲。可以看看英国人、日本人写的很多东西,他们对自己的的嘲讽比对别国人辛辣多了。这里有一种宽容和自信的态度。
寻找“文化中国”
南都:在和艺人下乡演出生活在一起,短时间内怎么把陌生感消除掉?
田川: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因为我在日本太长时间没说话了,回国后我很想和陌生人说说话。与草莽艺人打交道,我突然有了一种归属感,也许这是父辈们来自农村的血缘在起作用。那些艺人们被长期忽视,当看到一个操着北京口音,拿着相机的家伙出现时,就想跟你倾吐。实际上大多的时候,都是他们在说,我在听。我说我想拍你们,他们都很热情,没有拒绝的,一路上都在照顾你。一两天陌生感就消除了,中国乡土社会有很多可贵的东西,让人感动。书中那些二人转演员,演出完了都跟我睡在一张床上,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他们大红大紫的时候,老在想那天晚上他们在床上说的话,有种做梦的感觉。
南都:面对书里的人物,给杂剧丝弦艺人拍照,你觉得他们很可怜。但到二人转的时候,你对他们有很崇高的敬意,怎么来理解这种复杂的情绪?
田川:因为太少人关注他们了。比如丝弦,它是河北省非常重视的一个剧种,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也是很大的一个剧团,但当演员们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出现时,会不断请你为他们拍张照片。
他们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尊严了,为了拍一张照片,那么大岁数的老演员,天天爬起来去晨练,我要不去,他早就不晨练了。你说这是有尊严吗?我心里有一种悲伤,我们的文化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
南都:选择拍哪些艺人,有什么规律?
田川:我当时自费去拍艺人时没什么钱,所以选择比较近的北方。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文化因素。后来我也去南方拍过,包括川剧变脸、福建的布袋戏等等,但是我没有写到书里,因为我没有共鸣。中国文化,每个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熟悉北方,只能写最熟悉的,我到陕西就已经有些隔膜了,所以我走到咸阳就不再往西走了。
南都:书中序言说,“为文化中国做一部纪录片,《草莽艺人》正是这个想法的起点”,这个纪录片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田川:序言中我没有把这事说透。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用一种“文化中国”的史观去看历史。“文化中国”靠什么来支撑呢?一个戏、一件文物、待人接物、举止言谈……是这些具体的细节。只有通过教育,通过滋养灵魂,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最根本的细节改变,最终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我是做历史纪录片的,你站在一个什么态度上去创作:是去迎合越来越粗鄙的大众趣味?还是建设一点什么,给大家讲故事的同时提供一些文明层面的思考?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
南都:近期的计划是什么?
田川:我现在在做纪录片《西洋镜———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外国摄影师从19世纪中叶开始拍摄中国,一直拍到现在。我们历史书上的很多照片都是人家拍的,但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意。没有人去梳理这些东西。这些外国摄影师有很多传奇故事;他们为什么来拍中国?他们拍到了什么?我希望能做一些细节的工作,让我们的心灵更丰富一些。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赵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