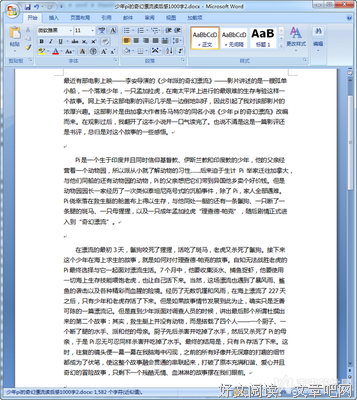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一本由楊.馬泰爾著作,皇冠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50,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精选点评:
●好久没有这种打开第一页就想一口气读完的感觉。一是内心的猛虎,就是那些焦虑与不安反倒是我们活下去或者尝试更多的原动力。二是,R.P这只老虎最后无情的离去,让我们明白生活一点也不像π,大部分人和事在恰当的时刻必须结束,我们要接受告别,因为他们不会像3.14一样无限重复下去
●前面很冗长,后面很精彩,结局很回味
●翻得不好 但是书很精彩
●书不如电影精彩
●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动物版本的故事精彩,人类版本的故事残酷。
●好看
●一般
●又生生念完了一本书。。。
●前三分之一在地铁上读得昏昏欲睡,后三分之二在睡前读得欲罢不能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读后感(一):越读越重
如果我不是在微博上一圈又一圈的转载分析中被正面击中无数次,而是单纯的站在书店里翻看这本书,那么无论是这本书的前10页,还是前200页都不会引起我购买的欲望,事实上,就算我已经开始读了,前200页依旧让我读的很索然,不知道我这样的算不算非主流的感受,这本书一点都不符合我阅读的习惯,一点都引不起我阅读的兴趣,全文对我来说也无法引发任何思考,刚刚合上这本书,我的感觉就是:谢天谢地,终于读完了,当读一本书成为一种负担,那不读也罢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读后感(二):关于信仰
看过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我便喜欢上了这个故事 ,买来原著一看究竟。看后感觉原著与电影之间的差距实在不小。电影除了故事引人入胜之外,更偏重视觉效果。读书则使我更深入主人公的心灵,一个有信仰、灵魂高贵的人。
宗教与信仰
派儿时参观了一个印度教庙宇,某种令人动情的神秘的东西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象。宗教的种子从此发芽,不停成长。这个灵性的少年在一个神圣宇宙子宫里,一切都是在那里出生。他能看见那核心,并意识到神的存在方式不仅仅在寺庙里,而是以更加宏大的方式存在。宗教不仅仅是礼仪和仪式,还有它所象征的意义。宇宙通过印度教徒的眼睛对派产生了意义。梵天,世界的灵魂,用经线和纬线在上面织成存在之布的支撑框架,布上有各种时间和空间的装饰。非人格的梵天,没有质量,不可理解,不可描述,不可企及;人们用可怜的语言缝制的外衣——真理、统一、绝对最高实在、存在基础总是被撑破。人们通过部分的理解去接近它;人们通过某些特征——仁爱、慈悲得以识别。
14岁时,派在教堂遇见了马丁神父,他便认识了耶稣,从此他想成为基督徒。15岁时他遇见了苏非派教徒,一个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并一起进行虔诚赞颂真主安拉的仪式。当他和安拉相遇,从此之后以派为中心的小圆和一个大得多的圆的中心重合了。
当梵学家、牧师、穆斯林智者三位宗教人士在广场上同时与派相遇时,派的秘密暴露了。三位都在抨击其他的教派,并强调信仰只能有一个,让派做出选择!派说:“圣雄甘地说所有宗教都是真实的。派只是想热爱上帝而已!”
每个教派都是在用自己教派独有的方式在赞颂神,从而解读宇宙。这就好似盲人摸象。有人摸的鼻子,有人摸到腿,有人摸到尾巴而已。宗教通过各种叙述来解释我们是谁?为什么存在?充满了爱的善所拥有的广博而无穷的能力。而神学和科学都是人类解读宇宙的方式。
经历与磨难 ,生存与死亡
神可以忍受厄运、背叛、屈辱、死亡。当生活中经历了痛苦折磨后,每次新的痛苦都令人无法忍受又让人感到微不足道。人们在寻找自己内心中的神,这时自己便是一尊神。
派经历家破人亡,经历生离死别,看穿人性与兽性。当信仰的形式与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宗教要求信仰者素食),人会选择生存。毕竟活着才能信仰。他在与理查德.帕克(孟加拉虎)的生命保卫战中得以存活。他们是伙伴,派对它倾注了感情。没有它,派会早就丧失斗志吧,在无聊与绝望中死去。登岸后,理查德.派克头也不回的消失令派伤心。若说儿时他父亲让他看老虎吃羊的惨烈情景,相比这次,他的心情更加低沉百倍吧。
派经历的数次死亡瞬间都不足以让我这个胆大的读者发自内心的恐惧,只是在小岛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中发现牙齿的时候,让我的后脑冒出丝丝凉意,头发有竖起来的感觉。这是一座死亡之岛。岛上的生态系统会把任何生物代谢掉。初登岸时的狂喜,感谢上帝的恩赐,原来这是又一次的自然的大考验!安于现状是对生存智慧最大的挑战,是死亡最悄无声息、最阴险的胜利!死亡很强大,令人心生畏惧。而生存需要更强大的勇气、智慧和信仰。
我们努力了解宇宙,了解神,在朝圣的旅途中出生和死亡,再次出生又再次死亡,一次又一次,直到终于摆脱将精神囚禁的外壳。行为的不同决定了人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不同,每个人的自由又有多少呢?
生命的真理在于人们心中的精神力量,是可称之为灵魂的东西。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读后感(三):Everything is about moving on
大概是电影上映一周以后,阿毛在QQ上短我:
-快去看少年pi。
-看啦,正在看书。
-我觉得李安挺残忍。
-他还是手下留情了我觉得。
-我越想越怕,特别是网上有人说那个岛是尸体,狐獴是尸虫。
我想了想,回说:不是啦,那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就想成是个岛啦。然后把那段经典的关于死亡爱上生命的描写(Life is so beautiful that death has fallen love with it, a jealous, possessive love that grabs at what it can. But life leaps over oblivion lightly, losing only a thing or two of no importance, and gloom is but the passing shadow of a cloud.)发给她看,她还是执着的问了一句:如果说每样东西都有指代,那个岛到底是什么?
我说:不重要了。
前100页的岁月是草灰蛇线
我喜欢看pi在印度的那段时光,上学路上的动物们各式各样的色彩和姿态,为防止认错人而假装在动物园门口揉眼睛,小朋友们笑话他的名字,要正式入教前找父母谈话而爸爸妈妈却互相推诿,爸爸用买冰淇淋来逃避宗教的话题,就像每次回头看红楼,总爱读那几篇姐妹们吟诗作画行酒令的热闹,不管这后面埋了多少草灰蛇线,我总选择忽略掉,只享受这片刻欢愉。当然,这不得不提到李安为Pi的生活添加的那个女朋友,关于莲花的暗喻和最后那个系在小岛上的红绳呼应着,真是妙笔生花。
第二个故事一定要讲
网上有人说要带孩子们去看这部影片,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孩子们看的故事,它太残酷,有人说不理解pi的信仰不理解片中的宗教意义,也许那是你未听全第二个故事的缘故,你如果看到那个法国厨子是怎样不施麻醉砍下台湾少年的腿,在他死后把他的所有内脏晾晒在船舱内,一刀接一刀的捅死pi的母亲,砍下她的头,而母亲带血的头颅则划过pi的双手沉入海底,你还觉得这是孩子们现在就该接触的东西么?孩子们还是看看哈利波特吧,阿瓦达索命不曾留下伤痕,摄魂怪可以被快乐的回忆力量击退,佛地魔只是一片被切碎了的灵魂。
i为什么没有变成Dexter?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人联想到一起,在年少时一样经过血的洗礼,Dexter变成一个杀手,没事爱把人切成小块扔海里,Pi却结婚生子工作正常生活?仅仅是因为pi信仰上帝,因为pi把这段杀人嗜血食母的经历加之一只老虎身上,加之绝境之下人类的兽性?那么,我们也可说Dexter也有自己的信仰,他相信自己,相信养父Harry和他的code,他说自己杀人行为是由他的dark passenger引发的,他自己常常没有选择,而被内心的冲动控制着去杀人,这样又和pi有什么区别?
他和Dexter相似之处不是因为他们都杀过人,而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很孤独,Dexter封闭了自我,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真实的情感,他也许有妻子有妹妹有儿子,但他在心理上是孤独的,而这竟是人类最不能忍受的痛苦,pi最后是一个人漂流在大海上,与世隔绝,人类是属于社会的,如果没有交往,他们自己构想出一个来完成人际关系的缺失,Dexter和他的dark passenger以及活在他幻象中的父亲,Pi和他的Richard Parker,以及那个瞎掉的法国人、还有小岛和狐獴。不同之处则是Dexter停留在过去,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母亲被电锯分尸的血色记忆,而Pi已经扬帆远行,试想如果这个少年直面杀人、嗜血、食母,他终有一天会奔溃发疯,汉惠帝看到吕后把戚夫人变成人彘之后就终日忧郁最后死去,pi选择了moving on,他说生命轻轻一跃,只丢掉一两件不重要的东西,他说自己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读后感(四):Pi的一生
不能不说,先看电影再读原著这种认识文本方法会造成先入为主的阅读定位。同时,又因先看电影,读者阅读至故事结尾也失去本应震慑心灵的悸动——这导致阅读快感缺失。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较之原著《Life to Pi》(或翻译为“Pi的一生”更贴切)难免有所改动,但我相信电影的改动更体现导演自身对文本解读。拍摄电影时,导演对原著删减,展现原著某部分内容的详略也体验了这一点。
单看电影,我曾被这短短两小时却涵盖宏博内容的电影所震撼!电影里涵盖了对宗教,信仰,人性,观念的思考,与其说是一部让人闲逸轻松地观赏的历险电影,不如说是一道以3d视觉盛宴作幌子包装精美的哲学命题。我内心的确因这电影对李安产生敬畏。我原以为他既是导演,又是故事编剧,心想是何等境界才能把庞大命题纳入一百二十分钟内?观影后感,就像凡人在克利须拿口中洞察宇宙而一阵晕眩;又像原著中形容宇宙和信仰关系的比喻,我总能感觉梵天撑破“电影”外衣。语言无法涵盖只能以信仰力量意会的宇宙,实在不能尽道,于是通过电影优雅展现,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及后阅读原著,才知道作者是扬,马特尔。李安正是喜欢扬的作品才执意拍成电影。虽然实际情况与我的理解有差距,但内心仍是对李安导演充满崇敬,读了原著,才体会把这样的作品搬上银幕要不失深层含义实在不易!
先看小说的叙述视觉和叙述主线。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觉,叙述主线有两条。第一条是以作家“我”拜访Pi先生,寻找“让你相信上帝存在”的故事作主线,叙述视觉是作家“我”;第二是以中年的Pi先生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作主线,叙述视觉是中年的Pi先生,叙述视觉仍是第一人称“我”。这部分故事可分三小部分,先是讲述少年Pi在印度治里对宗教的虔诚和热忱,描述Pi自身信仰的萌芽和认识,接着是讲述沉船事故后,少年Pi和孟加拉虎“理查德.派克”在太平洋上的求生经历,最后讲述少年Pi历经227日漂流在墨西哥获救,并接受日本货船公司人员对沉船事件调查。以上就是小说的文本框架。
作者视觉,作者不一定等同于叙述者“我”。
作者意图:确立故事的真实性。
小说的叙述视觉选取,定位了作品叙述故事的局限性。小说并非以全知视觉进行叙述,对事件、人物的描述和评价都以叙述者“我”为主导。纵观小说,第二主线的故事所占篇幅最广,读者不得不聚焦于中年Pi先生的对生活经历的回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一主线的叙述者作家“我”,只是偶尔加入对“中年Pi先生”的居所、饮食习惯、家庭成员的观察描写,努力凝造小说人物Pi先生的真实性。同时,作者扬也在小说序言里交代了小说创作背景,极尽其力渲染故事人物真实性,让读者把文本中的作家“我”与小说的作者扬等同。假切要建立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等同这一关系,从而凝造故事真实性,作者便没有在第二重故事的叙述中加入自身的评论。同时,作者也避开“元小说”的写作方法,更没有在叙述第二重故事上运用全知视觉,在这里,作家“我”充当了中年Pi先生的听众,以及往后交代日本货船公司的信件以及调查事件的录音记录,均能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
i先生的视觉,每个人复述事件必然加入自身对事件的理解与认识,复述就是故事。
作者意图:是少年与孟加拉虎相依为命的海上漂流,抑或是海难者充斥血腥的屠杀求生?
电影和原著都以中年Pi先生为叙述视觉讲述自身于海上漂流的故事,以Pi先生回应日本货船调查人员原话:“每个人复述事件必然加入自身对事件的理解与认识,复述就是故事。”因此,故事的真实性永远是难以考证的。然而,故事到了最后,作者也独具匠心借Pi先生之口,向我们再度叙述另一个没有漂流吃人岛,没有老虎,没有斑马的故事。这一部分在三百多页的原著中所占篇幅大概仅有三页,在120分钟的电影里所占篇幅也仅有10分钟不到,而正是这一笔让小说脱离了简单俗套的冒险故事,同时联系了原著前半部,使读者联系宗教和信仰对小说再度审视、认识。
也正是这一笔,让读者后背发凉,原充满奇幻色彩的作品瞬间涂上血腥色彩。令读者震惊心寒的阅读预设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因为我们都认识所谓的“现实”,我们就像日本货船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不相信人能与老虎海上漂流227日仍能活着,我们不相信世上存在夜间湖水变为强酸的吃人岛……我们不相信故事,因为那不真实,我们只满足于事实真相。
但真实,又是什么?
真实对于我们而言,真的如此重要吗?
故事藉此再度轮回至宗教信仰之上,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没有亲眼见过上帝,但是他们能从世间万物中感受到上帝的神迹;伊斯兰教徒信奉真主安拉,任何时候,穆斯林也不忘感激真主神恩浩荡。信仰,凌驾于事实之上,形成解读世界的语言,构建了教徒所生活的世界“真实”。在少年Pi的眼中,经历海难后,他和猛加拉虎理查德.派克海上漂流227日,在漂流旅程中土狼先后咬死斑马和猩猩,最后老虎咬死了土狼,老虎还吃了另一个法国海难者,最后,没有依依话别,理查德.派克上岸后离开丛林。——这就是真实。然而,读者不难发现,Pi叙述的两个故事都能找到对应点:断腿的斑马与截肢的水手;咬死斑马和猩猩的土狼与杀死水手和Pi的母亲的法国厨师;咬死土狼和吃掉法国人的理查德.派克与杀死法国厨师并吃之的Pi先生。作者生怕读者不能发现这一关联,还刻意安排日本货船调查员对此进行讨论……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类似的关联伏笔比比皆是。小说卷首也借中年Pi的角色说过类似的话——“我总是想象动物们穿着人类的衣服,有着人类的社交圈生活……”
当然,当人连最基本的生存也难以保证的时候,便会“异化”与兽无异,但“异化”所不能泯灭的是良知,正因此厨师毫不反抗地面对Pi的屠刀,也正因此经历违背伦理的漂流经历也异化成充满奇幻色彩的海上漂流。即使是为了生存,为继续活着的理由能为杀戮,为违背教义(杀生、食肉)找到合适的借口,但是良知永不卖帐。你要问上帝于何处,你要问神在何方,我会告诉你,神在心里,他是我们每个的人的良知,他是每个人对是非对错,对善恶美丑的明辨准则。以精神分析学角度而言,良知、神、希望是“超我”;理查德.派克就像是Pi的“本我”,他是纯粹的欲望,是食欲,是活着的欲望,正因为有这股最原始的欲望相伴,Pi才能找到生存的动力,“如果没有理查德.派克,我根本活不过来。”正因为有危险相伴,才迸发生命的动力。也正因为人存在原始欲望的“本我”,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我,我们的心内无时无刻均有野兽相伴,而仰望神的高度,构成了俯瞰自我的“超我”,那才是一直守护着Pi一生的神,幻化为化为不同的宗教构成Pi的信仰。因此,我认为不少解读者把电影和小说中的“理查德.派克”仅仅解读为为人类潜在的“兽性”也有失偏颇。
读者视觉,面对Pi叙述的两个不同的故事,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
作者意图:真实与事实,你的选择构成了属于你的真实。
小说到了最后,我们也面临选择。获救后的少年Pi向日本货船调查员叙述了两个不同色彩的故事,调查员最终选择了前者,并作了相关调查报告。而当作家听过中年Pi先生的叙述,作家也最终选择了前者,原因是:“因为故事里面有老虎。”
那么,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故事?
人类的相信与接受,并非界定于现实与事实真相。故事更接近现实,更接近我们经历知识层面上的真相,只能说更“可信”,而“可信”只是性质,“相信”却是选择。你可以穷途末路仍内心保持乐观,因为你相信希望;你可以受尽挫败仍对明天有着信心,因为你相信未来。相信,是一种信仰,只要你的信仰在,路就在,“神不许诺光荣和福乐,但他保存你的信心。”
信仰,是每个人的选择,就像读者之于故事,就像虔诚教徒之于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