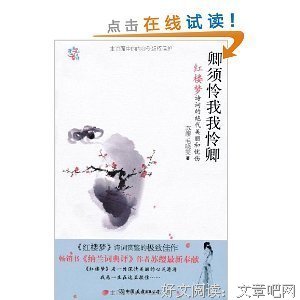
《卿须怜我我怜卿》是一本由苏缨 / 毛晓雯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卿须怜我我怜卿》精选点评:
●还不错~文艺范加上红楼~
●眉间微蹙,唤作颦儿。她的娇嗔,只有他懂。他的感觉,只有她知。知音?恋人?有谁知,有谁晓?那一首首的诗歌,是谁的咏叹调?是谁的悲戚歌?枉凝眉。枉凝眉?
●喜欢编排 钦佩一个人写出来了几个人的人生
●年轻的时候挺喜欢,岁数一大发现都是些啥玩意,年轻真不能看这些,影响三观。
●关于宝钗的解读十分有智慧。非常值得女生读的红学评鉴类书籍。
●初中、当年觉得,会写诗的人,真好啊
●有点堆砌辞藻的脂粉气,不过对一些诗词中用的典故有详细解释,倒给了我这种文盲提供了便利。
●1 很多东西即使有注解我也不能够全然理解,有时候读书,看到书中人真切的痛楚,感觉不到,其实也算是辛酸之事啊。2 书上说,一部《红楼梦》就结束在它开始的地方。突然就想到过去大头说的那句“当我们走到一定地点的时候,一定会回头。好像来回牵扯总是离散聚合。 3 最近不想再读任何悲情书了。
●女人的心思,男人总是很难读懂啊,权当欣赏吧
●感觉没有纳兰词评得那样好,毕竟每个红迷对书中的诗词都有自己的理解,过多的去解析描述反而失去了诗词的意境。不过作者的古典文学修养还是让人拜服的,文中有一处写到作者学生时代效仿红楼女儿集结诗社,遇到了初恋学长后来共结连理的故事,看来中文系才是演绎古典才子佳人爱情的圣地,诗词唱和情愫暗生,令人心驰向往的一场风花雪月……
《卿须怜我我怜卿》读后感(一):在Briarcliff中葬花
在疯人院Briarcliff中,一个形容枯槁的女子挥着锄头挖坑,一个小坑,挖了很长时间。她朝里面放入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满满的花瓣。填好土之后,她洒了一把泪,自言自语:
花开易见落难寻,一杯净土掩风流。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她继续对着风儿说:我是天上的一株仙草,因受了神瑛侍者的露水,今生还与他一世的眼泪。这时跑来一个圆脸男人,嘴巴里含着一块石头,大叫:看,这是块宝玉!我从小就含着,别人都没有。瘦削女子拍拍他的头说:你奶奶喊你回家吃饭了。男子塞给她一块手帕说:有点冷,看你都流鼻涕了,擦擦吧,这送你了。
不远处的桥头,另一位身形匀称的女人心里暗骂:贱人就是矫情!一阵春风吹来一堆柳絮,落得她满头白发。她甩甩头,对着天空大喊: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她继续对着风自言自语:我选择男友的标准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本科也要是清华的。含玉的男子在去奶奶家的这桥头问她:最近读什么书?她对着风说:文学名著--《读者》。
《卿须怜我我怜卿》读后感(二):读中随感
在读苏缨的《卿须怜我我怜卿》,是一本评析《红楼梦》诗词的集子。如果这也算是再读红楼的话,应该已经第四遍了吧。
不得不佩服,《红楼梦》的确是一部有着太多寓意可挖掘的旷世奇书,每一样摆设,每一场对话,每一首诗词,都似是埋下了深远的线索,能引起人们无穷无尽的猜想。多年来,以破解《红楼梦》为业的“专家”不计其数,对此书的研究大概直到中华文明毁灭的那一天才会结束吧。
只有一点很奇怪,这次读《红楼梦》,脑中一直回响着某个人说的一段话,我记得是在《访问》中看到的,但不确定是哪一位被访问者说的:大概意思是,中国人的格局仍然嫌小,所以写不出像《百年孤独》那样气势磅礴的文字,即便是被文人们奉为圣经的《红楼梦》,也还是透着局促的小家子气。
我爱拉美文学,胜过很多所谓“大师作品”的英美文学,却从来没想过要将之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相比较,也许在潜意识中,根本就觉得两者是从完全不同的人文历史中孕育出来的,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再想深一层,是不是也有一种自卑,觉得自家的作品被自己人赞誉到天上都好,却走不出国门,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都拿不到。国民们大可以安慰自己说:咱们的作家写作并不为拿奖,但是否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思想高度始终无法到达世界的层面,物质超出别人一百年又怎样,境界仍然落后五百年。。。
这种自贬而悲观的论调,看在一众“愤青”们眼中,又是大逆不道的罪吧。我常常在反思,或者说,是试着慢慢去了解不同种族人们的分歧,了解得越多越发现,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他们仍然一无所知。中国人吹嘘着自己早已能用开放的眼光、包容的胸怀去认知世界,同时也愤怒地指责世界不肯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理解中国。。。且不论对方是不是愿意来做这件事,我们中国人,难道就真的认知了世界了么?
笼统一点说,我们都是带着阶层和隔阂的烙印成长起来的,这种共性在绝大部分本土作家的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曹雪芹先生更不用说,本身就处于“封建社会”,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所以我们的作品常常让人感觉,虽然已经使上了百分之二百的力气,却仍然憋屈得要命,历史总是沧桑,伤痛总是彻骨,爱恨总是揪心,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像是裹在了厚厚的水泥层中,动弹不得。
有时候倦极了为了避开这些“沉重”的文字,我宁愿逃匿到港台的“迷乱、轻佻、放肆”的文学氛围里,纵然他们夜夜笙歌,今朝不知明日,至少肉体是自由的,爱得无所顾忌,堕落也很美丽。如果将世界文学打个比方,我觉得,欧美文学就像雍容华贵的贵妇,拉美文学像狂野不羁的吉普赛女郎,亚洲文学则像蹙眉敛额莲足微露的小家碧玉,美则美矣,却不好去抛头露面的。
也许与生俱来的东西确实很难改变,欧美、拉美有某种我们不可企及的传统,民主、自由、博爱的观念从孩子出生起就被灌输,而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教导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学的,净是些“有用”的东西,当某一天面对的是“有用”的东西没教过而“没用”的东西没学过时,就茫然而惶惑。这样一颗只装得下眼前方寸之物的心,怎么可能跳得出世俗的框架,洒脱自如地享受生命,写出令人灵魂飞奔的文字?
犹记得很多年前读盗版《百年孤独》的时候,书的装帧很烂,翻译好似也不太通顺,情节也记得不清楚,但心是自由的、狂喜的,暗道竟然有人能这样穿梭过去未来,摒弃性别、年龄、肤色、种族的分歧,超越宗教和信仰,跨越生死的界限,肆意而热烈地活着,心中之火就这样被点燃。。。相比之下,似乎《红楼梦》带来更多的,是对人性的理解,却不是生命的原动力吧。
《卿须怜我我怜卿》读后感(三):梦断红楼第几重
离恨无情天,总累有情人。世间万象,惟人最苦。因有情,故觉人生有限,生命无常;因有情,所以如我饮水冷暖自知,纠结于痴痴眷眷缠缠绵绵之中。人间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切的生离死别,一切的哀怨忧愁,全因这一个“情”字。
曹雪芹瘦死西山,对月浩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百年如一梦,解说者络绎不绝,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所有这些评述,可有谁了解曹雪芹的“痴”,明了曹雪芹的“味”?人生况味,乃自独得,他人若想穷极细微,无异于西西弗推石上山,终属徒劳无功。但这不代表我们只能阅读,不能深入,不能赏鉴和探究。
《卿须怜我我怜卿: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就是这样一本赏红楼世界,探曹公况味的书。作者苏缨以一个女子特有的细腻巧思和曼妙文笔,深情款款地带领读者慢慢走入大观园女儿的生活,领略海棠诗社那不复再有的美丽诗意,赏鉴她们写下的一首首洋溢着灵光和忧伤的诗行。不敢说作者到底得了曹雪芹的多少真味,但这种书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尝试和努力,于情于理,都应该给予肯定。
在卷帙浩繁的有关《红楼梦》的书籍中,这一本还是值得一读的。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这书印制精美,让人看了不忍释卷,而是它确有靓丽之处。
苏缨是一个女子,一个多情、哀伤、敏慧甚至有些锐利的女子。这样的一个女子,打小就浸润在古典的书香里,五六岁就阅读《红楼梦》,并呆呆地痴迷于钗黛华美悲情的诗词,咀嚼得满口生香,把玩得深入骨髓。即使不能深谙其中三昧,也算是有了起码的赏鉴资格。因为,纵观有关红楼的赏读书籍,大多是男子所为,一般不谙女性情思,没法设身处地地掂量和点评金陵十二钗的悲剧人生,即便写得繁花似锦,但终归隔了一层。而苏缨,一个无比聪慧的女子,从一个女子特有的情感维度去赏析大观园女儿们的诗作,这种切入方式本身,就占了很大的性情优势。虽然难免有私人化的情绪宣泄,但以情解情的新颖视角,也算是解语,还是能带来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
人生自是有情痴,梦断红楼第几重?红楼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长长的梦,是曹雪芹苦心孤诣地为我们创造的一个美幻的梦。在这个缭绕云端的梦的宇宙,到处都是风流的种子,处处皆是因情惹来的孽债。风月霜涯、琉璃绿瓦,不是人间富贵花,这梦,在醒来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不过是一场过时的花事,一堆破碎之花。似幻似真才最真,如梦如幻才是幻。因因果果,循环轮回,前世今生的情,此生此世的累。谁能说得清是是非非,分得明来来去去。那么多纠缠,那么多断肠,其实,全为着一个“情”字。这个字是进入大观园女儿世界的钥匙,深入她们内心隐秘地带的不二法门。苏缨抓住了这个字,用这个字去理解她们的人生,她们的命运,也就理解了曹雪芹的良苦用心。
林黛玉的桃花诗,薛宝钗的柳絮词,琴妹妹的怀古绝句,不管如何美艳,因了有情,因了多情,都落得一个凄艳的结局。身世如水流,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对情之苦,情之累,也体会最深。所以才懂得惜花葬花,懂得天地的无情常在,人生的凄凉不再。也因此,对宝玉的爱怜,她会以死相报。卿须怜我我怜卿,在浩渺无垠,无法穷尽的时间的灰烬里,这一点脆弱的怜惜,或许是这蜉蝣人生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大荒山青埂峰是梦,警幻仙境是梦,贾王史薛是梦,大观园的女儿国也是梦,一层一层的梦,一层深似一层,云山雾障,烟花缠绕,问这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突围,能够勘破?不舍得,就放不下,就回不了头,就得活在痛苦活在轮回的梦幻里。
如破碎之花委身大地,他们的爱情,她们的人生,终究尘埃落定,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