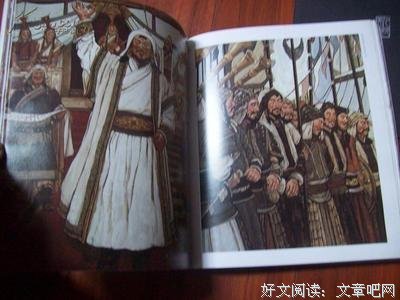
《成吉思汗蓝调》是一部由Roko Belic执导,Paul Pena / Kongar-ol Ondar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美国盲人唱者学了呼麦去图瓦找存在感的故事。跟成吉思汗啊神马的没有丝毫关系好么!
●语言形容不了的震撼,呼麦让我泪如雨下,它呼唤了我的灵魂。音乐才是真正的人类语言。
●老美图瓦历险记…Paul靠听cd学会了呼麦!!!太牛逼了吧
●图瓦是蒙古乌梁海部落的人 ,而这里说的速不太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大将军
●什么碰撞都不比文化碰撞刺激,什么文化碰撞都比不上音乐文化碰撞带感。音乐很棒!
●〃我放牧的九十匹骏马 ——我的九十骏马呢,肯格瑞 我生活的九旗人们 ——那九旗在哪呢,肯格瑞〃
●如果没有最后半个小时,这部电影就没有现在的光彩夺目,充其量就是一部记述音乐交流和Tuva人生活的纪录片(兼论到冷战后的政治),但最后这段纪录大大丰富了电影的维度,而且paul的形象大大丰满起来,使得这部纪录片脱离了简单的猎奇。国内的独立作者应该好好看看这部片子。
●wow!
《成吉思汗蓝调》观后感(一):原汁原味
我有这个影片的全部文件,非常喜欢,非常想要的童鞋可以豆邮我。当初是在电驴下载的,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载。
快速通道http://www.douban.com/note/142245187/
《成吉思汗蓝调》观后感(二):电影之外,唐努乌梁海
以音乐相交,音乐无国界。
但音乐、情谊之外,我反而更加因为Tuva(图瓦)而触动思绪,如今的中国人还有多少记得唐努乌梁海?中学的历史有提及的(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历史还有没有说这个,因为在文天祥等人都可能被剔出中学课本的今天,我是很担心以后很多历史人物、事迹和古代国名地名都消失在我们的课本里!)。可是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唐努乌梁海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经属于中国的版图,是谁把它生生分裂了出去?罗刹人。一个不断鲸吞蚕食我们领土的贪婪无止境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引以为师、看作铁杆好友?今天你无视它的威胁,并不断助长它的强大,明天,它就可能成为葬送你的坟墓。
当人与自然共处共融的时候,总会充满各种美好的声音与旋律。。。但愿我们常能发现。。。
对蒙古人的“呼麦”有着浓厚兴趣。加上听说本片曾被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并被选为台北电影节观众票选最佳影片,所以即使还没有机会观赏,也要推荐。。呵呵
转一篇名为袁越写的影片介绍
《成吉思汉布鲁斯》
图瓦人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灵魂,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就是它们在说话,从山谷的回声到河流的水声再到牲畜的叫声等都无一例外。这些自然界的声音都有着复杂的和声。为了更好地模仿这些“语言”,图瓦人的祖先发明了“喉歌”,其特点是:喉咙在发出一个音高恒定的低音的同时,把此音的某个泛音有选择地放大,使人听起来就像是两个音在同时出声。唱“喉歌”的高手还能够任意变化这个被放大了的泛音,甚至能唱出一段旋律,听起来就像是有个笛子在吹一样,十分奇特。
这是一部纪录片,主角是一个居住在旧金山的名叫保罗·皮纳(Paul Pena )的美国黑人。他是个布鲁斯歌手,在美国没什么太大的名气。皮纳是个盲人,又有些胖,影片一开始就用不少镜头描述了他独自一人去街角小店买东西的情景。看着他拿着手杖颤巍巍地在阴冷的旧金山街道上行走的样子,不免让人对他产生出一丝同情。
1984年,皮纳从苏联的短波广播中听到了图瓦族的“喉歌”,他立刻被吸引住了。从此他自学了这种演唱技法,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演唱当中。当一个图瓦族代表团于1993年来美国演出时,皮纳为代表团表演了自己的“喉歌”,把那些图瓦族歌手镇住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美国会有一个黑人能唱“喉歌”!皮纳和团里的一位主要歌手,也是当年图瓦族歌唱大赛的冠军孔噶奥·翁达(Kongar-OlOndar)成了好朋友。翁达邀请皮纳去图瓦参加1995年举办的图瓦族“喉歌” 比赛。
这件事很快被一个年轻的电影导演罗科·贝利克(RokoB elic)知道了。贝利克看了多年的PBS,并从PBS 的旅游节目里认识并爱上了广漠的中亚草原。他自学了俄语、图瓦语等许多语言,并决心要把那里的生活介绍给美国人民。贝利克大学上的是一所电影学院,因为他很小就喜欢电影艺术。当他知道了皮纳的故事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主题,便自愿跟随皮纳一起去图瓦比赛,并担当皮纳的翻译。
翁达把皮纳请进自己的家里作客,用上好的图瓦酒招待皮纳,还领着皮纳走遍了图瓦的山山水水。皮纳是个盲人,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之处,翁达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耐心地照顾皮纳。两人经常在一起唱歌,切磋技艺,而且他们唱歌时互相是那么地默契,隔在两人中间的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种族的差异,地位的差异等等统统不存在了。就这样,一句英语不会的翁达和只会几句图瓦语的皮纳在“喉歌”的帮助下成了好朋友。皮纳再也不寂寞了。
皮纳真的去参加了图瓦族的“喉歌”比赛,并得了Kargyraa唱法的第一名。但更重要的是,皮纳赢得了最受观众欢迎奖。当皮纳在台上弹着布鲁斯式的吉它,用刚学会的几句图瓦语现编了几句词,再用“喉歌”唱法唱起一首图瓦民歌时,台下掌声、口哨声不断。图瓦人从皮纳身上看到了世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而皮纳则从图瓦人身上重新找回了艺术生命,找回了青春,找到了信仰。
这部电影为图瓦文化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图瓦文化不再只是一种复杂的唱法,一种新奇的异国风情而已了,她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没有依靠金钱,没有依靠政治,而是依靠人类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图瓦文化和世界文化终于在人类的共性这一点上取得了和谐的统一。
2005年保罗·皮纳去世
《成吉思汗蓝调》观后感(四):如果远方呼唤我,我就去远方
每次看到关于民族的东西,总是会搬好小板凳好奇的问艾江。
艾江觉得好奇怪,我怎么突然研究起哈萨克族来了,其实并不是研究哈萨克族,是对所有未知与不熟悉的感兴趣。
特别是当我真的了解到“消失”这个词语时,从他人镜头中看到实实在在的事物不会存在时,感到“虎躯一震”,就像楼兰古城一样,就是沙漠中的一粒随风而逝的沙子,灰飞烟灭,就算有这么多的书籍、影视资料,我依然无法能够切身体会它的美,哪怕古今中外至今都对它的消失保有超高的研究热情,它的神秘,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想一探究竟。
难道它的神秘,不是因为它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它的过往全都埋葬在了时光里,我们只能在时光里想象它的世界吗~?
消失真的很可怕,历史上消失的事物实在太多。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哈萨克族朋友当时告诉我决不和外族通婚的说法,必须“血统纯正”,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封建,大清朝早就灭亡怎么还这么保守,但此刻意识到这不是保守,这是他们用他们唯一可以做到保护自己族群的方法,是他们世世代代守护族群在这片地球家园上繁衍生息的方式。
我是拥有人种最多的汉族,是不能理解人口数量四位数,五位数民族的害怕感。但是这不能成为我简单粗暴的偏执己见。所以我不会再去偏执的嘲笑艾江关于民族的说辞。
少数民族不但人美,他们能歌善舞总能让我成为小迷妹~
上周看了一部关于音乐的纪录片,也是LP群的小哥哥推荐,据说很感动,我反正是被感动了~
一直以为呼麦“喉音”唱法是我国内蒙古少数民族独有的唱歌技巧,后来了解到,呼麦不止是蒙古族独有,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内蒙民族也会这种传统唱法。
我从网上了解到呼麦是图瓦共和国的民族音乐:
图瓦人的文化特色较鲜明地表现在音乐上:他们拥有世界其他民族少见的“呼麦唱法”,即利用喉头压力产生不同频率的泛音,使得一人能够同时演唱多个声部。
上网又搜了很多关于呼麦的音乐,谈不上十分喜欢,却也觉得好奇,如果说古老的中国祖先是用石头图画去描述他们看到的世界,那么图瓦族就是用呼麦歌颂他们的地球家园,呼麦的唱法实在太神奇,《贡嘎》、《极低》纪录片中也有呼麦的音乐出现,于是我把片子又撸了一遍。
当我再看第二遍时,发觉镜头开始时随着音乐在切换不同的画面,以为是摄影由于第一次拍片的结果,再看明白就是片中的主要人物以及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的由来。(这部片子的导演是两兄弟,拍摄纪录片完全是业余,片中所有的人都是业余人员,比如引导保罗一行从美国飞到图瓦共和国的组织者就只是一名修理工~啊哈哈,没错,树枝修理工,戳中我的笑点,团队成员全是业余,按照当事人的是说法就是个怪咖团队,搞笑的是,其中一个电台老炮儿开心到心脏病发差点命丧图瓦~ ... ... 很多搞笑的点~)
aul pena是美国的一位盲人blues吉他手,片子最后有说保罗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是怎么学习图瓦语言。图瓦语是没有词典翻译的,不像我们中文可以有中英译文词典,图瓦语是没有的,而保罗是用一个特殊的盲人扫描仪把每封信扫描出来,生成一系列盲文码,把图瓦语转换成俄语,再把俄语转换成英文,最后用英文生成盲文语言。
所以在开头的几个画面中,其中有一帧用手指触摸盲文的画面,结尾拍摄的保罗顽强学习图瓦语有所呼应。
虽然是盲人,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眼睛的看不见而缺乏发现美的心,空闲时间的他总是会用他的短波收音机搜索各种外国语课程学习,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无意中搜到了一波莫斯科的强烈电台信号,里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不是平时他所听到的声音,这种奇怪的声音是他第一次听到。
好奇心永远是所有美好故事的开端,因为对这种声音的好奇,保罗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探索。尽管有好奇心的驱使,寻找的结果却始终无果,保罗只得把最后的神奇魔法棒指向住所附近街角的一家“环球音乐”的小店寻找,意料之外的惊喜永远是在你不抱希望的那一刻,所以才会让我们又惊又喜,保罗和店员的交流中获知这种音乐的来源可能是来自图瓦。
那一刻,从亚种跨越太平洋吹来的风将在不久的将来营造一段跨国情谊。
每件事情的转折总是会因为另外事件的起因,当保罗的太太因为疾病离世后,保罗陷入大半年都处于恍惚状态。意识不会让你沉迷太久,保罗某一天突然想到曾经在广播中听到的图瓦音乐“呼麦”,于通过在街角音乐店买到的图瓦音乐碟片,跟着CD一起保罗学会了图瓦语言。
保罗参加的图瓦“喉唱”比赛中,他用自学的图瓦语演唱赢得了场下持续不断的掌声,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保罗唱完歌准备下台时,有人给保罗献花,我没有想到的是只有一支花,不是一束花,我不知道这一支花代表着什么,我会脑补很多,比如当地经济,比如观众的喜爱,而保罗拿着那支花,一直离场都没有把它给到别人,那一刻,我意识到:保罗怀着赤诚的心到图瓦,有幸参加当地歌唱比赛获奖对于积郁的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无关乎奖项,这是一种认可,一种对音乐赤子之心的认可。
看到这我不得不叹一口64年的老气,这个奇妙的世界就是这么神奇,往往那些被上帝亲吻过的人,总在无意中给我们这些被上帝亲手捏制的完人狠狠一棒槌。
所以我经常会觉得,鸡汤也真没有那么的令人恶心,在现实世界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惰性如影随形,就比如我本来准备周末更新这篇稿子,我上周就看完了,可是因为懒,觉得加完班后实在太累,想休息,于是就躺在沙发上想象自己是个没有脑子的“大白痴”,内心独白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总要休息,休息,一休说的,休息一会儿”,但又有另外一个声音不停在说:“包子都说他现在看不起你,你不是他的偶像了,”看吧,总想做好,总想天衣无缝,总想事无巨细,可往往事情的进展总不会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总是不会完美,总是有缺憾。
刚下班的路上,看到《三日为期》新更新的一篇关于拳击的文章,题目我很喜欢:我想做一次英雄,哪怕只有十秒。
谁还不是努力活出生活新鲜的模样了~
四月份去了趟四川,想着好久没有睡沙发,于是在豆瓣找了个沙发主,很高兴一开始就能顺利遇到接待的沙发主,于是安心在重庆玩了几天后就直奔成都,当时也没想太多,毕竟相互都是陌生人,说了点工作,谈了下人生观,世界观,然后互道晚安,匆匆一晚,第二天我就去往色达路上了。
就此一过,知道她是位公职人员,朝九晚五的工作后会去录音棚和小伙伴们组队录歌,有时候会去参加演出,四川实在是一座音乐城市,九眼桥下的流浪歌手总能唱到心间,我也就没太在意她唱歌这回事。
没想到她不仅唱歌,还自己写歌作曲,并且今年还有幸与一位音乐大佬学习,看着她谦卑的发着朋友圈的照片,我着实被感动到。
她每一次的默默都潜移默化给予了我很大的力量,想到今天中午和同事聊天,说到我写的公众号,我说,我现在尽量整理自己的逻辑不让感情太充沛,不止一个人说过我太过于碎碎念,感情戏太丰富。
结果同事很肯定的说:看了一圈,其实你写的是我会有想看的,其实你的风格有点类似把与自己相关的事情用文字进行描述,有点类似在写故事,所以对于吸粉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我个人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风格不用换,真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需要刻意去粉丝养成,你的目的就是记录,你就记录就好,说不定慢慢就形成了你的风格。
被这样的话语着实温柔了一把,不求结果,享受过程,你看,哪怕生活糟粕,还是有人在吟诗对唱~对不对~
还是要加油,虽然一把年纪说加油二字实在好丢脸好没出息噢,但一想到黑暗中总有人举着一把明灯,就感到前方一片光明。
下次一定要去看你现场,我们还要好好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