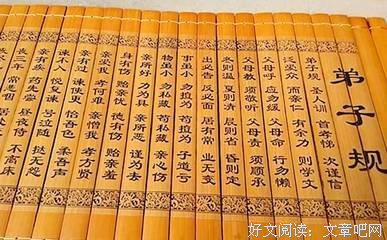
《陈旧人物》是一本由叶兆言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书收录了数十篇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小品文,其作者叶兆言是叶圣陶先生的孙子,所以书中许多掌故旧闻都是鲜有人知。民国是传统和现代、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等等因素对立又交融、互相建构同时又互相消解的沉重时期,而作者却努力用小品文这种轻松的形式展示这一时期人物的复杂性。写潘汉年早年混迹上海文坛那篇令人印象深刻。
●三星半
●八卦
●又见西南联大,惭愧居然在昆明居然没来得及朝拜
《陈旧人物》读后感(一):消闲之作。
消闲读物,不过在只言片语中叶兆言对现代作家的品评更有价值,特别是对一些形成思维定势的作家,从作家的角度去谈作家更有意义。例如对沈从文的评价,只要看过沈从文全部作品的都知道,1949后他的不写作政治只能是背景,主因还是他在1947年左右已经进入了瓶颈期了,可惜总有人一叶障目。 PS,上海S姓作家给胡乔木抱怨没书房,其实这房子得到后他转手给了儿子。
《陈旧人物》读后感(二):从《陈旧人物》想到《安持人物琐忆》
我看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其中有几篇还挺感兴趣。一篇有关吕叔湘,另一篇是王泗原。感兴趣前一篇,是因为原来知道这是一位语言学大家,但此文说到了他在语言学之外的一面;后一篇的王泗源我不知道,但他做的事情及其做事情的场景却让人有所感。
挺想就此写点什么。为避免“抄书”时往里敲字,先到网上去找,发现有关吕叔湘的一篇网上确实有,而且还被作为中学语文课的阅读篇目(“读完完成第11-13题”)。想一想还挺有意思:一个当代作家回忆一位现代语言学家的文字,被作为语文课的阅读材料。但仔细一看,这篇“阅读材料”是经过节选的,我最感兴趣的部分都被“节”掉了。比如文中引述老先生1980年代末期为《沙漠革命纪》所写题记中有关中东冲突根源的一段话就被删掉了,但这段话却真的非常能够显现老先生的人文关切和清醒认识,拿到今天看仍然很有启发意义。
有关王泗原的一篇网上也有,而且也是中学语文阅读篇目。但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篇文字本身,而是文中所描述的王泗原当年写作《古语文例释》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为此我到学校图书馆专门借了这本书想看看(原想买一本,但对自己阅读文言的能力实在没有信心,所以就想先测试一下:如果行,那就买一本),但一翻之下发现,叶兆言在文中所讲的使我最为之所动的内容——1970年代初期从干校回来,文字形成过程中与叶圣陶老先生的互动(非常感人),最后形成洋洋40万言——全部来自该书的“自序”。
我有些沮丧。不是对王泗原老先生的书,而是对叶兆言的文。叶兆言是叶圣陶之孙,我一直以为,有了这一层,《陈旧人物》以及《陈年旧事》中应该更多一些直接感受,少用一些“剪贴板”。说起来,这样的要求可能有些高了,即使有家庭背景做底,毕竟这些人、这些事的发生时间还是超出了作者的生活场景。
于是我想到了《安持人物琐忆》,作者陈巨来,述说清末民初文坛(书画界居多)大腕旧事。两书放在一起似乎可比性不大,我这里只是想说:“道听途说”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亲历亲为”沉淀下来的内容。这里不妨推荐一下:《安持人物琐忆》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八卦书,一本信息量很大的八卦书,一本带有很强作者主观色彩的八卦书。你不能将其作为“信史”来看,但可以帮助你揭开那些名人对外着力营造出来的公众形象,还原一个个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场景(顺便说一句,书中人物我最感佩的是袁克文)。
当然,这样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当下中学语文的阅读材料。
《陈旧人物》读后感(三):乱七八糟笔记之,陈旧人物钱钟书
读叶兆言《陈旧人物》。坐着读,躺着读,翻到哪页看哪页。睡前回忆起有趣或有味的段落,觉得心满意足。
每篇都是写人,文人,旧时文人——但不限于作“文字”之人。从康有为到施蛰存,从齐白石到陈寅恪,作者用功之深,交游之广,让人羡煞了他的好时代和好身份。
也写钱钟书。从论文答辩上老师借《围城》,谈到如何选择钱钟书作为毕业论文。中途,叶先生来了这么一句:“毫无疑问,我太好高骛远,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钱钟书的粉丝。”心中一惊,倒回去看作者生年,是在1957,写作时间是在2009。掐指一算,叶先生写此文时已年过半百,何以用到“粉丝”这样的新潮文字?又写,别人问起为什么《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他“喋喋不休解释,一次次强调,一次次叫好,”“完全像一个拉赞助的。”又是扑哧一笑。有趣有趣,莫不是我水瓶座?年轻时卖弄新潮,尚在情理之中,人到中年仍然能够毫无生涩地使用它们,作者非得有份年轻的心才行——至少,要爱这个世界。
上次交笔记,谈乌尔斯·弗劳希格《莫扎特说话了》。老师红笔在旁批注:“太天龙八部了!”这才发现自己搞怪搞得老气横秋,实在算不得高明。所幸的是,在那些小小地方,倒有些潇洒。
去年我也写钱钟书来着,看了好些资料好些文章,杜撰了钱先生灵魂赴瓦普吉斯看群魔乱舞,探访魔鬼老朋友,途经成都,与小帅谈《纪念》,救我于作业之水火。有人批评有人鼓励,有人被气得吐血,有人一笑了之——仅作无赖嘴脸搪塞过去。钱氏大家,非我等小儿研究得的。但看不到山的全貌山的精要,看看山上一颗果子的晶莹剔透,也是有意思的。顺便提一句,小帅偶像有俩人,一是眉山苏东坡,另一位就是先生了。
另外,今天修改某同学的《消失的音乐季》,长难句看得我触目惊心,改啊改啊改,小朋友难过得差点哭起来。年少时不懂长句的可怕,如今读到长达一百五十余字的句子,才知道老师所言不假。不怕,不怕。只要心灵活泼不僵死,一切都容易。
老师递给我这本书时说:“拿去读,慢慢读,反复读。”阿弥陀佛,但愿我能有这样的耐心。
小帅的乱七八糟笔记
《陈旧人物》读后感(四):话说浙江人当年在文坛有多厉害——《陈旧人物》摘抄
叶兆言的《陈旧人物》,他说也可以把“陈”当作动词,也就是钩沉旧人物。确实,书中所列各位无论当初如何轰轰烈烈,拿到当今都已经“旧”了。但是,即使是旧人物,身上也总有些东西让今人扼腕、敬佩、或者忍俊不禁。所以,我就当一把文抄公,供大家欣赏——当然,最直接地,是你找书自己看。
这是第一段,话说浙江人当年在文坛的厉害。
近代史上说起一个人对地域的影响,首推曾国藩。人杰地灵,有了曾国藩,便有了后来源源不断的湖南人才。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能和湖南人叫上板的,大约也只剩下浙江人了。记得沈从文曾发过牢骚,说湖南人倔强木讷,怎么都得过精明的浙江人。他说这番话,是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正是蒋委员长得意之际,手下养着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浙籍大将,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个个都是手握重兵,炙手可热。湖南人有感而发,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不会这么说了。国共争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手里,湖南人终于深深出口恶气。出水再看两脚泥,历史最后证明,还是湘人厉害,以毛泽东领衔,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胡耀邦,竖起手指数数,有一大串。
熟悉这些掌故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既是中心,又是风口浪尖。秦琼卖马,对处在愤青阶段的人来说,这段经历非常重要。毕竟是世界观形成阶段,有这个开始,才有后来的正果。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史书上说,毛经常去旁听蹭课,深受高人启发指点。蹭课听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长知识不用怀疑,变深刻也理所当然,感觉中他一定会有些郁闷,因为听来听去,都是些浙江口音的人在讲课。
当年的北大,差不多就是一个浙江村。先说大学校长,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任源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像蔡元培这样堂而皇之、好玩一把同乡会的倒也不多见。在现代教育方面,蔡元培差不多就是祖师爷了,他取消了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据朱偰先生回忆,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比一半还多的是浙江同乡。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后来又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此后许多年,各省的大学校长和历任教育部长,按照朱希祖先生的说法,都是“蔡先生振拔之人”,所谓“枝叶扶疏,弥漫全国”。浙江人果然厉害,文武俱佳,一百年前已经证明。今天北京的浙江村居民,与当年同乡比较起来,口袋里银子会多一些,说到文化要逊色许多。竟然有这么多的系主任,清一色的浙江人,恐怕连地处本地的浙江大学,也不敢这样无所顾忌的放肆。当时北大系主任中,做头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而诺大的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同样是浙江同乡会。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阴线鄞县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日后名声很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那年头像他们这样的浙江人,也就是中文系跑跑龙套,一个讲授中国小说史,一个讲授新文学和东方文学。
说到近现代教育,蔡元培之外,还有一个浙江人章太炎绕不过去。这两个人都是光复会的领袖,都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作出巨大贡献,到民国之后,又都把精力转到教育上。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可忽视。蔡元培的门徒是教育界的权贵,章太炎的弟子则是文史方面的精英,是各大学国文或历史系的主任或名教授。一代通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与蔡元培乐意关照同乡一样,章太炎的弟子也多为浙江人。一九三六年,太炎先生逝世,其弟子十名联名呈请国葬。这十大弟子个个都有头有脸,都是显贵,以朱希祖为首,然后是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自然又是浙江老乡占绝大多数。
以上文字来自“朱希祖”一篇的第一部分。这里顺便考考你,下面这几个字怎样读:朱偰,夏元瑮,鄞县。
《陈旧人物》读后感(五):僵死的往昔
人的过时,一方面是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是陈旧的思想。说起来有些令人沮丧:一旦被落入“历史”的长河,人似乎就会如同阴暗斗室里的古董沾染上灰尘,或如长久不吃的水果渐渐散发腐气,稍许靠近了些都会令人掩鼻而走。除了那些专业研究者们还会凑近而些瞧瞧这“发酵过度”的滋味如何,有些本是亲近的后代或许都表现出些许嫌弃之情。这并不需要诧异,正如克尔恺郭尔在批判柏拉图时所说:
他将认识之能力归于生命之回忆,于是人生的旅程竟成了追溯的航行…回忆是反方向的重复,那只是僵死的往昔…好一个僵死的往昔!人文学者们如同盗墓者一般将这些尸体挖出来,疯狂搜刮着他们身上还算有些价值的知识,尤其是当无法处理所谓“现代性的困境”时,就会如同花光了钱的孩子向父母伸手要钱。这并不是说孩子不够努力,孩子不该要钱——只求索取,不求回报,似乎并不是好的后代应有的行为。
扯远了。这里只想聊聊这些陈旧人物。故事的来源是叶兆言先生的《陈旧人物》,记载的是生活在动荡时期的文人艺术家们身上的故事。也许你会认为这些故事对当下的生活会有某种启示。不过这不是我选取这些故事的原因。我仅仅觉得有打动我的地方。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想了想,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他坦白,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然而可以一边失败,一边继续做,因为不仅从成功中能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刘半农被《新青年》据稿,因为他学识太浅,这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于是就去了法国苦读六年,混了个“语音学”博士的头衔;钱玄同则是刘半农的好伙伴,他在语言学上比刘半农更加离经叛道,主张废除汉字,走拼音的道路。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课,很少有学生选修,因为过于枯燥无聊,分数也给得抠门。有时候空旷的教室只有桑个人,他还是要点名。他是个平和又认真的人,30年代鲁迅来北京演讲,偏偏拒绝清华,作为清华系主任朱自清一定觉得没有面子,但他仅仅在日记里写道“访鲁迅,请讲稿,未允”。穆时英是一个很会炒作自己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儿小四的味道——他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一开始受到学校生活的影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些闯荡江湖的平民,动不动就张口骂人,用的是不良少年的视角,这种粗犷之气在当时颇受女生的喜欢;成名后,他开始流连于舞场,以“体验生活”为名到处放荡,艺术成为了无耻的挡箭牌,声色犬马,结果越走越远,也越来越浅薄,最后成为了无聊女读者们的玩物。周瘦鹃在解放后日子过得还不错,兴趣从小说转移到了盆栽,可没想到文革开始后,他的花园被夷为废墟,诗文书画尽失,之后在园中投井自杀。这种事大概太多了,如同弗兰克尔描述集中营中的一个故事:一个退休官员恳求长官保留他的那些荣誉勋章,结果长官当他的面全部焚毁,这个人当场疯掉了。作为陈寅恪最好的朋友,吴宓是个书呆子,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传言因为听说昆明有家牛肉馆取名叫“潇湘馆”,他提着手杖一顿乱砸。另一方面,他对世上一切女性都有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热爱。他带着学生上街,从来都举起手杖拦住过往车辆,让身边的女学生先走;虽然物价飞涨,但他还是要带着心爱的女学生去下馆子;最荒唐的是为了女学生作弊,自己翻译了文章在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推荐出发发表。陈寅恪的学问自然不用说,其悲惨的晚年总是令人叹惋。他当年在德国留学,后来又在法国和瑞士读书,一战结束后去了哈弗攻读三年,最后又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据他女儿回忆,这些日子陈寅恪每天都待在图书馆学习,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并没猎取过任何学位!他的学问实在太深,掌握了近20中语言,中年双目失明,后期著作完全凭借记忆,在研究水平上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李叔同只是一名普通的兼课老师,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国文,英文,绘画,钢琴,演戏,几乎无所不会。他是中国最早画油画的,第一个画女性裸体画,创办了最早的话剧社,书法被称为一绝,几乎在每个领域他都做到了顶峰。可在别人都倾慕的地方,他停下了,选择成为一名和尚,成为了弘一大师,在佛学上也做到了第一流。他的伟大之处非常简单,就是认真——他做老师的时候,有同学摔门,他便守在门口,有谁又摔门了他理解追上去请求他不要再这样做,然后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同学们都说他的鞠躬比什么都厉害。另外有一次,学生透了东西,学监问他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学监先向学生认错,因为学生偷东西,是老师没教育好,然后宣布偷东西的学生出来认错,如果不认,老师将自杀谢罪。说道做到,并不能欺骗学生。学监考虑半天,还是不敢采取。李叔同以身作则,处处严于律己,说明做一个徒有虚名的教授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真正的先生。沈从文患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抑郁症。1949年,面对生计问题,他不得不接受命运给他提供的令他方反感的东西——政治。他此生最大的寂寞是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再写了,生活中忽然什么也没有了,努力了半天也写不出来,终于在文物研究上取得了成就,算是一种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