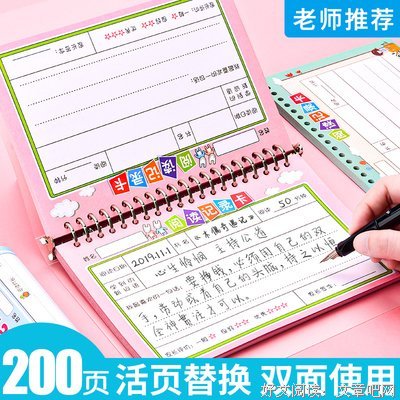
《叙事的胜利》是一本由[加] 罗伯特·弗尔福德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2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叙事的胜利》读后感(一):在叙事中书写叙事
最近比较集中地遇到“叙事”这个词。当然之前也很讨厌总遇到“宏大的叙事”这个词。因为高频的出现,却空洞而且不知其意,就像一个标签一样,不贴上就显得不够专业,所以各种文本充斥着宏大的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我们从各种媒体里都会得到各种形式的故事。流言、传说、新闻、小说、广播、电影等。这些叙事将我们框在一个框架中,既可以让我们通过故事书写和构建我们共同的故事,同时也由于我们自己不满足故事的内容而不断添加自己虚构出来的故事情节,构筑谎言或者虚幻,包括新闻在内。我们可能被教育着用同一种观念看历史,阐释历史。也会用约定俗成的期望来评判小说、电影。一种叙事方式也有它的生命周期,从一开始的被迷恋到最后被批判并摒弃,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被创造出来。但讲故事的方式是始终不变的。我们需要故事创造出共同的想象,来保持互相依赖结成群体,确保文明的持续,甚至是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我们不能迷恋叙事的绝对真实性,因为我们也是不靠谱的人,会因为欲望而回避真相的存在。我们总是相信我想相信的。作者还是很乐观的认为,现代媒体的应用让故事的密度更大,它让“我们变得更好了:叙事给了我们一种体谅他人的方式。但它也有负面作用。让我们自鸣得意,相信自己了解的比实际了解的更多。它有办法操纵我们的意识。它会误导我们”。
《叙事的胜利》读后感(二):“叙事”使我们成为人类
每天都有很多故事诞生。它们或者从世界的另一端通过信息流巨大的媒体传递而来,或者来自胡同里摇着蒲扇的老太太们的口口相传,或者来自我们案头的某本故事书或者某个经典电影中,抑或者,它们就藏在我们记忆的某个无意识的角落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越来越多的鸡汤文开始在我们社交媒体的时间轴上横行。它们用看似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讲着直击心灵的大道理。它们制造共鸣、制造观点,甚至制造事实。我们每天在信息流中,读着这些或真或假的故事,感悟着它传递出的焦虑或者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自己的日子。
而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也变成了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文体”。越来越多的笔端开始从宏大历史转而关心众生世相,在克制情感中力图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从个体经验中表达时代经验。个人生活的深度挖掘和历史范式的宏大广博交织纵横,在行进式的叙事里无限探索并抵达着真实,疏通着文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我们比祖辈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吸收各种各样的故事,因此叙事成了我们生活中基本而不可替代的需求之一。这些故事或真实发生,或想象虚构,或者,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它究竟来自哪里。现实混沌柔软、模糊难辨。叙事这个动作由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共同完成,携带着我们熟知的生活和我们未知的深远,给这些故事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罗伯特·弗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中教我们听故事,讲故事,他穿越由都市传说、杰克·尼科尔森、《艾凡赫》、纳博科夫、性丑闻与闲谈,以及《罗马帝国衰亡史》构成的奇妙图景,将半个世纪以来作为记者和批评家的经验浓缩成了一部论述人类生活与故事之间相互塑造过程的著作。在那些来自交谈中的,尤其是我们讲述自己和我们认识的人的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中,强调不受拘束也不被认可的叙事形式的价值,把自己日常应用于文学的认知工具带入业余的故事讲述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讲故事的方式。但是这“文学的民间艺术版本”,在人们的生活中,永恒地神秘和重要。
《叙事的胜利》读后感(三):人类生活和故事相互塑造
文 | 潘文捷 ,来源:界面新闻APP“一周新书推荐”
https://m.jiemian.com/article/4724583.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杰克仅凭一次引诱就向上跨越了几乎六个社会阶层,这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情节,那么《泰坦尼克》这样的故事在叙事的历史当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批判《飘》等多部作品当中存在种族歧视的今天,你是否好奇,这些流行的关于权力关系、社会、历史、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方面的理论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不妨从《叙事的胜利》一书寻找答案。本书是被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指定为“梅西公民讲座”讲师的罗伯特·弗尔福德进行的五场讲座内容,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总体上是对“讲故事”这个主题进行的一次探索。
弗尔福德被誉为加拿大“第一流的文化记者”,在本书中,他从不同的角度讲解了叙事的历史。比如第一章指出了流言的叙事基础,把流言与精致的虚构相连,探讨了人们在建立自己身份的过程中所捏造的个人历史;第二部分讲述了历史学家如何用宏大叙事和历史范式来描绘文明的进程;第三章探讨了新闻学以及都市传说的文学形式;第四章讲述了相对主义时代、怀疑和不确定时代的故事讲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并且讨论了在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等人影响下的后现代学术理论如何让“教授和学生们都变成了警官”;在全书的最后,作者讲解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艾凡赫》如何一直矗立在叙事性大众文化的背后,成为这种文化的开创者和灵感来源。听故事、讲故事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人类生活和故事相互塑造的过程,让读者获得对于叙事的不同视角和理解。
《叙事的胜利》读后感(四):叙事经历种种挑战后的胜利
从流言开头总是吸引人的,尤其这个流言是大作家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影射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与他好友之间的私情时。与流言进入文学中相对的是用叙事来虚构自己的生活细节的人,这被调侃为“传奇小说家”。「虽然人是喜欢“象征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但叙事比分析更能模仿现实的演变。」
近年来宏大叙事被质疑,因为宏大叙事不可避免地站在叙事者感到满意和舒适的角度来建构历史,采用简单的概述、用来支撑自己的理论,而往往有曲解和错误。比起宏大叙事,现下的历史注重的不是权力中心而是边缘、不是强者而是弱者。宏大叙事会去寻找历史范式,寻找必然性,因为寻找范式总比承认历史中的随机性来得不那么让人痛苦。但是叙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评断,而且叙事就暗示着故事的结果已经预先注定,读者就不容易试着去理解在当时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中人们的生活状态。
* Bowdlerize 删改一词来自 Bowdler 教士,他剔除了吉本著作里对基督教的所有批评和他认为不道德的段落。
都市传说,比如肾脏失窃,是出现在转发和震惊体里的常见叙事,是人们用来解释世界、安顿自己恐惧感的方式。在都市传说里,人们获得的好奇感削弱了怀疑的态度。新闻也是从这种好奇感开始的,新闻逐渐变成叙事,会被剪辑、被虚构,发展出来“新新闻主义”,也就是后来的非虚构文学。
不可靠的叙述者,是从现代主义开始用相对主义的怀疑一切的眼光开始看待生活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将文学视为政治的,比如狄更斯对女性生活的伤感描述后的性别歧视,在文学批评里它反对威权主义,但这种反对的文风常常也变成威权的口吻。在这种后现代的批评里,社会观点已经被立好了左翼的方向,从而文学被权力关系、社会、历史、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话语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共识里,叙事是欺骗,因为世界不是由开端、结局和中间部分组成的,如果要虚构,那必须是完全自觉的虚构。
司各特的《艾凡赫》里的骑士精神,影响了许多创作者,从小说到电影创作。这种“叙事的伟大成就在拟真”的理论被攻击——布莱希特提出间离效应,强调演员在表演。纪录片的出现也是否认虚构叙事。而先锋派开始颠覆叙事本身,以及戏访戏访的叙事。出现了电影明星,他们的人设也变成了叙事。
《叙事的胜利》读后感(五):囊括一切的“叙事”:从吹牛、坊间传闻,到电影的陈词滥调
作者罗伯特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化记者。本书旨在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不仅仅是作为写作者职业的叙事,还是人一生经历到的叙事:关于自我、历史、文学、时政,等等。
章节的题目便足以引起读者兴趣。实际上,在每一章节中,还会提出叙事的一个或多个有趣的特质。文章并不拘泥于形式:既非文化记者式的分析报道,也不是论文写作,它们是作者“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写下的思考。不仅仅每篇切入叙事的角度的洞察十分精妙,为这种洞察收集资料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对既有“知识”的阐释的方式也十分新颖有趣。
一
叙事最初的形式,便是“言说”:将我自己或其他人的事情说给另一个人。我们在对事件还原的努力中,理顺思路,在重现事件的过程中,将回忆固定下来。“Stories are how we explain, how we teach, how we entertain ourselves, and how we often do all three at once.”
叙事将过往的生活重新构建,并赋予意义。这种特质也使得有一些人用虚假的叙事代替真实的生活,吹嘘他没做过的事情。“Narrative[…]has the power to mimic the unfolding of reality.” 在虚假的叙事中,他希求的事物得以实现。
这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真正经历的生活能与我们读到的生活“竞争”吗?“Is it possible that being continuously surrounded by compelling stories makes us uncomfortable with our own less impressive tal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通过信息媒介,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精彩的故事,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则显得愈发平淡和无趣。
相比起其它的几章,这一章结构没有那么紧凑,谈论的也不是学术界关心的要点。但作为第一章,它意图展示叙事与生活的交互。一方面,人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理顺生活,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把生活与“故事”比较,“叙事”影响着生活。
二
如今,当人们说起“宏大叙事”时,往往持批评态度。
宏大叙事曾将“神”从人类历史的叙述中剔除。历史的发展不再是神的旨意、向着神指定的方向发展。“人类理性”替代了神。
人们不得不为过往,为历史寻找理由,让过往具有“意义”。上帝死了,他们找到的替代是:一切都在向着“文明”“理性”发展。历史有着固定的发展模式,中国、印度、西欧,都遵循着这一模式。这种对历史的叙述,以汤因比和吉本为代表,被写入课本,成为一代人所认为的“真理”。
而今,随着“宏大叙事”被批判,这种对历史的认识也成为过去:即,拣取一些被认定是“文明演进的重要参照”的事物,用来标识历史阶段的叙事。什么是“Civilization”,什么是“Humanity”,不再是确定的。与汤因比和吉本时期的确定性的姿态相比,“no serious writer in our time deploys so much easy poise, so much certainty about his ability to reason towards an authoritative conclusion.”
三
在《街头文学与新闻塑形》一章中,作者首先讲了一些“坊间传闻”和“都市传说”。虽然它们缺乏真实性,但却体现了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环境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的需要。“The urban legend parodies our desire to have the world explained in the form of stories.”
紧接着,作者开始追溯“新闻写作”的历史。18世纪,伴随着新闻业的发展,读报纸“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People don’t actually read newspapers. They get into them every morning like a hot bath.[…]Journalism was creating a new human desire: the hunger for fresh stories about current events.” 人们对“传闻”的渴求在空间范围急剧扩大。与远方的人类的连接感成为了一种“必须”。
新闻业开始有了它自己的规范:比如记者在报道时不能表露出他主观的倾向等等。新闻报道的形式越来越固定,帮助了新闻业的标准化和产业化,但事件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却被减弱。
一些记者开始探索新的新闻写作的形式,将新闻与“creative writing”结合,其产物,简单来说的话,大概便是国内近来十分热门的“非虚构写作”标签下的作品。我们熟知的“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大体上都属于这一类别,国外则发展得更久,比如《邻人之妻》等作品。
将新闻写作与坊间传闻并提是有原因的。其意图便是强调它们的共同特征:为了传播而牺牲的真实性。在具有故事性的新闻写作中,往往会把发生在一个情景的细节替换到另一种情景下,以取得更深的共情。乔治奥威尔在新闻写作中,就曾将同一天同一地点看到的事物用到两个不同的他并没有经历过的场景中。
五、
叙事可以成为一种“模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方面,相同的叙述在不断重复其本身,另一方面,这种一直被重复并强化的叙述,反倒成为了一种现实,或能够影响现实。
作者拿电影作为例子,无论是《泰坦尼克号》中自我牺牲的杰克,还是西部片中惩恶扬善的牛仔,这些角色的行为都符合一种“预期”。这是一种普遍人性角度上的“预期”。它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人性不再是“不可理解的”。无论是中世纪,罗马时期,火星人,还是铁皮人,童话里的稻草人——无论背景如何,“人类”的情感有了惊人的相似性。而“大众传播” (narrative mass culture)中的人物行为所遵循的逻辑,在200多年间都有着相同的叙事模式。
这种模式化的叙事也影响着现实。浪漫主义小说的叙述中,“骑士精神”的话语就被延用到了美国南方“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在宣传话语中,描述士兵遵循着与描述骑士相同的词汇,南方也被称为“她”——一个要骑士去守护的美好的女性角色。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想象被嫁接到南方战士的英勇的叙事上。
――
一切都是叙事:有关个人,有关历史,有关时政,一切都是思考的对象,并无高下之分。思考因此面对着一切,也依靠着叙事,叙事将经历固定化,为历史赋予意义,让现实成为浪漫的。这就是一个文化记者经历着的叙事。
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很不错的。书中最宝贵的不是干巴巴的知识或理论,而是不受限的写作形式中迸发的许多奇思妙想,包括对材料的排练组合。比如第二章中关于汤因比和种种趣事;第三章中提到新闻业的历史、《Times》杂志的发展、作为记者的乔治奥威尔;第四章提到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不可靠的叙述者、纳博科夫的作品;第五章中从美国南方的历史谈到电影等等。看似没有边际的漫谈,实际上总是紧密结合着每章的主题,一环扣一环地推进,引导思考。引述资料时不仅含有对它本身的评述,还推进着对主题的探索,兼顾着趣味和深度,这无疑需要十分深厚的写作功力。
不过,前面说过,本书的书写不基于一个单一学科关注的特定问题,形式十分自由,因此包容了许多作者“灵光一闪”式的智慧,使得它读起来十分有趣,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一些局限或遗憾,在作者的思考不全面、或欠缺深入的理解时,这种缺乏深思熟虑的写作则显得浅显,有时甚至显得无知或偏颇。
对于我来说,阅读本书的另一部分乐趣来自于,能了解到作者罗伯特作为一名成功的文化记者所拥有的“基本功”,比如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书中时而流露出的,他对记者的报道式写作的不满也非常有趣,比如,他抱怨说,新闻写作要把信息尽可能地放在第一段,极少有读者能跟进到最后一段,新闻仅仅供读者粗略地扫一扫,最大程度地获取信息——仅仅有这么一丁点的价值。这些絮语和字里行间外的信息对于同样想从事文化记者工作的我来说是很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