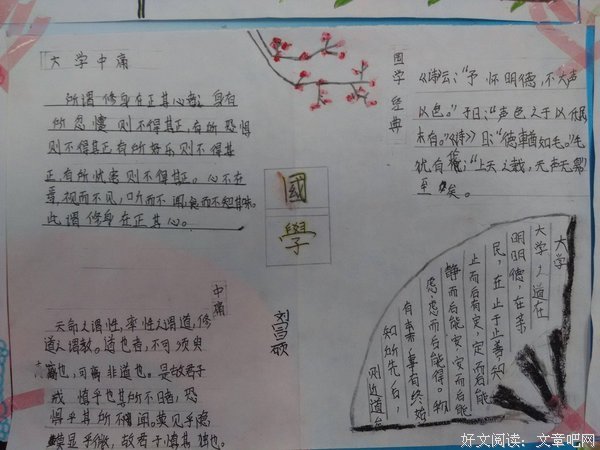
《年轻人的国文课》是一本由张一南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书是依据张老师在北大“大学国文”课程上的内容整理而成的,简单得理解,大学国文是北大开给偏理工科院系的通识教育课。这一事实导致这门课在相当多的理工科学生看来像政治课一样,是为了毕业需要应付的东西。因此能够激起学生听课兴趣并对国文产生继续了解的欲望就显得十分重要(当然我相信张老师也尽量使其内容严谨了)。大学国文课程一般由两个板块拼接而成,比如我当时选修这门课时选的就是李娟老师的“语言学”和张老师的“古代文学”的拼接课程,两位老师各负责前后半个学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李娟老师的课程全程都是语言学干货,但学生们的参与度并不高;而后半学期,同一批学生却在张老师的课堂上表现了更高的热情。张老师的国文课也在校园内成为了大家选课的一个热门(开设大学国文的老师很多,就像开设高数课一样),张老师也在有趣之余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有了更切身的理解,或者说激发学生产生了脱离文本本身的带有自我意识的思考。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张老师的这门课在现有的北大通识教育课程的范畴下已经做的相当不错了。
当然,上面的褒奖也仅限于“现有的北大通识教育课程的范畴”。当这些讲稿成为了一本书,它便脱离了上面的原始语境,受众群体大为扩大。但是我认为以“年轻人”(年轻人普遍对国文缺少兴趣)为受众时,其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否定的。就像我们总觉得《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在书里满嘴跑火车,但假如没有它吸引人的文本构建,当代年轻人更有可能对明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报以更大的冷漠与偏见。毕竟这书写得再有小毛病,也远好于民间口耳相传环境下年轻人能获得的知识。
《年轻人的国文课》读后感(二):春风东来忽相过——年轻人的国文课
我讲的情商,就是史部,是教君子做事的;我讲的文艺,就是集部,是教君子作文章的;我讲的识见,就是子部,是教君子思考的。”
记得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讲一个警察向福尔摩斯大谈莫里亚蒂是如何博学:“他用两个电灯就给我讲清楚了公转和自转(大意)”。
科普的作用大概就是向零门槛的人说清楚一个比较恢宏的主题。可以说天地,也可以说人心。
譬如当年林庚先生所著《西游记漫话-林庚》的#大家小书# 系列,譬如张一南先生讲的这本《年轻人的国文课》。
张先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说“有趣”不免有些轻慢,但还是希望用这个词来形容她的谈笑风生。一个人文学者放下身段而为小书,图穷匕见,敢有自己的观点;金针渡人,敢有自己的态度。各种话题信手拈来,恰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素日里觉得正襟危坐也有些捉襟见肘的话题 ,举重若轻,令人轻叹缓带轻裘,概莫如是。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于是到了门口,张望一番。
王世襄的公子王敦煌要学字,启功要他自己去读贴:喜欢谁的字就学谁的。张先生选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随手选的这些篇目排在一起,渐渐有了它们自己的灵魂。”
为什么去学习,自然文艺载道,自然薪尽火传,但自然,是因为这些文章是如此的美。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其实这些美丽的篇章,是如此的绰约多姿。道德文章,其美如斯之盛。持诵吟唱,首先就是为这种美停留,甚至炫目而迷。
于是“欲穷其林”,于是“歧路亡羊”。
于是在门口张望之后,又将如何?且不说抵达彼岸,岸在何方?
“培养君子的情感模式的;是教君子做事的;教君子作文章的;教君子思考的。……我想要教给学生的这些书,原来无非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士人,或者说,怎样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类。……我希望,凭借我传递给他们的观念,我的学生可以在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一些。”
用一句朴素的话来讲,读书的功用,甚至无妨用功利这个词,就是让读书的人像“一个读过书的人”:
凡此种种,不过就是希望成为一个君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或者用古人的话讲:境界。
诚哉斯言,善哉斯言。
这样的境界可以从我们熟悉的故事中来。
王力先生说过:熟字俗典容易出错,因为常以为已经了解,所以不会翻书也不会觉得自己不解。讲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还得要靠讲故事的人见过的陌生人要更多。
多到何数?数近无量。
所谓熟悉,不过颠倒。颠倒之后,见贤思齐。
这样的阅读究竟能带来什么,自然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但总有一点可以莹然在握,齿颊留香:
汉语毕竟令人迷醉。
你将再一次因为汉语是自己的母语,而感到庆幸和骄傲。
《年轻人的国文课》读后感(三):自序 我就这样写了一本国文讲义
犹记从社科院向北大调动的那一年,我攥着一张商调函,连工作证也没有。看着我从大一的小孩子一路长大的教务老师“闵大爷”递给我一本《大学国文》课本,说:“你去上课吧。这本书讲肯定是讲不完,你自己挑着讲讲。”
就这样,我开始在北大讲课了,做上了我一生最向往的工作。
我妈说:“我怎么觉得你跟魏敏芝似的?”我说:“还不如魏敏芝呢,魏敏芝还有个村支书去介绍一下,我们系书记都不搭理我。课堂都是我自己找。”我妈感叹曰:“你们北大不光对学生天才教育,对老师也天才教育啊。”培训是不可能有的。
我没受过师范教育,只不过爸爸妈妈是老师,我又从小爱给小伙伴讲故事。后来读博士的时候,我因为特别想当老师,有意训练自己,在社团里办过好多讲座,所以在博士生里还算是会讲课的。可是我毕业去了社科院,没有课讲,“宅”了五年,等到回北大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都快不会说话了。
当时我很怕在课堂上丢人,怕助教师弟觉得,回来的不是那个会讲课的师姐了,更怕对不起选课的弟弟妹妹们。正好当时工作的事还没定,在社科院也没什么事做,于是我决定写逐字稿。最初一版讲稿的写作,陪伴了我那一段寂寥又有些惶恐的日子。
翻开由我的老师和师兄编订的教材,我猜测着他们选入每一个篇目的目的。这些篇目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既然反正讲不完,那我就只挑我喜欢的讲。我挑的篇目都是在我成长过程中留下过深刻印记的,所以我想我的学生也有必要知道这些。那些我当年读起来就头疼的篇目,我就悄悄地舍弃了,算是藏拙。又因为我的本行是中古文学,所以我选的篇目难免会偏重这个时代,其他时代的作品我也有选的,那往往是让我有过特殊感触的。
在拼凑讲课提纲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随手选的这些篇目排在一起,渐渐有了它们自己的灵魂。它们先是汇聚成了几个主题,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人情,关于事理,关于文辞。它们在提示我,何必按课本讲呢?
想想我当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很少有按课本讲的,因为课本是学生自己可以看的。我又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学生,在老师给出题目之后,总爱加上点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决定,把课本抛到一边,按我的主题讲。我决定用自己的视角去诠释这些经典文本,并且加入了另外一些感动过我的作品。
在没有课讲的日子里,我整天挂在微博上。我在这里观察,人们都在想什么,什么话是大家爱听的,什么话又是不能说的。有时候,看到网友说了什么话,我总是会想,这个问题古代文学老师应该跟学生说清楚,这个阅读能力语文老师应该注意培养,想完以后总无非是失落,我什么时候才能教上课呢?现在终于让我讲课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哪些东西是我最迫切要传达给学生的呢?就这样,我在讲义里塞进了满满的“私货”。
我有什么要告诉学生的呢?其实我没有特别高的学问,也没有特别出奇的教学技巧。我唯一的长处,就是在北大听过不少年的课。在北大的弟弟妹妹面前,我自认就是一个课代表,在老师没时间讲课的时候,把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东西传达给他们。老师说的曾经感动过我的话,我一定要再告诉他们;我们那时候的有趣的规矩,我也一定要告诉他们,就像我们那时候高年级学生给大一学生的启蒙那样。
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传统。所谓传统,就是高年级学生想要告诉大一新生的那些事。校园有校园的传统,文明有文明的传统。之所以想要让那些事传下去,是因为那些事曾经陪伴过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让我们决定要让后面的人也体验一下。不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有资格成为传统,只有那些让每一代人都决定要告诉下一代人的事情才是。
而我在这里,无非是做一张滤纸。传统从我的生命中流过,就像几千年来曾经从无数读书人的生命中流过那样。我会想要让我曾经感受过的美好继续流淌下去,会把这些告诉比我更年轻的学生;而那些曾经令我不快的,我想把它们挡在我这里,至少不急着告诉学生们。我的讲述,其实也是选择,我这一代的选择。只有完成了这一次的选择,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次的传承。
感谢北大的同学,给了我比胡适之更高的礼遇,没有把初登讲台的我轰下来。我的课程意外地受到欢迎,竟然成了不太容易选到的课,在学期初不太忙的时候,教室居然会坐满,甚至需要站在过道听课。这实在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教学相长”是真的。在这样的鼓励下,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讲稿。念起来不顺嘴的,改掉;没有响的包袱,删掉;过于卖弄流行梗,离传统精神远了的,删掉;过于私人化的体验,可能会冒犯到某些同学的表达,删掉。每一次讲课,都是一次重新打磨讲稿的过程。
我不知道我把多少同学讲明白了,我倒是经常讲着讲着,把自己讲明白了。我会在讲台上突然发现:噢,这件事的逻辑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这个故事的前情就是那个故事啊,中国历史原来是连续剧啊;这个现象和那个现象原来是一回事啊。我几乎是随机选择的那些篇目,渐渐地凝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讲着讲着,我才发现,原来我讲的夫妇、父子,就是经部,是培养君子的情感模式的;我讲的情商,就是史部,是教君子做事的;我讲的文艺,就是集部,是教君子作文章的;我讲的识见,就是子部,是教君子思考的。原来我讲的这些,还是翻不出古人说的“四部”的手掌心。而且我讲的顺序还是“经史集子”,不是“经史子集”,倒也不愧是从六朝入门的。或许,古人的四部分类法,也是从这样的讲述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吧。
我发现,我讲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君子,或者说士人。我所喜欢的这一切,原来都是士人生活的某一部分、某一个方面。我读过并记得的这些书,我想要教给学生的这些书,原来无非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士人,或者说,怎样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类。
我想,这样我也算是尽到了一个通识课教师的职责了。我传达的与其说是知识,毋宁说是观念。我希望,凭借我传递给他们的观念,我的学生可以在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一些。在我心目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受众群体,我只能传递对他们来说有用的,而势必会牺牲掉全面和严谨。我的观念,显然不可能适应所有环境下所有人的需要。我知道我能影响的范围实在没有多大,我只是努力地多讲一次课,希望能多帮助几个人。
后来,我又不断地接受新的工作,到中国科学院大学讲课,也到网上讲课。我的讲稿不断充实、修改,与最初的几篇课文渐行渐远,而我心目中的课程体系则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稳定。
在我的讲授中,最受学生欢迎的仍然是那些故事。被训练写诗、写论文的我,曾经是多么地鄙视故事这种形式。但是实践告诉我,只有这些故事,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迅速地调动课堂情绪;也只有这些故事,在课程结束后仍能让学生记住,从而留给他们反思的时间。我想要讲的道理,他们也许并没有瞬间听懂,但是这些有趣的故事,会让他们一直记着,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直到有一天,他们再次想起这个故事,明白我真正想说的话。这颗种子还是自带营养物质的,故事会携带很多的文化信息,它把那些枯燥的理论和法则,变成了一个鲜活的文化场景。
在课程的考核中,我也越来越强调“印象”。我不想让我的学生去记忆什么知识点,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形成一个印象,对传统文化的印象。根据这个印象,他们可以编写自己的故事。所有学到的知识,也应该变成这些故事里准确的细节,以及对细节的准确解读。在这样的故事里,他们会实现自己的成长。讲课的时候尽量讲故事,考核的时候注意考“印象”,这是我这几年得到的新的教学经验。
大概,这就是所谓“活的传统”吧。由活着的老师决定哪些话还要继续说,然后让活着的学生带着这些印象继续成长,传统因这些人的存在而存在。没有板着面孔的引经据典,没有皱着眉头的虚张声势,这些活着的年轻的人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融会着传统的精神。如果能这样,传统才算是活过来了。
几年下来,我对这套课程越来越熟悉,但也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曾经的爆款网络话题,竟然已经开始过时了。年轻人的想法,比起几年前,也产生了变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告别这一套课程,去新的领域探险。而另一方面,我仍然希望我的这一套课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决定,把这套讲稿最终固定下来,变成出版物,献给更多没能听到我讲课的同道中人。这是一个纪念,也是一次告别。我将人生中一段快乐的时光封存在这本书里。也许在多年以后,我还会翻开这本书,然后发现,啊,我那个时候就这么想过;或者发现,啊,那时候我竟有过这么荒谬的看法;或者只是追忆一下初登讲台的艰辛和荣耀。如果能这样,也就足够了。
感谢浦睿的团队帮我出书,帮我实现梦想。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年轻人的国文课》读后感(四):北大国文课|君子是怎样养成的?
这本上市不到两周就加印的新书,来自堂堂爆满的北大国文课!
《年轻人的国文课》,是在北大校园备受学生欢迎的古典文学通识课。
作者张一南老师80后生人,她在微博上了解90后、00后,又回到“经史子集”中寻找智慧,传授给学生。
书刚一上市就好评满满,名校学者、微博大V纷纷推荐。
张一南博士以轻松优雅的风格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带读者一步步领略传统文化中的美妙风光。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非常精彩,开卷即爱不释手,虽是普及读物,但以扎实的学问做支撑,很有价值。一南老师是真正的读书人,下功夫,悟性好,也长于表达。《登楼赋》一篇,是我看过最好的解读。
——胡旭(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本书讲文学名著,处处皆有洞见,可当得“通透”二字。
——李天飞(作家,《西游记》校注)
张一南的《年轻人的国文课》里写到了屈原、李密、嵇康、陶渊明,这些不算是顶级网红的古代名士,有一些论断很有趣,值得一读。
——安意如(作家)
年轻人的视角,促膝长谈的语调,令人捧腹的脑洞……《年轻人的国文课》在手,如同亲临现场,远程上北大。
——彭敏(作家,中国成语大会冠军,中国诗词大会冠军)
“原来我讲的夫妇、父子,就是经部,是培养君子的情感模式的;
我讲的情商,就是史部,是教君子做事的;
我讲的文艺,就是集部,是教君子作文章的;
我讲的识见,就是子部,是教君子思考的。”
张老师的国文课上,有顶流圣贤,先秦诸子;更多的则是小众名士,嵇康、李密、曹植、陶渊明,讲述他们的故事,逐句解读诗句,演示这些中古名士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教给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君子。
“我读过并记得的这些书,我想要教给学生的这些书,无非是教我们怎样作一个士人,或者说,怎样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类。”
让我们跟着《年轻人的国文课》,重返北大课堂,看看君子是如何养成的。
1、 君子爱人——心甘情愿,以爱为荣
培养君子,首先培养君子的感情。儒家传统的君子教育,从夫妇开始,“夫妇是人伦之始”。
一切不从诗教开始,不从爱情开始的国学教育,都是伪国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爱情诗,从《关雎》开始。
以雎鸠起兴,因为它在古人心中代表着理想的爱情。古人认为雎鸠是种“挚而有别”的鸟:“挚”就是真挚,是忠贞之鸟,坚守一夫一妻制;“别”就是区别,面对爱情的反应有所分别。
身处爱情之中必然是“挚”的,而“别”就尤为重要:不需要和对方一样,也不强求对方和自己一样,因为爱讲究心甘情愿。
同时,《关雎》本身还是一个君子追求淑女的故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深藏不露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
于是君子行动起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喜欢的东西,就去追求,并为此提高自己的修养,让自己确实有可爱的地方,这是一种贵族精神。这是孔子给年轻贵族的爱情教育。
2 、君子行孝——先慈后孝,层层递进
儒家的思想向来是对地位高的人要求高,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如果你是一个贤者,一个君子,那么儒家要求你的道德是完美的,这叫“责备”。如果你的地位低,就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按照儒家的思想,对“慈”的要求必须比“孝”的要求高得多。
所以《弟子规》就凭“弟子规”这三个字,就违背了儒家思想。儒家,先讲“慈”,再讲“孝”。
那在父慈的前提下,君子该如何孝呢?其中又有个层层递进的顺序。
首先是《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首先要求珍爱自己,好好活着;
然后是《论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孝第二个要求,而不是照顾即可;
最大的孝在《中庸》,“夫孝者,善记人之志,善述人之志。”孝的最高境界就是继承父母的志向,传承父母的精神。
张老师还告诉年轻人,为什么要讲孝,“在古代,孝是唯一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私情。
一个人想要用私情与公权力抗衡的时候,只有抬出孝来。”所以我们得明白,当古人说孝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什么。
3、君子行事——话里有话,懂得傲娇
君子形成了自己的情感模式,就要到社会上历练扛事,这时就需要情商了。君子的情商,具体而言,就是要听得懂别人话里的话,还要会说话。
比如李密的《陈情表》,就是李密给皇帝写的奏章,一封“拒职信”。起因是皇帝几次要任用李密,可李密却不想赴职,他有祖母要照顾。但仅仅讲自己的理由还不够,对方可是皇帝,于是李密恭敬地发了张“好人卡”: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
您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肯定不会不让我行孝、侍奉祖母吧?
比李密“拒职信”更傲娇的,就是嵇康的“绝交书”了。
嵇康的好友山涛要调离岗位,推荐嵇康代任自己的原职。嵇康自由无拘,蔑视礼法,当然不肯。于是他郑重其事地给山涛回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
“……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
总结起来就是:我太懒了。我常一个月或半个月不洗头发不洗脸,不是闷痒得不行,都不会去洗;甚至我躺在床上宁可憋着尿,也不愿意起身……
我真的太懒了——所以没办法胜任你推荐的工作(其实我就是看不上你推荐的那份工作)。
4、君子创作——淡妆浓抹,皆能相宜
君子立足社会,不仅需要情商扛事,还需要创作,有自己的“代表作”。但每个人的创作风格有不同,同样是表达自己的高贵,有人正着来,有人反着来。
陶渊明就是反着来,他以反贵族的姿态成为贵族。
他描写的生活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位著名隐士的居住环境朴实无比,田地草屋,柳树桃树,俨然一个农家小院的样子。
最后收尾他说“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院子里什么都没有,但有的是清闲。大家注意,他的诗,都是大白话,少有格律对仗,这就很不贵族。
自种地,让衣服占了露水,这是不贵族的;但是坚持自己的心愿,不委屈自己,这又是典型的贵族性。
比起不让衣服站上露水,保持自己强烈的自我意识,显然是更重要的事。真正的贵族,为了坚持自己的心意,是不怕吃苦的。
而曹植,作为六朝诗的最高境界,他是非常贵族的。他写诗,讲究修饰,辞藻华丽,情感却十分节制。
我们知道,曹植的一生大起大落,但是他在诗里表达的情感却非常节制,因为他的节制,才越发动人。这是贵族文学的最高境界。
他的《侍太子坐》,写的是曹丕的一场宴会。上流社会的宴会,一不小心就写得跟《小时代》似的。但是一个真正的贵公子怎么写呢,“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
他从自然落笔,从冷色调落笔,“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写富贵(在当时,夏天能用冰,是很奢侈的事),他从清凉的触觉写。最后写道“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在这一片奢华之中,他只看得到一件“清”的东西,是他的哥哥。
曹植还是陶渊明,只是风格不同,诗的内里都带着真实又节制的感情。君子写诗浓淡皆宜,但总能传达出心里最动人的情意。
5、君子思考——诸子百家,各有见识
君子培养好了情感模式,到社会上有高情商来扛事,后来又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这些已经足够立身扬名了。那接下来还需要干嘛呢?接下来就是总结人生经验,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识。
“见识”是传统的说法,一般来讲就是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它的叙述不那么文艺,主要在传统的“子”部里,也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见识。
虽然诸子百家流派众多,但都是传统文化的不同分身和显影,也就是君子士人在不同情境下的思考方式。
儒家是个士人,讲究礼义廉耻,专为“高富帅”服务
道家像个神仙,看惯古往今来,专为“学霸”服务
阴阳家是物理学家,研究天体物理学
法家相信人性恶,也为“学霸”服务
名家是礼仪老师,专给人讲名物制度、礼仪规矩
墨家穷酸又高尚,为小知识分子阶层代言
杂家杂七杂八,各沾一点
农家搞农业技术,只为百姓吃饱饭
小说家像群众吃瓜,专门搜集民间故事八卦
派别不同,各有见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其实就是君子在不同情境下的思考方式。
要成为君子并不容易,从感情到情商,从代表作到思想见识,要想知道一名真正的君子的升级指南,且来康康张老师《年轻人的国文课》是如何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