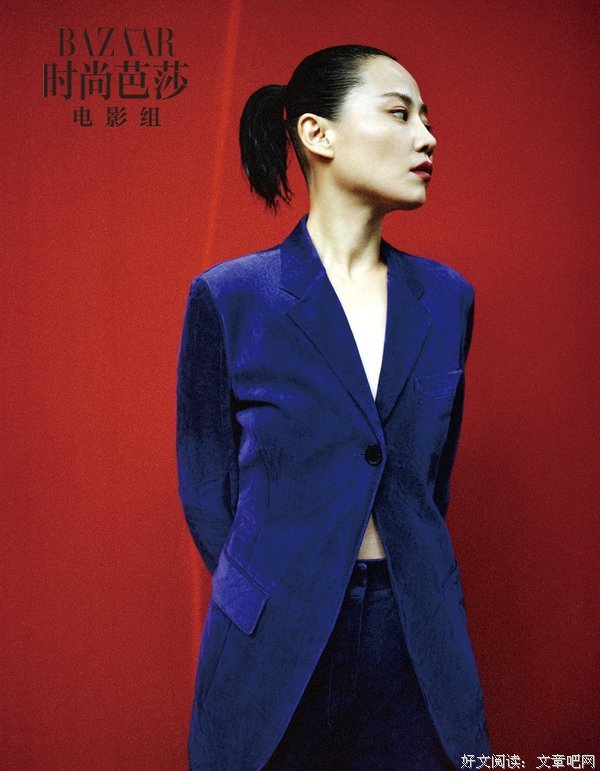
《如梦之梦》是一本由赖声川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8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昨晚关了手机,把《如梦之梦》看完了。第一感觉是,我一定要去看这场八小时的剧!我要看许晴演的顾香兰! 有人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赖声川说,你要通过很多人的故事,才能懂一个人的故事。 人生不就是,从一个幻梦逃入另一个幻梦。在金光闪闪的鸟笼里做梦,你爬过高山,越过大海,你看过最壮丽的风景,但你一次次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在鸟笼里。 死是什么?难道不是你通过梦,去了另一个世界,开始全新的生命? 顾香兰和五号,都在生命中的最终,讲出了自己的故事,讲出了自己的悔憾,讲出了曾经轰烈的爱恋只能留在曾经,多年之后的重逢也无法抵达彼此。 如果有一座城堡,城堡里有一个湖,趴在湖上,你会看见自己,你会去吗? 庄生是我,蝴蝶也是我。
●浮生若梦,如梦之梦。兜兜转转,一个梦境套另一个梦境,一个故事解释另一个故事。走不出,逃不脱。
●赖声川的这出戏悲怆、宏阔而充满历史感,从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的世界视野,类似近年常被提及的“星球文学”(cosmopolitan literature),台词、场景的细节鲜活真切,漂浮着历史和经验的泡沫,在成吨的事件之中,人像幽灵一样回忆和重返,但是却不再有近代意义上的“乡愁”可言,从中可以体验到作者收放自如的、精密中透着酣畅的文本编织能力和情绪收纳能力。最后一幕的千禧年仪式,与序幕中秦始皇求仙的故事对照,加上“庄周梦蝶”母题的不断串引,表明剧作家想要通过这出戏完成一个世纪(甚至是上千年)的象牙微雕。此剧中的“千禧年”之夜的场景已经悬置了“千禧年”在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宗教感,它只是部分地迎合了人们对于世纪末的颓荡、悲哀和缱绻的想象,尤其是在这一个世纪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我们所有、惟一的“现代”
●一场梦不管是一秒钟还是一千年,不会因为它的长度而改变它是一场梦的事实。到底是蝴蝶梦到了庄子,还是庄子梦到了蝴蝶,如果人生是一场梦,那么醒来是什么。
●2020.03.20-2020.04.09 阅读本书
《如梦之梦》读后感(一):杂记
浮生若梦。若梦非梦,
浮生何如?如梦之梦。
书店老师第一时间给我推荐了这套书。后来发现,身边有一些记得你喜欢什么、知道你适合什么的朋友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每日在午睡里挤时间看这本书,一周多,终于在今天看完了。想看《如梦之梦》不是一天两天,但是至今也还是没看到现场版。大学的夏天,现代文学教授课前闲聊,伴着呼呼的风扇,她说她很想买一张机票飞去上海看一场话剧,于是自那一刻起,我便知道,美好的事物不来,你可以自己走过去的。
三个楼层、八个方位、八个小时、三十多个演员、三百多套衣服、三百六十度环绕舞台,穿越两个时间(民国初年、现代)与五个空间(台北、巴黎、上海、北京、诺曼底)。无缘现场,但纸张媒介上形成的场域丝毫不阻止我们进入那个世界。
探索不同艺术形式对于同一内容的表达,是我长久以来乐于探索的。电影与书籍,话剧与文本,在感叹艺术的多元性的同时本质是在感叹生命的丰富性吧。我们,有着发达的知觉能力,直接或间接,无论在谁人的日子裂缝里都能感受世界的冷暖与流变。
对于这个话剧本身更多的思考应该是什么呢?也许,下面这句台词就是我所理解的一切了:幸好人类还有遗忘的本能。
《如梦之梦》读后感(二):愿你今晚好梦
标记读过之后 豆瓣提示这本书出版至今还只有十个月《如梦之梦》好像是一个观剧的里程碑,能看到现场的剧迷一则是抢票经验丰富,二则是观剧的坐功不错。至今没有抢到过《如梦之梦》的票,也没有搞懂莲花池座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疫情期间鼓励消费,绍兴这边投放很多消费券。在曾经的文艺圣地--人文图书里找书时意外发现了这本剧本。
故事整体的时代背景是赖声川一贯的风格。如果拆开来讲,就是几段有缘无分的的小故事吧。因为一些偶然的线索,不同年代的主人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也旁观者别人的故事,如我们一般唏嘘不已。
事物发展在矛盾中前进,人的执念也是在同这个世界的对抗与和解中来回拉扯,难得身处其中又活得通透。如天仙阁吃茶有独特的规矩,可伯爵一来就什么规矩也没有了,或依靠沈先生根本也解释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反之伯爵与顾香兰鸡同鸭讲的十天半个月,两人的脑海里可能都出现了自由的巴黎的样子,并且相信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
剧中,看向城堡附近的湖能看到自己。或者这就像你抛掷一个硬币,由正反面来决定是去做作业还是打游戏一样,在抛出前的一刻心中已有了答案。当局者迷,即便好梦易醒,梦过醒了又如何,总比噩梦好一些吧。
《如梦之梦》读后感(三):如梦人生,活在当下
剧本式的书厚厚一沓却很好读,分别用了两个下午看完。有机会看现场的话,应是很值得一看的。
书中用人物AB角叙事,表达的是不同时空同一人物,即使是阅读,也能深入其境地感受舞台上的交错插叙表达。
开头是齐国庄桁梦中修行的故事,定了整本书的基调。人生如梦,若梦非梦。
接着是牧羊人的故事,引出5号病人去巴黎寻妻,故事就开始了,从台湾到巴黎,巴黎到上海的旅行(梦境),在上海,故事又从三十年代的上海开始,从上海到诺曼底,到巴黎…是梦里的故事,还是故事里的梦,到最后已经不重要了。
5号和顾香兰是什么关系?5号病魔缠身,想在旅途中寻找到病魔的根源。顾香兰,一个旧上海的青楼女子,她生命中的两个的男人,一个是丝绸小开王德宝,一个是有权有势的法国伯爵。
伯爵是傲慢自私的,所以他从对顾香兰一开始的『一见钟情』,成为名流太太,培养她的画画爱好,到后来她在他眼里是『低处』『妓女』,没有令人意外。意外的是这样一个人写了庄如梦的故事。
在巴黎的最后一面,他看到烛台时说『其实对我也没什么意义』,人生若只有初见,点到为止应是最好。
爱情在最开始就达到了最好,怎么走都是下坡路。
王德宝也是如此,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住他的爱情,经年之后再找到顾香兰,此时的顾早已不是彼时的顾。即使没有国内那场活动,想他们回国以后也是柴米油盐,心心念念的遗憾和爱在平淡中磨灭。
书里说,花是奇妙的东西,正在盛开,同时也在凋萎。我正在享受爱情的同时,爱情也在离我远去。
是这样。
故事环环相扣,像是一个轮回,顾香兰死时抓着5号的手,叫他亨利…5号最后找到他妻子了吗?他找到了吧…
结束时是巨大的孤独感袭来。
“其实我们一辈子就好像一出戏,这出戏是我们自己编的。等戏演完了,落幕了,我们可以走出剧场了。”
如梦如戏的人生,活在当下为好吧。
《如梦之梦》读后感(四):浮生若梦。若梦非梦,浮生何如?如梦之梦
说实话,如果不读这本书,我早已想不起文章标题的这句话,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偶尔谈起如梦之梦,总会隐约记得如梦之梦这四个字,似乎是来自于某一个高深莫测句子,但这句子,却早已在岁月的云雾中模糊不清了。
2013年4月7日,8个小时,上下两本,我在保利剧院独自一人观看了《如梦之梦》这部剧。是我人生的第一部剧,我记得剧终是临近当天的午夜12点,演员谢幕时,我站着拼命地鼓掌,拼命地流泪,我是如此激动,那种内心的某种情感,某种表达终于被人讲出来的感觉,我至今仍难忘。在读书时,我才意识到,匆匆6年已经过去,2013年变得遥远,而且那时,我25岁,刚刚步入社会,稚气未脱。
再也没看过《如梦之梦》这部剧。我记得很清楚,2013年,我买了上下两本的票,上本在第三排,下本在第一排。两本票价均为880元,有些贵,但没有如今这样难买。读这本书之前,我总怕,我总怕如果我再去看这部剧,因为我自己变了,所以不再能体会到那种感受了,心里害怕自己的改变。但读完书,便渐渐放下心来。我确实变了,但万幸的是,这种感受仍未改变。
翻看了一下看完剧后写下的剧评,感觉那时的自己很年轻,稚嫩,但是也更加敏感。不妨贴在这里,算是一趟借由《如梦之梦》所做的一场穿越时间的梦好了。
夜深,燃烛,述梦
我很幸运,能够第一时间拿到这本书。用了一天时间读完,完全是手不释卷。从头至尾,每一个字都能让我有所回忆,有所感触。原来读剧本是这样的感觉,于是我想,如果我是剧中的演员,也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有其他同样新鲜的感受吧。我一字一句的读,甚至连最后的每一次演出的演职人员名单都读了。发现2013年4月1日,《如梦之梦》北京版首演,我竟误打误撞,阴差阳错的几乎成了第一批观众。
人生的第一部剧,但自那之后,我便很少看剧了。我对这部剧的感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剧中那些男人对顾香兰的感觉一样。这部剧已经把我心中的感受说尽了,其他的剧便只是消遣了,那会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是的,没有意义。上面这句话,像是剧中哲学家的喃喃自语。
不过我的这种感觉也许并不准确,而那时我的感受似乎也并没有那样丰富。因为我是观众,而这6年,在我的人生里,我却是真正的演员,我在这如梦的人生中,抑或是如人生般的梦中,经历许多,体会许多,也丢下了许多。我在这似乎很短又很长的六年里,似有也似无的,有了些许更多的共情。在人生之梦里,我不算是一个很合格的演员,但终究,我也并不只是一名观众了。
人果然还是要读纸质的书,那种拿在手上的感觉,眼神随字句移动的感觉。书是有重量的,页是有触感的,字句是有温度的。恰好,今天又下起雨来,我坐在下雨的窗前,告别了手机、电脑,找回了被我深埋在内心很久的那种最喜欢的感觉,我很难精准的描述这种感觉,仿佛是一种既忧伤,又喜悦,既欣慰,又失落的感觉。
很巧,今天,同样是临近午夜12点了,夜同样深了,似乎在这样的时刻,结束如梦之梦是一种命中注定。所有的过去,未来,似乎都不重要了,只集中在这一刻,这跨越的一刻。让人有百般情绪却无从述说。
我似乎忘了看剧时最能击中我的那句台词,但今天我找到了。“为什么我们最爱的东西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也给我们最大的痛苦?我决定改变。我觉得,让一刹那的时间扩大成永恒不散的记忆,还不如满满地活在那一刹那之中。就好了。”
是呀,就是那一个刹那,这一个刹那,某一个刹那。也许,一直以来,我始终活在2017年4月7日午夜12时的那个刹那里,只是自己未曾觉察罢了。
浮生若梦。若梦非梦,浮生何如?如梦之梦
今年,若能有机会重看一次,就太好了。
全文完
写于2019年7月28日
巴斯特德
《如梦之梦》读后感(五):从世界戏剧到千禧年假说
——赖声川《如梦之梦》中的二十世纪图景
谈论戏剧往往离不开实景演出,但是当剧本单独以书籍形式发行时,它就成为一个自足的审美对象。虽然不可否认,《如梦之梦》剧本是为了演出而创作的,但当笔者读到其单行本的时候,仍然被其出色的文学成就所吸引,它所构筑的那样一个失重而想要重新找回引力方向的世界,一个人们失去了绘图能力而仍然试图对世界进行测绘(mapping)的世界,一个其色彩、梦魇的繁复和情绪的渲染使任何演出都显得滞重、粗莽和局限的世界——当伯爵夫人说“巴黎快要秋天了,我们在这里失去时间了……失去时间了,一切在混乱中,你在绕……在绕……一切在绕……有别人吗?”,这段台词充分隐喻了《如梦之梦》全剧所表征的生活状态,每一个词似乎都浸染了市场展演和后现代的感官性、混乱与迷幻。人们用以假乱真的方式生活与迷醉,虽未彻底放弃希望,却又随波逐流;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哲学思辨上,但也保持着对彻底世俗化的最低限度的拒绝。剧作的主题轻巧地叩击了流徙、死亡和末日,使人想起贝克特的名作《等待戈多》,但是又仿佛是在一个后末日的时代,人们虽处于灾异状态,但是对于新的变革的指数却没有什么期待。
《如梦之梦》是一部鸿章巨著,作品涉及的时间从1932年持续到2000年,地点从北京、上海、台北蔓延到法国巴黎,以一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嵌套起十二幕往复穿梭、来回变换的故事,其中有梦中之梦,有生离死别,有时间和空间的流离与迁徙。已经有很多人对其“时空结构”作过研究,如王少伟《<如梦之梦>舞台时空设定对即兴创作的启示》、林婷《论仪式对当代戏剧艺术空间的拓展:以赖声川<如梦之梦>为例》,但是这些分析多是以演出的时间长度和戏剧舞台的“舍利塔式”的设置为研究对象。赖声川指出,这种让演出舞台环绕观众形成四面立体演出效果的剧场受到佛教信徒围绕舍利塔转圈的仪式的启发。[1]但很少有人从戏剧文本的角度作出分析。如王少伟说:“不同于一般舞台演出两小时以内的时长,八小时的演出对于演出团队和观众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考验。”[2]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挪用当代方兴未艾的“世界文学”的框架,从“世界戏剧”的层面对《如梦之梦》剧本的时空结构进行一番探究,也许更有助于澄清赖声川戏剧写作的本体论特征。多年前出版的余秋雨的《世界戏剧学》虽然使用了“世界戏剧”的名词,但是更多地是指日本、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或地区戏剧的大杂烩。也许我们可以改写大卫·达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的定义,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答案。达姆若什认为,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是一种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阅读模式。相应地,可以说,“世界戏剧”是通过翻译、改变、重演,对民族戏剧和各种地方性的戏剧进行了重新排序和多重聚焦,通过在不同地方上映和被观看、与多种群体互动并实现自我更新的戏剧类型。
说《如梦之梦》是“世界戏剧”并不在于它在指标上达到了如上硬性要求,而是它以一部戏的方式提喻了二十世纪的经济生活、情感生活、政治生活的多种现象,把超现实主义者、革命者、吉卜赛人、妓女、贵族、侍者、小商小贩等五行八作的异质性身份整合在一个情节链条之中,它的背景涉及医院、咖啡馆、餐厅、酒吧等场域,把1940年的巴黎和1941年的上海并置在一起,这些因素一起展现了一种世界史的眼光;在这些不同场域、不同人群、不同历史脉络的辩驳、争执、碰撞、分裂、流散中,我们发现任何一种被呐喊的或被娓娓道来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处世哲学,都变成商榷性的、装饰性的了,阶级话语与情欲、荒诞派与革命并置在一起,这种马赛克式的巴洛克奇观和拼图艺术解构了一切它试图通过叙述而加上着重号的生活秩序,从而使读者感到餍足、厌倦和疲惫。另外,它还内在地结构了处于异域的华人和身处中国的外乡人等多重身份,其中最明显的在于“伯爵”对于中国和中国女人的“蝴蝶夫人”式的错认,他在中国“从来不出门,从来不吃中国菜,不去认识中国人”,过着完全法式的生活,但是却叶公好龙地眷恋着东方的哲学、绘画和女人。伯爵与顾香兰的故事,也是东方情调与现实的东方女子的故事,男性意淫与女性实际的故事。顾香兰的前往法国,伯爵的前往上海,两道反向而行的轨迹,都是被生活中模糊、微弱而难以辨析的欲望拖动,这方面,《如梦之梦》是“反戏剧”的,主人公没有古典戏剧的激情和“性格”,他们仅有着萨洛特式的“向性”,在被生活规约的通道上作着混乱的流动、斟酌、试探,有时候不辞而别,戏剧本身的目的即在于挖掘和辨明这种汹涌、微弱的潜意识,而它的规模和野心则是全球性的,佩雷克的《生活使用说明》在一座房子中缩写了一个世界,赖声川则试图在一场对话中完成同样的事。于是人物被分成了A系列和B系列,他们往往只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的面孔(persona),他们彼此交织、重叠、消解,构成了一个人一生中的“布恩迪亚家族”系列,而它言说的对象则正是一个星球的百年“孤独”。
顾香兰屡次提到的“笼子”的隐喻,可以看作是“世界戏剧”和“千禧年图景”的具象化:“其实我想我是摆脱不了的,笼中的小鸟虽然飞出去了,但是它已经受了伤,它的心已经死了。我到法国去就像换了一个笼子一样。也许笼子变大了,跟世界一样大……你们大家要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往后再有什么事,都要坚强地活下去。”[3]从张爱玲的绣在屏风上的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到顾香兰的“笼子”,女性的天空仍然是低矮的。“其实我们一辈子就好像是一出戏,这出戏是我们自己编的,戏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是我们自己在决定。”[4]就像穆旦的一首诗:“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赖声川的这出戏悲怆、宏阔而充满历史感,从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的世界视野,类似近年常被提及的“星球文学”(cosmopolitan literature),台词、场景的细节鲜活真切,漂浮着历史和经验的泡沫,在成吨的事件之中,人像幽灵一样回忆和重返,但是却不再有近代意义上的“乡愁”可言,从中可以体验到作者收放自如的、精密中透着酣畅的文本编织能力和情绪收纳能力。最后一幕的千禧年仪式,与序幕中秦始皇求仙的故事对照,加上“庄周梦蝶”母题的不断串引,表明剧作家想要通过这出戏完成一个世纪(甚至是上千年)的象牙微雕。此剧中的“千禧年”之夜的场景已经悬置了“千禧年”在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宗教感,它只是部分地迎合了人们对于世纪末的颓荡、悲哀和缱绻的想象,尤其是在这一个世纪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我们所有、惟一的“现代”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前夜,我们经历了“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它的尾声,我们经历了冷战“历史的终结”。赖声川并非想要对我们“现代”的历史作一个总结,但《如梦之梦》确实是一个富有褶皱和空间感的长卷,它的文字本身也承载了后革命的疲惫和乌托邦已死之后的一丝肆意与倦怠。但它是一部有力的、充满情感强度、能够调动人们身体经验的戏剧,一部能够让人想起卡尔德隆和库斯图里卡的戏剧。通过这出戏中之戏、梦中之梦,我们也辨别到了处于追寻、失落、彷徨和辗转中的自己。
注释:
[1] 林婷.论仪式对当代戏剧艺术空间的拓展:以赖声川《如梦之梦》为例[J].戏剧艺术,2015(01):4-12. 第五页。
[2] 王少伟.《如梦之梦》舞台时空设定对即兴创作的启示[J].戏剧之家,2019(01):27.
[3] 赖声川. 如梦之梦. 中信出版集团: 北京. 2019. 第263页]
[4] 赖声川. 如梦之梦. 中信出版集团: 北京. 2019. 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