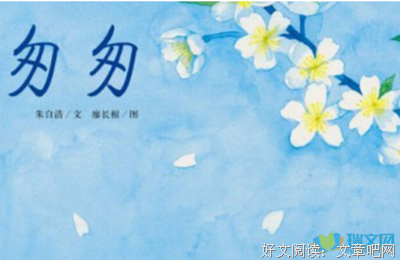
《时间的玫瑰》是一本由北岛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4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对诗却是差那么点
●北岛老师亲身示范如何在不懂八国语言的情况下对诗歌和翻译做出评判,然而却足以让人信服,现代诗歌拥有无尽的力量,书中是饱含热爱和真挚的解读,完全不忍心对它苛刻太多呀。
●北岛喜欢一些抒情有韵律的诗歌,不怎么谈智性的诗歌,当然诗歌大多都是谈论探索人生和生命的。对九位诗人写作和人生的勾勒也向不熟悉的人作了通俗的普及。
●受教。
●读这本书来学习读诗
●一个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我们迷失方向。他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是,除了英文外他并不懂其他外文,按理说他是无法区分牧羊人和狼的,或许他自己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时间的玫瑰》读后感(一):是谁传下诗人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照亮迷雾,带给我安宁
作为一名石油钻井科研工作者,诗,诗意,好像同我没什么联系。可是多年前的一天,万圣书园的一个学生模样的管理员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帮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诗意的世界,她指着一本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说:“这本诗集不错”,从此我的神经衰弱症有了解药。
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实习生,在漫长的海外工作的日子里,我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数据、工具、报告和合同,每日绞尽脑汁、胆战心惊地为了自己的事业忙碌。“逻辑”是工程的灵魂,毫厘之间的错误可能就是几十万美元的损失,一天的工作下来,常常累到瘫软。可是躺在床上,脑袋里的那个小马达还是在不停的转呀转,想算法,想模型,想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步……加之一个单纯的、老实巴交农村孩子就这样进入了社会,发现现实和想象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从小就有的神经衰弱的毛病愈发严重,苦不堪言。
这个时候,是阿多尼斯、辛波斯卡、博尔赫斯、北岛、顾城、三毛、李娟,还有村上春树们每天晚上把我从那个“逻辑”的漩涡中解救出来,他们有的是诗人,有的写诗一样的文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打开书,让他们的语言静静的流淌在脑海,进入他们那个充满诗意、没有一二三四的世界,那些纠缠、压力、迷惑和委屈很快就冲淡了,就这么安宁的进入了梦乡。
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一味一味镇定剂,随着书读的越多,依赖性也就越强,每当有一段时间太忙不读,人就会变得焦躁、抑郁,然后马上转向他们求助,可能此生是摆脱不了了。
最早接触北岛,是那本《城门开》,当时的感觉是:诗人写散文,就好比摇滚歌手唱情歌,直抵人心,必成经典。今天,又读完了这本《时间的玫瑰》,好像又开启了一个世界,他手把手的教我们怎样去欣赏一首诗,告诉我们诗人的命运、经历和思想如何注入语言,让我们了解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诗人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如何努力的维持的自己的纯粹和正直,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通过这本书,我也明白了:诗不只是文字的艺术,诗也不止会静静的流淌,诗里有善、有恶、有波涛汹涌,还有生离死别。
现在的我还是会失眠,但书和诗,依然是我最信赖的解药。
最后,引用高晓松那句话:“人生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时间的玫瑰》读后感(二):诗歌是诗人手握时间的玫瑰后留下的香氛
我现在在想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这一本书的问题。跟着他读诗是必然的首选项,其次这些篇章花大量的精力描写诗人的生平,其实写得不够详细,但如果仅是了解生平看维基百科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毫无疑问的答案只有一个:一个诗人的诗魂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的诗。
/洛尔迦——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1898年6月5日-1936年8月18日
西班牙诗人 活跃在20世纪初的黄金时代,死于政治斗争。
风格自由自然,富有音乐性,多用短句,主题常常是爱 死亡和生命。
对达利劈过腿(呸哈哈) 跨领域艺术家,精通音乐和戏剧。
诗歌集《深歌集》 代表作《梦游人谣》《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
/特拉克尔——陨星最后的金色
1887-1914 德国表现主义诗人
诗作中充斥着颓废死亡的气息,诗歌上的颓废往往有其特有的意象范围,比如黄昏、秋天、寒风、衰亡、陨星、荆棘等,这在特拉克尔诗中尤其明显。他正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的。在短短的写作生涯中,他完成从浪漫主义向表现主义的过渡。代表作《赫利安》《给孩子埃利斯》《挽歌》
而诗人本人的生活也被毒品 情绪不稳定 性格孤僻 抑郁症围绕。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
奥地利诗人,一生漂泊流浪,曾是罗丹的学徒。活跃于20世纪初期。
在作品中将自我感觉外化物化,注意意向的准确性与可感性。
诗歌集《时辰集》 代表作《秋日》!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1920-1970 德国诗人
二战前出生的犹太人,就足以描绘出他悲惨的一生。一生都在经历着身份上的外界排斥。
边缘化的身份背景和苦难的经历
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简短、艰涩,感觉鲜明,通过语言的破碎性赋予语言以陌生化的独特感。
代表作《死亡赋格》《卡罗那》《数数杏仁》《用一把可变的钥匙》《串成线的太阳》
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1931-2015 瑞典
《时间的玫瑰》读后感(三):时间的玫瑰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被里尔克《秋日》中的名句打动,“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某些时刻人会懂这种感受。北岛《时间的玫瑰》在文体上不好分类,集诗歌、散文、诗论、艺评、传记与访谈等多重文体于一身,按有人的说法叫“诗歌传记"。选取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九位诗人的代表作,以诗人角度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还原,评论与叙事结合,读起来不像读诗选那么累。 有些诗选读起来累,因为语言高度抽象,如同音乐,如果仅浮光掠影的欣赏,也可被旋律和节奏感染,但要读懂,读通作者的感情与思考,确要下一番功夫。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强大的诗歌是难读的,其可记诵性源自艰难的愉悦,而艰难到一定程度的愉悦就是一种痛苦。”读诗会痛苦,这也难怪现代诗歌走下坡路,这无用的苦差,很少有人愿做。 读诗无用,跟读书无用被后是一个道理,这无用是社会标准的评价。读诗读书无用,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还会阻碍人成功,人的时间是一定的,花在无用之事上多了,成功机会小了。古训书中自有黄金屋,所说的书是四书五经,读四书才能做官,现在确是无用了。反过来说,这种无用对个人来说,并不必然。 诗歌会增强我们对语言与世界的感受力。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使人感受事物,是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形式主义另一代表雅各布森认为诗歌的功能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偏离实用目的,而指向其形式自身,包括韵律、词汇和句法。文学语言中的声音和意义之间、语法结构和主题模式之间均有特殊的呼应关系。“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变得陈腐、滞钝、“自动化”,文学语言则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等手段,使日常语言“陌生化”,从而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我们世界新鲜的感知。” 八十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年代,久旱逢霖,一代诗人成长起来。而后影响渐微,首先是被电影电视等娱乐形式挤压,还有现代诗歌自身可能出了问题。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可能均出了差子。传统诗歌本应是现代诗歌的宝藏,而中国现代诗歌,传统的一再中断。“”五四”运动就是第一次中断,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否定,造成早期白话诗的苍白幼稚。左翼运动的革命文学致使诗歌沦为宣传的工具,是第二次中断。而第三次中断是“九叶派”后中国诗歌的巨大空白。”而外国现代诗歌翻译,也有问题。有些翻译佶屈聱牙,乱改原意,把外国诗歌改的面目全非,也有为了凑韵,硬生生将形式考究的诗歌剪切成豆腐干。“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性是不可译的,除非译者在自己的母语中再创造另一种音乐。而押韵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创造的其实只是节奏,汉语的内在节奏。” " 诗歌中既要讲“奇”,又要讲“通”。所谓“奇”,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而“通”,按我的理解,则是一种诗意的合理性。"这是北岛好诗的标准。 “诗歌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和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作为诗人,北岛对诗歌现状忧虑。然而诗歌不正应该如此吗?一小撮儿的人做的无用之事。叶赛宁说“诗并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诗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幸与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艾基语)。而诗人最好的归宿是,“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ritten in water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时间的玫瑰》读后感(四):写作就是迷失的君王
每次涉及到和诗歌相关的书籍,或者提笔写一写对诗歌的评论,我就会有种挺复杂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有点尴尬。因为我自己虽然也写诗,但多数时候还是凭感觉创作,一些技巧上的东西,其实不太谈得来。另外,我在二十岁之前,一直秉承着一个观点,就是:“诗歌是相当个人化的东西,生发自人的灵魂,不应该去奢求别人理解。”所以,我那时写诗的态度是相当“封闭”的,羞于拿给身边的人看,也确实没读过多少好作品。
当然,今天回头看,我依然认为自己当初的观点没错。只不过,那种“封闭”态度,的确不可取。它更像是,孤独者的自怨自艾,也带有一丝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色彩。我想,此类态度,可能是内向者独有的青春期记忆吧。就像诗人北岛说的那样:“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我觉得自己这半年对诗歌如饥似渴地阅读,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召唤。前所未有地,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融入到一个宏大的传统中去。
在这本《时间的玫瑰》中,北岛为九位他心中“最伟大20世纪现代诗人”分别作了小传。其中还穿插了北岛对这些诗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对不同译本的评价。坦白讲,在阅读过程中,我挺意外的。因为本书每一章的结构和笔法都不大相同,没有采取统一笔调,去进行套路化写作。考虑到这九个章节,原本是《收获》杂志2004年连载的一个专栏,我觉得就更为可贵。因为当作家为一本杂志撰稿时,他在时间上会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写作是不自由的。北岛在后记中也写道:“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足可见,截稿期带给他的压力。北岛无惧时间紧迫,精心雕琢文字,为不同诗人立传。这样的写作精神,我由衷敬佩。
北岛,原名赵振开,中国当代诗人
本书提及的九位诗人,有四位我过去曾读过,另一半很惭愧,确实是闻所未闻。北岛采取的这种写作方式有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立体感。他在介绍完诗人一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后,立刻插入该诗人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疑能够加深读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时间的玫瑰》确实部分解决了,我在阅读上的一些疑惑。比如:我半年前试读了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诗集《孤独者的秋天》,他对色彩的运用自成一派,意象比较迷幻,我就不太理解得了。这次读《时间的玫瑰》刚好有一章专门讲特拉克尔,随着北岛的讲述,我才明白了解读表现主义作品,不能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而要把它和事物内在的本质进行映衬,否则是不可能读懂的。也就是说,我过去那种纠结于意象本身的解读方式,用于特拉克尔就不合适。如北岛反复强调的那样,解读一位诗人,必须找到打开他作品的“钥匙”。我想,这可能是自己在未来的时间里,需要着重积累的一种经验。
在《时间的玫瑰》所收录的九位诗人中,有两位我尤其喜欢。一位是德语大诗人里尔克,他那首《秋日》给我留下太多感动,至今读到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我今年四月份,专门写过一篇和他相关的文章,所以就不赘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找看。
另一位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除去他因为犹太人身份,在二战期间所经历的坎坷遭遇之外,我更被他诗歌中那种流动的音乐感所折服。他就像是在用文字谱写一部乐章,节奏起伏多变,扣人心弦。策兰最有名的诗,当然是写给战争的《死亡赋格》。但我个人更偏爱的,还是那首情诗《卡罗那》,下面分享给大家:
卡罗那
策兰 著/北岛 译
秋天从我手中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从坚果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
而时间回到壳中。
镜中是星期天,
梦里有地方睡眠,
我们口说真理。
我的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相看着,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
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血色月光中的海。
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
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本诗具有一种递进感,从第一节,面对时间流逝的那种犹豫不决,到最后用简洁的“是时候了”四个字,给出肯定回答。它所描绘的正是人面对爱情那种复杂感受,一种欲言又止,徘徊不定的心态。诗的前两节,时间感强烈,它的主要作用是为抒情主人公“我”作情感上铺垫,进而引出下文的“决定”。第三节是我最喜欢的段落,第一行“爱人的性”点明了本诗的爱情主题,富有画面感。其中最美的一个比喻,是把“睡去”比作“海螺中的酒”,给人一种不断沦陷,又难以自拔的感觉。第四节则将全诗推向高潮,第一句,表示两人决定向世人公布他们相恋的秘密。第二句的意象“开花的石头”,无疑标志着两人爱情的解放与升华。最终用“是时候了”收束全诗,干脆有力。
另外,北岛在本书中对文学的“现代性”做过一个简短讨论,这刚好是我最近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前些日子曾读到这样一句话,说:“现代人写的诗,未必具有现代性。”我想,对现代性缺乏认识,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多数人对物质的现代性感受更深,但对文化的现代性,则大多处于一个“未启蒙”状态。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谈及“经典”,我身边的一些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那些19世纪的法国长篇小说,或者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等,这个现象相当普遍。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或者否定他们的地位。而是想说,这种认识,其实反映了人们在阅读上的一些误区。即,冗长,读起来艰涩的小说,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就是经典。这个观点是相当可笑的。19世纪的文学,包括更早时代的作品,因为离我们的距离远,读起来稍困难些,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你读《堂吉诃德》,甚至去读《荷马史诗》,这种感觉会更明显。但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正常感受,误当成衡量经典的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文学在上个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手法固然精彩,但它并不适用于现代人的表达。如果我们采用一种典型19世纪的笔法来写小说,事无巨细的描写,拖沓的叙事节奏,略显夸张的人物刻画,我想当代读者是很难读进去的。如果我们采用文言律诗的形式写作,也很容易产生一些形式大于内容,浮于表面的作品。
现代文学重视对人内在本质的挖掘,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作品结构上都进行了大量的革新和探索。在美学上,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特征。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审美上对“现代性”缺乏认识,长远来看对艺术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比较浅,有不少模糊的之处,希望自己下一阶段的阅读,能让这些观点成熟起来。
北岛与特朗斯特罗默的合影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还重点强调了诗歌翻译的问题。我很欣赏他的态度,毕竟对一部作品的译介工作,无论如何都不可当成儿戏。这是译者应有的操守,同样也是对作家的尊重。但在评价他人的译本时,北岛确实有失公允,或者说,是对自己翻译的版本太过自信了。首先,他采用英译本来翻译全部诗人的作品(当然,这和他只擅长一种外语有关),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太科学。因为对一些德语、俄语诗人来说,英文版也是翻译过去的。用翻译过的版本,进行二次翻译,肯定有它的局限。其次,北岛在评价译本时并没有给出原文,使读者无法进行自主的判断,多少有点“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感觉”。就我未读过原文的感受,只比较中文,我觉得就有不少人译得比北岛更好。不过,话虽如此,北岛对译介工作的态度,依然值得我尊敬。
我在前文中曾说过:“诗歌生发自人的灵魂,不应该去奢求别人理解。”因为我心里明白,在这个时代寻求别人理解,是件成本极高的事儿。私底下的社交尚且如此,何况晦涩的诗篇呢?可回想起书中,北岛和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友情,那种诗人间心意相通的默契,我又的确有些艳羡。
虽然嘴上说不奢求别人理解,但如果真有一个人出现,我想自己也许会兴奋得无法自持吧。
《时间的玫瑰》读后感(五):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催散我们诗歌的梦
当明白了这本书是专栏写作集成册子之后,便能理解了为什么有许多杂乱而无用的篇幅。
很多内容是不需要在文中点明的,显得支线过多而庞杂,有很多背景介绍,完全可以一笔带过,却写了数页纸的痕迹。
但这些都并不妨碍这本书的重要性,一方面介绍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另外一方面又让人得以一窥北岛的诗学思想。
洛尔迦难道不是最惨的吗?被处刑而死,显得悲壮而又草草收尾。
《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第一节看的让人心惊胆战,《梦游人谣》写的确实是好。也能理解为什么洛尔加和博尔赫斯看不对眼——他们本来就不是一类人。
说来好笑,百度百科上关于洛尔迦的词条,八成都是从北岛的这篇文章直接搬运过去的。
这位“安达卢西亚之子”把他的诗同西班牙民间歌谣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诗体:节奏优美哀婉,形式多样,词句形象,想象丰富,民间色彩浓郁,易于吟唱,同时又显示出超凡的诗艺。近70年来,他的诗歌作品对世界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著名诗人勃莱谈到他的作品时说:“洛尔迦的诗歌佳作是人类智力的楷模。”
特拉克尔是“窥见内心黑暗地狱”的奥地利伟大诗人。
特拉克尔一节注水严重。关于一战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介绍过多,居然用了整整三页纸,其实只是可以一笔带过的背景。
说老实话,特拉克尔的诗作充斥着衰颓和崩坏的意象,哪怕是在绚丽的色彩描写,也蒙上一层淡淡的灰色,但《给孩子埃利斯》中最后两句:“黑色露水滴向你的太阳穴,是陨星最后的金色”反而是我觉得他最好的诗句,虽然在这里,金色的陨星也是分崩离析的意象。
特拉克尔没有拿到维特根斯坦的资助而死去,让我觉得非常惋惜。
特拉克尔是德语诗歌的“黑暗诗人”,与里尔克、保尔策兰一同鼎起20世纪德语诗歌的辉煌,这位让维特根斯坦捧卷终生的人是诗人中的维特根斯坦。
到了里尔克故事变成喜剧,北岛明显不喜欢里尔克,直到文章末尾才有所改观。这大概是因为专栏约稿的关系吧。
他只重点提了《秋日》一首诗。这首诗说实话,绿原翻译得并不赖,但是北岛依然认为自己翻译的较好,我觉得差别倒是不是很明显。至于里尔克孜孜以求的物诗,在北岛这儿直接被省略了,《豹》也只不过做了翻译的比较,而没有深入的分析。
说实话,《秋日》确实算是一首好诗,但是对于《预感》的翻译分析,私以为陈敬容和绿原的最后一段都和北岛不相上下。
而里尔克因为自己的自尊,而和罗丹翻脸的事件,更是让人不禁发笑。
赖内·玛利亚·里尔克与叶芝、艾略特被誉为欧洲现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里尔克的存在主义诗思更是深深地影响到后来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与萨特等人,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一大诗性源头。里尔克的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很高。它不仅展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雕塑美,而且表达了一些难以表达的内容,扩大了诗歌的艺术表现领域,对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策兰真的是伟大的诗人,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的自杀是可以避免的,但某种意义上又是无可避免的。
说说翻译名字的问题。一般同样的一个名字,法国和意大利的翻译成保罗,而东欧的翻译成保尔。策兰是德国人,这是一个尴尬的国度,不知道应该翻译成什么样,在《时间的玫瑰》中,北岛翻译成保尔策兰,但更加得到公认的翻译名字,应该是保罗策兰。
或许是因为诗人本身的经历跌宕起伏,北岛在书写这一篇的时候,笔调也是跌宕起伏的。
而保尔策兰的诗歌也具有其独特的吸引人的魅力。
《死亡赋格》奇特的行文节奏深深的吸引着我,《卡罗那》《数数杏仁》也令我深深着迷。而我不喜欢他晚期的诗作,这和北岛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不喜欢保尔特兰晚期的诗作,诚如我不喜欢艾基一样。
策兰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成为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至于特朗斯特罗默,我该如何去诉说呢?大量的他本人自己所写的篇章,占据了这篇篇幅,很明显是因为诗人本人在世,而北岛无法客观的去论述他的成就,只能大量的注水。
我们当然很能理解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北岛对于自己友人的小心翼翼。
特朗斯特罗默在1990年中风,而只能用左手写作,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对他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这一点有点令人惋惜。
而对于《果戈理》一诗的讨论,让我发现了特朗斯特罗默诗歌本身具有的意义,这首诗如果按照北岛的理解,确实是写得太好了。
但说实话,我无法理解《写于1966年解冻》五行诗中的惊心动魄,无论北岛如何去渲染,我也无法理解这首诗中的力量。我只能瞥见特朗斯特罗默诗歌中的力量和他本人伟大的人格魅力。
瑞典著名诗人,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同时是一位心理学家和翻译家,1954年发表诗集《17首诗》,轰动诗坛。在2011年10月6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
曼德尔施塔姆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他改变了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本土诗歌传统,而汲取西方的文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杂糅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诗歌成果,并将这种诗歌传统传承给了布罗茨基。
在关于《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这翻译探讨中,我认为刘文飞翻译的最后两句比北岛的要更好,而整体则是北岛更佳。至于《地平线窃去了我的呼吸》,我觉得杨子翻译的整体比北岛翻译的要更合我的心意。而菲野翻译的《列宁格勒》第一段,虽然可能参照的是不同版本的诗作,但是确实翻译的有诗歌的味道。关于第一段的明显不同,北岛居然没有加以探讨,我觉得这是失责的。
至于不断的进行翻译的探讨,对曼德尔施塔姆生平的介绍,和对赵一凡交往往事的回忆,显得文章有些杂乱,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文章本来就属于专栏写作的随笔,作者这样写,融入了自己的感悟,也介绍了诗人的生平,这是一种写法,本身是无可指摘的。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苏联天才诗人。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终于要说到帕斯捷尔纳克,我不知道应该是把他作为《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来介绍,还是作为一名诗人来介绍,更符合他的特性。
在强压统治下的俄国一路活到自然死亡,获得诺贝尔奖却因为强压而不能领取,这本身就已经是够传奇的了。在北岛的笔下,他更加传奇,因为北岛用奥尔嘉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往来串起了整篇文章。
从开头到结尾,这是这么多篇章里最富有人性和神性兼备的一名诗人。
来讨论一下诗歌翻译,我觉得菲野翻译的《二月......》第一节比北岛翻译的水平要高超。“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抒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这才是真正的诗歌,这是真正达到了北岛要求的,在翻译中创造新的节奏和新的韵律。而毛新仁的译本确实是烂的没有办法看,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异议的、大家都可以认同的看法。
帕斯捷尔纳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俄罗斯诗歌神坛的呢?到了最后,他基本已经是最伟大诗人的代名词。是他捧起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也是他毁了他们。我知道,我这句话说的太过武断了,但是我总是放不下这个念头。
在廖伟棠笔下,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这么说:“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在这里我澄清一下,这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也不是茨维塔耶娃的诗作是廖伟棠《末世吟》中的一句诗。
而在俄罗斯的高压下,诗歌越来越受束缚在无事可写的情况下,转向小说创作的帕斯捷尔纳克,也取得了自己的伟大成就:《日瓦戈医生》。
而关于《哈姆雷特》的翻译评论,北岛对于张秉衡这种硬把外国诗歌翻译成每行字数都一样的做法,进行了让我觉得酣畅淋漓的批评,这是我一直以来想说的话,却没有说出来,这是一直让我看普希金诗歌看不下去的原因,但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审美出现了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和我思考一样的人了,还是北岛先生,我把他的话原文抄录至此:
“与张祈译本相比,张秉衡译本还靠点谱,但却用的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形式——等于给解放脚穿小鞋。为了凑数凑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节奏,不信你大声朗读试试,要能念顺溜才怪呢。热衷这类豆腐干形式的还大有人在,因为我看基本上属于翻译界的“前清遗老”。”
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等。1957年,发表《日瓦戈医生》,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受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被迫拒绝诺贝尔奖。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1982年起,苏联开始逐步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
至于艾基,原谅我是真的不能欣赏他的诗作,我认为这种豆腐块式的诗歌是真的没有可以解读的余地。
但是从张枣和他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歌的理解,还真的是比较深刻的,虽然他的诗歌写出的形式让我非常不喜欢。
让我最不喜欢的一首便是北岛奉之为圭臬的《梦:为煤油排队》,奇怪的分行和奇怪的分段让我看了非常难受,我不想多评论这一节了。
至于狄兰托马斯,我只能说他是一位最率真而最富有个性的诗人,他的死法和古龙类似,他们都是游戏人间的浪子。
而关于对《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的翻译探究,让我决心以后,如果明知这个诗人是以双关矛盾修辞法和节奏韵律见长的话,那不如直接去看原文或者英译版。北岛在把“催动”译成“催开”的时候明明说了:“我得承认,我把众口一词的催动译成催开是一种小小的冒险,但我认为催开有一种直接性,更具视觉效果。”,但在后面的逐句解释中,又出现了诸如“绿色导火索与花朵的因果关系,正是通过催开这一动词连接并推动的,如果用另一种处理方式,或置换另一个动词,就会毁掉这一句,甚至整首诗。”这实际上分明就是对自己翻译版本的一种无限的拔高。
这也是很多批评这本书的人,认为北岛写这本书翻译比较的目的就是贬低前人,拔高自己的翻译作品。我认为贬低前人这个是批评得有些过了,北岛原意大概并不是拿这些前人当作箭垛,他只是把他们的肩膀当作自己脚踩的基石,以显示出自己诗歌的伟大而已。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因为北岛的语言习惯,几乎塑造了半个现代诗坛,但这种毫无节制的拔高,自己让人会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蔑视。同样的感觉,在我读马原的著作的时候时常见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马原的小说,但不喜欢他那副自命清高的模样。
至于我手上这本《时间的玫瑰》,在431页《北岛译〈死亡也不得称霸〉》的时候,把字印歪了,如果这本书不是我在图书馆借的,我一定要打电话到出版社去申请赔偿。
关于这首诗的翻译比较依然是我之前的看法,北岛太过于拔高自己了,我觉得三首翻译的成就都差不多。至于《特别当十月的风》一首诗,抛开所谓海岸译本和王烨译本的结构性错误不谈,我觉得北岛的诗歌在整体层面就是不如前两者读起来舒服。很多词句的运用让我感到刻意,让我感到是为了诗意而诗意,而采用这些词汇,让我感到非常的失意。但如果真的接受了北岛的观点,确实翻译应该精确,而他的精读翻译做到了精确这一点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我喜欢这首诗,狄兰托马斯的绝大多数诗我都非常喜欢。他的风格,非常贴近我本身希望能够达到的创作风格。
这一篇关于狄兰的文章,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的整体是倒叙的,先叙述最后几年和狄兰托马斯死去的时候,在叙述他的中年他的经历,再回溯到他的童年遭遇。这个叙述结构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发现想成为大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拒绝服兵役,你看这本册子里的大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可是为什么要成为诗人呢?就像后记中所说的一样,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听上去美妙,其实也不过是废铜烂铁的时代,过了废铜烂铁的时代,我们又进入了什么样的时代呢?谁也说不清楚。“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和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
我不是一个喜欢写书评的人,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希望留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