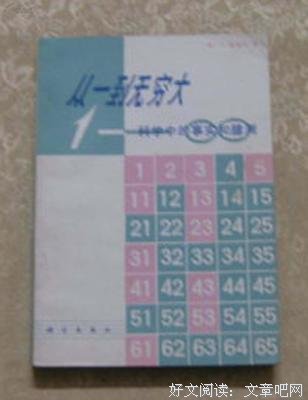
《总体与无限》是一本由[法]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家里蹲大学读完了
●相當難讀,不過時常也給漢語讀者帶來親切感。
●這是讓海德格爾給虐出內傷了……麽
●列维纳斯批判了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的“总体”,因为总体最终消解了“主体/同一”和“他者”。正义(与他者面容相对时来自他者的责任)先于自由(主体乃自因,万物皆备于“我”)。他一直强调主体与他者的绝对分离,两者间隔了一层“虚无”。同一/主体/有限 与 他者/无限 是必然分离的,它们并不在一个黑格尔的总体中,也不会在海德格尔的中性存在中溶解。主体必须无需他者就能实现独立,因为没有独立的主体作为一端,就无法遇见真正的他者;他者是绝对他者,无须主体的“光”就先行存在,他者是无限,主体欲望他者,通过欲望出离封闭自足的沉浸在享受中的生活,走向责任,走向伦理和正义。
●欲望是可欲望者之在场引起的对存在之绝对性的侵蚀,而可欲望者的在场因此是被启示出来的在场,这一在场在一个存在者身上开凿欲望,这一存在者在分离中将自身体验为自治的。列维纳斯厉害得有点晦涩
●批评西哲的总体性,将我们定位于无限而非总体,强调伦理学的绝对优越性,在无限(形而上学),他者(伦理学),上帝(神学),和平(政治学),末日审判(历史学)中找到一条通向真正的生活的伦理道路,也就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存在者本身。这条道路就是处于世界的我们与不在这个世界且不能被在场化和被内化到我之世界的绝对他者之间的关系——无限观念。一个既外在的,但又在超越中暗含了对于对象的占有的距离。这个距离也就是形而上学,就是列维纳斯的欲望,具象化就是面孔。这种既封闭又敞开的内在性也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列维纳斯无意是最独特的,尤其是伦理学的绝对优越性在与海德格尔对读的情况下启发更多。但问题就是后来德里达也提到过的,绝对的他者背后恰恰是列维纳斯要反对的绝对的自我。但他者性的伦理立场需要坚守
●隐喻和修辞或许就是法国哲学的特点吧。将“他者”置于一种绝对的距离之外,重新建构了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确在西方传统存在论哲学的汪洋之中投下了一枚巨石。然而,读过之后仍然对这种思维脉络存疑,即列维纳斯否定了自我主义的暴力,但是强调他者的高度是否同样会带来一种暴力。其次,面对面的关系又是否一定会带来我的自我质疑,既然我是自足的,又何必一定要对他者进行回应? 书的最后讲到的爱欲现象学太过晦涩,过几日再来看完吧。
●陌生的语言,悠远的意境。有诗意
●感觉列维纳斯已经驳倒了海德格尔了,厉害。他者理论,一个重新看待世界的维度。每一个偶然都是绝对的一次更新。不知道保罗·利科的他者理论是否与列维纳斯有渊源。
《总体与无限》读后感(一):持续更新
随便翻到的//我对他人的脸的经验,拒斥对象化,you can not kill。 destitute:即脸上是完全什么都不遮蔽的,脸是一种脆弱的没有防备的是有一种“脆弱性”——这对你产生一种需求——一种destitute,一种请求——你要去回应他——这种回应是无限的。responsability原初地是一种无限的。是一种prefect duty而不是一种in prefect duty(意味着没有那么多责任)——但是列维纳斯认为你经验到的责任是无限的。——你得把你嘴里的最后一块面包给——这就是这种无限的责任的召唤。nature egoism ⚠️⚠️⚠️不是我先有主体性,而是你的主体性恰恰是在对他人的回应中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有把别人对象化的倾向,所以上述经验会作为一种trace突然显现一下,作为一种trace留下来。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你都会觉得你需要somehow response,即使只有那么一个闪念——随后很快就把他对象化了。对他人产生的一种经验产生了伦理的要求。列维纳斯认为经验没有对称性——你站在你的角度如何我无可思考。我永远是一个first-person真正的伦理经验永远是我对你有责任,而不可能存在任何“将心比心”之类的。而且伦理永远是两个人之间的。当超过两个人,就不是伦理学,而是政治哲学或是其他什么的了。
《总体与无限》读后感(二):重读列维纳斯
在鸡年和狗年春节衔接处写下列维纳斯的读后感,论外在性。
列维纳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存活下来并在现象学说中犀利的批判了海德格尔而不落口舌。他的“同一”是如何到达的?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现象学说被政治家裁剪以利于统治的“正义”,也就是道德奠基于政治之上,这种事原本不新鲜,但列维纳斯试图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梳理一种哲学规则,一种绝对的无限。超越了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甚至尼采的虚无。
在那之前,新德国人甚至现象学没恰当的标准来建立价值判断。列维纳斯把伦理阐述为一切与众生之前的考量,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到犬儒主义,历史与物质的神话,个人的恐惧或者国家的罪行,都是巨大的后果产生的一种模拟两可的世界观。而列维纳斯把伦理和这种(黑格尔)由历史来判断价值与真理的方法描述成了无限的组成,并不需要虚构更多的不可思议的概念,对列维纳斯而言,只要无限是由不断前行的虚无的无限趋近,人类还是有获救的可能性。这是对海德格尔的死亡思想的彻底摒弃。
在除旧迎新之际,全体中国人倡导德孝团圆终身奋斗之际,让人忍不住思考什么是真实,甚至什么是真理。在2017这趟漫长的过年回家之路,我渐渐意识到:最终没有一个人不在从意识的基本水平开始,殚精竭虑地追寻赋予其生存以和谐一致性的形式或态度,这种一致性(同一)是我(也许是很多人)缺少的。
不论表现还是行动,为了存在,为了生存于这个世界,都渴求一致性。可以说,人对世界的看法比世界的现实要更好。但更好并不是说不相同,而是说它是统一的。人不能摆脱这个分散的世界,而使人的心灵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那种热切的追求,正是对“一致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不甘心平庸的回避。这里面包含着列维纳斯的“伦理”的可能性。这种伦理包括对效率,节制,爱的反思。
在一切反抗中都可以发现对和谐一致的要求,但个不可能拥有它,遂创造了一个替代的世界。
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祝愿文明远离历史上的形式的原则与堕落的价值,把新鲜活泼的美德置于社会思索的中心地位。
愿新年得到肯定性的自由。
《总体与无限》读后感(三):列维纳斯的门槛
9月份我看到了此书的书讯,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兴奋与讶异。这就像一个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样。因为在这之前,对于我这样一个守候故纸堆的人来说,我的愿望无非就是期待我欣赏的,喜爱的作品有中译本面世。那列维纳斯的全集是我最为期待的梦想。但这个梦是非常奢侈的,因为这是只能依靠他人才可能实现的梦。尽管这非常渺茫,但我知道列维纳斯的思想的影响力的作用,以及看西方哲学的译介情况,我相信,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意想不到。
所以9月份看到这本书的书讯,我当时的感受可想而知,非常感动。尽管这不是全集,但这是列维纳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我立刻就去京东购买,但发现还没有到货,我便去询问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结果更是意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这本书可能会有活动,我就按耐住这份心情,耐心地等待活动开始。最后我终于在国庆日见到了这本书,拿在手里翻动着书页,我竟然还有一点激动,看着这本书上的句子,对我来说,这太熟悉了,但又很陌生。
熟悉是说我之前看过《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还有《导读列维纳斯》与《他者的境遇》。陌生是说,列维纳斯的哲学思想,对我来说是一座珠峰,非常多的问题我至今一知半解,甚至还有很多问题是全然不知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还会如此期待它呢?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不能通透地理解它,这恰好是我不紧不慢地摸索它的原因,所以反而,每有一点收获,就如同意外之喜;另一方面是列维纳斯的经历,震撼了我的心灵,要我无法不去了解他的著作。其实反过来说他的著作也是他特殊的经历中的一部分。
他深陷在双重的痛苦中,一方面是亲人的惨死,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质疑西方哲学。他的一生就是这种痛苦所伴随的一生。他活了下来,没有绝望地走向死亡,在质疑中,他撼动了西方哲学的根基,走出了一条朝向他者之路。如果说雅克·德里达解构了西方哲学,那么列维纳斯解构的是伦理学。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列维纳斯遭遇的门槛就是在这种质疑中开始的,在这之前,他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充满热情地沉醉在海德格尔的课程中。可是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血洗开始了。列维纳斯因身着法国制服,他的犹太血统没被战俘营的德国士兵发现,才免遭不幸。他在战俘营里开始思考他的哲学问题,完成了《实存与实存者》的主要章节。后来他才知道他的亲人,除了妻子和女儿被好友布朗肖提供藏身之处活了下来外,其他亲人,全部遇难。
他在《异于存在》一书的扉页上用希伯来语和法语表达了对在这场浩劫中死去的亲人与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用法语写道:纪念被民族社会主义党所屠杀的600万人中的亲人,以及在各种信仰和各个民族中,那无数由于同样的对他人的仇恨、同样的反犹主义而遇难的人。用希伯来语写道:纪念我的父亲XX,我的母亲XX,我的兄弟XX,我的另一位兄弟XX,我的岳父XX,我的岳母XX,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参考《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P43页)
在这场屠犹运动中,海德格尔站在了法西斯一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他的哲学思想与他的选择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列维纳斯曾经相信的一切都在这种选择中步入了黑暗。从那个时候开始,哲学死亡了,同阿多诺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样。无疑是说文学死了。其实,无外乎是指西方的文明遭到了质疑。
从这开始,在这条反思之路上,就会清晰地看到哲学思想并不是常人所说的向善之说,更不是什么无用之物。相反,在哲学中所彰显的力量不亚于一位在战争中能征善战的将军的影响力,更不亚于一位政治家的野心。依照我的理解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宏观脉络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是主体,主体之外是我的客体世界。我要认识客体是什么,只有认识了才可能进一步把握它。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写文章要有统摄全文的主题,主题之外是被主题统领的,或者说主题之外是为突出主题而存在的,是为主题而服务的。
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还是如此,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场浩劫发生之后,如果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的方式没有问题,如果是正义的,为什么这种灾难还会发生?从第一个例子来说,在我的视域之内,是通过我支配它,我的视域内是一个总体,我之外的他人全部都可以纳入到这总体之内,一切都因为我的意识而开始。归根结底来说,这是一种一元论思想,是凭借经验可以逐渐去认识的。列维纳斯认为这里没有差异性存在,换言之,这种思想扼杀了他者的他异性,所以这是一种充满暴力的哲学。再接着用第二个例子来说,阅读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会主动地寻找主题,构建文本也是如此。文本是我的客体,我可以找到主题,或者说中心,逐渐地认识它。这个过程无异于第一个例子。但是列维纳斯的文本里充满了对无法描述之物的言说,给读者的认识再也不是可以被把握的,而是无法被认识的。在他所经历的毫无退路的不幸岁月之中,他撕开总体的外衣,走向无限的外在,这异于存在的,缺席的在场。
比如此书249页书写的这样:(女性)爱人,既是可把握的但同时在其赤裸中又是完璧无损的,它超逾对象与面容,因此也超逾存在者,如此这般的(女性)爱人位于贞洁之中。本质上可侵犯又不可侵犯的女性,“永恒的女性”,是童贞女,或贞洁的不断重现,是快感之接触本身中的不可触摸者,是当前中的不可触摸者——未来。它并不像一种与其征服者进行战斗、拒绝其物化和客观化的自由那样,而是一种处于非存在之边缘处的脆弱性;在这一非存在中,不仅寓居着那消失者和不再存在者,而且还寓居着那尚未存在者。童贞女始终保持为不可把握的,它未遭谋杀便已垂死,它失神恍惚,它躲避到它的将来之中,它超逾任何被允诺给预期的可能。在作为有之无法名状的沙沙声的黑夜之外,还有爱欲性的黑夜在延伸;在失眠之夜的背后,还有被遮蔽者的、隐秘者的、神秘者的黑夜,它是童贞女的祖国,它在被爱欲遮蔽的同时又拒绝爱欲——这是言说亵渎的另一种方式。
这段我理解为是对异于存在的描述。“本质上可侵犯又不可侵犯的女性”,“快感之接触本身中的不可触摸者”描述的是不可描述的外在,说明是不可描述的本质,因为不可描述所以有了这样充满悖谬性的描述。“是当前中的不可触摸者——未来”。这是从时间上来理解它的不可描述,因为此刻它并不在场,或说是缺席的在场,是无法被把握住的此在。但不是说它很强大,以至于无法被把握,恰恰相反,列维纳斯说“它未遭谋杀便已垂死,它失神恍惚”。这种脆弱区别于“与其征服者进行战斗、拒绝其物化和客观化的自由那样,而是一种处于非存在之边缘处的脆弱性”。这表明她异于存在的差异性极可能被侵犯。它是如何存在于总体之外的呢,列维纳斯形容道:在作为有之无法名状的沙沙声的黑夜之外,还有爱欲性的黑夜在延伸;在失眠之夜的背后,还有被遮蔽者的、隐秘者的、神秘者的黑夜,它是童贞女的祖国。“童贞女”是不可侵犯的,是我的绝对他者,这里列维纳斯将它比喻为神秘的暗夜,黑色的夜晚遮蔽了差异性,黑色的夜晚的无名,正是处在总体之外的无限外在。是为不可描述的在场。
除此,“上帝”,“死亡”是列维纳斯重点论述其外在性的“主题”(对无法言说的言说),雅贝斯的一篇文论叫《踪迹只在荒漠里》(lightwhite 译),是为纪念列维纳斯而作。他这样说:这就是悲苦,在爱内部的爱的绝望,在痛苦内部的无限的痛苦,在谵妄内部的炽热的谵妄。这就是在其深深的至尊中被租出去的被动。这,如同无底的悬崖,如同一切黑夜的黑暗。
列维纳斯的哲学观念,无非是希望人类走向善,善为第一位的哲学,是伦理学。他人在我面前,他未开口,就以他的别样的存在告诉我一个伦理学观念,他的生命不可侵犯,意味着我不可以杀人。如雅贝斯说:善——首先,在自身当中对他者而言是善的东西,以及在他者当中对自身而言是善的东西。与己为善,与他人为善中,尊重他人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暴力永久缺席,走向和平。列维纳斯是我的绝对他者,列维纳斯的文本是我的绝对他者,使我重新思考与他人的联系,认识生命的要义,丰富了我的思维方式。如果我能够深刻地明白善待他人,反思己过,这首先归于列维纳斯的哲学。另外,由于我的学力所限,还请大家批评指正。之所以会写这篇,很大程度是无法掩饰的热情所致。在这里我将一首小诗献给列维纳斯:
我爱上你
令我心醉
神迷
我爱上你
在寂静中
打探我的消息
明晰
那一种风情
却不曾见
也不曾听说
我爱上你
在差异中
识别
本书能有中译本面世,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终于读到了列维纳斯的原著。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些内容原著表述得更为通透,一些研究此文本的专著对此的理解反而要我一头雾水。当然这也与我的理解能力有关,以及缺少相应的阅读经验有关。这缺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列维纳斯的原著。在此希望越来越多的列维纳斯的著作被译介过来。
在此书的前言中,最后两段里列维纳斯的书写十分令人动容,我将它抄录在这里,同时结束全文:在读者(他们对于这场追求的一波三折自然是如此的无动于衷)的眼中,这就像一座深林,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向我们保证找到猎物。但至少我们想促请读者不让自己由于某些小路的崎岖坎坷和最初的艰难而气馁退缩。必须要突出最初部分的准备特征,但是全部这些研究的视域也要在这里得到勾画。
然后试图打通由书本横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屏障而言,并不表现为诺言。它只属于语言的本质本身,后者通过前—言或注释时时刻刻瓦解着它的语句,反驳着所说,努力不拘礼节地重述那在不可避免的繁文缛节中已被误解之物,而所说却在这种繁文缛节中心满意足。
初稿于2016.10.04
参考:
《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
《导读列维纳斯》。
《他者的境遇》。
《总体与无限》读后感(四):从列维纳斯的“他者”概念看我他关系如何可能
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将同一对他者的欲望开启的伦理关系作为他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中将他者同化为中性整体的存在论—自我学相区别。在前者的哲学中,他者处于外在性地位,是我不能把握的“无限”,他者与我的超越关系开启了伦理的结构,他者的面容和话语为我的自由和责任提供依据。列维纳斯试图突破主体哲学中他人是我可掌握之对象的思维,在总体的破裂下建立起我与他者的关系。
列维纳斯认为,绝对外在于我的他者,是处于至高地位的无限,他不是共同概念下的个体,不可被我的意识把握、还原。他以彻底的异质性成为我的陌生人,他的出现打扰我在家状态的自我主义,对我的自发性提出质疑,使得我打开家门迎接他,跳出内在的自我世界。其中,女性他者的在场使我自身得以在与元素的分离中聚集,这种在我的内部被建立起来的亲熟性成为我居家的内在性条件,为好客、欢迎他人的到来做好准备。
他神显于面容中,始终保持对我的超越,通过面容向我呈现自身,依据自身自行表达,同时又不断摧毁和溢出给我展现的形象。那赤裸、不幸的面容求助于我,但他又不在我的世界,而是处于超越我的支配地位,是高贵和谦卑的统一。他人作为这种无限观念终止了我的权能、激起我的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出于我的需要、不能被满足,它是无利害的善良,只能加深。我通过话语接近他人,这种话语是一种对我的教导、质询,激发起我的善良、唤醒我的责任感,话语使得他人与我建立起伦理关联。
他者作为无限观念的溢出、处于绝对者地位,他者与我关系中的善超越作为总体的存在这三种不同侧面可以追溯到不同的思想来源:笛卡尔、希伯来犹太教和柏拉图。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将上帝视作无限的、完满的存在者。我的思维确定了我的存在,但是怀疑着的我思是不完满、感觉的,正是对无限的观念让我意识到我的有限性,反思的我不停倾向于一个完美存在,不过,我却不能完全理解这样一个无限观念本身,它处于最高等级,不属于提供知识的观念范围,因而我作为有限者与处于无限地位的上帝是彻底分离的[1]。列维纳斯继承了笛卡尔的“无限”观念,将之赋予不可被我观念化的绝对他者。他者不是一个对象,“无限地远离其观念”,保持完全的外在性。正是这种无限的“溢出”在有限中激发起我去接近他的欲望。这种继承保留了他者作为无限的完整、分离,防止他被我表象从而重新被纳入整体中,也给予了他者犹如上帝般的崇高地位,使得与他人接近的欲望能够在我之内发生。
同时,列维纳斯作为一位犹太哲学家,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也明显地影响了“他者”概念的解释。他曾在《塔木德四讲》中,阐释过犹太教如何面向他人的问题。他讲到,并非上帝的他者某种程度比上帝更为他者,我必须在赎罪日获得上帝的宽恕之前得到他人的宽恕;对他人的冒犯本身是对上帝的触犯。因为如果个体得不到尊重,上帝或历史的宽恕就得不到协调[2]。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者的地位在犹太教中与上帝的地位某种较密切的关联,因而他者在列维纳斯哲学中处在很高的位置有其宗教渊源。除此以外,对于我他关系中他者在面容中的神显、话语作为承担责任的原始功能,也在他对《塔木德》的解释中有所体现。
从柏拉图那里,列维纳斯借用了理念作为最高之物来处理我他相遇中的“他者”。理念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是“据其自身”存在的,而列维纳斯则借用这个不被观念化的形象作为他者的进行自我表达的面容,而不是像康德所认为的对外部存在的认识依赖于自我的心灵结构。此外,对于超越的存在者与分离的存在者,列维纳斯还说到,“在柏拉图那里,它则存在于善相对于存在的超越之中。这一论断本应当充当一种多元论哲学的基础……”[3]他认为,柏拉图哲学中对于善的追求高于存在,因而从伦理的善出发的多元论能够超越一元论的总体存在论,这种哲学存在着打破总体的可能。
吸收了这三者思想资源,列维纳斯从对“他者”的解释出发,形成了一种与主体哲学完全不同的角度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
近代的主体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到康德发展到高峰,而胡塞尔继承康德哲学结合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最终将内在自我理解为外部一切事物的构造来源。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主体转向,他把我的内心和我头脑中的观念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标准,打破了从古代到中世纪建立的一套外部的客观真理标准。此时他关注的更多是知识的获得、判断问题,他人和我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他太多关注。他只是将我的存在由我思确定这一结论推论到他人身上,他人是另一种思维确定的主体。我能用我的思维确定我的存在和广延,那么我也可以认识他人、他的思维。笛卡尔哲学处理我他关系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过多注意到伦理在认识论中的特殊性,他将主体的认知能力推广到一切事物,忽略了他人不是能被认识和把握的广延,因此我对他者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源自“我思”。
列维纳斯既有对笛卡尔的继承,又有和他完全不同的考虑。为了防止将他人视为可知的主体,他借用笛卡尔的“无限观念”来说明对他人实际上在不断溢出我对他的把握,通过他的面容、他的话语,他在表达的同时又在将自己不断隐去,超越于可被塑造的形式。在列维纳斯看来,他者的面容、裸露的不幸的双眼向我袒露时,已经在挑战我权能的正当性。我真的能跨越界限到另一个完全独立于我、活生生的他者身上吗?直面他人的脸,这已是界碑。
在康德那里,主体哲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康德看到笛卡尔哲学中作为认识主体的我是有限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他希望可能认识普遍知识的自我能超越自然现实中特殊的自我。在先验哲学的背景下,他将自我分析为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经验自我包含着我当下现实的感觉材料,而纯粹自我则与普遍法则的要求一致。由此,他的认识主体被分为有限主体和无限的道德实践主体。在此基础上,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先天、义务的伦理关系,自我的经验是感性的,理性要求自我排除特殊情感和经验从普遍性出发,实践应然的道德行为,从而实现自我立法和我的自由。一方面,他论证了道德行为来自我本身,并非来自外在的“他律”,但是另一方面,康德预设了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这种道德要求更多倾向于内在自我对普遍准则的承认,但很难不流于形式;他将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视作理性的要求,而不是原初具有的、自然的伦理关系,这种道德观点事实上是为实现主体的理性和自由服务,并不是从对我他伦理关系出发来考虑我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如何安置他人的自由、承担我对他人的责任。而他者在无差别的普遍理性中属于被抽象之物。
不同于康德,对列维纳斯来说,我和他人的伦理关系是自然的、先于理性的,对女性他者来说更是如此。女性他者通过与我既在场又不在场的联系,建立起我自身内部的亲熟性,使得我的在家成为可能。而对非女性他者的他者来说,他的面容已经打开了原初话语,“(这是)理性主义所祈祷的话语的开端”,在表达的话语中,“相对于这种解蔽而言,与表达着自己的存在者的关系已经先行存在着了”。列维纳斯认为,伦理关系先于以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后者作为存在一般的揭蔽是知识的基础,而康德哲学首要考虑的就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伦理问题被放在认识论的语境下被考虑,自然,他者的角色仍然逃脱不了被主体认识的范围,更不用说主体性原则预设了我的自由即实现我对普遍准则的负责,略过了讨论自由发生条件中的他者。在列维纳斯哲学中,他者的面容展露出一种虚弱求助于我,这种命令是一种责任的呼唤,我的自由必须考虑到对他者的责任。如果只停留在把自由理解为主体自己对自己的内心或理性负责,那么就始终停留在单个的我的领域,无法保证自己在实现这种自由时不会伤害到他者。这里也是犹太教中对他人责任的体现,“把人离弃于绝粮之境——是一种任何情况都不能减轻的过错”,[4]列维纳斯说,这无法被拒绝。
最后,深受康德为普遍知识寻找根据影响的胡塞尔继续康德先验自我的道路,但他将我思的主体进行彻底化,越过了康德在先验自我之外设立的“物自体”,使得一切外在的实在世界皆离不开自我能动的意向性构造。一开始的我他关系并未进入胡塞尔哲学首要考虑的范围,他更关注的是认识主体在获得普遍知识的明见性时的位置。他将我思把握为先验的、先于世界存在的。但是,如果在主体中被构造起来的世界要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还必须面对他人如何通达这一世界的问题,否则它就只是我的纯粹内在的意识构造,这使得胡塞尔不得不正面回应我与他人的可能性问题。他在20世纪早期便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却是在后来比较长的时间里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给出解释,在多本著作中都有对此问题的论述,其晚期作品《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第五沉思》对此问题可以算做出了总结。他通过类比化的统觉先对他人身体进行构造,进而赋予他者内在心灵,把他者逐步构造为和我一样的主体,因此在我和更多他者之间才可能形成统一的共同体,逐步证明我所把握到的这个世界对他人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胡塞尔处理我他关系是为了证明先验自我是一切意义构造起点,不但是从我的内在性出发去理解他人,而且没有把有生命的他者和无生命的物区分开来。
与之相反,列维纳斯所反对的,正是胡塞尔这种对他人的把握和构造,胡塞尔将认识论方法扩大到伦理问题中,将我的主体性施加到他人身上,越过了伦理的界限。为避免这种倾向,他者作为不可被我构造的“无限”、他人虚弱的面容、他人对我进行表达的话语等,都是列维纳斯试图去避免胡塞尔哲学中主体对他人施加的“暴力”。
主体性原则自启蒙运动以来已逐渐被普遍接受,道德行为的实施主体在于我而不在他人,为了我的自由和理性我需要对自己负责。不过,尽管康德有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主张,当我和他人相遇时,我真的能考虑到他人的需要而不是把他人仅作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吗?仅停留在我的责任和自由层面如何能突破自我和他者建立真正的伦理关系?主体原则下的伦理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逐步构建了一套冰冷而高效的理性系统以来,人与人打交道时自我保全的特点也逐渐明显。在市民社会领域,为了私人利益的完整,我需要和他人保持距离,在发生经济往来时,他人很容易被作为实现我的利益和目的的“工具”,即便他人有可能得到我的尊重,这也很难被看做一种伦理发生的条件。如果进一步,再放大到国家政治层面,理性的官僚系统中制定政策的人很容易将他者消解为抽象的符号、数字。用一个列维纳斯反对的“总体”比喻也许可以做一个反例,前者就像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主体,而那些承担政策者某种程度可以比作这种主体所要面对的“他者”。这种关系下,伦理和宏观政治目的相比微不足道,居于高位的“我”如何能真正走进“他人”的世界?无数个活生生的人被简化为最大多数人,简言之就是一种人,那么我只需要满足这一种声音的需要,有时甚至可以被强加为这是你的需要。就像2017年末,北京市政府在短短几天内强行清退上百万外来人口,我们不否认他们的居住条件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但是看到政府不给任何缓冲时间甚至动用暴力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我们可以问,那些官僚系统里的人在制定这种政策时有没有把那些无助、绝望的底层民众当成有生命的“他者”呢?
列维纳斯独特的“他者”解释和与之相伴的不同于近代主体哲学的我他关系,构建了为他者的伦理学。他试图使他者离开那种被动的、服从于主体意志的位置,结合犹太教的传统给他者如上帝般崇高、无限的地位,同时这样的他者又不是对我施行暴力、压迫我的居高位之人,而是裸露他的面容彰显自己的脆弱、不幸,想要我对他承担起责任,正是这种责任给予我的自由以正当性。他看到他者很容易遭受来自自我的同一化的暴力,这种暴力的极端就是谋杀、大屠杀。确实,这样一种理论看起来与我们已经习惯的伦理完全不同,尝试站在他者角度重新审视我他关系难道不会阻碍我的自由、我的主体完整? 他人的至高地位难道不会对我施加暴力?列维纳斯可以回应,在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之前,我和他人处于分离状态,我在居所中已经得到满足,与他人的联系并不是为了满足需要,恰恰是因好客向他人打开自己的家。因他人在支配地位时才能质疑我的自由,和我在话语、教导中建立联系,与无限他异性的联系使得我们处于总体之外,这种关系根本上是和平。他将这种社会关联称为宗教。
也许正是因为他者哲学背后和犹太教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让与之距离较远的大多数人觉得难以理解。在他融合了宗教经验的哲学中,不能否认的是亦有一种理想化倾向,这种我他关系也有对谦卑、低下的我和既高贵又虚弱的他人的预设。另外,我的疑问是,这种带有比较浓厚犹太教色彩的我他关系能否符合人类普遍的原始经验?抛弃了总体的多元论依靠着话语就能从根本上维系和平吗?历史如何在保持特殊性的、分离的个体状态下被书写?我觉得他在一些侧面还没有给出比较清楚地说明,有时仅是一笔带过。
总之,哲学家的思想是面对前人遗留的问题为当下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就在于他为长期被遗忘的“他者”打开了伦理学的新维度,他可以让我们对当下习以为常的伦理生活进行反思并参考他的哲学进行选择。依照这种路径,我认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在现代社会是有可能从为他者负责的角度使得陌生人与我得以通达的。
参考书目: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商务印书馆,200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
孙小玲:《从绝对自我到绝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朱刚:《多元与无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
[1]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
[2] 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商务印书馆,2002
[3]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56页
[4]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85页
《总体与无限》读后感(五):“我们孤身一人的处境…”
每个人都易于认可这一点:任何进入列维纳斯的努力都会经历无尽深重的缠绕。[1]
这篇文章要聚焦的则是“我们孤身一人的处境”[2],世界向我奔涌而来的一刻。
它或者是《从存在到存在者》(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里的“有…”(il y a),它令人战栗的窸窣声,在战俘营和失眠的黑夜里;它或者是《总体与无限》(Totalité et Infini)里的“享受”(jouissance),沐浴在阳光和风尘间,幸福的眩晕与潜藏的不安。
上篇 夜之无名
猎狼犬的世纪扑上了我的肩,但是我的脉管里流的不是狼的血,……把我带入叶尼塞河流淌的夜,那里的松树触向了星星;我的脉管里流的不是狼的血,只有相等的人会杀死我。——曼德尔施塔姆:《狼》《从存在到存在者》刚一开篇,列维纳斯便宣告:这本书尽管“很大程度启发自”他曾经的思想导师,马丁·海德格尔;但同时“也受离开这种哲学气候的深层需要所驱使”。要知道,列维纳斯在求学年代曾经是海德格尔和现象学的忠实拥趸,他在少年时期因一战而在俄语区内到处搬家,随后却远赴德法学习胡塞尔、柏格森、海德格尔的思想(甚至还在弗莱堡上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课程)。他谈论胡塞尔直观理论的学位论文把萨特引诱到现象学的花园,但当这位犹太人在30年代着手写作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的时候,却因为传主宣誓加入纳粹而中途夭折了。这次创痛、这次隐约的背叛给列维纳斯带来的影响是永久性的:他几年后的第一篇原创性论文《论逃离》(De l’évasion),据英译者Jacques Rolland的评论,写作时“在德国或法国作为一名犹太人就会被残暴的存在抓获,被那些与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可靠的共在(Mitsein)关系的人们围困着”。而在往后的作品里,纳粹的阴霾和对海德格尔的抗拒时而复返。比如在《从存在到存在者》里,贯穿全书的“存在”(l’être/l’existence)[3]便是与海德格尔的一次别离,同时也是面对时代的呼号。
虽然这时他还没有如同后期作品一样踏出存在之“总体”或是“超逾”(au-delà)存在,只是在刻画存在的变奏,而非“存在的他者”,但这一版的存在却也与海德格尔哲学,“我们时代最闪耀的哲学”背道而驰。如果哲学也秉有自己的乡土性的话,那钟声的敲响、林中空地的开显和“深奥神秘的交缝”就铺设了海德格尔的路途;而在德军战俘营里写作的列维纳斯,他“本真”的感觉却是破碎、动荡,以及被子包裹住自己也清晰可闻的“存在的匿名窸窣声”:
我们在战俘营里描述的,以及在这本解放翌日出版的作品里阐述的“有…”(il y a),可以追溯到我们童年所萦怀的其中一种奇异缠绕,每当寂静幽幽作响,而空虚充盈欲满时,它就会在失眠当中重新浮现。“我们总已经活动在对存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海德格尔的这句名言历久弥新。只不过在列维纳斯的经验里,存在不是人们借以理解世界的曜光,而是无法用反思去把握的、陌异的(étranger)黑夜,它仿佛从世界的外缘突围到我们身边,与光的秩序全然相异。这样的存在被列维纳斯称之为“有…”(il y a)。Il y a(英译为there is)是法语里的无人称句,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被说出来,
(1)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被说出来(il y a…):光照的缺失使得事物的边界和轮廓迷离恍惚,物与物之间不再清楚分明,无从寻觅存在着的对象(objet qui est)[4],但正是在这种对象-客体普遍的不在场里,“有…”彰显为悖论性的在场,而人们也只能以无端崖之辞去勾勒它:这是一片无法还原的“沉重氛围”和躁动(grouillement),是描述现象学无法描述的[5]“存在-密度-场”(乃至有学者将之与否定神学联系起来),是单调的、缺乏形式的质。昨夜星辰昨夜风,夜是不在场的在场。
(2)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把它说出来([il] y a):我不知道“有…”从何处来,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诞生、不知道死后会尘归何处一样,科学的解释(地球自转、卵细胞受精、有机体分解)搀扶着我们沿着因果链爬升,但受神学影响甚深的列维纳斯则提醒人们要注意因果链断裂之处、它无法溯回的谜团(énigme):黑夜、诞生、死亡,作为谜团的现象埋伏在所有的日常性背后。黑夜是匿名的。
(3)我们也不知道“我”在无人称句里的语法位置。“无东无西,始于玄冥”,我与夜色融成冗长的黑影,意识的注意(l’attention)被无人称的警醒(vigilance impersonnelle)替代,前者锚向客体、将意识灌注其中,假设了指挥着它的主体的自由和权能;而后者则仅仅是我们失眠时躺在床上、双眼一睁的警醒和“熬”夜(la veille),我们即使在“思考”,也没有充当思考者,而更像是无名的思绪在黑夜里漫流而过,用列维纳斯更为后期的术语来说,或许这就是对被动性的经验,最小限度内的主体仅仅是一具受体、一位接受者,一个宾我而非自我,我冒险将之称为最小程度的自身(soi)。
恰恰是这样的含糊性(équivoque)——人称和事物的消隐、沉默——使得我们被“交予”(livrer)“有…”,而不是凭借自由意志或是能动性“通往”存在[6]。
事到如今,我们大致描述了在列维纳斯语境里作为“有…”的存在,它的三个性质:作为氛围而非对象、作为谜团的匿名性,以及失眠者在其中作为最小程度的自身。此时拥有自由和权能的自我尚未降临,如今只有不得不面对“有…”的宾我,他无能为力,无路可逃。
这就是为什么列维纳斯,这位黑夜之子,难以体会我们面对存在时的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会是面对死亡的畏(angoisse),也即是“向死而在”。因为我们被存在“紧紧裹挟,像黑夜一样使我们窒息,而它不作应答。”“有…”令人恐惧(horreur),使人“害怕存在”(peur d’être)。我们在失眠的时候、在各种形式的“猎狼犬”虎视眈眈的时候就会重温这一幕:
“有…”……它的事件本身就在于一种不可能性——在于一种与一切可能性的对立——入睡的不可能性、松弛的不可能性、瞌睡的不可能性、不在场的不可能性。失眠是《从存在到存在者》的典型场景。梦魇般的当下在无限延续,不像游戏一样随时可以抽身离开。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被转译成“死亡的不可能性”,“有…”宛如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幽灵和鬼魅[7]重返人间,失眠者却不得不承受这些非人之物。存在的喃语使我们“害怕存在”,而不是“为了存在而害怕”(peur pour l’être,列维纳斯对“畏”的解析)。或许恐惧就是最初的“伦理”事件,尽管这里没有面对面,而只有躺尸似的自身和“有…”的重压,不过是无伦理的伦理,布朗肖就说:
通过恐惧,我们出离了我们自己,被抛到了外部,在令人恐惧之物的形态下,我们体验到了完全外在于我们、他异于我们的东西:外部本身。这是与他异的存在相逢的片刻,我们与陌异性本身的关系。如果说,“存在的匮乏即是恶”这一久远的传统由海德格尔所继承,从而存在与虚无的双生戏法只是为了让存在者走近存在、“为了存在”的话,那么,列维纳斯,这位纳粹的战俘则敢于直呼:“存在从本质上是陌异的”,以及: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纠缠不已的恶。人类要面临的最沉重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存在。
当然,这一结论里所援引的存在是“有…”,一种以黑夜为它的特征形态的存在。“存在本身即是恶”不是一个先天为真的论断,而更多是列维纳斯写下的战时笔记,以及对没有兼顾到这重重黑夜的战前哲学的控诉,把存在指认为不可知论式的黑夜大概只有对存在论秩序的异乡人来说才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从存在到存在者》的同情性阅读得以可能的条件便是,我们与他经历了相似的黑暗,能体会他作为犹太人,被投入战俘营、与妻女分离,无时无刻都在侵袭着他的恐怖气息。或许在2020年的初冬我们会尤为感同身受,人与人之间被不可视的病原体和政治机器隔离开来(不就是“有…”的忠实写照吗?),即使在白日也过着夜行动物般的生活。
或许离题了。
“从存在到存在者”,我们至今也只讨论了存在,而作为能动主体的存在者则直到这一时刻依然销声匿迹。毕竟我们先前涉足的“有…”被列维纳斯与不可能性——总归是逃脱存在的不可能性——捆绑在一起,看起来,存在者的降临还遥遥无期。
但读者会发现,《从存在到存在者》在经历“失眠”这一节后便仿佛经历了一次震荡,第一句话便是显眼的“入睡的可能性”。入睡就是对黑夜之“有…”的逃离,却不是要逃往哪个理想国度,而只是要躲避过分充盈的存在。
但入睡如何成为不可能性中的可能性呢?入睡又与尚未到来的存在者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虽然“有…”看似没有出口,我们无路可走,但列维纳斯的时间观又为他无中生有出一条生路:时间是转瞬即逝、无法延续的,“时间并不像江河一样在流淌”,而是由瞬间(instant),而且是相互独立的、不可分解的、作为事件的瞬间铰接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次重新开始,一次创生,这就使得瞬间能够作为绝对的当下,像耍魔术一样卸去过去的重负。所以,就像笛卡尔突然迸发的“我思”一样,失眠者——它曾经只是在“熬”夜的自身——,他的意识就有可能在某一瞬间刺破夜空,降临到他身上。
同时,失眠者的“原意识”,按列维纳斯的思路,是位置感和方位感,即“这里”(ici)。我意识到背负着我的场所(lieu)和基础,毕竟按照列维纳斯对“我思”的强力阅读,我思通往的是第一人称现在时的“我是一个思想之物”(je suis une chose qui pense)——这里面的“物”字彰显的是“作为实体的思想,也就是说作为某种被放置(se pose)之物的思想。”实体(sub-stance)的前缀sub-表示的便是“在……之下”,“这里”是意识的收敛,收敛至我被放置其上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在其后被充实为床褥或是大地。“这里”已经迈出最小程度的自身了。
待到下一步,我不仅仅拥有了对“这里”的方位意识,还会滋生“我在”这里的身体感,或称体感(cénesthésie)。列维纳斯同样把身体唤作事件,我“突然”(作为事件的瞬间)意识到在床褥之上还有我的身体,我从一个失眠的极点充实为占据空间的身体。“睡眠的呼唤产生在躺卧的动作中”,身体感是入睡的可能性,漂浮在黑夜中的失眠者意识到底下有什么东西(场所)在托负着他,而在这场所之上的恰恰是他的身体。
这是一场从匿名的“有…”中赎回自身的运动,原初的差异化事件,一连串精细的事件发生在奇迹般的瞬间里。列维纳斯称之为存在者在存在中间的名词化运动,或称出显(hypostase,这个法语词在宗教上有“位格”之义),出显要探寻的是“名词(substantif)的显现”,而溯源至哲学史的话,则标示的是“由动词表达的行为转变为由名词表示的存在这一事件”。名词指称的是实体,而被“有…”的夜色掩埋的失眠者则难以称得上是实体,甚至连失眠“者”也只是权宜的代称。惟有当他被放置到“这里”、拥有了对自己身体的意识后,他作为一个被托负的实体才总算浮现出来。通过出显,存在者(existant)在无人称的存在(existence)[仅仅是一个辅音的消泯] 中显现自身,“存在者所承担的存在(l’être)从今以后是他的存在(son être)”,存在被所有化了,存在者在昏昏然的边缘域(“有…”)之中确立自我。这是权能的开端、自由的原点:我可以入睡了。
列维纳斯又把这一系列的、从“这里”到身体的意识发生学看作是手刃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利器,ex-istence的前缀表向外绽出,但在列维纳斯的构想里,至关重要的、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出离(ex-)是与匿名存在的告别、出显为存在者的运动。这反倒是向自我的撤回(repli,无论是“这里”,还是身体,还是名词化,都是向内回转的运动。列维纳斯称海德格尔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distinction)没有抵达(或:不够“源-初”)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分离(séparation)——无存在者的“有…”——以及作为动词的去-存在无法赎回存在者在“有…”/存在当中的名词化过程——这“完全年轻的瞬间”。至此,《从存在到存在者》这份长篇缴文就基本告一段落。
当然,在结尾处列维纳斯还匆忙预告了他者的到来,但这篇文章的论证负担已经像“有…”一样将笔者折磨不已了。我只好专注在“我们孤身一人的处境”。
不过,还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列维纳斯在《存在与存在者》成书三十年后的增补的“第二版序言”里,列维纳斯也自忖,书里一连串对存在论差异的颠倒仅仅是“第一步”[8],而且“它可能有些时候过于匆忙地论定了这个概念[注:即‘有…’]所包含的诸多可能性”,因为出显是主体从中性的存在/“有…”之中的突围,但“去-中性化(dé-neutralisation)不会携带真正的人道意义……而会转向无动于衷(indifférence)……”这可以看作列维纳斯(乃至我们)转向他人和人道主义的契机。
而在接下来的《总体与无限》之旅中,我们将会看到“有…”所包含的“诸多可能性”,同时也是“我们孤身一人的处境”的诸多可能性。
下篇 世之将倾
时代流入一个人体内,流入一个王国……昨天你还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强壮有力,还是时代的宠儿;然而,今天另一个时代来临了,你还被蒙在鼓里呢。——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从存在到存在者》(1947)再到《总体与无限》(1961)需要经过一座战前与战后之间的莫名桥梁。
战俘营里夜夜相伴的“有…”在战后春光的抚慰下回归日常,失眠不再像梦魇一样吊挂在字里行间,取而代之的主线是与他人的相遇 [第三部分“面容与外在性”],是“超逾面容”的、与爱人与孩子的关系 [第四部分],以致“《总体与无限》被熟知为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
看起来,战争的创伤和“我们孤身一人的处境”已经被边缘化。
但是,按照《总体与无限》的叙述顺序,我们依然能看到在自己被“呈交”给他人之前,依然拥有与他人相分离[9]的内在生活 [第二部分 “内在性与家政”],这是《从存在到存在者》的延伸,毋宁说是重写;而且,他人“只有从一个自我出发才能被见到”,这预示着论述自我、论述他人的前史的这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思路都在怂恿我们探讨《总体与无限》与《从存在到存在者》之间的互文性。而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会先从《总体与无限》第二部分的关键词“享受”出发,讨论它的各种相互勾连的形态,并且等待“有…”的再次袭来。
我们在过活(vivre de)。我们还在享用(vivre de)[10]生活,享受生活。我们享受食物,我们享受“劳动、观念、睡眠”。享受,我们沉湎(se nouririr de)[11]其中的活动,是与生活的接轨方式。它的前身或许是《从存在到存在者》里的浸泡到“有…”当中的“无人称的‘意识’”(«conscience» impersonnelle),享受是朝向自身的收缩和旋转,像是在不停吸气一样,是撤回至自身的感受性(affectivité)。这种回撤运动我们刚才在黑夜里见识过,对“这里”的意识以及体感。不过存在者并不会立即在享受的洪流间现身。
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里运用了一对新范畴,同一与他者,来阐明这种运动。享受是他者的同一化,这些他者是我们享受的事物。同一同时涵盖了自身(ipse)和相同(idem)两义,同一化即是事物逐渐被享受者吸纳的过程。享受与朝向他人、奔向外部的伦理学运动相对,是朝向自身的运动,并且“冲撞着大地的陌异性本身”。
我们接下来试着描画享受的三种形式:
(1)享受食物。食物作为外在之物是相对于自我的他者。享受食物与表象行为截然不同,进食(alimentation)是“对意义的溢出”,通过意识活动构造出来的“意义”无法充饥,无法解渴,无法满足需要(besoin)[12]——需要是享受的配偶,是肉体上的、可被满足的需要。满足需要的途径即是将他者同一化。意识活动要后于食物,甚至要受食物的制约(例如:喝红茶不能尝出辣),而这他者通过我们的口腔、我们的消化系统被咀嚼,被吸收,“对存在的啮食”将面包片和红茶的陌生力量消磨殆尽,招安为与我们同一的养料,满足我们的需要。
(2)而其他事物乍看上去难以兼容上述隐喻,但它们依然“指向我的享受”:
作为物资或用品,日常使用对象从属于享受——打火机从属于人们抽的香烟,餐叉从属于食物,酒杯从属于嘴唇。这番论述的要紧之处就在于,列维纳斯拓展了我们对“事物”的理解(John Salis语),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不只是对象,也不只是用具/工具,它们不是相互指示,而是内缩到我的享受行为中,成为“为我”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享受这“同一的漩涡”来捲动,乃至“预设”了享受,事物与人秘密地关联在一起。(1)中的隐喻——将他者吸纳到我的同一性当中——从进食-消化的具体行为延伸至整个对象世界:桌子供我看书,电脑供我玩游戏……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养分,这,就是生活的自我主义。
(3)但我们享受的也不仅是具体的对象——正如我们沉没其中的“有…”也只是无形的氛围——还有环境(milleu),或称元素(élément,亦有“环境”之义),事物
处身于空间中,沐浴在空气里,扎根在大地上,坐落在大街小巷。环境对于事物来说始终是本质性的。事物在元素中显现,又在享受中“返回”到环境里,仿佛一个词和一句诗一样,我的阅读过程(享受)在两者间交替穿梭。环境仅仅呈现出一面(face)——我们可以捧着鼠标,反复转动,来构造它的模型;但大海和季风都只有唯一的侧面——列维纳斯又旋即补充:“真正说来,元素根本就没有面。”观看者早已内在于环境里,沉湎其中(或:沐浴其中),这是一种“没有出口的内在性”,没有边界的纯粹的质。
之前也使用过相似的描述来形容“有…”。
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被续写为“在元素之中存在”。骄阳、白雪、冬天的街道,雪覆盖了小汽车……事物和它们的环境接续映入眼帘,被给予(donné)到我们——享受的内转运动连绵不绝,“一如不断地淹没、吞噬、把我席卷而去的波浪”[13],我来不及思考,“我接纳(accueillir)它们而不是思考它们”。
进一步而言,列维纳斯以感性(sensibilité)来勾画我们在元素中的享受方式。感性是“未经反思的自我的素朴性”,但又越出本能——列维纳斯仿佛在与弗洛伊德,这位在《超越快乐原则》里通过细胞生物学论证本能/驱力的大师进行一场隔空的对话,享受的生活才是属人的生活——感性不指向任何对象,皆因“任何对象都分解为享受沐浴其中的元素”,感性只是沉浸在元素这“没有支撑者的纯粹质”里。它不像梅洛-庞蒂的知觉那样,建立在现象间的层级之上,并筑立起世界秩序;而只是“终止于所予物,不去直面任何未来和可能性”(Alphonso Lingis语)。或者按列维纳斯本人的用语:享受“满足于”所予物。列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里已经为享受和感性可被满足、“它直接处在终点处”的特性预备了一个雏形:意向的真诚性(sincérité),“对象与欲望(désir)[14]之间准确(exactement)[15]一致的结构”。而幸福(bonheur),则是需要的全面满足,享受的高峰时刻使人们“变为存在的主体”——这是同一化运动的高潮,发生在一个清白无辜的瞬间。这是一场事件。幸福是《总体与无限》版本的出显,但幸福不是从“有…”当中绝处逢生,而是享受的正午时分。周围世界的他异性被膨胀的自我挤压出视界之外,由享受的运动凝结而成的存在者在这宛若天堂般的图景中浮现出来。
就好像,战俘营的地狱一季里蕴含的恐怖记忆都被冲刷干净,“当下即未来”的战后幸福生活充斥在《总体与无限》的每一行字之间。但是,
难道“有…”不就像阴影或是幽灵一样出没在列维纳斯的作品里,像一具反反复复归来的亡魂,从无意义、中性和含糊性的时分归来吗?我们走到了与《从存在到存在者》接壤的边线。
幸福是机运所致,“食物之到来就像一种幸福的偶然”。从幸福中自我奠基,或是从“有…”中入睡,看起来——尽管在和平时代这么说会有点奇怪——一样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事件。总会有一些时候她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面包,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城市会不会在顷刻间被大雨淹没。我们的幸福总会消逝。将来(avenir)不代表总是在到来(à venir)、尚未到来。或许已经到来。一份致命的不安正在临近,享受隐隐约约昭示的是不稳靠性(insécurité)。
皆因元素的起源并不是任何能够出显自身的实体,它们来自无处、来自“无何有之乡”,是虚无的畸胎——乃至我们只能说:元素是无定性(apeiron)[这是一次对前苏格拉底文本的微妙嵌合:其余的arche遇见渊深之apeiron],却不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元素的泉源是深不可测的无端,就像“有…”一样是匿名的,或者说:这是元素神秘的无面状态。阳光和海洋的背面是非人格者——“元素延伸到‘有…’之中”。
我总归在黑夜的边缘滑行[16]。享受是“并不与自身一致的自我之振动”,我们每时每日都投身其中的享受终究还是暴露出它深渊般的差异化运动,“有…”的陌异性始终在威胁着享受,尽管人人都会忘记这点。这就使得我们所有的内在生活比起是天堂更像是一座孤岛,享受的不稳靠性在周围“勾勒出一道属于虚无的边线”。
但是,按列维纳斯的说法,也正是这摇摇欲坠的“孤身一人的处境”把我们带到家和居所里。家是黑夜的弧边。家拥有“治外法权”,是护佑着我们的秘密乌托邦。家与元素保持距离(尽管“距离本身…既是疏远又是接近”):沐浴在元素里的享受转渡为透过窗户对元素的观看,列维纳斯称之为享受的延迟,家使我们能够从元素中抽身而出,而通过“支配性的目光”去占有元素;与此同时,劳动也能通过我们的双手(捕获的动作)去掌有元素,把弥漫在天地间的元素归为家里的动产。而正是凭借眼睛和手、家与劳动,对元素的占有行为悬搁了享受的不稳靠性——却不是对它的消除,而只是对末日的永恒延迟。占有比幸福在同一化的程度上更进一步,存在者在幸福里经历了他的个体化时刻,而占有则赋予他权能以及自由,赋予他操纵周围世界的能力和可能性。
只不过,占有是隐藏的暴力行为。人类在大地上筑居、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听起来像是地球村口耳相传的英雄史诗。但占有和享受,这些同一化运动都建立在抹杀他者的他异性之上:食物曾经是无数的生灵,我们的居家又挤占了多少大自然的领域,又有多少人已经无家可归?幸福是自我主义的原罪。所以,在《总体与无限》接下来的部分里,列维纳斯将要求自我,孤身一人的自我转向他人,迎接这场至高的审判。
我们嗅到了弥漫在《总体与无限》里的哀悼色彩。相比《从存在到存在者》,写自战后的《总体与无限》(的第二部分)反映的是人们在废墟之上重建个人生活的尝试,试图在元素的普照下完全忘却战争的黑夜。但幽灵从来不会缺席。一枚又一枚鱼雷埋伏在我们自以为幸福的孤岛生活之下,世界随时倾倒,而即使我们运用人之为人的才智,去筑起房屋庇护自己、去炮制工具增添力量,也只不过把世界的背叛时刻一再推迟。
但它依然还在这里,请不要忘了它。无可言明的“它”。
[注:我省略了所有只标注页码的注释。]
[1] 篡改自“每个人都易于认可这一点:知道我们是否没受道德的欺骗极其重要。”(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页)
[2] 篡改自“la situation où l’on n’est pas seul……est conscience morale—exposition de ma liberté au jugement de l’Autre.”(“人们并非孤身一人这一处境……就是道德意识——将我的自由暴露在他者的审判之下。” Levinas : La philosophie et l’idée de l’Infini [暂缺页码])
[3] 或许,至少在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以及Le temps et l’autre这两本书里,existence/exister不应翻译为“实存”或“生存”,毕竟列维纳斯本人曾经述明:“让我们再次回到海德格尔。您不会不知道他的区分——我已经用到过了——在Sein和Seiendes之间、être(存在)和étant(存在者)之间的区分,但为了谐音的缘故(pour des raisons d’euphonie),我更喜欢用exister和existant来翻译,倒不是赋予这些术语以生存论(existentialiste)上的特殊意义。”(Emmanuel Levinas: Le temps et l’autre, Quadrige, 2004, p.24)但John Salis指出,列维纳斯自己在《从存在到存在者·》中曾区分开“个人、种、集体、上帝这样一些由名词指称的存在者们,以及它们的存在之事件或行动(l’événement ou l’acte de leur existence)”(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15),而将存在(Sein/existence)看作行动(即使是存在的行动)都像在重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曾经击碎的传统概念。(John Salis : Levinas and the Elemental, in Claire Katz and Lara Trout (ed.) , Emmanuel Levinas :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umeⅠ)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353)
[4] 柏格森的“被划掉的存在”(l’être biffé)。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103; 另参 Philip Lawton : Levinas’ Notion of the “There is”, Emmanuel Levinas :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umeⅠ) , p.253
[5] “[描述现象学的] 描述要呈现的是人物(des personnages),而‘有…’却是它们的消散。”(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112)
[6] 同样是与海德格尔的潜在对话:“Au lieu de servir à notre accession à l’être, l’espace nocturne nous livre à l’être.”(“夜的空间不会帮我们进入存在,而是把我们交予存在。”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96,加粗为后加)
[7] 值得一提的是,列维纳斯终其一生都在重返这个例子——无论他思想的其他部分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动。
[8] “这种颠倒仅仅是一次通往比存在论更为古老的伦理学的运动的第一步……”(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Préface à la deuxième édition)
[9] 这样的分离“为无限观念所要求”——无限的维度由他人开启——也正是它才使得与他人面对面的伦理关系“得以可能”(《总体与无限》,第34页)。
[10] 这是列维纳斯的文字游戏:vivre de的两重义项,见《总体与无限》第88页朱刚老师的译注。
[11] “对于行为来说,那种沉湎于(se nourrir de)其活动本身的方式恰恰是享受。”(《总体与无限》,第90页)
[12] 在列维纳斯的语境里,需要仅仅指可被满足的需要,与指向并不缺乏之物、指向“无限观念”的欲望(désir)相对。
[13] 《总体与无限》,第116页。抑或这也是列维纳斯的文风本身?“…没有一般哲学论证的那种仿佛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而是一股仿佛从遥远地极升出的力量推动着语言像排浪一样不知疲倦地冲击着彼岸。”(刘文瑾:《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他人的面容与“歌中之歌”》,三联书店,2012,第43页)
[14] 列维纳斯在《从存在到存在者》里大概还没有区分需要(besoin)和欲望(désir)——这里的欲望应当更接近于《总体与无限》里的需要。
[15] 据姜宇辉老师指出,exactement除了“准确的、精确的”这层含义,还有“真实的”(qui respecte la vérité)这层“更重要的”含义。笔者在此游移不定,暂译为“准确”。(姜宇辉:《“无世界的他者”与“无他者的世界”——深入解读<从存在到存在者>兼论列维纳斯与德勒兹的差异》,收入《列维纳斯的世纪或他者的命运:“杭州列维纳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2页脚注)
[16] 这会让人忍不住联想到拉康-齐泽克的jouissance(与列维纳斯的“享受”是同一个法语词,或译为原乐、痛-快),朝向死亡驱力的极度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