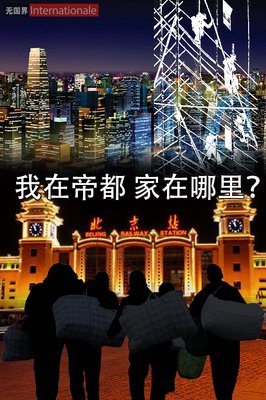
《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是一本由[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学时代读过的第一本书是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大一的时候上过德语文学通识课,当时报告做的是布莱希特的长诗《老子出关的传说》,获得了老师的肯定(大概是大学第一次被老师表扬?),很遗憾这本诗集没有收录。当时查阅资料就发现布莱希特的诗竟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也很关注。不知道是翻译的原因还是作品本身,抑或是读布莱希特的同时我还在读米沃什,总之这本诗集不够打动我。布莱希特善于叙述,也善于抒发,但是过于叙事化、政治化的诗歌,缺失了不少诗本该有的味道——隐喻、深刻。希望以后布莱希特的翻译可以由德语直接翻译,最好再多加一些注释。
●布莱希特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和众多以“我”为支点,深入挖掘内外自我的现代诗歌不同,他把自己“代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角色”里面,以戏谑,夸张,反讽等戏剧手段表现与自我视角迥异的东西。他的诗无疑是追求社会效应与读者反映的,他表面上故意放低身段,像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取悦读者,骨子里却相当严肃,克制与保持智性的冷静。
●诗歌还是应该直接从德语原文译出。黄老师是很有经验的诗歌译者,可惜因为从英译本译出,准确性打了折扣。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德国戏剧家,诗人。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一——史诗剧的创立者。 我承认,我没有希望。盲人奢谈出路。我看见。当错误作为我们最后的伙伴也被用光,面对我们坐着的,是虚无。 去哪里呢?不知道。远离谁呢?你们全部。 那是相爱的一对。 你也许会问:它们在一起多久了?一会儿。 这之后它们会怎样?各走各的。 看来是爱牢牢维系着相爱者。 要做到当你离开世界,不仅你是好的,而且留下一个好世界。 在黑暗的时代,还有歌吗?是的,还有关于黑暗时代的歌。 马雅可夫斯基的墓志铭:我避过鲨鱼,杀过老虎,吃掉我的是臭虫。 我,幸存者。
●使人开心的诗。一个人能这么坚强又温柔又直接地活着。布莱希特同志
●流亡時期詩尚可
●他那完美的政治抒情诗至今读来仍觉熟悉,是他的伟大,更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平庸。
●晚期的很好。
quot;我不需要墓碑,但是 如果你需要为我立一个 我愿意它刻上这些字: 他提出建议。我们 把它们落实。 这样的铭文将使 我们大家都增光。”
致后代
“确实,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 不狡猾的话是愚蠢的。光滑的前额 暗示感觉迟钝。大笑的人 无非是还没有接到 可怕的消息。 这是什么时代,当 一次关于树的谈话也几乎是一种犯罪 因为它暗示对许多恐怖保持沉默?”
《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读后感(二):诗歌是对社会不公的抗议
布莱希特写了很多有力量的诗,描写贫贱者的命运,这些诗脍炙人口,可一读再读。 比如《妓女伊夫林.罗传奇》;《关于杀婴犯玛丽.法拉尔》;《给迈克的煤》等等。 他也赞扬爱情。我最喜欢的是《汉娜。卡什》之歌,没有钱的女子爱上了一个水手,风雨同舟五十年,尽管没吃没喝。 他的情诗写得很深情,如“情歌之四” 我最亲爱的人给我一根树枝 树枝上的叶子是褐色的。 已经快到年底了, 而我们的爱才刚刚开始。 在《学习赞》中,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因为 “开始吧!你必须了解一切!你必须取得主导权!” 在《补丁和外衣之歌》中,他清楚地说明无产者的诉求 我们要的不只是补丁 我们必须要一件全新的外衣 我们要的不只是一片走味的面包皮 我们必须要整个新面包 我们要的远不只是找到一份活儿 我们必须要全部的工厂 还有煤矿和钢, 还有控制国家。 还有其他很多好诗,智慧、幽默、随时都在质问自己的良心。
《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读后感(三):为什么要提到布莱希特和他的政治诗
一、为什么要提到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说:
“为什么要提到我的名字?
1
我曾经想:在遥远的未来
当我住的房子已经坍塌,
我坐的船已经腐朽,
我的名字仍将和别人一起
被提到。
2
因为我赞美那有用的,而这
在当年被认为是卑贱的;
因为我与所有宗教斗争,
因为我对抗压迫或
因为别的理由。
3
因为我为人民,
并把一切交托给他们,从而尊敬他们;
因为我写诗并丰富语言,
因为我教导怎样做人或
因为别的理由。
4
所以我觉得我的名字仍将被
提到;在一块石头上
我的名字将留下;我将会
从书里被印入新书里。
5
但今天
我承认它会被遗忘。
当已经
有足够面包,为什么还要面包师?
当新的
降雪就快来临,为什么还要赞美
已融化的雪?
如果有未来,为什么
还要过去?
6
为什么
我的名字应该被提到?”
二、布莱希特为什么写政治诗?
布莱希特说:
“我心里觉得
那开花的苹果树很惬意
而那房屋油漆工的演说则很恐怖。
但只有后者
才会驱使我走向书桌。”
“我总是想:最简单的话
已足够。当我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的心一定会被撕成碎片。
如果你不挺身捍卫自己你就会倒下去
这你肯定明白。”
“你们,将在我们被洪水淹没的地方
浮现出来的人啊,
当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
请你们也记得
你们逃脱的
这黑暗的时代。”
《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读后感(四):请带着宽容想起我们
了解到布莱希特是因为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引到的他的诗《怀念玛丽安》。后来才意识到自己早已听过他的大名,是在表演相关的讨论中。
不懂诗歌,所以只简单谈自己的理解。
政治讽刺诗很多,读来让人感受到作者的良心,尖锐,痛苦和挣扎。再了解到他二战期间曾经流亡的经历,愈发对布莱希特仰之弥高。
最初报告我们的朋友被屠杀时,有人惊呼。然后是一百个人被屠杀。但是当一千个人被屠杀并且屠杀不会停止时,沉默便扩散开来。 当做坏事像下雨,没有人会叫声“停”! 当犯罪开始堆积起来,它们就变得看不见。那些获进贡的人 要求人们牺牲。 那些吃饱喝够的人向饥饿者描绘将来的美好时代。 那些把国家带到深渊里的人说统治太难.....鉴于那个政权的强大力量, 它那些集中营和酷刑牢房, 它那些吃饱喝足的警察, 它那些受胁迫或腐败的法官, 它那些装满一座座建筑物的 卡片索引和疑犯清单, 你会认为他们用不着害怕 一个单纯的人公开说的话。还有同情心:
但我怎样又吃又喝,如果我吃的 是从挨饿者那里夺来的, 而我这杯水属于一个就快渴死的人?他们愈是受苦,他们的受苦似乎就愈自然。谁会去阻止海里的鱼受潮湿? 而受苦人自己也用这种……漠不关心对待他们自己,缺乏用善良对待他们自己。 多可怕,人类如此容易忍受现状……呼吁弱者联合起来:
所有那些思考世风如此败坏的人都拒绝呼吁一群人同情另一群人。但是被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是不可或缺的。点题的《致后代》一首,感觉也是充满了丰沛的感情,对后代的丰沛的感情。
愤怒,即便是对不公正的愤怒也会使声音粗哑。啊,我们 这些想为友善铺设基础的人自己却不能友善。 但你们,当人终于可以帮助人的时代来临,请带着宽容想起我们。作为诗人的痛苦和自豪感也在诗集中出现多次。他写的《探访被流放的诗人们》让我笑死,简直是诗人们的同人文。
布莱希特对中国人也很有兴趣。诗集中好几次提到了中国。对了,他还有一部剧,叫《四川好人》。
情诗也很美,怪不得一辈子不缺女人:
当我们夜里躺在彼此怀中, 月亮也不如你。就是有些诗让女性看起来不舒服:
你可爱的摆动使我想起科尔基斯, 当那天美狄亚漫步走向大海—— 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要你穿这么一条裙子的理由。低级理由对我已足够。还有基♂情:
两条独木舟 从眼前滑过,舟里两个青年 赤身裸体:他们并排划桨, 谈着话。最后,这么薄一本我读了半年才读完,惭愧。
《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读后感(五):布莱希特:车轮下的良心
“一个人要不被车轮压死,需要多大的运气啊,我真感到惊诧!多少突如其来的思想!多少个朋友!”
这是布莱希特在剧作《四川好人》中发出的感慨。另一位处于困境之中的读者,自然会深刻地记住这样的句子。确实,一个正直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早或晚地会遇上自己的道德焦虑。突如其来的思想和一定数量的朋友,也许并不重要,总会有那样的时刻,你将在镜中,确认自己心脏的位置。无论以何种方式,一个人总是会向前走下去。
可以想象到,同样地,写作也是某种纾解的方式。那样的焦虑,必定事先存在于写作者的经验之中。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这也是建立关系的时刻。作为一位经典作家,这是布莱希特初次向我呈现的情境。
对我来说,布莱希特实在是一位特别的作家。读到《四川好人》,正是在自己广泛阅读外国文学的时期。布莱希特的剧作译本,是不可被绕过的文学经典,我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些作品中,另一部使我不得不回想的是《伽利略传》,“从黑暗中走出理性,它一天都守卫在大门前”。
而我第一次记住他的诗作,是在汉娜·阿伦特的评论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译者是王凌云、谭毅。在关于布莱希特的那篇文章中,阿伦特引用了这一句:“不再顾念他的整个青春,但唯独不包括梦幻;/长久地遗忘着屋顶,却永记屋顶之上的天空。”屋顶上的天空,保有澄澈的蓝色,它仿佛只在人们沉睡时才显现。“黑暗时代”这个词语,正是阿伦特从布莱希特诗作中摘引出来的。
再一次被布莱希特触动,是在那首《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译者是绿原:
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 在一条落雨的村路上 黄昏时分我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鞠躬示意,求我们带他一程。 我们有房屋,我们有空间,我们把车开过去 我们听见我悻悻地说道:不 我们不能带任何人。 我们走了很远,也许有一天的行程 这时我忽然吃惊于我的这个声音 我的这个言行和这 整个世界。这种惊讶,也传递给了我们读者,带着一种曾经发生过的隐痛。我想起一幅外国画家的作品,在临近海边的一片田野里,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前行,他的身后跟随一个透明的鬼魂,它有一只骷髅头。也许我可以复述出那样的场景,但很难传达出同样的情绪。
诗人批评家张定浩曾经谈论过布莱希特诗歌在汉语中的处境,他的感慨是,从德语直接译出的诗作,反而不如从英文转译的更好。当然,这也是因为那时的市面上很难找到布莱希特的诗集,我们也无从了解诗人的整体轮廓。现在,经过等待之后,一本相对完整的布莱希特诗选终于得以出版了,译者是黄灿然。
整本诗集按照时间顺序编选,将布莱希特的诗人生涯分成了七个时期。我在灯光下摊开这本黄色的诗集,从中寻找自己所需的事物。首先,我查阅了那首“屋顶之上的天空”,还有那首“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果然,这两首作品都选入了书中,并且标注了写作日期,前一首写于1917年,后一首写于1937年。而黄灿然先生的译文有所不同,这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接着找到的,正是《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惊讶。“但这一切,哪怕是最熟悉的部分,/我都使它们产生惊愕。/一位母亲给孩子哺乳,/我描述得难以置信。/一个看门人把一个冻僵的人拒之门外/我表现得闻所未闻。”这是1935年的《剧作家之歌》。布莱希特用短短几句话,勾勒出这种“惊愕”、“漠然”、“怜悯”交织的情绪,也重复展示了《四川好人》中的两极处境。而这种简明、清晰、线条式的诗歌语言,正是他所擅长的。
似乎布莱希特,正属于席勒所说的“天真的”诗人,或者用另一种译法来说,是“素朴的”诗人。他的简练、他的箴言体、他的社会实践和写作文本混合起来的一种综合形象,都使得他与另一类“感伤的”写作者完全不同。黄灿然在译序中引用了乔治·斯坦纳的评论:“对他(布莱希特)来说诗歌几乎是一种日常探访和呼吸”。与席勒的二分法类似,布莱希特自己也做出了差不多的判断,他认为,歌德之后的德国诗歌存在着两大阵营,“主教式的和渎神的”;显然,格奥尔格和里尔克属于前者,而布莱希特当然将自己置于后者。
“过于敏感的良心,若不被伟大的活动力保持平衡,是会造成忧郁的人的。”这是歌德对艾克曼道出的一句箴言,也许恰好能够用来比较布莱希特的境况。还是在阅读《四川好人》之前,我就曾在诺贝尔奖作家卡内蒂的自传中领略了布莱希特的形象。卡内蒂眼中的布莱希特,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写作者,“以各种方式让人觉察出他对‘高尚的’道德思想的蔑视”,“他取舍的东西必须立刻为他所用,这些都是他的原材料,他利用它们不停地生产着……他是一个一直在制造东西的人”。“原材料”和“生产”的说法,确实也贴合了斯坦纳所说的“日常探访和呼吸”;但至于“对道德思想的蔑视”,显然,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是布莱希特为自己套上的一层外衣,正如青年卡内蒂看到的那“一身无产者装束”。这身装束,正好可以用来象征布莱希特持续一生的“活动力”。
在同一个时期,布莱希特与好友本雅明都被左翼思想吸引,但两人作为诗人的呈现方式又完全不同,本雅明看起来确实是过于忧郁了。译序中引用道,“布莱希特一开始就使自己与流浪汉式的局外人维庸的‘尘世’诗歌为伴,而不是与他所见的德语传统中的放纵和深奥为伍”。在整本诗集中,布莱希特确实没有把诗当成“艺术”,而是当成“工具”——也许早期名作《回忆玛丽·安》除外。
诗集中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两首晚期诗歌。一首是1944年的《我,幸存者》:“我当然知道:这么多朋友死去/而我幸存下来纯属运气。但昨夜在梦中/我听见那些朋友说到我:‘适者生存。’/于是我恨自己。”另一首是1953年的《难受的早晨》:“那棵银白杨,本地著名的美人,/今天是一个丑老太婆。那个湖/是一口洗碗水的臭坑,别碰!/金鱼藻中那些倒挂金钟廉价又艳俗。/为什么?/昨晚在梦中我看见一些手指指着我,像指着一个麻风病人。指节受劳受损,/破碎。//你们不了解!我尖叫,/良心受谴责。”
这两首诗,都是布莱希特记下的自己梦中的尖锐自省。同样地,这也使人想到阿伦特在评论文章中提到的布莱希特的诗学悲剧,而她也确实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这两首诗。阿伦特认为,当布莱希特为斯大林写出颂诗,他也就受到了丧失才能的惩罚。但她同时也同意《致后代》的著名结尾,请人们不要对他审判得过于严厉。阿伦特虽然批评布莱希特的政治实践,但也首先懂得他的“流泪谷中的黑暗,和巨大的冷漠”。
这本诗集恰好没有收录阿伦特提到的那部分政治性诗作。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布莱希特选集》中,收录的诗歌主要就是这种类型。它们可以在同样是近期出版的冯至译作《德语七人诗选》中找到。对照这两部分作品,读者可以看到,写口号式诗歌的布莱希特,确实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光泽。这也使我想到,在冯至先生自己的诗歌全集中,相较于四十年代的沉着思辨,他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显得苍白、空洞。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可能是同一种悲剧。
回到阿伦特文章的结尾,她总结道,“在20世纪以及其他任何时代,要做一位诗人是多么艰难”。而我也又一次想到开头引用的《四川好人》,做一位诗人,同样也是需要极大运气的事情,多少突如其来的思想,多少个朋友。诗人布莱希特,最后留下了怎样的面部模型呢?我们暂且读完诗集中的最后一首,它写于他去世的1956年,可称是遗嘱式的作品:“我总是想:最简单的话/已足够。当我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心一定会被撕成碎片。/如果你不挺身捍卫自己你就会倒下去/这你肯定明白。”
2018.8.23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