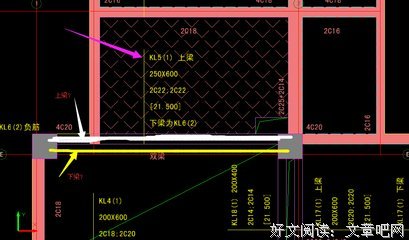
之所以花较多的篇幅介绍我的祖辈父辈,究其原因,我固执地认为,后代的性格塑造与思维方式跟祖辈父辈有着极大的关系。
所谓的性格与思维方式随着年龄与世事的变化自然也会随之改变,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与此同时,我又固执地认为,无论年龄世事如何变化,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存在着多种样式,但,底色不会变,存在于灵魂深处的某个东西不会变。
于是,我在梳理那些旧事的同时,一直试图在这些絮絮叨叨让人烦躁的文字中,寻觅出个一二三四来。
爷爷初到克拉玛依,自然是举目无亲的。在异乡的城市,没有文化,要想吃到一口热乎饭,就要靠膀子的力气。
老天爷终归不会辜负劳动的人们。在那年月里,爷爷不光能吃饱饭,每月还有一笔不算多但很可观的薪水。
这薪水,绝大部分都要寄回乡下,寄给奶奶,好让一家老小也都能吃饱穿暖,日子能过得稍微好一些。
每次寄完钱,爷爷总是欣慰的,也是惆怅的。欣慰之处在于,钱就要到妻儿老小手里,家里可以置换粮票,换取口粮了。
惆怅的地方则是,他总想给家里人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他没有文化,不会写字。
偌大的工地,100来号工友,会写字的极少极少。找人帮着写,总归有诸多不便。
爷爷买了本新华字典,每天干完活以后,在灯下识字练字,遇到不会的便标注下来,抽空去请教那些识字的人。
从此,爷爷有事没事就给家里写信,就像写日记样,几乎天天都在写,数千里之外的他,跟妻子跟孩子仿佛永远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在工地上,爷爷认识了一位老乡,听说东北正需要人,薪水要高一些,还可以打猎,采野味,俩人便一起去了东北,去了大兴安岭地区,给人家架电线杆。
爷爷在大兴安岭地区干活,自然是辛苦的。作为平原地带的人,很难适应大兴安岭的气候。
2017年5月,我骑车穿越小兴安岭,尽管防护装备很到位,但仍然感到刺骨的不习惯的冷。
由此,大兴安岭的冷,可见一斑。何况,在那个衣物缺乏且保暖效果不理想的年代。
干完活,爷爷和其他工友们就睡在简陋的道班里,夜里温度零下几十度,他们就那样式蜷缩在棚里,捱了一夜又一夜,一月又一月。
当时,爷爷买了一个毛毯。据说,他常常裹着毛毯在床板上就睡着了。那毛毯,现在在我家里,那是爷爷留给父亲唯一的家产。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爷爷逝世之后,父辈们分家产,分到最后,就剩一条破毛毯没人要,归了父亲。
除了毛毯,这些年,父亲还保存了一张老照片,是爷爷的,黑白的。
70年代,小姑嫁到了本地的一个矿上,在矿上打扫卫生,正式工,没啥辛苦活儿,就是签个到,混日子。姑父是矿上机电科的技术员。
爷爷从千里之外给小姑寄了许多东北特产,人参,木耳,野生蘑菇等,这些都是爷爷自己在大兴安岭里摘的。
寄给小姑,是想让小姑帮父亲在矿上找份工作,用于打点。其时,父亲已经10多岁了,俨然大小伙子了。
用爷爷的话说,得走出去,不能窝在老家,在乡下,地种得再好,一辈子还是老农民,永远都走不出去。在矿上,就是干个杂活出点苦力也没事,至少生活有盼头。
工人阶级才是老大哥嘛~!
期间,还闹了些插曲,关于小姑闹着要上吊的事。这段故事,现在写不合时宜,后面再慢慢叙述。
好在,小姑为父亲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主要就是,给井下的工人送饭。
也是在70年代,本地新开了一处矿,矿上招工,爷爷便从东北回到了家乡,从此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一心想着抓革命促生产的煤矿工人。
在矿上工作的父亲是不安分的,他觉得那样式的生活很枯燥,看不到未来,便辞了职。
那时节,辞职是需要勇气的,毕竟,正式工这个铁饭碗是脸面,也是筹码。
可能也不需要什么勇气,那时候的父亲同样是个毛头小伙子,脑子一发热,不干也就不干了。
父亲是偷偷辞职的,瞒着爷爷。爷爷知道以后,骑自行车去了父亲所在的矿,兴师问罪,好好的正式工,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显然,爷爷拿父亲是没辙的。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许多年后,我大学毕业之后,父亲托人为我安排了一份所谓体面的工作,在报社实习。
我一声不吭地跑了,跑到了外地,在一家台资企业当一名PCB技术员。后辞了职,在一家私企,给老板当助理。
后,又辞职创业,做网络应用开发与推广。
.........
父亲对我的工作选择也是没辙的。
他偶尔会抱怨:混到30岁,你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当初,进报社多好,熬到今天,也不用整天为生计发愁了。
父亲显然不知道现如今传统报社尴尬的市场地位。或许,在父亲的认知里,在报社工作,是很体面的吧。
每次父亲埋怨我的时候,我总笑着说,咱爷俩谁也别说谁,都挺会折腾的,当初我爷爷不也拿你没辙吗?
父亲听我这么一说,便不再说话。
他眨巴着眼睛,习惯性地轻咳几声,呆呆地望着窗外,记忆似乎被拉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