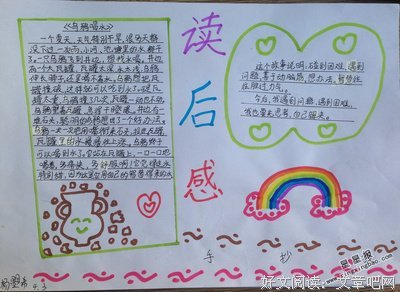
《乌鸦》是一本由(美) 博里亚·萨克斯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60图书,本书定价:手工精装特制毛边本,页数:20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小书,超级贵!!到了后,我先滞留了好几天才看,先看的《渡鸦之城》再看的这个,布质的书皮上纸质的一只乌鸦图案,看起来异常严肃,打开后里面做旧的布质书让人摸上去很舒服,再看里面一张张图片,瞬间觉得很值得了(咳咳咳,说这么多,还以为我是狗托)但是这本书的早前版本可能已经绝版了,某宝上的全是影印版,强烈建议配合《渡鸦之城》这本书食用效果更佳~爱乌鸦人士首选
乌鸦:非是我带来了死亡,而是死亡召唤了我
终于有一本以乌鸦为主角的科普向读物了!乌鸦作为预言和厄运的象征一直在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以中世纪为题材的的作品中乌鸦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作者从地域和时间两个方向出发,对乌鸦本身以及关于乌鸦的文化进行了介绍。 鸦科鸟类可能起源于现在澳大利亚所在的大陆块,并随着大陆漂移进入亚洲,之后快速向欧洲和美洲扩散。乌鸦的智力非常高,远超它们在大自然中生存所需要的智力,除了基本的生存活动,它们会在无聊时编出游戏自娱自乐。乌鸦善于观察和学习,稻草人通常只能保护麦田一至两周的时间,乌鸦会快速地发现这些假人没有任何攻击力并开始戏弄它们。乌鸦也会学习研究使用工具,虽然只是对工具简单的操作,在这方面比灵长类的黑猩猩聪明许多。它们有较长的寿命和较短的繁殖期,这也使得乌鸦能够发展出世代相传的家族关系,未育有后代的乌鸦会帮助父母一起照顾雏鸟,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就此诞生。在群居生活中乌鸦会通过声音和动作的组合进行交流,它们能够共同狩猎协助育儿,这让乌鸦的社会生活变得复杂而精妙。 从远古的神话时期到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有鸦科动物的身影,在不同地区它们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远古时期的西伯利亚、中亚开始出现渡鸦崇拜;铁器时期的凯尔特人将渡鸦摆成张开双翼的形状埋在墓穴底部,渡鸦成为祭祀一部分;美洲的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同样崇拜渡鸦。鸦科动物不仅出现在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的宗教故事中,也在各个地区的城市传说中有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是法国、英国、冰岛都有他们的身影。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从来不缺乏乌鸦的身影,它们大多被用来营造一种预言、厄运和死亡的神秘氛围。 这本书的装帧十分漂亮,从封面到内页全部用银字在黑纸上印刷,插图并没有追求色彩,用简单的双色展现出一种版画的质感。整本书可以平整地摊开,纸张切边做成了毛边的效果,视觉效果和手感都很棒。只是每次阅读都会有很多黑色的粉末从毛边切口掉落,而且读完以后手上会有极强的灰尘感,同时随着精美的装帧一道而来的是高昂的价格——这个小小的家伙售价足足99元。
《乌鸦》读后感(三):喜神 乌鸦
在唐代以前,乌鸦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有吉祥和预言作用的神鸟,根据《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述,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则是对太阳为金乌化身的说明和解释。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 唐代以后,才有了乌鸦主凶兆的学说出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 但是不论凶吉,儒家常用“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教化人们“孝”和“礼”,因此乌鸦的“孝鸟”形象是几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本草纲目·禽·慈鸟》中称:“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乌鸦是否真的具有这种习性,还有待证实。 “萨满教”是东北原生民族“满族”的传统教派,在其教义中乌鸦是喜神和保护神。清代文献《满洲实录》中记载有“乌鸦救祖”(清太祖)的传说。东北山民们进山打猎也有“扬肉洒酒,以祭乌鸦”传统。至清太宗专门在沈阳故宫清甯宫前设立“索伦杆”祭祀乌鸦,并在沈阳城西专辟一地投饲乌鸦,不许伤害。清顺治帝入关后,亦在北京故宫内设立“索伦杆”保持了对乌鸦的最高规格的崇拜。 在西藏和四川一些地区,乌鸦也是作为一种神鸟来崇拜,无论是发掘的吐蕃文献还是西南地区的“悬棺”和“天葬”习俗,均证明这一点。 道教宗祠武当山,更是把乌鸦奉为“灵鸦”,并在山上建有乌鸦庙,“乌鸦接食”为武当八景之一,就是进山的游人,也会随身携带一些食品,散放给乌鸦来啄食。 与中国比邻的日本,乌鸦是超度亡灵的使者。日本文化认为但凡人死都会成佛,但是无法成佛的就会成为怨灵在人间徘徊行恶,而鸦的工作就是超度这些怨灵,不过说白了就是让他们魂飞魄散。在日本,人临死时有乌鸦在附近的现象,被解释为作为度亡者的鸦在一旁看守死者,防止他的灵魂变成怨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八咫鸦,也就是说三足乌,这个形象从中国传到日本后成为了武人贺茂建角身的化身。此鸦有三只脚,颈项上挂着八咫勾玉,受天照派遣到人间,解救了因为迷路被困在熊野山中的神武天皇东征军,到现在神社里依旧供奉着他,后来八咫鸦便成为熊野本宫大社的神纹,象征着“忠实、诚实、大无畏”的精神。另外乌和鸦是不同的东西,与鸦相反,乌也是一种类似于怨灵的妖怪,是鸦死后化做的。
时至今日,其实我们已经很少关注乌鸦了,不仅如此,大部分鸟儿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是因为它们因为某件奇闻轶事登上了新闻头条,忙碌的现代人早已走出了自然崇拜,投入实用主义的洪流之中。一切自然事物不再具有神奇的魔力,而成了最常被忽视的日常背景。
乌鸦也不例外。
它们很少在人类的视线中盘旋,即使偶尔现身,除了科学家,也鲜有人愿意为之停下。但有这样一个好奇心爆棚的美国人,不仅把目光投向了乌鸦,甚至翻遍了古今中外世界各地的传说、文学、艺术作品,把关于鸦科鸟类的内容巨细靡遗地罗列了出来,拉开了一幅属于它们的画卷。
于是,有了这本洋洋洒洒的《乌鸦》。
在乌鸦身上,人类寄托了自己所有的想象与期许;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所有动物在人类眼中,都带上了拟人的色彩,人类社会的种种都被映射到了动物王国里,每个人、每件事都能找到一种对应,甚至被贴上标签,融入传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博里亚·萨克斯首先带着我们穿越了古老的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埃及和罗马,再到中国,他告诉我们,乌鸦与死亡之间有着不可名状的联系。乌鸦喜食腐肉,因此被赋予了与死亡有关的角色,戴上了令人恐惧的光环;它们是神的代理人,象征着惩戒、荒凉与消亡。同时,乌鸦的另一种特性则为它们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形象:人们在乌鸦的叫声中迎来日出,因此又被视之为光明的符号、预兆之鸟。在熟悉的神话后羿射日中,后羿射下来的太阳就是三足乌。
步入中世纪, “人们较少像古代一样求助于动物的预言,而是更多地把动物当作道德教训的提供者或审美沉思的对象”。这或许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渐渐意识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看待自然事物的眼光从一味的崇拜转为辩证,再加上宗教的渗入,早期的传说纷纷带上了神性的影子。很显然,乌鸦在宣教布道中,同样承担起人类给予的形象。它们有时被视为恶,譬如伊斯兰教中的五个坏蛋之一;有时又是善的化身,每天都为躲避德西乌斯皇帝的隐士圣保罗带来半条面包。
到了20世纪,人们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渐渐挪到了对阶级、对社会的回顾与反思,由此出现了很多“拟人论”,即“用熟悉的制度来描述动物社会,把它们的社会说成是君主国、军队、社会主义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当前的时尚”。乌鸦的角色也不例外。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煞有介事地说道,乌鸦(寒鸦)的社会里有等级之分,怀有高傲的心理。联想到他的纳粹理论家身份,这种挪用和曲解也就不足为奇。
直至今天,我们多数时候看见的乌鸦是严肃的,俨然死神的代言人,象征着必死的命运,是厄运的信使,乌鸦的盘旋被视为时间以及生死的循环。但有时乌鸦也会以一种活泼快乐的形象出现。非常吊诡的是,无论哪一种文化,乌鸦在其中的角色总是善恶并存,它们是死亡,又是新生,是神圣,又带着亵渎。这种善恶二重性使得人类对它们的情感也同样交织着喜爱、尊重、崇敬与厌恶、恐惧、鄙夷。这或许与书写者有关:身份不同,看见的风景亦不同。
博里亚·萨克斯写道,“我们经常忽视乌鸦,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实际理由去关注它们”,而这本乌黑、小巧、银光闪闪、带着绸缎般光泽的《乌鸦》或许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理由,在下次看见乌鸦的时候,不妨为它们驻足一会儿。
《乌鸦》读后感(五):乌鸦的自我修养
它是《伊索寓言》中出镜率最高的动物,“乌鸦喝水”的故事也早已被人们熟知;它常常出现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同“枯藤”“老树”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它也总被编入各类神话里,以神秘预言家的形象示人。由于外表的限制,人类不会像对待一些漂亮的鸟类一样亲近乌鸦。实际上,除去那些普遍的认知,人们对乌鸦的秉性知之甚少。
美国学者博里亚·萨克斯的《乌鸦》一书,既是一本有关乌鸦知识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极简乌鸦文化史。作者凭借对乌鸦多年的系统考察和研究,从动物科学、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文学艺术等多个维度,为我们讲述了有关乌鸦的各种知识和八卦周边。
打开《乌鸦》黑色的封皮,翻开如羽毛般绒滑的书页,那些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部分,终于被放置到合适的位置,形成了一张完整的乌鸦拼图。
一、我对爱情有坚持
乌鸦是一夫一妻制。“在古埃及的象征体系中,乌鸦代表了忠诚的爱情。”当埃及人想表现战争之神和爱情女神的结合时,他们会画两只乌鸦。
如果说同样代表爱情的鸽子象征着爱情的纯洁,那么在乌鸦这里,爱情则意味着相守一生。鸽子代表的爱情是理想化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而乌鸦的爱情,更多地象征着世俗意义上的婚姻。
在古希腊,乌鸦甚至代表了圆房,象征着吉祥婚姻。如果一只乌鸦死去,另一只绝不会再找配偶。正因如此,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把婚礼上出现单只乌鸦看成是凶兆,这意味着新郎或者新娘不久就会死去。
二、自娱自乐是我的生活哲学
乌鸦的智商不容小觑。新喀鸦被研究证实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鸟类,不仅会使用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金属丝掰弯做成钩子,钩取自己想要的食物;日本仙台的乌鸦发明了开核桃的好方法,它们把核桃衔到公路上,绿灯的时候经过的车辆会把核桃压碎,等到红灯时它们再去叼起来吃掉。
然而,乌鸦并没有因为高智商而傲娇,反而“沉溺于明显无用的游戏”,把智商用到了很多无聊的自娱自乐上。“比如衔着一根小树枝飞向空中,扔下这个玩具,然后又俯冲下来,再叼住它。”“没有明显的原因,它们可能会单脚倒挂在那里,或在飞行中腾空后翻。”
阿拉斯加的乌鸦甚至会把积雪敲碎,用雪块做成雪橇顺着倾斜的屋顶往下滑。乌鸦还会利用各种方法调戏人类,以至于很多人开始觉得乌鸦很讨嫌。但显然,“乌鸦是个快乐的家伙,尽管穿着黑黑的外套”,幽默感让乌鸦的人生充满了闲情逸致和各种乐趣。
三、保持神秘感
乌鸦非常懂得“距离产生美”的道理,尽管它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中很常见,但乌鸦很少“朝人类的方向多看一眼”。有时候,乌鸦可能就在不远处,但它更喜欢与人保持适度的距离。
乌鸦的神秘让很多艺术家为之沉迷,它是爱伦·坡的宠儿,是梵高最后的画作《麦田里的乌鸦》中的意象,更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死亡的象征。
古人的图腾要么是凭想象勾画的强大动物,比如龙、独角兽一类,要么是一些带有神秘气息的动物,比如猫头鹰、蛇等等。或许正是凭借神秘感,才让乌鸦也在图腾界拥有了一席之地:它存在于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上、印第安人的织物图案中,在北欧神话里战神奥丁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肩膀上,它也大量存在于各式各样的纹章当中,成为智慧的象征。
当我们和鸟类祖先在四亿年前分道扬镳的时候,自然选择让我们进化出完全不同的生存策略,而乌鸦显然是鸟类中的佼佼者。虽然人类自信是比乌鸦更高级的动物,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还真该向乌鸦学一学。
《乌鸦》读后感(六):《乌鸦》:一部极简史
脑海中是否曾经闪现过这样一幅画面:在某个早已凋敝的边陲小镇的一隅,一群外表乌光油亮的乌鸦黑压压地齐聚在一棵歪斜破败的古树光秃秃的枝桠上,它们就像是随时准备走上刑场的犯人,又或者像是预告黑夜即将降临不苟言笑的使者,寂然,大多数时候只是低垂着脑袋沉默不语,偶尔发出几声凄厉而萧索的叫唤,在黄昏的阴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你是否被眼前这场景深深吸引住而挪不开眼睛? 这幅画面——连同以乌鸦为意象的中国古代文人骚客诗文词曲,诸如“枯藤老树昏鸦”“月落乌啼霜满天”等—— 一起建构了人们对乌鸦这种独特鸟类的诗意想象。当然,此类图景也只是对乌鸦这一形象多重想象中的一种而已,而它们也并不总是足够诗意和令人愉悦的。相反,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人们对乌鸦这一群体可谓又爱又恨,怀有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和态度。 在博里亚·萨克斯精心写就的这本名为《乌鸦》的书里,他从对乌鸦这一依旧显得神秘的群体的浓厚兴趣出发,钩沉历史,打捞碎片,尽全力探究和还原了人类对乌鸦本身及其延伸出的文化形象的认知的发展过程。 本书共分为“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亚洲”“美洲土著文化”“浪漫主义时期”“乌鸦之王”“20世纪及以后”等几章,从时间、空间两方面来分开探讨人类对乌鸦认知的进程。而在这其中,对词源学的运用显然对理清常被我们较不严谨地统称为“乌鸦”的鸦科鸟类的各种称呼有着巨大的帮助。 毋庸置疑,在以往历史中(至今也有不少人依然相信),乌鸦这一形象常常与死亡、厄运、诅咒等这些不吉利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这种对乌鸦看起来怀揣着愤怒和仇恨的情绪是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逐渐滋长起来的,这背后总是闪过宗教信仰的阴影,又常常牵涉到乌鸦本身的一些习性。首先,大多数鸦科鸟类家族的成员本身外形确实并不讨人类欢心:它们几乎从头到脚都是黝黑的,而黑色总是给人一种不佳的观感——它使人嗅到死亡阴郁的气息。另一方面,乌鸦的食腐爱好也“从中作梗”。在中世纪末期瘟疫爆发和战争连绵的年代,人们时常会看到乌鸦啄食战场上死亡士兵的尸体。不过这一现象也并不一直被认为是与“恶心”相勾连。在那些喜欢把生命视为一种轮转循环的文化环境中,尸体被喂给鸟类是令人感到宽慰的。事实上乌鸦的食腐特性也确实有助于加快生态循环,对人类生活具有裨益——大量动物尸体被及时分解阻止了由此可能产生的病毒细菌进一步扩散蔓延的可能。曾几何时,农民们对侵扰农田的乌鸦恨之入骨,把它们的降临认作是对自己辛苦劳作成果的蹂躏,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猎杀,但事实却最终证明,相比于乌鸦吞食谷物(而它们其实主要目标正是害虫)带来的那点小小损失,害虫给农作物带来的灾难则要大得多。 让我们把视线投向过往吧。类似于乌鸦这一物种起源以后在世界各地的进化分化,在宗教传统业已成为固定体系和巩固阶级统治手段的资本社会与原始古老的土著部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乌鸦的形象变得极为复杂、多元。笼统来说,有关乌鸦早期形象的建构总是逃不开创世神话、先知降临或者其他与神迹出现有关的这样的故事,与众神关系的或远或近则变成了判别乌鸦形象的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 正如我们无法将某个人简单地评判为是好是坏,从多重维度出发对乌鸦进行评价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简言之,研究这一形象还需结合迥然不同的时代因素与相异的宗教文化背景来分开讨论——于是我们可以乌鸦在其中延展呈现出的多种面貌:它是可憎的,又或者是令人敬畏和崇拜的,还可能人类对它们是爱恨交加的。当然,相比于前述总是与神话传说等扯上关系来参与创建乌鸦这一既有形象的方式,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科学、丰富而全面的手段来研究这一群体:分类学、动物行为、人类学、文学艺术…不一而足。令人惊讶的是,与外界强加给我们中大多数人对乌鸦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同,乌鸦的智力在它的鸟类同胞中是数一数二的,并且它们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呆板、无趣、惹人生厌。相反,它们在有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机敏幽默的一面,这全凭你是否会去耐心观察和发现——尽管现代社会高速竞争的快节奏生活总是让我们对它们雀跃跳动的身影熟视无睹,更无心停下脚步对其仔细研究一番。 不过,细数乌鸦形象不断被建构的这一浩瀚的历史,最微妙的一点或许在于,不管乌鸦的形象如何被深深嵌进勾勒着人类社会发展图景的古老墙壁里,乌鸦与人类的关系始终显得若即若离。它们就像是身在其中但又超然物外的“局外人”,冷静、不动声色地审视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诸般种种,那灵快抖动脑袋的动作间未尝不含有它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隐晦态度——这背后的含义人类始终难以破解。 一部乌鸦文化简史,就是半部凝缩简练的人类历史,从中投照出我们自身的镜像。拨开历史的迷雾烟云,我们得以窥见乌鸦的隐秘踪迹,但它们真正的面貌却始终掩盖在神秘的面纱之下,亟待我们去用心发现、一探究竟。
《乌鸦》读后感(七):那愉悦的亲近的阅读之美
嗜书,是一种瘾。日渐沉迷,而我不愿戒断。
有些书,端凝如长者;有些书,亲切如挚友;有些书,要在长久的相处中,才能觉得他的好;还有些书,第一眼,就意乱神迷。揭开面纱之后,他们袒露灵魂,有些渐次乏味,外在的妍丽无法支撑内在的干瘪;少有的几次幸运,那简直是,仿佛啜饮醇酒,醺醺然,神思迷醉,余生皆愿与他偕老,日复一饮,沉酣如梦。
我捧起《乌鸦》,轻抚封面,描摹乌鸦的形体,拉过一张白纸,捡起一支铅笔,悄然复刻他的轮廓。他可能来自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岛、日本的仙台市、北冰洋的因纽特海岸、西伯利亚的荒原、巴西的雨林,或者离我家不远的公园的树梢。世界上到处都有乌鸦,还有各种乌鸦传说,人们都说乌鸦是预言家,也许是真的。在古希腊,乌鸦就是智慧和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同伴,而文艺复兴时期乌鸦被视作少女潘多拉的化身,宾夕法尼亚州雷纳佩族人现在仍然传说,当第一场雪覆盖大地之时,乌鸦就会出发去拜访造物主……
这是一部“乌鸦极简史”,作者博里亚·萨克斯搜集了与乌鸦有关的大量材料,神话、传说、祭祀、崇拜、自然、文学、诗歌、戏剧、绘画、艺术……爱伦·坡诗歌里的那只黑鸟,那副面孔看上去阴沉而一本正经,胆儿一定不小,从阴曹踱出来的远古乌鸦神情阴冷,那黑羽毛如同灵魂谎言的象征;梵高在最后崩溃之前画了《群鸦飞过麦田》,蓝、黄、红、绿的线团盘缠纠绕,天空低沉地压在麦田之上,鸦群似黑色鬼魅掠翅飞过,气息不祥。
在乌鸦的黑色羽衣之下,有一个斑斓的神奇世界。了解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无用,就为了消遣,随便看看啦。消遣是生活的调和,得到惬意的感受,其实并不容易。
“微物史”的书籍,要想吸引人,必得有些特别的魅力。本书作者另一部主题相近的《乌鸦之城》中文版前几年就引进了,讲述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内容也有趣,反响很一般。为什么呢?因为工艺。
《乌鸦之城》与《乌鸦》都是零碎知识的呈现,只读文字,阅过即忘,轻泛的些微的喜欢也就如风散了。这一类型的书,本质上都“小家碧玉”,要把气质突出,就要有精巧的妆扮。而工艺,工艺的美,装帧与实质的完美结合,才会真正让人爱到无可自拔。我为《乌鸦》而荡漾,而钟情,我爱他,深得我心,美意流转。
不管叫寒鸦,还是渡鸦,天下乌鸦一般黑。全本高级黑卡纸,把脸颊贴向书页,闻不到油墨味儿,于瞑静里去体验光滑。一页一页,翻来翻去。你有没有意识到,书是自带乐感的?当拇指迅速掀动书页,《乌鸦》的声调飒爽利落,插图与文字印刷仿用极有质感的亮银刻蚀,仿佛音符跳跃于乐曲的间奏。我联想到欧洲中世纪古堡餐桌上锃亮的餐具在指间转动的光亮,《乌鸦》的气质就是古意盎然的珍本,时间的味道。毛边的构思也是为此吧。《乌鸦》的毛边很低调,不需要动刀子去裁,也没有牵丝挂缕的烦恼,绒绒的一层,羽毛一般掻过。
在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并非全部一个劲儿沿着直线演进,而是有可能从往昔、从过往给当下一些借鉴。书籍曾经是昂贵的奢侈品,缀满了珠宝,只属于少数人享用,我们要感谢平装书的出现,让阅读成为公众行为,进而推动了社会思潮的解放。而如今,人们也常常受困于泛滥的出版,书出得太多了,好书太少,而且破坏生态。电子书的兴起,似乎在预言纸质书的消亡。真的吗?我觉得,不大可能。有些应该要电子化,而纸质要抓精品,精品不是说精装华丽就是好,《乌鸦》的装帧很难得地将简素与绚美合为一体。电子书和纸质书是不同的载体,带给我的感觉也很不一样。像《乌鸦》这样的书,只有通过实体的触摸,才能感动于阅读的欣悦,与我所建立的联系,是科技无法替代的情感,私密的亲近。
总有些书,在我们内心的花园里会长成特别的风景。草木葳蕤,爱意丛生。
图片欣赏:
顾舜若摄影顾舜若摄影《乌鸦》读后感(八):透过乌鸦的视角看人
在我们所熟悉的鸟类中,乌鸦可能是争议最多、遭受误解最大的一种。这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都能看出点端倪:一个人嘴巴臭、预言坏事,常被称作“乌鸦嘴”;但与此同时,却也有“爱屋及乌”的成语,这与更早的典故“瞻乌之望”,其实原本都指乌鸦集于屋乃是吉兆,故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传说。汉代还曾有许多乌鸦栖息在御史府柏树上,因而御史府又被称为“乌府”、“乌台”。但大抵从唐宋之际以降,乌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渐次下降,从原先预兆吉祥的神鸟逐渐变为不受人喜爱的灾厄化身,原先对乌鸦的那种崇敬则转移到了同属鸦科的喜鹊身上。
翻翻美国学者博里亚·萨克斯这本《乌鸦》,就可发现,不仅中国人,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乌鸦的观感都可说“心情复杂”。当然,虽然他旁征博引,但最熟悉的毕竟还是西方与北美文化中乌鸦的意象,对其余地方(尤其亚洲)难免还是有遗珠之憾。不过其中至少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不同文化对乌鸦的敬畏,原本都不是因为乌鸦本身,而是出于对它所怀的神秘力量的尊崇;而当人们在思想和技术上逐渐取得对自然的支配权时,乌鸦的魔力就被祛魅了,它或是只剩负面力量,被视为灾星、地狱使者,或是因其黑漆漆的外表而遭人嫌恶。
最初它受人敬畏,无疑也是因为一身不同寻常的闪亮黑羽。北亚和北美土著的神话体系中,乌鸦、渡鸦普遍被视为神鸟,这意味着,它其实就是天神或自然力的化身。据人类学者詹姆斯·弗雷泽在《火起源的神话》中所记,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神话中,“乌鸦在各种事物的起源故事里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第一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乌鸦就教他们制作钻木取火的工具。在北极的雪原上,几乎纯黑的乌鸦极为显眼,它在不同的土著民族心目中,都被看作拥有与生俱来的魔力。
不过,那些实现了“轴心突破”的文明中,人作为个人逐渐敢于依靠自己,因此在这些文化中,乌鸦都逐渐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圣经》中它的形象复杂,但大抵是受诅咒的;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佛教文化中也将乌鸦视作“邪恶不正品德恶劣者”;中国文化算是最温情的,独尊儒术的汉代将乌鸦称为“慈鸟”(许慎《说文解字》),这乍看仍赞许乌鸦,但无疑是将乌鸦的形象道德化、世俗化、祛魅化了,正如现代人所说的“勤劳的小蜜蜂”只是一个道德形象,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神圣的。甚至一些土著民族后来也转变了看法: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传说中是乌鸦俯冲进恶魔口中,阻止了它的吞日之举,才使得人类现在有了白天;可是蒋彝在1970年到访日本时却听当地人说:阿寒湖一带乌鸦太多,阿伊努人视其为恶魔的化身,不怎么喜欢它们。
更有甚者,当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代逐渐基督教化之后,一些动物之所以遭到贬低与敌视,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在早先的异教文化所具有的神秘性,它们成了异教力量的象征,被斥责为撒旦的化身。不止乌鸦,狼和熊也有同样的命运。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在《色彩列传:黑色》中推断,乌鸦形象在西方的降低,正是从基督教时代开始的,原因之一是“光”作为上帝的象征为教会极力推崇,而“黑暗”则遭到贬低和驱逐,于是“到了封建时代,黑色的正面意义几乎荡然无存,而负面意义则占据了它全部的象征义域”,对黑色的憎恶是当时神学家的普遍认知。这对乌鸦这样一种几乎全黑的鸟类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它们日渐被视为死亡和地狱的使者恐怕也与这一宗教心态的转变有关,而不仅仅像本书所说的是因为乌鸦食腐肉的习惯——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它们之前也有同样的习惯,却受到敬畏而非这样的污名。
乌鸦的形象到了近现代再一次翻转,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因为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文明,正是一个异教精神复兴的时代。借用启蒙运动历史研究权威罗伊·波特(Roy Porter)的话说,“启蒙运动最关键的概念就是自然”。随着自然逐渐被现代技术征服,心怀愧疚的人们对自然界涌起了一种矛盾的情感:它既被残害,又被浪漫化,而这看似相反的两点,归根结底都因为其未被彻底驯化,是人类永恒的对手。和很多鸟类不同的是,乌鸦很善于在人类聚居的城镇生活,但却不容易被驯化(在这一点上它们更像猫而非狗),并且还会在田地里与人类争食,它是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野生元素之一。美国曾将之视为害鸟,鼓励人们大肆捕杀,但最后又不得不承认它在整体复杂生态中的作用——在我们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故事,只不过针对的不是乌鸦而是麻雀。这一点上,它的形象接近于强盗:既是文明社会的威胁与叛徒,但像水浒和罗宾汉这样逍遥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侠义形象又被人们所浪漫化。
在这里,乌鸦变成了一个新的象征,它同样是自然的缩影,但却不再是那种左右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而变成了一个不驯服的力量,我们试图控制它的结果很可能是自食其果,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谦卑地与之共存。在这一点上,又何止是与乌鸦如此?一如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中所暗示的,杂草本身其实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它既被文明人所憎恶,又因其生命力和不驯服而受文明人钦敬,说到底,它们就是作为文明社会对立面的自然界本身。
人们在看待一种生物时,不可避免地会在它们身上投射自己的文化观念,因而其形象的变迁,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就相当于一面镜子,反过来折射出当时人的群体心理。亚里士多德撰写了第一本动物学的科学著作《动物志》,其中有意无意地将不同物种看作人类的各个王国,彼此之间存在联盟与敌对状态,这恐怕本身就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状况的投射。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吉卜林和北美的西顿,则将野生动物描绘为文明社会的浪漫主义叛徒,与资产阶级男女的颓废迥然不同,隐然把它们看作捍卫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而种族主义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则强调自然界不间断的斗争,声称自己所看到的寒鸦都被精确地组织在一个金字塔社会结构中。而到了现代,花了大半生研究乌鸦的贝恩德·海因里希,则强调“渡鸦和人类一样,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倾向于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
虽然现代人乐于承认“乌鸦很像人类”,这看上去是一种更为人道、也更文明的姿态,但这种视角究其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心理学已经揭示,人们很容易偏爱那些更像人类的动物,有时情不自禁将他们拟人化,宠物之所以得宠,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脸部容易召唤起类似对人类孩童的情绪;但这也可能让人忽略了动物与人的差异性。乍看起来,我们已经放弃了对乌鸦身上神秘力量的敬畏,改用一种更科学的态度来观察和理解它们,最新的科学研究尤其强调乌鸦在智力上的突出表现——无论是它的语言能力、对人脸的识别与记忆,还是制造工具的能力——但不论如何,“乌鸦智力处于鸟类世界顶峰”这样的论述,归根结底仍是对人类凭智力居于动物世界顶端的类比。我们只是以此再度确认,就智力的优越性这点而言,乌鸦真的很像人类,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理由去喜爱它们。但这仍是人类的视角,至于乌鸦是否因此就更喜欢人类,恐怕就不得而知了。
*已刊2019-07-05《第一财经日报》,题目改为《从吉祥神鸟到灾难化身,东西方文化中乌鸦的相似经历》 ------------------------------------------------------------------- 勘误:
.87:在古老的波斯宗教中——其中渡鸦是胜仗之神乌鲁斯拉格纳(Verethragna)的化身:确切地说是“斗战神” p.132:13世纪的阿拉伯百科全书作者,伊拉克的哈姆杜拉·阿尔-穆斯塔法·阿尔-卡兹韦尼(Hamdullah Al-Mustaufa Al-Qazwini):按,此人生于1281年,其主要活动年代其实应算14世纪;此外,其姓氏Al-Qazwini应指“加兹温的”,宜译作“加兹温尼” p.150:乌鸦解释说,鸟类已经有一个国王揭路荼(Garuda),即毗湿奴(Vishnu)的鹰头坐骑:按,Garuda佛经通译“迦楼罗”,即大鹏金翅鸟,天龙八部之一 p.257:日本人经常以收获之神案山子神(Sohodo-no-kami)的形象制作稻草人:按,日语“案山子”(かかし)即稻草人,但此处读そおど。据《古事记》须久奈比古命神话,此神是“山田的曾富腾”(山田のそふど),“此神虽腿不良于行,却了尽天下事”(此の神は足は行かねども、尽に天下の事を知れる神なり),他单腿伫立于田地里,察知世间变迁。 p.298:参考文献独缺第四章“亚洲”的部分,而从后面的“文献目录”看,作者在撰写“亚洲”部分时无疑是参考了相关著作的(如p.303提到《罗摩衍那》的英译本,以及《中国神话学》(Chinese Mythology)。疑此处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