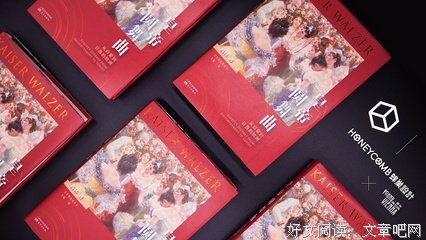
《皇帝圆舞曲》是一本由高林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皇帝圆舞曲》读后感(一):公众号文章集合册
看完这本书后,我有着深深的疑惑,后来看了序,我领悟了。该书序中言道”起初,本书的文字整理工作,并没有既定的头绪,只是按照高林先生在过去写作中已有的、较为完整的篇目进行整理......还将一部分内容发在公众号上......."所以,我懂了为什么该书的风格是这样。
本书主要的时间背景是在19世纪的欧洲,其书中的内容与思想并没有连贯性,就是作者将他自己感兴趣的人或者事件写成一个个的小文,所以,阅读该书时,会发现前章与后章关联性不大。
之所以不喜欢该书,除了它不是严肃文学,更是在写某一人物时,其人物的成就影响力几乎不写,其人物的成长经历也是选一些内容写,更多的是不知真假的小故事与作者个人感悟,举例:写巴尔扎克时,作者描写巴尔扎克穷得嗷嗷叫(书中原话),转行到了出版业,结果被债主逼得嗷嗷叫(也是书中原话),说巴尔扎克天天想得是如何发财,没事就忽悠朋友瞎做生意以及挖财宝.......穷凶极恶之下开始写书赚稿费......
以上就是巴尔扎克的书中内容......
我不想评价其内容真实性,只是想说,此类文章,还是去看公众号吧,更省时间。
《皇帝圆舞曲》读后感(二):是我肤浅才会被装帧跟宣传欺骗
之前趁着618买的,在买了不看罪大恶极的原则驱使下,过了半年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 看完之后,我对着封底的上架建议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如果是一个想了解18~19世纪的欧洲历史的读者,在欧洲史的分类区里看到这本装帧精美、宣传词高级的书,十有八九会将它加进购物车。再之后顶着一头雾水看完,也可能看了一两章就打着哈欠合上书感叹‘欧洲历史真复杂啊’把它塞进书柜。 如果是个对欧洲历史有些涉猎的读者,本着严肃的学术心态买来这本书,大概也是一边挠头一边问‘这本书到底想说个什么’。 要说这本书通俗?几乎隔两页就会插入小半页的注视,作者更是见缝插针引经据典来提高文章的学术浓度,刚入门的读者被唬得晕头转向。 可是这书也实在谈不上严谨,以明星人物作为描写核心,却不提他具体的所作所为成就影响。若是考虑到将本书的目标人群选为对这些人物历史有了解的读者,也不是不能理解,可同时又在其中安插了许多出处不详的故事,然后又以这些故事表达对人物的感悟。 作者的自序里说,希望能让读者看到的是一本轻松愉快的书。这点可以从行文里看出作者的努力。 好好的一本书怎么会做成这样子呢,看看编者的话就明白了。 本书是以高林先生于公众号发表的文章集结改编而成,成书后分为5个大章节,看似其中的小章节都以大章节为中心,可这些小章节原本也不过是在公众号上,作者以个人兴趣写成的单独篇章而已,前后并没有什么紧密联系。 而公众号上的文章也不可能给你搞严谨学术,只是给爱好者打发闲趣罢了,自然造成集结成书后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 有一说一,这种公众号结晶书我觉得不太行,虽然纸张质感装帧印刷都很舒服,但咱们到底看的还是内容哈。 当然也怪我自己肤浅,老是会被这种宣传语跟装帧骗到。
《皇帝圆舞曲》读后感(三):读后
时间碎片化的今天,
哪来得空闲看书。
你、我、他
满脑袋的知识焦虑,
于是
一本本“砖头”被搬回家。
哈布斯堡、德意志、罗曼诺夫,
多么高大上伟光正,
可惜
你与它们不只隔了几百年,
还有整个欧亚大陆。
还好
有替人读书的高林,
闲谈似的讲述间,
伏尔泰、俾斯麦、弗兰茨,
巴尔扎克、弗洛伊德、普鲁斯特,
走到我面前,
光环被卸下,
我看到了另一个他们。
《皇帝圆舞曲》读后感(四):《皇帝圆舞曲》:一本“过时”的书
阅读本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作者本人也来自十九世纪的欧洲,多处的行文、语气让我想起了茨威格。在那个年代,写成历史书本的语言似乎可以是更华丽一些的。
让这本书“过时”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所描写的对象:十九世纪。这个世纪有时被人称做“美好年代”,很显然不是因为这个世代的人活得有多么畅快、舒适,而是因为这个世代的人还满怀希望,而这是经历过其后年代的人所不敢拥有的奢侈品。
当然,最能显现本书“过时”的事实是,本书中居然有一篇在认认真真的讨论马克思为什么蓄上一把大胡子。这个冷笑话也只有二十世纪后的人们才会先疑惑的抬起眉毛,然后咯咯直笑,因为十九世纪的人们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自1848年以来,大胡子就跟革命气概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思想标志之明显,让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50年代下了一道法令,规定所有的公务员都要剃须。
这里有幅漫画,讲的是1868年奥地利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发生的一件趣事——新任内政大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着一把美髯。漫画中的大臣走进了一间官员聚集的房间,那群官员惊呼道:“就是他!先生们!一个蓄须的内阁大臣!奥地利完了!”
当然,这把大胡子确实能解释本书一半以上的内容,那就是雍容华贵、讲究贵族礼仪与风度的十八世纪宫廷是如何遭遇到一把大胡子的入侵的。这把胡子在文化上是男人下颌上的那些毛发,在政治上则是一部宪法。
以后人们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的原因时,往往会指出这么一种观念上的诱因,那就是十九世纪的人们对战争持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正向观感。他们认为战争犹如森林中的野火,烧去枝蔓,而让树木更健康。如果我们撇去这种言论中所蕴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断,把它放到十九世纪的历史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信奉这种观点,正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真实的。
十九世纪的世界,相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暴烈,以及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和缓年岁来说,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竞争状态中。而正是这种状态让欧洲列国都纷纷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在更严酷的时代,国家来不及进行这样的改革,而在更和缓的年代里,政府没有生存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来进行改革)。我们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顺便说一句,黑格尔专门为这次战役写了一本书,称它为“历史的终结”),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俄罗斯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实际上,不独欧洲国家如此,当时凡有志于自强的国家莫不以立宪为任务。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大做出口加工贸易、靠外资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条件,要想增强国力,只能靠国内社会与市场的内在发展。要与列国争竞,就不能不稍假民力。明治维新时日本元老院就在《推进国宪复命书》(1878年)中写道:“(当今世界)以开明兴盛著称的国家均采用立宪之政……不伸张民权,国家则分崩离析,所以君主不能独享其权。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权,使君民之权各得其所,非制定国宪不可。”
既然宪政不可避免,十九世纪的统治者们由此进行着一场艰辛的政治园艺工作,企图把它与旧制度嫁接在一起。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奥地利,都纷纷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最低限度的立宪政体”。这往往意味着有一部被当真的宪法,有一个功能受到极大削弱但仍有一定实权兼吵吵嚷嚷的民选议会,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这种体制从正面的角度讲,这是赋权与政府的自我约束,从负面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以看成是威权人物对政党和人民的某种“驯化”。于是政治分裂的因子就内含其中。
本书颇具慧眼的地方之一就是指出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其实都有某种共通之处,他们既是“最低限度的立宪政体”的设计者与维护者,也都深受中内含的政治分裂之苦。
比方说拿破仑三世的理想是实现“进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虽然都是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但却努力向旧王朝靠拢,做“驯服法国革命的人”。但是帝国的革命色彩让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这个头衔又让他和共和派反目。在没有确定社会阶层支持的情况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的是反复的借力打力与政治腾挪。他需要用公决、普选产生的立法团来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但又不能真的将之化为政治现实。为了应对这个两难局面,第二帝国需要一个张扬的君主,需要议题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传、游行、节庆、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险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盖他帽子下面那只拿着兔子的手。
作者接着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身上都嗅到了波拿巴主义的味道。
在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一直有一套防御性弹性改革策略,即主动有控制的进行政治改革,以保证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王室与贵族手里。《俾斯麦回忆录》中有一则故事,是腓特烈·威廉四世当笑话讲给俾斯麦听的。当时俄国同普鲁士还是盟友,沙皇尼古拉找老朋友普鲁士国王借两个低级军官,帮他背部按摩,理由如下:“对于我的俄罗斯人,只要我能盯着他们的脸,就不愁对付不了他们,可是背上没长眼睛,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到我身旁来。”沙皇本人猜忌其臣民如斯,普鲁士国王无疑引以为戒。俾斯麦自己呢,也否认自己是绝对专制统治的爱好者,他自承“我一直认为君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一种独立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监督”,以免君权肆意妄为。
不过,尽管王室与贵族都承认,有必要让普鲁士——德意志臣民享受一定的经济自由、私权保障乃至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决定将政权拱手相让。他们所希望的建立的这个体制,是“君主民辅”。根据1871年帝国宪法,帝国立法机构由两院制议会构成,分成上下两院,上院是联邦议会,由各邦派出代表构成,掌握实权。下院才是普选出来的帝国议会,权能很小。官吏任命、军队统率、内阁组成均不在帝国议会权限范围内。帝国议会的最大权力在预算方面,它可以同意或者拒绝政府提出的预算。不过,即使它拒绝,政府还是可以仍然按照上一年的财政预算获得资金,而不至于断粮,有学者因此讽刺说,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此言非虚。
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帝国议会的真正作用在哪儿呢?它是一条护城河,能够吸收并缓冲德意志人民的政治热情。第一,它让大家伙能有个念想,消停消停;二,为政府提供合法性;三,最重要的,当时德国社会是很多元的,各邦有很强的地方主义情绪,又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的对立,再加上城乡差别,帝国政府预计将看到社会上多个阶层、集团或组织将为了选票而互相斗争,帝国政府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四,它制造一种渐进主义气氛,给政府以从容布局的时间、空间。
“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工具性宪政”所蕴含的分割对抗性质,才让俾斯麦有机可乘,可以利用皇帝与议会的矛盾,来让自己数十年大权在握,让威廉一世笑称自己是“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当皇帝”。只有理解这个逻辑,才能明白作者对俾斯麦的下述评语——“(他)背靠君主来压制议会,又反过来用议会控制君主”、“俾斯麦满足于依靠帝国议会各党派的的分裂和不团结,利用他们各自的利益矛盾,来操纵帝国议会的票数推动自己的统治时,他就成了一个帝国宰相府里的拿破仑三世。”
至于威廉二世,在作者看来,恰恰也是拿破仑三世的翻版。他的个性与早年境遇并不能充分解释他那些变化不定的决策,那些极富鼓动性质的帝国叫嚣。帝国结构性的政治分裂才更有解释意义。他是个宪法君主,但是这部宪法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就故意留下冲突的隐患。像俾斯麦那种高手自然可以在这些冲突间游刃有余,乃至利用这些冲突掌握权力。但威廉二世并不在此类高手之列。他应对政治困境的方法同拿破仑三世一模一样:直接跳过现有的政治机制(议会、宰相府与政党)向民意喊话,以民众的真正代表自居。他扑向一切能引发民众支持率的政治议题,做出相互矛盾的表态。在那个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里,于是他成了帝国主义的推动者与代言者。其原因无他,他和拿破仑三世一样受制于分裂的国内政治结构,只能用表演取代统治。而还有什么表演比胸脯昂扬、旌旗招展与外人对抗更鲜明夺目呢。他们的结局也一样,将各自的国度贸然带入了一场并无必要的军事冒险之中,并最终摧毁了自己。
所以,高林这本“过时”的书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过去时代的一个历史机制——最低限度的宪政机制并不能保障王朝万世长存。俾斯麦有一次给他妻子写信,如下:“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此事正如此。
当然,这本书还讲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太懒散了,就不赘述了。
注:已经发表在《上海书评》上了。
《皇帝圆舞曲》读后感(五):高林:睡神、梦神与你我 ——《皇帝圆舞曲》自序
高林:睡神、梦神与你我 ——《皇帝圆舞曲》自序 | 青年维也纳
原创: 高林 青年维也纳 2月21日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
经过了漫长的工作,《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终于出版了!谢谢帮助本书出版的每一位朋友!感谢青年维也纳的所有读者们!本文为作者高林桑的自序,只有2575字,五分钟左右读完。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和文学之间已经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也横亘在文学和生活之间。历史和文学、文学与生活,甚至历史和生活之间都变得泾渭分明。
我们以问题意识来划分时代,并赋予时代以主题。我们总结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把过去的岁月看作“绝对精神”演变的不同阶段,以至于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历史当中的人看作无足轻重的点缀。如果说维也纳宫廷把普鲁士刑法中禁止的那种同性之间的行为叫作“波茨坦病”,那么,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大概可以叫作“柏林大学病”或者“黑格尔病”。
当这本书里的文字要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作为一个典型的没有黑格尔命却害了黑格尔病的人,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反复问自己:“难道这些东西可以成为一本书吗?”难道一本书不应该是某种思想的载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精神”的一种体现吗?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让自己从这种症状里摆脱出来,你们也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找了面镜子照了照自己,然后我就再也不去想什么“绝对精神”了。
其实,历史、文学和生活原本是三位一体的。100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说:“人生模仿艺术远过艺术模仿人生。”如果说“模仿”意味着距离,那么,历史和生活之间其实连这层关系都不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考古学家认真地考察中世纪公共墓地的遗骨,据此分析中世纪普通人的预期寿命,甚至根据海底沉积物里的花粉浓度来判断古代的温度变化。历史与我们之间其实并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历史就是我们自己。
比如,当你读到这里,把书翻回扉页想看看这个东拉西扯的作者到底是谁的时候,买这本书时的那个善良的、好欺骗的你,就已经随着这个动作走进了历史。
是的,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好意思把这本奇妙的书交到你们手中。坦白说,我自己从没想到它最后能变得像今天这样完整、井井有条而且浑然一体。这都是我伟大的朋友一霖和袁业飞的贡献,因为这本书的最初形态只是一系列独立发表的文章被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起。
如果说它们发表时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我能想到的大概有两点:第一,它们都是一个叫高林的人写的;第二,它们都是高林这种“历史生活化”,我们姑且不说是“庸俗化”的观念的产物。基于这种观念,我把历史看作过去时代里人的生活的总和。
在过去的每一个时代里,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因此也是相通的。当我们看到那些久远年代哀痛的父母给自己夭折的孩子留下的纪念物,或是那些遥远年代里发源难考、旋律质朴的情歌,再或是一首几经流转,依然被反复吟唱的悼亡歌,如果它拨动了你内心深处某些温柔的部分,至少在那一瞬间,你和古人是声息相通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通灵”感。
在过去的岁月里走过的那些人,其实从没有真正远去,只要你愿意寻找,在雕塑、绘画、建筑中,在他们眺望或者俯瞰过的山河大地上,在他们留下的诗句或歌声里,他们的生命都在继续。
当历史成为你和古人之间的桥梁时,当你透过历史感受到那些古人的心灵时,历史所扮演的其实是文学的角色。我们在文学里感受别人的心灵,体验别人经过浓缩的生命,然后享受到文学的乐趣与温暖。
假如我们抱着同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它也完全可以提供相同的服务:文学用自己的手法去表现作者的时代,历史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当历史还没有变得远离我们时,它和文学之间并不存在那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那是兰克会开心地捧读瓦尔特·司各特小说的时代,当人们问他:“《昆汀·杜沃德》在历史细节上是准确的吗?”兰克反过来问:“《昆汀·杜沃德》在细节不准确又怎么样?”
这是一些关于过去的文字,如果一定要提供一个坐标,那就是一本关于“近代”欧洲的书。再具体一点就是关于“美好年代”的书。可一旦具体到这个地步,误解也随之而来,因为一切“术语”其实都有标准含义,比如,美好年代(LaBelleÉpoque)原本指的是一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它是一个法语词,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关于法国的部分却并不多,所以解释也就不可避免:
维也纳城这是一本关于“美好年代”这个时段里的欧洲的书,从柏林到巴黎到维也纳,我们写了很多东西。
在全书的前半部分,我们追溯了美好年代的开端,第一章我们谈到了19世纪的史前史,18世纪的启蒙时代——旧制度下的最后时光。
第二章我们以一种浮光掠影的态度扫过拿破仑和他的帝国,然后进入了19世纪的真正开端——复辟时期,以及那些停留在两个世纪交界点上的人。瘸子塔列朗在这里显得有点突兀,但这种突兀其实正是让我们把他留在这里的最大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凸显了这个时代作为分水岭的特点。
这个理由也可以解释梅特涅,梅特涅和塔列朗在这个时代里有众多的共同点。这两个人构成了一座桥梁,让我们从那个戴扑粉假发的年代,走向那个留络腮胡子来表达自己自由主义立场的近代。
在这个时代,第一个被我们请出来的人是拿破仑三世,因为从统治手段上说,拿破仑三世是近代一系列波拿巴主义式统治者里的第一人。从个人气质上说,他也是第一个真正面对现实,以一种近代政客的精神去扮演君主的统治者。
在他之后,有趣的人相继登场,比如爱玩游艇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还有他那个同样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尚教主培养的,既爱玩游艇也爱玩汽车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还有沉默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他们一起构成了美好年代的顶层。
在他们之下,一个正在兴起的阶层“中产阶级”正顶着“布尔乔亚”的帽子急切地登上历史舞台,比如,可爱的巴黎社交明星普鲁斯特,还有在维也纳的身体健康、欢蹦乱跳版的普鲁斯特——施尼茨勒。他们构成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
在他们之后,我们将看到一个世界的落幕,当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终结。
当你终于看完了这段喋喋不休的独白翻到正文时,我希望你看到的是一本轻松愉快的书,这也是我“历史庸俗化”主张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本历史书或者关于历史的书没有意思,那还不如不写。
作者高林历史之于你,应该像睡神与梦神,紧紧地抱住你们,蒙住你们的双眼,带你们走进梦乡。因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其实早就沉睡在历史的怀抱里了。
欢迎关注作者的公众号:青年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