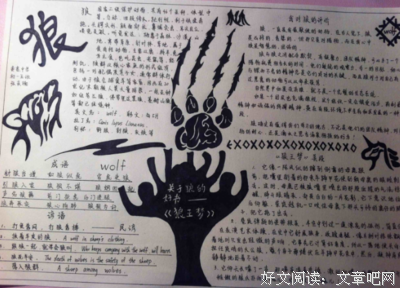
《知觉的世界》是一本由[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共七讲,百来页。第一讲的出发点和胡塞尔类似,还是针对现代科学提出疑难,通过指出现代科学的局限性引出知觉世界。 第二讲,具体通过艺术(尤其是绘画)来讲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关于空间的思想转变,这部分其实和《非理性的人》中“现代艺术的证言”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自己领会。 第三讲第四讲,继续延伸从空间谈到整个知觉世界的探索。第五讲,反驳了近代笛卡尔开启的或者说反驳了整个哲学史上的物质精神区分的二元论,从外部对人进行重新评估。第六讲,具体谈艺术方面的现代性,和《非理性的人》中例证非常类似。 第七讲,讲现代艺术哲学态度的转变以及古典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区别,以及追问这种区别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古今之争的意味),最后梅氏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书篇幅不长,值得一看。
《知觉的世界》读后感(二):世界如你所见
一切艺术研究都该从知觉出发。
而是说电影脱离了观看便不再有意义。
电影,永远是某位观者的电影。
他从自我的知觉出发展开对电影的研究。
而他的研究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人类的知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共通的。
理性在此失效了,因为艺术诉诸感官。
我们用感官体验艺术。
世界并非如你所见,是因为感官被日常经验遮蔽。
如同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在观者身上完成。
《知觉的世界》读后感(三):扫雷
1(页2行1)这个Emile Henriot不是什么法兰西学院院士。
2(页5脚注2)这里不附上原文根本看不出区别。我只找到葡文版,似乎这里不一样的是“仅仅”和“我就能”两处。
3(页17行9)据文意,这里的“不能互换”应为“不能改变的”。
4(页19行7)据葡文版,“视角主义”即perspectiva ,应为“透视法”。
5(页20行1)“从画家出发奔向这个点”即vão do pintor ao horizonte,应为“从画家出发奔向地平线”。
8(页23行12)据文意,“低估了这个星体的大小”应为“高估了这个星体的大小”。
9(页30行2)据文意,“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接起来”应为“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连接起来”。
11(页42行9)据葡文版,“价值”即interesse,应为“兴趣” 。
12(页48行4)据文意,“生物以及我们自身尝试赋予它以形式”应为“生物包括我们自身尝试赋予它以形式”。
13(页51行5)“一个在世的存在者”即uma existencia jogada,应为“被抛的存在者” 。
14(页59行12)据上文,“灵魂和身体之分”应为“精神和身体之分”。
《知觉的世界》读后感(四):备忘|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
全书七讲,篇幅短小,内容相对轻松。一些观点并未展开,但作为对梅洛庞蒂的入门了解(关键是他本人写的哦!!!),值得一读。
在第一讲中,他首先指出了知觉的世界和科学的世界在当下语境中的对立。他没有论证二者孰优孰略,也没有指责理性主义的广布,最多只是借科学的不足,试图为知觉的世界正名:科学的世界无法达到绝对客观,它对物理事件的近似表达呼唤我们去重新认识知觉。
随后从第二讲开始,他带领我们正式进入知觉的世界。二、三、四、五这四讲都是对知觉世界中不同因素的阐释,遵循的脉络线索是按照惯常的分类依次讲解这个世界的形式(空间)和内容(感性之物、动物性、从外部看人),却同时表明古典科学二分法的僵化界限应当被打破,世界实际上是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呈现的,由此,形式和内容会发生混合,时间的性质也会突显。这也就是说,上述的脉络只是我为了理解讲座的线索而进行的简化归类,而在梅洛庞蒂那里,内容和形式、物和物的位置的相辅相成始终贯穿在讲座里——“人并不是一个精神和(et)一个身体;而是一个合同于(avec)身体的精神,并且,此精神之所以能够通达诸物之真理,只因这身体就好像是黏附于诸物之中的。”
展开来看的话,“空间”一讲的重点在于揭示其异质性,基于空间同我们的联系的紧密与否,不同的空间/方向之于我们的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同时,通过本讲,物不仅更加深刻地渗透进了原本与之界限分明的“空间”,“空间”作为物的呈现方式也顺理成章地渗透进后几讲的阐释中。“感性之物”一讲最开始较为狭义地从与人相对的、填充了空间的“物”着手,在统觉的认识能力外另辟蹊径。比起理智的综合行为,梅洛庞蒂更满意于现代心理学“情感意谓”(une signification affective)的解释(类似于“通感”?),“这情感意谓会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结起来”,“物的统一性并非处于其所有的性质之背后,而是相反,物的统一性为它所有的性质所确立,每一个性质都是全部的这个物。”也正是由于“情感意谓”,“人驻于物,物也驻于人”,超现实主义的l’objet trouve便源自这个逻辑。第四讲和第五讲终于过渡到广义上的“人”。但他不是古典思想家所认为的“完成了的人”(un homme accompli),而是如第四讲涉及到的福柯式的“边缘人”,或如第五讲所述,我们是每时每刻都需要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确立自身的人。“反思”不再是理性分析式的观念提纯,而是打破封闭的边界,彻底以陌生的目光(也许是甲虫的)来检视自身以至人类。
第六讲“艺术和知觉的世界”主要以艺术作为开启知觉世界的方式,带我们重新感受何谓“对物本身的观看”。绘画、电影、音乐、文学,都可能“以一种感性之物的方式存在,是以一种处于运动中的事物的方式存在,我们当在其时间性的发展中知觉此物之律动,而且此物在我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并非一个由种种观念所构成的整体,而是这些观念的一个徽章(embleme)或画押字(monogramme)。”
第七讲,梅洛庞蒂把一直潜藏在讲座中的这组对立焦点拎出,作为最后的总结:“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与古典世界的“单一”和“确定”相比,“现代思想表现出了未完成性和暧昧性这一双重特点”。但他仍然不以优劣来评判二者的高下分别,而是饶有趣味地指出:“现代”意识或许不是现代才有的真理,而是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真理,只不过因为我们正在经历所谓的“现代世界”,所以这真理才表现得更为醒目。
时间对记忆的掩埋使我们无从知晓,当下的先锋是否已在过去萌芽或仅是过去的重演。
《知觉的世界》读后感(五):Merleau-Ponty:《知觉的世界(Causeries 1948)》摘要
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王士盛,周子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3
一部成功的小说并非作为某些观念或论点的堆集物而存在,而是以一种感性之物的方式存在,是以一种处于运动中的事物的方式存在,我们当在【86】其时间性的发展中知觉此物之律动,而且此物在我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并非一个由种种观念所构成的整体,而是这些观念的一个徽章(emblème)或花押字(monogramme)。【按:这七篇由梅洛-庞蒂撰写的“讲话”于1948年由他本人在收音机节目中演讲播出。这本书非常简洁地将现代思想不同于古典科学对知觉世界的看法呈现出来:科学并不握有绝对和全部的认识,没有绝对的观察者,任何观察都与观察者的处境紧密相关,知觉的形式和内容并非了然无涉。“人并不是一个精神和(et)一个身体;而是一个合同于(avec)身体的精神,并且,此精神之所以能够通达诸物之真理,只因这身体就好像是黏附于诸物之中的。”【20】这也决定了现代思想的未完成性和暧昧性的双重特点。】
知觉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感官及日常生活经验所揭露给我们的世界,乍看之下好像最为我们熟悉不过,因为要进到这个世界,既无需仪器,也不用计算,好像只要睁开经验生活在其中就可以了。科学则宣称这是假象,"真实的世界并非眼睛所呈现给【4】我的这些光、这些颜色、这场肉身景象,而是科学所告诉我的它在这场感性臆象(ces fantasmes sensibles)背后所发现的波和粒子。“笛卡尔甚至说无需求助于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就能发现我的感官是虚幻不可信任的,并由此学会只信赖理智。比方说我看见一块蜂蜡,它是什么呢?它肯定既不是这白晃晃的颜色、不是它或许还在散发着的花香、不是我拿起它时所感觉到的这种绕指的柔贴,也不是当我把它扔到地上时它所发出的沉闷的声响。即使失去了全部这些性质,这块蜡也不会因此就停止存在。比如说,我若把它熔化成液体,它就会变形成为一种无色的液体,不再有什么闻得出的气味,也不再有可拿捏的固定的形状,但这块蜡依然存在。“这说明有一个不会受物体状态变化影响的不带任何属性的物质片块,也就是说无论物体的状态如何改变,那种占据空间的能力、那种接受不同的形状的能力会留下来(而且无论这物体到底实际上占据了哪个空间,无论这物体实际上到底接受了何种形状,这些空间和形状都绝对不会固定到物体的根本属性中,都不会固定住物体)。这(留下来的不变的能力)就是蜂蜡那真实而恒在的核心。[……]所以,真正的蜡就必然不是能通过眼睛看见的。真正的蜡只能通过理智构想出来。”【6】这里,知觉和科学的关系就好比表面现象和真正现实之间的关系。现代思想并不质疑科学的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是为了限制科学的研究领域,它想弄清楚的是,“科学是否提供了或者是否将能够提供一幅完备的、自足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封闭的关于世界的表象,以至于科学之外再无真正的问题可问?”【8】自19世纪末以来,科学家们就习惯不再把他么的规律和理论看作自然中所切实发生的事件的准确反映,而是看作永远都比自然事件要简化的模型。观察无极限,无论何种观察,我们的构想中都会有变得更加完备更加精确的空间。因此,科学的任务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完成。相对论物理学确证了绝对而最终的客观性是个虚幻的妄想,任何观察都是处境性的。
空间:古典科学是建基在空间和物理世界的明确区分之上的。“在古典科学看来,空间就是个完全均质的环境,在此环境中物体以三个维度布展开来,并且在此处所中物体的同一性并不受位移的影响。[……]【16】几何的领域是严格地和物理的领域分开的,世界的形式和世界的内容是不会混淆的。位移并不会使物体的几何属性发生改变,物体的属性若在位移之后发生了变化,必是因为伴随着位移——但并不是因为位移——物理条件发生了变化。”然而,随着非欧几何的兴起,我们开始认为空间本身就是弯曲的,位移这一事实本身就会改变物体,世界中的物体不再能够自处于一个绝对的同一性中,世界的形式和内容被混合了起来。于是,严格地把作为纯粹概念的空间和具体地呈现给我们的感官的空间区分开就变得不再可能了。令人惊奇的是,现代绘画探索出的结论与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古典教条把素描和颜色区分开来:先勾勒物体的空间图式,然后再给这些图式涂满颜色。塞尚则认为,““涂颜色的同时必然也是在勾勒图式”,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在被知觉的世界里还是在那意在表现此知觉的世界的画上,物体的轮廓及形状都不是和各个着了色的模块分开了的;这些模块包含了一切:形状、颜色、物体的形体外观以及物体和它周围诸物体的关系。”【18】关于绘画的古典教条是建立在视角主义之上的,画家并不是在给出物体呈现给画家的尺寸、颜色和外观,而是在试图给出物体为传统绘画规则所规定下的尺寸和外观,也就是说,当把目光投注于地平线上某一个固定的点时,当风景画中的一切线条都因而从画家出发奔向这个点时,物体所呈现出的尺寸和外观。“画家如果想成功地彻底控制住这一系列的所见并从中提取出一个永恒的、唯一的风景,就不得【20】不破坏掉自然而然的看的方式。比如画家就必须得时不时地眯起一只眼睛,借着铅笔去目测清楚一个细节处看起来到底有多大——然而这种做法难免就会改变这一细节本身——然后把这些都置于一个分析性的看之注视下,并进而在画布上构建对风景的再现。如此这般再现出来的风景完全不符合任何自然而自由的看,这般再现出来的风景宰制住了自然的看之动态的开展,并且,这般再现出的风景还取消了这自然的看之律动和生命本身。”自塞尚以来,很多画家都开始拒绝遵从几何视角这一规则,而想要抓住并再现出风景在我们眼底下的诞生本身。在这些画中,从来没有两个物体是同时被看到的,存在不是现成地被给予了的,而是通过时间显现或浮现出来。现代绘画的空间,按照让·包兰(Jean Paulhan)最近的说法,乃是“心所感觉到的空间”,这一空间就在我们附近,并通过我们的肢体及器官和我们结合在一起。随后梅洛-庞蒂提到了马勒布朗士对地平月幻象的解释,在月亮初升之时,月亮是处于田野、墙壁和树木之上的,这些交叠在一切的物体使我们感觉出了月亮的遥远。但如今,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知觉场的一个一般属性:在地表这一水平层面上物体看起来的大小是相对恒定的,然而在垂直层面上,物体看起来的大小则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迅速地缩减。这是因为对于我们这种陆生的存在者,地表这一层面是我们的生命运动于其中的层面,是我们活动于其中的层面。此幻想并非马勒布朗士认为的纯粹的理智活动,而是由于空间是异质的,是和我们身体的各种特点有着紧密联系的,是和我们这样一种被抛在世界上的存在者的处境有着紧密联系的。
感性之物:不同于经典心理学所认为的,物是由一些不同的性质呈现给了不同的感官,然后再由理智的一个综合行为将这些性质统合为一个体系所形成的,现代心理学注意到,物体的任何一个性质都远非严格地独立,而是都拥有一种情感的意谓(une signification affective),这情感意谓会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结起来。“说蜜沾手和说蜜甜是两种说同一件事情的方式,这两个说法都是在说物和我们的某种关联,都是在说物暗示给我们的、强加给我们的某种行为(conduite),都是在说物所拥有的某种引诱、吸引或曰迷惑那在它面前的自由的主体的方式。蜜是世界朝向我的身体的、朝向我的某种特定的行为(comportement)。正是因此,蜜所拥有的各种性质并非各自独立地码在蜜里,恰恰相反,这种种不同的性质是同为一体的,因为所有这些性质都是在表现蜜的同一个存在方式或曰行为方式。物的【32】统一性并非处于其所有的性质之背后,而是相反,物的统一性为它所有的性质所确立,每一个性质都是全部的这个物。”物并非处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所思考的中性的对象;每一个物都向我们象征着某种特定的行为,都向我们提示着这一行为,都激发着我们或正面或负面的反应。“每一个物都向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诉说着什么,每一个物都穿着人的品格(顺从、温柔、恶意、抗拒),并且,物反过来【34】也活在我们之中,作为我们所爱或所恨的生活行为的标记。人驻于物,物也驻于人——借用心理分析师的说法就是:物都是情结(complexe)。塞尚亦持此观点,他曾说绘画所力图传达的正是物的“光环”(“halo”)。”加斯东·巴什拉把现代诗人弗朗西斯·蓬热对水的评论(并非被观察到的性质,而是它向我们说了些什么)扩展到了所有的元素(气、水、火、土)。在这些著作中,巴什拉把每一种元素都看成了某一类人的心灵家园,看成了此类人魂牵梦萦者,看成了主导此类人生活的那一为其所最钟爱的境域,看成了那赋予此类人以力量和幸福的自然圣礼(sacrement naturel)。“长达三十年,超现实主义力图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体中——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失而复得的、弥【37】足珍贵的物件中——寻找那“欲望的催化剂”,或者,正如安德烈·布勒东所说,寻找人的欲望于其中显现自身或曰“结晶”的地方。”
动物性:古典思想中,动物不是被看作机器,就是被看作人的初级形态,比如许多昆虫学家毫无犹豫地把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特点投射到动物那里。我们对小孩、原始人以及病人的看法也类似,被探讨的存在者要么是被看成类似于人,要么就是被看作不过是一个盲目的机械,一个活着的无序体,并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给其行为找出意义。这是因为古典思想家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成了的人(un homme accompli),这完成了的人矢志于去做自然的“主人【44】和占有者”,正如笛卡尔常说的那样;并且,这完成了的人因此至少在原则上能够穿透物之存在,能够建构出一种具有至上之权威的知识,能够解码一切现象——不仅仅是物理自然意义上的现象,而且还包括历史现象及人类社会现象,能够用原因去解释这些现象,并且最终能够发现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异常导致动物、小孩、原始人和疯人偏离了真理。古典思想中的理性享有神一般的特权。[……]【45】我们上面所谈及的种种异常,其价值便不过是供心理学去观奇猎异,便至多只能在“正常的”心理学和“正常的”社会学中被施舍给一个边缘性的地位。”今天,我们发现,上述看法或曰教条是大有问题的。正常的成年人并不“拥有”从其行为所能重构出来的融贯完整的体系,“他永远也没有真真正正地免于这些不正常。他必须谦逊地检视自己,必须在【46】自己身上重新发现所有的幻想、所有的梦、所有的巫魅性的行为、所有晦暗的现象。所有这些,在他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都是一直强有力地施加着影响的。所有这些,甚至都在他对自然的认识中留下了种种罅隙——诗正是穿行于此罅隙中。”大人的、正常人的、文明人的思要比小孩、病人、原始人的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认为自己具有神一般的权利,这思不能失去与这一生活的非理性根源的接触(人类生活中的种种隐晦和困难),它必须承认世界是未完成的,此文明和认识并非不可置疑,而理性的最本己的功能正在于去论述、去置疑此文明和认识。
从外部看人:虽然三千多年来关于人,人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但是这些经常都是通过反思才发现的东西。笛卡尔,比方说,离开了外部之物,并且仅仅通过发现自己是个精神才清晰地把自己界定了下来,也就是说发现自己是一种不占据空间的存在,是不在物之中延展开的,而只是那纯粹的对自我的意识。很显然,这个纯粹的精神只能在我自身这里找到或者说触摸到,其他的人永远不会是纯粹的精神,我只能通过他们的身体才能认识他们。“诚然,他人对我来说远不可被还原为他的身体,他人是这样一个身体:是一个为各种各样的意向所激活的身体,是一个作为许多行动和话语之主体的身体,这些话语【58】和行动回荡在我的记忆里,正是这些话语和行动向我勾画出了他的精神风貌(figure morale)。”因此,从外部去思考人就意味着对某些理所当然的基本区分——例如灵魂和身体之分——进行重估。比如说愤怒,事后我们去反思愤怒是什么,我们就会注意到愤怒包含着对他人的某种(负面)评价,由此,我们认为愤怒就是一种思,发怒就是在如此思考:他人是可恶的。然而这反思是徒劳地,因为只要我回转到愤怒这一经验本身(正是这一经验本身引发了我的反思),我就不得不承认愤怒并非在我的身体之外,愤怒并非从我的身体之外激动着我的身体,而是和身体密不可分地在一起。笛卡尔也因此说过,“灵魂并不仅仅是身体的主宰和统帅——正如舵手之于船那般,而是【63】和身体非常紧密地合一的,以至于灵魂在身体上受苦遭罪,这层关系清晰地体现在比如我说我牙疼的时候。”不过按照笛卡尔的观点,灵魂和身体的这种合一是我们几乎无法去谈论的,我们只能通过生活经验去体会这种合一。笛卡尔的理论传人们确有理论怀疑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事实上所是者和原则上所是者分离开。如今的心理学家们则极力强调这一事实,“我们并不是首先活在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意识里——甚至都不是首先活在我们关于物的意识里——而是首先活在关于他人的经验里。我们从来都是在与别人接触之后才感觉到自己存在着,而且,我们的反思——即向我们自己的回归——其实非常有赖于我们与他人的密切往来。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很会分辨他人脸上的欢喜、愤怒及恐惧了,虽然他此时还完全不可能通过检视他自己的身体而得知这些情感的肉体性特征。这是因为:他人的身体——这有着种种姿势的身体——对这婴儿来说是一上来就有着一种情感意谓的;这是因为:婴儿不仅仅在他自己的内在精神中学习何为精神,也同样在可见的行为中学习何为精神。成年人自己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的是他的文化、教育、书本和传统所教他去看的东西。我们自己与自己的接触永远都是通过一种文化——至少是通过一种从外界所接受的语言——才得以进行的,这语言引导着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么看来,那纯粹的自我,亦即那既无工具也无历史的精神,在作为一种批评性的手段去和周围的观念向我们所施加的粗暴压迫和侵占做斗争之时,是好的,但是,这纯粹自我或曰纯粹精神若想实现为切切实实的自由则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工具,【66】必须参与到世界生活中去。”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但每个人也需要其他人。我们被抛到这处境中,我们有身体,有个人的历史和共同的历史——我们找不到绝对的安稳,而必须不停的努力以缩小我们相互间的分歧,以解释清楚我们被误解的话语,以显明关于我们的那些被隐藏的东西,以知觉他人。理性——以及诸精神间的相互理解——并非就我们的后盾,而是有待我们去抵达。人的生活永远处在威胁当中;是为了从心态上准备好迎接那些罕见而珍贵的时刻:在这一刻,人们认识了自己,并且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