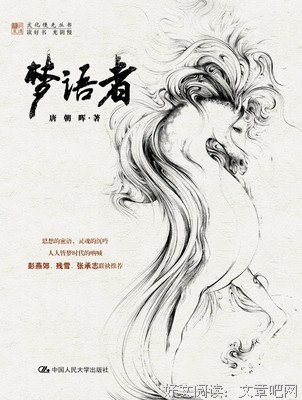《梦语者》是一本由唐朝晖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32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梦语者》读后感(一):有的人死去了,但你不因此悲哀
片断。
比如《古庄》,越读你会越发产生一些静谧的恐惧感,那文字中烘托出的是万物生灵的神性和鬼性,老人如此,壮年的兄弟如此,鸡鸭牛羊如此,山头和神秘的墙如此,万古如斯的村庄如此……有的人死去了,但你不因此悲哀。
人总是要死的,万物如此,墙会倒塌,罪孽会泯灭,打开的门总会关上,关上的门被风和年岁给啄蚀了去。
百感交集,越读你会越发惊奇,作者是如何保持一种饱含人味的浪漫的纯真,去描述那些仿佛见过却又难以推测它们发生过的山村野事。它仿佛不符合你熟悉的任何一种文体——小说?散文?诗?
仿佛发生过的一切,却很难发生在你身上;
仿佛虚构的事,却敲开你心里的门——如果午夜时你仍保持清醒,以一种认祖归宗般的心境去寻找自己;
美的语言,诗化的情境;那仿佛你十分熟悉却从未经历的人生和事物,你感觉到它,它却不存在于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揪心的城市,甚至——你的爱情,你的女人,你天真的孩子和慈善的父亲。
作者是位诗人,是我的同乡。或许也因为我自命为诗人,因此惺惺相惜。然而我这个“诗人”,没有他这个诗人那般好的人生,那般美好的文字,那般坚持而又坚持的纯真的对文学的热恋,一种真的浪漫。
2012.7.4.
《梦语者》读后感(二):带有痛苦的美(彭燕郊/文)
带有痛苦的美(彭燕郊/文)
《梦语者》作为一部自我精神记录的手记式作品,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在对人类生存经验的总结上所作的努力。诚然,它只是揭开几乎是未被观察过的(甚至是无法观察的)人类生存状态和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状态。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哲理性的描述全然是诗化的,抒情味浓郁而又绝不带有浪漫主义那一套呼号、呻吟和绝叫,同时也不带有任何人工的诗学取舍的痕迹,存在于清澈心灵深处的被作者用想象力、用艺术构思如此自如、如此从容不迫地纳入诗里的,我们几乎想说是神圣的诗境里的,所有这些闪亮的具有人文价值的人类经验,就像一江春水在诗的河床里流动着,内在沉着有力,外表却那么文静,怡然自得地浩浩荡荡。
这部规模近于宏大的精神史诗是以对生命价值、生存取向的追索、叩问为基调构建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诘难式发问无不或多或少带有些悲壮、沉痛,甚至濒于绝望的忧虑。应该说,作者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境地,然而奇怪的是,读它却使人感到温暖,如静夜聆听知己诉说心曲。人们曾经担心,20世纪以后的现代诗是不是会走向学院式的玄学,甚至走向颓废,因为人类对自我状况的思考和由此而生的追索和叩问都近于无从回答,近于茫然。然而诗人却以他的理智和诚实让我们感到亲切,以他的诗作营造出一个诗化的温暖的人文空间,难道这不就是现代诗生命力的鲜活表现吗?
这部心灵手记也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的一往情深的向往,与之相适应,它的风格也是自由的。不可以将自由理解为盲目的自我扩张或是颓败的涣散,它展示给我们的自由的态势甚至近于无形,我们甚至找不到“自由”这个词,然而我们确实能感受到那种渴望和向往。我们知道这里说的自由简单地说就是生命不受压抑地、自在地生长。毫无疑问,这显示了作者的创造力。在作品风格的构建上,作者娴熟地运用了从自由诗到散文诗的诸多形式。曾经有人认为,自由诗没有格律的制约不可能成为诗,而散文诗又是比自由诗还要危险的体裁,诗的特点在散文诗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了。毋庸多说,请读一读《梦语者》吧。它不以“不顾一切”的“怪”吓唬人,不以“抛弃一切”的“乱”迷惑人;它紧紧把握住艺术创造最高原则之一的“分寸感”。它新,但不“怪”;它勇于创新,但不“乱”。在作者这里,散文诗是挥洒自如而且得心应手的。诗歌史上每一种诗体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很显然,作者之所以要用散文诗体写作,就因只有散文诗这种体裁特别适宜于现代人用以创作严格含义上的现代诗。《梦语者》以及与它同性质的作品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梦语者》读后感(三):梦语者或者局外人
梦语者或者局外人
弋舟
这本书的版权页显示,它被归于散文集。唐朝晖告诉我,这是本散文诗。而我,捧读之时,却顽固地将它视为了一本关乎个人与时代的小说。散文与散文诗的分野何在?如果仅从分行的密度上来甄别,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那么,散文诗与小说的分野又何在?“虚构”在这里似乎成为了一个检验标准。然而,是否“虚构”,真的应当成为检验的标准吗?就好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在文学这块版图上,“真实”大约才算是唯一的量器。没有不“真实”的文学,当然,我是指好的文学;同时,也没有不借助“虚构”便能抵达文学“真实”的好作品。
在这本集子里,唐朝晖首先在取材上遵循了我们约定俗成中对于散文抑或散文诗的那种预判,它非但貌似有一个现实的基础,而且也的确真的有一个借以让自己起飞的根基。前者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写作者的轮廓:来自湖南乡村,十五岁在石灰窑做工,逐渐成长为一个诗人,如今于京城之中算不得功成名就,但也差强人意地游刃有余。这难道不符合一本小说通常的架构吗?所不同的只是,唐朝晖假以“散文诗”的笔墨,更多赋予了自己这番成长史一派吟哦的气质。他写故土,写师友,以扑克牌的方式写今天自己的林林总总,词语成为他的入口,风雨雷电,热浮冷静,结结实实一副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分子派头。但恰是这幅派头,让他在这个符合“散文”陈规的所谓“真实”之上,凭空跃起,摸着了艺术那种更为普遍的规律。
形式主义,多么好的词。如果你算得上是个多少明白艺术的人,就该明白我是在指什么。丰富的意象有时候会令人觉得不知所云;节奏占据了那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有时都破坏了意义。然而就这本集子而言,唐朝晖以自己的文学能力,恰恰让这些破坏意义的不知所云,完成了让人摸不着“散文诗”成其为“散文诗”的因素的这种效果。他用他的形式主义,在文体上成就了更为高级的某种蒙昧。在我,只能将这种蒙昧往小说的方向靠拢了。
在我们的文学教科书中,散文与诗似乎关注的更多是朦胧,而不是明晰,相反,小说叙事的结构却周正、严整。但艺术岂是如此条分缕析的简单事?作为艺术的复杂性,这本集子给出了上佳的例证。唐朝晖以“散文诗”为名,放大语言与音律的统治地位,在一种灵巧的相互关系中,将“实”导向了“虚”,并且,从中完成了只有小说才格外强调的那种周正与严整。于是,奇妙的滋味出现了,作品开始了下一个层面上的蒙昧。这便是形式的骄傲,他从中找到了一种巨大的可靠性。
对应于“形式”,当然便是那个“内容”了。——天可怜见,我们只能如此笨拙地来谈论文学。
人人皆梦时代的呐喊——这是这本集子封面上印的字。如果所言不虚(如今岂敢相信封面上的字?),那么,这是否堪可视为这本集子的“内容”?
老实说,随着年逾不惑,我已经逐渐开始排斥阅读那些简单以“我”为基本对象的文字。“我”当然重要,这几乎永远毋庸置疑。我所反对的,不是“我”,而是诸般“伪我”,就好比,我们从来反对的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泛滥的伪现实主义。被我们的文学语境所戕害,散文抑或散文诗,似乎拿出“伪我”腔调的风险更大一些,有感而发乃至直抒胸臆这些教导,常常被扭曲到将写作者的格局必然缩小的地步。所幸,唐朝晖却在这本集子里写出了“第二个我”(甚至某个章节就是以此为题目的)。于是,“他”出现了。随着行文中“他”的出现,反观与自查就成为了可能,虚构就成为了可能,逼近真实就成为了可能。由于这个“他”的出现,集子中大量使用的“我们”才变得令人信服,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起码在代言“我们”这样一个规模的时候,变得更具说服力。这让唐朝晖独语一般的文风,奇妙地具有了某种更为深刻与铿锵的力量。这时候,他就不是在窃窃私语了,那个“我”焕然有了为一个时代发声的气质。“我”的所有悲伤,“我”的所有欢乐,原来就是这个时代其实早已昭然若揭的气质。
“我”是如此弱小,从性情乃至体貌,都如此弱不禁风;我又何其强悍,在精神中,至少在臆想里,会对着破门而入,强行劫掠“我”的自由的警察说:滚出去!就好像书名《梦语者》是对于封面上那句有可能成为卖点的话的反动一样,当“我”与“他”,“我”与“我”如斯相悖之际,非但文学的张力凸显而出,而且时代之荒谬,岁月之虚无,翩然于文字之中具备了那种可称之为“内容”的意义。如此,这本集子便令人珍惜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我们截取与定格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部分真相。
也许会为此沮丧,但无论如何,呐喊显然不是唐朝晖的根本气质。在我看来,他更善于的还是喟叹。于是,他罔顾逻辑上的不合理,在封面推荐词的指向下,依然使用了《梦语者》这个书名。对此,我以艺术的名义向他致敬。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作家,一个诗人,首先应当警告自己的就是:即便要呐喊,也应当以那种梦语者般的、符合艺术准则的方式开口。天生艺术家、形式主义分子,这些品格保障了唐朝晖发声之际的这种格调。在这个谱系上,他显然有着自己情有独钟的来路。对此,书中关于七月派诗人彭燕郊先生的那部分书写可资为证。究竟,唐朝晖倾情的,依然是那种极富教养的文学之路。这当然是一条纯正之路。
每当我扫过《梦语者》这个书名,几乎就要条件反射一般地想到《局外人》这三个字。它们之间当然不仅仅是修辞上的仿佛,更多的,是那种内在的、极富教养的、饱含着文学性深情与复杂的一致。
有了“真实”,有了“形式”与“内容”,有了这样一种来路的纯正,唐朝晖的这本集子,就完全具备了立于书架之上的价值。
《梦语者》读后感(四):中国版《惶然录》:停留然后前行
夜深人静之时,我读完唐朝晖的《梦语者》之后紧接着读了几篇有关它的评论,包括彭燕郊、张承志的序言以及残雪的读后感,我很奇怪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唐朝晖的《梦语者》与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相提并论。我不能确定唐朝晖是否读过《惶然录》,但我在这两本书之间能找到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那一篇篇短小的文章,都象梦中人的呓语,他们都不求别人的理解,与其说他们的书在寻找读者,不如说他们只是在进行自我对话,他们都不在乎世俗的名利,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呓语中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厌弃与随波逐流,对于他而言“停留便是希望”,而对于唐朝晖则是“停留,然后前行。”,他的这本《梦语者》便是他停留时留下的支言片语。
虽然心灵在高处之时,《梦语者》与《惶然录》有许多相提并论之处,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唐朝晖的《梦语者》无疑有着太多中国人的印记。像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唐朝晖出生在一个宁静的乡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一步步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于是我们毫不奇怪,在他的意象里,城市和乡村仿佛是他生命的两极,他反复吟唱,他对于乡村的吟唱是牧歌式的,而对于城市的吟唱则矛盾得多,他厌倦城市带给他的焦虑与围困,但也许这种焦虑和围困,才能激发他吟唱的欲望,城市的吟唱与乡村牧歌式的吟唱不停地相互激荡,最终上升到生命本质的高度。
记不得谁说过的一句话,无论你走向何方,故乡都是你的最后一站,许多年之后,当唐朝晖回到他那魂牵梦绕的古庄,他在感受母亲般温暖的怀抱的同时,也深深感觉到一种被撕裂的痛楚:
“终于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夜晚,不需在城市里度过,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开始切入古庄,与魔影对话、交谈、撕扯。”
“进入这个安静的世界,突然与奔跑叫嚣的城市断裂,耳朵寂静得有一种压力,我怀疑自己是魂游故里。敲打自己的脑袋,听到骨头与骨头的撞击声,城市与古庄的声音相识了,但仅一秒钟的时间,它们又朝各自的方向逃去。它们注定难以走到一起。”
古庄是唐朝晖生命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是他创作的源泉,对此他毫不隐瞒:“古庄的每件细微的事都深烙于心。我的第一行文字,都是热铁与肉体相触时那嗤然腾起的烟雾。往来如影,紧紧相随,让我一天天走过风雨长短亭。”,但即使古庄与他的生命、创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象大多数走出乡村,久居城市的人一样,乡村只是梦中的、想象中的归宿,事实上他永远也“回不去了”。
故乡回不去了,而城市又给了他什么样的感觉呢:
“在岩石的城市里,我为自己招魂,风让草枯荣复返,生命的血一点点消隐。三十年了,手中的枪始终找不到射杀的目标。”
“从岩石中站起,我满身的砾石,翅膀早已消隐。但第三只眼睛依旧坚守眉宇间。仅借着乘虚而入的光,我们无法弄干净这些混乱的石子。太阳阴沉沉的脸,深刻的含笑照视。从岩石中站起,魂如水。”、“诵读了一个时辰《心经》,想哭,在如今的年代里,流泪的地方都被水泥和建筑占领了。”
故乡回不去了,城市又不是他梦想中的家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无数次的试图逃离,只是逃离也无处可去,无可归去,在此,个人的感受上升为一种整个人类的困境,而正是种困境造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疼痛,面对这种疼痛,我们忍受,我们停留,然后前行,虽然没有方向和目标。
“在疼和麻木之间,我宁愿把鹰放在疼痛的血液里,听骨的铮语和风吹过骨折处的哨声。”而正是这种疼痛,让唐朝晖开始思考人类那永恒的主题,那就死亡。
就象唐朝晖面对疼痛时的坦然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面对死亡时也是坦然的,我们看不到他对生命无常的感叹,看不到他对生命虚无的绝望,只到的只是他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与欣然:
“我庆幸自己会死。我终将被死亡占领,我举杯,庆幸自己曾经活过。”
“我是死亡路上的一棵树,长在众生必经的路上。”
“死,就象经历一场动人心魄的爱情,恐惧、激动,心寒,最后平静下来,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至此,我们见证了一个诗人的诞生,他将生命的苦难转化成了生命的诗意,将个人的命运上升为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不是他自己,他是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许多人盯上自己,解剖自己的头发和鞋子。”
“红白蓝的色彩一起围攻你最后的眼神。”
“眼睛在最后一天消失,与眼神一起开始漫长的黑色逃亡。”
我不太清楚唐朝晖作为诗人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前辈们的影响,但《梦语者》无疑是可以作为诗集来看的,因为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无具体指涉的东西,而它们所表达的正是现代人所面对的疏离、纠结、焦虑、冷漠、茫然而又永远归宿,但即使如此,他依然不肯停下前行的脚步。
刊于《读约》第80期:
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80/wenzhang/detail_2012_07/16/16054495_0.shtml
《梦语者》读后感(五):梦语时空中的灵魂独舞——浅析唐朝晖《梦语者》的“梦语”方式
文 罗小凤
梦语者,顾名思义,梦中独语也。鲁迅在散文诗《野草》中开创了“独语”的话语方式,以此“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进行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钱理群语),塑造了散文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后来,何其芳以“画梦”的姿态将“独语”的方式与“梦”结合,开辟了一方与鲁迅所着意构筑的灵魂之重不一样的心灵轻语空间,形成了不同的话语风格。时隔数十年,唐朝晖糅合两位散文诗大师的话语风格,而秉承了“独语”的话语方式,以“梦语者”的姿态“独语”,形成了其独特的“梦语”方式。诗人坦言:“《梦语者》,是我1991年到2008年的一部精神史,生活和物质仅成为外在的导火线,精神或者说灵魂在黑暗和辛劳中游离,失魂落魄。”(《从〈一个人的工厂〉到〈梦语者〉》)可见,诗人的“梦语”其实是其内在精神与灵魂的呈露,《梦语者》便是其心灵史、灵魂史,诗人通过在其诗中创设一个独特的梦语时空,导演了一场凝重的灵魂独舞。
这场灵魂独舞分为七幕,即“心灵物语”、“古庄”、“歇斯底里:轰炸炸轰”、“与城市相关”、“他人是面具”、“安•家”、“扑克牌”,这是他灵魂独舞的各种剪影,是他“梦语”的七个片段,既有暗光、自然、灵迹、疼痛、梦幻、影子等“心灵物语”,呈露了诗人以“尘世之心”对外在世界与现实社会的感知与体验,又有“歇斯底里”、“轰炸炸轰”等呼告,渗透了诗人对人类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困境的思考,还有对城市中的植物、历史、人、阴影、现实存在状态、宿命、梦想等城市景观、人类生存现实的凝视、追索、探问,并在“他人是面具”中对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实质进行了叩问,同时还在“安•家”辑中从“无色透明的下午”、“门里门外”、“混沌初开”等平常的生活场景抽取诗思,将其灵魂的独舞落实到尘世的现实场域,却又不囿束于现实的牢笼,而是诗人寻找灵魂之居所的一种努力。而“扑克牌”一幕则戏剧性地以“扑克牌”这一物象为基点展开,以不同的牌式呈现人生、生命存在的各种生态样式,正如诗人指明的:“亮牌已近半,抓到的分数,显示了昨天的命运和指数。未来依旧沉睡在迷雾中。”(《扑克牌•手记》)画外之音虽然诗人并未言明,却不难理解:人生就是一场牌局,每个人抓到的牌不一样,命运便不一样。诗人正是在这极富暗示性的戏剧场景中将其导演的一场凝重、沉潜的灵魂独舞拉上帷幕,读者则被推入一片冥思的沉寂之中。
这场灵魂独舞是在特定的梦语时空中进行的。“梦”是《梦语者》的核心关键词,唐朝晖在其散文诗中精心设置了其诗歌话语展开的“梦”境背景,操持“梦语”的独特话语方式,构筑了一个似真似幻、似醒似睡的梦语时空。唐朝晖的诗中,几乎无处不是“梦”,无时不在“梦”中,他“靠梦走进自己的世界”(《梦书部•梦》),认为 “梦的时空依旧伸手可触”(《1998年12月31日》),甚至曾看到“梦真实地飞过下午的天空”(《恐怖》),对“梦”情有独钟,《黑桃9:梦》中他清晰而坦诚地呈现了这一点,他认为“我从小到大都在做着梦”,“我只要一合上眼睛,身体和精神就没有了世俗的生活,就进入梦的世界。从小到大,从未间断,每眠必有梦。火车上、汽车上、床上或深或浅的瞌睡等等状况中,我都会有梦”,并认为“我”有两种活法,即“我醒着活着”和“我梦着活着”。或许正是由于诗人对“梦”的特殊情感与经验,他不仅在《梦书部》中对“梦”尽情地进行诗意演绎,在《黑桃9:梦》中呈露自己的“梦”经历和自己对“梦”的感悟,在其他诗中也一次又一次地写到梦呓、呓语、梦想、梦幻、“梦”。于诗人而言,梦便是现实,现实便是梦,由此他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梦”时空。在这诗意而梦幻的时空中,周围的人、事、物等外在现实世界悉数远退、隐匿,诗人澄澈地面对自我,面对内心,面对灵魂,采取了“喃喃自语”、“暗语”、“呓语”、“梦呓”等话语方式,如梦中呓语般流泻其内心的感觉、情绪、思想,由此诗人构筑了彰显其独特魅力的“梦语”话语,别具风格地呈出了其独舞的“台词”。
这场灵魂独舞是从诗人灵魂深处开始起舞的。“灵魂”是朝晖散文诗的另一个关键词。诗人曾指出:“诗歌是我们这颗尘世之心进入灵魂世界最直接的武器”(《从〈一个人的工厂〉到〈梦语者〉》),朝晖的诗都成为他的“尘世之心”进入灵魂世界的武器与路径。在朝晖看来,“灵魂”不仅是人的“心”,也是宇宙万物的“心”,它不仅“存在”,而且具有生命力和各种形态,可以“一跃而起”(《1999年1月1日零点》)、“泛波而出”(《蝴蝶》),拥有“脐带”(《可能的我》),可以“打败”身体,“灵魂的雨水”能打湿足印,“灵魂的鸟”可以“飞起”并“穿透乌云拨亮惊魂的闪电”(《转机》),而“在音乐中,灵魂必醒”(《面具10:唤醒》)……在诗人的诗行间几乎可以触摸到灵魂的实体,感受到灵魂的生命、声音、气息与力量,由此,诗人勾画了一个鲜活的灵魂生命,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灵魂”世界。不仅如此,诗人还在自己所构筑的独特的梦语时空中与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直接探讨灵魂的轻重、有无、迷失、碎裂、萎缩等极为抽象而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买卖》中不无讽刺和戏谑地构设了一幕买卖灵魂的戏剧性情节,由一个人的“给我来点灵魂”到母女的“给我们一点灵魂吧”再到人群的“给我们一些灵魂”,剧中人物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在戏剧性中不无悲凉地呈露了人类灵魂陷落、缺失的状态。朝晖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当下人类灵魂状态的危机与困境,并努力探求突围的路径,如在《轰炸炸轰》中,他认为人类已经“灵魂萎缩”,“解救我们的惟一办法:歇斯底里的轰炸轰炸”,是对人类突破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之路径的深入思考。“我的灵魂与耳朵拚杀”(《轰炸炸轰》)、“眼睛是惟一穿过身体与灵魂对话的一条通道,她们借助于它走出身体的重”(《重影》)、“在空茫质问自己的灵魂”(《混沌初开》)等诗句无不都在叩问灵魂,呈现出诗人对灵魂陷落困境的忧虑、抗争和寻找自我灵魂突围路径的努力。
这场灵魂独舞是彻底孤独的。自从“躲避崇高”的宣言响起,浮躁年代里的浮躁人类极少投注目光于灵魂层面的沉重问题,哗众取宠、大众化、通俗化、消费化、快餐化等写作取向衍生的作品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字泡沫堆积的“盛宴”,当人们争相为这些喧哗与繁华的“盛宴”喝彩时,关注灵魂的诗人注定是孤独的。唐朝晖沉默在高声喧闹的人群中,“看着灵魂一点点从身体周围消失,只有肉身还在支持,背景是完全的黑”(《星球》),他只能悲哀地沉默着,沉默地走入其个人的梦语时空里清醒地“梦语”着:“寂寞的黑色开始吞噬你的身体,灵魂已经远离。身体的膨胀,在变换。眼睛在最后一天消失,与眼神一起开始漫长的黑色逃亡。”(《星球》)这种“黑色逃亡”是个人的命运,更是整个星球上人类的命运,甚至是所有星球构成的宇宙的命运。诗人就是这样,直指生命存在与灵魂存在等终极层面的根本问题,他常以“梦语”的方式从日常生活与个体感受中解剖出人类经验与人作为存在的终极价值,对自身、现实人生、内心矛盾与困惑以及自我存在与人类存在进行着冷峻的审视。如《心灵物语》组诗中他对生命、命运、死亡、人性、人作为存在的价值等终极性问题进行了探本溯源的思考,诗化的语言中饱蘸哲思、智性;《可能的我》、《天堂外的呓语》、《死亡之书》、《死亡练飞》等诗读来让人不能不产生震撼之感,这种震撼来自于诗人的思维方式、视野的敞开和灵感的迸发方式,这些关涉人作为生命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被诗人以精到的语言和意识流片断呈现出来,其中蕴涵的人文价值、人类经验显然是值得挖掘的重要精神资源。对此,彭燕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唐朝晖的诗“具有闪亮的人文价值的人类经验”和“哲理”,显然是精准的。
唐朝晖在梦语时空中导演的这场灵魂独舞是当下灵魂话语缺失的年代里一幕独特的风景。然而,由于这场独舞里所触及的许多沉重的话题并非浮躁年代里浮躁的心境能领略与共鸣,因而一直以来唐朝晖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或许是他一直未能引起评论家们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其厚度与重量或许尚需要时间去验证、品味、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