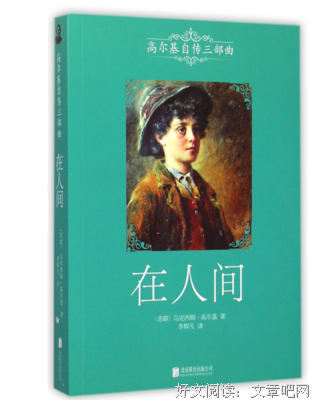《人间滋味》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4.80元,页数: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间滋味》读后感(一):愿为真诚
早在初高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片《端午的鸭蛋》,这是我爱上汪老文章的开始。上大学的时候,读《受戒》,这就是我对感情的幻想,天真,不傻,但为真诚。 读着此书,忍不住就想将自己阅读的乐趣传递给他人,《故乡的野菜》开篇讲荠菜,两样凉拌小菜,杨花萝卜和拌荠菜,写得急真,坐在桌案前,仿佛手上有筷,伸出去就能推到那宝塔形的荠菜。如此便按耐不住,指给朋友看,未几眼过便还回来,表示——读来无趣。 我反驳,此间的生活若是无趣,还有什么有趣有味。可现在回想,为什么我爱汪老的文章,写吃之人大有,但唯此处最是真诚,亲切平和,可也是太平和了,世上最纯净的感情,有些时候也要写清楚了才能为人所知,譬如《受戒》,这是普世的美好。但于散文中,总没有那么形象化,一份蔬菜至于眼前,原本就不爱吃之人,怎么能感受到其中滋味。 我是爱吃之人,“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说的至少一半是我,《豆腐》篇,从北至南至少有十来种豆腐,南豆腐、北豆腐、豆腐脑、“老豆腐”、豆花、水豆腐、干豆腐、千张、油皮、豆腐干,还有拌的、煎的、烧的、炒的、煲的,我都吃过,没吃过的,看着文章想想,似乎也品出了些滋味。故此爱读此书的原因也很明显了,读一本书便能色香味俱全,夫复何求! 热爱生活的人是不是一定热爱美食,我不知道,但总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眼耳鼻身意,佛家谓之六根,为心之外缘,若是有一根清净了,似乎也有了超脱之意。我是爱吃的,便是豆汁儿,也要捏着鼻子喝下两口,“难喝!”好歹也在回忆里烙下了深刻的味道。 写豆汁儿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观察这个世界,我的老师教我:“对于体验型的人生,任何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这是我在这里读到的,你必须真切的感受了这个世界,才能说你爱它。那个拒绝读荠菜的朋友一心向往隐居,可连两碗小米粥不就着菜都喝不下去,我说他叶公好龙,还满不服气的样子,希望他能读读汪老或者林海音,这都是我觉得极有灵性的人,他们总能抓到生命中浅淡的点,然后发出自己的光芒。 如今我们谈手作,谈匠人,很多都是隐居于城外,一心去琢磨一件事,看得多了,好像就少点什么意思,或许是因为不够了解,便觉得观之无趣。为什么文艺渐渐不是一个褒义词,就因为其中似乎空了许多内容,没血没肉,便只能是一个形容词。 汪老是不同的,他的散文就是他的人,大概说话也会是如此语气。讲到自己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沽源在塞外,是清代贬谪官员去的地方,龚自珍说:“北行不过独石口”,便是这里了。汪老在此处镇日对着土豆写生,还要画出不同品种的区别,想来总要比现今的人们寂寞多了,可寂寞到了汪老笔下好像也成了趣味——镇日“对坐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或是发现了有一种麻土豆的花,竟是唯一一种有香味的土豆花,还成了全国少有的吃过这么多种类的土豆的人,文章末尾还不忘向中国农民推广一下罗宋汤和沙拉,外界条件都是其次,此处传递的,只有真诚。 我读汪曾祺也有些时间了,也想大言不惭说自己是汪老的私淑弟子,可是仅仅沾了个皮毛,只好安慰自己,至少学到了对生活的态度。世间总不能都是平和之人,此间乐趣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若能在其他领域有一番作为,也是幸事。于我而言,已是温吞至此了,便将自己一点乐趣说出来,我这篇随笔,与汪老的用意也是相同的。 第一,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也包括我自己; 第二,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吃吃,也就吃出味儿来了。 你当然知道。我这里说的,也是与文艺创作有点关系的问题。 感谢汪老师。
《人间滋味》读后感(二):致敬是最好的评论
老海糊辣烫
老海是回民,专擅糊辣烫。我没见过他,但小时候常吃他的糊辣烫。
老海的糊辣烫算是家乡的名吃了,小城人都知道。一有心情,就说“走,喝老海糊辣烫!”老海和糊辣烫似乎成了同义词,一提到老海,就想到糊辣烫;一提到糊辣烫,也只能是老海的糊辣烫。
老海的小店开在八小隔壁,不大的门面。里面乌漆麻黑,灶台案板上一层黑垢。桌子从店门一直摆到街边,来晚了就没位置。老海的糊辣烫在家乡人气鼎盛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但常去吃,爸带着我。我一去就赶紧找座儿坐下,替爸也抢一个。
爸端的糊辣烫来了。大海碗里漂着层红油,牛油。碗里很烫,但不冒烟,让油盖住了。不明底细的舀起一勺就喝“唉哟,烫死了!”红油上撒了些长半寸许的蒜苗。油是红的,蒜苗半青半白,煞是可爱。牛油的腥膻混着蒜苗冲劲,一嗅,食欲就大开了。
舀一勺汤,轻轻吹吹,喝进嘴里,一股热流从口到胃,这一路都又辣又热,三口两口下去,额头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吃到半碗,就算在冬天,手心脚心都开始冒汗。要是夏天,更是大汗淋漓,从水里捞起一般,那叫一个痛快。据说有人感冒,就来吃老海的糊辣烫,效果比吃药强!
汤里主要是粉丝--红薯粉,豆粉。还有土豆丁,牛肉丁,黄花菜。
汤用牛羊大骨熬制,味厚汤鲜,不清汤寡水,勾了粉芡。喝嘴里,又糊,又辣,又烫,是谓糊辣烫。
同样的材料,搁别人手里,做不出这个味。人们只能乖乖地穿过半座城,来吃老海的糊辣烫。喝着糊辣烫,就着锅盔或大蒸馍,绝配!
老海的糊辣烫为什么这么好?还是有诀窍。老海备料下料时,把自己一人关厨房里,旁边不许站人。端出来的,就是一锅锅煮好的糊辣烫。
老海是个孤老,无儿无女,手艺又不外传,做了几十年,眼见得越来越老了。小城人开始担心,老海死了,再到哪儿喝这样的糊辣烫。
人总是会死了,有一天,老海死了,小店关张了。小城人再也喝不到从胃暖到心的糊辣烫了。别人也开始卖糊辣烫,生意清淡,一喝,满不是那个味儿。
曾经沧海难为水。
小学二年级,一次喝老海的糊辣烫。喝完一大碗,爸突然很吃惊地看着我“你的门牙呢?”那时正换牙,门牙松动。“门牙呢?”还能去哪儿?肯定是喝糊辣烫时脱落,顺道吞肚里了,浑然不觉!
让人忘我的老海的糊辣烫!
《人间滋味》读后感(三):人间滋味
读到炒米和焦屑一篇,对“炒米”这个东西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在网上各种搜索,也想象不到滋味,想来前几年去兴化玩的时候没能吃上实在是有点遗憾..
后来“干丝”一篇却是勾起来我对南京的记忆,可能因为和家乡同是古城初到南京竟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在南京大排档听着评弹遇到了这碗煮干丝,今日在书里再读到很是开心。
煮干丝-南京大排档
说来南京的饭菜当初是真没怎么吃习惯。我一个西北胃却吃的精细,从小在大姑家混吃混喝,姑父是上海人口味偏甜,居然养成了甜豆花吃肉粽的习惯。在南京,第一次明确的发现大油做的菜我是不爱的,大排档里的芦蒿,试了好几家的狮子头,总吃着腻味,有点可惜.. 后来问道常在南京住的朋友那边的菜是否都是大油做,答曰“是吗?没注意过。”哈哈哈。红豆圆子我是最喜欢的,冷天里热乎乎的一碗,十分满足。想来都是四五年前的事儿了。
书过一半,有几节印象深刻的。
有一,蔬菜名字前加了“胡,番,洋”的都是外来,比如胡萝卜、番茄、洋葱。
有三,“采葵持作羹”的葵是冬苋菜,类似于木耳菜。——老爹很喜欢用木耳菜烧汤。
昨天陪浩哥去电子市场买手机,路上很堵,闲来我问他蚕豆为什么叫蚕豆,他想了又想,应该是蚕吃它的豆叶吧。我说不是,是养蚕时候吃的豆。又说名字前面带胡洋番的都是外来的蔬菜,他说这个我知道,我问那胡豆是外来的吗?他答应该是吧,随后一惊,胡豆不就是蚕豆吗?我说是呀。他笑了起来,你这还是一环套一环。说说笑笑时间过得也快。
面茶一篇最有意思。
『教员生气了,骂他们是混蛋,是面茶锅里煮的球:一个是“面茶锅里煮铁球——混蛋到底带砸锅”;一个是“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
面茶,不知道正宗的是什么口味,感觉有点像家乡的油炒面,或者叫油茶。早饭的时候必要泡个油条。德富祥的油茶卖的最多,加了花生芝麻很香,家旁边市场上卖的则放杏仁我也喜欢。
最后说昆明和泰山。
去云南的时候初三毕业,刚中考完,第一次和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出去玩。三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的。汽锅鸡究竟有多好吃,大概是十几年之后的今天提起云南的美食,还能不假思索的说出这个名字。和小伙伴一路上的种种精彩历历在目,奇奇怪怪的酒店,染坊,在大巴车上看到的提着山竹的小姐姐。汪先生这本书里未提到山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流行。我去云南的时候见到好多提着山竹别走边吃的小姐姐,很好奇,从未见过。后来终于自己买了,果子如蒜瓣,吃起来不得滋味,说是有淡淡的桔子味也不具体。后来流入中原腹地又遇到不少说爱吃山竹的同学,不明所以。
泰山。爬泰山的时候我刚从华山上下来没半个月。爬华山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一行五个人,吭哧吭哧爬了一晚上。回家在床上硬是躺了三天,有朋友期间来家里找我,笑我走路像个小老太太。再爬泰山有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呼啦呼啦一口气爬到山顶,山上起了大雾,天街十米不见人影。常在山上工作的人都裹着棉棉的军大衣,我穿着短袖短裤也不觉得冷。待到下山之后再回头望,山顶已是黑云滚滚,想来已经开始下雨了吧。
读毕。文字轻快随和,初冬的西安,读来温暖。上一本有这种感觉的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我很喜欢这一本。五颗星。—2017.11.9
《人间滋味》读后感(四):民以食为天!
这本书拿在手里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一如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连纸的味道都那么好。君子之文如其人,也是淡如水,却香,香到让人无论何时看了都会觉得饿。哪怕只是他信手拈来的绿豆、苋菜,都是令人神往的美食。也许这就是心美便一切皆美,情深则万象皆深。
很惊叹汪曾祺老先生对生活有如此细致的观察,敏锐的体验。娓娓道来有一点淡,汪曾祺老先生似乎更有味道,更有力度的讲述,不是炫耀,也没有说教,凭借的是那一种对生活的浓浓的兴趣和热爱。
汪曾祺不仅能写,而且还将其写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这主要得益于他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和关注。我们说一位作家的文章好,好在什么地方?是他对生活的体验、认识深刻,是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再就是他写出了大家心里想到了,但却没有说出来的认识、道理和体会。就拿对五味的爱好来说,山西人爱吃醋,四川、湖南、湖北人爱吃辣,广东人爱吃甜,我们都知道,比如,“山西老乡爱喝醋,缴枪不缴醋葫芦”啦;火车一开入娘子关,响声就变成“喝醋”“喝醋”啦。等等。谁也没想到它们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看起来,对生活的热爱,应该包括它的方方面面,自然 “吃”也是一项重要的方面,“民以食为天”,很是有道理的。
在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中关于饮食、地方描述的一些文字,读起来很有趣味。既有人间的气息,又脱离了生活的俗气。看他的作品,文字不急不火,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他体验生活记录下感受,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回味出一种清新的生活。他是江南人,是那块土地滋养了他的性灵。那种细腻的、温和的生活艺术,多么有个性。原来艺术中个性的保留是那么的重要。
就这样渐渐的喜欢上了汪曾祺老先生写的文字,平平淡淡的,极细腻,又毫无雕琢痕迹,其实却蕴含着某些生活的小哲理。“听”他平静地说着,不会乏味,亦不激昂,算不上大气却仿佛牙雕般精致,时代的痕迹很明显,似乎一打开书就走进了一段时光,字里行间的文化气息和温馨感让我很是留恋。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位老先生打趣得紧,又会隐隐觉得他有种淡然,这种淡然,不是那种行文可以营造的淡然,而是他良好的家教和多年的博学所带来的骨子里的清雅。他又似乎很低调,有着一个大隐隐于市的文人身上的干净与清澈。他自己也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看汪老写的饮食书确实是一种享受,美食在笔下成了一种艺术品,其实都算不上美食,每一种都是极具风情的小吃,简单,而入味,让人愿意一遍一遍的读,文化的气息从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小日子的味道让人心生喜欢。 读起来甚是欢喜。
:这套汪曾祺插画集套装新购入的,很喜欢,很精致。
《人间滋味》读后感(五):汪老的美食文学
汪老是以卷袖下厨为乐的。实践出真知,故而他写吃食,往往不局限于告诉看官煎炒烹炸的步骤(若如此便与食谱无异),还要详细解释一番如此那般做的原因。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汪老传的不是菜谱,更是四方百姓的饮食之道。
天地万物皆有道,在三百六十行登峰造极的状元无一不是详熟了各行之道。要悟出这“道”来,首要的是无限热爱,肯钻研,有情怀;另一不可缺的是悟性,也就是天资——汪老在吃食上,绝对是异禀。
中学读汪老小说集,受戒、大淖记事等文还是删节版的,那时就很爱他朴实可爱的文风。今又在图书馆翻得一本将汪老写吃食的文章编集一处的书,便如遇故友。书架上还有梁实秋先生著《雅舍谈吃》,看书名便取了来,与汪同读。这一读才知文人与文人写吃食亦有不同,如见其人。
就拿写烤肉这一样来说,从汪梁各摘出两段如下:
北京的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柴,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
“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
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大火烤着,外面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足蹬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地吃肉,一边喝白酒,很有点剽悍豪霸之气。满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平常食量,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的,有的是。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
——汪曾祺《贴秋膘》
正阳楼的烤肉支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径不过二尺,放在四张八仙桌子上,都是摆在小院里,四围是四把条凳。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桌子,抬起一条腿踩在条凳上,边烤边饮边吃边说笑,这是标准的吃烤肉的架势。不像烤肉宛那样的大支子,十几条大汉在熊熊烈火周围,一面烤肉一面烤人。女客喜欢到正阳楼吃烤肉,地方比较文静一些,不愿意露天自已烤,伙计们可以烤好送进房里来。烤肉用的不是炭,不是柴,是烧过除烟的松树枝子,所以带有特殊香气。烤肉不需多少佐料,有大葱芫荽酱油就行。
——梁实秋《烤羊肉》
梁称烤肉架为“支子”,汪称“炙子”,大概是民间口耳相传,没有一定之规。汪老的特色就在于那一番对“炙子”工作原理的解释——短短几句,就点出那燃烧的果木、炙子铁格、烤肉、汤卤之间相辅相成,让看客有如醍醐灌顶。我想这是汪老要告诉我们的:如此平凡普通的烤肉架子中,是不平凡的中国饮食智慧。
梁先生说那烤肉的佐料,不过“大葱芫荽酱油”而已,芫荽就是通常说的香菜。(梁先生是大翻译家,用一生独立完成莎翁全作的翻译,对蔬菜的名称习惯偏西洋化并不难理解。)汪老写的则好像是把祖传秘方给抖了出来:“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香菜就香菜吧,一定得给你强调多放;掺一点水,得多灵的舌头能尝出来?所以我推测,一碟佐料都能写得如此详尽,要么是下厨去亲眼观察,要么是与那调制佐料的堂倌聊闲天听得的——无论哪种,汪老做得,且常做,其他文人则鲜有能为之——文化人下馆子,上桌雅厅,满座高朋,谁去有空搭理店小二做了些什么!
汪老在《咸菜和文化》文末写道:“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能出此言则无怪他汪老对吃食探寻记录之用心至极。
读汪老写吃食,如听祖父传授本家名菜。
汪老写扬州菜一道干丝的做法:“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置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这般处理辅料的细节烂熟于胸,不是“老饕”,谁能照料得到?
讲凉拌黄瓜皮:“……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这还只是汪老笔下的一道小凉菜。
梁先生是不爱亲自烤肉的,“一面烤肉一面烤人”,言语间透着些不屑同列,梁等文化人常去的正阳楼,也是“比较文静”,可以享受优质服务的场所。然而汪老似乎没怎么去过那里——他说北京城最好的三家烤肉是烤肉宛、烤肉季、烤肉李。像汪曾祺先生这样的老饕,是不太会委曲求全的。
《人间滋味》读后感(六):“北京人炒萝卜条,则为南方人所不喜”
几年书看下来,我还从未给一本书写过一篇书评。小时候写的那些读后感,对我来说也都不能算什么正儿八经的“读后感”,无非是总结全文,提炼中心思想,随意附和歌颂一番,最后再绞尽脑汁结个尾。连自己的“感”都没有体会出来,怎么叫“读后感”呢?
汪曾祺的这本《人间滋味》,我是有读后感的。面对文学大家的书,我这篇连书评都不敢称,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自己读后有感而发。说是有感而发,不如说是二十几年菜吃下来,就着这本书消化了一下,才吃出菜的味道来。
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只是在书店经过它,上面画着我爱的大闸蟹,一看又是汪曾祺写的,就忍不住买的。以为汪曾祺写的是一篇篇根据他钟爱的美食写的回忆或者故事,结果发现他写的不仅仅是关于那些和食物有关的回忆,还从食材本身出发,谈论了地理人文,和一些社会形态。
书里提到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北方人对待某种食材如何,而南方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会在文章里重复提到这种现象,也不奇怪,毕竟南北口条不一,这两年也三番五次地成为了最具话题性的段子。无论是豆腐脑该是咸的还是甜的,月饼里到底该不该放肉,元宵节吃的是汤圆还是元宵,番茄炒蛋要不要加糖……一旦和食物扯上关系,南北网民就能马上拉下脸来互相据理力争,仿佛自己吃的那种才是最正宗的,而别人吃过的都是山寨货。
我之前写了一篇关于肯德基的乡愁情节的文章,下面有人问我:难道你不想馒头吗?难道你不想面食吗?我真想回复他:我是南方人。
在汪曾祺对于这些分别具有南北特征的食材的描写里,他就像一个正襟危坐的法官,细细写着北方人的传统做法,而南方人又因为什么而避而远之的。比如大家最爱争辩的豆腐,他写“北方人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这是侉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北豆腐、松花蛋切成小筛子块,同拌、无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而已。好吃吗?” 写得又生动又有趣,把北方人的重口和南方人的清淡这么一对比,好像在让两方横眉竖眼的人照了照镜子,让大家都站在对方的角度领教了一下口味。
他还提到了南方人常食薤,有个北方的食品商场批发了薤来卖,只有南方人趋之若鹜,北方人却只是不信任地看看就走了;他有一次特地买了一些薤给北方同志吃,他们吃了一口却说,不好吃!这哪有糖蒜好吃!
看到这里,我不禁心想:我们南方人还不爱吃糖蒜呢!
结果汪曾祺马上另起一段写道:哀哉!人之成见之难于动摇也!
留学两年,这种情节我倒是真的处处体会得到。且不说南北同学的差异,关于做菜放不放糖的趣事我就能说上三天三夜;虽然说西方人较为海纳百川,很多新鲜事物接受程度较高,但面对食物,他们却很难走出味蕾的舒适圈:每次我从中国街回到学校,都会带点零食给我的意大利组员吃。有一次带了麻薯,意大利人拿在手里,担心地看了看,又捏了捏,我期待地在边上说:你吃吃看!他们犹豫地说:我先拍张照片。然后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有的人大呼好吃,对于这种谜一般的食物爱不释手;有的人咬了一小口就皱紧了眉头,放在一边再也没动过。
其实这也很正常,中国食物之于西方人,正如奶酪生肉之于中国人一样。即便是汪曾祺,在书里谈到“起司”,都形容为“一股酸臭味”,而芝士真正在中国市场流行,也才这两年的事,而且也仅限于年轻人的圈子里。
有一次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吃火锅,我朋友带着她的意大利男朋友,为了找点话聊聊,他舀起一块百叶结,问我们这是什么。百叶结没什么英文的专用名词,我们就统一回答:豆腐,就糊弄过去了;结果他又舀起一块豆腐皮,我们说这也是豆腐;好死不死,他第三次舀起来的又是一个豆腐泡,我们犹犹豫豫,最后还是告诉他“这也是豆腐”,大家都笑起来。最后,看得出这位这意大利人实在是接受不了中国的火锅,闷头只吃火锅里的年糕,这可能是唯一一种和意大利食物最相似的食材,嘴里还是违心地说“好吃、好吃”。
此外,整本书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许多字我竟然都不认识。包括上文所说的“薤”,我也是百度查了以后才打出来的,还有许多植物、鱼类的学名,我既不认识,又别说知道怎么读了,有些食材只能通过做法才能猜测它大概是什么。此外,由于在出国前,我从来没有进过菜市场,每次我妈宣布家里要吃什么菜,大多是用家乡话告诉我,或者用“家乡式普通话”告诉我的菜名,很有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普通话应该怎么念。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鳜鱼,我一直不知道汪曾祺说的是哪种鱼,知道他说鳜鱼可以做成松鼠鱼,我才明白:哦,他说的是桂鱼。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么多我不认识的字和食材里面,确实有许多他写到的美食,我从小都没有吃过。且不论那些北方专利的美食,就连那个南方人爱吃的“薤”,我更是从小都没听说过。我认知里的那些中国美食,都是我在自家厨房里,外头酒店里吃到的,那么汪曾祺书里那些我不曾听闻过的食物,它们到底还在饭店的菜谱上吗?
我有时候看一些讲述中国美食的纪录片,尤其是上海美食的,讲到那些老克勒爱吃的上海菜,现在年轻人却吃的越来越少,恐怕会失传的菜,我就隐隐地担忧。以前我妈妈单位马路对面是宋庆龄幼儿园,幼儿园深处有一家本帮菜馆,妈妈经常带我去吃那里的“红烧划水”,也就是一盘鱼尾巴,我特别喜欢吃。直到现在,我吃鱼都喜欢先从尾巴吃起。那家餐厅很早就已经关了,除了一些老牌的本帮菜馆,我很少在新的餐厅里再看到这道菜。
如果说在本地有些菜都逐渐失传,那到了海外的那些中国城,中国菜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了。我很怀疑,有些从小就出生在海外的侨民,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家乡菜是什么味道的吗?要谈起海外的那些中餐馆,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只能叹气,那些馆子,只要做得能像家乡菜馆里的菜三分之一像,就能拍手叫绝了,怎么还能要求让他们做出来味道一样呢?
即便是自己做,也难免会加上个人的嗜好。我挑食,葱姜蒜绿叶菜一样都不喜欢,能把祖国美食传承过来的菜,也就只有我自己爱吃的那么几道,这样一来,今后我的后代能吃上的祖国美食就更少了。
我害怕的是,中华美食传递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再捧起这本书的时候,一大半的食物都不认识了。
所以说,南之鹅肝,北之熊掌,最好是什么都要尝一尝,什么都要试着去接受。我最佩服汪曾祺的就是,我明知他是高邮人,通篇文章看完,却不知道他到底算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偏袒的菜系,什么食物都能侃侃而谈,就连他自认不擅长喝的茶,他都能写个两三篇文章出来,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想即便是放在所谓不那么固步自封的年轻人身上,我们也很难像汪曾祺那样去接受那么多元的事物。
《人间滋味》读后感(七):文坛小厨·汪曾祺 ‖ 有毛不吃掸子,有腿不吃凳子
01
汪曾祺在文坛上绝对是个奇人,年轻的人知道他或许都是因为《端午的鸭蛋》,吱一声,蛋黄就流出来的,于是知道了高邮有咸鸭蛋这样的好物。
别人看京剧,都是嬉笑人物,评论情节,或指摘一些服装、场景之类,他看《金玉奴》倒好,竟然惦记起了豆汁。
02
他有篇散文就叫《豆汁儿》,就说一北京老友带他去吃饭,问他敢不敢吃豆汁。
于是他立刻放言: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凳子,大荤的不吃死人,小荤的不吃苍蝇”的人。想必他这句也是从哪里的俗语摘取过来的,但是却别有一番文化人俏皮的味道。
03
汪曾祺也是个作家,像《受戒》、《沙家浜》这些,要是从事现当代研究,绝对逃不了他。但是从他的生活趣味来说,他还是更喜欢做菜、吃菜,这样说倒是像个广东人。不过在散文中他经常喜欢提到的就是某位作家特地来找他,然后点名让他做菜吃。
在一篇叫《干丝》的散文中,他用结尾一整段来写作家聂华苓和外国丈夫跑来北京要在他家蹭饭吃的事情,文中他还颇为得意地写道:
“几个什么菜,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大碗煮干丝。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想必“淋漓尽致”这四个字已足够可以展现汪曾祺的自豪之情了,没想到汪曾祺还继续说,自己因为知道聂华苓是湖北人,但是又常在国外,所以吃不到正宗的淮扬菜,自己做了煮干丝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汪曾祺这里仿佛是一个正在接受美食专栏采访的厨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04
汪曾祺是江苏人,所以对于河鲜是情有独钟的。
他有篇文章叫做《鳜鱼》,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是鳜鱼,于是他解释说,鳜鱼就是鯚花鱼,这下我就一下子明白了,小时候在小姑婆家,小姑婆经常给我做葱油扁鱼吃,但是扁鱼除了肚子和背脊外围一段没有小刺,其他都芒骨。唯有鯚花鱼,那时基本上只有大刺,因此吃起来特别痛快,所以后来就喜欢上了葱油鯚花鱼。
汪曾祺也说了,“鳜鱼是非常好吃的。鱼里头,最好吃的我以为是鳜鱼”,“鳜鱼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清蒸、干烧、糖醋、做松鼠鱼,皆妙。”
所谓的松鼠鱼,就是鯚花鱼身上鱼肉割成花瓣状,裹粉放入油锅炸嫩,捞出再浇上番茄酱,撒上松子,一般酒宴上常常会上这道菜。所谓松鼠桂鱼,桂花鱼就是鳜鱼的另称。
05
汪曾祺论美食的时候,也不会忘了肉。
他有篇文章就叫《肉食者不鄙》就是来为肉食者正名的,而且里面一提起杭州就是东坡肉,古代说东坡肉就是白猪肉放酱油煮,一下子看不出门道,其实东坡肉还是很有讲究,汪曾祺文中说:
“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但是功夫全在火候。先用猛火攻,大滚几开,即加作料,用微火慢炖,汤汁略起小泡即可。东坡论煮肉法,云须忌水,不得已时可以浓茶烈酒代之。完全不加水是不行的,要加酒。”
这算是道出了东坡肉的真谛。我虽然不喜欢吃肉,但是如东坡肉这般,我爱吃瘦肉部分,因为东坡肉都是在大锅里煮久了的,是天天煮,时时煮,而且加酒加作料,极甜。要吃得提前做好才行,不是到了餐馆想吃就能吃的,还得问有没有。吃的时候按块来卖,筷子一碰那已经被酱汁染红的瘦肉部分,那肉就能掉下来,就连那甜甜的酱汁都能和着一碗白饭吃下去。
06
汪曾祺最有趣的还是在他讲自己画马铃薯的时候,当时他自嘲被派去沽源画马铃薯图谱,感觉是被流放军台,他被远离家人,文中也直言谈心的人很少,只能天天对着马铃薯,大的小的,好吃的,难吃的。先是搜集品种,然后一个个拿来画,文中说:
“画完一个薯块,我就把它放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
他被外派到那么荒凉的地方画马铃薯都能那么开心,吃马铃薯还吃出了花样,述说马铃薯品种的样子如数家珍,最后离开还要带些薯块回去,可见是个实在的美食者。
《人间滋味》读后感(八):无穷滋味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经历一次手术,对我人生有冲击的一次手术,也让我对健康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这种时候看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让自己回忆起童年,了解人间滋味,对美好生活无限渴望。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关于饮食、地方描述的一些文字,读起来很有趣味。既有人间的气息,又脱离了生活的俗气。看他的作品,文字不急不火,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乐趣。他体验生活记录下感受,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回味出一种清新的生活。他是江南人,是那块土地滋养了他的性灵。那种细腻的、温和的生活艺术,多么有个性。原来艺术中个性的保留是那么的重要。在他的笔下,一根不起眼的荠菜都能让人无限回味。且不说滋味如何,会让你无限遐想。
饮食书确实是一种享受,美食在笔下成了一种艺术品,其实都算不上美食,每一种都是极具风情的小吃,简单而入味,让人愿意一遍一遍地读,文化的气息从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小日子的味道让人心生喜欢。 读起来甚是欢喜。
爱吃,不是狼吞虎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吃进肚里等于没吃。爱吃,我觉得吃还得吃得用心,吃得幸福快乐。这个总结很精彩。爱吃,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人活着,就要活得有滋有味、兴高采烈的。
最后的总结是,自己的学问不够呀,整本书,好像是生僻字大全,我都不认识。并且有许多食物追根溯源的名字,古时候的名称,不禁佩服中国人这"吃"里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可见"吃"绝对不是只吃这么简单,用心起来里面要下功夫的可地方多着呢。
总之是看完之后,我又更热爱生活了。
《人间滋味》读后感(九):吃遍八方美食 品尝人生百味
汪曾祺老先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自诩为“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这是何等的境界。如果没有过往岁月的难忘经历,如果没有对各地美食的留恋,恐怕难以形成这些精妙的美文。
汪老先生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画面感很强,每每描述一种吃食,就像是在你面前展示制作工艺一般,令人垂涎欲滴,忍不住想要品尝。全书文章通透自然,引用了较多的历史典故,针对多种食材介绍了各地的不同做法。既有南北方不同习俗的对比研究,更有作者的主观品评。在此基础上,汪老还谈了亲身体会和见闻,并结合美食美味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尤其是大量引用了历代文人墨客对美食的记载和评述。或是诗文,或是典故,无不为八方美食平添了几分历史厚重感。如《故乡的食物》一文,就引用了“资深美食家”袁枚所作《随园食单》中关于高邮咸蛋的记载,颇有趣味。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也使汪老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无论是华夏中原还是塞外边疆,无论走到哪里,汪老都会遍访当地美食。这期间,当然也有很多趣闻。据说,汪老为了寻找地道的“臭豆腐”,曾经领着几个老头,闻着臭味,直到靠近一家公共厕所……由此可见汪老对美食美味的热衷和推崇。手把肉、豆腐、野菜、鱼等等这些美食都在本书中有大量篇幅的描述。原料的取材尽管异常简单,但是做法却是异常讲究。比如高邮咸蛋和内蒙手把肉。高邮咸蛋的蛋黄里面有红油溢出,这可比平日所见到的干瘪的鸭蛋诱人太多;内蒙手把肉用白水煮开后,蘸了料吃,真是鲜嫩无比,大快朵颐。这也应了“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酣畅舒爽之气。羊肉腥膻与否都不会影响到肉的口感,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饮食习惯。
本书特别注重介绍各地不同的饮食习惯。比如《豆腐》一文,就介绍了南北豆腐的多种做法和历史渊源。拌、烧、炒、炖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可以使用在豆腐上,这也映衬了豆腐具有无味调和、海纳百川的天然优势。
《人间滋味》读后感(十):做一个有文化的吃货
一起买了汪曾祺的三本书:《人间草木》、《人间滋味》、《人间有戏》,可以视为汪曾祺的“生活三部曲”了。《人间滋味》一书多数内容是与吃有关的,看着像是作者在不同时期所写散文的合集,所以有较多内容在书中多次提起。总体感觉,汪老的语言很朴实、生活化。因作者的家乡就在江苏高邮,所以书中所写的一些物产、风俗都较为相似,而且多次苏州的传统食物,感到非常亲切。不过,有些传统的美食如今已不复存在,或者已换了另一种说法,还需做一番查阅考证,才能发现如今尚存的传统风物。
也许汪老在昆明居住的时间不短,书中对昆明的食物介绍得不少,可以为去昆明找美食的吃货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线索,不失为一本昆明美食的参考书了。
谈到美食文化,内涵就落在文化二字上,因此所谈的不仅是美食,更有各地的物产、历史、环境、风土人情,这方面在书中也有了较好的体现,汪老还旁征博引一些历史典故,可见对饮食、对文化理解的深度,是一本有深度的文化生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