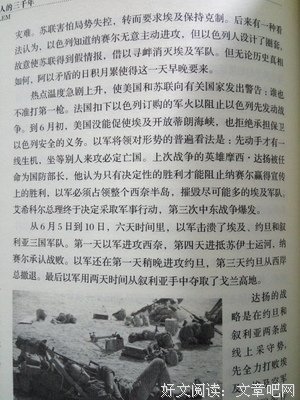《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是一本由[美] 阿迪娜·霍夫曼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一):圣城耶路撒冷的建设者们
对于圣城耶路撒冷的历史,之前了解的内容并不是很多,不过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曾先后是这块土地的主人,都将耶路撒冷视为自己的宗教胜地,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具有更为坚实的感情和宗教力量。
对此书细细阅读,通过作者的描述,让读者从建筑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了这座美丽的城市。19世纪前,这块土地归属奥斯曼帝国管辖,随着帝国的解体,以及第一次世界战争的爆发,该地归英国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联合国同意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英国托管结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束,耶路撒冷遗留下大量的城市废墟,许多倒塌的房屋等待修建。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不断涌入,如何建设这座城市成为英国托管时期管理者及其重要的工作。首任英国总督斯托斯,极力想建设好这座城市,规定:“城里所有的建筑都必须使用耶路撒冷当地的白色石材,要有统一的建造规范。”这项法令至今仍影响着这儿的人们,自然现在的人们也应该感谢总督斯托斯,否则托管时期的城市建造积有可能显得杂乱无章。
为了建设美丽的耶路撒冷,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纷纷云集到这里,为城市绘制出合理的城市规划,有门德尔松,有哈里森,有霍利斯,有阿什比,有里士满等等众多的建筑师,也有为建筑添砖加瓦的欧迪安。作为女作者为了写好此书,遍访耶路撒冷各地,读者可以从作者对霍利斯遗存着很少的资料中,窥探到调查过程及其困难。
对于门德尔松,拥有犹太人的血脉,傲慢嚣张的著名建筑师,其在德国建有不少著名的建筑。对于建筑设计,他的设计不仅仅只有建筑物本身,还包含其他的各个方面,如建筑绘图、材料选用、庭院设计等等。当在德国给其妻子修建豪华的别墅时,其妻子的穿着打扮也都由门德尔松亲自设计。
虽说战争的临近,德国和英国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而在巴勒斯坦却显得极度的平和之中。这让门德尔松有机会去认真思考,去仔细规划即将建造的、适合巴勒斯坦当地风情的城市建筑。在德国,门德尔松曾经拥有极高的名声,然而当来到巴勒斯坦,他的建筑风格还是收到来自巴勒斯坦、美国等地各类人士的批评,即便是建筑项目获批,在资金上有时也得不到出资方的全力支持。
随着巴勒斯坦几个主要建筑修建完毕,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让门德尔松极度失望。再加上战争风暴日益临近,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众多因素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家乡耶路撒冷前往美国。即便是在美国,还是想随时收到来自巴勒斯坦相关人士的召唤,最终在旧金山遗憾地离开人间。
提到奥斯汀·哈里森,巴勒斯坦政府大楼的设计者,可是此人显得低调。在巴勒斯坦修建建筑之前,基本没有多少重要的建筑问世。当来到巴勒斯坦,时任总督却极度信任他。其众多建筑中,最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却是巴勒斯坦博物馆。
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
耶路撒冷城市土地之下,是多个古老年代的堆积物而成,有些像国内考古地层有多个地层带堆积而成。博物馆于1930年6月19日奠基,施工中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坟墓以及许多希腊化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陶器、钱币和首饰。看到此不由得暗想,如果现在再来修建这座博物馆,会不会用玻璃将地层隔离开来,以便让参观者可以从上层看到古老年代遗留的痕迹。
当时博物馆的建设区域内,有一棵神圣的大树,哈里森在建筑规划时有意以其为中轴线。当几十年之后大树死去,整个建筑还能保留对它的依恋。里面曾藏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不过现在由于其所处地地理位置,在东西耶路撒冷分界线之上,导致参观者稀少,门庭冷落。
由这些建筑师先后在英国托管时期打造的建筑,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迈入到老建筑的行列中,不过也正可以通过它们,了解那段特殊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城市文化。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二):《在精神故里重建家园》
——读《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
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哪座城市会像耶路撒冷一样因自己的历史而自豪,同时,也没有哪座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为自己的历史所拖累。耶路撒冷的每一层尘土都是历史的遗迹,这座城市就建立在“18米、24米甚至30米深的废墟之上”。而当我们提起“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由此而生的复杂情感也会像那些现存的或毁弃的建筑一样,在虔诚的夙愿中变成圣殿或尘土。
“未读”的新书《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通过讲述一战后英国托管时期三位建筑师参与耶路撒冷新城建设的经历,为我们重新考量这座城市的精神脉络提供了建筑意义的新视角。
这本书的前言标题《雅法门的那一边》不知是不是有意借鉴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标题形式,总之,这样一个标题无疑会将读者迅速的带入到一个不太久远却也可望不可即的旧岁月的缱绻之中。
一百年前的新城建造史,是耶路撒冷几千年历史更迭的一种现代版讲述,它所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角力并没有多少新意,正如这个城市被不同势力反复占领与收复多达44次一样,这样的建设也只是某个古老故事的又一次重述而已。
建筑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实物承载,其客观性相对的存在于时间之外。因此,每一栋建筑都有其使用功能之外的特殊意义,不论是私人宅邸还是公共设施,都必然的含有建造者关于“永恒”的野心。而在耶路撒冷这种野心尤为显著,在这个争议之地从来不存在纯粹的建筑。每一个统治者都对“圣地”抱有十足的野心,而建筑是这野心最有力的书写。而作为耶路撒冷的建筑师,如何更好的周旋于“政治符号、现实状况和意识形态”,如何搭建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实现多元文化的和平构想,可能是专业学术之外的又一种不可或缺的建筑礼节。
建筑师是城市的刀笔吏。历史的写就往往充满着斗争和妥协,建筑作为历史的物质标识当然也在其中。正如每一次权力的交接都伴随着斗争,有责任的建筑师都将面对相同的困局,那就是照顾原生文化与大众审美的矛盾,这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的简单考量,而是审美的更新与继承。在民族争斗敏感时期的耶路撒冷,所有建筑都是阿克萨清真寺与所罗门圣殿之间的较量。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风口,三位身份不同的建筑师——德国犹太人门德尔松、英国托管政府职员哈里森、阿拉伯人霍利斯,都在这个争议之地上重塑着自己的身份,并渴望通过建筑,在怀念与憧憬、丑陋与荣耀、遗忘与新生、眷顾与雄心的相互交错中重新塑造人们对信仰的虔敬和展望。
正如建筑师阿什比所说,“这座城,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而先于一切的,它是一座理想主义者的城市,此外,它更是理想主义者在此后世世代代里将他们自己与城市一同撕碎并糅合的一座城市。”建筑作为时间之河的醒目航标,不论其是否会如苏格拉底所说的“美物难存”,它们都是城市历史的骨骼。而作为“纪念性的建筑和毁灭性的浩劫紧密相连”的耶路撒冷,它的建设还远未完成……
2018.2.1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三):是谁缔造了今天的耶路撒冷?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
没见过耶路撒冷之辉煌的人
终其一生也见不到一个合意的城市
没见过圣殿全貌的人
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一座辉煌的建筑”
——《塔木德》
诚如诗歌所言,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座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充满争议,又像耶路撒冷一样充满魅力。近日,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座应许之地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耶路撒冷”本意为和平,但这座和平之都时常处于战乱、炮火、动荡之中,然而正是因为饱受争议,缔造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
数千年硝烟散去,那些耸立的建筑群定格了如今耶路撒冷的面貌。
圆顶清真寺( The Dome of the Rock )伊斯兰教圣地,它闪闪发光的金顶一直是耶路撒冷最著名标志之一。穆斯林相信圆顶清真寺中间的岩石就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和天使加百列一起,到天堂见到真主的地方。
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犹太民族的第一所大学,同时也是犹太民族在其祖先发源地获得文化复兴的象征,始创于1918年,落成于1925年,这是以色列最高学府,被称为“中东的哈佛”。
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馆(Rockefeller Archaeological Museum)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博物馆。它兼具东方和西方色彩,收纳了与迦南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等诸多族群相关的文物,其呈现的历史画卷是多声音和多彩的。
当然还有肖肯花园、巴勒斯坦银行、中心邮局、哭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这些经手历史的洗涤、各具特色的建筑汇集成我们共同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些建筑是谁缔造的呢?还会有人记得他们吗?是什么让他们构思出这些楼宇和城里其他伟大的建筑呢?又有什么是站在21世纪的耶路撒冷的城市里看不见的呢?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阿迪娜·霍夫曼在寻找,她也想让更多人去寻找。她创作的《直到我们建立了耶路撒冷》是一部与圣城建筑、建筑师密切相关的书。其简体中文版由「未读」旗下社科品牌「思想家」出版发行,由中国著名建筑师唐克扬博士等翻译。
是谁记得耶路撒冷的建筑师们?
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而言,阿迪娜·霍夫曼的名字是陌生的,但对中东地区的人们而言,她却是亲近的。虽然阿迪娜·霍夫曼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目前是卫理公会大学和美国明德学院客座教授,但25岁时她就移居耶路撒冷,从此开启了25年的当地生活。
作者:阿迪娜·霍夫曼阿迪娜·霍夫曼的写作题材一向关注中东地区和犹太人的历史文化。2010年凭借《我的幸福与幸福无关:一个诗人在巴勒斯坦的世纪生活》获得英国温盖特小说奖;2012年,与丈夫彼得·科尔(著名诗人、翻译家)合著的《神圣残片:开罗犹太手稿的失而复得》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优秀犹太文学奖;2013年获得美国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
在耶路撒冷生活着的这近四分之一世纪里,阿迪娜·霍夫曼每天都会路过耶路撒冷城市西侧的主干道——雅法路,在距离雅法路的一头大约90米远的地方,她还会路过圣城中最具表现力也最精致的公共建筑之一——巴勒斯坦银行,毗邻银行旧址的是这座城市的中心邮局,它比前者更宏大,更对称。然而,并非所有的建筑都像是这两座显赫的建筑那样被层层看守,在这些高耸的建筑物背后,还有破落的公寓和教堂,在锡安广场的破旧中心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建筑群。
这些建筑群出现在同一片视野中,大多数人看后都会感叹,但阿迪娜·霍夫曼不只是叹为观止,女性的细腻和作家的敏感促使她产生了更多的想象。当她回溯耶路撒冷的历史时,发现这座城市在经年累月地变迁,城市中的建筑也在不断地演变,多达40余次的占领与更迭,一次次埋葬了这座城市,又一次次重现擦亮历史的眼眸。阿迪娜·霍夫曼沿着耶路撒冷的街道向下挖,找到了三位背景迥异的建筑师,而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汇集成《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
这三位非比寻常的建筑师究竟是何许人也?
耶路撒冷以其巨大的包容和关怀,向世人呈现出上帝赐予的多样、复杂的城市面貌。也源于耶路撒冷的召唤,一波波建筑师涌入圣城,直到他们建起了耶路撒冷。本书拾起了三位文化背景迥异的建筑师的记忆,他们分别是埃里希·门德尔松、奥斯汀·哈里森、斯派罗·霍利斯。
埃里希·门德尔松埃里希·门德尔松是一位天才级德国建筑师,以设计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作爱因斯坦天文台著称。现实中他是一个怪老头,傲慢、缺乏耐心、蔑视他人、尖酸刻薄,戴着厚厚的眼镜,用一只眼打量着犹太同胞荒废了的圣城。由于没有任何明确远见的领导,耶路撒冷的建筑四处涌现,毫无美感,门德尔松深深谴责这种短视的做法。自诩为“以色列真正的后裔”的他,似乎是感受到耶路撒冷的召唤,从德国来到这座百废待兴的城市,企图规划一座城。然而构建这座城市的计划并没有门德尔松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愈加严峻的大环境、超前理念的不被理解、犹太身份的尴尬与动荡、与客户首肯的合作与决裂、英国关于巴勒斯坦政治地位的决策与暴乱……凡此种种,分解了他规划一座城市的设想。在艰难时刻,门德尔松秉承“自然的秩序”,在耶路撒冷留下了肖肯花园、巴勒斯坦银行、希伯来大学等建筑瑰宝。最终战争爆发了,门德尔松离开了他们渴望的——曾被他们称作心灵归宿的地方,等待着被耶路撒冷召唤,可惜病魔再一次扑向了他,这一次,他失去的不只是眼睛,他在异乡失去了生命。
奥斯汀·哈里森奥斯汀·哈里森是个充满戏剧性的建筑师。他年纪轻轻,却是一位经历了数次战争、厌倦打仗的老兵;他是一位本质上爱好和平的人,却始终与和平无缘;他年轻时就逃离了英国,并没有想过要回去,却把女作家简·奥斯汀认作先祖,且骨子里拥有不可撼动的英国特质;他特立独行追求自由,却是英国托管政府的首席建筑师,必须接受体制的约束。看上去,命运似乎总是和他开玩笑,但哈里森经受住各种戏剧化的颠覆,在建筑事业中,他表现得格外睿智与沉稳。他拥有深厚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建筑知识,热爱传统建筑元素,于是在建筑英国托管政府的中心邮局时,将其设计成外观正统,内在吸收许多传统元素——从叙利亚风格的深浅穿插条纹的石匠工艺,到巨大木质双扇门的几何装饰镶板;他在暴力频发的空气中工作,伴随着特有的耐心与决心,回应着层出不穷的财务问题,最终缔造了伟大的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馆。而在建筑完工之时,热爱和平的哈里森悄悄地从即将战乱的耶路撒冷离开了。
埃里希·门德尔松是犹太企业家雇用的顶尖德国建筑师,奥斯汀·哈里森是英国巴勒斯坦工程局的官方建筑师,相比之下,斯派罗·霍利斯似乎并不知名。实际上,霍利斯不仅没有名头,甚至名字也是个悬案,他就像是漂浮在耶路撒冷空气中的幽灵,直到阿迪娜·霍夫曼去寻找他。霍夫曼通过几处建筑上的署名开始找寻这个被历史遗忘的建筑师,逐渐找到两张模糊的照片,继而是相似的姓氏、一堆法律文件,从而勾勒出他曾经的生活情景。而在这寻找的过程中,和神秘的霍利斯一样,出现了一群与建筑有关的人物。在沉默一个世纪后,关于霍利斯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而本书《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本叙述建筑师斯派罗·霍利斯的书籍。
耶路撒冷三千年后,他们又经历了什么?
提到耶路撒冷,我们会想到什么?
或许是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历史,亦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动荡和恐慌。细数近年来耶路撒冷的书单,从《耶路撒冷三千年》始,国内出版业开始了更多对于圣城的探索,写不完的应许之地却在文本中出现了一个悖论——似乎鲜少有人将眼光投向本世纪两次大战期间。
意为和平之都的耶路撒冷,数千年来持续被战乱、争议包裹,我们却忘记了她和平的面目,错以为“乱”才是她的本色。然而,这座城市包容着一切,也悲伤地厌倦着一切。《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正是起于三千年的辉煌历史后,止于二战后四分五裂的巴以冲突。其背景是在一战后、二战前欧洲与中东的大环境,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看似动乱,整个世界徘徊在战争的边缘,但耶路撒冷开启了一段平和惬意的时期。
20世纪20年代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门前的英国士兵本书通过现存的建筑,找寻上个世纪建筑师们的记忆,同时也向众人呈现,在这段鲜少被人提及的历史中,那些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们都经历了什么。
埃里希·门德尔松来到耶路撒冷,并不是为了结交什么朋友,但他却无意间结交了很多朋友。他和妻子露易丝热爱生活,对人友善,追寻耶路撒冷的本土风格,宁愿住进一座古老的风车磨坊,也不愿住进新建的公寓里。正是在那座古老的风车下,他开始建设这个国家,同时也建设他自己。 奥斯汀·哈里森看似内向,但始终忠诚于他的朋友们,他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热爱和平之心,将多民族、反战的因素融入建筑中。斯派罗·霍利斯不可捕捉,但我们拾起更多平凡人的往事,那些无名的建筑师神奇地修复了赫赫有名的圆顶清真寺,霍利斯的岳父家族待人真诚、医者善心……背景迥异的他们,传达出相同的渴望——追求完美与热爱和平。《直到他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不只是建筑师们用建筑记载这座城市的故事,众生也在用生命记录着“耶路撒冷”的渴望。现在的耶路撒冷局势,能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共同的渴望始终不变。
这是一本无法被归类的书
回到书籍本身,《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是一本无法被归类的书。
若说是建筑史,并不准确。相比厚重的、冗长的史学专著,它显得短小精悍,截取片断回望整段历史。本书描写了“一战”后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重建过程中,三位不同背景的建筑师参与建造耶路撒冷新城的往事。其中,既有知名的天才级别犹太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英国托管政府的首席建筑师奥斯汀·哈里森,也有不为人知神秘的幽灵般的存在阿拉伯建筑师斯派罗·霍利斯,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建筑背后的故事。在文本推进中,故事是主线,宏大的历史成为这些主人翁的背景,处处显人情。
若说是人物传记,也不尽然。作者采用移步换景、历史回溯的写法,重点刻画了三位建筑师的往事,但在主人翁的背后,还有众多建筑遗迹和人物群像。雅法路、金顶清真寺、希伯来大学,大卫王酒店、洛克菲勒博物馆……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桩桩建筑历经沧桑得以保留;门德尔松、扎尔曼·肖肯、哈依姆·魏茨曼、爱因斯坦、马丁·布伯、汉娜·阿伦特、梅尔维尔、弗吉尼亚·伍尔芙……还有无数不知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群,一件件小事串联出睿智的犹太过往。著名建筑或不知名私人宅邸,被仰望的或被遗忘的人们,都出现在同一个文本中。
耶路撒冷的无法被定义,或许注定会制造出一本无法被定义的建筑书。耶路撒冷以其巨大的包容塑造着众人,不可计数的百姓也以赤诚的爱缔造了耶路撒冷。历史在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正如阿迪娜·霍夫曼所憧憬的那样,以坚实的表土层开篇,一路向下考古挖掘,旨在追寻旧日的三座耶路撒冷城市,拾起这些鲜少被人记起的人物记忆。
是谁缔造了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建筑师,也是每一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民。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四):一座迷人的圣城,一本书和它的缔造者
刚拿到《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首先就被封面上的这群人吸引了,他们是谁?耶路撒冷的建造者吗,一群工人、建筑商?如果是,他们为何面带笑容?耶路撒冷这座城是如何被建起来的?
在此之前,我对耶路撒冷的了解,仅限于一座位于死海沿岸的圣城,几大宗教的发源地,无数的古老建筑,虔诚犹太人站在哭墙下沉默祈祷,还有三千年辉煌的历史和而今媒体上硝烟缭绕的报道。同样陌生的,还有这位作者——美国犹太裔作家Adina Hoffman,此前未在中文世界出版过任何作品。据维基介绍,她是著名翻译家、诗人彼得·科尔的妻子,从1992年,也就是25岁时便从美国搬到耶路撒冷,一住就是25年,她热爱中东文化,专注于犹太历史写作,曾出版过在犹太文化圈影响很大的获奖著作《神圣残片:开罗犹太手稿的失而复得》,获得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的赞誉。可我依然不知道她是谁。
在无雪的帝都北京,我带着满脑子的问号翻开书,也被卷入了时间的漩涡......
“雅法路,从雅法门延伸开来,起初只是一条朝圣与骆驼之路,从旧城雅法门的附近延伸开,横过新城,向西蜿蜒穿过山丘和干涸的河谷,又通过一片平地,最终到达雅法港,它甚至一度从港口延伸出去......这条路让耶路撒冷向世界敞开,又将世界带向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历史便由此开始——”
接着我才知道,她要讲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一战后、二战前属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而非后来成立的以色列。
作者说,她每天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着路边的历史建筑,总是带着一种沉思,沉思这座伟大之城许多未曾实现的憧憬和蓝图。这些百年前的建筑,饱经风霜而伫立,见证着其他建筑和人群的来来往往,它们脚下的土层又埋藏着更多的历史。既然有伟大的建筑,就会有伟大的建筑师和建筑工,雕梁画栋的艺术家,怀揣理想的商人,还有英国统治者,他们毫无疑问对耶路撒冷都曾怀有不凡的雄心壮志。
她所做的,仅仅是挖掘这些不同人物眼中三座不同的耶路撒冷,也引出了三位建筑师和那个年代围绕耶路撒冷新城建造的曲折迷人的故事。比如,山顶上的希伯来大学,沿用近百年的巴勒斯坦邮局大楼,商旅不绝的雅法路广场,如今依然围绕着是非的哈达萨医院,还有融合阿拉伯、古希腊罗马、古巴比伦三种建筑风格的洛克菲勒博物馆.....还有,散落在城中那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精美住宅。
这些都要归功于一位逃难至此的德国犹太建筑天才、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建筑师和一位名不见经传、只服务邻里的本地建筑师。更隐秘的是,耶路撒冷旧城最大的地标建筑圆顶清真寺,那夺目的金色穹顶和镶满青蓝马赛克的外墙,在百年前竟然一度被烈日、风沙和鸟粪摧残得摇摇欲坠。多亏一位英国工艺家和一位亚美尼亚陶艺大师组建的团队,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奇迹般地修复了这件属于全人类的杰作。
它是一部难以被简单定义的历史文学:有建筑师对明日家园的伟大构想、能工巧匠的艺术蓝图;有流离千年的犹太民族复国之路、时代缝隙中欧洲的战争疑云,近代中东的紧张焦灼的空气;有商人的精明善变、医生的大爱无疆和工匠的锲而不舍;有日薄西山、不复威权的帝国晚景,也有百废待兴、繁花似锦的圣城新生。这本书关于历史、文化,也关于建筑,更关乎一座城市过去与未来。作者在书中不断地挖掘建筑建筑师背后的故事,却发现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被挖掘。
犹太人从欧洲来到耶路撒冷,回到祖先生活的土地。这是第一部的主题。以独眼的天才犹太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抵达巴勒斯坦开篇,他曾被称为“欧洲建筑界的尼采”,过着往来无白丁的上流生活。但此刻,他仿佛是一个走进玩具房的孩子,对中东的环境和建筑文化欣喜若狂。他站在阳光刺眼、狂风扑面的斯科普斯山顶,眯着眼,构想着一座犹太人、阿拉伯人共存的乐园。他和妻子露易丝刚刚逃离了纳粹的迫害,在犹太富商肖肯的邀请下来到巴勒斯坦。当时的耶路撒冷,堆砌着一战的废墟和丑陋的建筑大杂烩,丑得甚至令他感到“羞耻”,这让骄傲易怒的欧洲顶级建筑师难以忍受,毕竟他还为自己的邻居爱因斯坦设计著名的波茨坦私人天文台。在英国总督和两位犹太同胞的协助下,他开始了圣城规划之路。巴勒斯坦银行、哈达萨医院、肖肯图书馆、希伯来大学这些响当当的建筑拔地而起。然而麻烦依然不断,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同行的妒忌、政治力量的角力乃至好友的背叛,都让他在巴勒斯坦的建造步履维艰。由于新的大战,他被迫离开了巴勒斯坦,最终逝于美国加州,但他依然完成了他的建筑人格,也为无数流离失所的犹太同胞指明了家的方向。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和平。年轻的英国政府首席建筑师奥斯汀·哈里森,一位才华横溢的帝国公务员,一位喜欢旅行、写生的单身文艺青年。这部分也是个人最爱,因为他温和的英国气质和说走就走的潇洒。他和我们一样,不喜欢坐班,讨厌开会应酬,也讨厌出席门德尔松主办的名流聚会,他总是用各种方式避开应酬。在快速完成英国总督和项目主管交托的画图任务之后,他便安顿好自己的小白狗,去整个中东和地中海沿岸采风、到访无数的希腊罗马遗迹,吸收目光所及的建筑精华,用在了作品之中。
他不是那种消极厌世的“佛系青年”,而是开放的世界主义者。他住在亲自设计的农家小石屋里,与作家们通信,欢迎全世界所有有趣的灵魂。然而喜爱和平的人,心底总会有战争的阴霾。他少年时就逃离了繁文缛节的故乡,后来参军,在血腥残忍的索姆河战役中生还。他从堆叠如山的尸体中爬出,逃离战场,没人比他更厌恶和畏惧战争。在他设计的博物馆内部,铭刻着一句苏格拉底的名言:“美物难存”。因此,这座美好建筑的建造同样一波三折:挖地基挖到古墓群,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上层主管的干涉,升级的暴力冲突,但奥斯汀的多元文化理想,对和平的渴望,依然留在了他的建筑当中。
伟大之城在何处?耶路撒冷到底是谁的耶路撒冷?英国、美国?阿拉伯人、犹太人?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或许,耶路撒冷是属于她的建造者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第三部分,作者走在2014年的耶路撒冷,注意到一些华丽的阿拉伯陶瓷建筑,主要是一些本地人的住宅,这些建筑墙壁的角落,都有同样的铭文“斯派罗·霍利斯,建筑师”。她带着巨大的好奇心,采访了当地历史学家、社区居民、东正教会、档案馆,期间得到了许多当地市民的帮助,包括一位放下偏见的阿拉伯博士生。她寻着蛛丝马迹,追寻1914年的神秘民间建筑师斯派罗·霍利斯的事迹,而手里掌握的材料,仅有两张照片和几处建筑物上的署名,但她获得了更多新的信息,发掘到那个时代更多不为人知的市民故事。要知道,即使是今天的东耶路撒冷、与约旦边界,依然冲突不断,在没有军队的保护下到处乱闯是有生命危险的。她说,她就是会在这座城市里越陷越深。建筑师霍利斯是一个象征,仿佛城市的幽灵,见证着圣城的市民文化和建筑的流动性。
直到本书结尾,作者她依然在寻找,关于耶路撒冷新城的故事也并没有到此结束——我想,她的心中也有某些希伯来祖先们的坚韧品质吧。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五):耶路撒冷真的建起来了吗
耶路撒冷,一座位于中东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旅游者评价说,如果没碰上严重的巴以冲突,耶路撒冷称得上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城市,新城现代而繁华,老城宁静而多元——在这座城市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朝圣地;然而一旦矛盾激化,耶路撒冷立马就会成为冲突最为激烈的焦点之一。就在不久前,一贯喜欢特立独行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决定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而对于这个打破了地区和谐的决定,几乎全世界都在反对,联合国大会更是在纽约当地时间12月21日上午10点,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以128赞成、9票反对和35票弃权,通过了要求美国撤回将其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议案。
那么,耶路撒冷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为什么在它的身上,会密不可分地凝固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情结?为什么——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而1988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则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它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首都呢?!
还是先不管那么多了。因为巴以冲突,因为以色列复国,因为五次阿以战争,世人记住了耶路撒冷;因为这座城市同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所以它又被称为“三教圣城”,这种尊崇的地位无与伦比!但知道它名字的那些人,真的清楚耶路撒冷的历史吗?真的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吗?!在美国散文家、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阿迪娜·霍夫曼的笔下,在《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这样一本书中,也许,能够找到一座名为“耶路撒冷”集现代与古老的名城是如何被重新建造和“缔造”起来的!如果耶路撒冷有情感、会诉说的话,也许,它更愿意自己成为一座纯粹的中东古城,一座拥有3000年历史的名城;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和平与纷争成为了它最重要的标签!
阿迪娜·霍夫曼在《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中讲述了三个文化背景迥异的建筑师的故事:埃里希·门德尔松是一位天才级德国建筑师,以设计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作爱因斯坦天文台著称,他从德国来到这座百废待兴的城市,想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座城市规划好;奥斯汀·哈里森是个充满戏剧性的建筑师,拥有深厚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建筑知识,热爱传统建筑元素,缔造了伟大的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馆;而斯派罗·霍利斯似乎是一个已经被历史遗忘了的建筑师,却仿佛无处不在,就像是漂浮在耶路撒冷空气中的幽灵……
从头至尾,阿迪娜·霍夫曼都是在以一种极其冷静的笔触在讲着三个与耶路撒冷的不同时代联系在了一起的建筑师,是他们,以及更多他们的同行,重新“缔造”了耶路撒冷,留下了很多把历史的味道永恒地凝固了下来的建筑物,构成了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但是仿佛也仅此而已。虽然他们的文化背景迥然相异,但他们一定都想以自己的专业为这座城市留下点最纯粹的东西。他们确实也做到了,但这座城市却偏偏不那么简单、纯净!很显然,它背上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了!建筑以外,它还需要承载更多更重要的内容……
一座伟大的城市,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的呢?至少,它不应该让人第一印象,就下意识地想起冲突、想起战争来吧?!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六):建筑——耶路撒冷的灵魂
很久没有这样一次性完整的看完一部非虚构类的作品了。提到耶路撒冷,便总是给人一种神圣却又混乱的矛盾之感。 她的神圣是由于这里是三大宗教的圣城,而混乱也是因为她是三大宗教的圣地。而有关于它的著作无非尽是围绕着这三大宗教去讲述它的历史,它就像被三个孩子争夺的玩具,全都视其如珍宝却又使其遍体鳞伤。 翻开这本书,感到本书并没有延续一贯对耶路撒冷所描写的套路,作者阿迪娜-霍夫曼从建筑的角度切入对耶路撒冷这座世界圣地进行新的诠释,从这座城的美与丑到她圣身的每一处残垣与瓦砾,都记录着她的一生。 犹太人的那部经典《塔木德》中曾这样形容过耶路撒冷:“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都在耶路撒冷。”而此书便在告诉我们这里的美,不仅仅只是美在了她的神圣与精神,也美在了她的外表,她的一石一砖一瓦,她的每一寸土地美在了她的名字耶路撒冷。 一站后1920~1940年在英国托管下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三个不同的信仰与原则的建筑师如何打造了一座新的耶路撒冷。他们就像是这座城市的医生在最好的时期为耶路撒冷号脉、开刀、缝补、医治。是不是出于巧合,还是偶然中所蕴含的必然,书中所讲述的三位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奥斯汀-哈里森,斯派罗-霍利斯,分别来自不同的信仰与地域。门德尔松一位典型的德国犹太人,哈里森则是英国委托的建筑师,最后最神秘的人物霍利斯则是一位阿拉伯建筑师。 我们跟随建筑师的眼睛,去观察这座废墟之上的城市,一座被不同的势力占据又收腹多达44次的城市之下是近三十米深的废墟。当门德尔松看到这座城市中犹太人的土地丑得让他感到羞耻,却又可以让这位世界上最好的建筑师大展拳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门德尔松的理想并未能如其所愿。但其所流传下的建筑却带着他的理想扎根于此。相比较于门德尔松而言哈里森的命运就更坎坷一些,由于没有门德尔松那样世界级的声誉,哈里森就只是默默的听从安排以至如今他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仅管事到后来总是不尽人意,但不得不说哈里森的坚持是成就这座新城的关键。在书的后半段以至结尾作者霍夫曼讲述了她跟随着不同的人与不同的建筑,追寻着一个神秘的名字霍利斯,他在这座圣城留下的记号,在一点点揭开他与耶路撒冷的神秘面纱。 仅管书中的排版有些不尽人意之处,如:图片缺少标注等,但其独到的视角,探求了耶路撒冷与其建筑的过去与产生。虽然我们无缘看到这三位建筑师所构想的耶路撒冷的真正样子,但我们可以追寻通过他们的坚持群呈现的一座世界最美的城。又几十年来对圣城的争夺无处不在警醒世人,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七):有一些人,应该被记住
终于看完了这本厚厚的《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这本书。刚开始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它同我看到的很多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一样,是一本历史书籍。其实我忽略了它的副标题: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这本书主要讲的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相关的一些建造者的故事,也就是说,主要讲述的是人物的故事,而并非仅仅讲的是时间上的历史上的故事。
这本书是由一个个人物,而且是有史实可寻的人物组成的一本书。越读到后面,我越是敬佩这位作者。她经过了大量的考察与深入的研究才将缔造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这些人物串联了起来,就像深埋在地下的一些文物一样,有些人物的历史已经被人们封印了,上面可能覆盖了很多很多历史的痕迹。但作者就像是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些覆盖在它们表面的残余拨开一样,他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有很多人物,我是第一次听说,我想对于世界上每一个看这本书的人来说,很多人物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因为这些人物距离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他们又在耶路撒冷这个遥远的城市,更与我们有很远的距离。可是他们却鲜活的展现在了我们眼前,这就不得不说作者的才能与智慧了。
后来我了解到作者阿迪娜,是一位美国散文家、传记作者,文学评论家,她一开始是出生在美国的,后来移居到耶路撒冷,在当地生活了很多年,她写了很多关于中东地区和犹太人历史文化的作品。比如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有一篇文章叫做《犹太法官》,她写道,她发现了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起先做法官,后来又做了律师的一个人物叫做约姆.托福哈蒙。可她在网上却搜索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物的资料,她想这些资料一定被尘封起来了,于是她到相关的部门去寻找这些材料,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但经过多次努力,她终于看到了关于这个人物的第一手的材料,她也突然觉得自己和这个人物离得越来越近了。
我想这个感觉同我上文说到的那种,她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扒开,覆盖在上面的尘封的感觉是一样的。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写道,我沉浸于摆在我面前的文档和它们激荡起的思绪里,以至于几个小时里我都没有站起来过,一直弯着腰,用数码相机给文件拍照,我没吃午饭,也没喝水,而且工作人员宣布,档案馆将在五分钟后关门,我觉得我正从某个奇怪的梦里醒过来,带着轻微的头晕,我蹒跚的走出档案馆,走进依然明亮的阳光下,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某种精神恍惚下走向了那座房屋。
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吧,它给人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又让人愿意为他付出,为他做出艰辛的努力。这种时间与人物的牵绊,一直吸引着作者义无反顾的去进行研究。这本书中有很多有才能的人物他们都是从其他一些国家迁徙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并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就像这本书中第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门德尔松这个人物以及他的妻子。他们都是在别的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几经辗转,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起初他们是犹豫的,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这座城市,但是经过犹豫之后,甚至来来回回数次之后,他们还是留在了这座城市,说明这座城市对于犹太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了解历史,但我觉得了解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我们能够更加真实的看到那个时代里人们的生活状态。这比简单的了解一些时间概念,一些历史事件来说重要得多,因为我们无法穿越回去,而我们要了解的也并不只仅仅是一些事件的发生,更要通过当时的人们来给我们现在的生活一些启发,一些感悟。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八):可能的译后记
出版品牌“未读”的赵女士找到唐克扬,说有一本讲活跃于近代耶路撒冷三个建筑师的书想找唐老师翻译,唐老师跟出版机构商量能否由几个人共同翻译,他来把控质量,并在微信群中问大家有没有意向。最后,郭博雅、姜山、黎乐源、李卓璋、尚英南,及唐克扬,我们六人组成的翻译小组,共同翻译本书。
Interlab书作坊过去曾作为练习,翻译过On Weathering: the Life of Buildings in Time (Mohsen Mostafavi & David Leatherbarrow, 1993),通过接龙的方式,当天轮值的翻译者将一个段落翻译完后放到微信群中,并与其他成员讨论其中的疑难点,第二天继续如此。由此,我们也渐次理解了建筑和城市类书籍的翻译过程,其中包含知识、语言、逻辑、故事、感性和历史的多个层次。在微信群中接龙、讨论、再加工的工作方式被我们称作“超级城市”,因为它像一个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关系在小小微信群中的模型,其中包括即时的回复、有意义的讨论,也包括拖延、信息冗余。
本书的翻译,也是排好了接龙的次序,每天由一个人发两页书的中文翻译到微信群,再全员讨论关键字词、广和狭的历史、建筑细节的具体形式等不容易把握的问题,包括英文中冠词在某处隐含的指义等。不定期地,多人微信语音集中解决这段时期的问题。翻译基本完成后是两轮校译,每一段落的译者、校译者和第二遍的校译者是不同的三个人,这样交叉校对、订正、统一文稿。历史、地理、民族、政治、人物、建筑的专有名词部分则由李卓璋来订正、统一;最终的文稿删去了关于庞杂背景的大多数注释,但每一个具体人物、地点、事件等的背景信息对于我们译者真正理解作者的意图而言必不可少,这些注释中的大部分也都由李卓璋查找出来,发到微信群中,并以注释的方式附在工作文稿中。交叉校对得到的准确译文,又主要由唐克扬老师从头到尾批注、修改,使文字的阅读感受通畅、优美。在翻译、校译、理顺文脉进行的“漫长”过程中,由于升学、工作等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有拖沓、断档的时候,但最终还是看到“直到我们建成了耶路撒冷”的一天。
本书串起了散落在耶路撒冷的历史、故事、轶事和空间,作者对于语言的复杂性的游戏给译者——我们——以甜蜜的折磨,那是某种诗意、诙谐、黑色幽默,有时故意引向困局,或啰里啰嗦,却又隽永的叙述方式,毕竟它所要呈现的历史就总是自相矛盾,充斥着消化不良导致的黑色幽默。作为译者的我们,也试图贴近作者和历史的原意,并让这些意味能够见容于中文表达的框架之中。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九):新城
耶路撒冷以天主教之都而闻名,这也是我唯一能把这个城市记住的契机,有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我一直想找机会了解一下,它的文化必然与其他城市不同。耶路撒冷分为新城和旧城,如今的样貌和从前大不相同,人们喜欢它也大都是喜欢它如今的样貌。喜欢一座城市,我认为需要有两点打动自己的内心,一是城市的格局样貌,二是文化底蕴,耶路撒冷则同时具备了两点。当地的建筑风格与我们常见的有很大差别,很多人都无法理解那些建筑的美,但是了解了创作的初衷与其设计感所在,就知道这个城市到底美在哪里了。
书中讲述了三位参与建立耶路撒冷新城的建筑师背后的故事,由此多角度展现了其特点,在这条路上他们经历了许多困扰,这也是与当下的社会背景仅仅挂钩的。我对一个城市的喜爱程度,直接取决于它的文化底蕴,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都是在这里起源,毋庸置疑会有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尤其在这个欢迎所有犹太人定居的地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又带来了新鲜的文化,所以它如今的样貌综合性也很强。
可以说这几位建筑师就是艺术家,他们在建立这座新城的时候是享受的状态,通过他们不同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理念的建筑。不过话虽如此,我依然不是很喜欢这种建筑风格,但是通过这本书我理解了背后的缘由。其实这几个人是没有什么大联系的,可是历史正是因为有原因才能够连续地进行下去,作者以这三位建筑师来拼接这段历史也是很新颖的一种手段。这本书中讲述的都是城市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作者能够整理出这些史料可见花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只有真正生活在当地的并热爱那个城市的人才会看得更透彻。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于耶路撒冷了解之路的捷径,这个外表就能够看出历史痕迹的城市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探索,尤其是那些对宗教有着特殊信仰的人们更是应该了解一下这里的背景。通过城市能够接触到更深的文化,古人的思想和他们的创造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他们手中的产物能够看出需求与发展进程。这座城市能够以如今的面貌呈现出来,是经历过很多磨难的,后人们更应该去珍惜。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读后感(十):耶路撒冷——理想主义者将自己与它一同撕碎并埋葬
quot;这座城,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而先于一切的,它是一座理想主义者的城市,此外,它更是理想主义者在此后世世代代里将他们自己与城市一同撕碎并糅合的一座城市。" ——查尔斯·R·阿什比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所有学习过建筑史或城市史的人都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和书写是极为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世纪战火纷争,文字记录、影像资料甚至战争亲历者的访谈结果都很难完整地、细致地复原历史原本的样子;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和资料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冲刷,很多资料表层受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需要突破文化、语言甚至“无证之史”的重重障碍来还原客观事实。《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的作者阿迪那·霍夫曼却偏偏挑选了二十世纪初的耶路撒冷,从故纸堆里一点一滴地拼凑出了这座令人着迷又心碎的圣城的建设历史,以及书写这座城市的三位伟大而神秘的建筑师背后的故事。
1934年,来自希特勒德国难民的著名柏林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抵达耶路撒冷,开始了属于他的时代。在这之前,他曾参与一战,在前线夜间值班的时候他“倾尽全力去绘制这些想象中的建筑”,活在他所说的“源源不断的憧憬中”。二战爆发之前他辗转荷兰、南法、英国,最终得到了巴勒斯坦权贵的赏识,前往耶路撒冷。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连续出现的财务、法律法规等问题的周旋,暴乱兴起、难民遍地。门德尔松必须认识到复杂的新中东现实,并避免在接连变换的政治局势中被当成炮灰。1941年,在一系列失望和打击下,门德尔松远走旧金山,再也没有踏上耶路撒冷这片土地。
第二部分主要围绕着1922年至1937年间巴勒斯坦首席政府建筑师奥斯汀·圣巴布·哈里森(Austen St. Barbe Harrison)。这位公务员“沉浸在拜占廷和伊斯兰建筑的传统之中,发现自己在英国统治的窒息和暴力的条件下工作”,将对异国土地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巴勒斯坦公共事务处无尽的日常琐碎之中。哈里森后期为耶路撒冷倾注了大量惊人的想象力、时间和关怀,最终被当地建筑史学家看做英属巴勒斯坦时代建筑师的代表、官方城市规划里“几乎唯一一位缔造者”。
而在最后一部分,作者阿迪那·霍夫曼穿过今天耶路撒冷的街道,寻找可能是希腊人又可能是阿拉伯建筑师斯派洛·霍利斯(Spyro Houris)的痕迹。据说有关霍利斯的记录都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被损毁了,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完全被遗忘,他的宏伟的亚美尼亚瓷片建筑仍然矗立着——或许这是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上文化流动性的一种证明。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很难被归类为建筑史或城市史。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搜索书中出现的建筑名称和城市地图,来帮助理解文本。阅读作者阿迪那·霍夫曼的文字,像是一次考古发掘的过程:二十世纪初的耶路撒冷的土地下埋藏着的一层一层纪念、遗忘、理想和伤痛,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城市中,必然有着属于个人的追逐。
quot;我不会停止内心的搏斗, 我的剑也不会在手中安眠,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