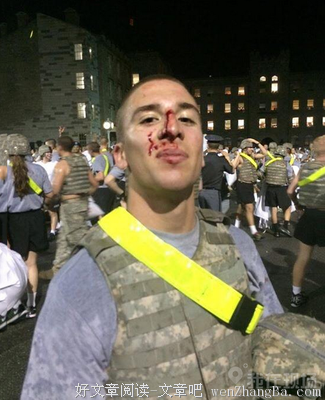血枕头
1
一觉醒来,章山发现枕头上有块血迹。硬币大小,呈暗红色。
他到厕所对着镜子看看,头脸上没有血渍,往耳朵眼里掏掏,也没血,也不痛。
这时厕所门给擂响了:“章山你格老子(四川方言)还要好久?马上上早自习了!”
章山一慌,撩了把水擦擦脸,连牙都没刷就出来了。
擂门的人叫陈达,是章山的室友,个子不大,脾气却很暴躁。
这不能怪他,任谁高考复读,脾气都不会太好。而章山已经复读两年了。
穿好衣服,章山汇入上早自习的人流中。身边都是十几岁的复读生,没穿校服,也没人交谈,沉默地向江县中学涌动。
江县中学并不是一个中学,只是一个复读班,全封闭管理。因为出了几个状元,连外省的落榜生都慕名赶来,把这个川西的小县城活活捧成了“高考县”。
教学楼顶上,钉着七个大字,用红漆写着:“置之死地而后生”。
章山不想读了。除了高考,还有其他出路。但是他娘不这么认为。
“妈妈再苦再累,也要让你考上。”她总是这样说。
章山最怕他娘皱眉,但是他娘永远皱着眉头,一想到那些刀刻般的皱纹,章山就喘不过气来。
等晚上回到寝室,章山累得脑子都不转了,把枕头翻了一面,就睡死过去。
哪知第二天起来,血迹又出现了。
章山一手支着床,愣愣地看着枕头上的血块,冷汗从后脑勺慢慢沁出来。
这枕头是宿舍发的,罩子妈妈前几天刚洗过,还微微带着洗衣粉的香味,现在两面各带有一团血迹,印在米白色的枕套上,格外刺眼。
枕头里面没有异物,章山的头脸上也没有发现任何伤口。
当天晚上,章山说什么也不敢睡在枕头上,想来想去,只好把枕头塞进柜子,又拿几件厚衣服叠在床头,翻来覆去到下半夜才迷瞪一会儿。
好在醒来后,什么痕迹都没有。
章山拿起衣服来里外看了一遍,没有血迹。他又抹了一把头脸,还是没有。
章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才准备起床。
哪知他脚刚落地,就发觉冰凉粘湿一片。章山把床帘一掀,发现屋里赫然泼洒着一地血红。
伴随着滴滴答答的声音,鲜红的液体还在从他衣柜的缝隙中涌挤出来,不住下淌。章山长在农村,每次见到杀牛,总是惊讶牛的血怎么这么多,怎么这么红。
现在的宿舍,好像有人在他的床前割断了牛的喉咙。
章山的心猛地一顿,终于喊叫出来:“啊!”
陈达被章山的喊声惊醒,迷迷瞪瞪地坐起来,拉开床帘,好一阵子才看清了屋内的景象,忽然双目圆睁,高声骂道:“我靠!我靠!”
好像觉得这两声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跟着用更大的音量骂道:“我靠!怎么这么多水啊!”
“水?”章山好像还在恍惚里。傻傻地看着陈达光脚站在血池里,连脚背都染红了。
陈达赤着脚,“啪啪啪”地走到厕所拎了一把拖把来,开始拖地。
拖布很快就浸红了。陈达弯腰去拧拖布,血红的液体从他的指缝间淌出来。
章山连话都说不出,呆呆坐在床边,翘着两只脚不敢放在地上。
不多时,陈达就发现液体的源头来自于衣柜,于是猛地拽开衣柜门。
章山顿时看见了里面的枕头:被血浸得透了,皱巴巴地蜷缩在衣柜一角,像一个血肉模糊的胎儿。
陈达用两根手指拎住枕头提了出来,血水成股流下,砸在地面上,水声不断。
陈达骂道:“你有病啊!把湿了的枕头往里放。”看章山瞠目不答,又补了一句:“你格老子疯了啊!”
章山没法还口,他连自己怎么穿上衣服,怎么踮着脚逃出寝室都不知道。
“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章山脑海中只有这两句话。
2
他刚出寝室,就当胸撞上一个人。章山低头一看,原来是同班的小周。
小周看见章山,立马拉着他的手臂,问道:“师兄,你没事吧?”
江县中学实行严格的男女分隔制,附近看不到一个女生,而小周白白瘦瘦,比女孩子还文弱,还偏偏特别喜欢自己。
章山复读两年,大家瞧不上他年纪大成绩差,只有小周还亲亲热热地管他叫“师兄”。男生都笑话小周“娘炮”,章山虽不想跟着取笑,但被他拉住胳膊还是怪不舒服的,于是把他手拿开,道:“没事没事。”
“真的吗?我看你脸色不好。”小周道。
章山想起宿舍的血迹,和那个血枕头,心中又恐慌起来,终于吞吞吐吐地说:“我……那个……遇到点怪事儿……”
小周满脸关切,又道:“师兄,你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就跟我说,或者跟老师说。楼下有个管仓库的薛老师,人很好的,一般的老师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管,薛老师不一样。”
说到这,小周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道:“我以前遇到点困难,都是薛老师照顾我的。师兄,我跟你一样都是农村出来的,成绩也不理想,薛老师从来不嫌弃。我陪你去找他吧,有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
“啊,不了,不了,”章山道。
看着小周那双殷切的眼睛,他微微地有些尴尬,只得边走边道:“我先走了啊,该上早自习了。”
走在路上,宿舍里的景象一直浮现在眼前。一想起那只血枕头,章山心中就是一惊,一步也走不动了。
他一停下来,后面的同学就撞上了他,也没说什么,像溪水绕过礁石,继续涌向教学楼。
章山咬了咬牙,转身往宿舍找薛老师去。
到了宿舍楼下,章山半天才在楼梯转角后找到一扇绿色木门,式样陈旧,油漆斑驳。木门应手而开,湿霉的气息迎面扑来。
时值深冬,南方没有暖气,章山走进门里只觉身周一片冰凉。走廊的尽头有一道门户,微开一缝,桔黄色的暖光打在漆黑的通道里。
章山向着灯光赶了两步,脚下便绊到一物,低头细看,却是一头死猫,白骨利牙,不知在这躺了多少年月。
章山看它死状狰狞,不由得绕开一步,刚迈开腿,便感什么活物在脚边蠕蠕而动。章山心中一紧,差点叫出声来,却发现是只活猫,眼睛在黑暗中金黄两点,探照灯般地瞪视了他片刻,便溜进那道门户中去了。
章山松了口气,赶忙伸手把那门推开。
门里坐着一个年轻人,微胖,带着眼镜,正对着炭炉烤火。看章山进来,他似乎十分意外,屋里没灯,炭炉的亮光照着他惊讶的表情。
“请问……您是薛老师吗?”章山道。
那年轻人没有答话,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章山站在门口,局促起来,实在不知该如何讲述这些怪事。
年轻人微微一笑,道:“先进来坐吧,烤烤火。”
他年纪比章山大不了几岁,言谈表情却极是沉稳,又是和气。章山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些亲近之感,交谈两句,终于把血枕头的事情吞吞吐吐地说了。
哪知薛老师安安静静地听他讲完,丝毫没有质疑或者取笑的意思。他用手指敲着太阳穴,想了好一阵,终于道:“你等一下。”跟着去屋角翻弄出一个枕头,放在章山面前,又道:“你把手指放上去。”
这个枕头跟章山的枕头一模一样,都是宿舍统一发的。
章山看了一眼薛老师,将信将疑地把食指点在枕头上。枕头里填充的是人造棉,一压就出现一个小坑。
他在宿舍地下室里用手指点着一个枕头,旁边还有人郑而重之地看着,章山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荒唐。
他正想说点什么,忽然手指尖湿润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凑近枕头,只见血红的液体迅速聚集在压出的小坑中,转眼已经没过了半个手指甲。
章山大叫一声,像被火烫了一样把手缩了起来。
食指不痛,也没有伤口。枕头上多了一团血迹。
章山心脏狂跳,看看手指,又看看枕头,脸色吓得雪白。
薛老师却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把枕头放在一边,道:“没事,你别怕。”
章山带着哭腔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薛老师看着他,缓缓道:“你知道神树吗?”
3
神树是一棵百年榕树,就在教学楼后面。开始是当地乡民逢年过节在树下烧点纸钱香烛祈祷平安,后来被家长和学生用来祈祷高考成功,据说特别灵验。
它名声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但凡在江县复读的都要去拜一拜,以至于树下常年香火不断。
章山一愣,说:“知道呀。”
薛老师点点头,又去屋角忙碌了一阵,转身把一个东西交给章山,道:“你去把它埋在神树底下。别拆开看,埋了就走,记得不要回头。”
章山低头看了看,见手中是一个折得密密实实的纸包,隐约看出里面有些字迹,犹豫道:“这是什么呀?”
薛老师道:“别多问,先去埋了吧。”
章山还想说些什么,忽然眼前一团东西闪过,刚才遇到的活猫窜上薛老师的膝头。章山吓了一跳,手里的纸包都差点掉了。
薛老师微笑着抚摸猫头。那猫儿是寻常的虎斑猫,虽然仰头享受着主人的抚摸,两眼却包含敌意地盯着章山,把他瞪得直发憷。
薛老师一面逗猫,一面缓缓道:“别担心,埋了就好了,快去吧。”
章山“嗯”了一声,只得起身走了,临出门,薛老师又叮嘱一句:“记得别回头啊。”
上午的课程已经开始了,章山捏着纸包,走在安静的校园里,天空明亮,空气清新,刚才去过的地方,遇见的人,说过的话,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但手里确确实实捏着一个薄薄的纸包。
章山深吸一口气,想道:“别管了,趁这会儿人少,赶紧埋了完事。”
哪知刚看见神树,他就停下了。
树前正跪着一个妇人。蓝布衣服,花白头发,瘦瘦小小,正是章山的妈妈。
***妈双手合十,祝祷了一会儿,又开始磕头。每磕一次,额头都贴在地上,久久不肯起来。
章山远望着巨树下的母亲,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妈妈迷信得厉害,一个农村妇女,小学都没毕业,不信这些还能干什么?
章山四处望望,还好没有同学看见。他悄没声退了几步,从教学楼的另一头绕到神树背面。
这是他第一次走近神树,只见冠盖如伞,遮天蔽日,密密麻麻垂下无数气根,树身虬结粗大,三四个人也合抱不拢,树枝树杈上满是红布条幅,清一色写着“金榜题名”,有些枝杈绑得太多,连树皮都看不见,红彤彤一片。
树下满地都是香烛燃完后剩下的木棍儿,有几柱香还在苟延残喘,悠悠飘出些青烟。血红色的蜡烛油,一滩一滩地到处都是。
章山叹了一口气,蹲下把纸包埋在土里,又放块破砖算是做个记号。他琢磨着是不是应该祷祝点什么,想半天又想不出来应该说啥,就拍拍手站起来走了。
刚走没两步,身后就传来一个声音:“山山!”
章山一愣,还没等反应过来,他的衣袖就被人扯住了。
章山顺势转过身来,眼前果然是***妈。
“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没去上课?”妈妈问道。她的眉头依旧皱着,额上还沾着少许泥印子。
父亲死后,妈妈一个人务农把他养大,为了供他复读,开始在江县附近的灯泡厂做工,此刻手臂上还带着做工时穿的袖套。
其他陪读的父母多半在江县租个房子一起居住,章山妈妈为了省钱自己住在工厂,给儿子租了个两人间的宿舍。
“我……我出来上厕所。”章山答道,一边把衣袖从妈妈手里抽出来。
***妈点点头,又道:“有脏衣服没有?我下回把洗好的衣服送过来。上次给你买的奶粉,喝了没有?”
妈妈一开始问问题,就停不下来,章山“嗯嗯”地对付着。
终于,***妈小心翼翼地问:“那个……那个模拟考,分数出来了没得?”
章山心中已是极不耐烦,答道:“没有,还没出来。”
***妈点了点头,道:“恩,没事,考得不理想也不要紧,还有半年呢。妈妈相信你,妈妈再苦再累……”
这样的话,***妈说了无数遍,此刻又说起,仍旧是哽咽了,续道:“再苦再累……”
章山看见妈妈的泪水,心中反而升起一股说不出的焦躁,又是羞耻,又是愤怒。
从小他就在这双泪眼的注视下长大,以前见妈妈哭的时候,特别难过,说不出的内疚。随着长大,难过慢慢变成麻木,麻木又变成愤怒。每一次看着妈妈皱着眉头流着泪,章山就喘不过气来。
“我要去上课了,”章山冷冷道。
“对,对,快去,别耽误……”妈妈擦着眼睛,连忙道。
章山转身就走了。
白天功课紧,晚上一回到寝室,章山的心就往下沉。好容易鼓足勇气推开房门,却发现地板上干干净净,别说血迹,连水迹也没有。(爱情故事大全 www.wenzhangba.com)
再一抬头,发现枕头被晾在窗帘杆下面,米白色,连之前的两小团血渍也不见了。
章山摸了摸枕头,微微有些潮湿,已经没有滴水了,枕头正下方还放了个塑料脸盆,盆底的水也是清澈的。没想到陈达这小子,脾气这么暴,做家务却挺能干。
当天晚上,章山难得睡了个好觉。可惜睡到下半夜,就被一个怪声吵醒了。
4
那是水珠滴落的声音。
先是缓慢地,有节奏地,就像没有关严的水龙头,一滴一滴砸落在塑料盆里。
章山躺在黑暗中,睡意全无,听着自己的心跳随着水滴声越变越快。他想喊醒室友,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想去看个究竟,却始终不敢掀开床帘。
滴水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密。一两滴,三四滴……像屋檐滴下的雨水,像开春化开的溪流,像有人终于拧开了那个龙头。
盆已经装不下了。血水开始在地板上蔓延。拖鞋,地上的垃圾,开始漂浮起来。
血丝顺着垂下的床帘缓慢上爬。章山双唇颤抖,满脸是泪,眼睁睁地看着血红色在四周的床帘上冉冉升起,而四肢却如同被胶结在床垫上,一动也是不能。
终于,有一缕血水蜿蜒地漫上他的床铺,缓缓贴上他滚烫的皮肉。章山只觉得腰间一冷,仿佛有尖刀刺入,终于大叫一声,坐起身来。
他一把扯下床帘,周围却哪里有什么异样。枕头已经干了,皱巴巴地挂在衣架上,地上的盆子里还装着昨晚那点残水。天已蒙蒙亮,陈达没有拉床帘,四仰八叉地睡得正香。
章山心脏狂跳,泪水和汗水顺着下巴滴在被子上,整个人如同虚脱一般。
他顾不上叫醒陈达,披了衣服就下楼去找薛老师。
大清早,薛老师依旧在炉前烤着火。
章山费了半天劲才讲完刚才的见闻,跟着失魂落魄地问:“薛老师,这是做……做噩梦了么,这梦……这梦……”说着就痛哭起来。
薛老师皱了皱眉头,问道:“昨天你离开神树的时候,回头了么?”
“没有啊,”章山脱口而出。紧接着又改口道:“喔,我遇到我妈,她在后面喊我。”
薛老师叹了口气,把脸转向炉火。
章山心中砰砰直跳,问道:“怎么了?”
薛老师低头思索一阵,又收拾出一个纸包递给章山,道:“没事,你把这个再拿去埋了。记得,不要回头。谁叫你,都不要回头。”
章山看看手里的纸包,又看看薛老师,嗫喏道:“老师,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中邪了?”说着又要流下泪来。
薛老师叹了口气,轻声道:“小章,这不是你的问题。江县中学是个煞气很重的地方,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到这里来的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很少有开开心心的,他们的怨气、焦虑和愤怒一年一年越积越多。运气好的,就离开了,运气不好的,就熬不过去。”
章山止了泪,怔怔地听着。他也知道江县中学每隔几年总出几条人命,有跳楼的,有失火的,有食物中毒的,还有的学生忽然就不见了,上午的课本还在桌上摊着,下午人就消失了,家长老师怎么找都找不到,只在学校后面的鱼塘边发现他的皮夹克。
放水的时候,章山和好多同学都围在塘边看热闹,只见塘水一尺一尺地降下去,直到露出塘底的黑色的淤泥,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章山到现在还记得那同学的父母抱着皮夹克在塘边痛哭的模样,也不知道学校花了多少钱才摆平这件事情。
“小章,你知道江县中学煞气最重的地方是哪里吗?”薛老师问道。
看他不答,薛老师缓缓道:“是神树。”
“神树?”章山失口叫道。
薛老师点点头,道:“对。你以为死去的人都是因为绝望,因为熬不过去,但欲望比绝望更可怕。绝望会让人伤害自己,欲望却有力量去伤害别人。百年来,神树纠结了太多人的欲望,要升官发财的,要长命百岁的,却从没像现在一样年复一年地接受同一个欲望的包围。”
“欲望越强,煞气越重,伤害也越大。它摧毁年轻的孩子们,折磨他们,让他们崩溃。这已经不是一棵树的问题,是整个江县中学的问题。很多丑恶的事情甚至正在发生,但是没有人在乎,因为没有人真正在乎这些孩子。这整个地方都不安全。”停顿了一下,薛老师又说道。
章山听得目瞪口呆,怯怯地问:“那为什么……我的枕头为什么……”
薛老师叹了口气,道:“这些煞气会寻找一切可能的缺口来伤害你,也许是一个人,一支笔,一个眼神,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为什么是我?”章山急道。
薛老师抬起头来打量着章山。他虽然比其他同学都大,嘴边已经长出绒毛般的胡须,却也只有十九岁。
他身子瘦高,四肢显得格外细长。脸色很苍白。因为昨晚的惊吓,眼下还带着深深的青色。
“你见过草原上狮子的捕猎吗?”薛老师想说。“它们总是追着兽群奔跑,直到弱小的猎物落单。越是弱小的活物越容易被击溃,也越容易成为目标。”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只微笑道:“也许你比较特别。”
章山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又捏了捏手里的纸包。
薛老师道:“快去吧,明天就没事了。”
5
还好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熟人,章山赶紧把纸包埋了,想了想,又对着埋纸包的地方磕了一个头,才赶去教室。
早自习已经结束,连第一堂课都上了大半。班主任皱眉道:“怎么又迟到?昨天也迟到。你是不是不想上了?”
章山还没答话,坐窗边的一个同学就接口道:“我看见他刚才在给神树磕头!”
全班“轰”地就笑起来了。
班主任用教鞭敲着讲台说:“磕头你就能考上吗?你去年怎么不去磕头啊?照你这个成绩,你得磕多少头啊!”
章山给嘲笑惯了,闷不吭声地走到自己座位上坐下。
班主任又敲着黑板,大声道:“别笑了!笑什么笑!笑就能考上吗?”台下还是发出嗤嗤地笑声。
只有小周远远地从前排扭过头看着章山,满脸关切。章山却没有看小周,只注意到他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个陌生的同学,正回头对他微笑着,友好的微笑。
章山心道:“什么时候来了新同学吗?”
从此以后,一连很多天,没有任何怪事发生。
枕头早就干了。章山不敢用,也不敢留在宿舍,就给薛老师送回去了。
他常常去薛老师那里坐坐,薛老师也很高兴他的来访,连那只虎斑猫也友好了不少,居然开始绕着他的脚打转了。
他这才注意到,薛老师的仓库里,陈设极其简单,一张空桌,几把椅子,连灯都没有,只有一个炭炉,一直烧着。
每当他说起学校里的事情,薛老师总是饶有兴致地听着。学习虽然忙碌,总有男生会“偷渡”些漫画书进来,章山也看过,薛老师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总是津津有味,还不住询问细节。说到精彩处,两个人都拊掌大笑。
章山是独子,每逢此刻便想,要是自己有个这样的哥哥可有多好。
又一天中午,章山正想趁着午休去找薛老师聊聊,刚下到一楼,就看见妈妈正背对自己站着,蓝衣白发,提着大包小包。
他心中一烦,便踮着脚溜进地下室了。
进屋刚坐下,章山就捞起虎斑猫放在膝盖上逗弄起来。
薛老师道:“今天看你心情不错呀。”
章山一面摸着猫头,一面快活地说:“是啊,最近挺好,吃得好,睡得好,考试也不错。”
薛老师看他高兴,胖胖的脸上也露出笑容,道:“那就好,还有几个月,考完就好了。”
章山笑道:“是啊,挺快的。我还以为特别难熬呢。你不知道,最近班上来了几个新同学,人都挺好的。”
薛老师的笑容消失了,问道:“新同学?”
章山正捏着猫爪子玩,头也不抬地说:“是啊,新同学,有一个挨着小周坐,后来又有几个跟我一块坐在最后一排。我中午吃完饭还跟他们一块儿回来呢,也不知他们住哪个寝室。”
薛老师颤声道:“这些新同学……长什么样子?”
章山抬起头想想,道:“没什么特别啊,一个挺高,一个挺黑,一个总背个水壶,还有一个穿皮夹克的。”
便在这时,虎斑猫仿佛被他弄痛了一样,回头呲牙叫了一声。章山心中一憷,把它放走了。
薛老师神色郑重,道:“小章,这些同学不安好心,你别跟他们来往,考完后赶紧走,别回来了。”
章山一愣,道:“好。”又道:“我也回不来了,我妈肯定没钱供我再读一年。”
薛老师“嗯”了一声,眉头仍旧紧锁。他沉思片刻,又去墙角收拾出一个纸包,递在章山手里,道:“快去,把这个也埋了。”
章山拿着纸包,傻傻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薛老师看着他迷茫的脸,欲言又止。章山跟他认识以来,从没见他这般紧张,更从没见他如此关切地看着自己,仿佛又是难过,又是不舍。
章山心中忽然升起一种感动,鼓起勇气道:“薛老师,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的,一定告诉我。”
薛老师一怔,又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轻声道:“没事,就是以防万一,你赶紧去吧。”
章山点点头,正要走,薛老师忽然伸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道:“记住,别回头。”
这是章山第一次被他握住手,只觉得那手掌有些冰凉,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薛老师把那纸包往他手里握紧些,又道:“保重。”便放开了。
6
章山捏着纸包,一路小跑到神树下,把它和前两个纸包埋在一起,又赶紧往宿舍跑去。
哪知跑到半路,迎面撞上妈妈。
妈妈一看见他,远远地就开始招手,一边喊着:“山山!”
章山没办法,只能走到母亲面前。***妈依旧皱着眉,跟儿子在一起,她何尝不是战战兢兢,生怕惹他不高兴,生怕影响他考试。
复读了两年,面前这个年轻人变得十分陌生,嘴角眼神里常常带着恨意,***妈心中一酸,又强打起笑容道:“给你送东西,你不在,我就让宿管老师让我上去了。我看了你的奶粉罐,一点也没少,怎么不喝呢?”
章山的脸上又出现了焦躁厌烦的表情,***妈心中一跳,几乎想要逃开,却又忍不住问道:“最近考试了吧?成绩……成绩怎么样?”
章山冷冷道:“挺好的,进步了好几名。”
***妈终于忍不住了,抹泪道:“好,好,那就好。只要成绩上去了,妈妈就知足了……”
章山心中厌烦,又惦记着薛老师,哪知刚迈开步走,就听妈妈在背后问 :“你的枕头呢?”
章山心中大震,缓缓转过身,颤声道:“什么?”
妈妈的泪已经擦干,眼睛却还红着,道:“我刚才上你屋去,没看见枕头。你的枕头到哪里去了?”
章山心跳加快,只得答道:“我睡着不舒服,就给别人了。”
“给别人了?”妈妈急道:“怎么能给别人呢?枕头里面有我向神树求的符啊。”
章山一听“神树”两个字,冷汗顿时沁出脑门,颤声道:“什么符?”
章山的妈妈仿佛有些羞惭,轻声道:“我在神树下面磕了一千个头,又花了五百块钱,给你请了一道金榜题名的符。前一阵去你屋里送衣服的时候,悄悄给你缝在枕头里面了。山山,我知道你不信这些,你别怪妈妈。妈妈想帮你,又没有文化,妈妈也是没有法子……”说到这,眼泪又涌了上来。
章山只觉得天旋地转,大叫一声向宿舍奔去,身后传来妈妈的嘶喊:“山山!你去哪?你别怪妈妈……”
“我要去找薛老师!”章山心中只大喊着这句话。
奔到宿舍底楼,章山一把拉开绿色的木门,眼前却是一堵砖墙,把门封了个结实。砖色陈旧,绝不是新砌起来的。
章山一呆,抖着手摸上那堵墙。忽然开始捶打起来,一面打,一面哭喊:“薛老师!薛老师!”
墙纹丝不动,章山的手却痛得仿佛已经断裂开了。
小周正好下楼,看了章山失魂落魄的样子,赶紧过来拉住他手道:“师兄!你怎么了?”
一见小周,章山如同见了救星一样,握住他双肩,大声道:“小周!是你让我来找薛老师的,薛老师就住在这里面对不对!”
小周奇道:“没有啊,薛老师不住这啊。”
章山如遭雷击,口中只喃喃重复一句话:“不住这,不住这……”
小周见他这个样子,着实担心,急道:“师兄,我这就带你去找薛老师,你别急啊。”
章山愣愣地跟着小周走出大门。在宿舍楼后,有间平房,小周敲了敲门,里面便探出个半秃的头来。
小周道:“薛老师,这是我们班的章山。”
那秃子一看章山,立马眉开眼笑道:“啊,你就是章山,我听小周说起过。”
小周冲着章山,略带腼腆地说:“薛老师很照顾我的,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就跟他讲,他也帮我保密,从来不跟别人讲。”
秃子笑道:“好说好说,你们这些孩子啊,父母也不在身边,怪可怜的,老师不心疼你们,谁心疼你们呀。来来来,快进来。”
章山呆呆道:“宿舍底楼那个木门后面,以前……以前有人吗?”
秃子一怔,答道:“喔,那个啊,好多年前也是宿舍,后来有个学生复读了三年还考不上,就在里面烧炭死了,学校就把这个地下室封了。”
章山看着这个薛老师,只见他四十多岁,眼睛不住往自己身上打量,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在小周背上揉捏着,小周在一旁讪讪地笑着。
“快进来呀,别客气,来来来!”薛老师说着又伸出那只大手来挽章山。章山大喊一声,掉头便往神树跑去。
神树冠盖如伞,把章山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之下。
章山顾不上心跳气喘,跪地挖出了埋在树底下的三个纸包。
他拆开第一个,只见上面用黑墨写着五个大字:“放过这孩子。”
章山又拆开第二个,上面写着:“我死已足够。甘愿永世被封地下,绝不以他人性命度自己超生。”
第三个纸包里又只写着一句话:“只要你们放过他,让我怎样都行。”
章山捧着纸包,猛地发现这句话下面缓缓出现一个小点……一竖……又一点……一笔一划地写出“快走”两字,字迹歪斜潦草,却能看出出自同一人之手。
“快走!”
三个纸包都跌落在地。章山全身颤抖,默默地转过身,双腿如被树根牵绊,重得迈不开步来。
走不动也要走!他咬着牙,满脸是泪,一步一顿地向宿舍走去。
便在此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而温和的声音:“小章,你帮帮我……”
章山心中一热,眼前已是一片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