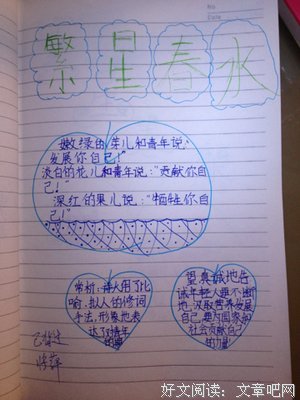●经验使我相信,每件事情都有它的时域,你是不能强求的,只有它的时域到了,一个偶然的亮光,自会把它带到澄明。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可是,我们的主角─“性书狂人”萨德,显然不属于实证领域,即不能在人群中寻找正例或反例以资证明便可了事。换句话说,把这个问题放到人群中凭经验问答,等于无。
那么,它应属于思想的事情了。这有点怪,没有比“性”更肉身化的事情,竟然属于思想的范畴并需寻求思想的规定。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春水煎茶,新绿初开。温一壶清茶,在春天等你,等你一袭青衫,横笛而歌在盛开的花海;我衣袂飘飘,独自漫步在幽僻的林间小道。是袅袅的清音亦或是淡淡的芬芳,踏歌而行的途中,与你,无约而相逢…… ----荷塘月色
●清晨早起打扫庭院,插花,焚香。白日劳作。晚上喝酒看月亮。春夜的海棠花在街上铺了薄薄一层雪。我等待你来接我回家,手里拿着我的白布衫。
背后那股力量已经把你推到悬崖边缘最狭窄幽僻的一条通道。穿过它,以全部的专注和心力。
万事万物,最终只有承诺和牺牲,会让我们彼此怀念。
“水往前走,花瓣自动脱落,衣衫上丝线褪色断裂,手背上脉管凸起蜿蜒山岭。无常逐一升起和熄灭,我对你赤子之心永存。”
●生命还在生命时就已死去,像落叶,一片一片地。
沉睡在我心灵深处的,是你吗?我知道你走得最早走得最远了,小白花沿路枯萎,点缀在黑夜如许众多的暗影上,使黑夜更加黑得朦胧破碎:
有一种东西,死去了,
却要现在背负着,将来偿还着,
我是穿过“不”的丛林走来的,
常以飘落为生命的起始。
你是世界的光,
我却在黑暗里走。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 ----沈从文《论闻一多 死水》
●从明天开始,我要把所有书本合上,关掉门窗,从楼上下去,沿着一条幽僻的小路,独自一个,远行。看路边的风景,听自然的乐曲,和所有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说句话,献上我美好祝福。采撷一片树叶,做枚叶笛,吹出悠扬的曲子,和着轻快的脚步,去远方朝圣…… ----孙守名《六月,独自出门远行》
●月亮渐渐的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模模糊糊地哼着棉歌。
这是一条 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 ,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象 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 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象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以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小园幽僻少人来,
石径曲斜生碧苔。
纵使花开无人问,
自将香馥洗尘埃。
●历史, 本来就有一些永恒的话题重复而不老, 因为有人生。—有的人,生来就那样熟悉地陌生着,像语言、语调,从古说到今。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男女需要爱情,爱情需要理解。有许多事业,比较容易找到爱情的伴侣。例如,作者在塔希提碰到的勒内· 布吕诺船长和他的妻子,虽然他也怀着梦想,哪怕这梦想像上帝的伊甸园,也不过是人间的种植园,但这梦想本身恰恰是需要男女来共同实现的,于是,布吕诺和他妻子自然就像亚当和夏娃那样的相亲相爱了。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爱情,不是纯生理的动物式性欲,也不是因异性的某种外部特征而引起爱慕的性爱,它虽然包含着前两者,但更要求着人格的完整和向精神性的事业升华的超越能力。换句话说,爱情不仅要求在对方感受性爱的欢娱,而且要求在对方实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理想。最持久的审美情趣和理想,莫过于爱人的自由创造的对象化本质取得了超越自身的社会形态,它引起社会的尊重,并在这种社会的尊重中直观我的爱情本身,爱情获得了尊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情总是对一个时代的超越而具有永久青春的魅力。你可以追求它,但不能完满地得到它,因为爱情对自身也是超越,当你以为得到她时,她或许没有事业的果实而枯萎了,她或许有了事业的果实而不再是爱情的花朵。这或许是爱情的悲剧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吧。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微微轻寒春已半,流水潺潺草芽长。陌上新柳妆碧玉,篱外细雨杏花香。乳鸦啼春树,飞燕三两行,争得春色任自忙。最是小院幽僻处,风帘花影动,漫自调清商,曲曲绕梁,声声婉转,字字断肠。叠叠青山外,相望两茫茫,问斜阳,既是三生缘定,如何频添伤?既是相守无期,如何能相忘?
●性,是否使人堕落了?
或,是否使人获救了?
我知道这问题没意义,因为每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反例都很容易成立。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又决非毫无意义,似乎它的无所问总有所问。一般总把“性”放在“男女关系”中理解(汉语日常语言中的“男女关系”十分准确地直指“性关系”),而“男女关系”是人的“自然关系”,人的“自然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然尺度,“自然关系”的“自然”是怎样的,或“不自然即变态”是怎样的,便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病理学的首要问题。于是“性问题”随着“性关系”一下落入实证科学领域,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的统计对象、规范对象或教化、治疗对象:除了数字化,就是肯定、否定、矫正、治疗,等等。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真正惊人的美,会有一颗期求极高的心灵。它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这是它天赋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及其历史,就不会是一个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不断追求、不断创造的人的历史。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幽僻的森林之中,从来都不需要人的光顾。
●小居幽僻处,草树互为邻。
窗冷温情少,楼高寂寞深。
余花无意醒,倦鸟有心沉。
何许分三迳?相思仅一人。 ----李暮寒《幽居》
●然而有的事业,特别是那些需要坚强的个性才能独步生命堂奥的哲学和艺术,光凭外在的意志和毅力不够了,还要心智的专注敏锐和精神的穿透力,才能越过炼狱的狭口取回天帝的火种。这是天才的事业,因而他多半难于找到可以堪称爱情的伴侣。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这些我曾拥有的同如许众多暗影的交往,突然撒落了。只剩下文字在黑暗中萧瑟地飘摇。歌声还在,唤我在死去时的眷恋中醒来,树叶不动了,原来你已沉睡在我心灵深处,为了承诺“背负现在,偿还未来”。
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如果写出的文字没有永久地欠负
那它还不能不配已经表达的
或许
文字,只是一种葬礼吧 ----张志扬《幽僻处可有人行?》
●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