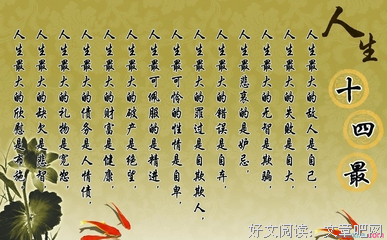●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墓碑上刻的一句话:过往的行人啊,请不要为我哀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都活不了!
●路人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如果我还活着,你就会死去。 ----罗伯斯庇尔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 ----永劫回归
●书是灵魂最好的麻醉剂 ----钱伯斯
●遇人不淑?
看看我们周围,不难发现,有些人换了若干家公司,角色永远是受气包,有些人换了若干个男朋友,角色永远是苦情女主角。为什么遇人不淑的总是她们?演员张静初在回应拒绝天价陪酒事件时,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什么样的气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所谓遇人不淑,可能只是因为你的气场正好吸引这样的人,甚至是激发了原本善良的人们心中藏得很深的那一点点恶。人人皆顽劣,谁都希望有机会能欺负一下别人。这个“别人”正好落到你的头上,因为你没有勇气像韦伯斯特或者张静初那样说“绝不”。
●只要提着正义之剑攻击,再柔弱的手臂也会力大无穷 ----韦伯斯特
●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不要为我哀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罗伯斯庇尔
●“你知道怎样对待死亡吗?”
“不管我们俩谁先死,另一个要到他的坟上去跳舞。” ----钱伯斯《在我的坟上起舞》
●生活就像是罗伯斯庇尔,因为它还活着,所以谁也别想好过。
●人们只会夸奖发明电脑的人与用电脑发光发热的人,站在荣誉榜上的永远是贾伯斯,是马云;很少人会记得电脑的贡献。做学问,切勿把自己变成了电脑,让自己去计算考证一些无限晦涩的事情,知识与思考终究要回到活生生的人身上。
●他们喜欢吉伦特派,却挑选了山岳派;他们决定了结局。他们朝成功者倾斜,将路易十六交给韦尔尼奥,将韦尔尼奥交给丹东,将丹东交给罗伯斯比尔,将罗伯斯比尔交给塔利安。他们将活着的马拉示众,将死去的马拉奉若神明。他们支持一切直到某一天推翻一切。他们最善于将摇摇欲坠的东西最后推倒。在他们看来,你根基深厚,他们才为你服务,你若摇摇欲坠,那就是对他们的背叛。他们是多数,他们是力量,他们是恐惧,由此产生公然的卑鄙行径。 ----雨果《九三年》
●任何人都无权让别人归属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简单: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遗憾的是,连开创《人权宣言》的法国精英们,也用鲜血对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婴儿。罗伯斯庇尔在杀人演讲中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美德、主权、人民”。其名言是:“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既然说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根据古希腊巴门尼德的理论,即正负之说,轻为正而重为负,那么人是应该选择轻还是重呢?而生命只有一次,同生命从未存在无半点区别。生命不同于物理实验,你不可能用实验验证假设,因为你没有时间。对轻与重的抉择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轨迹。那么永恒轮回后,事物的本质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事件不是为了反抗而发生,而是因为重演而存在。所以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不停出现,不断砍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有着无限的区别。
●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万能的。 ----韦伯斯特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评价卢梭)罗伯斯皮尔:我愿追随你那令人肃静的足迹前进,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在所不惜。在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为我们开创的艰险事业中,如果我能永远忠于您的著作给我的启示,我将感到幸福。 ----罗伯斯庇尔《哲学》
●我害怕的是,当爱无所不在时,或者在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中,却丧失了爱的感觉。 ----简·韦伯斯特《长腿叔叔》
●当卢梭推出“公意”的说法,这里的“民”,已经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个的个人的集合,而是美好和抽象的、非常虚幻的“人民”整体。而虚幻整体所拥有的权利,已经由罗伯斯比尔们,接着“人民”的名义在掌控和操纵。 ----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