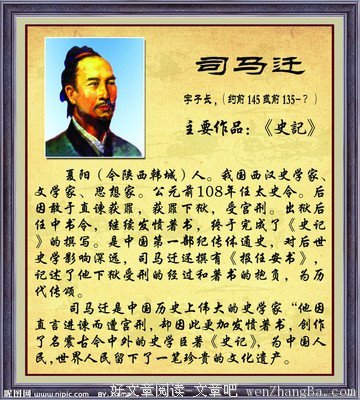●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
●东方朔是呗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席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易中天《汉武的帝国》
●道家有“存神养性”之法,然而“神无方而易无体”,神者生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神与形之间,神是生生不息之本,元元不灭之几,它与无方无体的“天德”有关。而形体则是神的依托、神的居所、神的活动空间的具体化。司马迁进而指出:“神使气,气就形”,这是说,神之“王令”是气,它空谷传信,以命四肢百骸,于是气血充塞了活的形体,一个绵绵神存、心物一元的血肉之躯融汇在天地之间。 ----《黄帝阴符经集注》
●聪以知远,明以察微 ----司马迁《史记》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 ----班固《汉书》 www.WENzhangba.com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司马迁《史记》
●娇生惯养是培养低能儿的摇篮,高山寒土使苍松翠柏更加挺拔。司马迁受宫刑,文章字字玑珠;李后主被囚禁,词境为之一新;唐明皇沉迷声色,导致生灵涂炭;成克杰腐化堕落,终于自取灭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是至理名言啊!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是在边缘,是卧底,是有不少闲有一点钱可以见佛杀佛见祖灭祖独立思考自由骂街,是被谪贬海南的苏轼望着一丝不挂的雌性女蛮人击水在海天一线,是被高力士陷害走出长安城门的李白脑海里总结着赵飞燕和杨玉环的五大共同特点,是被阉的司马迁暗暗下定决心没了阳具没了卵蛋也要牛逼千百年姓名永流传。 ----冯唐《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司马迁《西汉时期 司马迁 报任安书》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司马迁《史记》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司马迁《史记》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郑世平《身边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