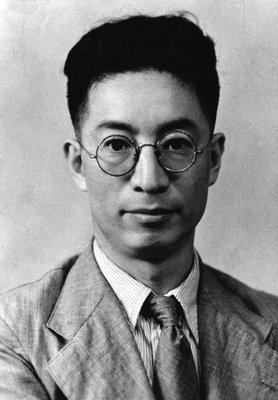《古道》是一本由[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道》读后感(一):路与思
交通方式深刻地型塑了人对时空的感知,通往上古时代的古道与以速度至上的现代交通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看似相反,但却像折叠的空间,始终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
铁路、公路只是为更快捷地穿过空间而被制造,像平面上连接两点的线段,人们只在意起点和终点,在那里空间像空气般隐没透明了,速度主宰着一切,空间沦为时间的附庸;而古道则是为了使空间重新凸出显现为它自身,它的广远无尽、它那单调得让人不寒而栗而又忍无可忍的空无一物,以及经过漫长行走感受到的茂盛葳蕤起来的时间和时间一并带来的无聊感,那里,空间不停地从四面八方“刺”入你体内,时间受到空间肘制而成为一种与被速度刻画的机械时间所完全不同的内在时间,就像柏格森说的,五分钟“理解”不了等待糖融化在水中的焦灼。
虽然现代人觉得路不过是始终敞开在那,可随时供人征用的东西。这可能是因为首先是人丧失了某种原始的单朴,进而路也受到腐坏。而古道则不同,它们原始单朴得还像条路,而路曾经是需要人维护、可隐藏或显现自身的东西,如潮汐路、时而被杂草吞没故而需要人在一头备好锄头的路等等。
那时,它们有着丰富而可爱的名字:朝圣路、林荫道、赶牲口之路、抬棺路、行兵路·····如此眼花缭乱的名称和千差万别的形貌及用途让人觉得单纯的“路”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但是它们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被订造成“风景”,即便是,也不过是牧羊人或抬棺人偶尔闲暇或放松下来,不经意地一瞥时才发生为风景,但绝不是某种现成的“持存”。
因此,相比于快速、枯燥乏味的铁路、公路来说,作为现代旅游业遗忘物的古老步道向来就不是给标准化游客预备的,它们以一种只诉诸于脚掌的“现象学丰富”忠诚地召唤并等待着浪游者、探险家和朝圣者。与其说是人选择路,毋宁说是路在挑选人。
古道既通向历史,也延伸近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向前走就是向后走,走向外部的同时也是交通内心。如果说步行与思想有着某种神启般的一致,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籍古道建立一种“生命地质学”,比如转山与灵魂超越,比如说“爱的交通”。
:作为政治家、登山者后裔的麦克法兰有着对自然十分健康、敏锐的直觉,夸张地说,我甚至觉得他继承了爱默生、梭罗的自然随笔传统,翻译更是上乘。恶岛、“悬人”、贡嘎山那几篇让人印象深刻。
《古道》读后感(二):行走
一位剑桥学者的行走散记。“写字和步行都是连续不断的动作,是一系列行动的针脚,始终不渝地前进在那一道接缝或水流中。”
关于行走、追溯的文字,无论虚构和写实,似乎都有种“向外走得越远,向内看得越深”的倾向,常常带着自省的意味。(此时想到了完全无关的《所罗门之歌》,一个美国的黑人男孩走了很远去寻根。)
步行,尤其是走上相当远的距离,并且发生在远离公路和人群的原野中的步行,似乎格外有种治疗和寻访内心的作用。双腿靠着肌肉的记忆机械运动向前,大脑就可尽情回访诗句和历史,或是仅仅辨识花草、听着云雀的晨间闹铃就好。
在现代化的路网系统下,步道编织出的网络仍遍布于大地之上——“pilgrim paths, green roads, drove roads, corpse roads, trods, leys, dykes, drongs, sarns, snickets”。“大声地、快速地读出路的名字,他们就成了一首诗或一种仪式”。作者的行走痕迹从英格兰到苏格兰(下海行了船),再到海外(差点爬了雪山),然后又回到英格兰,并重现了同样热爱行走的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生命的几个瞬间。在田野中徒步这件事情或许听起来是缺乏起伏单调如一的日记,但这本“探访内心”类的散文,丝毫不会有同样的感受被一再重复的感觉,读起来有诗意、真诚,且不失风趣。译者的好文笔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徒步旅行的标记者不仅有史前古墓前的石碑、古冢和长长的古坟,还有去年那灰白的树叶(在手心里一揉即碎),有昨夜狐狸的臭屁(鼻子里还臭烘烘的),有这分钟的鸟鸣(在耳中回旋)、有高压线、输电线塔抒情诗般的噼啪声,以及大田喷雾机的嘶嘶声。
”
人行道,本该是人类行走的道路,但你是否也会下意识地默认其为十字路口的斑马线?
必须走出城市,走进荒野,走进深山和森林,甚至迈进滩涂和泥沼,人类才能记起道路的初态。大地本身充满了文字、词语、文章、歌曲、标记和故事,道路带来的是本该是过程、情节,而非结果,是人类留下的踪迹,是历史残留和当今规划的共同载体。
《古道》是一本奇书,由剑桥学者罗伯特·麦克法伦2012年所作,他的研究和写作领域侧重于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二战之后的英美小说、当代诗歌和维多利亚时期文学,这是他类游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他行走于各种道途,言说这些道路和他自己的故事。他以爱德华·托马斯为精神偶像,在行走中理解哲人——包括他的抑郁症、以及短暂的从军生涯;也跟随伊恩、米盖尔、迪尔沃斯、安娜、谢泼德……各式各样热爱徒步领略自然奥义的怪咖们,在各式各样的地表留下自己追寻古径的脚步——
“宽阔海湾”号驶向苏拉岛,泛着绿色磷光的尾流就是他们在大海中留下的踪迹;马努斯岛上遍地的塘鹅翅膀,标记了岛民自古至今的生存手段;英格兰白垩纪区域的白色小道,留下了地质学和人文精神相互映照的踪迹;巴勒斯坦石灰岩地带,所谓的非法道路,印证着地理政治学的最新进展;贡嘎雪山下的盘山道路,夹杂在默默移动的冰川褶皱里,挑战了登顶的妄念,也宽容了转山者的虔诚谦卑……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当属布鲁姆道,早潮和晚潮之间的泥沼里似有如无的一条古径,软泥可能意味着危险,由扫帚、板条等农具构成最初的路标,至今无法在地图上标明,但至今仍是除了乘船外进出小岛的唯一方式。麦克法伦的行走始于浓雾,由很多海鸟陪伴,在最离奇的滩涂上痴迷于银色的镜面之路,将人同时带向大海和岸边……“明喻和暗喻孕育并发芽,比例的幻觉发生了,深度的骗局也发生了。”
风景(landscape)这个词源自荷兰语,本意是画。人类、艺术和理念彼此影响,最终,我们是被风景塑造的社会动物。我们和迁徙的鸟类、鱼类不完全一样,它们延续着亘古不变的空中、海中之路,而人类的道路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所以,几千年前的古道、刚刚落成的高速公路可以并线同行,彼此无法替代。
道路学,原来是这样一种人文哲思,是将哲学和文学覆盖到徒步远行的旅程中,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和艺术。当我们在麦克法伦的笔下读到露宿野外时听到的云雀叫声、沿途的野花和野兽,首先会被一种纯粹的、复古的自然主义之美所打动;其后,又能随着他追忆的诗歌、散文、绘画片段,洞察艺术家如何审视人类和地域之间的关系。
文/严杰夫
近年来,在都市白领中,徒步作为新的旅行方式慢慢流行起来。我们单位近些年来也“跟随潮流”,每年都会举办两次徒步活动。去年,出于好奇心,我也报名参加体验了一把。在印象中,徒步在流行之前,与登山一样,是一种必须具备一定专业技能和体质水平才能参与的活动项目。如今在经过改良以后,则几乎所有普通人都能染指。
不仅如此,流行于当今都市里的这些徒步项目,在宣传时还往往与所谓的古道联系起来。不过究其根本,这些徒步路线,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古道,却并不会有人去认真考证。所有参与过的人都清楚,这种渲染无非是给一趟枯燥徒步经历,增添上一份浪漫气息罢。有意思的是,有位英国作家也热衷于寻找古道并循之徒步,他就是罗伯特•麦克法伦。不仅如此,麦克法伦还把自己徒步的一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叫《古道》。
《古道》是麦克法伦“自然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心事如山》、《荒野之境》的题材与《古道》类似,讲的同样是登山或徒步过程中的经历和思考。正是由于这些作品都是围绕旅行展开,于是他也被视为新一代“旅行文学”的代表。
麦克法伦在自己的作品中似乎对于这样的身份和传承十分骄傲。作为英国文学研究者的他,自然比谁都清楚,“旅行文学”在英美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17世纪英国自世界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之后,几乎每一个英文作者甚至于许多艺术家,都留下了大量的“游记”。所以,在《古道》的开头,作者就写道,“看得越多,我越发现过去两百年间欧美的散文、诗歌和美术作品之中,有越多的小路与脚印穿针引线般相互串接”。这或许就是“引诱”麦克法伦走上追寻古道之路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古道》并不能就此被简单看成是一部游记。在麦克法伦的这趟旅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古道”,都如同最开始的那段伊克尼尔德小道,曾经被爱德华•托马斯这样的知名作家走过,或如同国内都市白领徒步的那些半真半假的古道,被无数人踏过。在他的这本书中,有些古道是远古时期古人行走的小道,如今常常被淹没在海水之中,很少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行走;有些道路更是可以追溯到白垩纪时期,是动物行走的路,更是早被遗忘在布满水泥、沥青制成的高速道路的现代世界之外。这样来看,麦克法伦的《古道》虽然也是在讲述旅行,却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这些徒步之旅来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麦克法伦写道,“脚步是看待大地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脚步成为人类触觉之中重要的感知渠道,同时又超越了触觉本身。通过脚步,徒步者与自然实现了交互和沟通,反而更深刻地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行走能够提升视力和思想,而不是鼓励退却和逃避”。麦克法伦自己就常常在行走过程中脱去鞋袜,直接用脚底去感知不同古道表面的土壤,实现与其的交流。
通过与古道的交流,徒步者不仅延生了对自然空间的认识,还拓展了对时间的理解。古道两边的景观随着时间而变化,“人一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哲语同样适用于行走。所以,当我们再次踏上曾途经过的道路,常常会发觉周遭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对于麦克法伦来说,行走不只是为了体验这种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重现记忆中的画面。他写道,“有一些景观,即便我们离开了现场也会跟随着我们,这些地方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即便事实上它们早已从眼前消失。”
麦克法伦借助巴勒斯坦之行来解说上述这种晦涩的哲思。他是在巴勒斯坦作家拉贾•谢哈德的陪伴下完成这趟旅行的。事实上,由于不是当地人,麦克法伦很难对巴勒斯坦本地景观的改变,产生太多直观感受。他更多的是依靠谢哈德以及徒步过程中碰到的一个巴勒斯坦家族的回忆,与自己的亲眼所见之间的差异,来完成这种想象。
有意思的是,谢哈德自己就是一位作家和徒步爱好者。在他的《漫步巴勒斯坦》中,就曾对麦克法伦行走的荒野之路的变迁,做过有力的描述:曾经那块“流着奶与蜜的土地”,如今在以巴战争的蹂躏下,被铁丝网分割成无数碎片;更令人痛心的是,今天想要在那些古道上放松地行走、散步,已经成为一种奢望。谢哈德的“漫步”于是便成为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
在《古道》里,麦克法伦尽管无法对谢哈德的这种苦闷,产生同样程度的感触,却也直面到了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打击。这种打击不止存在于当下的日常,更是触及到了过往的回忆:人们越是拥有美好的记忆,现实的残酷带来的打击就越是惨烈。
就是这样,在《古道》里,麦克法伦似乎有了某种魔力。他让那些在旅行中常见的石头、草木和空气,都有了讲述的欲望,从而对着行人诉说起一个个意味深长的古老传说。就是这样,借助行走,麦克法伦穿越于不同地域、文化和时空之间;依靠脚掌,他又感受着其中曾经或正在发生的喜怒哀乐。
麦克法伦用自己细腻的文字和感触,在展现了一段段精彩的旅行的同时,也构建起一个现代都市之外鲜为人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魅力,并不亚于凡尔纳等伟大作家曾经虚构出的那些地心世界或神秘岛。正如作者自己写道的那样,“想象禁不住追随大地上的线条——空间上向前,时间上则向后,去探寻一条路的历史和它先前的行路人。”
《古道》读后感(五):“我行故我在”麦克法伦 ——追寻自我起源的旅行
文|张德明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网络世界,试图以刷屏、网游、QQ聊天来寻求生命刺激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选择了走出家门,以脚丈量大地,通过亲近自然来感悟人生,发现自我。如果他们知道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一个英国人不但已经先于他们踏上了同样的征程,而且还让思想融入大地,脚印汇入古道,将行走的感悟形成了优雅的文字,他们是否会有相见恨晚之感,必欲一读而后快,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类似的写作冲动呢?
在我看来,罗伯特·麦克法伦是当代英国旅行作家中最为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思想的。翻开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之《古道》,没读上几页,你就会被他的优雅、精准,又极富想象力的文字所吸引,忍不住一口气读完。书中的每个描述和比喻——无论是对自然的观察,还是对身体感觉和心情的描述,都恰到好处,犹如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摸准静脉,一针下去,马上就抽出一管鲜红的血来。
精准、优雅的文字背后其实有着一个强大的旅行写作传统。与地球上别的民族相比,英国人似乎特别好动,热衷于航海、探险、拓疆、殖民。这或许跟其祖先维京海盗的血统不无关系。对未知空间的探索癖曾造就过一个横跨欧、亚、非、美的庞大帝国,也塑造了不列颠民族整体的文化人格。尽管帝国的余晖早已淡入历史,但敢于探索、精于观察、勤于记录和乐于表述的传统却深入了每个英国人的骨髓,积淀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纵观英国文学史,从公元15世纪曼德维尔爵士写下他的著名的《游记》算起,几乎没有哪位英国作家不曾有过长途旅行的经历,不曾写过或真实或虚构,或散文或诗体的游记或历险记。这些作品,或叙述作者本人孤身踏入陌生异域的见闻;或记录同行者的言谈性格和奇闻轶事,感悟朝圣路上的神迹和启示;或见证不同民族和族群的风俗,为其后传教士、旅行家和外交官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些至今依然是大英博物馆的珍品。
与其前辈作家相比,麦克法伦的《古道》一书自有其特色和亮点。作为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当代人,作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自然与自我这两大主题上,将步行视为联结人与地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介。正如作者在题注中说:“这是一本关于人和地的书:关乎步行作为一种寻访内心世界的方式,关乎我们走过的风景塑造我们的各种微妙方式。”对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提醒。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大规模压缩了时空,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忘记了存在的本根——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们几乎无需借助步行,便可实现无缝对接,坐飞机到机场,换乘地铁,再换乘公交或出租车到家;到旅游景点,选择方便快捷的自驾游,至多在后备厢里放上一辆折叠自行车。不知不觉间,我们和大地之间隔了一层坚硬的人工制造物。但我们认为这一切皆理所当然,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殊不知,就在脚的功能被遗忘的同时,本真的存在也正在陷入沉沦。
读麦克法伦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形而下的身体,还有脚——脚底板、脚趾、小腿、膝盖、大腿、腰椎、背脊、肋骨、肩膀;它们与我们的血管、神经、大脑紧密相连;它们会起泡,会疼痛,会淤血,会受伤,会断裂,会流血,进而会影响我们的感觉、情绪、情感、思维和判断力。原来,存在并不如笛卡儿所说的只是头脑中的“思”,而且还有身体中的“感”,并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微妙的感性;“我思故我在”应改为“我行故我思”。道路不是“思”出来的,而是“行”出来的。脚印就是写在大地上的文字,一个个道路之名连起来就是一首诗,甚至一部史诗,它叙述的是人类从古至今与大地对抗、妥协、默契、融合的历史。由此,麦克法伦抬高了“脚”的地位,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旅行文学以“头”为主的传统。请看这段告白:
“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
据我所知,在麦克法伦之前,还没有哪位旅行作家斗胆将自己的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但他以自己的行走体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脚具有这个地位当之无愧。脚给予我们方向感,让我们在胎儿时就在黑暗的子宫中摸索旋转,犹如宇航员在太空中为自己定位;脚给予我们道路,古道就是古人以自己的脚一步步丈量、踏勘出来的;脚给予我们合作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人类默契和团队协作的产物。一个人不可能创造出一条道路来。悠远的古道与城市马路、乡村公路、高速公路互相叠加,相交,重合,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路网,而人类的历史就存在于这张网络之中,也必将在这网络上延伸、扩展,并且不断继写、改写或重写自己的历史。
《古道》中,作家多次强调了他脱下鞋子和袜子,光脚走在古道上,翻越沟壑,攀登悬崖,触摸冰雪、淤泥和沼泽时的感觉和记忆。“对于我曾经赤脚走过的地方,我的记忆如果未必是更佳的话,那至少是和我穿鞋走过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主要能回想起它们的质地,对它们的感受,硬度、平整度和坡度——一处风景给人们触觉上的细节,而这些都经常不注意就溜走了。它们才是持久的无法磨灭的记忆,这些脚注,来自徒步者的肌肤与大地的肌肤的亲密接触……赤脚走路,你能清晰而敏锐地感觉到风景给予你的某种意外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也就是“走”进去,走向大地也就是走向自我,感知风景也就是感知生命。于是,通过形而下的身体感知,被遗忘的存在又回来了。
借助麦克法伦的脚步,我们仿佛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新鲜的、以往不曾见过的自然景物,恢复了因熟知而忽视、因忽视而麻木的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动觉。全书中随处可见意象派诗歌式的句子,精准地描述了景观的样貌及其对感官、心灵的影响:“雪在街灯圆锥形橙红色光带里落下来,像炉火里的火星一般闪耀”;“空气颗粒粗糙,忽隐忽现,仿佛老旧的纪实短片”;“赤脚踩在滑溜溜的黏土上很舒服,而每走一步淤泥都会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油腻如同黄油”。当思想变成了知觉,景观影响了情感,人的心灵自身的物质也被改变了。作家变得更加达观、强健,活力充沛,知觉敏锐,思维活跃而想象力丰富。
全书从追随爱德华·托马斯的伊克尼尔克小道出发,经历了在英格兰觅踪,在苏格兰寻踪,在海外漫游,最终以返回英格兰为终,圆满地画了个句号,犹如一部当代版荷马史诗《奥德赛》。而从书中所涉及的考古学、矿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来看,又好似一部包罗万象的诗性百科全书。作家从描述自己的脚码尺寸开始,最后让自己的脚印与另一只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脚印相遇和重合。“我在那名男子的最后一只脚印那儿停下来,那个五千年前留下的脚印啊,我的道路也停在了他停止的地方。我转过头,顺着自己走来的脚印朝南看。太阳再次透过云层斜射下来,忽然间,那些填满了水的脚印变成了一面面镜子,辉映着蓝天、微微颤抖的云朵,还有朝里面观看的那个人。”
至此,作家的自我形象与远古人类的形象合为一体,而追踪古道的行程,最终则成了追寻自我起源和本真生命的旅行。
(张德明,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西方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等)
《古道》读后感(六):行走,思考,在路上
罗伯特·麦克法伦
(Robert Macfarlane)出生于1976年,他的研究和写作领域侧重于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二战之后的英美小说、当代诗歌和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等。《格兰塔》前主编弗里曼称他为当代最好的行走文学作家。
我们穿透风景,在风景中寻找更美的世界;风景也穿透我们,让我们发现未知的自己。旅行的本质是获得对世界新的认识,为自身赋予新的意义。罗伯特·麦克法伦向读者描画风景对心灵的塑造作用,他的代表作“行走文学三部曲”(《心事如山》、《荒野之境》、《古道》),目前在国内已经翻译了两本,同时其新作《Landmarks》也刚刚出版。
“步行不仅是寻访风景,也是寻访内心”
《心事如山》讲述了人们对山的经验如何形成、继承、再形成并且延续至今。从地质学的认识到“崇高说”的创立,山峰在人们眼中越发清晰。地质学的发展让山有了穿透时间的意涵,注视高山仿佛能看到过往千百万年时光的痕迹。对崇高的审美潮流让人们迷恋高山带来的险境想象,身居高山体验到的惊人之美无法形容,濒临绝境可以带来“可怕的喜悦”和“危险的至福”,所以人们不满足,渴望亲自踏寻,在二十世纪征服了最著名的几座高峰,随后又因为生态观的发展转向对山的敬畏。
这本书讲述了众多攀登者的故事。马洛里登山是“因为山在那里”。去世75年后,他的尸体才在珠峰被找到,依然保存完好,坚硬如石,仿佛印证了他生前“像希腊雕塑”的赞誉。这是一本关于山之爱的书,在最极端最严苛的气候条件下,一切浪漫想象都被消解,人只能独自面对自身,勇气与懦弱、决绝与犹疑、登顶与失足就在生死一线间。
《荒野之境》是麦克法伦在英国埃塞克斯寻找荒野的过程与思考,并被BBC制作成纪录片,他亲自出镜主持。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只要我们学会寻找,就能发现这里依然存留着曾经的蛮荒气息。麦克法伦从内心出发,重新定义荒地对人类的意涵。
行走,思考,在路上。随着麦克法伦步伐的延伸,诞生出万般思绪,它们汇集成为《古道》。题注说:“这是一本关于人和地的书:关乎步行作为一种寻访内心世界的方式,关乎我们走过的风景塑造我们的各种微妙方式”。步行不仅是寻访风景,也是寻访内心。更重要的,是寻找风景如何塑造了我们自己。麦克法伦的脚步是踏实的,目光是平视的,每一次寻访都留下深深的印痕。他抛开工业化的便捷形式,徒步走入自然,注视着每一步行走时映入眼帘的风景,巨细靡遗地描绘它们,用文字让读者感受步伐带来的“从前慢”。
古道所代表的风景如何影响并塑造着我们?道路之“古”,引发了步行者的思古之幽。我们感悟到道路的召唤,然后出发。我们愿意踏足,是因为某些神秘力量的驱使,它们借由我们延续对古道的叙事。世界各地的古道旅行者,因环境而为步行赋予各自不同的意义。这同样可以解释一切风景对我们加诸的影响。
“书写天然未雕饰的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丽贝卡·索尔尼的《浪游之歌》是一部系统讲述步行历史的随笔集,有城市的游荡家,也有荒野的探险者。她在其中对行走的定义很精当:“行走的历史是一部没有书写过的神秘历史……在大部分时间,走路只是一种实际需求,是衔接两地间最自然的移动方式。将行走归类于一项探索、一种仪式、一类沉思,乃属于行走历史中特殊的一支……但在哲学意境上则迥然不同……行走的历史是一种业余性质的历史。行走闯入各个领域,包括解剖学、人类学、建筑、园艺、地理、政治与文化史、文学、两性,乃至宗教研究领域,而且行行重行行,并不在任何上述领域中驻足”。
蒂姆·迪在《超自然:麦克法伦和新自然写作》中将麦克法伦放在自然写作的传统中考察:“英国的自然写作大多关乎乡村,包括景致与风物,属于非虚构、非科学性的散文体裁,特征是会细致地观察活物,作者对有生命的东西是了解的,而且非常喜爱”,并赋予他独特的位置:“他描绘出一段迷人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张有关流行潮流与大众思想的地图”。他的书秉承了“自然写作”的传统——它们书写天然未雕饰的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约翰·缪尔是著名的开创者和实践家,因为亲自涉足才能真实感受。他写过很多相关的书,如《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夏日走过山间》、《我们的国家公园》等。
“那个五千年前的脚印啊,我的道路停止在他停止的地方”
在我看来,麦克法伦虽然被《格兰塔》誉为“当代最好的行走文学家”,但他的书和大众旅行文学并不太相同,和“自然写作”注目于自然本体的风格也略有区别。旅行是将自己抛入陌生之境,因此旅行文学永远有一种不稳定的“在路上”之感,这让它显出临时性。旅者因为偶然的机缘身处某地,他们不可能看到该地的全部面貌,只能记录下瞬间的经历与感受。要如何拓展和纵深旅者对在地的经验?这就需要引入大量的外部叙述,或是前人的书籍,或是对在地人士的采访。旅行书写的主体并非旅者的旅行过程,而是旅者带着问题去当地寻觅答案,这让旅行变成一次次探询,也让旅行文学与旅行的关系变得模糊。它不仅是旅行,也不仅书写风景,麦克法伦的书更具人文性,从自然回到社会,寻找旅行背后更牢靠的东西。
麦克法伦阐述风景如何塑造心灵,他不是将自己抛入陌生的世界中去碰撞、去偶遇,他已经有所准备,将前人带入自身印象,邀请行家朋友加入旅行之途。他的实地探访,不是未知前路的旅行,而是对他人经验的验证,并由此生发出自己的新体验。眼前的景观蕴含着意义,似乎在向旅者诉说,可临居于此的旅者无法解读,于是麦克法伦将它们翻译出来,让文字醇厚而饱满。他将使命感带入旅行:不单让读者看到新奇的世界,更是一种修行——通过旅行,我们发现陌生的前人和自己的相通之处,也发现了世界在变化与恒定间的无言规律,这让我们感到被理解,感到不再孤单。
这类旅行作家如简·莫里斯、V.S.奈保尔、保罗·索鲁等,往往具有资深的在地探访经验。简·莫里斯通过几十年当记者的经历,目睹风景之外的历史和时事,这就让她的旅行书写有了分量。《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和《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都是不局限于旅行记录的报道文学。《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和《欧洲五十年:一卷印象集》更是集大成的总结。如果说麦克法伦是书斋学者,通过阅读前人的著作诠释自身的旅行印象;那么莫里斯就是果敢的实践家,通过对时事的报道让旅行产生游览之外的意义。
我们阅读这类书籍,得以接近更广阔的自然,并通过更多元的经验开阔我们的心灵。这就像《古道》的结尾所言:“那个五千年前的脚印啊,我的道路停止在他停止的地方”,这是对麦克法伦风格的最好比喻,也是我们与他接近的方式。他的脚印和五千年前的脚印相遇,交错辉映出新的认识;他将自身的实践和前人的思考结合在一起,接触、对话,并继续前行,同时他也加入其中,通过文字成为新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