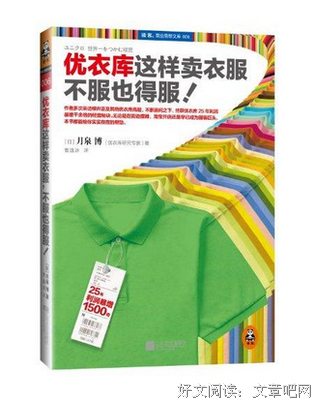《做衣服》是一本由[日] 山本耀司著作,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做衣服》读后感(一):山本耀司杀死山本耀司
山本耀司隔三差五的会在朋友圈火一阵。上一次大火的时候,是他在视频中说,不自己买单的女性都是bitch。很多人都在转,或拍掌称赞,或冷嘲热讽。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理解,[让女性逃离由男性决定的“女性化”]的真正含义。他盛扬独立女性精神,为独立女性制衣。这种制作理念多少来自其母亲的启迪。一是他的生母,即生养者母亲,一为文化哺育者母亲。
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三宅一生是日式风格走向国际的代表设计师。固然日本文化是山本耀司灵感的沃土,但另一个城市,巴黎,也不失为山本耀司灵性上的母亲。
1965年,靠着母亲的接济和打工时的积蓄,22岁的法律系毕业生山本耀司前往欧洲旅游。他与同伴横跨西伯利亚,到达芬兰,辗转其他城市,都颇感乏味。直抵达巴黎,那种气味、尘嚣、人与人之间的嘈杂瞬间就抓住了他。
四年后,他拿着服饰杂志《装苑》的设计奖学金前往巴黎游学。在法国时装界处处碰壁后,山本耀司日渐沉迷于皮加勒红灯区。最后出于对精神问题的担忧,他逃离一般的回到了日本。在《做衣服》一书中,这段经历被命名为《绝望的巴黎》,但是在结尾的时候,他却写道,[巴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femme fatale,宿命般的女人,令我迷恋其中,不可自拔。]
山本耀司对巴黎狂热的爱情,终于在他38岁的时候得到了热烈回应。1982年十月,他在巴黎时装周上展出了次年春夏服装设计。伸展台搭建在卢浮宫的中庭,是巴黎时装发布会的主会场。展出服装以黑色基调居多,随意地在一些地方开了洞,松松地包裹住身体,款式简洁,颜色肃穆。这种不同于以往成衣的价值观与美感,在西方时尚界投下一枚炸弹。山本耀司名声大噪,西方人给他和同时参展的川久保玲一个固定的称谓,Le japonais,日本人的复数形式。
巴黎给了山本耀司关于自由的灵感,关于混乱感的美学体验,也给了山本耀司做山本耀司的机遇。毫不夸张的说,山本耀司是在巴黎才真正登上世界舞台的,也是在巴黎的那些秀,成就了他的声名,也让他遇到另一位femme fatale,Pina Bausch。在遇到皮娜之前,山本耀司为理想中的女性制衣,遇到皮娜之后,为皮娜制衣。但皮娜不是典型的巴黎女子,山本耀司热爱的也非典型的巴黎。
我去过巴黎两次,却没有去寻找他的店,倒是逛了很多二手杂货店。从逛店中,我突然察觉,巴黎与伦敦有种吊诡的差异。山本耀司说,巴黎就像一个荡妇,充满诱惑。这说得没错,巴黎是不惧放浪形骸做个荡妇的。而伦敦的腔调却是守规矩。
我在伦敦也逛店,常常去Liberty (伦敦利伯提百货 )。三楼有个复古店,店主是个gay,有着修长的脖子,一张俊美的脸,穿着燕尾服。尽管他后来知道我全名,但每次也都还是像老式管家一样,喊我Lady Luo。
他家主营1920s到1960s的款式,时代没有损害衣物的美貌,那些衣服依旧保持良好,可以得知是教养优良的女士留下的,第一她们华裳无数,可能没怎么穿,第二也透露着爱惜东西的优良作风。
店主帮我挑了几件相当优雅的款式,但好看归好看,却都比我size要大很多,最终连他都放弃了。可我还是忍不住往哪里跑啊,有时买个丝带,有时买个耳夹,相对那些衣服,这些配饰的价格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一度很紧张,心想他大概会背后翻我很多白眼。
后来因为忙于去其他地方探索,有一个多月没有去liberty,见到后,他淡淡地说,“来了好几件新衣服,你要不要欣赏一下”。从那以后,我就突然厚起了脸皮,每次都去那里欣赏一下衣服,真的是欣赏,我站在那里,隔着透明罩看着裙子,他呢,就拿着鸡毛小毯子,扫扫帽子。
在伦敦人眼中,所有不节制的表达都是低劣的。但巴黎人不同,哪怕你一件也没有买,哪怕知道你不过是个路过的旅人,巴黎的店主也要在你离店前,拥抱你,然后说下次再来吧!哪有下次呢?但巴黎人不会想那么多,他们更在意此刻。
法语法语里有个词叫 “ici maintenant”,就是讲此刻。这歌词也是山本耀司美学概念的关键。因为懂得永恒不可得,因此保持对当下的在场,聚精会神,灵光四溅,就是当下反哺的恩惠。这不正是兴起于法国的存在主义精髓所在吗?
伦敦的含蓄,其实与山本耀司的不少理念相符合,但山本耀司美学要反对的时装语言体系正是伦敦式的。在谈到音乐的时候,山本耀司说过,披头士过于设计。是啊,过于得体,过于规矩。那不正是一个充满叛逆人格不能忍受的局面吗?他注定不属于那种被规训后的美学。
巴黎的热情是山本耀司讨厌的无间距,但巴黎却又带着他热烈拥抱的美学样本。大面积流行在巴黎似乎不可能。就连同是卖二手服饰店也不同,伦敦就鸡贼很多,很多复古款服饰全部都有批量式的生产。这正是山本耀司反对的无个性。虽然山本耀司的衣服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看上去不是来自一条流水线。简单而富有想象力的细节和复杂的剪裁,它们是随意和年轻的,巴黎的叛逆叛逆恰好是这种复杂态度的基调。除了叛逆,他还截取了巴黎最忧伤的部分,大量丧服版的剪裁,带着一种日本人对生命力的独特缅怀。美及其转瞬易逝的标本。这又回到ici maintenant去了。
在伦敦时,我去逛过山本耀司好朋友川久保玲的店,陈列了很多不实用但很有概念的服装,称之为实验服装陈列室也并无差错。里面充满有型的店员,但毫无撞款。部分店员本身就是小设计师,有一个涂着黑嘴唇的直男,留着金发齐刘海bob头,简直是妖孽在世。香港演员黄秋生也在逛店,店员远远地看着他挑衣服。
那天我穿得规规矩矩,Burberry浅棕色斗篷款风衣,拎着香奈儿的Leboy,踩着Valentino爆款。店员打量我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剧烈的窘迫。我觉得自己就是媚俗本身,或者说墨守成规就是媚俗本身。从那天开始起,我不太买品牌标识过于明确的衣物了。
一个UCL建筑系毕业的朋友告诉我,建筑即处理人与空间space的关系,所以服饰也是建筑。我猜山本耀司也是这样想的,他追求服装与人体之间的间隙,微妙的、充满东方禅意的间隙可以让空气在服装和身体之间自由流动。在山本耀司设计的服装中,有“间”,就像“字里行间”的“间”。
说来好笑,有人说穿山本耀司的女人看起来没人爱,这恰恰是山本耀司做男装的由头,他希望有与独立女性匹配的男性存在。这恰恰又是山本耀司对职业女性的一种宽悯。
还没有一个城市,像巴黎那样叛逆。山本耀司不止一次表示过他爱巴黎的自由。在我看来,正是对巴黎复杂的爱情,让山本耀司保持着终生叛逆,寻求突破。
上周四,山本耀司在巴黎的春夏大秀落下了帷幕。这个曾以大量运用黑色而为人知的男人,这一次他却讲图案印刷与织物之间的巧妙结合,融入更多印花,将统一的少量色调转移到多个色调的丰富组合上来。
人们说,山本耀司不再是他自己。
可我觉得山本耀司杀死山本耀司,才是山本耀司。
正如他说,[创造事物,本身就破坏事物。 打破现已存在的事物,让它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当然包括破坏一切,包括自我,方能再次创造新的自我。
涅槃重生,大抵如此。
《做衣服》读后感(二):此时,此地
如果想了解山本耀司这个人,可以去读这本书,然后通过这本书给的线索,去读他狂推的书、音乐例如坂口安吾的《堕落论》、鲍勃迪伦等等。
谈谈他的美学观
了解一个能够具有传播力的艺术家的美学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是很私密很自我的东西。
形式是”破坏后重立“。开篇他就说"人云亦云的流行并非趋势,我们并需拥有驾驭时装,赋时装以神韵的力量“,后一句听起来挺玄乎的,但是独创性和自我带来的美感,在山本眼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就更加直白地表述:”我认为创造事物本身就是破坏事物,完美是丑陋的,完美是秩序和和谐的呈现,是强制力的结果,自由的人类不会期望这样的东西“。这是山本的哲学。事实也是如此,大家都在渴求完美的自己和别人,但是不完美的人才是可爱真实的。所以山本自己的理解是自由,我的理解是真实。
真实也体现在他注重面料本身的质感而非纯粹的花色。“通过裁剪的不同来体现面料本身的质感,充分利用布料的特性来展现服装的个性”,面料本身的质感,读来觉得他在说面料本身的灵魂呢。我们的视觉,可能第一冲击是色彩、形状,然而当风飘过来,当它被人穿在身上,随着人的停止、行走开始变化,的确是令人着迷的,仿若看到了灵魂的形状。
对于穿上衣服的”人“,才是他剪裁出各种衣服想要做的真正表达。在我理解中,他所爱的特质才是真正他的美学的构成。本书中专门两章来写的,是他的母亲。作为一个父亲早年战死沙场的孩子,母亲扮演的角色对于他的成长一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母亲非常坚强,没有重新嫁人,而是重新学习做衣服来承担起抚养他的责任,每天工作到深夜,会有坏情绪,他虽然对这种选择颇有微词,却也是理解的”对于她来说,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不仅仅有一种使命感,还有一种坚韧的持之以恒的悲壮感“。之后也有去上庆应大学是报答母亲的意思。其中有一段关于高跟鞋的,他有这样一段描述:“就在这个歌舞伎町,我家旁边有间公共电话亭,又一次我见到一个妓女模样的女人在打电话,她只穿一件吊带裙,说话嗲声嗲气,似乎是在给客人打电话。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高跟鞋,和因为穿着高跟鞋而赫然隆起的小腿肌肉。””我一直以为女性穿着平底鞋自然地行走,才是最美的。“
所以母亲对他看待女性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依赖男人,坚强独立的职业女性在他看来是最美的。所以最喜欢的面料是用来做工作服的华达,喜欢黑色,具体的女性形象是“吸着烟,头发随风飘起,用沙哑的嗓音说'我呢,放弃了做女人‘“这是他心中的缪斯。帅的男性是”有担当肯舍命“的。
我一直以来的美学观都要有力量的存在。孱弱无坚持就像软趴趴的稀泥一样。山本可能也一样吧,从小就开始学柔道,开始强壮自己去和软弱做斗争。他母亲,又何尝不是呢?
一句俗语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贴身合体的西方服装流行欧美的时候,山本的”间“的美学传达着日本文化的精髓。遮掩着身材,而非完美的包裹,会让空气在身体和衣服之间微妙的流动。他用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大抵上,优秀的音乐作品,都在节奏上时而有零点几秒的延迟,时而又快出那么一点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合规矩,但这就是我非常看重的”间“。心领神会。
我觉得山本耀司很坦诚。
“我是个不喜欢刻意为之的人。我很难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像是要将自己不经意被触动而灵光乍现的瞬间表现出来。法语里有个词叫‘ici et maintenant’,意思是‘此时,此地’,这种感觉非常重要。””
山本耀司《做衣服》
褪去外界的光环,大师的身影,通过《做衣服》这本书冷静而又质朴的叙述,缓缓向我们走来。
山本耀司,时尚界的一代宗师。从最初的不被接纳,到后来成为巴黎时装界最受尊重的设计师之一,这位出身平凡的日本小个子男人,以命相抵,制作服装。向我们诠释了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热爱一件事情。
这本书以山本的自述开始,以回答采访问题结束,向我们讲述了设计师的童年、少年、以及成年之后影响他成为服装设计师的一连串偶然因素,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才有了他注定成为大师的必然。
日本人在我们眼里,一向是冷静、克制的形象,山本耀司也不例外,但在冷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炙热的灵魂。他所注重的此时此地的感觉,正是善待生命的秘籍。
见过太多挣扎在过去的漩涡里不肯走出来,或者过分憧憬未来却从不行动的人,现实中能够享受此时此刻专注当下的人,差不多已是凤毛麟角,让我对山本又多了一份尊敬。
当下,是生命停留在这一秒的状态,是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所谓锦绣山河就藏在你眼前的那杯茶中,当下的一切,皆是决定命运的万水千山。
活在当下,是有智慧的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过去已经逝去,未来总会死去,那还有什么是永恒?佛说,刹那既是永恒,转瞬即逝的瞬间是相机胶卷里的永恒。
活在当下,感受血液的流动。感受时间,从身体里穿过。过去、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感受这一秒的状态,享受此时此刻完整的你。
活在当下,不去透支未来的绝望。人总要长大,总要面对生离死别,最后赤裸着离开这个世界。若福报不够,还会带着病痛挣扎着离去。离去后灵魂怎么安放?这一连串消极的问题,如果不停追问,就会陷入绝望的没有答案的死循环。幸福的人,从来不和自己较劲。

活在当下,上帝的恩宠和世俗的荣耀并不冲突。
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享受这一刻的美好,时刻保持谦虚,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宝贵的知识,就是对平凡生命最好的馈赠。
《做衣服》,先做了,才有衣服。几十年和一日并没有本质区别,山本耀司传递给我们的精髓,就是这八个字:
活在当下,动手去做。
《做衣服》读后感(四):在荒谬的世界中复杂的生活
如何在交错的时间和空间集合-人类社会中驾驭自己,这种问题是我始终在探寻的。 山本耀司,一位被尊称为世界级大师的服装设计师。最初由Adidas的支线品牌Y3听到他的名字,这位有着性感长发的大叔就一直吸引着我。他神秘的气质终究使我买下这本《做衣服》,全书分背影、百问、如何做衣服三部分。 背影 这部分由连载于《读卖新闻》的《时代的见证者》改编。 就像和耀司两人促膝长谈,顺畅读下来,果然发现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 身无分文,在独身公寓中开始创作的人,这是耀司对新时代年轻设计师的期望,与他在东京新宿歌舞伎町出生成长向呼应,从无到有一步一步脚踩实地走起来的人,从只身一人直到改变整个世界的人,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着而且作为理想的未来状态。 从前我总觉得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生活一定混乱不堪充满矛盾,而那些成就满满能在社会中拥有一定地位的人,都有自己清晰的行事方法,是更纯粹的人。 耀司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荒谬的世界随处便充斥着矛盾,而正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将无数看似相悖的东西堆砌,造就了每个复杂的个体,其中能更合理的分配这一切还被命运眷顾的,便触碰到了成功。 他还总结了一个我一直有所感受却无法准确描述的问题。要运用起有限的时间来,尽力和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东西碰撞。有高才有低,有热才有冷,只有在不断和真实的事物、高水准的事物碰撞下,反弹回来,才能更加了解真实的自己。 关于他谈到的反抗运动,我是个喜欢hiphop的人,也算是反主流文化的支持者,书中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反抗到合作的转变,流动的时间里,没有什么权威是永久不变的。在反抗的最初,只有一少部分对权威持有疑问的人会接受,接着扩大反抗后投射出新的角度,新的思考方式,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反抗就实现了合作。 如果谈谈和他不同的观点,要穿经得起时间流逝的衣服,快时尚品牌充斥的今天,穿着廉价快时尚便失去了个性,这点我还是不怎么认同的,自然能穿起考究的服装是我所期望的,但这样凝聚了设计师和制作者心血的一件高级成衣也是价格不菲的,在大部分人还在为了活下去而奔波的社会里,未免真的有些不现实。如果说确实这样失去了个性,那也是生活无奈所迫。 要是再说起耀司所迷恋的那种抽着烟的独立女性,确实很令人神往啊。 百问 这部分中的一百个问题遍及了从浅显无聊到深奥繁杂的回答。 说下最喜欢的两个。 一是在问到早晨几点起床时,耀司说七点起床吃早餐后再睡个回笼觉,再起床大概十点钟,让我想到了之前看《挪威的森林》的时候,男主的生活,有需要努力坚持的时期,有放松娱乐充斥欢笑的时期,平时在公交车上就可以随意拿着自己喜欢的书籍抓紧时间阅读,该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想哭的时候放声大哭。成熟的人并不是完美无缺,洁白无瑕的,也不是只向着一个目标没日没夜闷头苦干的,而是在该干什么的时候就能马上去做,生活丰富而没有拖延症的。 二是在问到政治方面的问题时,他说他被骗了,或者他就是个傻瓜。理论上来说每个同龄人,所活过的时间是相同的,但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却各不相同呢,除了由于经济基础高直接“买”来的时间之外,还有对时间的管理和利用也是关键。在时间相同的基础下,对它不同的利用才形成了现在的自己。要是做某件事时你发现你和身边人完全不能相较,别担心,你一定也有他比不上的地方。人无完人,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我们也只需要在自己必须做和感兴趣的领域继续钻研下去就没问题。 总之这部分,让我更加了解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为人的耀司,而不是经过神化的遥不可及的大师。 如何做衣服 源自每个真实的探寻,发觉隐藏着的美。 那种每次制作新一季成衣的过程,在耀司手下更像是只有一个代号却没有明确目的的探险,他带着自己的助手深入衣料的深谷,由于敏锐的第六感,每次他们总能满载而归。 纵观本书,确实是本旁人了解耀司不错的读物,书页上下左右留白都是十分多的,我认为这是为了和他本人所倡导的日本“间”文化所呼应,而且更多的留白少了平常书籍文字密集的压抑感,是本适合在无聊时一口气读完的书,就像与一见如故的新朋友彻夜长谈,许多瞬间值得回味,内心久久不能平息。 服装设计,这是我未曾真正了解的新领域,而对于其中的元老耀司来说,我只希望在这宝贵的一生里,他能够一直通过设计服装传达他自己的思想,也能在当中获得足够的喜悦。 正如他所说的“以命相抵,制作服装”。
《做衣服》读后感(五):大师何以为师
对于在服装界混了将近二十年还依然只是一名工匠型设计师的我而言,山本耀司与其他大师一样在我心目中都具有神殿级的高大上地位。所以这本大师的手笔《做衣服》十分吸引我,我很想知道大师是如何成为大师的,大师又是如何做大师的。
打开书,出人意料的并没有功成名就者一贯的高大上腔调,相反却是一派平和之气,山本耀司只是从童年和家人出发,再至社会和朋友,一段段娓娓道来,自然而然的诉说着自己何以成为自己。这既非自传,也非功劳簿,只是一个老者品着咖啡回首来时路而已,而山本耀司的人生路,也正如扉页上所写:以命相抵,制作服装。
读山本耀司,不仅仅读他如何“做衣服”,也是读他的前世今生,他的童年经历、求学创业、父母友人、顺流逆流、心路历程,说是做衣服,却只是遵循内心去做人而已——这才是发乎内心的设计,跟随的是一颗与时代背景接轨的驿动的心,他在极度褒贬中行走自如,卓然不群的存在着,他从不迎合巴黎或金钱的口味去制作“流行”产物,所以他一直在引导潮流而非随波逐流,所以他是大师而非高效的工匠。
而放眼看去,如今国内的服装界,品牌雷同度高又缺乏创新和自我意识,一味迎合大众审美,一味抄袭别家畅销产品,又妄图用“潮流趋势”与“产品企划”的星火去逆转乏味雷同的需求趋势。这本身就是一件悲怆的悖论,南辕北辙之间,中国服装又要去向何处呢?难怪众多品牌中枪,纷纷关店抛售的倒下了。既想放下身段赚钱,又要抓着专家的形象不放,是成不了工匠也做不了大师的悲哀。
山本耀司的人生,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从未怀有与内心无关的庸俗目的,这也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深刻原因。
《做衣服》读后感(六):这本书和山本耀司的风格好搭……
我这个喜欢优衣库、无印良品的人,知道山本耀司的大名,却不知道他设计的衣服长什么样子,但是并不妨碍细读《做衣服》,而且津津有味。
首先,喜欢它的装帧,32开,小精装,排版细腻,文字亲切随意,如好友聊天,妙语连珠,令人莞尔,书脊有一条黑色的缎带,滑滑的,细细的,随你夹在哪一页,读完合上书,觉得这本书和山本耀司的风格好搭……耀司的风格是啥?自己看书嘛。
山本大师的父亲在他不满一岁时战死在菲律宾群岛,具体哪里,无从知晓,母亲说:“穿的是夏季军服,那应该是去了南方吧。”这是书中第一章节,提到衣服的第一个字眼儿,是不是有点心酸?
山本大师从小跟母亲长大,母亲是个裁缝师,工作狂,性格强硬,有时会为儿子犯错悄悄的哭泣,“她跪坐在榻榻米上,裙摆四下散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非常女性的姿态”。为了让母亲高兴,大师一直做个好孩子,考上一流大学,毕业后不想做上班族,在1965年去欧洲旅行三个月,从此爱上了巴黎。他的旅费来源是家庭教师的工作,教授英语和国语,“一心想把孩子送到好学校的妈妈们,把我当神一样供着,收入自然不菲……”我很喜欢这样的细节,大师就是大师,初到巴黎的时候,连红灯区的女郎都喜欢他,请他吃饭喝酒,谁说艺术家就该贫困狂傲没朋友呢,法国女人最有眼光了。
很喜欢大师谈到母亲的章节,他母亲说:“你就是妈妈人生的全部。”大师是怎么接这个话茬儿的?大师说:“听听,多么可怕!女人不该说的话她全说了!” 大师很有趣,他说最近常穿又很喜欢的一条裤子是——川久保玲。
《做衣服》读后感(七):杂记
1
制作精良,内容是七拼八凑而成的山本耀司感悟加传记,尤其是后面的“百问”,难为他这么认真地一一作答。
2
当然对于一个“做衣服的怪物”而言,文字什么的本就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能够准确表达想法即可,如同剪刀存在的价值,是通过精准的剪裁表现出设计者的观点,而非使用技巧上的眼花缭乱。
3
破除了小时候的一个疑惑:秀场上展示的所谓时装应该都是没法穿上街的衣服吧,有什么价值?
看过书后知道想反了,这些时装正是维系传统、带动潮流的珍贵联结物,可惜大部分通向庸俗化或妖孽化,走火入魔了。
4
高级成衣不是区别阶级的标志,“快时尚”的东西不是可以留存的衣服,设计师比艺术家更难以找到存在感。
5
可以迎合,不要苟合。可以破产,不要破功。可以赤裸,不要捆扎。可以退让,不要退休。
《做衣服》读后感(八):裁影
做衣服:裁影 Cloth and Shadow
刘曦
一代宗师山本耀司素来喜欢背影,他甚至常对自己的制版师们说:“服装要从背面做起,背面的姿态定下来以后再做前面。”这似乎是山本耀司作为“破坏时尚”的反叛者的最佳写照,然而如同被赋予的“人类最后一个手工艺人”的名号一般,在他身上集结了太多不明就里的标签,当时尚工业的新陈代谢需要一种新的风格驶入大众流行文化之潮时,山本耀司俨然化身成为了自己所厌憎的媚俗行列的偶像,被疯狂拥趸与崇拜,而他自己却依旧只留给所有人一个枯寂的背影。
或许是时候到了,宣布破产后的山本耀司依旧在东京独自做着自己绵延一生的工作——做衣服,可是市面上以Yohji Yamamoto之名推出的著作却汗牛充栋,其间宫智泉整理的《做衣服》一书显得尤为殊异。全书分为“背影”和“百问”两部分,前者以关键词形式如拼图般再现了山本耀司一路走来的点滴历程,后则宛若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巨细靡遗的提问触及山本耀司工作、感情和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二者互为借镜,明晰而浅显的描摹出这位孤独大师的剪影,却也在彼此的镜像之中,令这份剪影显得深邃而灵动。
追本溯源对于背影的执迷,山本耀司用了余韵一次,他认为“即将离去的女子的背影,既让我伤感却又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美丽。对于遥不可及,追无可追的女性的美,也许让我有一种背影情结。”早年父亲山本文雄于菲律宾沙场罹难后,母亲富美便只身前往东京学习裁减缝纫技术,并带着年幼的山本耀司在鱼龙混杂的新宿歌舞伎町附近开设了一家“富美洋装店”。这里的街道上麋集着美国驻军、“傍傍”娼妓和流氓黑道,打架斗殴并不鲜见,可美国大兵对待女性却比地头蛇要和善的多,这一幼时印象既铸就了山本耀司有别于大多数战后日本人对于美国及欧洲的非敌对态度,也让他透过女性认识了这个被男性操控的世界,继而对其抱有一生的敌意。
众所周知,山本耀司的世界黧黑如漆,可黑是死沉的表象,影才是生动的精魄,宽衣博袖、不规则剪裁乃至没有高跟鞋模糊性别的造型,这些都是山本耀司的服装特点,也是他对于母亲及所有女性发自心底的一丝怜惜。在黑色的笼罩下,正是这无处不在的魍魍巨翳方裁出了他手下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性感的性感和没有色调的色调。在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之中他分析了日本人对于影的巧心,“细究之下,东洋人具有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寻求满足,意欲安于现状的性格,对阴翳不会感到不满,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无奈,听其自然,反过来沉潜其中,努力去发现自身独特的美。”
这仿佛才是破解山本耀司恍兮惚兮的美学观的不二法门,去除服装所带来的桎梏与矫饰,创造出如影随形的恰切与熨贴,让每个人在这样的服装之中凸现自我,而不是风格,一如他自己所言“即使一根线,也要注入生命。”《做衣服》一书的台湾译本名为《制衣》,山本耀司也坦言自己喜欢为北野武和皮娜•鲍什这样的“坏家伙”制衣,但与其说是制衣,不如说是裁影,这影既是他深埋心底的旧时情结,也是他与西方对抗的东方哲学。
原载于《EIN》(2014 winter)
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http://www.ein.com.cn/magazine.php?id=55&show=255
《做衣服》读后感(九):反时尚成为时尚
读过的关于大师山本耀司的第一本书,细水长流的文字中没有波涛汹涌的激情,没有澎湃的气宇轩昂。只是一个人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在与未来的自己说你好,山本耀司在书中回顾自己与时尚,与制衣羁绊的一生,迷惘有过、失败经历过,但更多的,是让自己更加清晰自己的那条时尚之路,从四处乱撞到坚定不移,山本耀司活出了自己的态度。 书中很少的谈到了山本耀司怎样制衣,有哪些技巧,关于时尚有哪些指点。而是记录了山本耀司从对时尚懵懂之感到大彻大悟的成长之路。 众所周知的是山本耀司的制衣风格不羁,强调线条和衣服的廓形,在黑白简约的色调之间感受自由,让“反时尚”成了“时尚”,但偶尔也会不走寻常路大胆运用色彩来唱些反调,让人眼前一亮。这本书即讲述了他的时尚之路,从谈话、讨论、自述中了解给欧洲时尚重重一击的大师的不曾公开的生活与感悟,读过当知山本耀司自己的时尚世界从未被外界所侵入,严格甚至有些偏执地保留着一份对于时尚领域的最初的纯净与崇敬之情,为人敬佩。
《做衣服》读后感(十):做衣服,破坏时尚
最近有点无聊了,每次的无聊都来的措手不及、莫名其妙,早已习以为常。具体形容的话是夹杂着虚无和吞噬的幻灭感,像失去了着力点,出一记拳却感觉不到任何反馈。或许每次忙碌过后,这种短暂的无聊感就会汹涌而来、猝不及防。我跌在这种情绪里,出不来。
一、我们都是“好孩子”
作为一个擅长自救的人,我知道我得做点什么,不然这种情绪会在一段时间内毁了我。适时地我遇上了《做衣服》这本书,是山本耀司的回忆录。翻了几页就喜欢上了,嗯,字少,图多,更重要的是好看。
“我的年少时光,是一边目睹着母亲的艰辛一边成长的岁月。所以一直到高中,我都是个好孩子。或者说,我不得不做一个好孩子,从而在某些方面隐藏和抹杀了自己的个性。”
书中这样一句话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个超级大学霸,一个我曾经想约来聊聊故事却发现根本无从入手的陌生人,是机场那位曾先生。我记得我在四月初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当时说四月底的时候来兑现,我没怂,所以跟你们聊聊。
做为一个厚脸皮的伪艺术家,我一直打着发掘有趣灵魂的旗号耍流氓。有趣和无趣本来就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可能一个瞬间,起了好奇心就忍不住探究,也可能又是一个瞬间,失了所有的兴趣,从此抛之脑后,留下一声叹息。
曾先生是个特别的存在,我在他身上看见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影子,甚至于类似那种平行空间里如果进行了另一种选择而产生的人生状态,以至于我非常想知道他的经历。可,他不说。
这是一个从小到大一路学霸到底的人,一路名校,中西结合,大家眼里的好孩子。我始终不喜欢“好孩子”这三个字,这一纸标签,一旦被贴上了,终身负累。见面后的第一话题是他谈起的:抑郁。我愣了,一瞬间不知道怎么接,我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比我大了好几岁的高智商男子,脑袋里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被压抑久了的灵魂。
面具戴的久了就会长在脸上。交流的时间不长,我记得他几次提到:习惯对自己高要求。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对人格的结构有详尽的介绍,他说: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方向。自我要驾御本我,但马可能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曾先生对不对,起码他给我的感受是:长期在超我的监督下强行用自我压抑本我,是个至善至美原则极强,却限制了本我欲望的人。
这也合理的解释了他的那句:你知道男人说约是什么意思吗?写了这么久故事,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头一个这么直白,连拐弯抹角的余地都没有,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惹不起,不写了。
二、一起去使个坏
“喝着廉价的红酒,下赌注玩台球——我曾一度感觉跌进了绝望的深谷,不,那是一种坠落,在坠落的过程中还享受着一种莫名的快感。”
山本耀司有一段时间比较颓丧,日本人的作品在西方社会得不到认同,他自己也迷恋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恰恰就是这种坠落感唤起了他的本我意识,那种“一起去使个坏”或者“试试违背一下常理道德又如何”的感觉时不时的涌现。于是他逃离了巴黎,这个对他而言Femme Fatale的城市。
山本耀司的这种感觉,源于人性,我喜欢聊人性,不完美的人才有趣。换句话说,我讨厌一切对的、乖的、完美的、意料之内的、约定俗成的人和事,往往有冲突、有碰撞、有矛盾、有破碎的才是美、才是艺术。
“创造事物”的本身就是“破坏事物”。打破现已存在的美好事物,让它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破坏,不是吗?完美是丑陋的,是秩序与和谐的呈现,是强制力的结构,自由的人类不会期望这样的东西。我希望看到缺憾、失败、混乱、扭曲。所以我抗拒不了那样的邀约: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制约的东西,要不要一起去打破它?
从个体角度而言,我特别能理解那种“一起去使个坏”的心情,快节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需要情绪宣泄的出口,以短暂逃离不得不面对的人事物。我的宣泄口就是莫名其妙的约人聊聊、写不入流的文章、画丑的人像,把这三者结合形成一个闭环做成一个公众号,混淆视听,娱乐大众。我也特别期待能遇见那种瞬间抓住我的感觉:这就是我想写的故事,任我肆意发挥。
三、“间”,一种引以为傲的美学
当我们把不必要的标准套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既认同又憋屈的感觉,这就是“好孩子”和“使坏心理”在较劲。套句书里的话就是“讨厌被人摆布,讨厌被束缚,却又温柔的毫无用处”。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字,“间”。
“间”是什么呢?从音乐的角度讲,大抵上优秀的音乐作品,都在节奏上时而有零点几秒的延迟,时而又快出那么一点点,听起来似乎不合规矩,这就大概类似于“间”的感觉。再比如从设计来讲,山本耀司的设计一定会让空气在身体和衣服之间微妙地流动,这就是有“间”,它会产生一种余韵,一种擦肩而过的、稍纵即逝的美。
放在人性里,“间”就是一种人与人、我与我之间的空隙,是一种个体存在的舒适感。
我把亲情、友情、事情都归在人与人的范畴里,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独立个体的喜好、选择、哀乐,你的风格、态度、观念都需要活出个体思维感,并以此找到生命存在的使命。这就是“间”,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强加自己的想法定义他人,彼此有距离才真实。
而我与我之间的空隙又是什么呢?这得回到本文开头曾先生的事例,我与我即别把自己逼得太紧,所谓抑郁,都是自己造出来为所谓的高标准找的合理借口而已,这样的蠢事我也干过,所幸的是我及时发现平行世界里的另一面,身上标签的好坏不是那么关键而要紧,我没必要为了维护别人眼中的我,活的不自在,人生在世,开心二字最是重要。
山本耀司真是个有趣的人,简单几个片段,既把造衣哲学讲清楚了,又袒露了人生细节,这本书真好看,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