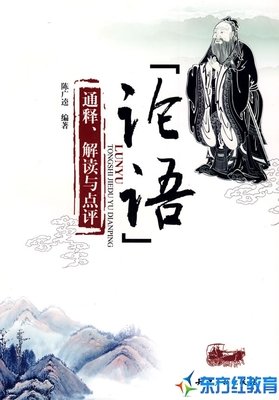《魔群的通过》是一本由[日] 三岛由纪夫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魔群的通过》读后感(一):生于美,死与美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受皇道派影响的陆军青年军官,以实现天皇亲政的主张,发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政变,但此次政变以失败告终,在日本历史上它被称为“二二六”事件,这一年,三岛由纪夫正值十一岁,情窦初开的年纪。此事件过后,享乐主义被视为恶习,就连有关“性”的话题都变得讳莫如深,颇有些谈虎色变。
在对性最懵懂、最殷切渴望的年纪,却被外界社会无情的阻隔在了逼仄的“安全区”里,政府美其名曰“过早的接受性教育不利于青春期孩童的发展”。在适当的年龄接受适当的教育,若是一味的控制孩童的思想,反倒会适得其反,就犹如渔夫捕捉河豚时,越是急切的想捉住它,它反倒会急遽的膨胀。
挤压一寸,膨胀一尺,青春期的三岛由纪夫对性的渴望逐渐变得丰盈了起来。从他十七岁时写的短篇小说《水面之月》就透露出了那蕴藏在心底的悸动,虽说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从这篇小说中可见他的个人美学已经初具雏形。
这是一部书信体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日本平安朝时代青年男女的哀婉爱情故事,女人对男人相思成疾,夜不能寐,“你就像石子滚动、水流碧清的小河,我就是布满黏滑绿苔的河床。河水奔流,消磨着我的身子;河水干涸,河床石子尽皆不动,我依然希冀那消磨我身子的瀑布流潭永远奔腾不息”,女人的一抔情怀在男人眼中不过是过眼云烟,男人向好友诉苦,痴情女子的念叨让他觉得厌烦,女子像苍白的飞蛾不停的向那晦明晦暗的光源撞去,即使翅膀残缺不堪她也不曾停歇,男子为了斩断她的念想,恋上了另一人,女子并未知难而退,只不过她将这情感封存了起来,就犹如被琥珀包裹住的昆虫,晶莹透亮的外壳下是女子未曾圆满的悸动,这悸动再也无法踊跃出来,它成了女子身体里最美的装饰品,男子看望女子时,缥缈的情感萦绕在他的周围,再也不见往日的氤氲,仰慕他的人似乎未曾出现过,他懊恼的离开了她,剃发为僧。
十七岁的三岛由纪夫笔下的恋情犹如阴暗潮湿的角落里的种子,兀自萌芽,兀自开花,兀自凋零,即使美得不可方物,依旧无人问津。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不过是镜中人。
青年时期的三岛酷爱雷蒙·拉迪盖的作品,他是一位法国神通作家,十四岁开始写诗,其后发表剧本、短篇小说及诗作,二十岁因病去世。日本文学评论家野岛秀胜羽曾评论三岛,“对于他来说,人生就是语言,语言就是人生。未熟的肉体是已经烂熟的语言的囚徒。”想必三岛也是如此评价拉迪盖的,拉迪盖在小说《肉体的恶魔》中讲述了猫如何偷取玻璃箱里奶酪的故事,三岛认为,“玻璃箱”象征着少年的成长以及社会规则,若想吐故纳新,被世界所认同,就必须打破“玻璃箱”,将所有的“金科玉律”弃如敝履,在当时,打破“玻璃箱”的唯一方法是战争,但是对于日本而言,战争无法打破坚硬厚实的玻璃箱,这是法国与日本的本质区别。
拉迪盖与三岛由纪夫所处的年代有着相似历史,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两人的文学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三岛由纪夫笔下的拉迪盖实则是他的化身。一战后期的法国文学呈现出一种“有毒绚烂”的青春时代,散漫、无秩序、癫狂以及犬儒主义泛滥,文学青年对待“青春”题材的小说、散文、杂文近乎狂热,三岛由纪夫曾说,“青春的特权大抵就是无知的特权。歌德曾言:对人而言,未知的方为有用,已知的反而无益。在大人看来,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各自的特殊际遇,但年轻人则把自己的特殊际遇视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战争时期的三岛由纪夫被诸多文学小团体视为天才,行文构造被众多文学青年奉为圭臬,二战结束后却变成了无人问津的软弱学生,他也因此离开了曾经青睐过他的文学团体,在《拉迪盖之死》这篇小说,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向博识而富有道德市民社会的诀别,是旷野的狼的胜利。”三岛由纪夫佩服拉迪盖能够在战后混乱的局面中创造出井井有条的秩序,若将战后文学比喻成一堆杂乱无章的线团,而拉迪盖就是唯一一位能够找出线头并将其拉平捋直的作家,这篇小说不仅仅是在致敬拉迪盖,也表达了他对日本战后文学的憧憬,希望他也能拉迪盖一般“在自身之中建立起秩序”。
“人这东西,一旦钻进美里出不来,势必不知不觉撞进世间最为黑暗的思路”,这是三岛由纪夫的美学理念,若他写《水面之月》时,其美学还是柔和液态,那么在他写《星期天》时,其美学已凝固成棱角分明的固态。小说讲述的是幸男和秀子这对恋人的故事,他们在日历的星期天上涂了各种色彩,代表着他们休息时拟定去往的地方,“绿色代表山林、原野,蓝色代表海洋、湖泊,黄褐色是大地泥土的颜色,也就是棒球”,在同事眼中,他们琴瑟和谐,举案齐眉,不是夫妻却胜似夫妻,惹得旁人好生羡慕,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艰难险阻,都不能阻碍他们早已拟定好的计划,他们充沛的恋情就像汲满了水的海绵,自身早已圆润饱和,还不时的浸透着四周的人们。一次意外的事故,列车的车轮从他们的脖颈处碾了过去,“事故一旦发生,这对恋人的头颅完整地并排于砂石之上。人们感叹与这位魔术师的技巧,内心里很想赞美一番司机神奇的本领。”
三岛由纪夫在战后时常陷入自我恐慌,自我亢奋的状态中,地球的昼和夜在二十四时内交替转换,三岛体内明与暗的置换却只在须臾间,他的文风也随着心情在美与哀的极致间相互转换,这是他虚无唯美主义的根源,他将笔下的人物拽入黎明又将其堕入深渊。
“追想与奔向彻底的毁灭完美契合之时,方能完成卓越的艺术作品。”
第一次仔细的读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不禁感慨作者繁复细密的文字,诡奇的想象。
本书作为三岛由纪夫早期短篇小说集,第一篇《水面之月》是17岁的作品。
这篇《水面之月》由7封书信构成,以不同的写信者写给不同的收信人,构思奇特。处读之下有点莫名所以,反复阅读,才能于细微处辨识写信者与收件人,辨识写信人的情绪流动,故事发展。而故事结局中男主人公的出家、死亡及夏萩的病,却显示出生活的残酷与无情。17岁少年的心思之深,于此可见。
另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星期天》,一对美好的青年男女,一幕幕浪漫与温情,结果却在归程惨死于车轮,生命戛然而止。
《花山院》中的晴明与花山天皇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又隐隐中似有天命。
末篇《施饿鬼船》对鸟取父子的心理、对话描画,精彩而入理,末尾更显精彩:“母亲生下我,不到半年就亡故了,父亲想必悲叹不止吧?” “朋友都来安慰我,当着友人的面,我哭得像个泪人儿,大伙儿说我没出息。”…… “不过,有句话很难启齿,那就是,你母亲的死对我来说,倒是一种恩宠呀!”
如果说故事的诡奇是三岛由纪夫早期作品的特点,那么,繁复细密的文字则是三岛由纪夫成就的关键。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随处可见三岛由纪夫的语言功力,有时能感觉到译者想要充分表达作者语言所感到的焦灼与无力。
《魔群的通过》读后感(三):我比你们都丧,但我有颜有才华
原文:我比你们都丧,但我有颜有才华
有个奇怪的现象是,日本作家热衷于自杀。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与三岛由纪夫,20世纪日本文学黄金时代的四位大作家,无一不是选择了赴死。
如果说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与太宰治走的是“文学路线自杀”,那么在“自杀小分队”中,三岛由纪夫是格格不入的那个。
太宰治就不行。太宰治可是和恋人双双投湖还被捞回来的人啊。
三岛由纪夫身上有种分裂的质地——感伤颓美的文学风格与他狂热的激进思想,竟然并行不悖。
或者说,三岛之所以是三岛,就是因为他身上有比别人更汹涌、更直接的欲望出口。
1941年,日本。
一个16岁的少年写了人生第一个中篇小说,兴奋地跑去找他的国文老师清水文雄寻求笔名。
“不可以用我的名字吗?”这个叫平冈公威的少年疑惑地问。
三岛由纪夫少年时“作为一个中学生,在《文艺文化》这样的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最好不要用真实姓名。”清水文雄说。
于是,“三岛由纪夫”诞生了。从此日本文坛多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
三岛由纪夫出生在东京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日本农林省水产局长,自己则毕业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法学部,入职大藏省银行局。
用浮躁的现代眼光来看,就是“官二代+人赢”的组合,开挂的啊。
算起来,16岁出道的三岛由纪夫,在其短暂的45年生命里,将29年的时间都献给了他的文学事业。
他的成绩斐然,小说、剧本、散文均有涉猎,获奖无数,不仅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文学大师,在西方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美国学界甚至将他称为“日本的海明威”。
2007年,三岛由纪夫自编自导自演的《忧国》(1966)公布于世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一个时刻保持着生命激情的作家,会和“懦弱”的太宰治一样选择自杀啊?
虽然两人在行动上表现出了力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差不多属性的人——三岛由纪夫是为了践行自己的美学而死的。
从三岛由纪夫现有的文学作品序列来看,《潮骚》《爱的饥渴》《假面自白》《金阁寺》《丰饶之海》是他的成熟之作,里面充盈着“我”对于无力改变现状的精神虚空感,及对于“美”的病态享用。
我最喜欢《潮骚》与《金阁寺》。在《潮骚》中,三岛由纪夫难得地提供了一个“小清新”的圆满结局。这也太不icon了吧!我想,反而能让人用一种相对抽离的视角,去拿捏他的态度。
《潮骚》剧照至于《金阁寺》,走投无路的“美”,常常让我震撼。既然世间的言语表达不出金阁寺的瑰丽与神圣,那么它的存在,真的是太痛苦了。
可以说,这个序列,是三岛由纪夫本人的内心巅峰。
那么更早呢?三岛由纪夫是否在一开始就已经这么丧了?
是的。
《上锁的房间》《魔群的通过》这两本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17岁至31岁的数篇短篇精选。其中《魔群的通过》中的13篇,大多让人眼前一亮,感叹“别人家的17岁”,已经开始思考欲望、死亡与丧失这些严肃的话题了。
英国著名记者亨利·斯各特· 斯托克斯曾说,三岛由纪夫的创作,是在无休止地演练属于自己的死亡仪式。
在他早期的小说《志贺寺上人之恋》中,遁入空门许久的高僧依然难逃红尘的劫,泪水涟涟地吻到了御息的身体后,用圆寂结束自己的一生。
《魔群的通过》里的短篇小说莫不如此,大约讲的是主动或被动赴死的决心。
用“怪异”“迷幻”“惊悚”形容它们,都很贴切。这个异常早熟的天才少年,用颓美清丽的文字纾解着内心的扭曲与痛苦。
《水面之月》写于1942年,彼时三岛17岁。全文由第一口吻的书信体组成,构思巧妙,情绪幽微,峰回路转,缓缓道来平安时代男女相爱的那些事。
情节大致就是,“我”爱你,但我也爱上了别人,拜访你之后,“我”一度苦恼,只好削发为僧,最后就染病死了。
我们还在做“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时,少年“我”对他的恋人说,想必你看到了一片庄严的虚空之界吧。
《相根工艺》中的男人,嚷着要和艺妓鹿子结婚,没有钱与爱的信心,鹿子自然不愿意。回到东京,男人就服毒自杀了。
《牵牛花》写的是妹妹。死于战后的妹妹,幼小的妹妹,常常在“我”的梦中回来。
……
《星期天》最有意思,讲的是一对普通办公室恋人被动赴死的故事。两人是办公室毫不起眼的角落的员工,拿着同样的薪水,工作兢兢业业,沉默寡言。
他们之间有个秘密,那就是独特的“星期天生活”。
工作日已经够不自由了,难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一定不能坏了心情!
男人和女人会严格“预定”星期天的颜色,有美丽的绿色、蓝色、黄褐色和黑色。绿色代表山林或田野,蓝色是海水,黄褐色是棒球,黑色是,电影。
《潮骚》剧照每到约好的星期天,两人见面游玩,却也因太顺利的、能被自己安排的幸福而不安。
男人与女人想,真的有可以调整未来的能力吗?
男人与女人想,这样的星期天,真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啊。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临时列车驶入车站。原本站在黄线外的两人,被身后的力量推到了最前面。
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手挽手的恋人,掉入了列车呼啸而过的轨道上,留下了两颗整齐的人头。
“星期天”死了,支配命运的侥幸也死了。
作者可真是一个丧到没救的人。
对了,他还是个中二少年,借着笔下人物的口,懒懒地发出“我即便被杀,也有着啥事都不干的权利”的感叹,并不留情面地调侃了“厌世的作家”——
“不被承认的作家都是厌世家,被承认的作家,则把信奉厌世作为长寿的秘诀。特别称得上厌世的作家一个也没有。”
乍看会被惊到:20岁少年,竟然看透了“作家的秘密”。
在那一代日本文学家中,三岛由纪夫是作品被翻译到海外最多的人,数量上超过了川端康成。他本人对诺奖也是充满期待的。
结果1967年,瑞典那边传来消息:日本作家获奖了,是川端康成。
没过多久,三岛由纪夫就完成了那个著名的自杀行为,也意味着,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获奖的机会。
三岛由纪夫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因为不得奖而郁郁寡欢,我觉得不全面。浸润在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深深影响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三岛也是其中一位。
莫言曾说过,“评价三岛只能从文学的方法,任何非文学的方法都会误解三岛。”
避开纷纷扰扰的自杀猜测,至少在这本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中,我看到了三岛美学成年前的模样——他是多么享受零零散散的赴死欲望啊。
《魔群的通过》读后感(四):三岛:炼金术与巫
收到书后读了一周,每天睡前看一两篇,南方夏日的夜晚闷热而寂静,三岛的文字如同窗外幽绰的花影,窸窸窣窣地入我梦来。
读三岛的短篇最有意思的是追溯他的创作生涯,寻出早期的短篇和成熟期的长篇里那些一脉相承且逐渐生长圆熟的主旨。第一篇作于十七岁的《水面之月》就已经足够惊艳:「她伸出一只冰冷而微汗的纤腕,我从她那手臂上感受到黄金般幽怨的重量。」《春雪》里那种哀艳优美的笔调在这里就已经初见端倪。《伟大的姊妹》里兴造邪恶的破坏欲正是烧毁金阁寺的沟口的雏形,《旅行者的墓碑铭》里次郎纠结的哲思还显得矛盾浮躁,到了《丰饶之海》里就成了大段诗意的哲学自白……跟读《上锁的房子》时一样,这种抽丝剥茧的快乐贯穿了阅读的整个过程。
三岛的年少时代几乎都是在二战和二战后的动荡中度过的,早期的小说反复描摹的也是战争给人的精神带来的荒芜。《山羊之首》对青年人放荡空虚生活的戏谑,《大臣》里对愚蠢官僚的讽刺,《魔群的通过》讲中年危机和犬儒主义,《星期天》和《箱根工艺》里写战后青年“有毒的绚烂”的悲剧,《复仇》的罪与罚,《拉迪盖之死》兰波式的天才乍现与寂灭。这类小说充斥着空虚、无秩序和反战情绪,是三岛对人间的哀恸和嘲讽。
另一类则是对他一贯专注之美学的尝试与探索。《水面之月》里迷离哀愁的男女之情、幽馥生冷的语言,《花山院》里帝王耽爱而遁入空门的古典式浪漫,《牵牛花》写冥界鬼魂的怪异诡谲,《施饿鬼船》美的残酷与情爱的幻影……我更偏爱这样的三岛,那种逢魔般的语感,对爱、美、残酷与死亡的描绘,永远令我为之心醉神迷。
三岛的长篇是太阳与铁,尽管笔锋仍是纤细的,但情调上是不可忽视的广袤与伟大,短篇则有一种新雪般的美,轻盈、飘忽、没有确定的形状和重量,不是要落定而是在探寻,意不在覆盖而是要掠过。三岛对语言神灵附体般的把控和锤炼在短篇里完全体现出来,「未熟的肉体已是烂熟的语言的囚徒。」三岛的语言完全是强横的、摧毁性的、凌驾并超越一切的,有炼金般的严谨和神圣,三岛是语言的巫师。
《魔群的通过》读后感(五):原来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作为一位三岛迷,从去年开始就期待着这部新的译作《魔群的通过》,前两天得知这本书上架,立马买了来读,看完全书,不由得再感叹一句“还是原来的味道,还是熟悉的配方。”
其实,我一直期望着像莫言先生评价三岛那样,即“评价三岛只能从文学的方法,任何非文学的方法都会误解三岛。”,来更好的理解三岛。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那么的复杂,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多重角色,还有着当时当地特定的情绪心态,况且三岛又是以那样壮烈的方式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认为很难将三岛单纯禁锢在文学领域。以这样的方式,不仅会将读者与三岛拉得很远,而且也会使得三岛个人简单化,这不符合人这一复杂化的情感动物。
去年看到陈德文先生译著的《上锁的房子》,总的来说,雾里看花般简单过去了,兴许是自己当时心绪还不够平静。如今,再看《魔群的通过》,其实还是会有同样的感受,译文使得三岛本身复杂而又暗涌的文字,显得更加富于思想性与哲学性。
但是当我打开本书,看到第一篇文章《水面之月》时,惊喜17岁时的三岛,俨然就是那个写《春雪》的男人,笔端散发着浓浓的古典气息;进入《山羊之首》时,依然能够看到三岛式的残酷美与暴烈美;再到《伟大的姊妹》,摘录两句如下:
松永自尊心的疼痛,某一天一旦变为无法忍受的剧痛,他的憎恨就不再朝向朋友,而是朝向自己所爱的那位少女。为何不给予实质性的回答呢?我们确实认为孙儿的行为是正大光明的。若不刺伤自己所不满意的老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人。这些话咋读起来,让人感觉三岛在强词夺理,出离于常人的认知。然而,笔下逸出的是他思想的精华,唯有从三岛个人的思想出发,方能将这些不合理化为合理。
《拉迪盖之死》确实为本书最佳篇章,文字中隐约地透着些许的暧昧,颇耐人寻味。
除了这些篇章,本书其他诸如肉体的重要性、夹杂着盐味的海风等这些熟悉的主题,以及大量哲理性语言文字的堆积,都彰显着三岛写作手法的印记。
鉴于三岛作品逐渐成熟的过程,以及篇章之间层次不齐的水平,本书我给3星。说实话,得好好学日语,争取有朝一日读原著,饕餮大餐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