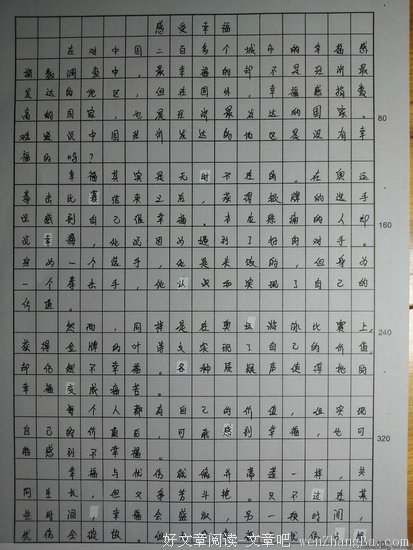《1491》是一本由[美] 查尔斯·曼恩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3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491》读后感(一):很有趣的美洲史前史
Charles C. Mann,他的著作不約而同的在華文世界登場,分別是本書《1491》跟衛城出的《1493》,都是講述美洲的故事,以哥倫布的到來為基準點講“之前”與“以後”的歷史。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是,衛城沒有選本書而是選了《1493》,這本當初我覺得跟《哥倫布大交換》重疊性會很高,所以一直到最近才趁著書展撿回家。
Mann似乎不是學術界內的人,但他身為一個媒體人,充分的掌握了現有的研究,還有他自己親身到現場的經驗,撰寫了這本《1491》--其實它很不好寫,因為這是個非常破碎跟缺乏證據的“史前”年代。而作者也不是寫了一本編年史,事實上這本書比較像是《國家地理》之類的雜誌的放大深入版。
霍姆柏格之誤(Holmberg`s Mistake),意指用片面的觀察,去推論全體的事實所造成的偏差。作者在一開始即引用這個詞,表示現在美洲考古學界正充滿著這樣的問題:
1.對美洲的人口的推測及人類何時到來的偏差。
2.對美洲文明的起始年代的低估。
3.對美洲人(印地安人)的人口銳減的原因的錯誤歸咎。
作者嘗試用自己的看法去撰寫這些問題,當然這些並沒有什麼“標準答案”,就跟其他上古文明一樣,考古不能解答的事情仍然太多,只是讀者可以透過Mann的書,重新去了解跟認識這些問題。
我個人嗜吃玉米,所以對他討論印地安人怎麼開始種植跟發展成主要作物感到特別有印象,尤其是,事實上學界對於玉米究竟是自己獨立的一個物種還是透過配種雜交而栽培出來的尚未定論,而作者微帶辛辣的筆調說,若是後者,那麼印地安人可是在上古時期就進行了一場偉大的基因改造工程,並且影響深遠到頒幾個諾貝爾獎都不過分。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Maya文明消失崩潰之謎,一直是學者們心中的禁忌,因為至今尚無人能解。或許有人認為是他們過度破壞了環境導致毀壞,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環境保護者為了警告世人編織出的神話。而Mann則引用了對亞馬遜河當地的住民跟其生態的一些研究,主張事實上印地安人並非“破壞者”,實際上他們扮演的是整個生態體系中的一環,甚至是“平衡者”的角色。真正導致一切失控的是歐洲人跟他們所帶來的疾病。正如同鼠疫或黑死病曾在歐洲扮演過的角色,大量人口銳減必然破壞整個社會結構,而外敵的入侵就成為最後一擊,或許這才是真正的解答。
而作者真正最有趣的論點是他最後探討印地安人的“遺產”,或者是帶給現代文明的“影響”,即這個人們眼中的原始社會,充滿著平等、自由、男女平權等精神,他們散播到了當地的歐洲殖民者的身上,然後反過來成為了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變革的火種。這個論點有點讓人驚奇,但反過來想,即使在所謂的舊大陸,人類社會最原始的面貌當也是如印地安人般生活,如今也只是“走回過去”而已。
這本《1491》目前只有簡體版,翻譯是還算流暢,只是他的註解處理法讓我有一頭霧水之感,中信有保留也有翻譯,但注腳卻不見了,只在最後標示大概是哪頁出現,這是一種幽默嗎?還是原文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扣掉這個不談,本書依然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Mann算是展現了一次成功運用跨學科的標準範例。
《1491》读后感(二):古老新大陆
这是一本有关世界历史的绝世好书,文章并未以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开始的欧洲侵略为开头来叙述整个西半球的历史。许多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都忽视甚至对哥伦布踏上美洲前的文化及文明成果不以为意。那些为黄金而痴迷的少数征服者们如何能够将数百万人创造的辉煌王国踩于脚下?难道北美大陆曾经只是一块等待先进殖民者开发的寂土?在曼恩这本耀眼新书《1491》中,科学作家查尔斯·C·曼恩对上述问题有所解答,并提出了更多近年来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中的问题。他总结道,1491年西半球(正如整个西半球历史)是一个“繁荣、多元种族的地方,一个充满各国语言、贸易、文化的地方,数千万人热爱、憎恨、敬仰的地方。”当然,对于研究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说,如印加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下这句话说出来已然没有任何新意或值得争议的地方,那就是长久以来,我们十分看重这些人群的文明成果和人口规模。但曼恩的观点却独树一帜,他认为如亚马逊文明和东美洲文明,这些地方长久以来却都被人们认为是人口稀少的一潭死水,与我们认为的更加开化的文明中心相去甚远。
曼恩认为,他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聚焦在三点上:印第安人口、印第安裔人、以及印第安生态(在妙趣恒生的附录里,曼恩解释了他使用“印第安”一次来描述西半球原住民族的原因。他在此处的选择与本人不谋而合,本人一些美洲印第安人朋友也更喜欢“印第安”和“印第安人”的称呼,而非“美洲原住民”。“美洲原住民”一词给人一种白人统治感和政治正确性。)曼恩做了大量研究,虽然他淡化了研究过程,但大部分内容中的大量标注与文献参考正说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在描写这一地区时,甚至还不辞辛劳地亲自访问,与主要学者进行探讨,这些学者们给了他对印第安文明“新的启示”。
这一点正体现在新大陆原住民所受到的待遇上,一些人也将其称为“古印第安”时期。这些替罪羊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C.·万斯·海尼斯与他的同事们,长久以来,他们十分信奉一种观点,就是第一次到达美洲的人是克洛维斯人,他们大概在12000年前通过大陆桥从西伯利亚来到美洲,到达后随即捕杀新大陆的许多动物,使其濒临灭绝。这一学派在面对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语言学证据和生态证据,证明第一批移民很可能在15000年甚至20000年前就乘船靠岸航行来到美洲时,他们对12000至13000多年前的古印第安遗址产生了怀疑。在这里,我必须得说,我同曼恩一样,接受在克洛维斯猎人到来前美洲大陆就已有人居住的说法。
这本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亚马逊河与奥里诺科河河流域。我在研究生阶段时,人们普遍接受南美热带雨林民族由各个安第斯移民部落组成的观点,认为这些民族认识到自己身处极度有限的环境中,由从前的开化国家沦落到了简单、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权威书籍《南美印第安人手册》第三卷中对此观点奉若神明。曼恩其中一个替罪羊也对此深信不疑——《史密森尼》杂志的贝蒂·J·梅格尔和她已过世的丈夫克利弗德·伊文思一样,均为亚马逊考古学领域的先驱者。
曼恩引述了大量论证,证明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并非只有小部落,原因是第一批探索亚马逊流域的欧洲人沿河看见了许多城镇,城镇里居住着许多人。数世纪过去了,亚马逊河与奥里诺科河的农学家和猎人们在人类学家的眼里,只是一群历经人口灾难、溃不成军的幸存者。这场人口灾难由欧洲流行病(如天花、麻疹)为开端,毁灭了整个西半球的原住民族。为早已消失的民族进行证明的是一些广泛存在的高地图案,如果从飞机上看,在玻利维亚东部的贝尼省以及玛拉诺阿拉人口稠密的城镇上方可以看到。玛拉诺阿拉文明曾在亚马逊河口的巨大岛屿上持续繁荣近千年之久。
曼恩认为,现在我们不应将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看做受环境所害的囚徒,而应将他们视为利用环境之人。这就是南美洲的真实情况,和中美洲、北美洲一样。比如说,250年前,一群侯鸽在北美洲繁衍生息,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土地上发现的侯鸽骨骼却少之又少。唯一的解释就是大量印第安农耕人口蓄意毁灭,减少这些吃种子的鸟类数量,因为印第安人曾一度被疾病所摧毁,这种疾病就是候鸽所带来的。
请记住,曼恩是一位记者,而且是一位倡导型的记者。这就使得他的倡导听起来过于热情,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根本无法完全掌控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南美森林(或者说是剩下的南美森林),就连西半球的印第安人在掌控自然环境时也并非常胜将军------大量数据显示,古代玛雅人过度开发环境,在公元9世纪灭亡。曼恩也倾向于他采访的最后一位学者的观点。就中美洲来说,他完全相信奥尔梅克人从中美洲最早的文明以及文明之母的地位,沦落到了众多文化中其中一个。那些真正挖掘到了奥尔梅克遗址的专家(包括本人)几乎没人同意此观点。同样的,他不加鉴别地相信韦拉克鲁斯州南部的所谓的“后奥尔梅克”手稿已经被破译,这种的观点大多数中美洲碑铭研究家都是反对的。
在阅读《1491》这本书时,人们会很快明白旧大陆上的各种疾病是如何摧毁整个新大陆的。这是全人类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人口灾难。单就中美洲而言,只有10%的印第安人在诺曼征服后的一个世纪后存活下来。贾德·戴蒙在其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里表明,这些苦难已远远在欧洲侵略者之前,因此失败的种子其实早已在征服者到来之前早已埋下,埋在了阿兹特克、印加等国。
人们也许会好奇,如果印第安人的身体对这些瘟疫免疫,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呢?他们会在仅仅几个世纪后,像印度人一样成功地摆脱欧洲的束缚吗?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会变成今天联合国大会中的玛雅成员国、阿兹特克成员国以及印加成员国吗?还会发生诺曼征服这一事件吗?
曼恩写下的这本书,给人以深刻印象,具有非常高的可读性。即使有人与书中基于数据得出的推断有所分歧,曼恩也确实给出了双方面的论证。《1491》是对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在的印第安人一个恰如其分的致敬,也是曼恩支持他们的原因。
《1491》读后感(三):创造了相当高的古代文明的印第安人
美洲土著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为印第安人(Indians,亦作Amerindian或Amerind),分布于南北美洲各国。公元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航行至美洲时,误以为所到之处为印度,因此将此地的土著居民称作“印度人”(西班牙语:“indios”),因原有称呼已经普及,所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称印地安人为“西印度人”,在必要时为了区别,称真正的印度人为“东印度人”。汉语翻译时把“西印度人”这个单词翻译成“印第安人”或“印地安人”,这是目前仍为最普及的用法。到了公元20世纪,一些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开始对“印第安人”这一名称进行“正名”,如印第安人在加拿大往往被称为更加政治化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等等。印第安人所说的语言一般总称为印第安语,或者称为美洲原住民语言。印第安人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以前的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正直、朴实、刚毅、勇敢、感情丰富、温柔、谦和、说话算数、忠厚老实、慷慨大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民族,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客的民族。哥伦布在他的报告中都有对印第安人高尚道德的描述。16世纪后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带给当地印第安人是毁灭性的灾难。据统计,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巴西地区有大约1000万被杀,美国西进运动中有100万左右印第安人被杀,到21世纪大约有3000万印第安人。拉丁美洲的男性印第安人基本上没有纯男性系列的后代。北美的情况更糟,在美国,印第安人仅占总人口的1%左右。美国进入2000年印第安人口大约有240万,大多数印第安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都居住在都市化的地区。美国有多个州,1000多条河流,200多个湖泊,以及无数城镇、山丘、河谷、森林、公园,用的是印第安人名称,如aMassachusetts、Arkansas、Dakota、Illinois、Oklahoma、Utah、Alabama、Arizona、Iow等源于印第安人的部落名称。此外还有Ohio、Missouri、Michigan Lake、Conneticut、Potomac River等。美洲的印第安人留下了相当高的古代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玛雅、印加人和阿斯特克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以太阳神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艺术,让人瞠目结舌,是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纳斯卡荒原巨画为代表的令人不解的“斯芬克司之谜”,至今仍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许多地区的印第安人还保留着自己的风俗和传统文化。他们至今仍喜欢穿富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服装,戴富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饰物。印第安人把羽毛作为勇敢的象征,荣誉的标志,还经常插在帽子上,以向人炫耀。拥有鸟羽象征着勇敢、美貌与财富。印第安人做饭时,仍喜欢使用质地粗糙的陶罐、石碗、木勺。有人生病时,他们采来草药,或将其点燃对病人进行烟熏,或煮汤为病人沐浴。
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报以敬畏态度。印第安人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欧洲基督教信仰所同化,但印第安的原始信仰仍然存在,宗教信仰在印第安人生活中占据很高地位。玛雅人的宗教信仰:原始宗教是崇拜自然神,以后逐步演变,有雨神、五谷神、死神、战神、北方星神、风神以及四方神等等。最高神为太阳神--------他是诸神之皇,上帝的化身,是“白昼”和“黑夜”的主宰以及文字和书籍的创造者。玛雅人也有“天堂”和“地狱”之说。在天上,住着天堂之神王;在地下,有地狱,由魔鬼和死神统治。玛雅人死后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部分取决于死的方式。阿兹特克人的宗教信仰:相信灵魂永生和一种由至高无上的主宰统治一切的观念。他们崇拜自然神,如太阳神、月神、云神、雨神、花神、玉米神等。阿兹特克人用“十字架”作为宗教的象征。阿兹特克人认为,世界已经过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由不同的神灵所统治。宇宙形如十字,中心为一火炉,由九至十三层天覆盖着分成层次的地下世界。整个宇宙被水所包围,由高位神双手托住。此神男女合体,具备生命和生殖的双重秉性。印加人的宗教信仰:印加人特别崇拜太阳,具有典型的太阳崇拜的特点。他们自称为太阳神的儿女们。首都的太阳庙是最大的宗教礼拜中心。印加族的祖先被认为起源于太阳,印加王更是太阳的化身。印第安人的节日特别多,这与古代印第安人宗教仪式特别纷繁复杂有关。印第安人崇奉万物有灵的图腾信仰,各部落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图腾崇拜的宗教仪式,一些仪式流传演化下来就成为至今魅力犹存的非常独特奇异的节日。印第安人的节庆多与宗教节日融合在一起,同时印第安人还保留了一些自己独特的节日,如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降魔节等,反映人类不同的生活观念、生命观念和灵魂观念等。土著人日是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节日,在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和9月的第四个星期五举行。在节日里,美国各地都要举行富有印第安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色的庆祝活动。太阳节也是秘鲁印第安人的民间传统节日,在每年6月24日都要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太阳节,历时9天。这个节日源自古印加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南半球,6月24日是太阳北偏后开始南移的日子。
《1491》读后感(四):做出选择的不是自然,是人类
从正月开始,断断续续地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把这本大部头啃完。坦言之,本书并不太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我期待看到的是古老的印加帝国,危地马拉的金字塔,古老的文明和总被误解却真实存在过的高等文明,是当年在川大望江图书馆里,热血沸腾的读到的《拉丁美洲笔记》那样克制却激扬的文字。
然则本书是以记述性的语言絮絮叨叨地写了写16世纪前的美洲,传说、自然、生态、甚至八卦无一不涉及,通俗是有了,深度却真的是少了许多。作者的观点非常直白: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低估了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的高等程度。
但这观点本身就是纯然西方的,是站在自身高人一等的程度来评判历史。这观点与中国史的研究倒是如出一辙。
撇开角度不谈,本书倒是有些很有意思的生态细节,或者说是史实。
比如P394所提到的“基石”物种,即“能影响到很多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繁荣”。机械化捕鱼的出现,导致鳕鱼适量急剧减少,而鳕鱼所捕食的海胆就失去了天敌。而海胆又以大海藻为食。于是,整片地区的海藻床消失殆尽,遗留了一片“海胆荒地”。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略汰理论诚然在宇宙形成的这无尽岁月里都算是正确的,然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之后呢?大概是人类而非自然进行的选择吧。
《1491》读后感(五):《世界史》作者麦克尼尔给1491写的书评,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New World SymphonCharles C. Mann is a journalist and his new book, while not without flaws, is a journalistic masterpiece: lively, engaging, and full of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oples who lived in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joined the two sides of the Atlantic together. Mann draws on wide reading in recent scholarly writing, supplemented by travel to the principal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landscapes involved, as well as by interviews with many of the writers who have challenged older notions about the pre-Columbian past.
Recent discoveries, especially in the Amazon region, make some new ideas irresistible; in other cases Mann summarizes recent controversies without committing himself to either side. In general he argues that pre-Columbian American history was just as diverse and as complicated as anything in the Old World, and that Indian skills were not inferior to European skills. He concludes that there were two different worlds, separate but equal.
Mann starts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he is not presenting “a systematic,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s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before 1492.” Instead, he says, his book explores what he believes to be the “three main foci” of the new findings: Indian demography, Indian origins, and Indian ecology. He could not possibly be comprehensive, he writes. “Instead I chose my examples from cultures that are among the best documented, or have drawn the most recent attention, or just seemed the most intriguing.”
The book begins by naming and locating many of the different peoples of South and North America with whom he is concerned, from Chile to Alaska. Mann then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the size of the Indian population, not with demographic tables, birth and death rates, and the like, but indirectly through narratives of what happened in three regions: Massachusetts before and after the Pilgrims came ashore in 1620; Peru before and after Pizarro captured the Inka monarch in 1532; and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before and after Cortés and De Soto conquered and explored Mexico and what is now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原文地址: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5/dec/01/new-world-symphony/
《1491》读后感(六):译者记:失败者的墓志铭
感谢中信出版社让我有机会翻译《1491》。感谢此书的策划编辑覃田甜、责任编辑王泱、责任编辑杜梁、营销编辑李娆等人的工作。很多人或许认为,此书与我们、与中国、与当前的时代和它面临的问题没有多少相关性。我认为恰恰相反。就此,我在翻译和修改的漫长过程中做了很多笔记,但最终融汇成了下面这一点文字。一孔之见,谨供参考。
下文首发于4月19日的《证券日报》。文章有改动。
《1491》译者记:失败者的墓志铭
人类历史成王败寇,胜者立言,负者族灭。百十年来地覆天翻,得势逆转,失势难安。一些文明兴起了,一些文明消亡了,自古而今,不外如是。
土著居民与欧洲来客对美洲大陆的争夺,成因之复杂,态势之激烈,影响之深远,教训之沉重,可称万年孤例。原住民群体的衰亡不仅影响了外部世界对其的认知,进而也影响了土著居民的自我认知。这些哥伦布眼中的“印度人”(即“印第安人”),迄今未能摆脱扣在自己头上的这顶帽子。在资本对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渗透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美洲原住民沦为了流行文化的猎奇对象;而近年来土著群体“伤痕文学”的矫枉过正和神秘主义的夸大其辞,又单向突出了种族灭绝情状之惨,与桃花源中和谐之美,使还原历史的努力险阻重重。
查尔斯•曼恩的作品《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是一本极为难得的严谨之作。这是一篇胜利者为失败者写下的墓志铭。它没有陷于道义之争,尽量避免了对任何一方的神化,毫不隐讳地详述了此间众生各自的所长所短,及其共通的狂热性、软弱性和投机性。它着力于描绘土著群体从开辟山河、经营土地到抵御外敌期间一以贯之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将其简单提炼为闭关锁国、被动挨打,最终身死族灭的弱势群体。
换言之,这是一本还原历史的翻案之作,但它绝非我们熟知的那种简单粗糙的翻案学,而是严谨治学精神与独立辩证思维的结晶。它没有做出制度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因果推断,而是突出了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以及相关学界在具体议题上的反复论争。
美洲原住民不是蠢人,不是圣徒,不是环保分子,不是共产先锋,甚至也不是这片大陆的初始居民。但他们隔绝于全球所有其余早期人类社会之外,一手创建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受制于欧洲人的枪炮利器,并最终遭难于殖民者的外来病菌。在此期间,他们犯下了所有可能犯下的战略和战术错误,以妥协求团结而团结亡。因其失败,美洲土著群体的历史发源之早、各地人口之多、社会形态之新、主宰环境之能,都湮没在了历史的汪洋大海中。而借助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种学等多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还原其本来面目,正是本书的主旨。
此书的主题及其内容对当代中国的警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若无多代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努力,近代中国必难逃脱相似的苦难命运,更无法取得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和话语体系。即便是如今,我们也难称胜者。“天朝”荣光之失、丧权辱国之痛,同样被流行文化解释为闭关锁国、被动挨打所造成的恶果。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之任重道远,发人深省。
在大方向上的主次分明、清晰自信,以及在具体实践中所必备的开放视野、独立思维,是今日中国过尽千重魔障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希望所寄。在这一点上,数百年来面目全非的美洲原住民社会的命运,以及本书对这一进程冷静细致的还原与讨论,颇有述往诏今之意。
《1491》读后感(七):中信出版社的书大多华而不实
《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查尔斯·曼恩。这本厚厚的书封面设计漂亮,内容简介让我很有阅读的欲望,于是,迫不及待地下单。然而,到手后开读,对作者的写作方式和译者的翻译质量相当失望,作者毕竟是记者不是学者,那种新闻报道的笔法东拉西扯,信息量有余,干货不足,全书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可以砍掉的水分,而且,每个章节主题不明确,更像是一些新研究成果的堆砌,连最基本的分析比较都没有,读完以后的感觉就是:哦,有这样的说法呀,逻辑和证据都不能说服我。书中的核心思想是,哥伦布前的美洲大陆是印第安人开发了上万年的土地,某些方面的文明水平不亚于同期的欧亚大陆,而欧洲人后来记载的荒蛮的美洲,反而是天花等疾病大规模流行后的结果。读完还是有一些收获的,对美洲史的了解又增加了几分,但同时也让我对中信出版社的一些时髦的大部头更加谨慎一点,中信就是喜欢翻译引进一些大而无当的所谓畅销书,乍一看名头很响,仔细一读味如白水。《1491》读后感(八):空旷疆域之谜/探险家的疾病早在殖民者抵达前就已毁灭原住民
空旷疆域之谜/探险家的疾病早在殖民者抵达前就已毁灭原住民——玛丽·德·安布罗西奥
早期欧洲探险家们曾为美洲的富饶而疯狂。原始森林覆盖陆地,美洲赤鹿等鹿儿众多,成群结队的野牛如奔雷般穿过平原,他们将报告发回西班牙、葡萄牙与英格兰。
鱼儿挤满了河流,肥美多汁的贻贝和蛤蜊遍布海岸。来自南美洲的传说中,原始森林的秘密金矿里埋藏着难以想象的财富。除了秘鲁的印加、墨西哥的玛雅,以及北方的原始游牧部落等少数强大的孤立社会之外,几乎没人生活在这个奇妙的天堂中。这片自由而奔放的丰饶大地,就如同来自上帝的礼物!
这就是你在学校中得知的教材版哥伦布时期新大陆。然而在一本引起争议的新书《1491》中,科学作家查尔斯·曼恩提出了一个修改版本。作为《科学》杂志及《大西洋月刊》的一名特约编辑,曼恩钻研了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资料,认为视美洲荒野为处女地的简陋认知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哥伦布时期的西半球就已经遍布人类的痕迹,”曼恩总结道。根据估算出的最高值,哥伦布抵达前有超过1亿人口生活在这里——超过了当时的欧洲。
多达美国本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地区曾经被耕种过,土地被修成梯田、施以灌溉,并修建了代表定居点的神秘土丘。在墨西哥,原住民已经在种植玉米,兴建富足的西红柿和豆类菜园,天文学、数学及文学的发展速度和深度足以媲美苏美尔人。印第安人也并非毫无建树:曼恩提出,个人自主和社会平等的印第安传统可能是美洲殖民者对自由与公平态度的最初灵感来源,并且影响了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的作品。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世界观呢?其对全球发展主流看法的挑战,就如同贾雷德·戴蒙德式的抽射一般,曼恩调查发现,最近的学术研究正越来越多地认为大量原住民死于欧洲传染病。
像天花这样的传染病曾盛行于16到18世纪的西半球,他认为,其传播范围比之前认为的要广泛得多。疾病导致的生态崩溃使得元气大伤的印第安人社会再也无法控制他们的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一两百年后探险家、传教士和开拓者们抵达这里时会有如此多看似“原始的”土地。作为探险家和征服者,秘鲁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墨西哥的荷南·科尔蒂斯,以及来自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早期奴隶贩子们将天花这类可怕疾病传播开来,这一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大灾难消灭了前哥伦布时期95%的人口。
后来的探险家们遇到的“原始人”被错误地认为是自古以来就游荡在森林中,并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孤立群落,实际上却是社会崩溃后饱受创伤的难民。
不大可能?许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这么想,曼恩认真探讨了这场激烈学术斗争的另一面。他访问了著名评论家、威斯康辛大学的非洲研究教授戴维·亨尼吉,后者在著作《神秘的数字:美国印第安人遭遇人口之争》中反对道,关于大规模死亡的结论缺乏证据支持。“我们能用内战和疾病来解释历史记录中的人口减少和流动,”亨尼吉告诉曼恩。“然而到底有多少呢,谁知道?”毫无疑问,这不仅是科学争论,也是政治斗争。印第安人事务活跃分子一直以来就在抗议,欧洲人故意低估原住民们取得的成就,为其侵占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迁入无人占领的土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位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人种学家在书中表示,“而只有少数‘野蛮人’的土地仅次于它。”但曼恩令人信服地争论道,要严肃对待这些结论。这些想法并非来自某些特例独行者“我想到了!”的一拍脑门式发现,而是来自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且缓慢积累的证据——广泛的考古挖掘,更优秀的年代测定技术,以及对历史记录更多的研究。当然,这些记录仍旧是片面和间接的。
西班牙人几乎销毁了玛雅人的所有书籍,仅有4本幸存(尽管仍有15000份文字样本残存于遗迹、壁画和陶器上),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并没有现代研究人员能理解的文字形式。“从这些来源收集事件就像是试图通过公园雕像上的匾额来了解美国内战一样,”曼恩承认。“有可能,但很棘手。”
因此证据趋向于趣闻逸事,并且会受到许多猜测。我们看到了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叙述的“人口稠密”的美国海岸线;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记录的南线沿路的“忙碌人群”;以及亚马逊探险记录者加斯帕·德·卡瓦哈尔(亚马逊女战士神话的创作者)的评论,他记述了遍及河岸180英里、富有而好战的滨河城镇。后来的探险家们报告中空无一物的这片相同区域被认为是大规模死亡的证据。怀疑论者将以此作为证据的人们比喻成“有人发现一个空无分文的银行账号,并声称这个空账号里曾经存有上百万美元,”曼恩写道。
不幸的是,也没有出现哥伦布时期的大规模流行病记录。然而后来数次大规模流行病的故事引人注意:18世纪的天花传染病大爆发始于现代的墨西哥城,并如同一连串鞭炮般经过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向南传播,向北则沿着圣菲贸易通道进入美国西南部,这一切都发生在四年之内。碰巧上述地区的印第安人传说与绘画中确然记述了失去父母、小孩和群落的悲剧。1794年冬天拉科塔族印第安人的人口调查中形象记录了这样的情景:一个浑身脓包的男人独自在他的圆顶帐篷里开枪自杀。
曼恩理所当然地将他的调查专注于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发现,但也希望能在经济学、社会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方面有更大突破。遍及两大洲的大规模灭绝真的发生过吗?作者访问了数名医学研究人员,发现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证据仍旧略显单薄:即使是在此一个世纪前的黑死病不过才杀死了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不是95%。并且我们从现存原住民的口述历史中也几乎从未有所耳闻——包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瓜希罗人,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以及北美印第安人,所以怀疑他们是否真能说清楚这些问题。
但是曼恩已经记录下了我们对世界发展观点的一个重要转变,我们的小孩上初中时不会再在课本中学习的一点。
《1491》读后感(九):值得大肆张扬的人类历史
以史为镜,一般理解是反射镜,通过先人、别人,照见(己之)兴衰和更替。不过理解成折射镜(望远镜),或许更解释得通。因为历史并不总是方便读者比对,越是陌生的反而越能够拓展认知和行动的边界。倒是研究者或读者,总不免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去解读他人的历史,造成歪曲甚至矮化。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目标就是为被主流媒介普遍歪曲和矮化的、哥伦布到达以前的美洲本土历史正名。为何说是被主流媒介歪曲?因为在美洲历史和考古史的专业圈子里,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美洲本土历史的复杂和成就已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不过,这些认识却长期不被圈外人所知。说起印第安文明,一般人大概能想到的也就是玛雅、印加、阿兹特克,但已被发现的成就辉煌的美洲帝国事实上远不止此数。奥尔梅克等古代美洲文明至少取得了与旧大陆不分轩轾的成就,但四大文明发源地(全部在旧大陆)的说法仍然牢牢占据公众的认知。新世纪的美国高中世界史教材,也只有9页内容涉及哥伦布以前的美洲。美洲本土历史的研究成果为何无法进入公众视线?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人与印第安人无涉,因而对此毫不关心;部分是因为印第安人相关的某些群体,包括原住民社团自身及某些环保团体,希望保持其“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因此刻意忽视或反对与此不符的研究成果。此种背景下,身为记者且长期跟踪美洲本土研究的曼恩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将到目前为止、学界所了解的、美洲人的真实成就大书特书,以推送到公众眼前。他确实做到了。作为一部考古及历史研究领域的科普综述类作品,本书目的明确,主题也也很突出。全书以三大部分对应三个论点:一、1491年前的美洲人口规模非常高(大致在5000万到1亿这个量级);二、美洲本土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度和多样性;三、印第安人曾大幅改造美洲自然环境以使其满足自身需要。在三个论点中,人口规模是文明复杂性(即第二个论点)成立的必要前提。第三点则是专门讲述作为基石物种的印第安人曾如何用刀与火持之以恒地改造环境(北美大草原和亚马逊雨林因而是天人合一的产物)。这既是用来反驳“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迷思的,也可以视作多样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展开。所以,本书第二部分力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历史悠久、环境多变的美洲,存在丰富的素材可以支持这一论点。为使论证引人入胜,作者没有死板地按时序或区域排列,而是随需将各个时空美洲的文明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令人信服的叙事链条。这链条中,有塔万廷苏尤跨越32个纬度的迅猛扩张,有瓦里以融雪浇灌的高原梯田,有蒂亚瓦纳科永不停工的神庙都市,也有马若拉在雨林中培育的千年果园,以及其他种种在幻想小说中都难以得见的惊人事物。支撑这每一事物的,都是一整个族群的兴衰历史。但同时,每一个族群也只在印第安人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占据一条枝桠。
在最后一章,曼恩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与等级森严的欧洲分道扬镳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自由和平等的重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同样推崇自由平等的易洛魁联盟的影响?富兰克林或杰斐逊并未在日记里奉某位印第安人为精神导师,这个问题没有书面证据支持。但考虑到当时人种混居的状况,说他们对易洛魁印第安人有切身的观察和体会应对所言不虚。这种体会对《独立宣言》的作用或许已不可量化。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人类社会是否还能从往昔的印第安人身上学到些什么?目前世界超过一半的重要农作物是印第安人培育的,这包括但不限于玉米、土豆、南瓜、木薯、花生、番茄、辣椒和烟草。没有美洲的农作物,人口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不可能。这证明作为整体的人类已经从印第安人的成就中受益良多。不过,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的不应只有这些。相比旧大陆人,印第安人缺乏机械和畜力,在金属冶炼等方面也有所不足,但他们却能够建立起与旧大陆同等规模甚至更为辉煌的人类聚合体,在美洲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中留下此起彼伏的文明痕迹,这足以说明其别有所长。善学者,从中可见的当不仅是昔日之伟大,更应是未来之广阔可能。
另,把地图反折作为封面很有新意,然而暴露在外的折痕太脆弱了,在书包或书架上抽插不了几次就破损了。
P264:注释中的“1150年”为“1550年”之误;
P284:“51华氏度(约零下17.2摄氏度)”,大概是“1华氏度(约零下17.2摄氏度)”之误;
P340:“1672年”应为“672年”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