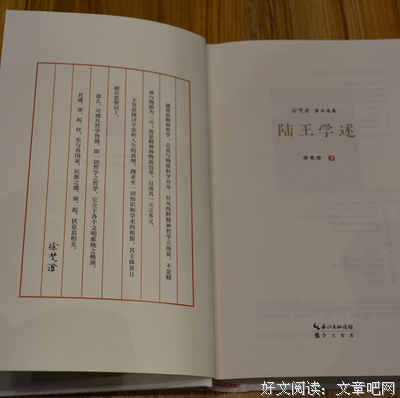
《陆王学述》是一本由徐梵澄著作,崇文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陆王学述》精选点评:
●先生是真爱孔孟之道啊
●心花同寂,宇内穷极,秉一心而天地之理得。
●《教言摘录》一章极好。
●中间的几章最为精彩
●果然是“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读不来读不来。
●几年前读过本书打印本,可读。今天这样的书拿来装逼都不够分量了。
●徐梵澄,研究过印度古教,也研究过德国哲学,总而言之,是冲着精神哲学。不过,在探讨中国精神哲学的时候,他找到了陆象山和王阳明作为精神哲学的代言人,在晚年写下了这本小册子。这本书最早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印行,后来徐梵澄文集又出了一版,崇文书局这版应该是第三版,小开本精装,文字舒朗,价格高
●接续牟《十九讲》,楬櫫船山、东原之学
●我悟性极差,并不能领会徐先生的高妙,感觉只是重温了一遍传习录。
《陆王学述》读后感(一):研究陆象山、王阳明心学的大作
徐梵澄晚年从整个世界哲学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这一脉心学,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最好这方面最好的著作了。诚如其在本书第4章“为何与如何”的最后指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仍其多种称名,如理学、心学、道学等,但舍精神哲学一名词而外,亦无其他适当且能概括无遗的名词可取。其所以异于纯粹思辨哲学者,则在乎躬行实践,内外交修,求其实证,即所谓“自得”,态度仍是科学的,脱出了玄虚。终期于转化人生,改善个人和社会,那么,亦可谓此为实用精神哲学。而又有进者,精神所统辖者如此弘大,故此哲学亦广阔无边,正不宜精细界划,中间存有充分发展的余地,留给将来。人类的心智永是进步的。
《陆王学述》读后感(二):程海霞 | “大知觉性”及其实现——徐梵澄论王阳明龙场彻悟之基本原理
(本文原刊于《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
内容提要:在《陆王学述》一书中,徐梵澄在证成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基础上,对其间的彻悟原理作了极为清晰地阐述:首先,“大知觉性”为龙场悟道得以实现提供了本体依据;其次,“大知觉性”的层次划分使得彻悟的位次得以明晰;再次,理智作为较高知觉性为彻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最后,彻悟的实现意味着知觉性层次的跃迁。由此亦反映出徐氏对神秘主义、心灵体悟所作的独特定位。其不仅仅是对“一悟便了”的钟情,更是对定然真实的推崇、对儒佛融合的精思。
关键词:大知觉性;彻悟;精神哲学
在阳明学的现代研究中,徐梵澄(1909—2000年)于20世纪90年代初撰成的《陆王学述》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徐氏借陆王心学而标举的“精神哲学”,就其名称而言,过于笼统而未显陆王心学的精义;二是徐氏的“异学”[1]经历使其著述仍具“从自己心上考验过”的传统特质,此与国内主流研究强调理性分析的导向有所出入。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时代发展,阳明学因时而化的融合式研究将是大势所趋,而徐氏所倡导的“立于各个文明系统的顶端”的“精神哲学”可以作为一个全新的基点。不仅如此,理性分析与心灵体悟之间的互惠也将成为学界之共识。此在阳明学的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对阳明龙场悟道的探讨。有基于此,对徐氏《陆王学述》中体现阳明龙场经历的“居夷处困”及其体现龙场悟道性质的“先知和彻悟”部分——尤其是后者,进行分析式解读,将有助于呈现徐氏“精神哲学”在阳明心学上的精密思考,有助于探究心灵体悟的学术定位,从而为阳明学研究的意义拓展提供参照。
引子
徐氏证成阳明龙场悟道的方式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阳明是时之撰文来说明。在论及阳明“居夷处困”的经历时,徐氏提及阳明所撰《瘗旅文》,并指出:“那时北人南行,其困难可想。而阳明罹宦官之祸,其文仅有悼伤之意,略无怨怒之情,非学道有得,诚有难于处于此种困境中者。”[2]二是通过《易经》“旅”“困”两卦之含义来说明。徐氏言:“《易经》是一部藉人生实事而明抽象义理之书,有‘旅’卦,也有‘困’卦。‘困’有亨通之理,故曰‘困亨’。‘旅’亦‘小亨’。皆言‘贞,吉’。”三是通过其境界及其事功与为学之大成来说明。徐氏言:“在阳明是一番大磨练,大彻大悟,从此身心内外表里如一,不但成就了伟大事功,几乎成了一生民之大教主。论其学至此已经三变,乃跻于大成。”[3]
此后两种证成方式,就徐氏思想的内在逻辑而言,实是一种,即以《易经》之原理,说明阳明大彻大悟而成大事功与大学问之效果。然而,对《易经》的体悟,于阳明龙场悟道尤为重要,因此,为展示阳明思想历程的方便,故以上分而为两点进行说明。在对阳明龙场悟道作了以上证成之后,徐氏极为详细地分析了龙场悟道所涵盖的“彻悟”原理。
一、“大知觉性”之宇宙本体
徐氏著《陆王学述》而“一系精神哲学”,将“生命”“思想”(“思维心”)、“情感”(“情感心”或“情命体”)、“身体”以及作为内核的“心灵”(“性灵”)统而为“精神”,强调研究“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即为“精神哲学”。[4]有基于此,在分析阳明龙场悟道之前的“先知”经历时,徐氏将此“精神”理解为“大知觉性”。此实为分析阳明龙场悟道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首先,徐氏以“感应”之“能”与“所”诠释阳明的“先知”经历。《王阳明年谱》载阳明31岁时,“八月,疏请告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徐氏据《王阳明年谱》而表述为“在山洞静坐,能知道友人来访,遂遣仆出迎”。徐氏虽言及“阳明下决心入洞习静时,已渐次得到相当的通力,然旋即弃去,谓此种先知为‘簸弄精神,非道也’”,但仍认为,“‘消息甚大’,这可说是某种感应”,“先知与感应相联,则其作用必有能感与所感两方面……必是一方面有发此消息者,另一方面有接收此消息者”。[5]
其次,在追溯“能感”与“所感”“中间”的“传达的媒介或联系”时,徐氏提出了“大知觉性”之观念。其言曰:“弥漫宇宙人生是一大知觉性,这知觉性之所表便是生命力。或者,如某些论者说弥漫宇宙人生只是一生命力,而这生命力之所表便是知觉性。两说是同一事,只是后说时时有无生命物一外在事实在相对,较难分说。毋妨假定知觉性是体,生命力的活动便是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此即宋儒之所谓‘体一’。而各个人皆是此同一知觉性的中心点,各个人彼此不同,此即宋儒之所谓‘分殊’。在人人皆有此共通之知觉性,共通的生命力,此之谓‘气’。气有同,则共鸣,乃相感。此即《易经》之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6]徐氏认为,此“大知觉性”即是“弥漫宇宙”的“生命力”。“知觉性”是体,“生命力的活动”是用。体用不离。由此不难看出,此种“大知觉性”即是徐氏所强调的“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即“精神”。徐氏认为,呈现为“生命力活动”的“各个人”“皆是此同一知觉性的中心点”,皆是这一“大知觉性”的不同会聚点[7]。此处包含着“体一分殊”的思想。所谓“体一”是“同一知觉性”即“大知觉性”,所谓“分殊”是指由此不同的会聚点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力活动”。因为各人不同的“活动”,即是“大知觉性”会聚点的呈现,因而具有“共通之知觉性”。此“共通之知觉性”在作用上,即是“共通的生命力”,徐氏称之为“气”。在各个具体的生命力中所包含的“生命力”的“共通”部分,即是气之同处。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共鸣”“相感”。由此来看,“能感”与“所感”的根源在于“大知觉性”之作用,即大生命力之存在,也即是气之存在。
最后,徐氏还用此“大知觉性”解释“发此消息”与“接收此消息”之可能。徐氏言:“于此我们又当假定凡人皆有一生命力的氛围,周绕全身。”共通的生命力是大知觉性的作用,而人皆是“大知觉性”的会聚点,因而,具有共通的生命力,具有气,此气即是“生命力的氛围,围绕全身”。徐氏虽以“假定”为言,然其又指出,孟子的“浩然之气”,便是“此知觉性的遍漫,充塞宇宙”。[8]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徐氏以“浩然之气”说明“生命力的氛围”从而说明“知觉性”的“遍漫”时,此已不是“假定”,而是证实。此后,徐氏明确指出:“由此一中心发出的信息,很易传达到另一中心点,穿过那另一氛围而注入其前方知觉性中。譬喻说,同此一水,一波传到另一波,造成了相同的震动。”[9]由此来看,“中心”不仅仅是“大知觉性”于人之会聚处——不同的人即是不同的会聚处,即是不同的中心点——而且还是“信息”的“发出”者,是发散点。“此一中心发出的信息”即是于“此一中心”(此人)而有的“氛围”(“气”)。“穿过那另一氛围”即是指两个中心点(两人)氛围的交接,有交接,便有各自的呼应。此呼应,如同不同水波的交接。
以上乃徐氏对阳明“先知”经历的理解,其所提出的“大知觉性”及其所会聚而成的“中心点”,以及这些“中心点”在体用层面的相互关系,为其诠释阳明龙场悟道奠定了宇宙本体论基础。
二、“大知觉性”之层次
在作为宇宙本体的“大知觉性”与作为阳明龙场悟道性质的“彻悟”两者的关系上,徐氏提出“大知觉性”的层次划分理论以及具体层级的上下双涵关系理论,清晰呈现了“彻悟”之过程。
首先,徐氏以灵妙与否作为宇宙大知觉性层次划分的标准。“我们大致是假定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在一知觉性中。若想象为直线,则由下至上可分许多层级,最下一层是冥顽不灵,最上一层是至灵至妙。实际它不可想为直线,最上者亦潜在至下者中。但就方便说,如同层级的分别是可存的。”[10]在徐氏看来,在指向上下两端的大知觉性的直线中,有一个自下而上、自冥顽至灵妙的层级。
其次,在“大知觉性”的具体层级中,有一级为“寻常知觉性”,也就是意识层,具有相互涵摄的上意识与下意识。“我们常人生活是在寻常知觉性里。此即告子之所谓‘生之谓性’,即动物知觉性。但寻常知觉性中是上、下双涵;此知觉性通常有说为意识,即上意识和下意识,或潜意识。”[11]此“寻常知觉性”是与“常人”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常人处于寻常知觉性层级。此亦是“通常”所谓的“意识”层。其包括“上意识”与“下意识”(潜意识)。用大知觉的上下层级来看,“上意识”与“下意识”的差别实在于分别趋于灵妙与冥顽的差别。徐氏将此种“寻常知觉性”还解读为告子的“生之谓性”(“动物知觉性”)。此“动物”之表述无疑是就其包含人在内的广义而言。孟子强调人禽之辩,人禽之辩实决定着浩然之气的产生,当不属于这一层级。徐氏以“动物知觉性”来表达其对人禽共有的知觉性的统称,并强调其中包含着“上、下双涵”的显意识与潜意识。
再次,在“包括人的全部知觉性”的“心”中,有道心人心之高下区分。“旧说‘心’是颇笼统的,这中间包括人的全部知觉性。高、上者称之为‘道心’,中、下者指称为‘人心’,统是一心,只是一知觉性。高者‘道心’,即孟子所说之性本善之流衍。”[12]徐氏在动物知觉性或意识的基础上,还举出一个“包括人的全部知觉”的“心”层级,分而为下之人心与上之道心两个层面,而孟子之性善即是此“心”层级之道心层(上层)。推扩来看,孟子以内在的仁义锁定人禽之辩,以“集义所生”定性“浩然之气”,皆直指此道心层。除孟子之性善外,徐氏还以阳明后学“满街都是圣人”之“感觉”为“寻常现象”来证实这一道心层的存在:“讥阳明学派者,辄诋其‘满街都是圣人’,谓为大失。但这在学理上是可说得过去的,所谓‘个个人心有仲尼’,在王氏是两次有门徒如此感觉,……那么,也是一寻常现象,但与世俗真实相违。”[13]此处徐氏所言及的“与世俗真实相违”当是指“心”层级中的道心层(上层)与人心层(中下层)之具体关系。
最后,“灵感”或“彻悟”乃是为“高层的知觉性”所“不自觉”“采纳”的“识感印象”从“储藏”状态“偶尔倾出”或“发露”的结果。徐氏以“本不识字却背得杜诗或希伯来文诗篇”为例,在强调其为知觉性作用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其间的经过。在总体倾向上,徐氏指出:“必是常听诵杜诗,……潜入乎下意识,也藏在那里。一遇到某种特殊心理作用的机缘,便发露到表面知觉性中来。”对于“一遇到某种特殊心理作用的机缘”,徐氏将此表达为“这必是心理作用经过了一番紧张”;而对于“潜入乎下意识”的内容的“发露”,徐氏言:“如同一个川堤塌破了,水便从高坪奔腾下注。”此处有一个“下意识”与“表面知觉性”的对比,是意识之潜与显之两层。在两者之具体关系上,在意识从潜到显的具体经过上,徐氏指出:“常时种种识感印象,皆可视为‘种子’,采纳入此高层的识田。”[14]言“采纳”,当是为较高的知觉性所“采纳”,而“高层的识田”,当是指为较高的知觉性所采纳而形成的新入种子与已入种子的生长地。
而于此“采纳”,又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或自觉或不自觉,自觉地是纳入寻常或中层知觉性中,这便成为记忆而可呼出。未自觉而被吸收的,便如同种子储藏在知觉性中,或变形或不变形,偶尔倾出于梦中。这在通常被误称为所谓‘灵感’,进一步方是‘彻悟’。”[15]贯通而言,较高知觉性对不同种子的“采纳”程度不同,从而形成了“自觉”生长与“不自觉”生长两种情形。自觉生长而形成“寻常知觉性”或“中层知觉性”中的记忆,随时可呼出。不自觉生长,即是以这一较高知觉性未曾自觉的方式在生长,如同做梦。而梦是这些不自觉的生长的变形或未变形的状态。其与记忆的差别就在于其是不自觉的生成,具有偶然性,不可随时呼出。然其一遇机缘,终要发露出来。徐氏以之为“灵感”或“彻悟”。在“灵感”与“彻悟”的差别上,徐氏言“灵感”的“进一步”为“彻悟”,大约是就其系统性而言:较为零星地发露,当是“灵感”;较为系统地发露,当是“彻悟”。
三、作为知觉性的理智
在对彻悟原理的分析中,在“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别上,徐氏提及了“理智”或“理性”这一概念。徐氏对理智进行了充分的诠释。
其次,对理智与知觉性本体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事实上知觉性受着生命力的推动,白天的作用亦有如夜间,或者可说常人白天也在做梦,其记忆,即过去的种子或印象浮到了表面知觉性中来;其联想,即多个种子集聚或结合,亦在此表面知觉性中,但一皆受了理智的约束,所以人寻常的行为,不致怎样荒谬。”[17]此时,知觉性与生命力不再是体用关系,而是互为体用。此时,生命力是体,知觉性是用。由此可以说,由于知觉性与生命力是一体两面,因而,由于生命力的推动,或知觉性由里及表、由潜及显的趋势,种子终要成长,终要浮到表面的知觉性中来。此知觉性本体就是大宇宙,就是一大全。其中的识象,凝而为种子,终是要生长。而记忆与联想,便是受理智分别监管而形成的知觉性之表面,是显在的意识。
再次,以“理智”引出对宋学中的“心”或“性理”的理解。“在宋学中,这理智也是‘心’,但也说为‘理性’,或‘性理’。后者的范畴似较前者为大,‘性理’统摄整个人性之理,则其间非事事皆合理性,统之曰‘心’,所以此‘心学’又称为‘性理之学’,是就内容而言。”[18]徐氏此处所言宋学,当是指汉宋对言之广义宋学,即指宋明理学,而其所言的“心学”与“性理之学”,亦指宋明理学总体。而在狭义上,心学与性理学实分属于心学与理学两个系统。在徐氏看来,宋学中的心学或性理之学的内容,不止于“理智”,而大于“理智”。其原因在“其间非事事皆合理性”,亦即其间除了“理智”分别或监管这种高层知觉性的“自觉”外,还包括某种“不自觉”。因此,心学或性理之学,其与大知觉性的涵摄面实是相同的。
最后,在此大知觉性的涵摄中,理智又是最为重要者:“但所着重者,仍是性之上焉者,孟子的恻隐、辞让、善恶、是非之心,皆上知觉性之德。属下层的食、色,则入乎本能之内,没有什么应当特殊加以存、养、扩充的道理。本能即是不学而能之能。”[19]在大知觉性的层次中,理智乃“上知觉性之德”,而下层知觉性则为人之食色之“本能”。由此来看,理智的分别、监管程度强弱实与知觉性之上下区分相配套。此处,徐氏对于本能所作的“不学而能”的理解,实是就“生之谓性”的寻常知觉性而言,表明食色欲望的种子本身未经理智、未经分别监管而不自觉发露到表面知觉性。在此意义上,越是本能,越是不自觉。越是本能,越不可据此而加以存养扩充。由此来看,在徐氏这里,正如理智是“上知觉性之德”,与理智相反的、具有“不自觉性”的“本能”乃是下知觉性即动物知觉性之特征。
四、理智的纠缠与彻悟的抵达
在理性与彻悟的关系上,徐氏认为,“时常是最高理性堵塞了彻悟之路”。就知觉性之原理而言,因为彻悟的产生,缘于种子不为所觉地生长。而一旦理智的分别与监管的涵摄变大,那么,未被“自觉”的可能性就越小,就越不能产生灵感,更不必言彻悟。然徐氏所言之内涵,并不如此。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知晓。
首先,彻悟之前提在于“识田中只有高等知觉性充满弥漫”,而此种状态要修习多年。“可以假定——这里只是假定——是有人修为得法,不急不缓,在潜意识中清除了一切良莠,即识田中只有高等知觉性充满弥漫,归于纯净了,即儒家所谓‘人欲净尽’。这是极困难的事,所以往往要修习多少年。”[20]此是理智分别与监管作用的彻底实现,而非将理智局限在特定的范围,以便为灵感留下地盘。此处的“高等知觉性”的弥漫,当是指理智作用的发挥达到了完全极致之状态。有基于此,不难看出,理智实有两种状态。一是处于自觉与不自觉相对峙的警惕、收敛状态;二是处于自能“自觉”的放松、发散状态。而唯有警惕、收敛,才为种子在识田中的零星发露提供可能。因此,灵感是零星的、微型的体悟。唯此放松、发散,才有弥漫之可言。彻悟并非灵感的量的逐渐增加,而是与“高等知觉性”相配套的理智“自觉”能力的最大化。灵感是相对于种子未被理智所监管、忽而表面化的知觉性。可见,灵感的产生,是知觉性本有的表面化的趋势以及相应的机缘,促使了种子在未被理智自觉的状态下而偶然表面化的结果。
其次,彻悟之先声在于“整个内在自觉性”要“受警策”。“久久之后,整个内中自觉性受警策到了最高限度,紧张已极,这时只要外物轻轻一触,不论是见到什么事物或听到什么声音,便如一气球爆破了。似乎一跃到了另一世界,撞开了一大建筑之暗门,见到另外一些琼楼玉宇。”[21]所谓“整个内中自觉性”,即是指理智的弥漫、自信而自然之状态。所谓“受警策到了最高限度,紧张已极”,实是指理智自觉的能力达到了最大的灵敏度。这一灵敏度与理智的弥漫并不矛盾,一定意义上,唯有弥漫到无所不在的状态,其灵敏度才可达到极限。在此意义下,机缘的触发,可使“整个内中自觉性”实现豁然贯通之状态,从而发生质的、彻底的跃迁。由此来看,与灵感不同,彻悟乃是修行到“整个内中自觉性”的全面统一的状态之后,必然触机而发的结果。
最后,龙场悟道是彻悟之境的实现。对于彻悟之境,徐氏有明确的表达:“一切皆似与寻常所见的不同,改变了,或更美丽了。知觉性似乎已经翻转过。……这时客观环境未变,只是主观心境已变,多人感到是这方是真实,是宇宙万物之真面目,只是光明的倾注,即儒家所谓‘天理流行’,而紧张既除,只有大的喜乐,是说不出的美妙,……是彻悟了。”[22]“彻悟”是知觉最大灵敏度(紧张)的忽然消除,是知觉从弥漫状态跃迁进新的层面,是一种更高的知觉性的产生。唯有如此,在前一种知觉性基础上所获得的、由“客观环境”与“主观心境”所构成的、定然的真实,在新的知觉性层面上,已被重新定位。这一新的定位,乃是最后的真实,是最大的喜乐,是“天理”之“流行”,是“光明”之“倾注”。由此,徐氏以为,王阳明龙场“中夜豁然大悟”实为“悟入了宇宙知觉性本体,从此一切皆了然无疑”。“宇宙知觉性本体”即是“新的知觉性层面”。正是有此体验式的定位,“一切”才“皆了然无疑”。徐氏特举阳明龙场悟道时“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为言,说明其“只是高等知觉性中的所涵,向其寻常知觉性中倾注”,认为“总归即此亦是‘道’,是‘见道’的经验之一种”[23]。由此,阳明龙场悟道的“彻悟”性质,得到了极为清晰的说明。
五、思考
关于阳明的龙场悟道,陈来先生曾以神秘主义加以定性。陈先生1987年尝撰文《神秘主义与儒学传统》,后改题为《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附于其1990年撰成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之后,其言曰:“因为已有此文,故本书正文部分对阳明思想中的神秘体验问题未加特别讨论。”[24]此后,徐梵澄于20世纪90年代初撰成《陆王学述》,对龙场悟道的彻悟原理作了极为清晰的论述。此无疑涉及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问题,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神秘经验”的合法性问题。
在冯友兰那里,哲学的合法性在于“可言说”[25]。在“贞元六书”的“新理学”中,冯友兰最初在《新理学》一书中强调哲学之思即是逻辑的方法。其后,在《新原人》一书中,冯友兰依人的觉知程度,将人生判出自然、功利、道德与天地等四重境界,由此造成哲学的逻辑方法与最高觉知之间的紧张。最终冯友兰以“负的方法”为此种最高觉知命名,从而使其获得了哲学上的合法性。此在《中国哲学小史》中有明确表达。对于“负的方法”,在此我们不妨作一划分:在广义上,其包括神秘体验的内容;在狭义上,其主要指神秘体验的实现方式。贯通而言,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于“真际世界”的探讨,即是关于更广意义上的人生境界的逻辑言说:就更广意义的人生境界而言,其仍具有神秘性;就逻辑言说而言,其为正的方法。而在《中国哲学小史》中,负的方法则有明确的实践指向——“静默”[26]。由“静默”而抵达的“神秘主义”[27],变成哲学的最后、最高状态。
与冯友兰将神秘主义推向哲学的至高点以确定其合法性有所不同,陈来先生将“神秘体验”视为宋明心学的“一个心理经验的基础”——既不普遍也不客观,强调“必须以完全清醒的理性来审视儒学的神秘体验”,并指出“熊十力哲学已经以一种完全不依赖神秘体验的全新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本体论”。[28]
对于龙场悟道,徐梵澄另辟蹊径,从大知觉性及其实现角度对其进行疏解,不仅对“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言说”,而且还将此神秘体验视为阳明“身心内外表里如一”的起点、“成就伟大事功”且“几乎成了一生民之大教主”的基点、为学“跻于大成”的标志。在阳明历“三变”而成的为学经历中,徐氏最重王阳明同样具有神秘体验性质的“先知”经历,以“大知觉性的宇宙本体”说明“先知”之原理,并视其为阳明“学术思想一大转折点”。[29]徐氏对阳明先知经历的此种推许,不同于阳明本人、阳明弟子以及学界主流的定性,后者皆以龙场悟道为阳明思想的“一大转折”。徐氏基于大知觉性的存在及其实现,对阳明“先知”经历与龙场悟道所作出的“言说”与定位,亦呈现出其对神秘体验的定位。神秘体验或意味着思想的大转折,或意味着为学之大奋起。此时的神秘体验既不在冯友兰所言的哲学最高点——唯有“静默”,亦不在陈来所言的哲学的最低处或哲学之外——心理经验。
徐氏对神秘体验的定位,实蕴含着“一悟便了”之情结。徐氏在言及“大知觉性”中“人的全部知觉性”层面(即“心”层面)中的“道心”时,曾以阳明后学中的“满街都是圣人”为例,说明其在“学理上是可说得过去的”。其所提及的“在王门是两次有门徒如此感觉”一事在王阳明之《传习录》(下)中有载:“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30]阳明在“锻炼人处”能够因材施教,“感人最深”,实在于其将两“门徒”的“如此感觉”置于各自的个性特征中加以有针对性的教导。此是一种在调整中前进的渐修立场。与此不同,徐氏立足于探讨“见满街人都是圣人”之可能性,力图以此证明“人的全部知觉性”中的道心层的存在。
徐氏此种“一悟便了”的情结,就学理而言,虽是悟修关系中重才质天赋之一端,却又为因材施教、触机而发提供了可能;就实践而言,虽或是电光石火般个体感受,却又为定然真实、非义袭而取提供了保证。实际上,为避免主观性,徐氏的“言说”,多以一种“假定”的形式呈现出来。徐氏在言及知觉性是体、生命力活动是用时,用了“毋妨假定”一词;在言及“凡人皆有一生命力的氛围”时,用了“又当假定”;在言及“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在一知觉性中”时,用了“大致是假定”[31]。此“假定”看似有假设的意味,实质乃徐氏自身之体验,为避免在客观性上受到质疑,便以此方便的形式表达出来。此“假定”与以知觉性层次为直线的“若想象为”“实际它不可想为”“但就方便说”等表达实有不同。后者完全是假设,前者则是徐氏本人的真实体验,而且是具有开放性的体验。此种体验不武断,畅导交流与呼应。
不仅如此,徐氏对神秘体验的清晰言说,实体现了儒佛思想的高度融合。徐氏推崇室利阿罗频多的新瑜珈思想,在其所翻译的《神圣人生论》一书中有“知觉的力量”“无上真理知觉性”“自我知觉性”之论述、《瑜珈的基础》中有“生理知觉性”的论述、《综合瑜珈论》中有“宇宙知觉性”之论述,皆为其以大知觉及其层次性讨论阳明龙场悟道提供了理论依据。此种大知觉性乃徐氏所倡导的精神哲学的核心。徐氏1981年在《神圣人生论出版协议》中言:“内容集印度韦檀多哲学之大成,所据皆《黎俱韦陀》及诸《奥义书》。数千年精神哲学之菁华皆摄。以‘超心思’为主旨,……虽时言上帝,然与西方神学相远。其宇宙观往往与我国大易之旨相合。稽于复性及变化气质之义,转与宋五子及陆、王为近。”[32]由此不难看出,徐氏在《陆王学述》中对阳明龙场悟道的疏解,实是其所建构的以大知觉性为核心的精神哲学的展示。就此展示而言,在大知觉性的寻常知觉性之层次与心之层次的关系,徐氏或未作清晰的说明。此处若作深入地挖掘,儒释之异同或可进一步呈现。由此来看,哲学就是借助于对“神秘体验”的不断追问,重新划定“清晰”与“不清晰”的界限。
[1]“梵澄无似,少学外文,长治西学,自华夏视之,异学之徒也。其居域外盖三十有七年,居域外不能无故国之思,所撰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学,出以西文者,自欧西视之,又皆异学也。”徐梵澄:《异学杂著·序》,转引自孙波:《写在前面的话》,《陆王学述》篇首,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版。
[2]徐梵澄:《陆王学述》,第83页。
[3]以上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84页。
[4]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5页。
[5]以上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77、89、93、95、96页。
[6]徐梵澄:《陆王学述》,第96页。
[7]按:笔者以“会聚点”来表述徐氏此处所言及的“中心点”,或易于呈现“弥漫宇宙人生”的“大知觉性”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影响。
[8]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97页。
[9]徐梵澄:《陆王学述》,第97页。
[10]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0页。
[11]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0页。
[12]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1页。
[13]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1页。
[14]以上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2页。
[15]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2页。
[16]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2页。
[17]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2页。
[18]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2—103页。
[19]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3页。
[20]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3页。
[21]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3—104页。
[22]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4页。
[23]徐梵澄:《陆王学述》,第104页。
[2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25]冯友兰言:“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冯友兰:《贞元六书》(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6]冯友兰言:“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27]冯友兰言:“神性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28]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413页。
[29]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84、77页。
[3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31]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第96、97、100页。
[32]徐梵澄:《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陆王学述》读后感(三):李卓 | 精神哲学与陆王心学——以徐梵澄《陆王学述》为中心
[本文原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本文以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为中心,考察徐梵澄对陆王心学的诠解。在徐梵澄看来,重温陆王是为了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徐梵澄从精神哲学的立场出发,借助“知觉性”的概念,对象山、阳明之学的心性与功夫做了独特的诠释。徐梵澄又以科学的态度和方式来研究“精神知识”、“玄秘科学”的领域,对宋明儒者精神修为中的“前知”、“顿悟”做了理性主义的说明。
关键词:徐梵澄 陆象山 王阳明精神哲学 知觉性
徐梵澄(1909-2000),原名琥,湖南长沙人,翻译家、著名学者。他精通梵、英、德、法等多重语文,系统迻译了印度韦檀多哲学的主要经典[1],有“当代玄奘”之誉,刘小枫称他为兼及中、西、印三大文明学术的大家[2]。
近代以来关注印度哲学的学者中,梁漱溟、汤用彤为人熟知,二人皆偏重佛教,主要以“印度哲学史”的方式逐一考察佛教以外各家的哲学思想。唐君毅的研究[3]以翻译文本为基础,倚重了西方和日本学者成果,并谦称自己“于印度之宗教哲学所见太少”[4]。徐梵澄则是直接从研读古印度哲学经典文本入手,对释迦牟尼诞生以前的学问——古韦檀多(Vedanta)哲学、特别是对印度近代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英文名SriAurobindo,1872-1950,被誉为“圣哲”,与“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并称)思想的理解和绍述上,现代中文世界的学者还没有能超过徐梵澄的。
徐梵澄的学术工作以迻译为主,所治则为精神哲学(spiritual philosophy)[5]。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译介以外[6],他还有一部重温陆、王一脉心学,吸收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探索建立中国的精神哲学的著作,即《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是书大约在1990年开始写作,1993年5月勘定完成,次年初版,又尝题作《陆王哲学重温》。其缘起,是徐梵澄应《哲学研究》之约作一谈王阳明哲学的文章,铺开后越写越长,于是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方向,由文而成书——“王阳明学述”,继而又加充实之功,写成“陆王重温”一书。[7]稿成只有十万余字,意在以最简单的文字来表达,不多说话。编辑认为字数太少,请徐梵澄再做补充,于是他又自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摘录阳明“教言”两万余字。材料取舍之间亦见其精神旨趣,就此而论,“教言摘录”或可谓以精神哲学为选材宗旨的“阳明粹言”。
徐梵澄用“精神哲学”来观照“陆、王学术”,是否提供一种绝对正确的理解,或许见仁见智,但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诠释,他对宋明理学的把握与众不同,而有其特色。他所提倡的精神哲学,迄今学界注意不多,也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本文即以《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为中心,考察徐梵澄对象山、阳明一派学术的诠释特点,以及他对“前知”与“顿悟”所作的说明。由于书中对各部分都有较为清楚的界定和解说,所以本文不免“寻章摘句”,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一、陆王心学是精神哲学
1.精神哲学的意涵
徐梵澄的叙述多依韦檀多学立言,有必要先对其稍加介绍。韦檀多学的古典是诸古《奥义书》,今典则是阿罗频多所著书。据阿罗频多之义,宇宙间惟有一“大梵”是绝对的“存在”,可分其为“超上”、“宇宙”、“个人”三面,其性质是“知觉性”。宇宙万物皆在大梵之中,大梵亦在万物之中。“存在”有七个活动原则,以七条河流或七道光明象征:“物质”、“情命”、“心思”、“超心思”、“真”、“智”、“乐”,彻上彻下只是一个“知觉性”。印度精神哲学分判上下两界或两个半球,“超心思”介于中间,贯通两界。可约略图示如下:
这里认为宇宙本原即是悦乐,是印度思想所独创,有其特色。对人的理解是:“吾人所以为吾人,及吾人将为吾人者,其力量乃在一高等‘精神’之权能中。我辈生存之本质,乃宇宙间无数人格之‘精神’自性也。吾人之性灵,亦即此‘精神’之一分。在此自性中,每人皆有其转变之原则与意志,每一心灵,皆自我知觉性之一种力量,所以构成其中神圣性之理念者,由此而引导其作用与进化,及自我发现与自我表现,终必趋于圆成。此即吾人之自性,亦即是真性。”[8]主张人之为人在“精神”自性,人生目的在于自我完善,希圣希天。
下面来看徐梵澄所谓的“精神哲学”意涵是什么,他说:
而人,在生命之外,还有思想,即思维心,还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体。基本还有凡此所附丽的身体。但在最内中深处,还有一核心,通常称之曰心灵或性灵。是这些,哲学上乃统称之曰“精神”。但这还是就人生而说,它虽觉似是抽象,然是一真实体,在形而上学中,应当说精神是超乎宇宙为至上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研究这主题之学,方称精神哲学。这一核心,是万善万德具备的,譬如千丈大树,其发端初生,只是一极微细的种子,核心中之一基因(gene),果壳中之仁。孔子千言万语说人道中之“仁”,原亦取义于此。[9]
何以现代可将此宋明儒学列入精神哲学一类呢?——因为二者内容大致相类,而宗旨颇同。在精神哲学中,普通总是以身与心对,中间还有一情命体。心则言情感心(heart)和思维心(mind)。在稍精深的瑜伽学中,还涉及其间之微妙生理体。论及人性,则分高等自性和低等自性。宋明儒学说为身、心、性、命之学,也是分别探讨,主旨或最后目的为“变化气质”。而精神哲学也着重“转化”。——两者皆着重身、心之修为……[10]
细绎这两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可见,就人生而言,精神是指人的“心灵”或“性灵”,乃是一抽象的“形上实体”;就形上学而言,精神是“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精神“超越”(超乎宇宙,高出世界)而“内在”(在宇宙内及万事万物之中),“超思维”(不可思议)而“可证会”[11]。精神是真实的呈现,而非理论的假设,精神哲学属于内学,不违理性却大于、超于理性,所以不能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推理的知识论进路企及,而要经由修为获得实证和契悟,以真实见道,内中证会精神真理。就人性而言,精神哲学和宋明儒学皆主张人性有高低之别,强调人内中具有神圣本性/本然善性,作为修为和转化的内在的形上根据;都要求以修为来对治、转化人性中的低级、负面,“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程颢语)、“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张载语),通过身心修炼以“转化”(变易“低等自性”为“高等自性”)和完善自身、“变化气质”以向上提升,“终期转化人生与社会”。精神哲学超乎逻辑,非心思所及,又注重精神修为,以全般转化身心性命进而改善社会为目标,这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而与中国哲学相契。
又:
通常说精神哲学,总是与物质科学对举;但从纯粹精神哲学立场说,不是精神与物质为二元;而是精神将物质包举,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且超出思智以上。那么,可谓凡哲学皆摄,即一切哲学之哲学,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其盛、衰、起、伏,实与各国家、民族之盛、衰、起、伏息息相关。[12]
这是说,精神哲学是以精神为根本的一元论。以精神哲学契会宇宙真理,该摄一切哲学。“以精神哲学该摄一切哲学”,较马一浮“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的浓厚儒家本位色彩,显然更易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这一提法也反映出徐梵澄世界主义的文化观,所谓:“我一贯反对将文化分成东方、西方,都是世界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13]。四海之内,心同理同,精神真理万古常新,无分于中西古今。
其次,精神哲学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正如牟宗三所谓:“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魔难之化解”(《五十自述•序》)。更进一步,必由学术会通,才能求世界大同,开辟永久和平的美好愿景。所以徐梵澄说:“然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既得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不妨其为异,不碍其为同,万类攸归。‘多’通于‘一’。然后此等现实界的理想,如种种国际性的联合组织或统一组织,方可冀其渐次实现”[14]。
2.精神哲学与宗教
从积极的方面看,精神真理历来多蕴含于宗教之内,徐梵澄指出:
无疑,至今精神真理多涵藏于宗教中,但宗教已是将层层外附如仪法﹑迷信等封裹了它,使它的光明透不出来。偶尔透露出来的,的确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达道,即陆氏所说之心同理同。
宗教多蕴含精神真理,可用以指导转化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宗教的益处所在。而宗教与精神真理的关系,恰如朱子所喻之“厚纸糊灯笼”。宗教仪法﹑迷信等层层外附犹如厚纸,阻碍了精神真理的朗现。精神哲学无宗教之弊,犹如撤去厚纸笼,灯之全体著见,精神真理通体透显。
从消极方面看,宗教的祸患不小。宗教战争以外,徐梵澄主要批评宗教的鄙俚不雅与愚昧迷信。宗教的鄙俚不雅是指其野蛮低下的一面,徐梵澄曾将所译书稿《五十奥义书》中不雅的部分悉数删去,理由就是这些文字太不堪,没有必要译出来。他谈及密宗的不足也说,密宗就是这一点不好,利用最野蛮最原始的东西,去讲出一番道理。[15]更有甚者,宗教往往藏污纳垢,迷信邪魔附于其中。对宗教,特别是流俗宗教如婆罗门道和印度教的流弊,徐梵澄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曾多次提及印度的瑜伽师招摇撞骗,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贻害不浅。古今宗教之偏弊,正赖哲学以救之:“唯独‘哲学’能给‘宗教’以光明,解救其鄙俚、愚昧,与迷信之弊”[16]。究竟言之,精神哲学是“绝对真理”,其地位高于宗教,故当以精神哲学为标准来考察某一宗教理论、宗教仪式的价值。所谓“若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推之,则凡一切宗教之理论及其仪法等,皆只算‘权教’(‘权教’与‘经教’对,‘经’训常,“权’指变),各随其时与地而立,即权宜也。即释氏所谓‘方便法门’”[17]因此,任何宗教皆有偏弊,唯精神哲学纯善无弊,唯陆王之学纯善无弊,其故下文述之。
3.精神哲学与陆王之学
何以提倡陆、王?徐梵澄说:
鄙人之所以提倡陆、王者,以其与阿罗频多之学多有契合之处。有瑜伽之益,无瑜伽之弊。正以印度瑜伽在今日已败坏之极,故阿罗频多思有以新苏之,故创‘大全瑜伽’之说。观其主旨在于觉悟,变化气质,与陆、王不谋而合。[18]
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19]
精神哲学一名,在现代常见,在宗教范围中,然与“神学”大异其趣。只有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的瑜伽学或“大全瑜伽”,多与相合。[20]
徐梵澄重温宋明理学,用现代眼光加以理解和审视,旨在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是准备创造一新的将来,不是召唤已逝去的幽灵而重苏一过去”[21]。“宋明理学,实卓立于世界,从之,我们可以认识自己”[22]。事实上,这也是徐梵澄对希腊、印度古典的态度,“温故”而非“复古”,“返本”是为了“开新”:“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23]。
徐梵澄何以独取陆、王之学?当然是心学与精神哲学的主旨相应。其实,即就“精神”一语而言,北宋五子与朱子多言“神”,宋明理学至象山而喜言“精神”。象山所谓“精神”即“心之精神”,是指本心自作主宰,自能精一自身。象山弟子杨慈湖进一步发挥“心之精神是谓圣”。阳明明谓“心之良知是谓圣”,而良知“凝聚为精,妙用为神”,良知即宇宙造化之心。可见,陆王一系所言“精神”与精神哲学之“精神”义颇相近。总的来说,宋明理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它与精神哲学的内容类似,宗旨一致。宋明理学与韦檀多哲学(古印度精神哲学)的教义中,有许多相同之处。具体而言,如以韦檀多哲学经典《薄伽梵歌》的主旨与宋明理学相较,“主敬存诚之说若合焉;理一分殊之说若合焉;敬义夹持之说若合焉,修为之方,存养之道,往往不谋而同”[24]。二者都注重修为功夫(印度谓之瑜伽学[25]),宗旨都是变化气质,进而转化人生和社会。而且,宋明理学有古印度瑜伽学之益,而不落宗教迷信的虚伪、妄诞甚至邪魔。在徐梵澄看来,“真所谓中国本土的哲学,只有这一套最觉声弘实大。远承孔、孟,是儒宗的精粹思想”[26]。就整个宋明理学看,陆、王最有实践与独创精神,二人皆能真实见道,是代表孔、孟的儒学正宗[27]。
二、心之虚灵明觉与知觉性
象山、阳明多言心而少言性,言心,多指道德本心。徐梵澄从精神哲学的角度对“心学”做出了新的诠解。在徐梵澄看来,不但陆王之学是“心学”,宋明儒学也是“心学”(“宋学之为心学”[28]),整个儒学传统是“心学”(“孔学是心学”[29]),这都是基于他对“心学”的新诠解而言,他使用的一个精神哲学的重要概念是“知觉性”。
何谓“知觉性”?“知觉性”原是韦檀多哲学的基本概念。精神哲学所谓的“知觉性”,并不是通常人在清醒状态下的知觉能力,“却是指存在的一种自我明觉之力,以心思为其中项;在心思以下,它则沉入生命底和物质底运动中,于我们为下心知者;在心思以上,它则升入超心思,对我们为超心知者”[30]。“弥漫宇宙人生是一大知觉性,这知觉性之所表便是生命力。或者,如某些论者说弥漫宇宙人生只是一生命力,而这生命力之所表便是知觉性。两说是同一事,只是后说时时有无生命物一外在事实在相对,较难分说。毋妨假定知觉性是体,生命力的活动便是其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此即宋儒之所谓‘体一’。而各个人皆是此同一知觉性的中心点,各个人彼此不同,此即宋儒之所谓‘分殊’[31]。可见,“知觉性”的概念近似牟宗三所谓“即存有即活动”的形上道体。“知觉性”独一(相当于“太极”)而遍在(相当于“一物各具一太极”),可假定知觉性为体,生命力为用,体用相即而不离。显然,强调“知觉性”自加显示为一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并主张虽无生命的物质中也有其知觉性,带有印度思想的特色。熊十力哲学强调宇宙实体既含物质性,亦含精神性,生命与心灵本来无二,与之颇为接近。
徐梵澄用“知觉性”的概念来讲心性,他说:
但性与心一贯,象山警发学人,以明心为主,乃直接由其所悟而出,直抉心源。但性指知觉性,亦广泛属大宇宙,故曰“在天者为性”。心为知觉性之最灵,属人此小宇宙,故曰“在人者为心”。心而不知觉,何以成其为心?言心则可知舍知觉性外无心,明心亦自然见性。[32]
象山反对解字而更不求血脉,所以反对分别情、性、心、才,但“若必欲说时”,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在徐梵澄看来,“心”“性”都是指知觉性,“性”是弥漫宇宙万事万物的“知觉性”,“心”是宇宙“知觉性”在个人的中心点,是虚说的一个虚明灵觉的位置。“倘不虚不灵,成个什么知觉性?因为虚,所以遍无不在;因为灵,所以妙用无穷”[33]。心、性同属于知觉性,所以“在天者为性”,“心既明则性易成也”。我们知道,朱子言心最重视“虚灵明觉”之义,他反复强调“人心虚灵”、“知觉不昧”,意谓心乃虚灵不昧之明觉,其作用唯是知觉,有虚灵之心,所以有知觉之用。徐梵澄这里以“知觉性”来诠解心,似与朱子言心的义旨相近,而与通常象山、阳明以“本心”言心的理解有所不同。事实上,这里所谓知觉性乃是“神圣知觉性”,朱子重视人的气禀物欲之杂,其所谓心只是道德上中性的虚灵明觉,属形而下者,而陆王所言心为形而上的道德本心,可谓虚灵明觉与天理合一。象山虽不言知觉,但“此心之灵”、“人心至灵”的表述所在多有,阳明也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而早在庄子、荀子,中国哲学已有心为虚灵知觉的思想端绪。究竟而言,道德形上的心和认识的心乃一心之二形,儒家心学传统强调道德心,印度精神哲学讲心则偏重知觉性。
象山明确反对程朱人心道心的区分,如他说:“谓‘人心,人伪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说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才粗便不精微,谓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恶,天亦有善有恶,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皆归之人。此说出自《乐记》,此说不是圣人之言。”[34]徐梵澄则使用“人心”“道心”来分别指称知觉性中的上下层级。他说:
但寻常知觉性中是上、下双涵;此知觉性通常有说为意识,即上意识和下意识,或潜意识。旧说“心”是颇笼统的,这中间包括人的全部知觉性。高、上者称之为“道心”中、下者称为“人心”,统是一心,只是一知觉性。[35]
当然,这只是方便的区分,事实上,上者亦潜藏在下者当中,并不是一条直线的上下层级。
徐梵澄对象山功夫论的理解也有特别之处。为学功夫上,象山教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36],“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37],“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是以强力来突破私欲、意见、习气等种种负面的障蔽,直下超拔,是“刀锯鼎镬的学问”[38]。如果说这是象山之学“激厉奋迅”的一面,徐梵澄更注重提揭其“宽裕温柔”的另一面。徐梵澄论象山教人宗旨时,使用了两则较少被关注的材料:
学者不可用心太紧。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39]
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彻骨彻髓,见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轻清,自然灵大。[40]
徐梵澄解释说:“今且以现代精神哲学绳之……皆是言治学之方,亦即精神修为之道。正如学打拳,初学不宜用力,不可勉强,要优游涵泳,从容不迫,只若持之以恒,久之自然中规中矩。思虑很难泯除,要在反观其起处,即一念之动,已能辨其正与不正,不正则改,亦自心知之。正如上文所言,‘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轻清,自然灵大’。这正如静坐时,似乎视听皆寂,然昭昭内觉,不是半昏迷半妄想之状态。心正则气正,气正则身体器官功能皆随之而正”[41]。
三、前知与彻悟
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对“前知”与“彻悟”的“原理”多有忽视,亦乏善解,或存而不论,或以“神秘主义”一言以蔽。《陆王学述》专辟一节“先知与彻悟”,特为详表,值得注意。与从神秘主义角度所作的诠解不同,徐梵澄视此为“精神知识”、“玄秘科学”的领域,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和方式来研究[42]。他认为“这两事是精神哲学中不一其说的,一般属‘别相’,因人而异;而非属‘通相’,在人人必然同一。但两事皆属真实”[43]。
《中庸》言“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前知”通常被看作一种神秘的预测能力。在徐梵澄看来,“前知”可以说是某种感应的结果,如同声波的共振。信息的传递,必有发出者、接收者以及传递的媒介。这一媒介即前文所言的“知觉性”,知觉性充周遍漫宇宙,类似物理学中的“场”,虽“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却能在空间的各处建立起媒介。“在人人皆有此共通之知觉性,共通的生命力,此之谓‘气’。气有同(其震动度如声音震动之频率相同),则共鸣,乃相感”[44]。
不过,仅有“知觉性”作为媒介还不能像现代用电话一样传递信息。做到“前知”,对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也有精神修为方面的要求,即“静则生明”,这关乎双方“知觉性”的层级高下。理学传统中的“前知”多由习静而致,习静之法不一,静坐通常是重要方式。象山、阳明教人静坐,也因此受杂禅之讥。倘若“知觉性”的境界较高,发出的信息易于传至接受者的“知觉性”中,接受者心境清明,犹如明镜照物,易于感知信息,那么就可以实现“前知”。可见“前知”即精神的契会,心灵与心灵之间通过“知觉性”相连接,这是一种真实的精神经验,并不神秘。
徐梵澄认为,宋明理学中真正的困难,在于着实见道[45]。陆象山上希思、孟,卓立大本,身体力行,可谓超然见道。象山教人开悟以见道,罗整庵因此批评象山杂禅。整庵说:“盖二子者之所见(杨简扇讼之悟、詹阜民忽觉此心已复澄莹),即愚往年所见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误而究言之,不敢为含糊两可之词也。嗟夫!象山以英迈绝人之资,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虚心易气,舍短取长,以求归于至当,即其所至,何可当也?顾乃眩于光景之奇特,而忽于义理之精微,向道虽勤而朔南莫辨,至于没齿,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明儒学案》卷四十七)。在罗整庵看来,象山教人开悟,不过是禅学的“光影”,与自己的禅悟的体验一般无二。“盖惟禅家有此机轴,试观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整庵认为原始儒家无此教法,所以此“悟”是“禅悟”。徐梵澄不以为然,他指出:“一有彻悟便称之为释家,这是流俗之错误见解。不单是由儒而悟道,由他道或其他宗教皆有证悟之事。笼统皆指为禅悟,是谬见,误解”[46];“凡开悟证悟彻悟皆属之禅,非徒所见狭隘,亦复忽略了开明进步之事实,终于未脱门户之见”[47]。其实,这属于修为的基层原理,是儒释道和其他宗教的“共法”。“大致悟入的程序是一,而修为的基层原理也同,在释氏则谓之“渐修”和“顿悟”,认为有这么最后一关得打通。修为的基层原理相同,所以陆、王之学常被人误解为‘禅’”[48]。
那么,如何才是“悟道”、“见道”呢?徐梵澄认为很难简要地说清楚。一是因为非常复杂,二是其中一些前提仍属假定,所以言之愈详,使人愈感茫昧。姑且大略言之。“盈天地间皆一知觉性”,如果方便说法,可谓“知觉性”有许多层级,“最下一层是冥顽不灵,最上一层是至灵至妙。……我们常人生活是在寻常知觉性里”[49]。由此可以进一步来谈“知觉性”之“识田种子说”:
程子曾说有不识字的某人,忽然可诵出一部《杜诗》,此说与近代西方某使女忽然可诵出其主人常读之希伯莱文诗篇,而自己其实不识字,更不必说希伯莱文。这皆是知觉性之作用。即下知觉性或潜意识中时常听到他人诵诗,在中国这例子,必是常听诵杜诗,在西方那例子则是希伯莱文诗,潜入乎下意识,也藏在那里。一遇到某种特殊心理作用的机缘,便发露到表面知觉性中来。这必是心理作用经过了一番紧张,如同一个川堤塌破了,水便从高坪奔腾下注。常时种种识感印象,皆可视为“种子”,采纳入此高层的识田,或自觉或不自觉,自觉地是纳入寻常或中层知觉性中,这便成为记忆而可呼出。未自觉而被吸收的,便如同种子储藏在知觉性里,或变形或不变形,偶尔倾出于梦中。这在通常被误称为所谓“灵感”,进一步方是“彻悟”。[50]
可见“识田种子说”近于唯识学阿赖耶识“现行熏种子”。“种子”不断纳入知觉性,精神修为至“人欲净尽”,可达“彻悟”:
可以假定——这里只是假定,——是有人修为得法,不急不缓,在潜意识中清除了一切茛莠,即识田中只有高等知觉性充满弥漫,归于纯净了,即儒家所谓“人欲净尽”。这是极困难的事,所以往往要修习多少年。久久之后,整个内中知觉性受警策到了最高限度,紧张已极,这时只要外物轻轻一触,不论是见到什么事物或听到什么声音,便如一气球爆破了。似乎一跃到了另一世界,撞开了一大建筑之暗门,见到另外一些琼楼玉宇。一切皆似与寻常所见的不同,改变了,或更美丽了。知觉性似乎已经翻转过。这如同在一圆球上直线似地前进,一到极顶再进,便到彼面了。从此上、下正相对而相反。左右易位,南北转易。这时客观环境未变,只是主观心境已变,多人感到是这方是真实,是宇宙万物之真面目,只是光明的倾注,即儒家所谓“天理流行”,而紧张既除,只有大的喜乐,是说不出的美妙,……是彻悟了。[51]
“私我”是知觉性的自体范限,随着精神修为的深入,个人的“知觉性”不断提升,彻底打破私我知觉性的墙壁,与神圣知觉性合一。又可把知觉性譬喻为一个容器,倾空其中的浊物,至“人欲净尽”,“只是光明的倾注”,知觉性中充满纯洁的事物——精神光明,即是彻悟。“知觉性的翻转”、“进至极顶再进”,是指从“心思”到“超心思”。“时常是最高理性堵塞了彻悟之路”[52],这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突破理性的阻碍。“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者,是思智已达极诣,无可再进,然后径路虽绝而风云大通。寻常谈玄学者,是思智尚未达极诣,犹未到百尺竿头。”[53]。思智进至极顶,再进就要跳出思智,向上一跃至“超心思”,至此则主客双泯,能所合一,实现彻悟,终于证会宇宙真理,获得静定和悦乐。
徐梵澄一生基本“译而不作”,《陆王学述》是他少有的专门著述。他用精神哲学诠释宋明儒学,盛赞象山、阳明一派,某些观点或许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例如他虽然强调朱陆并尊,但认为朱子“不见道”,又说阳明格竹失败,标示朱子格物“此路不通”,诏示来者免枉费心力于此。其次,书中对陆王之学没有较为全面地展开讨论,如只讲陆王之所同,于陆王之所异[54]未暇辨析。平实而论,这些都无关《陆王学述》宏旨,徐梵澄本来就反对在文字上深求,他在是书《后序》说:“这一小册子,……意在以最简单的文字表达这一派学术,不讲多话。读者若依此自寻材料,详细发挥,竟可欣赏其弘庞博大,亦又深奥精微。但主要纲领皆在这里了。”今观《陆王学术》,亦当如象山指示:“须看意旨所在”[55]。
[1]徐梵澄所译的印度韦檀多学经典,依古今划分,古典有:《薄伽梵歌》、《迦里大萨》、《五十奥义书》等;今典有:《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社会进化论》、《瑜伽论》、《母亲的话》等。此外,佛学翻译有:《安慧<三十唯识>疏释》(1947年)、《因明蠡勺论》(1952年)、《摄真言义释文》(晚年)等。
[2]刘小枫:《圣人的虚静》,载《读书》2002年第3期,北京:三联书店。
[3]唐君毅读《薄伽梵歌》译序后,写信给徐梵澄,谓:“先生平章华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执,感佩何似!弟在昔年亦尝有志于道,唯皆在世间知解范围中逞臆揣测,旧习殊难自拔。视先生之栖神玄远,又不禁为之愧悚”。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31卷〈致徐梵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第244页。有关唐君毅对印度哲学的探讨,参见彭国翔:《唐君毅与印度哲学》,载《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4]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31卷〈致糜文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第250页。
[5]1992年,徐梵澄所填“中国社科院研究成果表”业务专长(主要研究领域)一栏,内容就是“中国及印度古代精神哲学”。孙波:《徐梵澄传》,武汉:崇文书局,2019,插图。他又曾自述:“最不成功的最是我所锲而不舍的,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徐梵澄:《徐梵澄随笔 古典重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55页。
[6]除了翻译印度韦檀多哲学经典,徐梵澄的译事还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受鲁迅嘱托翻译尼采著作:《朝霞》、《快乐的知识》、《苏鲁支语录》、《尼采自传》、《人间、太人间的》(节译);二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英译中国传统菁华:《小学菁华》(1990)、《孔学古微》(1963)、《周子通书》(1978)、《肇论》(1987)、《唯识菁华》(1990)、《易大传——新儒家入门》(1995)。
[7]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51、71页。
:《徐梵澄传》,武汉:崇文书局,2019,插图。
[9]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5页。
[10]徐梵澄:〈《薄伽梵歌》注释〉,《薄伽梵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78页。
[11]“证会”即证验和体会。因其所“知”超越思辨,所以不能通过一般知识论的进路来把握,而只能内求,必须身体力行,亲自体验、体悟、体证以知。所谓“原出乎思想以外,非心思所可及,在学者犹当恢弘其心知以证会之,然后明其真,此则不得谓之哲学”(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译者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6页。)“精神哲学属于内学,内学首重证悟。悟入精神真理的某一方面,往往为思智、与文之所不及”。(徐梵澄:〈《玄理参同》序〉,《玄理参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4页。)
[12]徐梵澄:〈《玄理参同》序〉,《玄理参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2页。
[13]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842页。
[14]徐梵澄:〈《玄理参同》序〉,《玄理参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8—9页。
[15]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83页。
[16]阿罗频多语,也是徐梵澄所许之义。徐梵澄:《玄理参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34页。
[17]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58页。
[18]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31页。
[19]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24页。
[20]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3页。
[21]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21页。
[22]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4页。
[23]徐梵澄:《玄理参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205页。
[24]徐梵澄:〈《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薄伽梵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9页。
[25]“盖指陈为道之方,修持之术,是之谓瑜伽学”。徐梵澄:〈《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薄伽梵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4页。
[26]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3页。
[27]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65页。
[28]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235页。
[29]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5页。
[30]阿罗频多著,徐梵澄译:《神圣人生论》(《徐梵澄文集》第13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92—93页。
[31]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96页。
[32]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77页。
[33]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202页。
[34]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62—463页。
[35]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01页。
[36]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2页。
[37]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2页。
[38]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2页。
[39]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09页。
[40]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68页。
[41]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53页。
[42]这是徐梵澄一贯的态度。他晚年翻译《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梵译汉,未完成),也是想告诉大家这并不神秘。这里所谓科学,可参看密娜氏的解释:“在现代世界里,这种知识几乎未尝被认为合乎科学,然而它正是科学底,因为它具足一种科学寻常所必备的一切条件。这是一学术体系,环于一些原则而组成的;它循着精密底程序,而且,若严格地重复实现所规定的情形,便得到同样底结果。这亦复是一进步的学术,可加以专精研究的,且能以一种有规则合逻辑的态度去发展它,正如当今所公认的所有的科学一样”。密那著,徐梵澄译:《母亲的话》第一辑,《徐梵澄文集》第九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第62—63页。
[43]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89页。
[44]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96页。
[45]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3页。
[46]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67—68页。
[47]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77页。
[48]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04页。
[49]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00页。
[50]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01—102页。
[51]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03—104页。
[52]徐梵澄:《陆王学述》,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03页。
[53]徐梵澄:《玄理参同》,武汉:崇文书局,2017,第165页。
[54]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十二章第一节〈总述阳明与朱陆之异,与其同于朱而异于陆,及兼尊朱陆之诸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55]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32页。
《陆王学述》读后感(四):陈来:精神哲学与知觉性理论——徐梵澄心学思想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