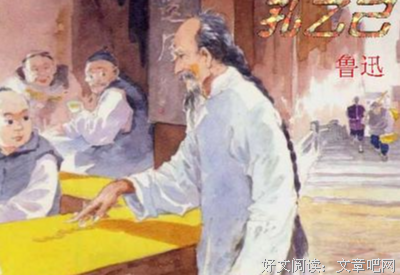
《历史性的体制》是一本由[法]弗朗索瓦·阿尔托格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2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性的体制》读后感(一):谈阿赫托戈的几处问题
典型的蜻蜓点水专栏写作,介绍萨林思和诺拉很不错,但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写作上简单枚举了几个例子,然后术语上也不值得推敲。首先是作者定性的几个概念,当下主义,英雄体制,未来主义。英雄体制也就是萨林思的所说的循环的,结构化的历史,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而当下主义和未来主义就很有问题了,虽然阿赫托戈在处理当下主义和未来主义中强调这两种时间体制是互相渗透的,交融的,并且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当下主义与未来主义的混合体,在列举的时候更侧重未来主义。(诡异的是阿赫托戈本人回避了历史主义,全篇几乎没有谈这个问题)
这个定性就很有问题,首先传统来说,无论是利科还是杜赞奇,霍米巴巴谈及民族主义与历史都强调的民族主义的当下性,比如杜赞奇评论民族主义史学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上黑格尔主义,它专注此刻,是一种圆圈式的时间观,民族主义史学表面上的变易的,穿梭于过去,未来,但是这种变易的表面背后却是被概念所操纵的,而作为变易本身的时间也只不过是本身不变的静止之物。这个圆圈以它的开端为前提,并且只有在终点才可以到达开端。民族主义史学家把本身断裂的时间合理化,将复线的历史化为单一的话语主宰的单一叙事,从而弥合了过去,此刻,未来的断裂,建立了一种在连续性的时间观。
而阿赫托戈在这里片面强调民族主义的未来主义性,也只能说它被民族主义所臆造的未来所蒙蔽了,民族主义运动中对于乌托邦愿景的强调,指向未来的复兴,比如意大利,到中国的公羊三世的复兴的包装,实际上指向的都是此刻,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求,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当下主义。
当然,当下主义的本身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文中提到的诺拉谈两种记忆,今天的记忆已不再是昨天的记忆,后者曾规范着社会—记忆。虽然是同一个词,但形式和实践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旧式的记忆,可以说是“没有过去”的记忆,它“永恒地”更新着“遗产”;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记忆”,它已被历史掌握并受到历史的改造。这种已然消失的社会—记忆很可能有点简单化和神话色彩,但它对今天对照分析记忆的价值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今天,已经完全心理化了,它成了私人的事情,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自我认同”的格局。这种记忆虽然还是以过去的关系为基础的运作,在这种关系中非连续性占据了上风。过去不再是直接的(de plain-pied)。因此,我们从“一种在记忆的连续性中认识自己的历史”,走向了“一种将自己投射在历史的断裂中的记忆”。这就是今天记忆的本质,它“不再是应该从过去汲取的、为人们期望中的未来做准备的东西;而是让当下呈现给自己的东西”。
这种当下主义,可以用第二当下主义(类似贝克所谓的第二现代性)来看待,这是一种更私人化,与黑格尔时间相抵牾的当下主义,由个人在碎片化的遗迹和场所之中选取记忆。一种流动的,液化的当下主义取代了原本固体的,单一的当下主义。
《历史性的体制》读后感(二):历史性的体制:人类学的回响
近几十年来,做“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家在和历史学家互动的过程中,围绕“历史性”这一概念展开对话,但人类学对“历史”、“事件”、“时间性”、“历史性”的看法却与历史学有很大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学科之间没有共享某些资源,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学家的这些灵感来自阿赫托戈。“历史性”最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与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等人有密切的关系。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中回顾了哲学视野中“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的概念, 他提出一种“历史认识的存在论”(existentiale au regard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可能性,它以历史本体论的方式迫近历史实在。Geschichtlichkeit作为“历史存在的条件”(la condition d'être historique)(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最先涉及到的就是“Geschichte”(historie)这个词本身。“Geschichte”派生为形容词“geschichtlich”,最后通过将形容词名词化的方式派生为“geschichtlichkeit”[1]。“Geschichte”在德语中既指过去发生的事件进程,也指了解这些事件的学科(Drummond,et al,1997:312)。(利科尤为推崇雷特-芬克(L.Renthe-Fink)和格哈德·鲍尔(Gerhard Bauer)对“Geschichtlichkeit”一词在用法变化上所做的工作 [2] .)而在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历史性”关涉的是历史的真实性,事件的事实性,或者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阿赫托戈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他 指出“历史性”的重点可以放在“人面对作为历史性的自身”或者“人的有限性”再或者“人对于未来的开放性”上。历史性表示的是“个人或集体置身时间中,或在时间中展开的历史条件和方式。”指的是“初步的疏离经验、自我和自我间隔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又恰恰是借助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范畴才使得经验本身可以理解和言说。正是这三个范畴的不同组合整顿了经验并赋予后者以意义。这里所说的组合意味着,历史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是过去范畴,也可能是现在或未来范畴。在这个意义上,阿赫托戈使用了复数的体制。这同时也表露出他的历史比较的野心,即历史性不是一个局限于欧洲或西方社会的工具,而是一个使各种时间经验得以理解的比较工具。
作为一名人类学学生,我尤为推崇后一点,这让我想起了早于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2003)出版的一部人类学作品:人类学家 M.Lambek 的《The Weight of the Past:Living with History in Mahajanga,Madagascar》(2002)。这本书主要处理的是马达加斯加马哈赞加地区人们的灵魂附体实践,这是一种与历史主义很不相同的历史性的经验。Lambek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Poiesis of History”,用来指涉马哈赞加的历史实践,人们在此一仪式中,过去、未来、现在相互交织,彼此共融。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当日本学者Minoru Hokari基于在澳洲Gurindji社群的田野(他自认为是历史学家)掀起新的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真实是什么”的讨论热潮时,当时欧洲的一些关注此一问题的人类学者则围绕“历史性”这一问题召开了多次工作坊(最突出的是2005的维也纳)。今天,在人类学的语境中,用历史性这一概念主要指涉当下的人们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过去,关涉未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阿赫托戈提出的 “历史性的体制只是扭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方式,或将三个范畴组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就像人们谈论希腊政治理论时提到的混合整体一样(融合了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而三个构成要素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阿赫托戈,2020:iii)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 词缀“-lich”在德语中表示形容词(-ell、-reich、-arm、-wert、-frei、-bar、-los等后缀都表示形容词。);词缀“-heit”、“-keit”在德语中都表示抽象名词。
[2] 这两部著作是L.Renthe-Fink.Geschichtlichkeit:Ihr Terminologie und begrifficher Ursprung bei Hegel,Haym,Dilthey und Yorck[M].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64.以及Gerhard Bauer.Geschichtlichkeit:Wege und Irrwege eines Begriffs[M].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63.
《历史性的体制》读后感(三):张旭鹏:历史时间与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
一、何谓历史时间?
历史时间是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不能按字面理解为是对时间的历史研究,即将时间这一概念置于历时性的脉络中,考察其形成、发展与演变;也不是对时间进行共时性研究,即探究不同地区或文化传统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同样不是对时间进行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史的研究,如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时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等。所谓的历史时间,主要是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的变化。一般认为,“历史时间”这一问题主要由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提出。虽然科塞勒克并没有为历史时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其多篇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历史时间就是指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变动关系。科塞勒克在其文集《过去之未来:历史时间的语义学》中指出,文集中的文章“都与一个既定的过去和一个既定的未来的关系有关。……这些论文不断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当下,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维度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它涉及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区分过去与未来,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和期待时,有可能把握像历史时间这样的东西”。
莱因哈特·科塞勒克为此,科塞勒克提出了“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这两个概念,用于分析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塞勒克认为,经验空间代表了过去,期待视域则指向未来。在现代社会之前,人类的经验空间处于连续性的状态中,过去不仅是现在的参照物,更为应对未来提供了方法和范例。未来因而是既定的、可知的,人们对之不会再有过多的期待。但是自18世纪以降,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持续冲击着这种以过去为中心的时间体制,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和未来不再有指导意义,人们将希望和期待都投射到一个新的未来之上。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视域由此发生了断裂,而历史时间即诞生于这种断裂之中,它指向了未来,代表了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
受科塞勒克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了“历史性的体制”这一概念,试图厘清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阿赫托戈看来,历史性的体制指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且服从于它的强大的时间秩序,分为古代的、现代的和当下的三种类型。其中,古代的历史性体制以过去为导向,对应的是科塞勒克所说的“经验空间”;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以未来为导向,从中产生出了“期待视域”。阿赫托戈对科塞勒克历史时间理论的推进之处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当下的历史性体制”这一概念,并用“当下主义”加以概括,即当下取代了过去和未来,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的参照系,也构成了人们今天的时间经验。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二、历史时间与历史意识
科塞勒克“历史时间”概念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历史意识的变化。正如科塞勒克指出的,期待视域的出现,意味着对经验空间亦即对过去的抛弃,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历史意识,它以进步主义和未来主义为特征。进步主义表达了今胜于昔的强烈信念,而未来主义则是进步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它强调对一切价值的判断和重估都要以未来为导向。也就是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如何,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对现代历史意识来说,过去与现在的分离是其产生的前提,也是人们得以摆脱历史的重负,面对未来的先决条件。科塞勒克以经验空间的失效,说明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但更多地侧重于个体或集体的日常经验。阿赫托戈则不同,他从政治事件入手,强调了社会秩序的变动给人们的时间体验带来的巨大冲击。阿赫托戈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开端,原因就在于法国大革命在革故鼎新方面史无前例的特征。他特别以夏多布里昂这样的保皇派为例,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时代断裂感。
《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1793年,流亡伦敦的夏多布里昂开始创作其处女作《试论古今革命》,试图将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历史上的诸多革命进行平行对比,进而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一古训的正确性,即法国大革命并非“史无前例”,它的人物和特点都是古今革命的再现。然而,夏多布里昂在写作过程中却深刻体会到,革命事态发展之迅猛、变动之剧烈,是以往任何经验都无法认知和把握的:“常常,晚上就要把白天的草稿涂掉:事件跑得比我的笔迅速;突然一个革命让我所有的对照都变成谬误。”夏多布里昂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已经催生出一个与旧有的时间关系冲突不断的时代,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现代时间秩序。
夏多布里昂如果说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现代历史意识,那么当下的历史性体制——阿赫托戈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其开端——则可以接续二战以来在欧洲逐渐兴起的后现代历史意识。1989年之后,冷战所铸造的世界格局消失,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支独大似乎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然而,单极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却是一种更加强烈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文明内部的冲突——族裔之间、文化之间——也在加剧。以往那种将人归属于某种群体的情感和认同消失了,代之以个体性的张扬,而这种个体性在以满足自我为目的的消费主义中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加速发展,它创造出一个急速膨胀的当下,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全部。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关于时间的体验是即时性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转瞬即逝的状态中,再无永恒的价值。甚至人们的历史意识,也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特征。对此,阿赫托戈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当下主义的自我封闭和短视关闭了未来。
三、超越当下主义与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
关于当下主义,阿赫托戈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由于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一分半钟的话题可以涵盖三十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在当下主义的时间经验中,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只专注于当下。其结果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与行为都以当下的价值来衡量,而与未来无关。当下主义的这一弊端,在近年来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等对全人类造成威胁的问题前,显得尤为严重。因为对环境和生态的消耗,完全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透支人类未来的表现。
而与当下主义相伴随的,是一种力图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悄然复兴,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回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粹主义排斥全球化,强调民族利益优先,它期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我们从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所用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以及英国脱欧、法国极右势力抬头等政治事件中可以一窥其端倪。这种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意识的再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主义的不满和挑战,但却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其结果有可能是,贸易和思想的壁垒被重新树立起来,有形和无形的边界再次成为人们交往的障碍。平坦的世界将变得沟壑丛生。
今天,在当下主义和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双重夹击下,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既不能沉湎于当下,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重塑现代的历史性体制或者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时间意识依然有其价值。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既定的方向感,人们才得以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
当然,对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需要我们同时考量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并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仅仅以某种时间向度为重。唯如此,人们才能兼顾经验(过去)、期待(未来)和利益(当下)的合理性,从而使人类通向未来之路,也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历史时间之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的最大价值。
《历史性的体制》读后感(四):历史意识和时间秩序:兼评阿赫多戈《历史性的体制》
如果要举出新世纪法国史学界的几部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弗朗索瓦·阿赫多戈的《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毫无疑问可以位列其中。今天,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 d’historicité)这个概念不仅出现在法语的维基词条中,出现在《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①]等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中,它还被史家们作为解释工具,运用于各个领域的实际研究中,如2014年出版的英语论文集《东南欧和西北欧的历史性的体制:身份话语与时间性》,[②]甚至近年来在法国颇受追捧的全球史力作《角色均等的历史》也不忘提一下阿赫多戈和他历史性的体制概念。[③]现在面世的中译本,特别是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中文表述,恐多有待改善之处。这里拟从自己粗浅的理解出发谈几点认识,以期进一步的讨论批判。
该著的核心概念是历史性的体制,简单地说,就是特定社会和文化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结合方式。但阿赫多戈只是挑选了几个历史片段、几个文本和近期的若干现象,利用这个概念去分析其中的“时间性”(temporalité)或“时间秩序”(ordre du temps),因而该著呈现较大的跳跃性,加之作者行文洒脱,尽管援引了很多著名学者的理论,但往往并不专注于条分缕析的说理剖析,情景化的描述远多于说理分析,这就给阅读该著造成较大的挑战。阿赫多戈的本行是古希腊史,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和列维-斯特劳斯是他重要的理论来源,尤其是在关于历史性的“英雄体制”的描述中。但本人对相关领域知之甚少,未敢置喙。对于阿赫多戈参考的另外两位重要学者,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和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本人稍有接触,这里拟结合他们的研究谈几点看法,对阿赫多戈的论述或有所补充和延伸,相关内容主要涉及历史和社会意识中的过去、未来和当下,以及历史叙事中的时间性等问题。
一.未来主义:历史性的现代体制
在历史性的英雄体制之后,阿赫多戈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历史性的“旧制度”和及“现代体制”。概而言之,历史性的旧制度反映在西塞罗的那句名言“历史乃人生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中,而现代体制则放弃了这个信条,认为未来必将展现出过去未曾经历的新景象。这与科泽勒克的见解存在高度的关联性。科泽勒克的文集《过去的未来》(Vergangene Zukunft,1979)的头两篇,分析了近代早期(约1500-1800)欧洲人的未来意象的转变,以及“历史乃人生之师”这一格言在1800年前后的退场。[④]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讨论未来对它有什么意义呢?科泽勒克和阿赫多戈都强调,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史学思考,都存在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举一个例子大概就能说明,历史,尤其是“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中的历史,与对未来的展望密不可分。1953年10月,年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革命壮举辩护时,追忆了祖国的历史,以及为自由和正义而牺牲的伟大先烈们,他辩词的最后一句话至今为人铭记:历史将宣布我无罪(La historia me absolverá)。[⑤]这句话的动词用的是将来时。
卡斯特罗的“历史”是贯穿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如果参照科泽勒克和阿赫多戈的理论,对于卡斯特罗这样的现代革命家,历史是目标明确的进程,他们就像荷马时代的诗人一样,具有“通观视野”(vue synoptique)[⑥],从过去通往未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一览无余,惟其如此,当他们介入历史时,才会深信自己是在推动这一进程,未来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行动的依据在于未来——必将到来的、比过去和当下更为美好的未来。现代革命者特有的意志主义(voluntarism)和自信大概与这种历史信念是分不开的。当他们以“历史”的名义言说时,这个概念并不是张三李四的某个具体的历史,而是科泽勒克所称的“总而言之的历史”(Geschichte überhaupt),也就是由某种强大的内在逻辑将各种片段性的历史贯穿起来的总体历史进程。
革命家的“未来主义”可能显得很激进。但在卡斯特罗的时代,可能还有一种更为温和也更为普遍的未来主义:这就是寓于自由主义之中的进步信念,即深信理性和科技必将带来更大的个人自由和人类的解放。但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人们都已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对于未来的乐观信仰的脆弱乃至虚妄。阿赫多戈思考的一个重大意义正在于,当这种乐观主义消失之后,当未来的前景变得混沌模糊时,史学和当代社会中的时间性究竟呈现何种样态?我以为这是“当下主义”之所以会引起关注的一个现实原因。但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回顾未来主义的现代性体制的诞生也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科泽勒克对鞍型期(约1750-1850年)新的未来视野的开启和确立有过经典阐述,相形之下,阿赫多戈在选材上别具一格,他对夏多布里昂这一独特人物的“时间经验”作了长篇铺陈。夏多布里昂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经历了某种“时间危机”、时间秩序的激变,或曰新旧两种历史性体制的转换。在18世纪陈腐的古典人文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夏多布里昂,认为古典历史文化具有解释当下之功效,人们可以“手执往日的火炬,照亮当下和未来的暗夜”。法国大革命刚爆发时,他觉得这场革命中一切都已在历史中上演过,只要回顾过去就能理解当下。这是“历史性的旧制度”,或曰“历史乃人生之师”这一传统信念的典型表达。但三十年之后,当夏多布里昂重新审视最近的经验之时,他觉察到自己当初的认知完全是错误的。阿赫多戈转述了夏的很多形象化的说法,以揭示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时间危机:在一条疾驰的航船上,河岸边的风景不断变换,船上的乘客却自以为一切如旧。夏多布里昂又说,每发生一次革命,他此前的古今类比都成了难题,过去的经验根本不能解释当下的变革。于是他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感:“我遭逢两个世代之间,仿佛处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我投身浑浊的水流中,满怀伤感地远离曾养育我的古旧河岸,带着希望游向一个未知的岸边。”这是一种新的时间经验。过去那种安稳的、连续的古旧时间,让位于不断变换的时间和未知的未来。用科泽勒克的概念来说,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愿景,或曰期待的视阈(Erwartungshorizont),已经超出了夏多布里昂在古旧河岸边的全部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但阿赫多戈还强调,夏多布里昂在美洲的观感同样蕴含着类似的危机。他曾像很多卢梭的信徒一样,认为美洲生活着高贵自由的野蛮人,但当他对美利坚共和国有所了解,并见识了印第安人的真实生活之后,高贵自由的野蛮人的神话破灭了,在这个新生的现代国家面前,有关人类遥远过去的黄金传说全都黯然失色。
要理解夏多布里昂的时间危机,应该注意两个关键要素,一是法国大革命对于“历史性体制”变革的关键意义,另一个是对于美国和美洲的实地了解后产生的冲击。阿赫多戈对这两方面都有重要提示,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作集中且充分的展开,他更专注于对夏的心路历程的勾勒。从理论论证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稍加补充。阿赫多戈把1789年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日期,认为它标志着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诞生。但法国大革命也像夏多布里昂一样,陷于某种新旧历史性体制的纠葛之中,这里他引述了诗人保罗·瓦雷里的一句充满悖论意味的话:“倒退着走向未来”,或者说,面朝过去走向未来。说它走向未来,既是因为革命者(如孔多塞)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宣告,法国大革命将启动走向无限美好的未来的伟大进程,也是因为他们(如艾蒂安-拉博牧师)从革命一开始就对“历史导师”提出了质疑:“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⑧]说它是面朝过去,既因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深受古代希腊-罗马典范的鼓舞,也因为革命期间的确有过效仿古代典范的狂热实践。
但在这里,或许阿赫多戈应该对革命者所谴责的过去和他们崇拜的过去做某种区分,我自己以前对此也没有充分的意识。这一区分得益于法国中世纪史专家贝尔纳·葛内(Bernard Guenée)的启迪。他认为,在中世纪这样一个并不赞赏创新的世界中,人们总喜欢援引过去论证当下,即相信“历史导师”的权威。但人们利用过去的方式不尽相同。中世纪首次大范围的历史论战出现在11世纪后半期和12世纪初,格里高利改革和授职权之争是其直接的诱因。当时教宗和皇帝的支持者都在寻找历史论据。但教宗派的论据源自更为遥远的、与当下没有直接联系的时代,皇帝派则援引延续到当下、较为切近的历史传统,葛内分别称之为“典范(exemples)论据”和“续前(précédents)论据”,后者可以论证当下的合理性,但典范则以复活更为古老和美好的过去为名,掩盖实质上的断裂和变革。[⑨]这是个很重要的见解。宗教改革时期很可能也出现过上述两种对过去的利用方式。[⑩]阿赫多戈也多次提及典范(exemplum)。就法国大革命而言,这种典范无疑主要来自希腊罗马,但我想强调的是,革命者拒斥的过去,则是一直延续到1789年的“哥特式”的旧制度、封建制等较近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对待过去的方式,其实是西方历史上历次重大变革中反复实践过的。
即便如此,阿赫多戈对于1789年的定位仍然是有充分依据的。由于大革命期间复古尝试的失败,尤其是经过后革命时代的反思(夏多布里昂就是反思者之一),直到18世纪仍被人推崇的古代典范,最终被认定对现代社会是无效的,用科泽勒克的话来说,历史导师退场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评判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晰有力。《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一开始就说,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是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然而,新的社会一旦形成,布鲁图斯、格拉古这些远古的巨人,还有随他们一起复活的罗马古董,全都消失不见了。新社会需要的是萨伊、贡斯当和基佐这样的解释者和代言人。[11]阿赫多戈没有引述马克思的话,但他提到了贡斯当和他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1819),认为这与夏多布里昂从美洲的观感中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他们两人都对自由概念作了“时间化”的理解。原始人和古代人的自由,毕竟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当这种环境消失之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此对当下和未来而言,它们并不是效仿的典范。
阿赫多戈还对夏多布里昂的美洲之行,与三十多年后托克维尔的那场美洲之行作了平行论述。在他的笔下,托克维尔已经完全走出了青年夏多布里昂信奉的“旧体制”,《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寻找的是一种“新政治科学”。这种平行阅读可以让某些文字产生新的意境。比如,夏早年相信,手执往日的火炬就可以走进未来革命的暗夜。《论美国的民主》结论中则说,“过去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12]历史导师已经被托克维尔当作破旧的古董扔在一边了。18世纪的作者还言必称希腊罗马,《论美国的民主》中却没有这些伟大典范的影子,如果说托克维尔确实提到过雅典的民主,那也只是为了否认这个典范城邦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13]托克维尔的手稿研究专家方素华·梅洛尼奥注意到,在《论美国的民主》出版时,托克维尔删除了一条颇有挑衅意味的注释:“总把我们时代的民主与古代以民主名之的事物相比,真不知厌烦……二者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根本不必拿亚里士多德来说服我。对我来说,看看古代人留下的雕塑就足够了。”这是民主概念的时间化。当然,托克维尔并不是认为古代文明完全没有意义,但他把这种意义限定在十分狭隘的范围中,如文学和审美方面。[14]如果把早年的夏多布里昂和美国之行后的托克维尔做一点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古典这个形象渐渐被疏远了,从典范(exemplum)变成了异乡(terra aliena),从当下应该努力追赶的伟大榜样,变成了无可挽回地逝去了的过去(pastness of the past)。托克维尔对古典的态度,有点类似现代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社会:那里虽然可以映照出现代人的缺憾,但并不意味着那里的制度和风俗可以移植到现代社会。
阿赫多戈关于自由概念时间化的阐述,关于夏多布里昂和托克维尔的古今之辩的提示,都可直接与科泽勒克对鞍型期概念变迁的经典论述对接和相互应证。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上引三部论著发表的时间,也可加深对科泽勒克研究的认知,尽管他考察的主要是德语地区:鞍型期的下限并不是1789或1815这样更具标志意义的日期,而是1850年左右。大概只有在大革命的风暴和效仿古典的尝试过去之后,经过一代人的观察和反思,历史导师的无效、这场革命的未来主义特征才逐渐清晰起来,而自由和民主等重要概念的时间化,也在这个反思的时代有了更为理论化的表述。
夏多布里昂和托克维尔都注意到美国对于未来的意义。夏最初到美国时,那里的仿古地名似乎证实了欧洲人对于这个异域罗马的想象,但后来他逐渐发现美国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不同,前者是风俗的女儿,而风俗会随时间而败坏;但后者是知识的女儿,未来知识的更新将有助于自由的维持。在夏的眼里,美国展现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新自由。对于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也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他甚至意识到,美国的当下就是欧洲的未来。因此阿赫多戈认为,对于托克维尔,横渡大西洋缩短了“经验和期待之间的鸿沟”,他在美国发现的是未来的启示,从而在时间秩序上颠倒“历史导师”的认知模式:新政治科学的启示来自作为未来的美国。但这种启示不是某种确定的、已完成的、有着充分经验的事物,而是一场正在发生、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运动,而且肯定有些托克维尔本人很不喜欢的苗头。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这种理解,很好地诠释了科泽勒克所谓“概念的时间化”的内涵:如果说18世纪的思想家仍然认为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是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无数次被演绎过的,那么到托克维尔的时代,它们都包含着明显的未来主义指向:民主、自由的进程有很多过去未曾有过的东西尚待经验——用阿赫多戈的话来说,这些概念中“尚未”的领域是开放的。
二、“当下主义”
以上我们主要把《历史性的体制》与科泽勒克的相关研究作了一个平行解读。不过,科泽勒克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欧洲的启蒙和革命时代,但阿赫多戈则把眼光向前和向后延伸了很多。他在该著最后一章中对“遗产”概念的阐述,不仅指出了这一概念在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中的表象,而且把时间轴向前和向后推移,分析了它在“历史性的旧制度”和“当下主义”中的形态。所以有理由把这部著作看作科泽勒克的续篇。
从一个更长时段的角度看,上文提及的概念的时间化、对古代典范的疏远,也只是某个时代的思想特征。托克维尔对于古典的看法,今天恐怕是很多人都不会完全赞同的。阿赫多戈著作的一个价值,就在于指出了鞍型期之后西方世界时间秩序的波动,如将时间的加速感发挥到极致的“未来主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缺口”或断裂(brèche)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时间危机;他讲述了本雅明等人对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困惑,他们都对时间中的断裂感有更深刻的感知。不过,对于一位法国史学思想的继承者,阿赫多戈或许可以给予马克·布洛赫更多的篇幅,这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杰出史家同样对令人困惑的时间问题发表过卓越的见解,而且中世纪史家让-克劳德·施密特已经在他那里发现了“当下主义”的早期表述。[15]
当下主义是阿赫多戈著作的核心概念之一。简单地说,如果在历史性的旧制度中是过去支配人们的时间体验和历史观、现代体制是未来占支配地位,那么当下主义就是当下、即刻的时间压制了对过去与未来的关注的历史性体制。这是个相当令人费解的说法,需要大量的示例性分析来使其具象化。阿赫多戈确实给出了很多的例子,不过,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层次或领域,他在论述时又没有在文字上做明确的提示和理论勾连,所以显得较为分散,似乎有进行更好的理论整合的空间。可以从世界史和国际层面、民族和日常生活这几个层次去观察当下主义的呈现。
阿赫多戈把1789年和1989年分别作为现代历史体制诞生和终结的标志性日期,后者又可视为向当下主义过渡的标志。法国大革命是现代革命的开端,因为它启动了追求理想社会的未来主义日程,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都可视为对1789年革命理想的升华(surenchère),或者“共和二年”的全面展开。但是,200年之后,这种革命理想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褪去了光辉,不仅因为苏东剧变、柏林墙的倒塌,也因为弗朗索瓦·孚雷“大革命结束了”的论点反映出,在大革命的母国,乌托邦革命的意识形态已经急剧衰退。破除宏大叙事的幻觉之后,未来不再一片光明。阿赫多戈说这是“晦暗且咄咄逼人”的未来,谨慎和责任取代了创造未来的进取精神。他认为遗产保护、环保运动与未来图景的转变不无关系,它们是当下主义历史性体制的征兆:当下所要挽留的,不仅有可能消失的过去,还有未来可能会消失的事物。如果阿赫多戈的著作再次进行修订,未来的图景也许应该抹上一层新的焦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技术敌托邦正越来越清晰的显现在“等待的地平线”(Erwartungshorizont)上。对思想界而言,告别乌托邦迎接敌托邦(dystopia),也许是半个世纪来最富戏剧性的“时间经验”了。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预示着冷战走向终结。对于这一事件和这个日期,阿赫多戈赋予各种时间意义。从世界历史意义而言,它意味着最激进的现代意识形态与时间秩序的终结。如果联系科泽勒克早年关于冷战的见解,也许这个事件对于理解当下世界政治不无助益。科泽勒克在《危机与批判》中认为,美苏之间的对抗是一场“世界性内战”(Weltbürgerkrieg),从历史角度看,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性扩张与现代人的历史哲学观念的后果,后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乌托邦信念,其历史根源在18世纪。[16]就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时间性”来说,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竞争,它源自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对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的预设和构想之不同。可以延伸一点,这种未来竞争不仅出现在美苏之间,甚至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同样存在竞争,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迈向共产主义的竞赛。[17]但观察一下今天国际政治中的话语,这种有关未来的宏大叙事看来已经消失殆尽了。在今天的大国关系中,现实的利益话语似乎已经笼罩了一切。按照阿赫多戈的理解,这是一种当下主义,人们的行为和眼界都在当下,世界进入了一个他所谓的“当下视角优先”的历史时期。
在关于当下主义的探讨中,皮埃尔·诺拉堪称阿赫多戈最重要的参照,他的很多论述,是诺拉在不同场合下都表述过的,尤其是与民族、记忆、纪念、遗产等章节中,这些文字可以与诺拉在《记忆之场》中的三篇导论性文章对照阅读:《历史与记忆之间》、《纪念的时代》及《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诺拉主编的这套巨著,其基本的设问是如何是在记忆浪潮开始吞没传统民族史叙事的情境下如何重新表述法国史。他一再表示,过去的法国史是以未来的视角书写的,尽管这种未来可能判然有别:或是革命的乌托邦,或是作为文明领航者的法国,或是恢复昔日“教会的长女”的地位。但是,所有这些未来视角,到20世纪末全都消失在地平线上。此时的未来已经丧失关注的焦点,它变得无限开放,不可预见,但令人窒息,当下则在千变万化中不断膨胀。阿赫多戈则引述弗朗索瓦·孚雷的话进一步强化诺拉的论断。这位大革命史专家在1995年写道:历史的超验神性基础已经动摇,未来已经封闭。
上面引述的这些话,只有放到20世纪末法国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中才能理解。前文已经提到进步主义和革命理想的衰落,历史已经丧失必然性(神性基础已经动摇)。就法国本身的情况来说,它的国际地位的衰落、二战后天主教影响的迅速衰退,以及欧洲建设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认知。20世纪末的法国人已经接受这个事实:法国只是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它是西方民主世界的普通一员,它的历史文化并没有突出的独特性,也不再能背负19世纪那种文明开化的历史使命;就国内政治而言,共和民主制度已经牢固确立,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未来已经封闭);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集体意识中的位置相对下降了。这不仅因为欧盟一体化的深入,也因为地方主义、族群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诺拉说的,民族国家认同在高处和低处都有所弱化。例如,一百年前,德法两国在边境是紧张的敌对关系,但一百年后的今天,边界已经畅通无阻了。与此相应的是,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空间,其地位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如果说19世纪的民族主义曾刺激着两国民众对边境问题的关注,在20世纪末,与边境相关的国民记忆已经从热记忆变成“冷记忆”,并有淡出公众意识的危险。
正是因为上述问题背景,《记忆之场》在中国可能不那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与法国不同,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民族复兴”已然清晰地展现在等待的地平线上:未来可期。中国的体量也难以使它被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实体吸收。因此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没有陷入当下法国那样的困境。这些大概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学界热议“何为中国”之类的问题的现实原因。但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法国人几乎连民族(nation)的口号都不愿意提了,民族和革命的宏大叙事已让位给了社区和家族的小叙事。[19]
这就过渡到阿赫多戈和诺拉强调的一个概念:民族已经成为遗产。这个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法国人已经失去历史纵深意识和时间上的延续感。在这个问题上,1989年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为迎接这个特殊的日子,法国学界出版了一部《大革命批判词典》,它的主编者孚雷和莫娜·奥祖芙在前言中说,今天的法国与他们儿时的法国鲜有相似之处,那是19世纪的法国,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传统的农民和工人已经难觅踪迹。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法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更为明显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太需要统一性了,而过去通过教育来维系的革命记忆就是在努力为他们塑造这种统一。共和记忆已经不再依赖炫耀性、战斗式的忠诚,而是已经融入一种共同的文化,它的褪色甚至就是因为自己的成功。对抗性的民族主义式微了,拿破仑战争,甚至1914年的战争对今天的法国年轻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20]他们甚至也不认为当下的享受的成果源自祖先的努力,没有dette——债的意识。当人们不再认为当下视为一个具有时间纵深的特定阶段时,过去和当下便不再构成连续的统一体,而与此同时未来也不再带有光辉和确定性:这就是国民意识中的当下主义。
《记忆之场》中有不少条目提到,过去那种极具民族性和政治化色彩的节日和纪念活动,如今都被已淹没在消费主义之中。在阿赫多戈的理论中,消费社会盛行的是当下主义的时间经验,人们注重的是瞬时性的享乐,为遥远的未来而省吃俭用已经不合潮流了。现代媒体和技术手段则让当下的消费变得“更加膨胀和肥大”,上下几千年的历程可以浓缩在几分钟的视频中,一组照片就能尽览几千公里外的风光。人们当下的视界极大地扩展了,但对时间纵深的感知则逐渐淡薄。阿赫多戈在这个领域的分析,或许可以“日常生活中的当下主义”名之。而且,这种当下主义应该比法国民族意识中的当下主义更具普遍性。阿赫多戈指出,全球经济生活中“短期主义”——如金融投机——的泛滥,也应该放在当下主义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因为人们不愿意像从前的企业家那样,对未来做长线的预期和投入,人人都希望赚快钱。我们甚至可以在人文研究这样的领域有同样的时间体验。在今天的学术考评体制之下,“板凳须坐十年冷”的训导正在悄然退场了,对学术成就预期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到极限。这种变化也许只是最近二十来年的事。在新的时间秩序中,阿赫多戈书中“给时间一点时间”的呼喊似乎有了非常实际的意涵。
就法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当下主义而言,1968年五月风暴应该是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日期,阿赫多戈也有所强调:当时巴黎墙壁上的涂鸦就已宣告当下主义的来临:“一切,一切都要即刻实现!”“不要谈未来!”这场风暴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其参与者都没有彻底的政治革命的意愿,而是各自发泄日常生活中的不满。换言之,当下的不满没有生发出乌托邦式的集体革命行动。[22]可否认为,孚雷所谓“未来已经封闭”其实在1968年就开始成型呢?如果当下主义的历史性体制与“后现代”的社会和思想现实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则可以在当下主义与“第二次法国大革命”[23]这一重要命题之间建立起关联。这也是皮埃尔·诺拉多次指出的关联。
在阐述从历史性的旧制度向现代体制过渡的危机时,夏多布里昂的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但在未来主义向当下主义的过渡中,阿赫多戈似乎没有这样强有力的案例。但是他提到的弗朗索瓦·孚雷是个可供选择的个案。他也是45年communism的一代知识人,但此后一系列的政治和思想事件促使他“幡然悔悟”,并在学术上拆解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实践的内在关联,以致最后写了一部反思20世纪communism的大书。似乎可以做一点猜想:孚雷的历史视角因为对未来的认知而做了重大调整,他也是在“时间缺口”上写作,“在当下的废墟上重审昨日的档案”。
但可能还有更大的不足之处。在讨论最近的这场时间危机时,阿赫多戈太过集中于法国和西方世界,尤其是当他以1989年这个日期作为当下主义诞生的标志时——这就更突显了其论述的片面。这个日期的确可以视为激进未来主义时间秩序(尚待实现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就是它的具体化身)的终结,但它最引人注目的实践发生在苏联和东欧,那里同样经历了一场未来主义幻灭之后的时间危机。我认为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可以作为《历史性体制》一书的平行读物。[24]在苏联解体前后,这个不安的社会的确可以看到未来主义和当下主义的冲突,以及未来主义的无奈退场。老一辈的苏联人以建设新社会为荣,心目中的英雄是飞上太空的加加林;但他们的下一代只关心如何一夜暴富,投机倒把的暴发户是他们羡慕的偶像;于是,凝结着过去的理想、过去的牺牲的勋章被仍在地摊上换几包万宝路香烟。对于曾沐浴过乌托邦理想光辉的那一代苏联人,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精神世界坍塌的声音。
从苏联剧变前后的“时间经验”看,它的确与20世纪末的法国有可比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别。首先,对大多数人而言,苏联解体后自由化的经历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往往导致他们怀念过去的旧时光。其次,与法国不同,民族—国家意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后苏联实体而言,根本没有走向弱化。在失去了乌托邦的未来后,民族的历史和光辉似乎能给当下充满挫折感的集体生活带来某种崇高感。我想Putin应该很好地操纵了这种社会情绪。民族的光辉和历史使命似乎能重建时间秩序中的连续性。更为广泛地说,冷战后的法国的当下主义,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民族—国家历史意识的相对衰落,因为很多后革命时代的地区(包括中国),并没有这种衰落,毋宁说它们像俄罗斯一样,都很自然地把民族主义,至少是关于民族历史的光辉叙事和“伟大前程”,视为重建时间秩序的替代品。诺拉可以尝试写一部“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史”,以切合民族“当下”的状态;但在其他地方,拉维斯式的roman national依然在发挥它的教化和规训功能。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它的形态在不同的地区应该是有某种时间性的差异:这也是科泽勒克的“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Gleichzeit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的一个表现吧。
当然,阿赫多戈对自己的当下主义概念的普适性和完整性是存疑的,他没有穷尽各种历史性体制研究的抱负,毋宁说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进路。他曾谈到,最近二三三十年出生的人,他们只经历过当下主义,它主要来自日常的生活体验。但可以告诉他们还有其他的时间体验。[25]这个想法与前文诺拉的看法是类似的:新一代的法国人如果不同意、至少也应设法去理解祖辈的价值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解体后的苏联世界,或许还有当下的中国——这种现象更常见的叫法是“代沟”。阿赫多戈和诺拉毕竟是老一代人(40后和30后),他们可能给历史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有着不同时间经验、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性体制下的个人之间,如何能达成某种对话和理解。但这样的工作似乎很棘手。如果当下主义理解了过去的价值观,它真的就不是“完整的当下主义”了。
三、历史叙事与时间秩序
时间秩序是阿赫多戈运用得最多的术语之一,但他没有对该术语与历史性的体制做仔细的辨析,有时二者是并列使用的。时间秩序是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波米扬一部著作的标题,他与保罗·利科也是阿赫多戈的理论武器库中的成员,在有关历史文本的时间性的探讨中,利科的“时间与叙事”理论应该是个很重要的资源。在学界对这两位学者的时间研究做深入讨论之前,这里想从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经验出发,就阿赫多戈论述中的某些话题做一点联想和展开。
对于文本叙事中的时间经验或“历史性”分析,阿赫多戈的尝试集中于《荷马史诗》有关尤利西斯返乡的叙事上。他还提到了奥尔巴赫《模仿论》第一章中的著名分析:《圣经·旧约》具有《荷马史诗》所没有的历史性。[26]这就转向了一个重大话题:西方历史时间观的演进。阿赫多戈强调,《出埃及记》已经具有强有力的线性特征,鲜明的未来指向,叙事也随时间的流逝而展开,这堪称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基督教对犹太时间秩序的改造,主要在于基督降生和受难这个决定性的事件,而当第二个决定性事件,即基督再临、末日审判到来时,时间也就结束了。这两个事件之间是一个过渡期,一种期待的时间。这种有关救赎的时间观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的世俗化版本可以说就是有关人类进步和解放的现代历史哲学:当历史最终抵达这个终极目标时,时间也就终结了。比如,我们很难设想 Communism实现后的历史和时间。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对此已有阐述。[27]但阿赫多戈强调,尽管现代历史哲学与基督教时间秩序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它对于未来的展望、过去所占的分量都很不一样。
让-克劳德·施密特说,对当代历史学而言,时间不仅是个研究的对象,它本身也是史家解释和叙事的基本范畴。[28]而且,正如阿赫多戈和奥尔巴赫在分析中指出的,文本叙事本身便有其各自的时间性,不管作者主观上有没有意识。当我们的史学叙事中使用“建元”、“鼎革”之类的术语时,大概也是有其特有的时间性的。历史叙事中的时间性有没有比较的可能呢?这里想提出一些问题,供讨论批判。
贝尔纳·葛内曾论及时间的单复数问题。在异教史家那里,历史叙事是在不断重启的时间中展开的,它讲述着不同文明和王朝的兴衰。我们常见的“建元”之类的表述,大概也属于这种不断重启的时间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时间仿佛是复数的。但在基督教的时间秩序中,整个尘世的历史,从创世到世界之终结,都是在一次性的时间(un seul temps)中展开的。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基督教史家,应该将整个世界历史作为一场有始有终的运动来处理。[29]但应该强调的是,一次性的线性时间观绝不是中世纪欧洲唯一的时间秩序。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耶稣降临纪年法,即“公元”纪年,直到很晚才确立其自己的统治地位,直到11-12世纪,它才在西方的正式文件中被普遍采纳,[30]史书中纪年法的也长期是多样和不统一的。[31]各种年代标注法长期并存。1232年,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份敕令上,日期标注为:主道成肉身1232年,罗马人的皇帝、耶路撒冷和西西里的国王在位诏令期(indiction)[32]第5年,罗马皇帝在位第12年,统治耶路撒冷第7年,统治西西里第34年。[33]这些情况可以表明,在相当长的中古时代,无论是在史学叙事还是在官方文件中,东西方的时间性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但基督教的确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时间秩序。当这种时间秩序世俗化为现代历史哲学、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确立为一种社会和思想事实之时,阿赫多戈讨论的“时间危机”、夏多布里昂式的困惑,是否也见于中国历史呢?就我有限的了解,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变”大概算是时间危机的一种表达:当下的危机超出了过去的经验空间,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也不足以应对这种危机。同样地,这种危机发展到五四时期对传统的全面质疑,与法国大革命之后托克维尔等人对古典传统价值的否弃,是否有可以比较的空间呢?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史学革命,在东方世界是否有对应现象呢?中国革命中旧社会与新中国这对对立概念的发明,是否像1789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可以视为某种现代历史性体制创生的标志呢?
当然,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独特性。很多对中国历史怀有温情的史家,很多以自己的历史和史学传统自傲的国人,恐怕难以产生类似于托克维尔的那种视古代历史为“异乡”的意识,他们或许以为过去作为一种活的传统存在于当下(presence of the past),或者对当下不乏积极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科泽勒克和阿赫多戈关于历史性的现代性体制的论述,可能还提示我们重新思考所谓“历史智慧”的前提。但这种智慧所赖以存在的前提,究竟是基于“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的前提为多,还是“世事如棋局局皆新”为多?或者更为调和地说,究竟如何平衡这两种前提呢?如果真的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呈现强烈的同质性和重复性,那么经世史学“汲取历史教训”的期望是否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觉呢?因为这种同质性、历史的所谓重演恰恰表明“历史导师”并没有对历史进程产生多大影响。这里我们期待科泽勒克《过去的未来》中译本的问世能引发相关的思考。但中国的近代先哲无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吕思勉就“前车之鉴”发表过很有意思的看法:
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34]
吕先生对近代欧人东来的认知,显然上接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变”。当他意识到“历史导师”(前车之鉴)不足以应对当下之经验时,他的史著当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时间秩序。时间危机中的夏多布里昂曾说,为了与思想发展协调一致,法国应该重写它的历史。1820年代法国的“史学革命”就是对法国历史的重写,它把中世纪以来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表述为一个连续性的进程。[35]清末民初的新史学运动,如梁启超对历史的进化式理解,大概可以视为晚晴的时间危机和历史性体制之转变的一个征兆。他批评旧史学“无一纲领一贯之”,认为在他所处的萌芽时代,“内外之动变,实皆二千年未有……近世史学,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又言,“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所以史学应该“求公理”。“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36]看到这些文字,我觉得他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民主时代的史学与贵族史学,是非常接近的。任公要以某种历史哲学、一种逻辑线索将中国历史贯穿起来,并指明民族的未来。这是他的“总而言之的历史”。
梁启超之后出现的进化式、进步主义的历史性体制很长时间内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思维和史学叙事。但在今天,正如在西方世界一样,这种进步主义色彩的线性历史叙事在中国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这里面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就历史叙事中的时间性而言,它当然也可以视为某种时间秩序的转型。例如,在很长的时间里,五种生产方式的更替是我们所熟知的普遍史和民族史叙事模式。今天看来,这种叙事本身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时间秩序:每种生产方式,或每个对应的概念,在时序上不能变动,而且都只能出现一次,因而是一组有严格时间位置的历史概念。这就是科泽勒克在讨论“历史”概念时提到的“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现象。[37]它是一种现代历史哲学在概念史上的表现。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萌芽等概念,并非完全不能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它们今天遭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单数”这种时间秩序造成的。如果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可以重复出现的类型概念,而非有固定的先后关系的、一次性的时间性概念,或许它们还能焕发出新的解释效力。宋代可以有资本主义的特征,明末也可以有。如果拿西欧的封建社会进行比照,封建主义的因素,或许西周、魏晋乃至唐末五代都出现过。当然,这种复数化、非线性的历史概念组合会产生另一种时间秩序,叙事中的必然性可能会有所削弱,但对历史必然性的怀疑和动摇,不就是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学界的一种潮流吗?这种潮流是否也是当下主义的某种面相呢?
补记
这篇稿子大约写于半年前。半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被隔离了好几次。而且,隔离似乎成了当下世界的一个政治隐喻。时间的缺口大概会使本文的看法逐渐失效。
最近几年我们都有感觉,冷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Pax America 一度给世界带来的玫瑰色正在逐渐褪去,各种 glory restaurations,great again似乎正在提醒人们,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酝酿出一个共享的未来。但大概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时代会以当下的方式走向终结。
最近半个月经常去院子里看看盛开的紫藤。我想起,年迈的列奥波德·冯·兰克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像他这样的老人,每年春天的碧草鲜花,像如约而至的老朋友那样来看望他,他感到十分欣慰。
是的,大自然的时间节奏能切实慰藉人的期待。感谢造物主的恩典,在历史时间的caprice和contigency之外给我们安稳的希望。
[①] 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等:《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②] Diana Mishkova etc. eds., ‘Regimes of Historicity’ in Southea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1890-1945: Discourses of Identity and Temporality,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③] Romain Bertrand, L’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 Récits d’une rencontre Orient-Occident (XVI-XVIIe siècle), Paris: Seuil, 2011, p. 358.
[④]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 pp. 1-66.
[⑤] http://www.emersonkent.com/speeches/la_historia_me_absolvera_page_2.htm
[⑥] François Hartog,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2, pp. 86-87.
[⑧] Rabaut-Saint-Etienne,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intérèts du tiers-état, 1788, p. 13.
[⑨] Bernard Guenée, Histoire et culture historiqu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aris: Aubier, 1980, pp. 347-348.
[⑩] 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9-22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670页。
[1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82页。
[1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83页。
[14] Françoise Mélonio, “L’Antiquité au temps de Daumier et de Tocqueville: qui nous délivrera des Grecs et des Romains?”,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no. 1, 2008, pp. 64-85.
[15] Jean-Claude Schmitt, “Le Temps. ‘Impensé’ de l’histoire ou double objet de l’historien?”,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48 année (n.189), Janvier-mars 2005, pp. 31-52.
[16] 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8, pp. 5-6.
[17]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九章第二节:“毛泽东追求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19]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commémoration, Paris : CNRS Edition, 2000, pp. 299-308.
[20]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s.,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88, pp. 21-22.
[22]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章:“日常生活革命”。另可参阅吕一民、朱晓罕:《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六章第六节:“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风暴”。
[23] Henri Mendras, La secon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5-1984, Paris: Gallimard, 1988.
[24] 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25] 弗朗索瓦·阿赫多戈:《灯塔工的值班室》,赵飒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58页。
[26] 参阅埃里希·奥尔巴赫:《模仿论》,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9页。
[27]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28] Jean-Claude Schmitt, “Le Temps. ‘Impensé’ de l’histoire ou double objet de l’historien?”, pp. 39-43.
[29] Bernard Guenée, “Temps de l’histoire et temps de la mémoire au Moyen Àge”, 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976-1977, pp. 25-26.
[30] Jean-Claude Schmitt, “Le Temps. ‘Impensé’ de l’histoire ou double objet de l’historien?”, pp. 46-47.
[31] Bernard Guenée, Histoire et culture historiqu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p. 155-160.
[32] 这是中世纪文书的一种日期标注法。Indiction起源于罗马帝国晚期重新核定地产税的间隔周期,一般为期15年。如果说Indiction中的某一年,即指这15年中的第几年。Cf. Olivier Guyotjeannin etc., Diplomatique médiévale, Turnhout: Brepols, 2006, pp. 50-62.
[33] Pascale Bourgain etc., Latin médiéval, Turnhout, Brepols, 2005, pp. 448-450.
[3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5] Cf. Marcel Gauchet, “Les ‘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d’Augustin Thierry”,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pp. 787-850. 另可参阅乐启良教授最近的论文:《介入史学的意义与局限——奥古斯丁·梯叶里对法兰西民族史的重构》,《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秋季号,第3-24页。
[36]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0-81,96页。
[37] Reinhart Koselleck, etc., “Geschichte/Historie”, in Otto Brunner etc.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and 2,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75, pp. 647-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