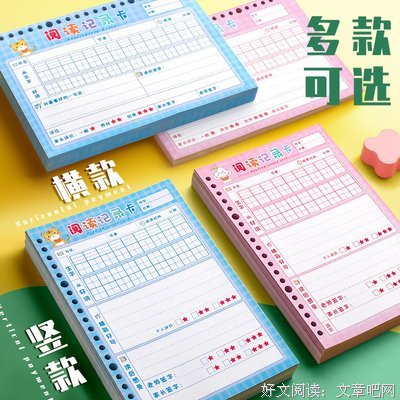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是一本由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页数:201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精选点评:
●选材和论证很巧妙,但并不够透彻。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儿童经济价值向情感价值转化的表征上,引发这种价值转化的结构性变迁则过于简略。泽利泽还是低估了市场的能量,强调标价被非经济的力量所左右,忽略了非经济价值也可以被经济本身塑造,因此猜中了开头但没猜中结局,今天的儿童市场不是情感价值的衰落与工具价值的回归,而是儿童从消费品转变为消费者,育儿各环节的全面市场化
●孩子原来越是个奢侈品,情感上有用的奢侈品。
●物的价值,无用与有用。 价值的社会属性,情感、文化等
●儿童相关法律与保险发展史,经济上可以算账,情感上没法算了。
●大开眼界
●翻译偶有雷人之语。本书把儿童放在百年历史里看待,没孩子没研究过孩子外行不好评价,启发性很大原来以为儿童是祖国希望天经地义呢,就好像过去以为看战争片看av的都是直男其实很多女的也看,眼前的事实如果不经过反思肯定是时间里的片面性加上主观自文化的偏见。
●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100年来,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孩子不再有劳动力价值,情感价值又无限放大了。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中国也一样。作者回顾这个过程是想告诉我们:孩子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变化,改变了关于孩子劳动的社会观念,又进一步改变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但我们并没有真的让孩子摆脱市场,只是转换了定价公式。很多时候,无价的情感依然需要金钱衡量。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两个养育问题:教育过度投资。某种意义上教育过度投资是孩子情感价值放大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社会问题,只是100年来市场和社会观念变化的延续。隔代养育。隔代养育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用作者的理论来思考,我们至少能看到一种良性的趋势,代际差异并不是冲突,观念的靠近会在合作中逐步达成。
●营销儿童,始终是自损八百的,短期寻求增长的触手无门可入时,孩子也不被放过。 关于营销听过比较尬的故事还是近代徐志摩飞机失事案例,当时的国内航空公司服务质量差风险高,在短期无法根治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向社会名人提供免费机票来对冲风险。营销社会名人乘国内航班的模式,意图改变人们对国内航空的印象,不巧结果还是出事了。
●从儿童人寿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和儿童领养三大制度的变迁来讲述在美国儿童社会价值的神圣化,从19世纪的经济上有用变为20世纪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但悖论的是,儿童价值的神圣化却导致了情感的货币化,例如领养制度。因此,市场始终受到非经济因素的约制和调整。这种经济上无用的儿童价值在当代性别平等、家庭民主化背景之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儿童成为成人的负担,我们需要对儿童价值和家庭模式进行新的界定。
●我觉得写得很干巴巴,有材料堆砌之嫌,略感失望。最后只记得两个感兴趣的点:一是美国社会早期普遍对“童工”抱有正面态度(培养儿童自力更生的某种磨砺),二是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化和交通的发展)是如何促使了这种态度转向负面。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一):对儿童的“爱”是怎么增加的
在儿童已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蒙田提及他早逝的孩子时说:“我有两三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就死了,不无遗憾,但没有过分的悲痛。”也不能想象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述:“劳动即玩耍……中世纪没有儿童。”
本书演绎了儿童生命神圣化的过程;解析了衡量儿童生命的经济和情感价值的三大制度: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儿童的领养和买卖;从而使读者“看到”儿童在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意识到,社会经济理性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并不像经典思想家预测的那样,有着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和不可避免的腐蚀性后果,人类意义系统和可变的社会关系也在持续地塑造世界。借助这一洞察,蒙田和阿里耶斯与现代世界的沟壑或许会减小;对于跻身在经济世界的儿童,如童模或童星,我们也会多一些解读角度。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二):。。。
100年来,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孩子不再有劳动力价值,情感价值又无限放大了。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中国也一样。作者回顾这个过程是想告诉我们:孩子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变化,改变了关于孩子劳动的社会观念,又进一步改变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让孩子摆脱市场,只是转换了定价公式。很多时候,无价的情感依然需要金钱衡量。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还好泽利泽给我们展现了丰富变量,让你能够看清变化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她最终的结论:市场会改变社会观念,社会观念也会改变市场。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两个养育问题。首先是教育过度投资。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过度投资是孩子情感价值放大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社会问题,只是100年来市场和社会观念变化的延续。其次是隔代养育。隔代养育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用泽利泽的理论来思考,我们至少能看到一种良性的趋势,代际差异并不是冲突,观念的靠近会在合作中逐步达成。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三):一段历史:曲折变化的儿童价值
某天和卢仨拾同志聊起两性关系,说到社会思想观念改变时,卢同志眼睛一亮,强行把话题拐了个弯:“你知道在19世纪的美国,如果一名儿童因意外丧生,事故过错方需要向其父母赔偿多少钱吗?”不等我回答,答案就率先出来了。“将死者生前可能提供的劳务价值减去其维持生活的所花费的费用,之后剩下的就是赔偿金。”
之前从没想过这方面的事,托无良媒体的福,在看到诸如死者家属向事故过错方索赔此类情况时,我总是无法避免地在心里将双方都画上叉,过错方须承担责任自是不用多说,但当我看到死者家属也将死者标上价格时,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仿佛真挚的感情染上了铜臭味,诚然家属索要赔偿无可厚非。类似的事不只发生在中国,儿童早夭是每个家庭的不幸,但儿童对一个家庭,在他们的父母的心中究竟有多重要呢?相比于我没有任何帮助的肆意吐槽,社会学家选择写了一本书来作答。在此鸣谢优秀的卢仨拾同志,托他的福我才得以借阅这本《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书中从童工市场、儿童保险、儿童市场等大致三个方面随历史进度剖析儿童在社会中的价值变动过程。说起童工,我第一反应是夏衍的《包身工》,之后就是契诃夫的《凡卡》,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作为中国人,对与长工、短工性质相同的童工在非常熟悉的,除了各类文艺作品的渲染,媒体对童工悲惨遭遇的报道也功不可没,文艺作品和媒体报道让童工变成了个别悲惨的例子,似乎所有不公的苦都塞给了这个运气不好的孩子,但在19世纪的每个国家里,童工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相比于今天的家长基于道德训练的目的而给儿童分配工作,19世纪的儿童是真正出于贴补家庭才去工作的,于是当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丧失孩子,确实是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19世纪的丧子父母在情感上的克制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置信的。
出于在那个时代儿童的高夭折率,父母情感上的淡漠也不难理解:“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被直接埋在后院里,正如今天人们埋葬猫和狗一样。”人们对早夭的孩子的悼念是冷静而克制的,即使刚开始是热情的也会因为数次失去而渐渐冷淡。之后随着儿童生命变得神圣化,儿童的价值从经济上的劳务价值转变为情感上的无价,而这一特性也在婴儿贸易中发挥着作用。童工被渐渐禁止,儿童都被送进了学校,入学率上升,妇女们代替儿童加入了职场,面对年幼儿童的经济破产,为了满足失去经济来源的儿童的消费欲望,“零花钱”的概念才渐渐被公众熟知并接受。(多么曲折的发展,青少年的零花钱来之不易啊!)
在今天,孩子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孩子的一点动静都会勾起父辈祖辈的心弦,如果孩子被拐卖,一个家庭就被毁了,而在19世纪的美国,有些婴儿就被当作生意的货物存在着,他们的价格就是他们的价值。儿童福利工作者的措施变成了婴儿贸易,并且这个市场愈演愈烈,从19世纪持续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这是儿童福利机构在社会福利保障不健全时的一条必经之路。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概念也不可能凭空就能在社会上得到拥护者,我们今天的许多概念都是在一条条弯路中碰巧形成的。而如今经济模式变得愈来愈复杂,许多儿童通过互联网挣到了比他们父辈更多的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儿童的价值还会经历一次剧变。
感谢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在司空见惯的事情中抽丝剥茧,还原了社会的观念变迁历程。感谢卢仨拾同志,在暑假前夕将这本书塞给我解闷,还不忘给我一份读后感帮我导读。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四):孩子真的是无价的吗?
这是一本经济社会学读物,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美国1870年代到1930年之间孩子在社会变迁中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变化。
本书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亲密关系的购买》等。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儿童的价值,立意就跟市面上同类型讨论儿童的书籍不一样,尽管这是选取美国1870年到1930年这段历史来作为论证依据,但在当下的社会,也是很受用的。特别是当下我们开放二胎以来,有的人随波逐流,看到别人生自己也生;而有的人却依然选择丁克,或者只生一个,到底是政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还是人们的观念影响着政策的改变?通过本书,我们能切实找到答案。
维维安娜·泽利泽作者首先探讨的是儿童在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改变。在18世纪的英格兰和欧洲,对于孩子突然的死亡,大家都是很冷漠,甚至是孩子的葬礼也是很简单操办,父母很少会去参加孩子的葬礼。但是到了19世纪,孩子的死亡成了很多家庭不能接受的,孩子过早死亡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父母也不再克制自己的悲痛的情感,出现了新的大众文学类型,越来越多的文章安慰失去孩子的家庭。这一场情感革命的变革,才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跟家庭重视孩子的葬礼,也开始重视儿童的生命,儿童心理健康也成了许多科学家研究的兴趣点所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孩子无法给家庭创造经济价值,唯一能回报给父母的是让父母情感上得到满足。有的人生孩子思想养儿防老,而有的生孩子仅仅是想获得情感上的满足,需求的不一样,孩子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需要是有用的。
越来越多的孩子会通过帮父母分担家务,通过自己付出的劳动力获取价值,让孩子成为家庭经济的参与者,越来越重要。可是到后面,童工却从工业中被推出,最大的原因缺少教育的孩子的技术已经满足不了工业化的发展,也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妻子跟孩子都不需要出去外面工作,单靠家里的男人就可以独挡一面了,孩子开始接受教育。对于儿童的保护,也开始立法,合理化起来,虽然过程艰辛缓慢,困难重重,但却能让孩子更加受到重视,将孩子从现金关系中排除出去,让劳工家庭对待孩子有了新的观念,孩子也是家庭一份子,是值得父母做出牺牲的。
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儿童保险的变化情况,这也是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转变的一个重大依据。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保险,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上保险,开始保障孩子以后的人生。在20世纪初,儿童保险成了保险业最具有争议性的产品,很多反对上儿童保险的人觉得把孩子的生命用商业来衡量,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对于孩子的死亡有利可图,是对神圣生命的一种亵渎。对于他们而言,被保的儿童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童工,一种情况是从死亡中赚到钱,另一种则是从劳动中赚到钱。而让儿童保险得到广泛关注,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儿童死亡葬礼的昂贵,只有保险才能让死亡的孩子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当人们对哀悼仪式有了新的需求,才会推动囊中羞涩的父母为孩子投保。在19世纪末期对贫困儿童体面葬礼关注的潮流,成了保险业的卖点,表明了父母接受了关于儿童的哀悼方式。
作者还分析了领养风潮的来临。这是孩子从有用到无价的过程在不断变化,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90年代的中国,领养跟儿童买卖也同样是存在的。愿意花钱去买孩子的,都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有的家庭喜欢男孩,就花更大的价钱买,有的家庭喜欢女儿,女儿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便宜很多。而这些家庭这么做,想要孩子的初衷,刚开始都是希望孩子有所贡献,起到帮助,经济发展决定了父母对孩子不同时期的需求。在19世纪的时候,孩子的劳动力能决定他们的交换价值,而20世纪的时候,只要他们能给家庭带来欢乐,就是有用的。领养的方式也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要符合领养资格,才能领养孩子。
本书的中文翻译出版已经有八年光阴了,翻译者王水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副教授,他跟本书作者研究领域一样,翻译风格通俗易懂,剖析的角度独特到位。本书在1985年还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赖特·米尔斯奖。
好了,让我们以希拉里·克林顿谈论到的儿童问题来小结一下这本书: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实现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读完《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你会明白孩子的存在,无关乎经济,无关乎价值,他们是独立而存在的个体,却因我们创造了他们的存在,变得神圣,我们爱孩子,爱的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五):儿童是无价的情感资产,也是“现金商品”
原载:https://mp.weixin.qq.com/s/atTUZt1SsGIa5BGck7Ooow
最能激起广大中产阶级共鸣的话题是孩子。为什么养娃越来越贵了?选择丁克的人越来越多,在未来孩子会变成一种负资产吗?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名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是理解孩子价值与价格的开创性研究作品。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的,而在情感上是无价的”,这种观念人们早习以为常。然而这种社会共识是如何出现的?泽利泽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她详尽展示了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对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社会如何“大于”市场?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的,而在情感上是无价的”,这种观念人们早习以为常。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会向父母提供钱和劳动力;孩子在情感上是无价的,因为他们给予父母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于是,人们一边抱怨养孩子太贵,一边又心满意足。
然而,这种中国人今天普遍接受的社会共识,是如何出现的?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名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给出了答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这本书,把变动的“儿童”观念处理成“特定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这个研究是具体针对美国语境的。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看待14岁或更小的孩子的态度和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18世纪的美国乡下,孩子一出生就被视作未来的劳动力,也是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传统中国人很能理解这种想法,在乡下,小孩五六岁就帮着家里喂鸡打扫和做饭了。
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以劳动力和工资来衡量儿童价值的功利主义的标准,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1860年之后,整个美国社会的迅速工业化,给贫困儿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城市的劳工阶级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年长孩子的工资,以及年幼孩子在家务劳动中的帮忙。
不过,在19世纪中期,美国绝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眼中的孩子,在经济上已经是“无用”的了。与养儿防老大不相同,中产阶级父亲为自己的生命投保,还用其他金融措施来保护他们还不能赚钱的孩子。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孩子的教育上。为孩子而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甚至为他们而节衣缩食。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逐渐普遍到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头脑中。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儿童劳动法和义务教育法推进,童工的数量逐渐下降。工业资本主义需要的是有技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儿童的生产性价值逐渐消失了。美国家庭对于“有用儿童”的诉求,逐渐被非经济的、教育性的诉求所取代。
一个正常的、可爱的孩子,不论来自什么社会阶级,都属于生活化的、非生产性的世界。他们上学、游戏,并从家里拿钱,甚至学习如何花父母的钱。
儿童工作,不再是“真正的”工作,它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教育形式,或者一种游戏。比如说,父母开工资让孩子干家务,不是因为需要一个童工,而是为了让孩子“锻炼锻炼”,赚赚零花钱,或者培养一种品格。
吊诡的是,20世纪“无用的儿童”,价格上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童工。在1930年代,没孩子的夫妇已经花高价从黑市上购买可爱的婴儿。早先,人们在领养时总爱寻找那些强壮、年长的男孩;如今,人们则更喜欢婴儿,特别是漂亮的小女孩。女孩在情感性导向的领养中,变得如此吸引人。
可以说,儿童的价值,从效用品转向了感情品。
这意味着,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世界,儿童反而变得越发神圣化了。孩子是超越商业主义的,是神圣和无价的情感寄托。
孩子价值的提升,与妇女家庭角色的提升是一致的。世纪之交,全职太太越来越流行,这种观念也扩散到了工人阶级的认知里,尽管他们不一定能有条件实行。总之,孩子与母亲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对于“真母亲文化”和“真童年”的想象,二者把家庭生活的神圣性提升到了新高度。
泽利泽还细腻探讨了世纪之交人们对于儿童死亡的态度转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
比如,为孩子买保险,在19世纪末期是为了买到一份体面的殡葬仪式,是对死去的孩子的一种尊重;而在20世纪,为孩子买保险则成了父母向活着的孩子表达爱与关注的方式。这种爱的象征性表达,也是一种准仪式性的生意。
这中间显然存在一种深刻的对立:人们一方面在文化上宣称儿童是无价的情感资产,另一方面则在社会安排上将孩子视为“现金商品”。
谈到最后,我们不得不说泽利泽真的很有“选题意识”和学科开创性。她的第一本书《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是透过保险来分析金钱与生命的交叉点,将可计算的价格与神圣的、无价的价值放在一起讨论。《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这本书也延续了这种视角,为儿童社会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泽利泽的著作,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们称之为“泽利泽视角”。那些此前被认为是“不严肃的”经济现象的命题,也得到了来自文化角度的分析。
/ / /
本期作家
维维安娜·泽利泽,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 古根汉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得主。她开创的“泽利泽视角”对经济社会学有着重要影响。代表作有《道德与市场》《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的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