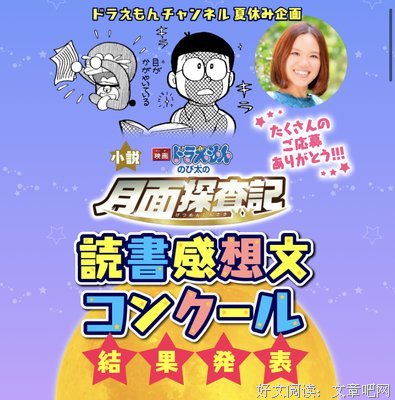
《我的探险生涯》是一本由斯文·赫定著作,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80元,页数:4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探险生涯》精选点评:
●1819世纪之交,世界的魅力
●好书!
●他二十岁时在探险东突厥斯坦,而我二十岁生日在沙发上看着讲述喀什噶尔的纪录片,理想的远方与现实之间格格不入。
●外面是加州的阳光,我看的真不太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尤其是google maps也查不到他又去了哪儿的时候。。
●读的不是这个版本,可能翻译不好吧,不好看。
●热血沸腾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书真难找,翻遍了喀什的新华书店都没找着...
●我反省我悔过,坚持了一半真的跪了,佩服能把这本流水线全部啃下来的人。
●看了半本,挺有意思。接着看下半本
●恨不得自己翻译
《我的探险生涯》读后感(一):印象较深的几个点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8278.html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次所到之处都是帝王级待遇,
4)他从别处带进Tibet高原的牲口显然都很难适应高原气候,每次都在两三个月内几乎死光,简直就像易耗品,所以一有机会就尽快替换成牦牛,
5)瑞典人身份或许是个有利条件,因为当时瑞典在英俄之间中保持中立,且与两者都颇为友善,而他穿越的地区正好是英俄Great Game的赛场,
6)他前几次旅行还没提到相机,第三次带了相机,不过视觉记录主要还是靠画画,可能当时的相机用起来还太麻烦,他画速写的水平很高,我在他另一部游记The Wandering Lake里看了很多,感觉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记录手段,这是我没料到的,
7)铁路和电报真不愧是杀手级应用,他每次旅行,俄国的铁路/电报线都比上一次又延长了一大截,有一次他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穿越广袤大草原的旅行,是一路数着电线杆走的,也让我吃了一惊,
8)Tibet 当局对其疆域内事务的控制能力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其阻止欧洲人进入的政策得到了相当有效而严格的执行,赫定的行踪每次都被牧民迅速上报,地方官履行职责也非常认真,
9)赫定用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装扮成Tibetan或Mongolian(而且他还有个有利条件:身材不高),可是每次都很快就被识破了,而同时,他的队伍中那些来自中亚和克什米尔的各种民族的人,却没有引起怀疑,可见种族纯属文化建构,毫无生物学基础,
哦还有件事也蛮有意思,他第二次去罗布泊是沿叶尔羌-塔里木河走的水路,半途在岸上设立了大本营,结果很快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做买卖,于是很快发展成一个繁荣小镇,甚至有人闹了纠纷跑到那里去找他仲裁。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8278.html
《我的探险生涯》读后感(二):他在路上
早就知道他有很多粉丝,却从没想过去读,直到这次新疆归来,又见有人把这书推荐为了解100年前新疆风物的最佳文本之一。遂买。不单有新疆,还有西藏旅行记,倍觉美好。
1、好旅行者的素质:由本书可见,意志坚定,身体好,有钱(赞助),好奇,宽容,坦诚而有沟通技巧,会绘画、摄影,有文字功底。基本就这些了,所以我是不够格的,虽说放弃相机了,但我却认为素描是最好的技能(本书附有赫定的素描,很是动人,胜出照片不只一筹)。在1900年代,赫定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中亚与一群回教徒、佛教徒为伴,毫无微辞腹诽。
2、那些风景啊。
A太阳下去了,紫色的光线从慕士塔格山的西面山坡渐渐地隐没。当那一轮圆月升起在冰川南面的石壁顶上时,我走出去领略我在亚洲所见最壮丽的风景之一。……我觉得仿佛站在极大的宇宙的边上,那些神秘的行星在其中永远运行不息。
那湖(纳克产湖,我对照地图没有查到今天的名字,该书的遗憾是没有配地图)呈圆形,水面上露着峻峭的山壁如同仙境一般美丽。我们摇着船到狭窄的美丽的湖湾,那里有金黄色的鹰类在峭壁上飞翔。湖岸上看守牲口的游民看见我们在水上幽静地前来,觉得颇为奇怪。他们从未见过一只船,赶快将牲口驱离湖边。
C湖水(大来登湖,在阿克赛钦湖以东,同样没有查到)的颜色和天空一样。红黄色的山脊的倒影映在水中。我们四周的画景美丽得难以形容。……太阳落下去了,形状如同一个火球似的,发出奇异的光辉照在湖岸与水面上,所有的山岭都照得如红宝石一般。波浪和水沫都是红的,我们仿佛是在一个血湖中疾驶。
D以下是圣湖的景色:东方有点发白,山顶上透出晨光来了,带玫瑰彩色羽状的浮云倒映在湖中仿佛是溜过玫瑰花园。日光射在廓拉·门达塔山峰上发出金紫色的闪光,反射光线笼罩在东山坡上好似一件光亮的外衣。廓拉半山中一朵云的影子印在山坡上。……我可以在那里住几年,看那湖面冻冰,冬日的风雪刮过水上和陆地,春季的来临要分裂整个湖水。后来又有暖和的夏风和成群的野鹅。我极愿坐在那里看见每日早晨湖上千变万化的景致。(啊,是的。。。。)
许多地方,不去到,并不知文字在说什么。读着赫定的简笔勾勒,知其只有未尽之意而无一字虚夸,神已不在此身,万里湖山飞渡,我飘远我悬浮。
他的笔也记着那些动物,野生的和他的旅行队驯养的。忽然疯掉的骆驼;没有见过雪的狗,对雪而吠,想要咬住雪花;沙丘上三十头昂首而立成一幅动人图画的野牦牛;混进队伍忽然发觉不对劲之后跑开的野驴;失偶徘徊不去直至被猎人杀死的天鹅;为了果腹忙着挖龈鼠洞而没有发现人走近的熊……
一个略带困惑之处是,那些随着探险家的足迹死在路上的中亚仆从们,甚至那些牲畜们。我无法想象,我终于成功达到一地旅行,付出的代价是死亡2名向导和10匹马、1只狗。这是我一直没能解决的心理问题,呵呵,所以一些地方我没能去,因为我不愿意雇挑夫,我总想伪装成非旅行者的样子,当地人是人,我也是人,他们可以的,我也可以,他们不可以的,我也不可以。这种心情从没说过,不知如何处理,看到这书忍不住晒一下,留作自我温存吧。
路遇几个藏人兄弟共妻时,赫定也忍不住幽默了一把,说这些男人,每个拥有2/3个妻子也就足够了,因为这些女人实在是又老又丑。哈哈。其笔下,从未过于强调沙漠居民和藏人如何淳朴,有时反倒见出狡猾。鄙意以为,此正乃赫定旅行深入之佐证。所谓淳朴云云,是今日旅行者最自以为然、自我投射的表现。那另一种文化,其实更多只是规矩不同、标准有别。
仅有一处对照地图有所发现:P384的塔古藏布,似应为今日的达果藏布。
《我的探险生涯》读后感(三):《我的探险生涯》的译本问题及其他
一、译本问题
My Life As An Explorer是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所做的一部自传,初版于1925年的New York。初版为英文本,正如Hedin在德文本的自序(见下述李述礼译本)里所说,“这本书最初是为着美国读者著的”。初版我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是三个中译本,下面就分别说一说这三个中译本的优劣。
第一个中译本是孙仲宽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1933年,题作《我的探险生涯》,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印行。我读的是1997年经新疆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版本。该书的整理者杨镰在“代序”中说:“1932年,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了,题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著名科学家丁道衡校订,而且出版在李译本之后。从文字本身看,孙译或更通顺一些。”他在这两段话中,犯了两个错误:1)李译本初版于1934年,事在孙译本之后;2)从文字本身看,孙译并不更加通顺。实际上,我最初读的就是孙译本,这也是我读Hedin的第一本书。我读过之后,感觉翻译得很糟糕。虽然作者的经历是不凡的,但还是很难让人有读下去的胃口。不过这个中译本的译名颇为精当,这是它的优长所在。而据杨镰推断,译者的底本应是一种英文本。如果真是这样,则英、中二语之间不经其他语种的过渡,自然是很好的。
第二个中译本是李述礼译的。这个译本初版于民国二十三年,题作《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由开明书店所出。我读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五版。1980年上海书店曾根据这个译本影印过,影印的底本应该就是我读的这一版。我对这个中译本的译名不大满意,因为“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完全是平添的。虽然这样的平添,不难找出相当的理由。根据这书的译后记,可知译者此前曾译过Hedin的《长征记》和《霭佛勒斯峰》。译者所译的《长征记》曾因译文不流畅受到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的批评,故而在这次翻译My Life As An Explorer的过程中颇有发奋之意。我读过后觉得他还是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译者自言他是从德文本译出的,则他所用的底本,已非“第一手材料”。不过开明书店的这本书印制颇为精良,阅读以外,留着收藏也是很好的。
第三个中译本是周山译的。这个译本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的。这个译本在豆瓣上的评价比较一般,但在我看来,其实也是颇可读的一个本子。译者的文笔是流畅的,而且毕竟翻译得晚,距离时下人们的语言习惯也更贴近些。这个译本的真正硬伤有两个:一是译者对于中亚地理并不十分熟悉,如译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博卡拉”一类,确实是不该犯的错误。博卡拉为尼泊尔城市,在当下地理界,布哈拉与博卡拉二名几为定译,二者是不应混淆的。虽然从音译的角度上说,布哈拉和博卡拉或许也没多大区别(捎带着说一句,痛仰乐队有“博卡拉”一歌,没什么歌词,不过还是很值得一听)。二是这个本子相较孙译、李译要少一章。具体来说,这个本子并没有把第六十四章译完,而是把第六十五章浓缩为一段话缀在了没译完的第六十四章后面。这种做法,如无相当理由,自然是很奇怪的。这个译本的书名同李译一样,都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同时这本书前后没有任何说明,读者因此不能知道译本所出,这也算是个缺陷。
二、其他
由这本书的译本问题其实不难联想到两个一般性的翻译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在这里还是不妨一说。
一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译者或者出版者是否应当避免自作主张、改变题目?我以为是应当避免的。我以为,当一本书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论贡献,究竟以书的作者为最大。所以,不论是翻译还是出版,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去尊重、保全作者的原意。即如这本My Life As An Explorer,直译过来应当是“发现家的我之一生”(见李译本译后记)。不过或许是因为太拗口了,孙译本就直译作“我的探险生涯”,这种译法是非常好的。可是“亚洲腹地旅行记”这七个字从何而来呢?译者和出版者为销路计,在出版时往往改变原名,这种做法不论中外都是很常见的。但“从来如此,并不就对”,作者本身甚或也不以为意,不过在我们认死理的人看了,总还是要替他辩个是非黑白的。
二是当一本书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最好不要经过别的语言的过渡。其中的道理我想是不消多说的。从前的条件不许,倒也罢了,现在学外语的人这样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应当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即“如果我不能掌握作者写作时采用的语言文字,那不妨把这翻译工作交给能够掌握它的人去做好了。抛开原本,根据译本进行翻译,它的弊端是很多的。”这种议论,务实的人不免要斥之为“天真”,但我想对于这种“无益之谈”,苏格拉底应该是很欢迎的。
《我的探险生涯》读后感(四):最后的古典探险英雄
这书比任何一本凡尔纳的小说都精彩。在今天google earth随手玩转的时候,古典时代的探索经历只能存在于对往昔壮举的想象中了,海上的麦哲伦、库克船长、富兰克林,极地探险家南森、阿蒙森、斯科特、沙克尔顿,甚至空中探险家林德伯格、查克·叶格。。。他们已成为人类探险的里程碑和历史印记。
斯文赫定的探险是最传统的大陆探险,就像游戏《帝国时代》里对陌生世界空白地图的探路者,他的梦想是刷亮地理协会地图中未知的区域。
欧洲人的执着和探险精神中国人很难想象,发自骨子里的。在坦桑尼亚旅行的时候,曾碰到年逾花甲的瑞典夫妇攀登乞力马扎罗山。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大航海时代,每个出海的人都知道他们逃脱不了坏血病,一次长途旅行,只有一半的机会能活着回来,但是一批批冒险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义无反顾驶向无边的大洋。400多年前,利玛窦从欧洲到中国途中,乘坐圣路易斯号到果阿,航行中有五百人死去,近一半。
历史书上把这些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探险家和传教士看成西方势力侵略的象征,我却觉得倒可以说是西方势力被斯文赫定这些天生的探险家利用了,他们利用西方国家的扩张野心实现自己内心自私的探索梦想。
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呢?18岁的时候,诺贝尔在巴库的油田上,有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他欣然前往,教完半年,毅然决定深入中亚内陆,开启童年就埋下的探索野心。开始的行程只是在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大半年后,盘缠所剩无几,依然决定继续旅行,最后流浪到人生地不熟的克尔曼沙赫城,已经身无分文,居然想起仅仅耳闻的一位阿拉伯富商居住于此,就去投靠,在富商的热情接待下走出了窘境。回到瑞典后,正好遇到瑞典国王要派使者出使波斯,听说有这么一位刚从波斯回来,会波斯语的年轻人,斯文赫定就成了皇家使者翻译官,名声大噪后,再也不用愁费用了,到处有人资助。从此,探险之门完全敞开!
他在旅行生涯中,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他好奇的心,遇到一个湖,就要去测水深,没有船,用羊皮做一个,就驶向冰冷的湖中心,测的时候,同行的另一个仆人还要往外舀水;他随着波斯王到厄尔布尔士山上避暑,他却想攀登达马万德峰,三天后登顶5,671米山峰后回来,所有人惊愕不已,甚至在新疆,还想尝试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虽然最后失败。在西藏,受到英国、清朝、西藏各政府的重重阻挠,还是不顾一切想方设法达到目的,当然武装的唐古特盗匪、可怕的自然条件更不可能成为他的拦路虎。他探索和阗河,仅凭普尔热瓦尔斯基提到过,但并不知道现在是否干涸,却坚定地走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陆,这次最悲惨的探险,最后只剩三个人活了下来,他没有找到河流,最后幸运地一个人在临死前遇到和阗河干涸后剩下的水塘。
斯文赫定的生涯是浪漫的,浪漫得让人羡慕流泪。他的文笔很好,在他的笔下,亚洲腹地的冒险历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阳光的颜色,山脊的颜色,深谷的颜色,湖面的颜色,沙丘的颜色,旅途在风、沙、山、水、炎热和寒冷组成的大自然中尽情延展,无数次致命的风险在他的笔下却轻描淡写般度过,仿佛这已然成为他生命的组成。
他的浪漫还在他的情感,旅途中忠实要好的仆人会体力不支或得病死去,陪他走过万里行程日夜相伴的小狗死在帐篷里,出发时带的马、牦牛和骡子到每次旅行结束会几乎死光,赫定悲恸地而又不得不经历着这一切,甚至打猎时也对猎物产生怜悯。赫定对林加庙洞中的修行者感触不已,他们追求涅盘,钻进小洞修行,用石头封住入口,与世隔绝,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光线,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只有僧人定时从小孔递进的简单食物。他在这本书写完后十多年,30年代的新疆探险生涯中,无意中救了败退的马仲英一命,他感叹马仲英军事生涯的豪气,专门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他和马仲英生命中的交集。
我们总是痛恨西方人对我国文化古迹的肆意研究,确实中国大量文物,像克孜尔石窟、莫高窟的文化瑰宝都遭到令人痛心的抢夺,斯文赫定也从他发现的楼兰古城运走了许多文物,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人的探索发现,中国有人对这些文物重视吗?王圆箓道士不是没有把敦煌宝窟的消息上报过,但官员却无人重视。西方人把中国的文物当成珍宝,中国人自己漠然视之,甚至大肆破坏,等人家发现了,轰动了,才重视起来,更可悲的是,还是带着向外界展示中国古老文化的目的。一些文物虽然在国外,但比如大英博物馆却免费开放,让民众认识接触,中国的文物却锁在国宝仓库与大众隔绝。所以我们说人家抢夺中国文物的时候,先想想中国人自己毁了多少。
之所以只给4分,是因为翻译。孙仲宽根据英文版的翻译在30年代当然无法做到名称统一,但本书的整理者杨镰,所做的工作是号称对书中的地名和专有名词重新做了校订,但我不知道校订了什么,大部分地名依然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不同,一些很基本的名词也没有采用统一译法,有的甚至可笑,比如:
苏丹Sultan,翻译成萨尔坦人,
萨珊王朝Sassanid,翻译成萨萨尼朝,
亚速Assyria,翻译成亚西利亚,
苯教,翻译成判波派,
仁波切,翻译成灵保奇,
科罗拉多峡谷,翻译成科罗拉多海峡,
日姓伊藤,翻译成依多,
。。。。。
数不胜数!忍无可忍!更不要说一大堆地名!如果一扫而过,根本不知所云。这些还好,1907年开始的第五次探险,所有西藏地名的翻译,几乎在所有搜索引擎上都找不到,一本地理探险的书,居然最基本的地名翻译无法做到接轨,那勘误作甚?好在地名后有备注英文名称,但因为很多地名是斯文赫定发现取名的,很多当年的英文译名也并非如今的统一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