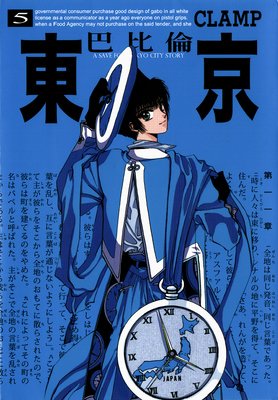
《巴比伦》是一本由[法]雅丝米娜·雷札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比伦》精选点评:
●我还挺喜欢的,充满内心独白,生活本来就是在自言自语。遥远到有些飘忽的迷糊心情,像做梦。
●挺喜欢。尤其是男人隔着行李箱拥抱和亲吻装在箱中的亡妻那段,被复杂的意味震撼、击穿。这本书说出了我心里想的:世界原本就是乱七八糟的,我可不想让它井然有序。
●一边读一边对译文产生怀疑
●雷札的三本里面我最喜欢的反而是这本。标准地铁书,一站一小节,散漫又紧密,是我喜欢的那种吃muffin的感觉。情节上算是《杀戮》的小说版,阿梅丽·诺冬式的岌岌可危。自身身份的不确定与依附于记忆的强迫症,导致了不受控地在他者里流浪。 非常喜欢里面的一些沉思:“对于小鸟,我们想象不出终极的迁徙。”
●后半本渐入佳境,想起《黑镜》鳄鱼那集。枝节冗余。
●扫完,没看懂,比两个剧本来说,相差的太多
●菜的。翻译再扣一星。
●雷札的小说像她的戏剧一样出色,当然,在展示冲突的时刻,对话的分量依然吃重,但从整体上看,引语的处理非常灵活;老年女性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冷硬又嘲讽的语气颇有阿特伍德的风格,叙事上依赖万花筒式的回忆,又让人想起莫迪亚诺。无论艺术形式怎样变,在她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寻找到一个相似的主题:人际关系中从来没有至纯至真,而人存在的意义又总与他人密不可分。看似和谐的夫妻关系中,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炸弹,但故事又不止于此。伊丽莎白的回忆始于让·里诺夫妇的意外事件和母亲的离世,双重打击下,她开始在意起逝去的人、离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细微痕迹,快照、旧书、胡桃夹都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重新翻开尘封了40年的《美国人》,弗兰克摄影作品中人物的特质映射在了现实之中,物景是关键,可惜人已经不在了,有些虚无,有些存在主义
●三星半
●书本身并不有趣,有趣的是其中看似杂乱无章的文字可以引起混乱的情绪。虽然说是谋杀故事,但是直线叙述的背后却是随时可入的波浪
《巴比伦》读后感(一):Ⅵ.践行G(定量之化)
【春上春树随喜文化】 起心动念 最终导致了行为结果 无论是哗众取宠 还是手持式吸尘器 混乱的奇思妙想 只能吃上树的鸡 给人生增添庸人自扰的问题 其中有正确的问题 和自缚的问题 最终的指向并无二致 如小鸡为什么过马路? 回答可以是各种深刻的哲学思辨 死亡是一道下酒菜 作为回到未来的路标 为新的生活接风洗尘 如果没有死亡 天堂就会变成地狱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巴比伦人将世世代代 永居其上 了解死亡 你才能继续前进 修得深度思考的学分 让打开的心结 得以延续 死亡随时随地 以一切皆有可能的 想象力生发 至于复活 反而没有那么大悬念
《巴比伦》读后感(二):2020.7.12
只有200页的《巴比伦》我从拆封到看完大概花了一个月...主要原因还是中间忙着赶ddl和期末考。考完了试,两天就看完了。 当时买书的时候冲着龚古尔文学奖买的,书封上写得倒是刺激,“一场由春日聚会引发的命案”,结果命案在第68页才出现几个轻飘飘的字,“我把莉迪杀了”。前20页都是在不同的餐馆里等菜的时候看的,雅丝米娜写得很碎片,我看得也很碎片,结果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一头雾水。200页里面在谋杀出现之前都是毫无顺序和逻辑的人物关系和性格铺陈,一会讲“我”的少年,一会讲让里诺,一会讲莉迪;命案发生之后也是主线叙述胡乱插着一些人物另外的碎片信息。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也是在暗暗justify人物“不可能”的动机。我不是很能看得惯这种叙述方式...但是习惯之后也还好。 让里诺和莉迪的夫妻关系像缩影,聚会上谈笑风生、夫妻和蔼,实际早已互相充满怨气,聚会上不合适的笑话也只是个导火索。书里关于让里诺的碎片信息很吃重,人物塑造也最立体。 伊丽莎白作为中老年(?)女性的第一人称叙述很冷静又带点嘲讽,母亲去世、让里诺家的悲剧,平淡的关于过去的回忆里也不免带上无奈和感伤。伊丽莎白和让里诺的关系挺有趣,不是恋人没有暧昧,只是朋友,精神世界中孤独和忧郁相通的朋友。她为什么热情帮助让里诺藏匿尸体?我总不免想起法语课本里一段节选,妻子拿着枪控诉丈夫不出轨自己。我们厌恶平淡无奇的生活,又不得不放手让自己就此沉溺,cling to那些已经离开的人的痕迹。 《美国人》里黑白的照片,物景是关键,物景才丰满人物。
《巴比伦》读后感(三):2020.6.10
读完这本是昨天的事了。前半段琐碎的内容,主要人物的出场和对物象的构建都带着一丝沉闷,看了一小半稍作休息,喝了点咖啡摆脱午后的困倦,继续阅读。难免将内容与《鞋带》联系起来:都提到老年夫妻的生活,故事中都有猫咪的出场。比起另一本使用的第三人称叙述,《巴比伦》用第一人称,通过一位青春不再的已婚女士的视角展开故事线。
讲述者不断使用插叙与倒叙交代自己与邻居让-里诺从相识以来的过程。(正是这一点在开头令我费了好大劲克服困倦理清思路)楼上楼下,邻里邻居,总是在楼梯间碰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多么亲密的朋友,却可以谈论起遥远的童年,她认为他是“认识的最温柔的男人”。让-里诺其人外貌平平,身材瘦小,此时我们脑海中可以出现一个皮肤不甚光滑的老年男士形象。与他相比,他妻子莉迪的出场更为明艳,一头橘色的秀发,在爵士酒吧唱着歌。
在故事讲述过程中不断插入的相片集可以视作一连串时间点的集合。我们可以从书里大致梳理出一些片段,一些掠影,和让-里诺夫妇婚姻里的留影。他们是重组家庭,莉迪有一个小外孙,常到他们老两口的家里来。他极尽所能想要讨小孩子的爱,“想得到人家的爱,这样做对吗?这种企图难道不可悲吗?”作者这样说。
我的心口一阵悲怆。继续往后读,继续发现残酷的真相:当一个懂得基本社交礼仪的成年人想表达对一个人的不喜爱,他大可采取许多不那么令人受伤的方式,只要对方与他没有深仇大恨——而小孩子,他们的爱恨更加直白,对一个人的不当回事儿和不喜欢都写在脸上,并且付诸行动,好像就要明明白白地喊出声来,“我不喜欢你”!很难说哪一种带来的伤害更痛,反正对于让-里诺来说都是一样的。他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期盼的一样。只不过他的自尊来得更加平缓,浓重,迟钝,被自卑的情绪拖着。
聚会上,让-里诺很快乐,他和楼下邻居请来的陌生宾客们把酒言欢,不断讲着俏皮话,像是把自己讨人喜爱的能力全部积攒起来,只为了这一天似的。的确,他在与客人们的交谈中感受到了那种似乎得到他人肯定的快乐,正如照片里那样,他笑得开怀。
然而他妻子在聚会结束后大发雷霆,认为他不该拿夫妻之间的事做调侃,他对她的取笑以及今晚的种种让她感觉蒙羞。他出门抽烟,耻辱感随烟雾慢慢升起。自信就和欢笑一起流失了。他再也不能忍受妻子神经质地挑剔鸡肉,再也不能忍受她每天只关注禽类的命运,再也不能忍受她对他外貌的指责,以及她和她的外孙对他的蔑视:你不配做里诺姥爷,这个孩子有自己的亲姥爷,只是他过世了。他只想让她安静下来,所以他掐住了她的脖子。因为愤怒持续冲击着他,还是因为他喝得太多了?总之当一切归于平静,她的眼神早已失去了神采。她死了。
他们爱过,但是婚姻像个奇怪的袋子,把两个曾经各自生活的人装进去,他们在其中忍受着碰撞:彼此的家庭,性格,习惯……有人在其中幸存,讲述者和丈夫“没有爱过”,平静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然很足够;也有人在其中受伤,甚至死去。不仅仅是婚姻,人际关系交织的网也在包裹着其中所有的人。我们生活在无边的大网里。
朋友们在春日聚会谈到的爱与生命的虚无,书中的哲思,都不能使本书被算在侦探小说的范畴,后半段类似侦探小说的结构反而更戏剧感,尤其是最后一幕。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看完又一部令人恐婚的小说还是没个结果。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怀想的美好世界,大概是坐在巴比伦河边追想的锡安。
《巴比伦》读后感(四):我选择为他藏匿尸体
“他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仪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隔离出个人的独特空间。”“我”如是形容我的秘友让-里诺。 雷札笔下的第一人称主人公伊丽莎白和里诺同住在一栋中产阶级公寓里。二人因习惯走楼梯的小小默契而相遇。两人相伴的方式日常琐碎:他带她去赛马庆生,带她去看生病的姑妈。 雷札很少写二人的对话,而是倾注于写“我”眼中的里诺。观赛马时的里诺喜形于色,与外孙处处争执又处处忍让的雷诺狼狈落寞;里诺人前的高兴和年轻的外表在“我”看来转瞬即逝,一本正经、驼背才是里诺更持久的面貌。 “我觉得,让-里诺•马诺斯科利韦很孤独。”这是“我”对里诺灵魂最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是“我”对自己的理解,里诺对“我”的理解。 因为这种理解,当里诺冲动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帮他藏匿尸体。 雷札的故事披着悬疑侦探小说的外表。然而,里诺的杀人动机简单荒谬,凶杀案的起因经过结果很快就在读者眼前清晰明了起来。如果把小说放在雷札熟悉的舞台之上,凶杀案只是构成了舞台的布景、决定了叙事的结构,但揭示舞台剧主题的要素一定是主人公抬着头、直立着说出来的旁白。
雷札反复引述罗伯特•弗兰克的摄影集《美国人》。摄影集里的人,颓败、狼狈、孤独。如弗兰克自己所说,这些人和场景在当时的美国,“到处都能找到,但是却不那么容易解释”。 “我”在观赏照片时质疑:是否所有照片都“题名颠覆阅读”,没有日期和人物名字的照片就毫无意义吗? 雷札似乎借“我”的口吻说出对照片的理解:照片不是因为它的讽刺色彩而被偏爱。标题不被记住;记住的是忧伤的五官和节外生枝出的薄阴天气。人物的纤弱让人感觉象征统治者的高墙吞噬着他们。这也正和弗兰克所说的契合,这些美国人难以被解释,只是触发着联想。忧伤、孤独等情绪,在现代美国社会过于大众,但依旧是复杂的、私人的。 “我”擅长于用阅读这本摄影集的视角观看、理解着生活中的每个人。比如,“我”把第一次见到的莉迪——她挽着里诺的臂弯——和摄影集里挽着军官丈夫、用心穿着、冲着镜头微笑的妇人联想在一起。“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女人“春风满面,容光焕发”,而是深感这转瞬即逝的瞬间无法续存。“我”习惯着质疑片刻的美好,习惯着接纳接踵而来的破灭感。 在雷札看来,这种破灭感是故事中每个人、摄影集中每个现代美国人(包括那个此刻微笑的妇人)以及现代都市人,都或早或晚需要面对的。男女主人公超前面对着这种破灭感及其伴随着的无奈、孤单等情绪,也因此,他们游离于人群外,又得以在人群外找到彼此、得以相互理解。
“之所以犹豫惆怅,往往不是因为大背叛,而是因为周而复始、微不足道的小失去。”行文间的一个小短句,尝试解释每个现代都市人的惆怅。而这种持续的小失去,持续带给皮埃尔失落感、孤独感、绝望感,最后竟然导致对各类犯罪类社会新闻向来都不敏感、把它们看作臭事和烂事的皮埃尔失手杀了人。 “我”打电话告诉每个人里诺杀人后被警方带走了。“在电话里,他们站在中间立场作出的所有评价,让我发觉自己是多么接近让-里诺,而不是克洛戴特,此前我倾向于认为,她的刻板源于某种形式的理性内省,现在突然感到,它暴露的无非是平庸的人云亦云。” 故事在写,每个人都如“我”和里诺一般孤独。可事实上,大家从未接近过彼此。 只有“我”的第一反应是帮助里诺藏匿被失手杀死的妻子的尸体。 “我突然就开始怀疑世界的协调。各种法则似乎彼此独立,相互冲突。”
《巴比伦》读后感(五):人际漩涡下的生存困境
(实在不好意思再发给导师问 这篇有无publier的可能..)
ur le bord des fleuves de Babylone, nous étions assis, et nous pleurions en nous souvenant de Sion.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旧约·诗篇》
雅斯米纳·雷札(1959—— ),法国戏剧家、小说家,其剧本代表作《“艺术”》和《杀戮之神》为她带来世界声誉,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她也因此曾两度荣膺美国托尼奖、英国劳伦斯·奥利弗奖。2011年,波兰斯基将《杀戮之神》更名《杀戮》搬上了银屏,使更多的受众逐渐了解雅丝米娜·雷札。
雷札创作类型多样,除了戏剧之外,她也从未停止过小说写作。2016年,小说作品《巴比伦》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和龚古尔中学生奖。小说以两对中产阶级夫妇为中心,讲述了一场“春日聚会”引发的血案。在犯罪小说的外表之下,雅丝米娜·雷札以她特有的幽默与敏感展开一幕幕日常琐屑、夫妻关系、社会生活的荒诞剧,展现了在繁杂的世界中失去归属的孤独。
披着侦探的外衣
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小说叙述者“我”名叫伊丽莎白,和丈夫皮埃尔住在公寓的五楼。六楼的邻居是马诺斯克利韦夫妇——让-里诺和莉迪,让-里诺在一家酒吧遇到了歌手莉迪,两人一见如故。因为不爱乘电梯,我和让-里诺常常在楼道里相遇。我60岁生日那天,让-里诺邀请我到欧特伊去看赛马。这天过后,我就喜欢上了让-里诺。我们时常一起出去走走,偶尔还到街角喝杯咖啡。我觉得他是最温柔的男人,有时彼此之间说些从不跟被人提及的知心话。
有一天,我打算组织一场“春日聚会”。而散场后的一个小时,邻居让-里诺敲门告诉我和皮埃尔他刚刚把妻子莉迪掐死了。丈夫皮埃尔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但我还是趁他入睡后帮助让-里诺把莉迪的尸体装进行李箱,打算放到不远处的工作室。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期发展。在公寓大堂,我们意外撞见聚会晚归的三楼女孩,我拿起手机,决定报警……
书写复杂的人际
让-里诺和莉迪这一对看似和谐的夫妇,为什么最后会走向这般结尾?究其吵架根源,仅仅是因为在聚会上,让-里诺讲了一个莉迪的故事。有次在餐厅吃晚餐时,莉迪问服务生给鸡喂的是不是有机饲料。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又问到鸡有没有在树上栖息?服务生觉得很滑稽,而让-里诺一直拿这句话打趣。争吵中,让-里诺指责莉迪每天只会同情家禽,而不是同情人类,这让他受不了。情绪失控后,他生生掐死了妻子莉迪。
事实上,“人际关系”一直是雷札笔下永恒的主题。无论是《“艺术”》中的塞尔日、伊万、马克因为一幅白色油画产生争吵,还是《杀戮之神》中两对夫妇、四个成人之间因种种琐碎而翻脸,无不都刻画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残酷、厌恶。《巴比伦》自然也不例外。人际从来不会简单,看似平静的关系之下暗流涌动,而“我”渴望逃离自我、逃离他人、逃离过去。
刻画生命的虚无
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一样,雅斯米纳·雷札似乎对照片也有着某种执念。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这本摄影集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了多次。在“我”看来,《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凄凉悲惨的书籍。“物景是关键。真正的联系在于物景。”人生虚无,仿佛只有照片是永恒。与此同时,“要是没有日期,没有中心人物的名字,照片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巴比伦》中,作家也没有吝惜笔墨感慨时光逝去,青春不再。正因为如此,以照片为代表的事物才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包括让-里诺提及的父亲常常念的《圣经》里的那句话:“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在犹太教的圣典里,锡安是耶和华居住之地,是耶和华立大卫为王的地方。一直以来,国破家亡的犹太人都期盼着上帝带领他们前往锡安,重建家园。或许,当让-里诺的父亲高盛朗读这句话的时候,他“曾有过一种对模糊整体的归属感”。只是这种归属感过于遥远,于是,命运才会“一半是痛苦,另一半大概就是所谓的虚无”。而这虚无,这孤独,恰恰是我们每个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