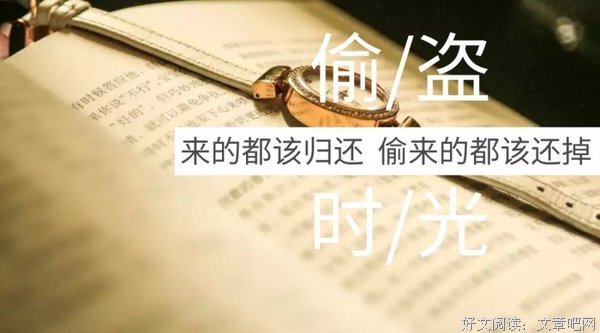
《盗窃》是一本由[法]萨布里纳·切尔奎拉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1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盗窃》精选点评:
●在地铁里读完的小书
●盗窃是一头戴着番红花、接骨木花、黑醋栗和蓝风铃的奶牛
●一场头脑拉伸操,看完神清气爽
●啊我爱这本书!
●啊!太了不起了!
●点到即止的哲学主题分析/可以激发兴趣,开启思路,将原本单一的主题引导到各个哲学流派
●这本书更倾向于对社会学的思考
●已购。看似涉及法学的题材,但是展开方式却极为开阔,追究盗窃行为的本质及其历史上的待遇变化。不过略有些偏重其理想化色彩的一面,恶的一面展开不足。
●再一次确定自己毫无经济、政治思维。
●美德如此崇高,连窃贼们在自己洞穴的深处也敬重着她。
《盗窃》读后感(一):何为盗窃
小偷是微不足道的窃贼
有时只有一个人
海盗是威慑不小的窃贼
不过只有一艘船
小偷的“不义”,海盗的“不义”
只因其狭小的规模
换得为人不耻的名声
你去摸一摸小偷的口袋
能有一块不过期的面包已是幸运
你去摸一摸海盗的衣衫
能裹住根骨的外露吗?
贫穷的强盗啊,注定不法
富有的君王,却因其庞大的舰队
占据了所有的正义和法律
盗窃、抢夺作为不道德的托词
成了为人口诛笔伐的盗贼
而占领、平天下作为智慧的托词
却铸就名满富足的掠夺者
就让那厚厚一沓的沉思录
将成为最不可思量的道德哲学吧
《盗窃》读后感(二):"强盗”的背后,有我们所蔑视的软弱
是什么让我们对亚历山大大帝和科尔特斯一类人物赞赏有加,却对卡尔图斯和拉菲亚特这等任务充满鄙夷?是前者的强大,也是后者的弱势,在“强盗”这个词背后,并非只有犯罪,还有我们所蔑视的软弱。——爱尔维修《论人》《盗窃》是围绕盗窃现象和偷盗者展开思索的一本小书。虽说是思索,其实本书更类似于一份指向性明确的大陆哲学相关文献综述,只不过由于作者擅谈电影、文笔上佳,才让那些引经据典不显得生硬难读,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盗贼的形象不断地被法律、电影、政治、文学领域被消费,这一形象时而正义、极具谋略,时而狡黠、无耻,但大众仍十分乐意为盗贼下一个定义,却只能在矛盾重重的盗贼形象中迷失。所以,盗窃和盗贼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解答盗贼形象层出不求的关键。
“什么是盗窃”,作者给出了三个贯穿全文篇目的维度:
1. 是一种掠夺行为,即我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取得某物,而此物是不可索取的。
2. 是一种财产的转移,也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可称为“重新分配”。
3. 是一种越轨的经验,一种乐趣的来源。
作者从“盗贼多穷人”即盗窃是穷人所独有的吗,引入“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盗窃之物是不可掠夺的?”,认为(一般认为是穷人独有的)盗窃行为所处的社会(私有制社会)本身就是由富人的盗窃为基础。为辩驳盗窃“非正义性”,认为盗窃行为是对抗契约精神和商品社会的“无偿-无私行为”。此两章可谓引子。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暗示了盗窃的劳动属性。依马的表述,劳动即运用了知识和技能实现自己的行为。在不少文艺作品中,有盗艺精湛的“匠人”盗贼(区别于莽贼)可通过习得技艺和聪明展现盗窃的艺术。正如斯巴达人的教育方式,让孩子通过历练盗窃能力获得计谋、掩饰、活力、敏捷、冷血、残暴、狡猾、果断等特质。盗窃的作品不是盗窃物,而是盗贼人本身。
而为何古代“侠盗”能成为人们的英雄人物。福柯认为,这是出于人们对出身于与他们相同阶级,自认为是不公不义之受害者并做出反应的盗贼有强烈的认同。盗窃原是一种政治性和颠覆性的行为,政权所害怕的是这类行为被大量效仿,因而采用两种途径阻止侠盗英雄形象的深入人心:一是对盗贼形象专业的塑造,讲盗贼依据“失足犯罪者”的本质划分为一个单独的阶级,而远离人民。二是大量塑造某种罕见的盗贼类型,如极为非凡的、智慧的盗贼,使人民对他降低认同感。
反抗式的盗贼,盗窃掠夺他们认为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即夺回。对于所有权的归属,社会主义学家已经提出过不少观点。尤其是资本家大量剥削劳工剩余劳动这一合法行为,可否说是一种对劳动成果的盗窃?蒲鲁东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占有替代了所有权,这种即是盗窃。他指出交换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解决办法。施蒂纳认为但凡所有权即是盗窃,对权力不再加以崇拜便将滑向无政府主义。使盗窃成为正义的行动,需要两个前提:要么盗窃行为被认为是对剥削盗窃的还击,要么盗窃行为针对的就是剥削者。窃贼,就是那些不再相信剥削者的财物是不可索取的人。
本书大部篇幅置于政治语境之下,从《贫穷》至《重新分配》贯穿一线,盗窃一题必须回归对社会正义的讨论。有人想,自然的不公赋予盗窃正义,而其不道德性却是由于剥夺者盗窃行为的道德。如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强调的,如果不是从私人利益的角度查看,而是以正义之名进行重新分配的角度来看,拉斯科尔尼科夫也不过是把盗窃的战利品重新分配给了自己。那么为了满足利益的盗窃和为了正义的盗窃并无什么界限。相反,原本十分吊诡的后者却更具备了可能性。
《盗窃》读后感(三):关于《盗窃》部分内容的小结
这本《盗窃》是法国哲学家写的,然后读库引进,这种哲学小册子很多观点还算是非常激进,我曾经拿了某一章节的开篇的《革命将至》的导言给我一个朋友来看,他看了就说,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盗窃》这本书的整个书写的背景也是延续西方文明世界经典的谱系,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家对盗窃的一些言说。
所以呢,对于这个中国读者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隔膜。
但是中国的财产权、“盗窃罪”等法律体系还是延续下来了罗马法及刑法法律体系。目前生活在中国不可避免的,是中西杂糅的。
如果对盗窃下一个定义呢,当然众说纷纭。
最标准的定义:对于财产权益非法侵占。
古典时代的财产权,当然包括不动产、动产乃至奴隶、子女、配偶。
现当代社会还有知识产权,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盗版了,免费下载别人的一些电影啊,这些是否算盗窃?
财产权益就涉及主体了,所有者、占有者,等等。
然后这个东西凭什么就归某个人所有?依据西方的传统,土地啊,世间的万物啊,都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上帝。
所以呢,洛克就会认为,虽然圣经上是这么讲,但是呢,个体的劳动将劳动所得从自然当中剥离出来,所以归属于个人所有,变成了私有财产。劳动所得产生的私有财产属于自然状态。
但是呢,霍布斯就会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财产权益不属于自然状态,而是法律的规定。
他也提出了在古代的斯巴达城邦的法律制度里面,青少年人盗窃不算罪过,后文当中还提及卢梭《爱弥尔》,卢梭列举了斯巴达训练青少年人的细节:教官把斯巴达的少年公民关在牢笼里面,几天不给吃喝,然后他们就充满了野兽的本能,教官下命令让他们去偷抢食物,并且不能被人发现;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接受鞭笞,在斯巴达,奴隶才被人鞭笞。另一方,则派其他少年公民负责守卫祭坛上的食物,不准被偷走,守卫者有鞭笞被当场抓到的偷窃者的权力。一攻一守,卢梭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在训练斯巴达的战士,斯巴达的少年经历历练之后,不论口才还是身手,都胜过雅典的同龄人,雅典人既说不过,也打不过。不过斯巴达的奴隶是不参与这些活动的。
古罗马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也记录过,斯巴达的少年偷窃了貂,塞入罩衫之下,宁可自己被貂的爪牙抓破肚皮死去,也不愿意被暴露,这种忍痛克制,被看作美德。
孟德斯鸠则区分了 交易与掠夺,交易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交易双方可能只顾私利,丧失公德,唯利是图。反而是掠夺者有时候会慷慨照顾公益。
这种思想在后世法国思想家当中有很多传承,不少盗窃者会辩解,自己的盗窃就是对于 现代日益增长的交易风气的反动。
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说,财产权的产生,既不是因为占有,也不是因为劳动,是一个无因之果。当然他的矛头是直指那种大资本家的,比如说组织了10个人进行劳动,肯定比单个人劳动10次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但是资本家只给工人们一些基本生活所需,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生育儿女,产生出新一代的劳动人口,大部分收益被资本家掠夺,资本家才是盗窃者。哲学家施蒂纳则认为,所有权本身才导致了盗窃。马克思则认为不论最后财产如何分配,都不公正,不如从源头确定生产资料公有制。蒲鲁东则认为这种制度不会激发出创造/生产动力。
在蒲鲁东看来,所有权本身就是一种盗窃,就类似于奴隶制本身就是杀人,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人道主义的背景。在西方社会看来,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支配一个人身心自主的权利,剥夺了他的自由意志,这就等于杀人。可能在东方社会,甘心为奴的人很多,至少贾府的豪奴的确比外面的自耕农要过得舒服。
福柯则进行了更加激进细微的文化批判,他认为,18世纪以来,侦探小说、侠盗小说在欧洲各国,大规模的出现,可能有统治阶级的阴谋。
首先社会制度层面,盗窃只是侵害财产的犯罪,被现代的刑罚制度进行处罚,监狱制度不会转化他们,反而让他们在监狱塑造更多的反社会认同。但是囚犯的身份还是让许多普通人望而却步,不敢模拟效法。
他很关注那些非正常的人类,比如说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轻微的犯罪分子,现代社会会有各种各样精致的学说,精神病学、犯罪学等等将这些和主流人口不同的边缘人,分门别类,在福柯看来,这是瓦解他们与人民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倒不是犯罪本身的残忍,他们害怕的是,犯罪容易被大规模模仿。
另一点,就是包括亚森·罗平的侠盗小说、高智商犯罪的侦探小说,这些精英人物智力超凡绝伦,与普通的侦探斗智斗勇,会让普通读者觉得自己望尘莫及。一方面他们嫌弃那些被贴上了犯罪分子标签的普通盗窃者,另一方面呢,那种精英盗贼又望尘莫及。这样就很大的瓦解了这种普通群众盗窃的意愿。
……
(其余暂时没有整理)
《盗窃》读后感(四):为什么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哲学对当代教育而言最实用的用途可能是拿来考试——哲学考试是法国每年中学毕业会考(BAC)的第一个科目,而这门考试的试题如今也演变成世界性的新闻话题。2018年的试题已经在6月公布,又有一些之前罕有人想过的提问将在试卷上与考生交锋:题目1:文化使得我们更具人性吗?题目2:欲望是否为人类缺点的标记?题目3:是不是只有通过经历不公正,才能认识什么是公正?哲学课是法国高中第三年的必修课程,通过每周数小时的课堂训练,学生将要在4小时的考试时间内选择一道题目,交出一篇包括解题、论证与总结的文本。
思考这些问题有何用?就连法国内部也形成了争论两方。一些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课程占据了学生们太多的时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面对哲学就像中国学生面对数学,在考试结束后,可能再也不会翻开一篇论述,而教育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实用的生存技能。但是法国的教育者们依然坚信,人类文明留下的哲学遗产能够帮助学生真正建立深刻的思维训练。
首先是对语言的掌握,没有对错的哲学讨论在无形中能让学生更好地组织自己的语言,即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公正”,但准确说出对“公正”的感受却是能够努力做到的事,这种“语言”的呈现感可以让你对一个抽象概念的理解变得清晰。这也是苏格拉底终其一生奉献的事业,他在雅典的广场上和年轻人讨论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胆量”等等。一连串的提问使人们对深信的事物产生怀疑,因为人们至少知道,如果不思考这些重要事物的本质,那人们将对其一无所知,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此外,思维训练也副生出良好的谈话习惯——日常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和没有逻辑的人聊天。如果我们能准确地将内心的“公正”描述出来,或许描述其他一些生活中更为复杂的情况会更加容易。从这个层面考虑,哲学确实是最佳的工具。公元前387年,柏拉图于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学园,那时的学生漫步在橄榄林中彼此激辩,寻找着老师口中的“逻各斯”(logos,事物的道理或理由),他们是否得到了最后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拥有的是关于他们谈话的记载。无论如何,那些不带矫饰简洁优美的语汇构成了谈话,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道德有所遐思。
但哲学在今时除去考试之外最为实际的用途,可能是帮你梳理现实。这个梳理的起点开始于想象。一个深刻的例子便是“时间”。“时间”或许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抽象的概念,起先是哲学家想象“时间”——赫西俄德认为时间是永恒的天神柯罗诺斯(Chronos),宇宙中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赫拉克利特说道:“时间是一个玩骰子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再然后,有人想要丈量时间,将其空间化,变成钟表上围绕指针的十二个点,还要将其划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三种单位。然而亨利·柏格森又说道:“脱离这种时间丈量,实际上才是我对时间的内在感觉。”于是,我们在圣奥古斯丁这里终于找到了意义的锚点:“说有三个时间(现在、过去、未来)是不对的,对于我们,只存在一个时间,就是现在;在其中我们有三种态度,过去的当下(当我回忆时),现在的当下(当我注意时),未来的当下(当我期待时)。我自身作为主体拥有时间的意识——我能够回忆、注意或期待——这使时间存在。”对概念的想象最终落脚于现实,如果认同圣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解读,相信你会更恰当地与时间相处,在现实世界中变得自由。
现代社会是不是对哲学失去了信任?哲学能不能证明自身是否仍然具有意义呢?就像人们对于时间的种种求索,这些疑问恰恰是现实被梳理之后的结果,正是因为对现实有所思考,才会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关乎现实的一切产生疑问,而哲学提供的批判能让你思考得更多,让你在思考后的行动更加符合自身的要求。想象那个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将全部精力与热情奉献给一尊雕塑的皮格马利翁吧,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他对自己亲手创造的伽拉忒亚产生了疑问呢?他是完成了一件至臻的艺术品,还是成就了其他更为形而上的崇高?无数哲学家替皮格马利翁思考了这个问题,他们思考后的结果进一步激发了更多艺术家的反思和实践,将艺术的意义炼为人类追逐不歇的完美。而这也是哲学往往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原因所在,如果回到古希腊,人们会说:“各种事情都有理由,但追求最后理由的思想就是哲学。”
诚然,如果在历史范畴内看待哲学,我们将会发现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哲学的历史命运比我们所有人想到的都更为复杂。“事实上每代哲学家都试图修改哲学的含义,甚至用新的含义挤掉原来的含义。”哲学家赵汀阳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哲学’好像是一个空着的括号,或者是个X,哲学家们在这个象征性的兼收并蓄的概念里填入非常不同的内容。”而这同时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浩渺的思想遗产,采撷其中的一些来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服务,几乎变成哲学最大的功能。哲学似乎是“万能工具”,可以用来解释宏观的社会与时代变迁,也能用来填补人们在日常消耗里的思维空虚。
但赵汀阳先生想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哲学在当今面临的危机。信仰科学的现代社会把科学当成“精神支柱”,然而,“科学虽然是最好的知识,却不能是精神支柱——知识再好也成不了精神。”在利用哲学梳理现实的过程中,哲学展现了它辨认事物源头的力量:我们痛骂一名偷盗的窃贼,而哲学则促使我们思考隐藏在偷窃行为背后的人类财产关系。等到这样的思考足够多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能获得一种不局限于时代与社会框架的精神体验,同时见证到人类文化的尊严。然而,赵汀阳先生遗憾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当今社会科学以及一般文化观念对哲学的忽视已经损害了文化的整体感觉,我们不难发现,现在关于政治、社会、道德、生活的话语虽多,却不能形成精神——不是通常所说的精神失落了,而是形成不了精神。”
于是,似乎可以将隐藏在这个话题背后的疑问抛诸于讨论:现在的人们还会认真打磨自己的思想吗?充斥着信息的大脑和一刻不停接受反馈的眼球是否还能让我们践行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自我关照”(soin de soi)?而又应该思考哪些事情呢?是制度、边界、各种主义等等这些被人类构建起的东西,还是思考人本身?伊壁鸠鲁提供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将时间拿来思考唯一的、真正的财富,即灵魂的健康。这财富无法与我们自身分离开来:它体现在我们身上。因此,伊壁鸠鲁还补充道,去追寻它“永远不会太晚或太早”。
1670年,布莱兹·帕斯卡尔出版了《思想录》,他在书中阐明了人的有限性,又在这悲剧般的人的共同命运中寻找到最能慰藉我们的存在理由。帕斯卡尔写道: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会死,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中,西西弗走向了他的巨石,达那伊得斯姐妹永远要去填满一个底部穿孔的木桶,而第一个被松绑的人走出洞穴,在山头看见了太阳,他决定重返洞穴,解放其他被铁链束缚的同伴。帕斯卡尔说:“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马塞尔·莫斯发表了关于“礼物”的论文,讨论“赠予”和“互惠”对人类文明的意义,而礼物的呈献与回献则构成了古式社会中交换的主要形式,人们甚至相信存在某种神灵,它要求对礼物的“回馈”是不可逃避的义务。“礼物”的仪式存在于万物之间,就好比先民在秋天丰收后举行盛大的祭典,将自己的收成作为礼物回献给自然。“礼物”仪式令人悸动之处便在于它所包含的慷慨本质与荣誉观念,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兴起,这种仪式本来蕴含的意义逐渐消亡,最终成为想象中的传统。
或许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哲学是人类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如果按照“礼物”仪式所必须遵从的规则,我们该拿出什么东西来“回馈”?又该“回馈”给谁?
参考资料: 刘敏,《触及根本的教育:从法国基础教育的哲学课谈起》 赵汀阳,《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其自我反叛》 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读库·哲学系”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