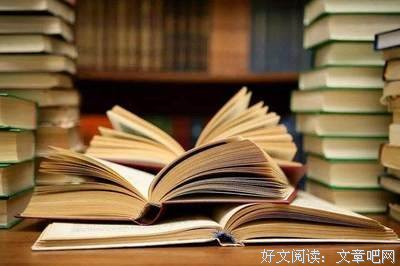
《魔山》是一本由(德)托马斯·曼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5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魔山》精选点评:
●放弃了。。还是过段时间找钱译本来读吧。。==
●再读一次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被此书影响的。
●危險的小說
●翻译令我纠结。
●旧:结尾老是给我一种仓促感,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生活也正陷入魔山。 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状态,迷人的孤寂感。 重新来打分评论。大概是因为冬天渐渐到了,前天约阿希姆走向死谷的情景突然出现在我脑中,接着《魔山》就涌了上来,我突然觉得我是爱这本书的。 当年《荆棘鸟》也是这样在某个时刻突然涌上了澳大利亚的气味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啊。
●终于还是看不完。。。阿
●书厚,拿得手累,每一页字太多,看一页总恍惚那么几下,然后睡着了,错漏了很多句子,很多情节,以后重读吧···
●可以。
●看睡着了,还是推荐托马斯曼的堕落吧,他的小说实在是太长且无聊了
●70天啃完70万字。感觉德国人能说啊。
《魔山》读后感(一):“我们在,死就不在”
题目是《魔山》里的一句话,好像《罗马书释义》里还有一句话,是说世界上存在死亡(具体记不清了)。这不是“两个观点”,而是一对矛盾的观点,有意思的是虽然互相矛盾却不是一对一错,而是都是错误的,我的看法是死是可以观测的,不能说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就像海市蜃楼能观测,但能说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吗。
我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在于讨论死亡,我想说的是写书不能不经思考、想起来什么就说什么,制造些错误与误解。
《魔山》读后感(二):P159 赛特姆布里尼如是说
分析作为启蒙和文明的工具是好的,可取的;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动摇愚昧的固执想法,瓦解原始的成见,葬送虚假的权威,换一种讲法,好就好在它解放、纯化思想,使人变得像人,让奴隶成长为自由人。分析又坏,很坏很坏,如果它妨碍行动,侵蚀生活的根基,无力塑造生活。分析可能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乏味的就像死亡,事实上它本来也可能属于死亡——与坟墓挺亲近,与尸体解剖挺亲近…
咆哮的好,雄狮! 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想。
魔山开卷一月纪念
8月7日 又過了月余,讀完了第六章~約阿希姆去了
355 卡斯托普滑雪遇險時的思想
什么高貴不高貴!什么死與生,疾病與健康,精神與自然!難道他們是矛盾?我要問:難道他們是問題?不,這不成問題。還有高不高貴也不成問題。死必然寓于生之中,沒有必然的死也便沒有生;主的人的地位正處在正中央、處于混亂與理性之間,正像他的國度也處于神秘的集團與不穩定的個體之間。... 人應該主宰矛盾沖突,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人比矛盾沖突更加高貴,比死也更高貴,對于死來說太高貴了——這便是他頭腦的自由思想;比生更高貴,對于生來說太高貴了——這便是心靈的虔誠信仰。這就是我做的詩,一首關于人的夢幻之詩。我愿銘記著它。我愿做個善良人。我不容許死亡統治我的思想!因為善良與仁愛存在于我的思想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的地方;死是巨大的威力。人摘下帽子對它表示敬畏,然後便踮起腳尖擦過它身邊,繼續前進。…
《魔山》读后感(三):光|懒惰是可怕的
很早前就听过托马斯·曼的《魔山》,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厚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会有时间去读它,直到开始在山上工作,这才想到也许这就是最恰当的时机。在《挪威的森林》里,一个女人对前来看望直子的男主角说“怎么把这种书带到这里来了?”,男主也觉得很抱歉(直子是他死去的好友的女友,也是他喜欢却不敢接近,只想默默守护的人),便觉得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为什么不宜出现在精神病疗养院里?直子是因为精神病才住进山上的疗养院里,而我也是出于某种逃避心理和过度抑郁才选择去山上,总之也有点不正常,这样的情况下读《魔山》,应该会很应景吧?
《魔山》一直被誉为德语文学里的扛把子般的存在,这我不懂,毕竟读过的德国文学少得可怜,托马斯·曼是拿过诺贝尔奖的大师,对这也不感兴趣,而且总是恶意认为这些大文学家写的东西对普通大众来说根本就是没法看的,要不是在喜欢的书里遇到这本书,我是怎么也不会看的。
如今书读完了,它讲一个荒诞的、细思极恐的长故事:一群有钱有闲的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休止地养病。
这就是我理解这个故事的第一点,“无休止”。《挪威的森林》里,直子的康复遥遥无期,带来一本写“无休止养病”的书显然是晦气的,更冒犯人的是,这些病人之所以会“无休止”地休养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在乎是否会痊愈——这是一群心理扭曲的病人,他们可享受养病了,用书中原话来说,就是“那么轻浮,那么愚蠢,那么放荡,那么缺少恢复健康的诚意”,如果你有个朋友干什么都笨手笨脚整天乌龙不断,你送他一本《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人家可能会尴尬又生气——你嘲笑我?!若是疗养院里有读过《魔山》而又过于敏感的人,恐怕也是要勃然大怒的,“你小子是在讽刺我吧?!你觉得我生病是故意的吗?!”
什么样的病需要“无休止”地养下去,而且这些病人还能如此心安理得呢?肺结核,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七年,当时的肺结核也不能说是绝症,只是治疗成本异乎寻常地高,需要修仙般的疗养环境、宫廷式的悉心照料、必要时还需要“人工气胸”之类的黑科技加持助攻,且稍有不慎就容易复发,毕竟得病的人那么多,而有条件治疗的人又何其少,众所周知,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也因此,与其说是来疗养院“治病”,倒不如说是来缓解痛苦和推迟死亡的,所以,他们才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向命运屈服。
向命运屈服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没有未来的,指不定那天早上就起不来了,那就算了,剩下的日子怎么舒服怎么过吧,于是人就开始变懒。故事的开始,汉斯只是到山上看望表哥,一来他就很反感:哇,你们这儿的人也太懒了吧?活得如此了无生气,整天不是吃饭就是静卧,其他活动几乎都是这两大项目的点缀,这过得都是什么日子啊,太空虚太无聊了!他很不适应,想快点回家,也劝表哥跟他下山,但表哥却说自己还没完全好,并且住在山上对汉斯也有好处,反正也是在度假嘛,就体验一把科学养生好了。
可“魔山”自有它的魔性,刚进来的人虽不适应,甚至是抵触,但他们的心理防线仍会一点一点地崩溃,不是被“将死之人”散发出的负能量影响,而是被及时行乐的快感吞噬,汉斯就是这样从不愿意待在山上、劝表哥下山,到适应并享受疗养生活,而当表哥不愿意无休止养病、打算强行出院时,他甚至成了应该“劝表哥留下”的人,他的冷漠使得来看望他的舅舅不安——但舅舅只是自己被吓跑了,他的意志力只够自己逃跑。
这山上的每个人都有“戏瘾”,都乐于扮演自己的角色,医生执着于让病人无休止地休息、治疗、观察、再观察,看谁谁都有病,看到出院的病人又回来继续疗养总是特别高兴(正常的医生可不会这样),甚至对汉斯说出“你能成为一个比他(指他表哥)更好的病人,我敢担保,我一眼便能断定谁能成为合格的病人”,语气轻松地仿佛在说那只羊的肉质更鲜美,这是一件你情我愿的事情,病人们也是非常入戏,比如汉斯对表哥怀有敬重和爱惜之情并不是因为他是表哥,而是因为他“病得更重”;汉斯还经常添油加醋地夸张自己的病情,以此使自己更受尊重,他甚至会因为体温接近正常而感到羞耻,此外还有无节制饮酒和交媾的病人,那位总是神经兮兮的意大利人一语道破天机:
“他们无一例外地在那里诅咒,实际上呢在此地感觉比在家里还舒服,生活懒散放荡却要求得到同情”,他们是真的病了,但他们享受生病,因为疾病给了他们豁免权,可以尽情堕落而毫无负罪感——可真的会毫无负罪感吗?
当然不,所有病人都对自己入院的周年纪念日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每个人都在极力忘掉它,因为它代表一些负面的东西,包括还未痊愈的身体,包括自己堕落的心,包括不愿意重新开始新生活的那股懒劲,这是他们“良心上的恐惧”。
说到这个份上,这书简直阴暗扭曲得不得了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嗯,主要是没有一下子就吓到人,而是让一个人慢慢地沉浸到懒惰的舒适里,慢慢地让他再也回不到正常生活、变不回正常心理,所有的变化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唯一草率的只有结尾——战争爆发,病人们下山了,汉斯去当兵,生命和故事一起结束,这个结尾收得非常仓促,托马斯·曼也真是奇怪,他可以花一百多页写第一天,用半本书的篇幅写汉斯如何日渐麻痹,却只用一段话就写他从麻痹中醒来,王子把睡美人从梦中唤醒都不止写一段话吧?
但这并不能算是烂尾,节奏再慢的年代,一个人荒废到这地步,重新出来生活恐怕也难免到处碰壁,何况他再没有特别亲近的、能关照到他的人,恰逢战争发生,故事也就此打住吧。
一个干净利落的结局。只有小说才能有的结局,若是在现实世界,这会是一个多么悲惨的结局呢?
《魔山》读后感(四):《魔山》阅读笔记
一、有关长篇小说
阅读长篇小说最错误的打开方式就是关注其长度。在阅读之前就开始焦虑、执着于作品的整体性认知——很多时候,这些所谓整体性认知都是些人云亦云的废话,且和作品没有多少关系。一部文学作品在你阅读之前永远是未完成,长篇小说尤甚。作为读者,你无法改变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故事的结局,但如果没有你心智的参与,它就无法获得意义,你付出的心智越多,其意义就愈深远。
从审美体验来看,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也不是篇幅。短篇小说与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有着更多内在的相似性:一是诗与短篇小说都吁求一种“冰山效应”,即其作者想传递、意味着的,通常都比字面意思所表达出的要多,诗行、叙事都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真正的庞然大物是未现身、不能直接看到的那个;二是对节奏的强调要多过对结构的考量,抒情诗和短篇小说都需要一种掷铁饼般的瞬时爆发力。而长篇小说,无论是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始终无法绕开“人物”这一要素——我的意思不是指人物性格,用“作者塑造人物性格”这种方式尝试去理解很多现代小说将是无效的。我将“人物”这一要素理解为长篇小说的锚,无论长篇小说这艘船舰航行到哪里,它都扮演着一个虚拟的世界之柱或稳定之源般的存在,围绕着它,世界得以展开。但正如船舰要在变动不居的海上航行,围绕人物这一虚拟中心组成作品世界的“结构”,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虚构,传统、精巧的“榫卯结构”固然让人赞叹,但如果一部作品的各个部分、环节、要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产生互动,发生联系,则更引人入胜,而这种产生关系的方式因人而异,由不同读者掌握的信息量、关注点及自身感受力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对作品结构的理解,即便这种结构方式就是作者在构筑其世界时所采用的方法。
二、“水平的”青年成长记
托马斯.曼把汉斯.卡斯托普称为“水平的”人,是“体面意义的平平庸庸”的人,也就是所谓“城市中产”。如果没有“上山”,卡斯托普应该像他的父辈一样,在由“世界贸易和富裕生活构造出的湿乎乎的空气”里,心甘情愿、理所当然和舒舒服服地呼吸吐纳,适宜自如,笃信“出了汉堡,在整个德国便没有人会熨衣服”这样的小市民偏见。
这样一个平凡而普通的青年,却被意外地推向了深渊:无论是实际,还是象征意义上,卡斯托普的旅行都不像“上山”,反而更像向着地狱的极速坠落、滑行,如同那些被从山顶上推下,载着尸体的雪橇。
在疗养院,或地狱冥府,卡斯托普被迫接受挑战:一是他所恪守的“体面”原则在这里失效了。他的隔壁是一対儿放荡的俄罗斯夫妇,在散步路上偶遇的是故意嘲弄他的气胸小团伙,即便是讲究礼仪的进餐时间,也有人把门摔的哐哐直响;二是死亡意识的渗透和压迫。他所住的房子、床位属于前一天刚咽气的美国女人,门外的走廊摆满用于急救的氧气瓶,像搅动体内烂浆糊一样瘆人的咳嗽声——这一切让这位“水平的”人无所适从,甚至深爱的雪茄都变了味道。他曾赖以生活的原则和习惯,在这里土崩瓦解了,他被迫抛弃“水平的”人的角度——所谓“水平的”人的角度,实际上就是没有角度,其看待问题的方式只是和别人,尤其是要和大多数人一样而已。
死亡的暴政之下,一部分人被痛苦压垮了(如“两个都是”女士),一部分人变得不羁而放荡,(如施托尔太太,帕拉范特检查官等等),甚至把病痛、死亡当成一种特权和享受(咳嗽都具有快感)。汉斯.卡斯托普亦沉陷其间,但他的同情心、求知欲,以及对自己、他人所持的开放心态,使得他并未像其他疗养客那样变得冷漠和麻木不仁,甚至还在这深渊里找到了久违的,爱的体验。
但这还不足以使他在此地幸存,作为一名青年,他需要接受教育——“有天赋的青年才不是一张白纸,在他们的纸上,倒像是用悦目的墨水写上了一切,既有对的也有错的;教育者的任务,是对的坚决发扬,错的呢,就通过切实有力的影响予以永远消除”。秉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成为陪伴卡斯托普漫游地狱冥府的维吉尔。这位人文主义者的身世谱系象征了肇始自古希腊,被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所彰显的欧洲人文主义精神。两人亦师亦友,在散步聊天中磨砺思想,探讨问题,俨然现代版本的逍遥学派。另一位精神导师纳夫塔相对赛特姆布里尼,其精神谱系要混乱、复杂、黑暗的多,其中有宗教神学,有马克思主义,有神秘主义,有对超人意志的崇拜,这些看似彼此对立、冲突的主义与观点被他天才般的扭结在了上帝或强力意志对于人类的绝对权威里。两位导师,一位落魄,同时近乎天真的乐观。塞特姆布里尼衣着寒酸、破旧,收入拮据,相比曾在欧洲纵横四海的祖父、父亲,塞特姆布里尼和其秉持的人文主义精神,已经沦落到“只能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吹毛求疵,尖酸刻薄地讽刺讽刺,以美好的乐于行动的人性的名义与之进行抗争,如此而已”(这也是当代人文主义的现实处境),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灰心丧气,反而积极编撰一本旨在消除人类痛苦,然而却注定无法完成的《人类痛苦百科全书》。另一位则虚伪、犀利,惯于以最阴暗的角度看待事物。作为一个没有“故乡和家”(实际和精神上都是)的人,他一边秉持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另一边却无限赞美上帝和宗教领袖们的绝对权力,一边把苦修与禁欲作为个人修行的信条,一边却又沉溺在个人物质生活的享乐之上。他痴迷于牺牲和献身,认为人类在抵达光明之地的过程里,两者必不可少(这套说辞我们并不陌生)。两人彼此争辩的过程,就是汉斯.卡斯托普不断学习,理清思想,形成自己判断力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增进自我的过程,塞特姆布里尼象征着人性中光明、理性的一面,纳夫塔隐喻着阴暗面(两个人被迫住在一幢房子里,算是一种象征),两者从不同方向拓展、丰富着卡斯托普对自我的认知,增长着他的人性。可以说,这是一堂极其生动、卓越的人生哲学课,只是时过境迁,在行动主义者和实用主义当道的今日世界,两位导师都显得迂腐、过时,在罐头加工车间或蚁巢,“民主除去以个人主义修正国家专制主义之外,别无其他含义”(塞特姆布里尼)、“政治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相互提供使对手丢人现眼的机会”(纳夫塔),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几乎等于叛国和背德。
在小说接近结尾时抵达佩佩尔科恩,是一个有着独裁者气质的商人,其含混而破碎的语言,隐喻着意识形态语言的神圣化企图。他的存在给两位导师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争论时,他呼唤天上盘旋的鹰隼的语言,就是吁求于保持缄默的暴力。其魅力在于精心构造的神秘和威严感(既像农夫又像雕像),以及酒神精神——不断挥霍生命力,以狂欢抗争死亡——但最终,在其生命力挥霍殆尽之际,死神以倦怠和虚无将其摄走。
“雪”一节,可以算得上卡斯托普正式出师的标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而在西方文学语境里,雪这一意象,更多和死亡相联系(比如乔伊斯《死者》等等)。《魔山》在这一点上也概莫能外,比如在卡斯托普静卧望着雪中风景之际,死亡以“伴随着似醒非睡的一刹那产生的寒冷之感”渗透进来。漫天的大雪散布出绝对岑寂和虚无的气息,人类施行在自然之上的文明化气息被驱散,大自然变得更为原始、野蛮、狂暴——毫无疑问,这种自然环境所隐喻的,也是人,个体的人,在超脱出构成自我的种种观念、意识、精神之后的超验、虚无的深渊。卡斯托普勇敢的迈进了这一深渊,并通过漫游天堂&地狱的混合构造体,清算了两位导师施加于自身的影响,得到了“爱是死的对头,只有爱,而非理性,能战胜死”。这样的顿悟。与众多读者热捧这一节相反,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一节,因为期间散发着我比较厌恶的,浓郁的弗洛伊德味道。梦境的阐释以及天堂&地狱异形混合构造体的构筑,都让人似曾相识。即便是不考虑弗洛伊德的影响,这些描写与整本小说处处涌现的,不动声色和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手法相比较,也显得太过直白而粗糙。
三、爱情以及其它
与“雪”这种章节比较,我更喜欢比如“关于人体的学问”这种充分展现托马斯 曼小说天赋的章节。这章是卡斯托普给院长贝伦斯设的一个局,目的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接近他的贝雅特丽齐——克拉夫迪娅(只是画像)。卡斯托普非常机智,顾左右而言他,从雪茄、绘画一直聊到人体结构问题,不失体面又得偿所愿的饱览了贝伦斯的画作。这章好就好在那些作为幌子的谈话也并非都是不走心的闲聊,很多内容可以和卡斯托普的心理和感受相呼应,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发乎情,而止乎礼”。除了卡斯托普和一言不发,但始终在场(也许是敏锐地感受到了参观者的注目吧,这裸露的躯体仿佛轻轻抽搐了一下,轻得几乎无从察觉——大胆讲一句:观画者甚至可以嗅到一股汗味)的女主角之外,两个“灯泡”的表现也相当出彩,约阿希姆刻意压抑的激情,贝伦斯话语中阴森的死亡味道。能把这些细微、转瞬即逝的感觉充分表达出来且不失风度,不能不佩服托马斯 曼技艺的精湛和其修养——这种场景和语言,没有一个高度文明化的写作与阅读背景是很难体会到的。
卡斯托普对克拉夫迪娅的感情特别有意思,他爱她,但不是以激情的方式,而是以回忆与理智(这让我不止一次想起柏拉图说的知识乃是回忆)。小说中的爱,更多的是卡斯托普爱的体验。所以卡斯托普暗恋克拉夫迪娅的部分写得极美:(她的眼睛)颜色像远山一般灰蓝灰蓝的或蓝灰蓝灰的,有时在斜睨着并不看什么的时候就会溶解,就会加深,最后会完全化作幽幽的夜幕。但是从那次虐心的表白——不光是两个主人公感觉虐心,读者也感觉相当虐心,很难想象一个男生,向女生表白,即便再语无伦次,也不会大段大段的谈论身体、疾病与爱情的哲学关系,其惨不忍睹的情况堪称一场人为的爱情灾难事故现场。两人交换的照片是X光底片,这又回到了死亡的隐喻,有时候我觉得托马斯 曼过于执拗于爱情→疾病→死亡的关系,反而让很多章节略显乏味。当克拉夫迪娅带着佩佩尔科恩回到疗养院时,卡斯托普的表现相当理性,甚至过于理性而丧失了读者对于他忠心等待的同情和怜悯。正如克拉夫迪娅对他精辟的概括:“狂热意味着:为了生活而生活。可谁都知道:您生活是为了增长见识阅历。狂热即忘记自我。而您呢是要丰富自我”。
最后,不得不说,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手法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陈腐和乏味,比如“7”这个可以让众多批评者们阐释和发掘的象征手法,我即便知道了其隐喻上帝7天造就世界等神话,对我的阅读也并没有多少价值,我对“魔山”的时间感停留在2年,或3年左右,更多的,就文本而言没多少意义(事实上,7年时间中真正起作用的也就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