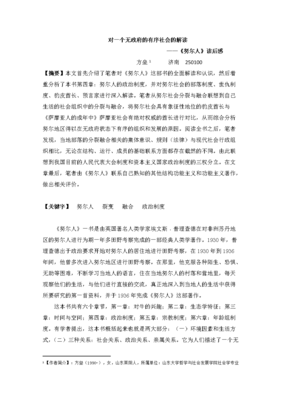
《努尔人》是一本由[英] 埃文思-普里查德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努尔人》精选点评:
●好啰嗦的一本经典
●莫名被萌到了,一群与
●EE普里查德和霍布斯的比较是真心坑爹啊!!!!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大头
●Amazing grace.
●前三章5分,后三章3分(个人偏好毁书不倦……)
●非常好读的人类学观察。很好玩的是,在关于努尔人与牛的很多段落里,把“努尔人”换成“现代人”,“牛”替换为“手机”,读起来也完全成立。生态学和整合经济的存在部分十分有趣。“技术是一种生态学过程”。
●好像真是国内才读这些古老的民族志...收获感觉比读那些新的“乱写”的收获大啊...
●喜欢努尔人的直爽。
●功能派的民族志读起来就是不用太费脑子,然后我的注意力就经常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修辞手法上==
《努尔人》读后感(一):牛背上的民族
对努尔人来说,牛群是家庭生活的重心,连家里的儿子结婚的时候都要参考牛群的数量。男人以自己拥有的公牛之形貌取名(OX-name),女人则以自己为之挤奶的母牛取名(CAW-name)。这样一来,努尔人的族谱听上去像是一个畜栏中的牲口清单……然后生活完全围绕着分牛,挤牛奶,放牛、吃牛奶、吃牛肉、喝牛血、牛器皿、牛骨装饰展开……甚至在牛尿中洗澡……
《努尔人》读后感(二):一些启示
1.牛肉、牛奶需要黍类植物补充,这样的饮食结构决定了半耕种半游牧的生存方式,进而决定了其群体性格。——生活方式决定群体性格。
2.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区分中得以确立,接触的人群越多,范围越广,群体内部相对更加团结,群体的层次越多、复杂程度越高。生活方式、习俗越相似,矛盾越深,而融合的可能性越大、程度越深。
3.酋长、“牛人”、预言家并非由一人承担,权威分散。其中,酋长并没有绝对权力仲裁争端,同时,除了战争时期,不存在高一级单位对低一级单位的绝对统治,法律需要绝对的权力来维护,权力的集中意味着能够迫使人们用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而非诉诸武力,也就意味着行为的收敛。亲人、家庭、宗族是自然而然的最小单位,只有当人们能够广泛接触,身处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中时,人们才能超越尽可能地超越自我,而另一种方式是宗教。
4.政治关系是相对的:a1在于a2对抗的同时作为整体a与b相对的。需要界定最小的单位,同时依据特定情境确定一个关系所在的特定政治层次。
5. P107 “物质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为物质对象是社会关系赖以绕之运作的链条,物质文化越简单,通过它表达出来的关系就越繁多。”
生态时间是人类活动的自然参照物,只因有人类活动它才有意义,而非相反。
因而,可以用这样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以人类生活的社会关系为底色,在此基础上观察一切人类行为。
6.因为,牛的价值的唯一性根本上决定了努尔人的行为方式,而它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其他的猎物和植物能够塑造另外的生活方式,但努尔人并没有竭泽而渔。以牛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选择的结果,人们的行为受客观条件影响,但客观条件却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7.神话是当前政治结构的反映。以宗族的代际追溯时间,继嗣谱系是政治地位的表现,只有有政治地位的人才能进入继嗣谱系。在这样的记录方式中,神话与生活相距的非常近,每一代人非常晚近的过去都成为了神话。
《努尔人》读后感(三):努尔人的时间
(一篇没写完的读书感想。)
埃文思-普里查德,把努尔人的时间观念分成两种: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前一个概念表示人们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说成是通过努尔人的劳作活动体现出来的一种时间表达法,它的最大单位为年。后一个概念与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关,它通过一种特别的制度年龄组来体现。
生态时间:年、大季、小季、月、天、小时
实际上,努尔人对时间的概念,都是与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也大致上可以说是都是通过事件来记住和定义时间的。对于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群体来说,具体事件在人们记忆中的深刻、持久,要远远胜过抽象化的时间名词年、月、季节之类,这是人类的共性。正如心理学者朱建军提议过的:用200字记录一个人30年、50年、80年的经历,你所能记下的就只有几个大的事件,比如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孩子……;凸显出来的只有事件,而不是时间,甚至也不是事件所对应的时间,20岁结婚还是30岁结婚,在这个线索里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
努尔人的一年是由“托特”和“迈”两个大季组成,大季里又可以分出小季。往通俗里说,一次雨季和一次旱季,组成了一年,对应的具体事件就是旱季在营地生活及农耕,雨季去放牧。在中国南方农村里,农民们常常用水稻的两次种收来分出来两个大季,早稻和晚稻组成一年,在这里没有放牧,也就更不存在努尔人的来回搬迁住地的情况。
中国农民对时间的记忆,其实和尼罗河畔的努尔人差不太远。人们回忆村里某个人的死亡、某次械斗、某次印象深刻的事件,往往只能说出来那大约是九月十月份,补充的理由是那时稻子快熟了或者河水干枯这样的带着浓重“生态时间”特征的情形。
努尔人对天的计数更显得笨拙,前天发生的事,他们要准确地表达出“前天”这个时间,则需要借助于中间经过了几次睡觉、挤过几次牛奶等来计算。
尤其要说的是“小时”。在今天的北京,早上上班高峰时去坐地铁,你一定会有印象极其深刻的感受:一,即使你想走慢一点,后面的拥挤也会令你慢不下来,你的行走速度必须和人群整体的平均速度保持在一个不相上下的水准上,那就是小跑着前进;二,人潮,而不是人,人在人潮里只是一个模糊得没有性别、面目、更毋论性情的影子,你是否心事重重、你昨晚睡得好不好、或者你刚刚经历了一个很悲伤的事件、早上做了一次最美妙的爱……等等,都无关紧要。
努尔人没有用来表示小时的概念。其实中国农村里也没有,至少十几年前还不经常使用“小时”这个概念。“清早”时人们去水田里插秧,“太阳初升”时小孩子开始在家里做饭,太阳高过对面的山峰时,在田里劳作的人陆续回家吃早饭,“晌午”时是中饭时间,太阳落山、天还没全黑时是晚饭时间……小时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一切都和太阳、月亮、天色等“自然时钟”相关。
埃文思说,努尔人是幸运的,努尔人没有和时间竞争的情感体验。母亲交代孩子“我在挤牛奶时回来”,男人和女人约定“月亮升起时去村后边”,等等,他们谈到的不是几点钟,更无关于几分几秒,但所指的时间每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一天可能包括牧牛、吃饭、种高粱、挤牛奶、聊天、睡觉……每件事都急不来,“一般来说都具有缓慢从容的特征”。
传说中成都是中国当下最著名的休闲之都,生活节奏最缓慢从容的城市。有没有人类社会学家去研究:在今天这样高速运转的社会里,成都为什么能够让时间慢下来?既要让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跟得上“中国速度”、“全球形势”,又要保持原来的时间态度和生活节奏,个中的秘诀是什么?
《努尔人》读后感(四):阅读笔记
一、研究问题
普理查德为努尔人写了三本书,分别是《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和《努尔人的宗教》,分别呈现和探讨努尔人世界的不同方面。
在《努尔人》的内容简介部分,编者是这样写的:“通过对一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对规范了一代人类学者从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范式提出了一个挑战性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1]我非常同意这段话。
读完本书,感到普理查德始终都在暗暗地地传达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无政府状态下也可以有非常美妙的社会秩序,普理查德称这种状态为“有序的无政府状态。”[2]虽然书中所有的句子都是关于努尔社会的,全是对努尔社会冗长细致的描述和探讨,没有一字一句提到我们所在的现代社会,但读者(比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和对比现代社会,想象如果像努尔人一样没有政府我们的社会会发生什么。
在赵旭东给《努尔人》中译本的再版序言里,他写道:“现代的社会如何建构出一种秩序,曾困扰着像霍布斯这样的现代性之初的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们,他们试图借助外在于社会的力来人造出一种秩序来……我们在读了《努尔人》之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为幽灵的霍布斯依旧存在。霍布斯先生费尽心机为现代由陌生人之间关系所构造出的社会设计出来的理想图式,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看来,显然并非有一种人类的普遍性,而仅可能是由英国的政治哲学家所认为正确的一种社会组织的形态而已。” [3]
看来民族志作品里的普理查德是一个高冷含蓄的人,全书丝毫不提他真正想反驳的那些主流的支配我们生活的理论和社会形式,只是默默呈现着努尔人的社会事实。
那么,在没有政府没有任何中央权威的努尔人社会里,社会到底是怎么组织运转起来的?
二、研究方法
普理查德的田野调查是在1930年到1936年间进行的。由于政治形势以及普理查德身体健康状况的关系,他的田野调查是几个月又几个月、一个营地又一个营地断断续续完成的,他在努尔人中所住的时间总共约有一年。
从普理查德的导论来看,他的田野调查过程艰苦卓绝,特别是在初期阶段。他居住的环境非常恶劣曾使他染上疟疾,因为时政原因不断遭到努尔人的猜疑和抗拒,不但没有翻译而且连完整的语法和词典书都没有。
后来普理查德渐渐融入了努尔人的生活,但他没有说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他只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里的人们开始到我的帐篷里来造访,到这里来抽香烟、甚至开玩笑或者闲聊。”[4]“当我与努尔人关系较为友好、对他们的语言比较熟悉时,他们便不断地来探访我,男人、女人、男孩子,从清晨到深夜,我的帐篷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前来造访的人。”[5]
普理查德收集材料的方法是访谈和直接观察。因为他的调查公开进行着没有任何私密空间,所以他没能培养一个自己的主要报导人,“我不得不对这个人群的日常生活进行直接观察和参与。从我的帐篷的门里 ,我可以看到营地或村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每一时刻都有努尔人在我身旁相陪。”[6]他的信息就是这样零零碎碎地收集起来的。
三、研究结论
本书要探讨的是努尔人的政治制度,普理查德在其中涉及了六个方面,分别是努尔人的生计方式、生态环境、时空观念、部落系统、宗族制度以及年龄组制度。
尽管本书只探讨与政治制度有关的内容,但内容细碎又丰富得像百科全书,很难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要问没有中央权威的努尔人社会是怎样运作的,也许我们可以从努尔人政治制度的特殊之处上来思考。全书来看努尔人的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被普理查德称之为“裂变原则”的那种分裂与融合的趋势。
关于这个原则,在部落系统方面,努尔人的部落分裂为各个裂变支,这些裂变支进一步分裂为二级部落支,二级部落支又分类为三级部落支,村落大多属于三级部落支。在宗族制度方面,一个氏族会裂变为几个最大宗族,最大宗族会裂变为较大宗族,较大宗族裂变为几个较小宗族,较小宗族裂变为最小宗族。
部落系统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主要有:“这种群体不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性社区,还明确肯定了与外敌作战时团结一致的义务,并对群体成员受到伤害时获得补偿的权利予以认可。”[7]氏族或宗族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只有当涉及族外通婚规则,某些仪式性活动以及一种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涉及到对凶杀事件的责任时,人们才需要把宗族看成是完全自治的群体”。[8]部落与氏族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两种系统,部落与地理分布相关,氏族主要与血缘关系相关,尽管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人们的生活在特定村落中首先受部落系统的影响,但同时氏族系统被包含在部落系统中,宗族价值观为部落赋予概念的一致性,村落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一般以亲属制度术语来表达。
裂变原则尽管说起来复杂但并不难理解。假设一个部落分裂为A和B两个部落支,A又分裂为A1和A2两个部落支,B分裂为B1和B2两个部落支,如果A1和A2发生矛盾,他们就是对立关系,但如果A1和B1发生矛盾,在A1无法独自应对形势的时候,A2和A1就会不顾之前的对立而联合起来与B1对立,以此类推。尽管努尔人实际的裂变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而且还有世仇、豹皮酋长等复杂的机制来保持分裂与融合之间的平衡,但部落支与部落支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是按照这种原理对立统一的。
但这种裂变原则就是“有序的无政府状态”的奥秘了吗?就形式来说我们的社会也是裂变的。地域关系上,省市乡镇村一级一级地裂变。血缘关系上,宗族支系家庭一级一级地裂变。我们也不难理解在不久前的农村社会里,两个兄弟发生矛盾时他们是对立关系,但其中一个兄弟如果和另一家人发生矛盾,这两个原本对立的兄弟就会联合起来与这家人对立,如果这两家人属于一个大家族,那么这个大家族与另一个家族对立时,这两个原本对立的家庭就会由对立变为联合。 尽管由于国家的存在这并不是我们的主导行为原则,但这种感情和逻辑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亲近的。那么努尔人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人们联合起来在生活中互助是很自然的,而在这种联合中为什么没有出现领导性的机构或者人物呢?在最后的总结部分,普理查德说:“政治结构的这些趋势或原则通过价值观念而控制着人们之间的实际行为。”[9]而“政治分裂的谱线主要是由生态特点与文化决定的。”[10]这就回到了前三章对自然环境的讨论,最后我找到的可能的答案是:“造成食物缺乏的自然条件以及简单的技术也会造成人口密度低以及居住地分布的稀疏情况。政治内聚力即发展的缺乏可能与人口密度低以及努尔人的分布有关。”而努尔人生活自由强调平等和尊重的文化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
没有想到我读《努尔人》最后会读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
[1](英)普理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译,华夏出版社,2002,P4.
[2] 同上,P7.
[3] 赵旭东,《分与合的政治变奏曲》,《民族学刊》2013年第15期,P34.
[4] (英)普理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译,华夏出版社,2002,P14.
[5] 同上,P16.
[6] 同上,P17.
[7] 同上,P7
[8] 同上,P233.
[9]同上,P206.
[10] 同上,P206.
《努尔人》读后感(五):《努尔人》中的生态人类学观
一、作者介绍
本书,即《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是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成名之作。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大概是他那一辈人中最有雄心的人类学家了,在1924年或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之前,他就开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成为马凌诺夫斯基最早的两个学生之一,1927年,他获得该学院的博士学位。[1]他虽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但1935年,他在牛津大学初识有着结构功能论人类学鼻祖之称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从此便转向了法国学派的理论表述。[2]因此,他后来的著作大部分都是一些理论性的作品,内容多是关注于人类学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的关系。而由作者的经历可知,作者兼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二者的影响。这一影响与学术传统,在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内容介绍
在该书中,埃文斯-普理查德所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中央权力的社会中,是如何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的。该问题的提出是有着历史性的大背景的。当时正值一战结束,被誉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欧洲被战火摧残,而与相应地,西方学者的自信心也遭受了打击。西方社会,是否是最好的社会?这一问题被提上了章程。而与其他的学者一样,埃文斯-普理查德企图从非洲的无政府的部落来进行讨论,认为即便是该部落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精细严谨的政府组织形式,但是其依旧是自我运行良好的社会。
书中所提出来的核心概念,既是所谓的裂变的社会组织原则形式。这种裂变制又恰恰是建立在一种“世系群体系”(lineage system)的分分合合的动态平衡的基础之上,这些便构成了努尔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让我们有机会反省我们的制度存在的非原初性和非唯一性。[3]
至于在本书中的生态人类学观念,在书中集中表现为第二章生态系统中。在该部分,作者描述了努尔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即(1)它是绝对平坦的;(2)它是粘土性土壤;(3)覆有稀疏、纤细的丛林;(4)在雨季里,这里布满高高的杂草;(5)这里常常遭受大雨袭击;(6)这里横穿着一些一年一次洪水的大河流;(7)在雨季结束,河流水位下降之际,这里又常常遭受严重的干旱。[4]由此可见,努尔人所生活地区的生态环境,大致可以分为雨季和旱季这主要的两个部分。而由于雨季和旱季这两个部分的生态环境的不同,使得他们不得不随着季节性的变化而在该地区的高山和草地之间进行着往返的迁移。正是这种迁移模式,使得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会随着积极性的变化而进行集中与分散,形成了他们的独特的又分散又联合的这样一种,看似是矛盾的,其实是合理的社会制度。
而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除了制约努尔人的社会制度之外,对努尔人的饮食结构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点应用于努尔人身上则是一点都不为过分。在一年的周期中,努尔人随着季节性地变迁而改变自己的食谱。具体来说,在每年的2月至5月,即干旱的时期,努尔人主要以鱼类为食,辅之以牛奶,而谷物和肉类则非常少见。与此相对应的是每年的6月至8月这一段湿润的时期,努尔人则以谷物和肉类为主要的事物,而鱼类则是很少见的。食物供应在全年中的变化以及它们在各个季节是否满足生活所需,是由生态变化的周期所决定的。[5]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对于努尔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这种食物性的变化,使得努尔人有食物充裕期和食物短缺期。这两个阶段造就了某些社会制度。例如说,庆典仪式往往都是举行在食物丰裕期的。高粱充裕是努尔人在雨季里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没有粥和啤酒的话,这种庆典的仪式便很少会完整,而且,由于这种仪式是由献祭组成的,因而也就需要用肉来构成。[6]这便不由得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作了注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挤出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1883)”。
随后,作者又从生态的观念入手,对于努尔人的物质生活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论述。作者认为,物质文化可被视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为物质客体是社会关系赖以运行的链条,物质文化越简单,通过它所表达出来的关系就越多。[7]而物质文化的水平,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态环境所决定的。
最终,作者总结了以下生态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第一,生态环境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第二,努尔人的混合性的经济之所以是必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生态平衡后的结果。第三,努尔人所处的这种生态性的特征给混合经济更有利于牧牛业的一种偏向性。第四,这种干湿性的季节生态电话,使得努尔人不好得以定距,而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性的迁移放牧。第五,严峻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是一种缺乏食物、低水平技术和缺乏贸易的社会,这种社会使得群体成员们不得不相互依赖,并形成一种经济集团,而这种互相依赖的经济性关系,迫使他们形成一种政治性的俗例。第六,季节性的迁移强化了村落政治的重要性。
总之,正是建立在这一章,即努尔人的生态环境的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才会进一步去解读努尔人独特的裂变机制。
三、评价反思
在这本书中,我们所看到的无疑是一种生态决定性的观点。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方式,而其所经营的那种以牧牛为主,同时伴以捕鱼和园艺的混合经济方式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8]由于食物的缺乏而使得努尔人形成较小的,互相依赖的经济共同柜体,相同的条件和畜牧生活则使得在远远大于村落的区域内生活着的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些都是由生态所决定的。
虽然在学术界中,系统的生态人类学的提出,远远在埃文斯-普理查德之后,然而,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所看到的便具有了先见性。
生态环境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其他社会条件之下,也是比较显见的。例如说,就曾经有学者将中国的政治文化归纳于一种“大陆文化”,而与之对应的,西方的政治文化归纳于一种“海洋文化”。在前者中,由于大陆的内深性和开阔性,使得中央政府得以早早建立,而要想在开阔的大陆中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就必须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政府。因此在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才会如此发达。与之对应的是,在后者的海洋文化中,由于海洋将岛屿隔开,各个岛屿各自为政,因此,中央的政府的力量,显然没有太大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的,便是以希腊为典型代表的城邦式的民主制,这种制度,经由欧洲带去美国,从而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的民主思想。
但是,生态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吗?这一点,或许需要更多的论证来进行解释说明。
[1]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2]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2017年,第ⅲ-ⅳ页。
[3]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2017年,第ⅷ页。
[4] 王铭铭主编:《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5]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2017年,第116页。
[6]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2017年,第128页。
[7]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褚建芳译,2017年,第128页。
[8] 王铭铭主编:《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