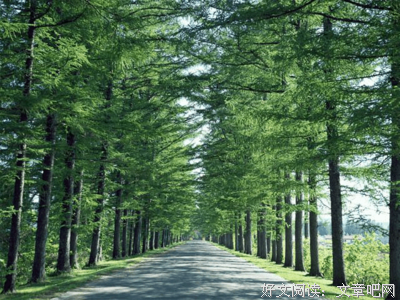
《植物之美》是一本由让-玛丽•佩尔特著作,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植物之美》精选点评:
●图是凑的
●图片很美。对一个理科盲来说还是有点太专业了= =
●没看完 随时看
●与《野兽之美》相比较,科普味道少了点,倒更像摄影作品集。不过挺赏心悦目的
●图片很震撼,可惜不会法文,翻译得太烂
●只翻完了图片,文字却不怎么读得下去。里面很多图片非常熟悉,有一些并且多年前扫描保存了下来。怀疑很久以前曾经就翻过这样一本书。虽然这个版本是第一次见
●4年前读过的,已经忘记了
●插图很喜欢
●闲书一本,案头消遣
●自然从来都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植物之美》读后感(一):植物的人文之美
书名中的美是一种抽象的美(所以不要被名字欺骗了)。书分三个部分介绍了植物起源与发展进程、人类驯化作物(包括玫瑰)的漫长历史、植物生存发展的现况以及未来。个人认为翻译翻的不是很清楚,但插画绝对是亮点,虽然很多插图与正文内容关联不大但是其中有许多出色的摄影作品和古典油画,并且编辑也找到一些古典油画中与植物的关联,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这些名作,这些也赋予这本书以人文气息和历史沉淀。
《植物之美》读后感(二):几点小感触
1,好的译本总是凤毛麟角吧,翻译过来的文字读起来感觉总是怪怪的,很有点像学校南北楼两边阶梯教室的台阶,走一步太窄、走两步又太宽,牵绊得很;
2,书名是《植物之美》,不过侧重点其实是在于副标题“生命源流的重新审视”,就像书中结尾处的一句话,“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同一事物,而且是惟一的事物——生命的两个方面”,追本溯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实应该是永远关注的焦点。
3,似乎很难不提书中的插图,除却极少数插图与书中内容的联系有太过发散之嫌外,这本书的最亮点无疑是众多美轮美奂的图案。
《植物之美》读后感(三):总有那么多美丽超乎想像
太阳转了一圈,从南窗到北窗。QQ群里有公告:据说大暑之后,大热15天。请准备好冰淇淋若干绿豆汤若干空调间里的心情若干。
此刻,太阳走了。余温像彗星的尾巴。
清晨到黄昏,12个小时的时间,2小时奉献给了进餐,2小时奉献给了午睡,1小时奉献给了习惯性地将书桌东抹西擦,还有1小时,奉献给了翻箱倒柜。《植物之美》躺在角落里睡大觉。我说你醒醒吧。太阳已经下山了。
可此时此刻,我深恶痛绝自己的无知和贫乏。这种痛恨,转换成芒针,一下一下戳进我开放的毛管。
哦,对。出口。行走时若看着前方,那么必然错过脚下的每一步。若痴迷于脚尖到脚跟的动作和幅度,那必然又错过前方。我们的一双眼睛,无法在看着挥霍的同时,再看着无辜。我若封闭了所有给予在动物身上的念想,包括人类,那似乎就多一分对于植物的亲近。
曾被挥霍过的岁月,曾被无视过的绿野,曾无缘走近的远,曾在慌乱错落中丢失的迷恋。
我只在自己,丢弃繁华的时候迷恋自然。我只在刹那有看见真心的时候,丢弃繁华。我只在弃绝了功利物质金钱地位的时刻,刹那看见真心。
去净寺焚香。净寺门口硕大的樟树,鸽子肥壮,姿势嚣张。我喂它们吃石榴,它们籽都不吐。寺里钟声响起,它们哗啦啦飞。数十米高的佛殿,瞬间就被它们穿越。它们入了净土,而我依旧在这边。
我以喂饲鸽子的心态喂饲自己。以自然的姿态。不,是倒过来。自然喂饲我,当我路过的时候。
《植物之美》,我说不出。
只知道,有时候我眼里看见的只是一种。千万种的一个侧面。它们葳蕤多姿,而我顽固地贫乏至今。每每面对自然,我总是羞愧。自开天辟地,自有生命以来,是植物支撑和喂养了动物。若再多知晓一点,知晓一些植物的智慧,植物的心灵,植物的美,就如此书所绘述的那般,那么我在下楼的时候,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再看见迎面那一排排低矮的冬青,眼神必会有所不同。
为什么读书?是为了感动,且不至麻木。
2007-08-02 18:55:02
《植物之美》读后感(四):生命的坚韧、美丽与庄严
生命的坚韧、美丽与庄严
——《植物之美》读记
多年前,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异”人研制了一台可以接收植物声音的仪器,只要他戴上无线耳机,就能够不断听到植物发出的声音。发明带来的结果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恐惧——在和风细雨、凄风苦雨、阳光灿烂、冰封雪盖中,刈草机的切割、斧头的砍伐、锯刨的酷刑下,花草树木发出频率分贝情感色彩不同的嘤哼歌唱细语呻吟乃至叫人神经颤栗的哭嚎!作品结尾是发明者由于无法忍受植物凄苦的声音而毁弃了自己苦心孤诣的发明。
作者的用心不言而喻。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以人类为万物主宰的世界上,植物似乎属于诸生命系统中最低的品类/等级,自有文明以来,有谁在关注倾听过植物发出的声音?或者说,有谁会认为植物会有自己的声音(科学认为植物没有中枢神经,因而没有思维,更没有智慧——某些科学家也承认植物可能有自己相互联系的秘密方式,但这同我说的“声音”并非一回事)?就连世界宗教中对生命最具博爱悲悯之心的佛教也认为植物没有第七第八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因而不能与其它生命等量齐观。人们伐取粗细质地不一的木头筑居、铺路、搭桥、造船、舀纸、烧炭、煮食,利用曲尽其妙的藤蔓花草点缀、酿造、烹饪、萃取、编织,依靠谷类、薯类、蔬菜、水果、油料作物、棉花、烟草等各色农作物提供的养料维生享受,它们排放的废气——氧,更为人类的生存须臾不可缺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从未重视/正视过它们(即将其看作是和动物界平等的生命。近数十年来似乎正在出现的“重视”倾向,其出发点不过是缘于人类生存的危机,因而依然是人本位的),究其实反而是在虐待、残害、毁灭它们!如果自人以外的生命的角度看,人类乃是它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最恐怖最致命的灾难,因为只有人类才具备破坏毁灭整个地球生命生态(当然也包括动物界与人类自身)的能力。
《植物之美》的体例系时下流行的“访谈录”形式,访谈对象都是法国生物学界的“大腕”级人物:让-玛丽•佩尔特,梅斯大学生物学、生药学名誉教授,欧洲生态研究所所长;马塞尔•马祖瓦耶,法国国立农艺学院教授,曾在二十多个国家从事农业发展工作; 泰奥多尔•莫诺,沙漠研究者,研究范围横跨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诸多学科,兼任国内外多家研究所、科学院的研究员;访问者雅克•吉拉尔东估计也非等闲之辈,因这一类“访谈”局外人根本不可能胜任。
对我这样的“科盲”(虽然也喜欢读点科学家传记、科普科幻)而言,几度阅读此书的过程是不时发出“是这样吗?”、“原来如此!”、“太奇妙了,简直不可思议!”的惊叹乃至震撼莫名的过程。除了自己由于对相关领域所知太少显露出的无知外,教育自身的狭隘贫乏老化恐怕是更根本的原因。几天前,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有关高考复习的节目——教师面对“祖国花朵”,神态庄严地念叨着一些诸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客观规律可循”或者“相对绝对”、“共性个性”、“量变质变”之类的蠢话与大词。“园丁”真理在手的自得让我不由悲从中来:几十年间,若干代人,你我他她,到底被灌输了多少这类的“政治正确”的“知识”?比较而言,人文科学领域灾难深重首当其冲,自然科学或可能稍好一点,但仍旧问题多多。比如某些“经典”的学说、理论、假说,事实是它们在几十数百年以来已经遭到了反复地拷问、质疑、批判、完善,有的已经接近重写或作了重大修正,但在我们这里却依然故我,光芒丝毫未减。实事求是地讲,某些伪“知识”的普及传授造成的恰恰是一种“集体性蒙昧”!更为严重的是,老化过时的知识可以置换更新,而一个人从幼至长的身心发育成长过程中浸润颐养积累形成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则很难转换和改变。
正是基于此,作为一个深受僵化教育之害的曾经的受教育者与远不够格的读者,在为自己对一些基本常识的无知乃至把谬误当真知而感到汗颜的同时,由衷地惊异于“访谈”以明晰的思路、鲜活的色彩、感性的表达方式、举重若轻娓娓道来的语调所勾勒出的一幅生命——当然主要是植物生命的诞生、发展、消失、重生、改变的历史长卷:
“嘭!这是宇宙!然后是我们的太阳及其卫星。经过10亿个可怕的年头……大地变冷,火山活动减少,灰蒙蒙的浓厚气雾使陨星的轰击渐渐停止。古怪而下等的创造物——我们的祖先,在当时覆盖地球的阴暗的水里出生。”
在所谓的生物界,实际上可以说存在着病毒世界、细菌世界、蕈类世界、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有人认为还应该将人类单独划分出来,因为这个最后出现的动物跟其他动物相比,差距实在太大),前三者都既非植物也非动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生命最初只存在于植物界。生物世界是植物世界繁衍了20多亿年以后的产物。植物是地球生命的始祖!”(在此意义上讲,“人是猴子的后裔,而猴子又是树木的后裔”的表述虽然太过夸张,却并非一句彻头彻尾的玩笑)
4.3亿年前,因气候干涸,海水消退,生命(绿藻/蓝藻类等)被囚禁在水潭、环礁湖和沼泽里面,适应环境的绿藻类幸存了下来。1000万年后,绿藻征服了陆地,这时出现了人们发现于爱尔兰的最早的木本植物——发达植物的始祖Cooksonia(实际上它个子矮小,没有叶子,像一棵5厘米高的灯心草)。
3.6亿年前,真正的植物问世,地球披上了绿荫:
“那是在恐龙出现前约一亿年……树林里没有小鸟,因为它们还不存在;没有采蜜的昆虫,因为花还没有创造出来;也没有蝴蝶和蜜蜂……还听不到我们所熟悉的嗡嗡声和习以为常的歌声、叫声。除了风的飒飒,地球一派寂静。”
进入二迭纪,气温骤降,物种大量消失,荒漠增加,前述适应炎热潮湿气候和沼泽生活的植物全都灭绝了……可正是类似灾难引起了球果植物的第二次变革,即发明了种子——脱水干燥后生命力处于减缓状态的胚珠(某些种子可以在恶劣环境下存留难以置信的久远岁月)的繁殖方式——这是大约2.8亿年前,石炭纪行将结束时。
“后来,在1.5亿年前,侏罗纪开始,气候更炎热、更潮湿……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球果植物森林,其种类之繁多远远超过我们所了解的球果植物。”这时,“某些爬行动物会飞了,变成了鸟……在森林里,绿色不再是唯一的颜色,声音也不仅仅是单调的风声。”
最终到了距今约1亿年的白垩纪,“花儿在热带地区绽开了,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地球,成为景观中的主色调”,种子植物应运而生(植物创造了种子,这同时有力地推进了它们与动物世界的联系,即由原来主要依靠风传送花粉和种子现在主要依靠昆虫和鸟类传送)再往后,开始于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期突然将繁茂的热带风光搅得乱七八糟——天寒地冻之时,树木只能排出而不能吸收水分,所以失水而死。于是它们创造了在一年里最寒冷的时期大量落叶的生存招数。用雅克•吉拉尔东生动的说法就是“树木在近二万年前创造了秋天。”
一万年前,人类创造了农业(此前他们靠狩猎、采摘度过了数千年),这是植物与生物发展史上一个极重大的事件(马塞尔•马祖瓦耶称之为“一场革命”)。某些植物象某些动物那样被驯化——植物世界不再都是野生的了。
这浓缩的一幕幕“拉洋片”式的场景当然称不上逼真再现,而只是约而言之,大而话之:“人们只不过是想象而已,我们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从掌握的信息出发,重新创立一种推理方式。在科学上,这就叫做理论。”(让-玛丽•佩尔特)
正如雅克•吉拉尔东所述,人类对植物(自然界)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他们创造了新的生态因素,改变了一切植物生长的条件,种子被移植到仅仅依靠鸟儿、昆虫和风远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运输工具的发展和生物流动速度的加快造成了植物不定位的大奇观,这种力量差不多可以与决定植物在地球上分布的气候大变迁相比。然而在另一方面,人类的行为确实又给植物(自然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由于有了农业,人,能够迅速增长。由于人口增长,森林被开垦,作物被推广,整个地球被占领……有人为了放牧几头牛,烧毁了富饶的热带森林,有人对杂草进行化学战,有人对水果和蔬菜添加兴奋剂……”
农/工业的疯狂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剧烈破坏导致了气候恶变,物种大量消失(动物的危机实际上比植物更甚,因为它们更为脆弱),所有这些已经关涉到整个地球生态/生命系统的安危存亡。
以化肥、除草剂、杀虫剂、机械的大量使用为标志,现代农业实际上已成为一门工业。被逐步筛选、改良的植物甚至已达到与原生种类毫无相同点的地步,其命运与力图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它的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到现代遗传学与遗传学家的出现,不仅只是使传统意义上的植物学与农学显得“过气”,植物学家农学家逐渐被遗忘,更为可怕的是将生物推向了“重组”的命运——随着一幅幅生物基因图的绘制成功,说我们这个星球尤其是其间的生命正处于千古所未曾经之大变局,一点也不算危言耸听(“植物世界被夹在城市化和荒漠化之间,被夹在物种灭绝和遗传实验之间,它的未来看来可能是暗淡的”)。可以推断,今后植物(当然也包括动物)命运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行为,而自然的法则会被市场乃至政治的法则取代——比如为了追逐利润/权力而使用“种子武器”、“食品武器”、“基因武器”等等。
这本“访谈”包括“野生植物历险记”、“人类入侵”、“大自然的未来”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与“法国现代真正的植物学家之一”让-玛丽•佩尔特的访谈)占据了全书篇幅的差不多二分之一,这部分内容也正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不必讳言,缘于各自专业立场(卖什么吆喝什么)、哲学观念、人文取向的不同,植物学家、“资深沙漠旅行家”与农学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以对现代文明背景下地球生态/植物世界的明天的预测为例,农学家偏于乐观,而前两者出言则谨慎低调,更多焦虑与忧患。在谈到物种的消失/诞生时,让-玛丽•佩尔特告诫道:对于野生世界,必须懂得,植物消失的速度远比新植物诞生的速度要快得多,就象“石油、天然气、煤经过了一亿多年才形成……目前,我们正在将这些气体用三至四个世纪释放到大气中!”这张资产负债表明显是消极的。马塞尔•马祖瓦耶却认为没有必要太过夸张,因为目前的森林还覆盖着26%的陆地(其中发达国家有1400万平方公里,第三世界有1700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1600万平方公里或多或少种植树木的林地),形势还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但是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森林不再以每年15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不过在更多的问题上(比如一个以金钱为基础、将竞争作为唯一法则的社会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效应),他们仍然具有相当一致的认识:
“沙漠是地球周围空气团流动的产物。但是很明显,人轻率地开垦,或在脆弱的土地上过度的放牧,也常常使形势变得严重。”(泰奥多尔•莫诺)
“至于转基因食物,有人正试图把它强加于人。这无疑是些多产的新植物,但是,它们也可能是危险的。它们现在在这儿可以获得收益,而其他植物会在明天的其他地方为此付出代价。”(马塞尔•马祖瓦耶)
“生物多样性对于生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刻,存在着突出的两极:尖端技术和大自然。问题是:如何实现两极的协同作用?”“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生存是同一个事物,而且是唯一的事物——生命的两个方面。”(让-玛丽•佩尔特)
自然界及活跃其中的众多生命博大精微,充满了不可穷尽的神奇与奥妙。仅以植物为例,从蓝藻类到转基因玉米,由于缺乏一个具体可感的参照系,其演进的宏观跨度的巨大无论是空间抑或时间都是人类的感官尺度所难以度量和想象的。为了使人们对地球年龄、植物生命、动物生命、人类的生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理解,就象卡尔•萨根在《伊甸园的飞龙》那本书里所做的那样,雅克•吉拉尔东也借用了一种传统而又合乎教育原理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将各个地质时期和无法设想的数十亿年拉回到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既然我们正处在世纪之末,那就假定45亿年(地球的年龄)等于100年,把地球算作是1900年1月1日出生……如果保持时间的同一比例,那么,生命起源于1923年。那时已有植物生命,当然是十分原始的。最初的单细胞藻类只是在很久之后才拥有了细胞核,即1986年。 1991年,植物第一次离开大海,适应坚硬的土地。那时,植物的进化加快:从1994年起球果植物开始生长。1996年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1998年继而出现了种子植物。最早的类人猿踪迹始于1999年7月,现代人时代始于6个月之后,即12月31日傍晚。同日宵夜,1999年12月31日22时4分,即现时的午夜钟声敲响12下前1小时56分,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了农业。”
由此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植物生命存在的历史远早于动物生命(更别说人类的生命)。如果将植物生命与动物/人类生命相比照,不管是从进化的绝对年龄还是从适应抵御生存环境的变异乃至灾变上讲,后者都无法同前者相提并论。书中有几个细小然而却是雄辩的例子,它足以说明植物生命具有何等的韧性与顽强:在长期无雨,似乎是生命禁区的撒哈拉沙漠里,居然普查出了800种植物(其中有一些种子——有的是被风刮来的——它们仍然在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等待偶尔的一场小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通布图有一种黄细心属的小植物,它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是在八天时间里完成的,然后,其种子开始耐心等待第二年的那场雨——一年的等待,为了八天的生命。不知别人会怎么看,以我的感觉,似这等默无声息的悲壮,微渺到难于被觉察的伟大,是可以被视作惊天地泣鬼神的,它昭示的是生命的坚韧、美丽、自尊与庄严。
的确,植物世界远比动物世界更能繁衍生存,正如边芹女士在《序》中所写:“我们最多一百年的生命,与寿命达几千年、几百年的植物,不可同日而语。加利福尼亚松树活了将近五千年;最新发现的羽扁豆种子已有一万年的历史,居然发了芽;而铃兰几乎是永生的。它们才是地球历史的真正的见证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人类愈演愈烈的野蛮暴虐、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毁坏背景下对植物世界的生存葆有几分耐心与信心——让-玛丽•佩尔特说,孩子们本能地被大自然吸引的方式表明,大自然铭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同一个事物,而且是唯一的事物——生命的两个方面。泰尔奥多•莫诺说,幸好消灭植物世界并非易事,让大自然消失甚至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植物之美》([法]让—玛丽•佩尔特等著 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