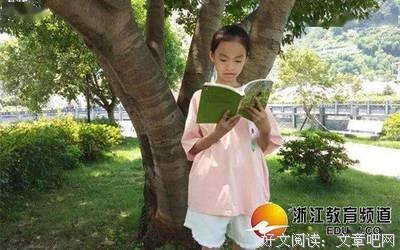
《人树》是一本由[澳大利亚] 帕特里克·怀特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1.10元,页数:7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树》精选点评:
●我喜欢里面能够默默忍受的男人,也许,这就是我身上所或缺的吧。
●人如树般生存,繁衍,壮大,销声匿迹,斯坦是一棵默默生长的太阳花,艾米是缠绕的藤蔓,守住了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生长,生根发芽,走出了森林却永远走不出阳光的微笑,此消彼长,永无止境
●不是我熟悉的表达方式,但在现阶段很适合我,把我拉回到只有自然意向的世界里,很好。
●工蚁的一生
●前半部分奇幻,后半部分家庭
●没有特别的感受,有点平淡。情节不吸引人,内涵上也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
●断断续续还没看完呢
●很不错,值得一看
●挺喜欢这种叙事方式。环境描写太赞。
●大学时代读过这本书,大概在九十年中期。这本书是我记忆中读过最有深刻印象的,书中对自然的描写,人心的描写非常的细节化和深刻。
《人树》读后感(一):曾经的感动
这是我在大学时读的作品。
那时,几乎不愿意错过每一位诺奖得主的作品。
很厚的一本书。
很美好的回忆与感受。
这是我工作后收藏的第一本书。
那时,经济拮据,但还是把它收入囊中。
很沉的一本书。
某些午后,我总愿意手捧着它,翻开发黄的书页,每一页,都值得回味。
我很喜欢最后一章,不多的几千字,我读了不知多少遍。
《人树》读后感(二):真是一本考验人的耐性的一本书
帕特里克·怀特的文笔细腻到让人发指的地步,之前知道这本书是因为看了一个小八卦,说这本书的俄文版译者因为翻译这本书得了神经衰弱症,后来又看到一个八卦,说大名鼎鼎的金立群和他的女儿因为要修身养性要翻译这本书,只是没翻译完。完全处于好奇的原因在孔夫子上买了一本二手书,想了解下这本书到底是何方神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完全进入了一个世界,毕竟,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没有读完一本这么厚的小说啦(上海译文版,1997年,700页),也许现在读这本书的出发点也是出于修身养性的功利诉求,总之,读着读着就进去了。
完全是一本描述普通人的书,从蛮荒之地成为悉尼的郊区,帕克经历了他自己的修炼过程,虽然书中着墨比较多的更多的是他身边的景物的改变和人物的改变,包括他的妻子、女儿、牛、狗、树.......但是帕克的主角地位却一点也没有因为这些描述而显得轻,这真是作者的一种深厚功力啊,就像金庸老先生的书 碧血剑一样,或者应该说金庸老先生的碧血剑像这本书,主角没出现,但是统摄整本书的灵魂的就是那个帕克,一个沉默的,说不上聪明的人。
读这本书首先得需要耐心,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作为澳洲小说家的杰出代表,这本书在1972年或者73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本身对某种文学传统的继承,还有那种炉火纯青的驾驭能力,让人生在周围事务的映衬下显得那么超然,这种超然或许是我们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的所谓现代人需要的,本身内心需要的。
那种看起来比较冗长的描述,没有一句俏皮话,完全地让人在里面变成了一个修炼内心的过程,说这本书枯燥也罢,无聊也罢,但是里面描述得所谓的 生命的意义和过程都却那么真实,大地成了这本书最好的注释,所有在大地上的事物成了见证生命的意义,这个阐述过程令人信服、佩服。
习惯喧嚣之后,也许我们需要过于喧嚣的孤独。
《人树》读后感(三):历史
我常常觉得时间就像一柱香,缓慢炒成灰烬,然后就消散了,永恒地消失,再也寻不见。这大概是因为不存在“时间”这种东西。康德在《纯粹理性》中也提到,很多categories不过是我们心灵所赋予自然的罢了,实际上并无这样对象的真实存在。一切都会随时间而逝去。所谓时间,不过是世界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一种状态的演变所呈现的一种现象罢了。要是如此的话,一个人在其中短暂的存在,又是有什么意义?
怀特书中的人物,从第一代到第三代,都没有考虑过生命的意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人并不需要考虑人生的目的或意义这类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考虑,虽然按Tinder的说法能够让你超越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会产生Sandel所说的你和日常经验的疏离。人类智能之所以能够远远走在其他动物前面,或许正是因为人有这种通过观念、想法来理解生活和世界的能力。但是,通常这种能力仅仅被用于解决技术性问题,即所谓的工具理性。但是人的这种智能也存在一种跑偏的可能,毕竟智能本来也是在自然选择之中被用于生存繁殖的目的。可以看到,在一些把自己的(天赋)智能用到出类拔萃程度的人们,往往在自然意义上是失败的,且不说哲学家艺术家单身未育或自杀的比例很高,甚至在受过高等教育、高智商的群体中生育的比例也相比底层人低。但是,在怀特的笔下,帕克和艾米却都有这种跑偏的冲动。只不过,作为一种没有接受到人类集体智慧熏陶的二人来说,这种冲动只是一种朦胧的诡异的感觉,不同于消除不快和追求快活的人所共有的基础冲动。帕克只是读过一点莎士比亚,而艾米什么都没接触过,甚至一直生活在与人类文化隔绝的小世界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只能靠自己来拓荒。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文化的荒原上,帕克、艾米和他们的后代,精神上都是一种自生自灭式的成长,父母对子女的这种parenting方式,安妮特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把这种叫natural growth,或许和人们口中的“放养”稍有不同。帕克的父母和帕克很少有交流。帕克的母亲看起来自己精神上都孱弱得需保姆。所以帕克不仅和艾米很少交流,帕克和他的两个孩子也很少交流。艾米自己也是有人生没人养得长大。二人对于孩子的成长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指导,他们也没有能力教导。帕克只能努力找点话和儿子能够说上几句,而艾米对于雷要么放纵要么哀求。这也导致了雷后来的行为不端和死亡。人们在谈到平等的时候,到现在,逐渐意识到生活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拥有不同的资源,起跑线不同,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拥有不同的父母,给孩子不同品质的人格塑造,也是造成不平等的重大因素之一。
《人树》读后感(四):工蚁的一生
《人树》2009年买的,但一直未读,后来搬宿舍,书就一直放在50多个大箱子中的一个里,想翻也很难翻出来读,最近读的这一本是豆友“乱看书”转让的,见乱看书的相册-乱看乱散(低价),见他卖得很便宜,就买了下来,花了三四个晚上读完。
主人公斯坦·帕克像只强壮、勤奋的工蚁,劳劳碌碌,平淡无奇度过了一生,像设定的程序一般履行着自己的人生职责。洪水来了,他参与救灾;战争来了,他去战斗;火灾发生,他去救人,平常的日子按部就班,种庄稼、修篱笆、喂奶牛、挤牛奶。然而别人很少了解他真正在想些什么,他内心需要些什么,他很少向别人袒露心声,他完全将自己内心世界封闭起来。他也有过柔情,有过欲望喷发的时刻——对于妻子、对于他的孩子们,然而,他往往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浑身的力气无处使或者一拳打在空气中。斯坦·帕克还让我想起了乌鲁鲁(Uluru)石,一样突兀,一样坚硬,内心的脆弱、柔暖隐藏在粗矿的外表里,他也小心翼翼的掩藏着这部分自己,生怕别人一旦发现会揪住不放,那就不再是自己了。他与妻子艾丽的婚姻,只能说是相互的需要,与孩子们的关系也只是靠血缘维系,很少有温情,他不懂得如何与孩子相处,和他们说些什么,于是放任孩子自己成长,也许与他当兵打仗的几年有关,也许与他本身的性情有关,当他想要告诉儿子某些东西,却发现已经过了那个时候,孩子已经与他疏离了。然而他的内心追逐着什么—— “男人等待这场暴风雨的时候,一双手懒洋洋地抚摩着自己那松弛的身体。这身上的力气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于是他变得烦躁不安,如坐针毡。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身上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因此,他虽然有力气,但又是无力的。他像山顶上细碎的电火一样,闪闪烁烁,明灭不定。”
斯坦·帕克的人生更像是在履行道义上的责任,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公民等等。他很少与人交流,更很少有真情流露,他更愿意找个无人的所在或者陌生的地方暗自发泄一通,然后回家照旧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说也奇怪,书中斯坦帕克的高潮出现在他证实妻子给他戴绿帽后有点失控的时候,他理解邮政局长的丈夫,但他不会像他一样去死。那位自己吊死的邮政局长的丈夫,人人都以为他是个懦夫,靠着妻子生活,书中也没啥镜头给他,多半是他妻子的讲述。他死的的时候,留下一堆画,画面给人强大的冲击感,其中有一副让人觉得羞耻——一位光溜溜的淫荡的女人,让艾米从中看到了自己。他死的时候,妻子将他的画贬得一文不值,仿佛是一些累赘,并为此感到羞耻,我们仿佛也可以看到这位郁郁不得志的丈夫,活在老婆的阴影下,头上戴着高高的绿帽子,所以斯坦发现自己头上也戴着顶绿帽时,他理解了这位丈夫为何去死。讽刺的是那些画如那些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死后却大放异彩的画家的画作一样最终让他的老婆发了财,更讽刺的是那位邮政局长最终留下的那幅期初让她觉得羞耻的偷汉的女人的画作——也许那正是她自己,她却丝毫不觉。是的,我们的生活也常常出现某位道德的评判家,道德那只是别人的生活准则,他们往往脱身于道德之外,不管他们自己有多么龌蹉,那都是无关紧要的。
故事以斯坦的死作为结束,我们的人生都会以死作为终结,我们劳劳碌碌的一生到头来是一场无,什么也没有。也许这也是我们许多人平平凡凡的一生。我们的内心却得不到满足,我们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来肯定自己,来给自己的一生下一个定语。不平凡的人甘于平凡是一场悲剧,平凡的人不甘于平凡则是另一场悲剧。当然,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何苦于执着地想要创造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过得安心快乐就好了。
《人树》读后感(五):时间这样过去就很好。
quot;When we came to live in Castle Hill, Sydney,I felt the life was, on the surface, so dreary, ugly, monotonous, there must be a poetry hidden in it to give it a purpose, and so I set out to discover that secret core, and The Tree of Man emerged."
“在生活单调沉闷、沆瀣丛生的表象之下,一定存在某种诗意的目的,我下定决心要追寻并找出那个秘密核心,由此,《人树》最终呈现在诸位面前。”
——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
不了解澳大利亚的人或许想不到,1788年1月26人,第一批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西方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当时英国的囚犯——澳大利亚在最初的时间里,是被作为英国流放起囚犯的苦寒地。而这或许就成了澳大利亚之后文学发展中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特异性最好的注脚。至少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这个澳州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是以写“怪人”和自己的“怪”著称。
《人树》正是这样一部处处透着“古怪”的小说。小说主人公帕克是去悉尼城郊开垦荒地的代表,同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一样,帕克外表缄默、坚韧,内心却时常焦虑不安——这是一个生命的拓荒者最宝贵的优点与最难以躲避的缺点。对拓荒者而言荒原成了遗世独立的逃遁之处,对阅读者而言,荒原第一次以一种绝佳的带入感进入文学领域,不再充斥着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与黑水盘蛇的沼泽。那不过是一处等待开垦的乡村,与业已建立起来的边陲小镇并无不同;那不过是一处能提供衣食的土地,与注定要建功立业达成梦想的美国则大有不同。人们在那里既没有闯荡未知江湖的快感与恐惧,也没有开拓新大陆之梦的豪言壮语,有的是生老病死、种植庄稼、放养奶牛,等待年岁慢慢逝去,而每一个时光流过的点滴自己都能毫无保留的感知:古典人生的喜怒哀乐浸淫其中,意识在草长莺飞的旷野间飘荡,情节则宛若长幅画卷不急不徐一一展开,那种对时间尊重享受、并不打算征服的优雅态度,或许正是符合“史诗”的定义的……于是我常常觉得怀特是20世纪西方的庄子。清冷月光下,一株直白明亮的树,这样的比喻绝对是适合他的。
怀特曾在《人树》中写道“这个世界正像他的意念一样,依然被禁锢着,冰冷而阴郁”——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怀特就处于这样一种类似的情感状态中,早年的留英生涯,参战,郁郁中被遣返回澳,际遇种种让他不得不妥善面对自己因年轻而焦躁不堪的内心,直到用文字和时间慢慢磨平曾经的锋芒——或许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说,怀特的成功之处也在于此,刻骨铭心的异化和孤独感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世纪病。
读这样的小说,首先能感受到的就是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清香,在意识流与古典情节描写的肆意转换中竟然半点斧凿之迹也无;整个故事并不波澜起伏,表面上的情节平坦就像是一条淙淙小溪,读起来毫不吃力,你不用担心故事里突然拦路跳出个陈咬金然后进入让人血脉上涌的高潮——这一点与西方古典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怀特的小说成了现代研究学者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的实验场,甚至有人称他为“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新批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先后登台,但至少有一点共识,怀特的小说(尤其是这部《人树》)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无处不透露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立体感——另一方面,怀特笔下人物的命运与其说是对抗环境不如说是对抗自己,因此我相信怀特是真正明白东方哲学对于“自然”的定义的,自是自己,然是这样,自然无非是自己如此的状态,天地万物,也莫不俱是有自己如此的状态,怀特暮年曾透露说希望能来中国一趟,尽管最终未能得偿所愿,后人也能从中一窥大师对于古典东方哲学的热爱。
《人树》是作家的第四部小说,正是由于它为作者赢得了国际声誉。瑞典学院在授予怀特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称:“他以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但怀特的目光却并未局限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不少研究者甚至将他与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相比,称他在探寻深邃井下的人性光芒这一工作上,跳动着一颗堪比托尔斯泰的心脏。——如“澳大利亚的创世纪”这样的褒奖词似乎也证明,不是谁都有幸被时间选中,获得面对亘古的伟大时人之为人的平和广博,人性的光芒,于是“Eyes which had a softness to them around the edges,while at the same time a penetrating glint.(对待事物的各个层面都温柔平和、同时又不乏入木三分的犀利的目光)”这样的褒奖被他的朋友Desmond Digby说出来,也丝毫不觉得突兀了。
历史从来不乏专事锦上添花之人,怀特对这一类人向来是敬而远之的,甚至被宣布获得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面对大批蜂拥而至的记者,怀特避而不见,也没有出席当年的颁奖礼。怀特以他慎独笃定而宁静淡泊的内心面对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他在自传《镜中瑕疵》中写道“要说关于自己的真话是很难的事情,然而,我感到必须勉力而为,因为许多人对我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即使是不少多年来熟知我的人,也显出他们对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毫无所知。”他坦承自己的同性爱取向,与自己的爱人在农庄里笑对人生,暮暮终老。
1990年,这个生性冷僻的伟大作家于自家安静祥和的农庄中结束他在人生备受争议的78年光阴,带着或许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篇幅浩瀚的书册,走下神坛,走向生命最终的静默。他晚年破例接受英国BBC记者访问时曾被询问他对于写作人生的最大体会,他的回答是:“It is the way of living a life,that makes me standing on my dignity and softness.If you ask me whether being regretful or not,i'll say,what a life passing by”。(“写作就是我生活的方式,它让我活得温和而有尊严。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选择这条路,我会说,时间这样过去就很好。”)
有不匮乏的生活资料,有相互守候的伴侣,有热爱并坚持奉献自己一生的工作,有平和安详的内心,真是的,即便只是旁观的阅读者身份,我也不免感慨一句,时间这样过去就很好。
最后,这里有一个介绍Patrick White的链接,名字很好玩,叫做“干嘛为Patrick White烦恼呢?(Why bother with Patrick White?)”
附:
1.Patrick White晚年在悉尼的家
2.《人树》小说原名<The Tree of Man>,来源于英国古典浪漫派诗人Alfred Edward Housman的著作<A Shropshire Lad XXXI>中的一句诗:"On Wenlock Edge the wood's in trou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