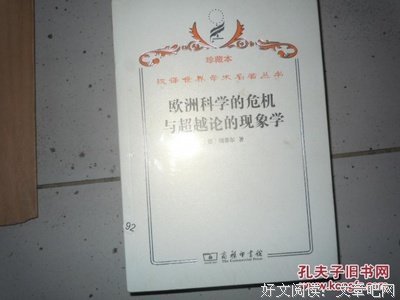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是一本由(德)胡塞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34,页数:6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精选点评:
●直接读最后的“译后记”更好一点。 哲学就是彻底、纯粹的理性! 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意识的本质,就是它总是力图发现更多的“第三世界”(卡尔 波普尔)中的东西。
●这算是胡塞尔比较简单的一部作品了,关乎欧洲文明的命运,开启通往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
●比胡氏其它书好读,至今还是有启迪作用。
●此译本中除了个别几处Idealismus被译为“观念论”外,绝大部分和Idee有关的词都被译为“理念”。如果先撇开一词多译的做法不谈(全书Idee的确更多地是作为胡塞尔批判的“理念”化思考的“理念”之意,但不全是),从译后记来看,译者先生对胡塞尔的Idee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译后记中引用的胡塞尔谈论柏拉图的那段引文所在的原正文段落之下就是胡塞尔开始谈近代哲学了,理念化的思维不是近代哲学才产生的,而是从古代哲学起就有萌芽了(《蒂迈欧篇》是对世界理念化解释的首次运作?)所以这一点上古代和近代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由于因果性近代思想使数学式理念化变为数学-物理学模式)。Idee在胡塞尔这里起码有三种含义,译者先生已提到了两种:理想性的理念和日常用法意义上的看法、观点(Ideen1被译为《理念》
●写在附录里的才是真心话啊,呵呵
●翻译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是一本啰里八嗦的演讲录。马克思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胡塞尔所做的工作正是重新表述这个问题:现实生活应该成为哲学的主题。汤是一碗好汤,只是勺子沉到了碗底,只能用手指蘸一下拿出来舔两口试试味道了。
●强烈要求国务院下发Transcendental的统一译名(超越的,倒不如是白日飞升的)。对于科学的批判好多数理知识晕。倒是什么地平线啊悬置啊对康德批评啊倒是懂了八成。
●胡塞尔的“天鹅之歌”,作为“严格科学”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谢幕表演。本作比起作者的其他作品显得更加清晰明了,从科学的、同时也是人类的危机出发,揭示客观主义的朴素态度,从生活世界和心理学还原两条路通达超越论现象学(通行说法为先验现象学)。
●我给这本书的名字打五星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读后感(一):希腊理性的衰落与欧洲科学的危机
只是粗略翻了一遍,作为胡塞尔终身动机的阐发与临终遗言,这本书需要精读。欧洲科学的危机是希腊理性的衰落的病症,胡塞尔由此一直强调理性主义不等同于客观主义,理性主义者胡塞尔并不是反科学主义者。黑尔德据此透彻的言明, “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 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 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
正是自然的数学化切中了意义本身:韦达 伽利略 笛卡尔是科学危机的三个关节点(1)韦达的代数术:韦达发挥了丢番图在运算过程中用字母表示数的技术,使得算术彻底成为了代数学和符号操作(2)伽利略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划分(3)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和主观主义。韦达的“一般”代数和笛卡儿在早期试图建立“普遍数学”其实就等于对量和数的一种符号理解,其结果是对几何学的一种代数解释。由此造成意义的沉淀和世界的机械运行。
本书除了批判的意义,真正的重心问题在于附录的《几何学的起源》。胡塞尔由其生涯起始之作《数的概念》开始,到其终端的《几何学的起源》可见其为科学之奠基的心血和志业所在。另外这本书还可以结合克莱因所著的《希腊数学思想与代数的起源》,结合希腊数学及其形而上学背景,回溯近代自然数学化观念发生的必要条件。
Hopkins等人对克莱因和胡塞尔的研究至少表明了一点,现象学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亲和性和明晰性,它让我们看到了积淀在历史之中的以往没能觉察到的意义和概念。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读后感(二):世界统一性的分裂:胡塞尔论近代客观主义的形成
1引言
胡塞尔(1859-1938)长久地被同代人看做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者”。但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后文简称《危机》)中,他却指出,欧洲精神得病了,不仅哲学如此,科学也是如此。他们共享的一点病灶就是所谓的“客观主义”——一种对完全脱离主观性的客观性的诉求。而有能力做出诊断、开出处方的只有一种真正的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②]。在后者的诊断下,客观主义必须被看做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而这篇论文的兴趣就在于考察胡塞尔对此的论证。为此,首先我将说明,现象学是如何作为一种克服怀疑主义的努力而诞生的。其次我将指出,在胡塞尔看来,近代的客观主义同样是一项克服怀疑主义的进程,但它是成问题的。文章的最后两部分将分述胡塞尔对客观主义进程的还原,
并且说明:在胡塞尔看来,客观主义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世界的统一性自身分裂的过程;即世界的统一体分裂成“真实”和“非真实”两个领域的过程。
2 现象学作为克服怀疑主义的努力
如曼弗雷德·索默尔所言,现象学的工作可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光学”,是一种寻求特殊观察方式的努力,以至于“……通过这种观察方式,那些自明的东西成为有疑问的东西,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了使自明的东西真正名副其实,还需要哪些条件。”[③]对胡塞尔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态度”。自然态度以“意见”的形式发挥着作用,如,一个东西的冷热、方圆、好坏,这些性质似乎是因人而异的。自然态度下的自明性设定了一系列不言自明的预设,而这些预设在自然态度自身范围中,却是不能发现的。自然态度允许了一种含混性,而这种含混性则导致了各式各样的怀疑主义,推而广之,这使得一切知识的基础变得可疑。现象学的目标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怀疑论(从而,严格的说,一劳永逸地解决可疑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希望将一切知识建立在一个真正自明的领域中,这种真正的自明性使得一切追问都成为无意义的语言游戏。
胡塞尔的策略是:我们必须考察那些甚至连极端的怀疑论者都设为前提的东西。譬如,我可以在自己面对电脑屏幕的同时怀疑自己是否正处于梦中,从而其实是在面对一个电脑的幻象。但是胡塞尔指出:我这个怀疑本身恰恰早已依赖于它的内容——一个“可能是幻象”的电脑现象了。如果没有这个电脑现象,我的怀疑将是没有内容的。那么这就是说:在一个更特殊的角度看来,怀疑与肯定只是与“电脑现象”发生的两种特定关系,而这两种关系方式本身是无疑的。
以此类推,胡塞尔认为,只要把以上事例中提取的原则进行普遍应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一片真正自明的基础,这片基础将使得一切建立于其上的科学都将是无疑且统一的。当然,这里将做的不是一个个地去阐明现象,而是进行一种一劳永逸的“观点切换”。这项工作类似于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但却是一种普遍地“现象化”。这项工作要求现象学家脱离自然态度,进入一种所谓“现象学的态度”。
3 客观主义作为危机
其实早在现象学诞生之前,自然态度中已经有种种克服怀疑主义的努力了。但自然态度仅仅把怀疑主义看做是客观性的缺乏,从而把克服怀疑主义的问题,把握成了一个通过取消主观性来增强客观性的任务。而这项任务最终导致了“客观性”、“精确性”的独裁,并且理性的意义也遭到了削减,成为仅仅与客观-精确二者相关的能力。当胡塞尔谈论“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想取消客观性,相反,他想要说的是,主观性和客观性二者应该处于一种健康的关系中,而近代思想史却只想执“客观性”一端。换言之,“客观主义”问题不在于“客观”二字,而在于“主义”二字、即在于客观性对主观性的独裁。胡塞尔想要让我们知道,现代科学难以发现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现在的时代自身恰恰活动在客观主义的后果链条之中。
占据客观主义中心的,最终是一种对“自在世界”的信仰——这个世界一方面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则是与主观-相对之维完全无关的[④]。这意味着一种关于绝对的客观性的规范成了自明性。胡塞尔最终指出,这种意图一劳永逸清除主观性的努力最终导致了欧洲科学的疾病——其病症在于,这个世界最终会使得人赖以行动的主观性无处安放,这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彻底摆脱自由和责任、从而与人性无涉的世界。胡塞尔晚年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如今接受的客观主义并不待在历史的彼岸,相反,现象学的态度最终能揭示出它作为思想史的发生过程,它的形成序列。理解现象学的追问角度在此至关紧要。现象学的问题不“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世界如何将自己发明出一个本质,并且忘记这一点的”。——在这里,本质指的就是《危机》中提到的“客观主义”理想。
因此,胡塞尔的考察蕴含着一系列追问,即:我们是如何从这个本质上只有一定客观性的世界中,逐步地发明出绝对的客观性理想的?我们又是怎么赋予后者“真实”的地位的,又是怎么把这个我们总是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贬低为指向它的“图像”的?我们又是怎么忘记这一点的?——回答这些追问的方式是把客观主义看做一个形成的过程。由于在现实中实现的行为是被动机所驱使的,所以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系列前后相续的“动机链”;其中,任何一个动机都不是没来由的:它被前一个动机所引发,而又为后续可能出现的动机提供了基础。 “几何学的起源”和“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即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两个环节。
4 几何学的观念化
需要预先澄清的是,胡塞尔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几何学的实际发现者不感兴趣,也不关心伽利略具体地怎么做到某些实验。在几何学方面,它重构出的是几何学得以发生的必然条件。而“伽利略”也是个代号,它指称的是那一群开拓者们共享的思想动机。胡塞尔在两个环节关注的是:那些古老的知识的实质是什么?它们是怎样作为传统,而为伽利略们提供了思想资源的?伽利略们又是如何把这些传统汇聚为一整套思想工具的?这套思想工具又是如何使自然的统一性分裂为“数学的自然”,以及指向前者的其余部分的?
伽利略将自然的数学化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先考察几何学的本质。为了避免自然态度中随处可见的误解,胡塞尔在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欧几里得几何学意义上的图形并不“实存”。真正意义的点、线、面和圆等等东西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我们现实经验到的领域,是一个本质上不精确的领域,是一个被各种“质”注满的领域。而胡塞尔要问的恰恰是:欧式几何的图形,它那“仿佛存在”的存在方式,是如何从这个领域中发明出来的?
胡塞尔的论述非常复杂。他首先把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质分为“形态”和“非形态”两个部分。世间实存的万物皆有这样那样的形态——在时间中,“形态”作为特殊的质,很容易被动地凸显出来。其次,在世界中的生存需要,使得我们发展出一系列处理“物”的技巧,而正是它们建立了初步的可还原规则。譬如,利用某些在位置上相对稳定的形态为准,测定其他形态的位置;又如,以一些简单的形态(如,三角形)为准,把其他形态看作是前者的复杂化。这种在操作上的还原技巧都是各种各样的测量术。它一方面在诸种形态中建立了可还原的联系,另一方面则为主观性之间提供了初步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只能为有限的相对性提供客观标准。
接下来的关键是客观性从初步阶段提升到绝对层面,以至于这种客观性将可以囊括一切时空中可能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实践的几何学(大地测量术)必须提升为观念的几何学。其中“观念化”行为居功甚伟。为此,我们必须追问观念化行为的实质。胡塞尔的答案是:观念化行为也可以从实践技艺中寻找它的起源:随着要求和生产力的提高,我们会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具体地处理形态之前,那个想要趋近的“极限形态”就已经被预先确定下来了。“极限形态”显然就是最初的几何之物。重点在于它悖论性的存在方式:它不于现实中“实存”,但能以“例示”的方式显示自身。至此,欧式几何的“观念的”几何形状就在世间获得了它特殊的存在方式。
至此胡塞尔只论述了单个的几何图形是怎么在世间获得它的“实存”的。事实上这还只是自然之数学化进程的第一步,距离伽利略接过这些思想资源还有一段路要走。接下来发生的是测量术与前述极限形态的交互作用。这里必须说明:测量术作为一种提供初步客观性的手段是十分古老的。事实上几何学在古希腊的名称“ γεωμετρία”,其涵义就是“大地-测量术”,这不仅意味着测量术的存在比几何学古老,甚至暗示后者要奠基在前者之上。
具体说来,测量术与极限形态,他们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有两条线索:
一方面是测量术在极限形态中的运用。这不仅导致了个别的极限形态间产生了紧密的关系,还导致了一种能自由自在地演绎出新图形的可能。这产生了一种“普遍精确”的理想——尽管暂时还只存在于“极限形态”的世界(即,几何学的世界)之内。
另一方面则是几何学在测量术中的运用。测量术活动的领域本来就是具体的生活世界,它用来建立一些形态与另一些形态之间的关系。但一旦测量用具的形态,与极限形态和数字两个元素建立从属关系之后,测量术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对自然的“应用几何学”——或进一步说,“应用数学”——了。
5 伽利略把自然数学化
可以说,在伽利略们着手工作之前,自然已经完成了其形态方面的数学化。对于伽利略们而言,他们的任务其实只有一项:把自然剩下的部分数学化,即,把那些非形态的方面给数学化。胡塞尔正确地指出:伽利略们并不是纯粹的发明者,相反,他们是传统之子——这意味着他们的发明也是建立在传统资源之上的。甚至可以说:伽利略们独有的,可能仅仅是对主观性的厌恶,以及对客观性的痴迷。
那么伽利略是如何把自然非形态的质的方面给数学化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颜色、温度、喜恶这样的质,似乎只有“比较级”,从而距离精确性非常远。伽利略的天才灵感在于:他在质与形态之间建立了一个从属关系,以此,质的变化就依据形态变化的中介而联系到了几何世界。伽利略,这位“既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⑤]的集大成者,把已经“应用几何学化”的测量术再度扩展了。而这加强后的测量术不再只是简单的活动在形态领域。它最终成了诸如水银温度计这样的中介:它建立了质的变化与长度变化之间直观的因果联系。伽利略的种种努力呈现出一种普遍意图:任意非形态-变化,必须直观地联系一个相应的形态-变化,并以此被间接地观念化了。简而言之:化质为量终于是可能的了。这个世界,至此正式地一分为二:居于主宰地位的“几何世界”,以及只是指向它的“现实世界”。
自然的全面数学化还有许多步骤,韦达则极大地发展了算术的代数化,而笛卡尔又建立了几何图形与公式之间的关系,更不必说后来的牛顿等科学家了。如果考虑到康德哲学也在此谱系中的话,我们就能理解,这个“伽利略认识架构”实质上已经主导了整个近代科学-哲学的走向。客观主义正是这条单向道的后果。客观主义认为:真实的世界,它先于我们的努力早已“在那里”了;而我们所做的努力,只是以不断接近的态势去“发现”它罢了。这种实践的结果最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自明性”,正如胡塞尔概括的:它“……立即就用观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⑥]。
6 结语
在这个客观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胡塞尔的论述中,该进程的第一步:
l 形态被以它的极限形态为准反向规定,丧失了自在。形态与极限形态间建立了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形态成了极限形态的指号(Anzeigen/indication);
指号的自身存在不重要,它的意义就是指示高于自身的内容。我们在客观主义的余下进程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构:
l 非形态的质(如冷热、颜色和轻重等),与形态建立了从属关系。质成了形态的指号。
l 生活世界的因果联系,原本是多种多样的,但也与某种特定样式的因果联系——形态与非形态之间对应的变化关系——建立了从属联系。其他因果联系成了形-质联系的指号;
l 欧式几何被建立为解析几何的指号;
l 几何整体被建立为数的指号;而数则成为代数的指号;
l 世界森罗万象之联系最终都建立为公式的指号,从而:
l 自然被反向地规定为一种前-数学,自然成了数学的指号,一种应用数学。
贯穿所有这些步骤,我们可以看到:客观主义的整个进程其实就是原初的世界统一性将自身分裂为两个领域的进程:一个将自身压缩为指号的具体世界,它指向一个只能以“被指示的方式”存在的“真实世界”。
参考文献
[1] 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 克劳斯·黑尔德. 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尼采.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M].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M].周颖,刘玉宇,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8] 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9] 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 雅各布·克莱因.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M]. 张卜天,译.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1] 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29页。
[③] Manfred Sommer,“Fremderfahrung und Zeitbewusstsein. Zur Phänomenologie derIntersubjektivitä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8(1): 3 - 18 (1984). ——中译文为倪梁康教授所译,首次刊载于:《场与有》,第四期,武汉,1997年。
[④]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33页。
[⑤] 同上,第68页。
[⑥] 同上,第65页。
*本文内容已载于《枫林学苑》,2019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读后感(三):王俊:厌倦与拯救——重读胡塞尔《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
摘要:胡塞尔晚年的经典文本《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通过对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现代化危机的根源,即意义的空乏、主体的缺失以及对责任的厌倦。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深化了此种反思,而阿伦特则在文化领域中确恰地表达了“危机”的状况。克服危机的拯救道路蕴藏于现象学的回溯研究之中,只有通过理性反思回溯到作为一切客体化行为之根源的主体视域和生活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全面认识世界所蕴含的可能性,主体及其自由方可得以保存,“人文主义态度”方可得以恢复。
一、欧洲人的危机及其来源
1935年5月7日,77岁的埃德蒙德·胡塞尔受到奥地利文化协会(Österreichischer Kulturbund)的邀请,前往维也纳作了题为《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的文稿在胡塞尔手稿中标明是写于1935年4月7日,以《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为题收于全集第6卷《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这也是胡塞尔生前确定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1],而作为此书核心内容的这篇演讲稿,可以说是研究胡塞尔思想的最经典文献之一。
1935年的演讲在维也纳“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响非常热烈,“两天以后,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个演讲(而且又是座无虚席)。”[2]在这个演讲中,胡塞尔首先从目的论和历史根源出发讨论欧洲人的哲学理念,随后讨论了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以及出路。因为演讲组织方奥地利文化协会的宗旨是“通过领导性的精神人物的广泛参与,以自由的或者保守的方式致力于欧洲在精神上的更新”,所以演讲最后很切题地以欧洲精神的重生和升华作为结尾。年迈的现象学创始人最后指出:尽管“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厌倦”,但是
“如果我们做好‘好的欧洲人’对诸危险中这种最大的危险进行斗争,以甚至不畏惧进行无限斗争的勇气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从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中,从对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从巨大的厌倦之灰烬中,作为伟大的、遥远的人类未来的象征,具有新的生命内在本质的、升华为精神的不死之鸟将再生。”[3]
那么,何为厌倦?为何厌倦?如何克服厌倦借由精神获得拯救?这些问题要从报告的文本中去寻找:厌倦是“危机”的表现,而“欧洲人的危机”首先是由科学引发的,或者说,就是科学的危机:在这里胡塞尔说的处于危机中的科学乃是指具体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这些学科形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理解。他在演讲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作为统治性世界观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却导致了人类生活的危机,在哲学的道路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危机?
胡塞尔认为,最为核心的“危机”在于,通过“实证主义的还原把科学的观念还原为诸事实科学”,因此导致了“生活意味(Lebensbedeutsamkeit)的丧失”或者“意义的空乏(Sinnentleerung)”;与此同时,哲学的地位,即作为“开启普全的、对人类而言先天的理性的历史运动”或“诸学问之王后的尊严”也随之丧失了。但是试图取代哲学位置的自然科学必然会失败,因为对它们而言它们的意义基础被蒙蔽了而且必然被蒙蔽,对存在进行阐释的总体性要求被取消了。而这一切要归因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精神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胡塞尔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把哲学的头颅砍去了”[4],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5]。
那么,为什么科学成就的增长和哲学、形而上学的失败会导致“意义的空乏”、并引发欧洲人的危机呢?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通过深入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及其要素给出了回答。在这里,他列举分析了数学的无穷量化观念,因果律和归纳证明等对我们今天理解世界的方式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
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无穷的观念。这个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希腊其它的具体科学。但是古代数学只有一种有限的封闭的先验性,在古代人们并没有达到通过数学(几何学、抽象的数字、集合理论)把握无限任务的高度。而“关于一种合理的无限的存在整体以及一种系统地把握这种整体的合理的科学的这种理念的构想,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新事物”[6],通过统一的数学抽象形式把握世界,这是伽利略把自然和世界数学化之后的尝试。在这个尝试中,自然和世界不再是数学的基础,而是相反,自然和世界成了数学系统中的一个理念化的集合(/流型Mannigfaltigkeit)。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几何学,在古代几何学是一种与生活世界密不可分的丈量的技艺,比如丈量土地。今天看来代表着整个空间-时间的理念形态的几何学,“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和一般测量的规定方法,这种方法起初是很粗糙地使用的,然后是作为一种技术使用”。一方面,“这种测量活动的目的在这个周围世界的本质形式中有其明显的来源”,而另一方面,“测量技术显然可以提供客观性,并为客观性在主观间的传达的目的服务”。[7]但是在经过对精确性和客观性的无止境的追求之后,这种经验性的丈量技术及其经验-实践的客体化功能从实践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成为一种纯粹的几何学思考模式,将富含意义的周围世界抽象为明确单一的数学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实践方面的相对性和当下的具体鲜活性被舍弃了,人们坚信由此他们赢得了一个普遍的、同一的、精确真理——一个单纯量化的世界。
除了数学方法之外,这种客观世界的普遍形式还借助于一种普遍的因果性,这种因果性作为直接的和间接的关联性把杂多的经验世界组织成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极端的统一性就是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归纳方法起了关键作用,把经验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推到普遍形式的因果关系就要借助归纳,世界的普遍因果性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和理念的极点,因此认识的获得过程实际上就是从经验事实上升到原理的过程,即归纳。从根本上来看,因果性本质上乃是一种假说,“尽管有证明,这假说依然是而且永远是假说,这种证明是一个无穷的证明过程”,而归纳的介入实现了从假说向普遍唯一真理跨越的过程。这种唯一性也就意味着放弃活的当下的丰富性,通向假想的单一意义,当这种单一意义成为世界的唯一意义时,就导致了“意义的空乏”。胡塞尔指出“处于无穷的假说之中,处于无穷的证明之中,这就是自然科学特有的本质,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先验存在方式”[8],自然科学的演进过程就是不断排除旧的证明为误的假说,而确立新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假说,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归纳有一种“无穷”的恒常形式,这种形式为自然科学这种不断破立的进步方式奠定了合法基础。自然科学不断完善,无限进步,不断接近那个假设的“极点”,即那个所谓的“真正的自然”,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正在提供越来越正确的关于这个自然和世界的表象,但是未曾设想这样一个直线型的无限进步观、甚至线型历史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们丰富的意义前提并没有在其中得到充分揭示。
以数学形式和因果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最终导向对世界整体的一个普遍的形式化把握,追求一个一般的世界、一个空的普遍公式,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就是这种将世界整体公式化(形式化)的尝试之一。他们“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暗中替代随即传给了后继者,以后各个世纪的物理学家。”[9]这种纯形式化模式下进行的符号思维实际上抽空了人原本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方法“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人类在其中丧失了回溯反思的能力。通过意义空乏的形式化作为技术的自然科学方法远离了直接的经验直观和起源的直观思维——科学本身的意义来源于这种前科学的直观,但是理念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恰好是隔绝了这个本源。
理念化和形式化实现了一种精确的客观性,它成功克服了主体经验世界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事实上在起源过程中它是以具体的经验世界为基础的。而一旦客体化行为的理念过程被绝对化时,它被与具体经验隔离开来,经验世界的基础被抽离。历史地看,这种绝对化过程与笛卡尔的沉思密不可分。笛卡尔的沉思把原本统一的世界分裂成两个世界:自然世界(cogitationes)和心灵世界(cogito)。而在他之后这两个系列并没有完全平行的发展,在霍布斯、洛克和休谟那里,自然世界逐渐占据了奠基性的位置:心灵世界依据自然世界的存在方式被自然化了。客体的存在有效性被必然化,决定了自然世界的特权,主体的意义世界在此被矮化和遗忘,因此出现了“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意味着绝对科学客观性的现代理想:“科学有效的东西应当摆脱任何在各自的主观的被给予性方面的相对性”,“科学可认识的世界的自在存在被理解为一种与主观经验视域的彻底无关性”[10]。
胡塞尔相信近代的“客体(Objekt)”观念以及作为对象之总和的“世界”观念通过伽利略和笛卡尔经历了一个普全的扩展和绝对化的过程。客观主义所把握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效用为目的的一个理念对象,而并不顾及世界原本所是的样子。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式包括预先设定的效用目的和对过程的实验性干预,这二者就是现代技术的两大特征。[11]这种技术精神背后包含着乐观和自信:原则上一切都是可研究的,因此作为对象总和的世界成为了现代科学可把握的总体课题,一个客观的对象集合。
但是在经验直观中,实际上所有感知行为都有自己的特定视域,视域意味着总是从某一角度观察,而自然科学所设想的无视域性则是对对象的去角度,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状况,在实际中对象不可能在意识中完整地被给予,因此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世界只能是理念化(通过因果律和归纳的过度使用)的结果,并且这个理念化结果被视为绝对的客体、原本所是的客体。如黑尔德(KlausHeld)所说,“自然的存在信仰在现代科学中上升到了极端:在世界的存在中,与主体的所有联系痕迹以及主体的世界经验的视角都被消除了。科学认识彻底摆脱主观-相对的被给予方式的限制,绝对的客观性成为最高的规范”。[12]
对客体性的过度信仰导致了当今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信仰,即相信能够通过一种恰当的方法超越一切主体相对之物,实现关于自在世界的知识的直接把握。其基本动机在于,以一种绝对客体化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起源,而否弃承担科学的主体性和为客体化世界奠基的意义构建的主体层面,或者将二者的奠基关系倒置过来,即认为普全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认识和意义构建的基础。其后果是自然科学占据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奠基性地位,同样作为科学形式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或者按客体主义方式接受改造(如心理学),或者被摈弃。随着这种客观主义观念的以绝对化的方式确立,根源层次上的主体层面、意义构建层面被遗忘了,这就是现代欧洲的危机或者“病症”,一种原本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学、哲学和生活的统一意义丧失了。这种技术的无限扩张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技术本身成了世界的主体,人作为世界主体的地位则相应地消失了。而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或者客体化方式原本只是诸多科学类型或者诸多思想方式中的一种,它们共同奠基于一个根源的意义构建层次之中,但是现在这种思想方式被绝对化,僭越了它原本有的范围,问题由此出现:世界的无限量化,唯一的线型发展观,绝对客观性的理念,主体无家可归。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的存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病症下的生活方式:我们只信赖量,数量化给我们一种确定感,主体感受能力随之消退;绝对的客观性把人的主体置于次要和附属地位,精神是物质物质世界的附庸;以因果性和归纳法为基础形成的线型发展观让我们对于技术时代的前景充满自信,从而割断和遗忘了历史……总而言之,降低主体性和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二、技术时代的文化危机
然而在胡塞尔看来,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在存在论层面上,自由就是一种主观构建的无限可能性,是作为经验游戏场的视域,这是无法通过对象化、客观化来获取的。对这种可能性的把握意味着人的责任,行为的责任,而一个与主体绝然无关的世界则意味着放弃可能性的视域,也就是放弃责任。因此胡塞尔说欧洲最大的危险在于厌倦,就是对可能性的厌倦,对主体责任的厌倦。人们习惯了依赖量化和绝对客观的理念,习惯了遗忘主体精神和历史;由于主体的异化,道德与责任在某种意义上退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只作为某些人的专业(伦理学家)。由此形成了欧洲人和欧洲文化的危机。
自然科学和技术时代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时代的危机,责任、道德与人和生活的疏离,文化和历史的沦丧。这些现象在胡塞尔之后乃至今天依然如故。海德格尔顺着胡塞尔的批判思路,把技术看作一种“摆置”(Ge-stell)权力,从存在论的层面上分析了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危机。这种摆置权力外在于人的生存,当人把自身移交给这种权力时,“人类就自己堵塞了通往其此在之本己因素(das Eigene)的道路。”[13]而且技术这种摆置权力作为排他性的唯一力量飞速扩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消除了主体相关性和视域性,继而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多元的生存和文化形态消失了,世界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模式下一元的、扁平的。[14]
一元的世界即意味着“意义的空乏”,海德格尔说,与这种空乏相应的是无聊的存在情绪,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生活节奏、娱乐、信息传递似乎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这种无聊、掩盖了这种无聊,但绝没有被克服,技术的摆置权力主宰了人类原本具有的可能性与自由,完整人性因此受到了损害。[15]
对于主体可能性和责任的厌倦,无聊的存在情绪,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技术时代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文化的危机。这种人类基本情绪和生存状况,以及对技术摆置力量下人对于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对人类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这一点汉娜·阿伦特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阿伦特认为,“文化”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即对自然的培育和对历史的照管。作为一个语词的“文化”culture起源于古罗马,意思是“培养、居住、照料、照管和保存,它首先涉及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培养和照料自然,直到让它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它本身代表了一种关爱照顾的态度,从而完全有别于竭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16]在“文化”这种方式下,自然被视作有灵性的、与人类生存相濡以沫的存在,不可被予取予夺。除了“培育自然”的含义之外,文化还意味着“照管往昔的纪念碑”,与历史记忆有着不可剥离的关联。人类除非经由记忆之路,否则思想不能达到纵深。[17]
但是“文化”的这种古典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摆置力量的盛行被逐渐忘却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并过度弘扬的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对世界的量化理解、客观主义、抽象化、工具化,注定将对自然则抱着一种掠夺式的态度,以及无视自然本身(包括人在内)乃是一个和谐系统的傲慢。而自然科学模式下,对于绝对客观性的推崇以及主体相关性的取消、归纳法、线型发展观,也割断了历史记忆,科学技术无需历史,因为自然科学总是乐观地相信自己在不断累积进步,不断接近真理,当下比过去好,未来比当下好。
对自然予取予夺的工具化、功利化态度,对历史的轻慢和割裂,势必导致文化的危机:传统和经典淡出、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关系消逝、历史虚无主义崛起、市侩主义对文化的挑战与侵蚀,如此等等。
阿伦特对于市侩主义作了精彩的分析:她说,市侩主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常见的,以布伦塔诺(Clements von Brentano)讽刺市侩的戏剧《在故事发生之前、之间和之后》为标志,这种市侩主义被诠释为一种精神态度:根据即时效用和“物质价值”来评判一切,从而轻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无用之物和无用职业。这种市侩主义正是文化上虚无而政治上犬儒的主流价值观念。[18]我们经常说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精神生活极度贬抑,厌倦精神层面,而物欲面相却高度张扬。
除了直接抛弃精神和文化的市侩主义。还有相对隐蔽和复杂的市侩主义。这种市侩主义被阿伦特称为“文化市侩主义”或者“有教养的市侩主义”。他们之所以对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感兴趣,是为了达到其自身的目的,例如社会地位、身份和经济利益。带有功利目的的市侩主义媚雅非但不能拯救艺术或文化,反而导致文化的全面解体,昨日的文化价值变成今天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消费品。因此阿伦特非常激烈地抨击了市侩主义对于文化的危害:
“文化对象首先被市侩贬低为无用之物,直至后来,文化市侩又把它们当作货币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更高的自我尊严。……在来来回回的交换中,它们像硬币一样被磨损,丧失了所有文化物原来独有的、吸引我们和感动我们的能力”。[19]
文化成为消费对象,人们试图藉此去掩盖现代生活中“意义的空乏”和无聊的存在情绪,但是如海德格尔所说,这并不能将之排除掉,也无法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消费文化产品无非令人们更轻易地“消磨时间”,但是在消费的同时,文化本身为了迎合娱乐口味被不断的碎片化和去人文化,其完整的精神本质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技术时代,自然被工具化、精神被抽空,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欲望被过度宣扬,胡塞尔说,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意义的空乏,导致了主体自由的丧失,导致了对于责任的厌倦;阿伦特则说,消费社会不可能懂得如何照料世界,因为它对所有事物的主要态度,即消费态度,注定要毁灭它所触碰到的一切。这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伦特所觉察到的20世纪以来人类和文化面临的巨大危机。
三、作为拯救力量的现象学哲学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危机、获得拯救?胡塞尔在他的演讲中已多有阐述,在演讲的最后,他说道:
“欧洲生存的危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欧洲在对它自己的合理的生活意义的疏异中毁灭,沦于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或者欧洲通过一种最终克服自然主义的理性的英雄主义而从哲学精神中再生。”[20]
当人类面对危机时,要么向下沉沦,陷入“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要么自我拯救,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拯救只有通过“理性的英雄主义”方有可能。
具体地说,对于当今自然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克服的途径乃是对这种已经被绝对化极端化的思想方式进行重新反思,把它重新回溯到作为一切思想方式之基地的“生活世界”上去,追溯作为结果呈现的意义的主体构建,追溯一种隐而不显的意义根源性和丰富性。胡塞尔认为,一方面对生活世界的把握是现象学的任务,而另一方面作为切入主体性层面和把握视域结构的步骤,心理学至关重要。但是旧有的心理学(比如材料心理学,白板说的心理学)并不具备这种把握能力,因为这种心理学本身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客体主义模式被构造、全然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定义和方式,一方面是数学化和极端理念化,另一方面则停留于主客二元论,按经验的实证主义将心理和精神问题视作人的实在方面,或将之归于一个幼稚的客观基地,因此它“完全不可能按照其固有本质意义将心灵——而这种心灵毕竟就是我,是行动着的,遭受着痛苦的我——变成研究的主题”[21],作为自然科学下一门特殊科学的“心理学的历史根本上只是一种危机的历史”[22]。在胡塞尔眼中,“只当布伦塔诺要求有一种作为有关意向体验的科学的心理学,才提供了一种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一种真正的方法的产生——即按照精神的意向性把握精神的根本性质并由此出发建立一种无限一贯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导致了超越论的现象学。它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客观主义。”[23]由这种意向性心理学出发而达到的现象学能够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把握方式,在根源处把握事情、把握纯粹的主体直观经验,即“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从他的自我出发,而且是从纯粹作为其全部有效性的执行者的自我出发,他变成这种有效性的纯粹理论上的旁观者”,“按照这样的态度,就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具有始终一贯地自身一致并与作为精神成就的世界一致的形式的绝对独立的精神科学”。[24]这种意向性心理学以及超越论哲学的课题“是主观-相对的、历史丰富的普全视域的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世界”,如此理解的世界已经在现代的客观主义研究实践中被遗忘了。先验哲学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它是对责任主体的思义(Besinnung),这个世界便是如此显现给这个主体的。而科学化的世界观点在遗忘视域的意识主观性的同时也遗忘了主体。因此哲学作为克服危机的道路在今天显得不可或缺,一方面它提醒人们保持主体的责任,另一方面则通过发生的视域构造理论为现代科学奠基,论证客观主义科学对生活世界的回溯性和依附性。
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最终要把握的是一个可以回溯到主观领域的世界,作为普全视域,“即作为指明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所有经验对象之权能性的游戏场”,即世界的视域特征。视域(Horizont)意味着,相关的对象总是在相关经验领域中保持置身状态(Einbettung),几何学起源于丈量土地的例子已说明的科学是起源于前科学的生活视域的,这种回溯在很多科学分支中都存在,比如算术和日常生活中的计数,医学和治疗疾病等等,它们都与一种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希腊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立足于实践技艺之上的知识称为“技术”(téchne)。但是现代科技则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割断视域联系的认识过程,科学认识成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在技术时代,哲学理性就是要回溯研究技术背后的视域联系或者主体相关物,而如果我们再往回追溯,则是有一个普全的视域,这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为一切具体视域奠基的超越论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最全面最根基的层面,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基地,所有的视域可能性都“积淀”(Sedimentierung)于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具体的视域和思想方式都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可能性。
对于根源和普全视域的回溯使人们有可能从整体上观照这个我们栖身其间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从整体上把握科学技术的来源和界限,从而具有一种对待世界之物的超功利态度、具有一种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和工具化视角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阿伦特将这种姿态称之为“人文主义态度”。这是一种文化能力和审美品质,是“无功利的”,它凝聚为有教养的个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和教养应当是与具体人生经验息息相关,不受技术时代知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限制。人文主义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人通过理性反思回溯到原初的本真状态,以一种“哲学源于惊异”的好奇心与爱心照料、安顿这个世界及其历史记忆,惟有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状态之中,人性的完整方可得到呵护,高贵的文化和传统才能得到保存和彰显,人类的危机才能得以克服。
在技术时代,哲学反思对于根源层面上主体相关性和意义建构的追溯,对于客观对象背后视域和生活世界的追溯,凭借的是一种理性的力量,一种避免极端和一元化,保持根源、可能性和全面性的力量。只有重新寻回并且维护这种根源、可能性和全面性,人的主体性和精神层面才能重新得以彰显,“人文主义态度”方能得以重新确立,人类文化和命运方可从“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中,从对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从巨大的厌倦之灰烬中”得以拯救,因为“唯有精神是永生的”。
参考文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rgänzungsband: Text aus dem Nachlass 1934-1937. Hrsg. von Reinhold N. Smid, 1993(Husserliana: Band XXIX)
- EdmundHusserl: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Hrsg. von Sowa,Rochus, 2008 (Husserliana: Band XXXIX)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克劳斯·黑尔德编:《生活世界现象学》,胡塞尔著,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
Weariness and save Rereading of Edmund Husserls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Man"
Abstract
Edmund Husserls classic text in his late years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Man" reveals the roots of modern crisis, namely the lack of meaning, the deletion of subject and the wearinessof responsibility, by the critique of the ideology of natural sciences.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Martin Heidegger furthers this reflection, while Hannah Arendt expresses the situation of "crisis" in the field ofculture. The Road to overcome the crisis bears in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henomenology. Only through the rationalreflections, whichreturn back to the subjective horizon and life-world, which standas source of all objective behaviors, we can obtain a truly 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 of the possibilities inherent in the world andpreserve the freedom of subject. The humanistic attitude can accordingly be restored.
--------------------------------------------------------------------------------
[1]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胡塞尔完成后发表于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哲学》书第一卷(1936),第三部分写完后胡塞尔打算再做修改,修改一直持续到1937年8月他病重逝世。这些部分是胡塞尔身前指明要出版的,加上后来整理的这个时期与此有关的一部分手稿,胡塞尔档案馆将之整理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Walter Biemel编,1976,全集第6卷)出版。
[2]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第2页(编者导言)。
[3] 同上,404页。
[4] 同上,19页。
[5] 同上,21页。
[6] 同上,33页。
[7] 同上,37-38页。
[8] 同上,50页。
[9] 同上,63页。
[10] 克劳斯·黑尔德:《生活世界现象学》导言,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38页。
[11] 同上,39页。
[12] 同上,44页。
[13]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151页。
[14] “摆置权力必须被经验为普遍地把可能存在和实际存在的一切当作可计算的东西和变成有所确保的持存物而带向显露的东西,——而且仅仅作为这种东西。摆置之权力并不是一种人类制作物……这种摆置之权力的无可避免和不可阻挡迫使它把自己的统治地位扩散到整个地球。……作为这种摆置之全力里的后果,地方-种族性地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暂时或者永远地?)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世界文明的订造和扩展。”(《同一与差异》,149-150)
[15] “遭受摆置之权力的人类,作为被这种权力、并且为这种权力而被订造者,推动对世界的持存保障,并因此把它推入空虚中。与此相应的是潜滋暗长的此在之无聊,就其表面来看,这种无聊全无来由,并且从未真正得到承认,通过信息生产、通过娱乐业和旅游业,它虽然被掩盖起来了,但绝没有被排除掉。人类的特性由于摆置之权力而拒不给予人类,此即对人类之人性的最危险的威胁。”(《同一与差异》,151)
[16] 参看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196页。
[17] 同上,196-209页。
[18] 参看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187页。
[19] 同上,189页。
[20]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第404页。
[21] 同上,399-400页。
[22] 244页。
[23] 402页。
[24] 同上,402页。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读后感(四):倪梁康:胡塞尔未竟之作《危机》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
内容摘要:撰写《危机》书的直接起因是胡塞尔1935/36年的维也纳和布拉格讲演。他在其中公开地对“人类历史”和“人类危机”的问题做出论述和研究,并由此而展开了一门可以说是现象学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讲演的文稿后来被扩展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的论著。胡塞尔身前正式发表的《危机》的两个部分自成一体,阐述了他对欧洲危机的实质与起源的看法。原先计划一同刊出的第三部分后来被胡塞尔留下做进一步的加工处理,题为“对超越论问题的澄清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学的作用”,其中包含他对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目的论的问题以及对作为现象学出发点的生活世界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个部分在胡塞尔身前未及完成,在他去世后才作为遗稿出版。
关键词:胡塞尔 危机 现象学 历史哲学 生活世界
胡塞尔在其毕生的哲学思考与创作生涯中差不多平均每十年出版一部书。惟有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是个例外:他不仅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而且也让海德格尔出版了他十多年前就已完成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到了三十年代,胡塞尔真正发表的著作也仍然只有一部,即:他以法文出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虽然他在三十年代末曾竭尽全力来完成和发表他的历史哲学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①],但最终得以出版的仅仅是其第一、二部分,它们实际上只能算是他发表在期刊上的长文。整部《危机》是胡塞尔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但最终也是他的未竟之作。
一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个现象学哲学的引论》的标题表明,胡塞尔开始公开阐述与人类历史、政治、文化有关的“实践现象学”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现象学哲学”的问题。此前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第二卷便是为“现象学哲学”而作的,但始终未令胡塞尔感到满意,因而在他身前也最终未得他的获准出版。他的一个基本信念在于,在作为本质科学的“纯粹现象学”的任务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令人满意的完成之前,作为事实科学的“现象学哲学”也就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开展,甚至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出,遑论令人满意的完成。因为任何事实科学的真正研究都以本质科学的相关奠基为前提。这与他在《危机》中揭示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是一致的:在伽利略之前的自然科学都难以被称作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囿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归纳和推断。而由伽利略开启的对自然的数学化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用某种本质科学来为关于自然的经验事实研究奠基的过程。(Hua VI, § 9)
因此,当胡塞尔于1935/36年在讲演和著述中公开地对“人类历史”和“人类危机”的问题做出论述和研究,并由此而展开了一门可以说是现象学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时,业内的人士或许会有各种不同的其他反应,但他们首先都会同样地感到惊讶。正如P.江森所说,“《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被理解为一种偏离开并孤立于胡塞尔的其他著作,是一种有所改变的、与时代危机境况相应和的现象学表达。”(Hua XVII,XVIII)但笔者在《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一书中已经列举并讨论过“对胡塞尔后期历史哲学趋向的各种评述”,其中涉及利科、梅洛-庞蒂、哈贝马斯、米尔曼、布伯等人。[②]这里不再重复赘述。就总体而言,对于胡塞尔的历史哲学思考,有些思想家会表示热烈的欢迎,例如狄尔泰、舍勒、海德格尔,他们都曾批评过胡塞尔的“非历史的”思想取向和思维方式;[③]扬·帕托契卡曾将它与胡塞尔此前于1929年春在巴黎进行的著名讲演相比照:“它[布拉格讲演]与巴黎讲演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论述的是一个在新构建的思想之纯粹苍穹中的设想,而在这里则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人们回返,它将哲学家的信息传达给处在极度危险中的人类。”[④]但另一些思想家则会质疑胡塞尔的这种“历史化”趋向,认为他由于受二战前时代危机状况的外来压迫而转向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最终放弃了追求永恒真理的本质哲学,例如王浩,可能还包括库尔特·哥德尔。[⑤]
然而正如笔者在《现象学及其效应》中所说,“将胡塞尔的哲学研究课题变化归咎于或归功于时代危机状况的外来压迫,这种做法若想得到合理的论证,首先必须提供这样一个证明:胡塞尔危机意识的形成不会早于时代危机状况的产生,因为前者按此做法应当是后者的结果。”[⑥]哲学人类学家威廉·E.米尔曼便认为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要早得多:胡塞尔“用他那敏锐的目光清楚地认识到:与危机密切相关的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绝望以及在世界观中向非理性主义的突变趋向,并且,他并不只是在关于《欧洲科学的危机》(1936年)的论著中才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至迟在1910年时便已认识到了这一点。”[⑦]虽然米尔曼并未给出关于这个“1910年”的具体论据,但我们至少在胡塞尔写于1912年的《观念》第三卷中已经可以读到胡塞尔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批评以及他的要求:“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理性的危难状况做一个了结”(Hua V, 96)。也就是说,还在一次大战之前,胡塞尔就已经预感到欧洲人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危机,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指出它和克服它。
二
撰写《危机》书的直接起因是胡塞尔应维也纳“文化协会”的邀请以及应布拉格“人类知性研究哲学小组”和“布伦塔诺协会”及“康德协会”的邀请,先是计划于1935年5月3日在维也纳做一个讲演,而后于5月中旬再在布拉格做几个讲演。(书信III,299)但后来因为布拉格方面的讲演因故推延,胡塞尔决定先去维也纳,并于5月7日在这里作了题为“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讲演。由于反响出乎意料地巨大,协会请胡塞尔于5月10日再将内容相同的讲演重复了一次。就此而论,撰写《危机》书的起因具有某种偶然性。在1935年7月10日致罗曼·英加尔登的信中,胡塞尔写道:“我来这里时其实并没有带着现成的稿子,因为很迟才决定必须在那里做讲演。……我根据最主要的东西自由发挥。题目是‘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前半部分:从其出自哲学的历史起源来澄清欧洲人的(或‘欧洲文化的’)哲学理念。第二部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危机的原因,哲学或者它的分支、即近代特殊科学失误的原因,它的职责(它的目的论的功能)——即为应当在欧洲作为观念而历史生成的更高的人类形态提供规范指导的职责——失误的原因。第一部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讲演,它用了整整一小时。因而我想就此结束,并为主题过于宽泛而道歉。但听众非常想要我继续说下去,于是我在休息之后继续,并且发现听众对第二部分很感兴趣。两天后[⑧]我不得不再次(在重又满座的屋子里)重复这个双重报告——又是两个半小时。这在维也纳是一周中的巨大轰动。与此相应,在维也纳的15天是一连串的持续负载,险乎已达到超载的边缘。”[⑨]当年11月,胡塞尔又去布拉格,并于15日和16日在布拉格德语大学与布拉格捷克语大学分别举行了两次内容相同的演讲。
胡塞尔标明完成于1935年4月7日的维也纳讲演文稿后来被扩展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的论著。1935年12月22日,胡塞尔在致其家庭的老朋友古斯塔夫·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写道:“现在重又是为付印而对讲演进行加工的痛苦。口头的讲演即使有了书面的准备也仍然不是一篇被言说的论文”(书信IX,123)。但将口头讲演改造为书面文章的困难在胡塞尔这里显然不是主要的问题。最后导致《危机》成为未竟之作的关键原因仍然在于胡塞尔的写作方式,它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等书的写作中已经表现出来。而在《危机》这里,问题依然如故。全集版《危机》的编者比梅尔在“编者引论”中曾描述过胡塞尔的研究手稿的总体风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胡塞尔对《危机》修改稿的处理:“胡塞尔的思想进程有时是跳跃式的。胡塞尔预告一个问题,然而在准备阐述这个问题时,他却让一个潜在的、而现在成了注意中心的问题吸引住了;以后他重又给出更大的总结,其目的只是为了将以往所思保留在当下。如果他在一个问题上停顿下来,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把握、重新拾起、改善、批评,或干脆将写下的东西丢弃。”(Hua VI,XV-XVI)
于是,接下来的结果用胡塞尔太太马尔维娜的话来说便是:“对讲演稿的‘编辑’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新构形、扩展和深化。”(书信VI,220)胡塞尔于1936年1月24日已经将完成的《危机》的第一稿寄出,但他接下来在1936年的全部工作日程却依然充满了对《危机》文稿的加工修改。虽然这年3月他突患胸膜炎,不得不一度中断写作。但自4月12日起,他又重新开始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这年6月10日致其学生、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契卡的信中,胡塞尔曾乐观地报告说:“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现在表明比我想象的要难,它已经慢慢地成熟起来。”(书信IV,433)可是此后两周之间,胡塞尔的心态便又有所改变,并在6月26日致帕托契卡的信中写道:“由于篇幅已经大大超出《哲学》的一个双册本的范围,我不得不决定做出改动,它恰恰是现在给我带来一个巨大的工作负担。”(书信IV,433)同年12月16日,胡塞尔在致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对我来说,写作这部著述[《危机》]的困难是无法言表的,恰恰是因为年龄障碍——而我尽管如此还不是在阐述和整理老的思想,而是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在向前迈进,获得最终的深刻洞见,它们以比我以往所知的、至少比我自己清楚意识到的更为深刻的理由来论证我的精神生活道路。与此相关,我突然在付印的过程中(!)注意到,我必须改变我的阐述计划。所以我在第一校时加入了一个不少于一又二分之一印张的附件,几乎是一篇自为的论文,而且还在第三校中又做了可观的改动。”(书信IX,128)
这封给阿尔布莱希特的信写于1936年12月16日。此前一天,胡塞尔刚刚完成对《危机》文稿的最后校改,而写信的这天也是他最后交稿的日子。因此,他在信中同时还报告说:“今天中午,我的作品(Opus)《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个现象学哲学的引论》为《哲学》第一册所准备的那个部分已经以最终修订稿的形式寄给贝尔格莱德的利贝尔特教授,现在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自我从拉帕洛的休养月以来的这半年时间是对我这个年纪之精力的一种苛求,而且无法设想会有一个休息日。……我现在必须阅读许多东西——但我的眼睛在去年变得糟糕了很多,我必须不断地去拿放大镜。而听力则差到了实际上已经很难与我交往的地步。……如果没有完成这部著作[《危机》],我就根本无法安心地死去。可惜我还不得不交付几个续篇,否则现在付印的整个部分都将始终是无用的,从中最终会产生一部篇幅庞大的书,日后,但愿是一年后,它也应当作为独立的著作出版。当然不是在德国。这里没有一家书社是对我开放的(所有的都被一体化了[⑩]),连尼迈耶出版社也不行,遑论其他出版社。因此我必须坚持,并且将每一分钟都奉献给工作。”(书信IX,129)
《危机》的第一、二部分终于发表在由贝尔格莱德大学A.利贝尔特教授在那里创办的《哲学》期刊1936年创刊号上。[11]由于胡塞尔1936年9月才完成修改,并于28日寄给利贝尔特,而最后的誊清稿是于1937年1月7日才寄到胡塞尔这里的,因此,可以推测,《哲学》期刊1936年的创刊号实际上是在1937年才真正面市的。
《危机》正式发表的这个第一部分讨论“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之表达的科学危机”,第二部分致力于“近代物理主义的客体主义与超越论的主体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澄清”。这两个部分自成一体,阐述了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实质与起源的看法,应和了《危机》书标题中的前半部分内容:“欧洲科学的危机”。在《哲学》创刊号上发表的这两个部分的前面,胡塞尔还加有一个前言,他在其中说明:“我在这篇论文中开始的、并且将会在《哲学》期刊的一组其他文章中完成的著述,是在进行一种尝试,即通过对我们的科学的与哲学的危机状况之根源的目的论的-历史的思义(Besinnung),对哲学需要进行一种超越论现象学转向的无可避免的必然性的论证。因此,这部著作就成为进入超越论现象学的一个独立的引论。”[12]
原先计划一同刊出的第三部分最终被胡塞尔留下做进一步的加工处理。这个第三部分题为“对超越论问题的澄清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学的作用”。它实际上构成这整部著作的另一个核心论题,相应于该书标题的后半部分的内容“超越论现象学”以及副标题的内容“一个现象学哲学的引论”,它们被用来说明通向超越论现象学的可能途径。第三部分由两个篇章构成:第一篇章“A.在回问中从在先被给予的生活世界出发进入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路”;第二篇章“B.从心理学出发进入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路”。胡塞尔计划将它作为补充篇发在《哲学》期刊的下一册上。在1936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胡塞尔在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兴致盎然地写道:“第二篇[《危机》]论文重又与康德等人相衔接,在现象学还原中对生活世界、而后是对哲学的阐释。然后,第三、四篇是现象学与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精神科学的关系。又一个工作之年!!”(书信III,309-310)
胡塞尔这里所说的第二篇论文应当是指准备发表的《危机》第二部分,而他所说的第三、四篇论文很可能是指他在与自己助手欧根·芬克商讨制定的《危机》其他部分的写作提纲中的“第四篇章:将全部科学都收回到超越论哲学之统一中的观念”(包括:1.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或生物学,作为对受到合法限定的世间问题域与现象学之间关系的形象说明。2.描述的自然科学(它们的先天作为“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与理想化的现象学。3. 作为普遍相互关联体系之统一的科学的“统一”。现象学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及“第五篇章:哲学的不可丧失的任务:人类的自身思义”。[13]
1937年的日子里,胡塞尔的确在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工作。在1937年5月31日致多瑞恩·凯恩斯的信中,他回顾说:“自此1937年初以来,我的身体状况十分虚弱。我大概在近几年里工作得太多,并且也必须克服一些困难。现在重又慢慢地好起来,以至于我还是可以对我的著述的第二部分进行加工,即对生活世界理论、以及由此出发对现象学还原的主要阐述的加工——是文字上的,因为思想上我早已处在纯然状态。”(书信IV,60)
然而不幸的是,同年8月10日,胡塞尔在浴室摔倒,伤及肋骨,引起胸部的炎症,从而不得不卧床休息。他在8月14日致瑞典哲学史家艾克·佩措埃尔(Åke Petzäll)的很可能是口述的信中说:“眼下我病了,因而不得不中断我的全部工作。”(书信VIII,283)在此后的住院期间,他还一直惦念《危机》的写作。有回忆者在1937年10月见证说:“胡塞尔相信他必定还会恢复力量并完成他的第二篇论文。”(年谱,487)1938年2月,他还对夜班护士说:“我还想完成一本书,应当会给我这个恩赐。”(年谱,488)
但是,这场疾病并未给胡塞尔留下完成《危机》的机会,它最终还是导致胡塞尔于1938年4月27日与世长辞,使得这部书成为他的未完成交响曲。完全可以说,胡塞尔在这部书上一直工作和思考到死去为止。
三
1937年元旦,即在撰写和修改《危机》第三部分的过程当中,胡塞尔自己曾对该书的意义做过一个总体评价:“这是关于我的生命之作的最终交待,作为内心结合的最终成果,它可能是我思想体验的最成熟的产物:以一种艰难的方式,从这个在其当下思义着的哲学家的素朴而封闭的传统性出发,逐渐引导上升,直至‘超越论还原’的真正自主性,直至发现他是‘超越论的本我’,以及发现由此出发和在此之中的普全的和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发现绝对的超越论的历史性以及绝对者的超越论的目的论。”(书信VII,225-226)
从现今研究者的视角来看,除了其他问题(例如交互主体性问题)之外,胡塞尔在《危机》中主要提出和处理了三个彼此间有内在关联的重要问题:
1.近代欧洲科学以及欧洲文化所面临的危机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维也纳讲演中作为第一论题被提出来的,也是《危机》书出版后最大的影响所在。对此问题的论述是第一、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第1-27节),即在《哲学》期刊上得到公开发表的内容。从这两部分的标题“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之表达的科学危机”和“近代物理主义的客体主义与超越论的主体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澄清”可以看出,胡塞尔将欧洲科学的危机仅仅视作欧洲人的生活危机的外在表现。真正的内在危机是欧洲文化的危机和欧洲人思维方式的危机。
“科学危机”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口号或公认的命题。因而胡塞尔从一开始便提出,自然科学与技术在近代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伽利略因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做法而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创者,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成为近代哲学的特征。[14]但在自然科学、甚至数学科学的领域仍然有令人困惑的含糊性出现,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之谜出现,它们最终可以被归结为主体性之谜。解决主体性问题需要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研究和方法的支持。然而这些解决主体性之谜的科学却始终在诉诸和援引自然科学,以它们为科学之精确性的典范。而自然科学这一方面却要求排除一切主观性的东西,排除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一切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数学自然科学由于技术化而被抽空了意义,或者说,它脱离开原初的意义赋予,排除了原初思维;另一方面,科学的危机同时也表现为,它丧失了它对于生活而言的意义。(Hua VI,3,45-46)
而从作为科学之父的哲学出发来看,胡塞尔认为,它在近代的发展史,主要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历史,是“为了人的意义而斗争”的历史,但它却因为不具备自然科学式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不再被视作理性人的自身理解,即对绝对理性本身的理解,而是越来越呈现出“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特征(Hua VI,11),普遍哲学的理想已然解体,哲学被视作某种文化类的东西或某种世界观。胡塞尔也在此语境中谈及“哲学的衰亡”(Hua XXVII,242)因此,“我们这些在这种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人,正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即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没,从而放弃我们的本己真理。”(Hua VI,12)这便是胡塞尔所说的意义上的危机。
2.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目的论的问题:
关于“欧洲科学危机”及其产生原因的回顾与思考已经与历史哲学的思考密切联系在一起。对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处理贯穿在《危机》的所有三个部分(第1-73节)之始终,它可能是胡塞尔撰写《危机》书的最初计划,也是最终目的。他曾在1935年6月中旬致其弗莱堡的学生费利克斯·考夫曼的信中说:“我立即重又捡起了我的因为对[维也纳]讲演的构思而中断了的历史哲学研究,它们实际上是自身领会的最高结论和超越论现象学的系统形态。”(书信IV,210)在《危机》书中也可以找到胡塞尔对这里的内在关联的再次指明:“我们的这些考察必然会引向最深刻的意义问题、科学的问题和一般科学史的问题,最后甚至会引向一般的世界史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与伽利略几何学有关的问题与说明就获得一种范例的意义。”(Hua VI, 365)正是在对欧洲哲学的历史以及从中产生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历史的回顾中,胡塞尔提出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目的论的命题。
就总体而言,胡塞尔在《危机》中提出了现象学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案,以及他对哲学的历史目的论的解释,还有他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论说明。
首先要留意他提出的“理解的历史学”的概念:“一切关于事实的历史学都始终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们总是素朴地直接从事实进行推论,却从不将这种推论整体所依据的一般意义基础当作主题,也从不研究意义基础所固有的强有力的结构先天。只有揭示出处在我们的当下之中、而后是处于每个过去或将来的历史的当下本身之中的一般结构,并且总地说来,只有对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整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历史时间的揭示,就其整个本质一般结构方面的揭示——只有这样一种揭示,才使真正的、理解的历史学、明晰的、在本真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学成为可能。这是具体的历史先天,它包纳了所有那些在已经历史地生成和正在生成之中的存在者,或者说,它包纳了所有那些在其本质存在中作为传统和传承者的存在者。”(Hua VI, 381)这里的论述表明:历史研究应当是对意义基础的本质结构的发生和展开的研究。这是理解胡塞尔后期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现象学的一个关节点。
其次是胡塞尔在这里提出的“历史”概念:“历史从一开始就无非是原初意义构成(Sinnbildung)和意义积淀(Sinnsedimentierung)之相互并存和相互交织的活的运动。不论什么东西根据经验作为历史事实被想起,或是由历史学家作为过去的事实而表明出来,它们必然具有自己的内意义结构(innere Sinnesstruktur)”(HuaVI, 380)。这个历史的“内意义结构”也可以导出对胡塞尔“内历史(innereGeschichte)”概念的理解:“如果通常的事实历史学一般,以及尤其是最近以来现实而普全地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学一般,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只能奠定在我们于此可称作内历史的东西的基础上,而且它本身只能奠定在普全的、历史的先天的基础上。这种意义必然会进一步导向已经暗示过的一门理性的普全目的论的最高问题。”(Hua VI,386)
最后,关于现象学历史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笔者在“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一文做了较为详细的顺利,划分了四种历史或历史研究的对象,以及通达这些对象的现象学还原方法。除此之外,这篇文章也以《危机》中的附录“几何学的起源”为历史现象学研究的范例讨论了胡塞尔历史哲学或历史现象学的整个思考。[15]
3.作为现象学出发点的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诸问题:
关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已经有诸多研究文献问世。这里的说明仅仅集中在《危机》语境中它与其他论题的可能关联方面。
首先,历史哲学的思考同样内在地与生活世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耿宁的研究表明:“胡塞尔在1920年前便已开始零星地运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了,但直到二十年代,这个概念在他的哲学中才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名称。”他同时也指出,在胡塞尔的《危机》中,科学的危机、历史的观念以及生活世界的问题是如何内在地结成为一个基本的论题的:“胡塞尔在二十年代仅仅犹豫不决地表露出来地思想在《危机》中则得到明确地贯彻:‘客观科学的基础在生活世界中,它作为人类成就与其他所有人类成就一样,同处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16]胡塞尔本人在《危机》中也对此有清楚的表达,它指明了一种从“科学客观性”向构造着这个客观性的“生活世界主观性”的转向要求:“至于‘客观上真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它是更高层次上的构成物,是建立在前科学的经验和思维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经验与思维的有效性成就之上的。只有彻底地回问(Zurückfragen)这种主观性,而且是回问以所有前科学的和科学的方式最终使一切世界有效性连同其内容得以成立的主观性,并且回问理性成就的内容与方式,只有这样一种回问才能使客观真理成为可理解的,才能达到世界的最终存在意义。因而自在第一性的东西并不是处于其无疑的不言而喻性中的世界之存在,而且不应单纯地提问;什么东西客观地属于世界;相反,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是主观性,而且是作为朴素地预先给定这个世界存在、然后将它合理化的主观性,或者同样可以说,将它客观化的主观性。”(Hua VI, 70)可以看出,转向生活世界的要求是与向超越论主观性做超越论转向的要求内在相一致的。
在1937年1月6日致其弗莱堡的学生、后来成为重要的社会哲学家的阿尔弗雷德·舒茨的信中,胡塞尔写道:“如果您而后写信告诉我,我的序曲(Ouverture)[即当时发表了的《危机》的第一、二部分]、我的那些方法的前释以及前释性的批判对您产生了何种作用,那么我会非常高兴。接续的部分[即当时未发表的《危机》的第三部分和其他计划发表的部分]会继续这些工作,并且会越来越多地指明必然的问题:‘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对作为巨大科学论题的‘生活世界’的发现,以及对彻底观点改变的动机引发:现象学的还原。而后从这个绝对的观点来看所有素朴-客观科学(实证科学)的真正问题域。但愿我这个年纪的精力还能够做到在三、四篇论文中来展开它。”(书信IV,493-494)胡塞尔在这里首先指出了生活世界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可能性,其次也指出了生活世界研究与现象学还原的关系,最后还指出了生活世界现象学研究对科学发展史研究和历史目的论研究的可能意义。
关于生活世界与胡塞尔批评的客观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黑尔德曾在他为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撰写的“编者导言”的第七节“客观主义批判与生活世界”中做出清晰的说明:“胡塞尔在他后期著作标题中所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就是一种意义的丧失,这种意义丧失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一个绝然的、与主体无关的世界——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将会放弃人的责任。”而“随着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科学’的提出,对那种随哲学与科学的产生而一同被原创立的、无成见的世界认识之要求具体地得到了满足。……胡塞尔认为,随着科学意向在无成见的世界认识基础上的原创立,一种对整个人类都有效的认识规范就会被提出。……在对科学的原初意向与此意向迄今的满足所做的这种历史的-现象学的比较中,人的理性的自身负责便会得到实现。”[17]在这里,从生活世界现象学到人类的自身认识和自身负责的历史目的论发展线索得到了清楚的勾画。
而关于生活世界与现象学还原的关系,耿宁在前引文章中给出了扼要的说明:“生活世界的‘素朴’本体论还不能最终被理解为本质上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最后的澄清只有在对先验主体性的反思中,在对‘普遍进行着的生活’的反思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生活中,世界作为对我们始终在流动着的当时性中存在着的、始终‘在先被给予我们的世界而成立。’(Hua VI, 148)”因此,“对这种生活的研究在方法上需要超越论的中止判断和还原,所以胡塞尔在方法上把生活世界的问题看作是一条通向超越论还原的道路。”[18]易言之,生活世界是现象学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这与胡塞尔强调现象学是世界观哲学,但本身不是世界观的说法是一致的。
这里最后还值得重提的是,笔者在《现象学及其效应》中还讨论过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生活世界问题域中的可能相互影响的问题。这里也需要再引克里斯多夫·雅默的合理看法:“无论如何,在十年之后,《存在与时间》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这两本书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是两部互补性的著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本,都会使对另一本的完整理解成为不可能。”[19]
四
胡塞尔的《危机》书未能如愿完成,身后留下一批相关的研究手稿。他在提纲中列出并在书信中提到的总共四部分的出版计划仅仅出版了第一部分(即《哲学》期刊上正式出版的第二部分)。而第二部分(即被胡塞尔压下修改,后来作为第三部分收入《胡塞尔全集》第六卷出版的文本)则可以被视作是基本完成的。此外,胡塞尔遗稿中有一小部分属于计划中的第三部分(即提纲中题为“将全部科学都收回到超越论哲学之统一中的观念”的第四篇章)和第四部分(即提纲中题为“哲学的不可丧失的任务:人类的自身思义”的第五篇章)的内容已被收入《胡塞尔全集》第六卷(页150-156)。
还在出版作为《危机》考证版的《胡塞尔全集》第六卷和作为《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研究手稿的《胡塞尔全集》第十三、十四、十五卷时,编者们(瓦尔特·比梅尔和耿宁)就已经预告要在胡塞尔写作《危机》期间留下的文稿中再做选择和编辑出版(Hua VI, XI)。1992年,《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补充卷》得以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九卷出版。[20]在其中得到发表的胡塞尔文稿的论题处在《危机》的语境中,时间处在1934-1937年期间。这些文稿按年代写作顺序排列出版。选编它们的目的在于,如该书编者(莱茵赫尔德·N.斯密特)所说,“对胡塞尔为《危机》的出版而在不同工作阶段所做的工作做出说明,并且对《胡塞尔全集》第六卷做出补充。”(Hua VI, 430)
--------------------------------------------------------------------------------
[①]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ua VI, hrsg. von Walter Biemel,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6, § 9. ——中译本参见:《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年。这里均简称为《危机》。
[②] 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年,页110及以后各页。
[③] 例如,狄尔泰批评胡塞尔是“真正的柏拉图!先是将变化流动的事物固定在概念中,然后再把流动这个概念补充地安插在旁边。”(参见:GS V, CXII)海德格尔认为应当将胡塞尔对待历史问题的立场称作“不可能的”(GA 20, 164 f.)。舍勒则干脆说:“胡塞尔是非历史的。”(GW VII, 330)这些批评都是针对胡塞尔在1910年的长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的反历史主义或非历史主义立场。
[④] J. Patočka,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Die Weltdes Menschen –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Walter Biemel, Phaenomenologica72,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76, S. XVI.
[⑤] 例如,王浩曾说:“哥德尔似乎不欣赏被人称作胡塞尔‘辞世之作’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般认为这部作品增加一个历史的维度,而且按梅洛-庞蒂的说法它‘暗暗放弃了本质哲学’。”参见:Hao Wang, Reflections onKurt Gödel, The MIT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87, p. 227。
[⑥]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同上书,页115。
[⑦] Wilhelm Emil Mühlmann, Geschichte der Anthropologie, Athenäum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Bonn 1968, S. 103.
[⑧] 实际上应当是4天后,即5月11日。
[⑨] 参见:《胡塞尔全集-资料》,第三部,E.胡塞尔:《E.胡塞尔书信集》(Briefwechsel),卡尔·舒曼(编),十卷本,多特雷赫特等,1994年,引文出自《书信集》第三卷,页302(以下在正文中直接标明“书信”、卷数与页码)。
[⑩]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是1933年出自当时德国纳粹术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将整个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统一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纳粹把军队和教会之外的所有政治社会机构都一体化,并将所有权利集中于希特勒一身。胡塞尔是在讥讽的意义上使用它。
[11] 参见:E. Husserl, „Die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in Philosophia I(1936), S. 77-176。现收于:Hua VI, S. 1-104. ——关于阿尔图尔·利贝尔特(Arthur Liebert)于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创办的这个《哲学》期刊以及他此前于1935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创建的“国际哲学协会”,有以下相关的三点需要说明:首先,利贝尔特原先是德国康德哲学学会主席,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由于其犹太血统,他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便从柏林流亡至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首都贝尔格莱德。(参见:Jan Patočka, „Edmund Husserl’s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c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in L’. Učník et al.(eds.), The Phenomenological Critique of Mathematis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Responsibility, Contributions to Phenomenology 76, Springer International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5, p. 17)其次,胡塞尔在此期间已经无法在德国境内出版他的著述。即使在德国之外的出版也受到来自纳粹政府的压力。1936年1月25日,帝国科学、教育和国民教化部强制要求胡塞尔退出由利贝尔特在贝尔格莱德创立的哲学组织。(参见:《胡塞尔全集-资料》(Husserliana-Dokumente),第一部,卡尔·舒曼(编):《胡塞尔年谱——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思想历程与生命历程》(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多特雷赫特等,1977年,页472——以下在正文中直接标明“年谱”与页码)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这个在贝尔格莱德创立的“国际哲学协会”当时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成员,其中的中国哲学界两位成员是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Lucius C. Porter)和张东荪(参见:Philosophia I, 1936, S. 422)。
[12] E. Husserl, „Die Krisis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inPhilosophia I (1936), S. 77.
[13] 参见:Husserl, Die Krisis der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Hua VI,a.a.O.,S. 516。此外还可以参见胡塞尔在另一处的与此相一致的说法:在1937年致德国作家、哲学家鲁道夫·潘维兹的信中,胡塞尔对《危机》的总体结构介绍说,“在第一部分中仅仅是前说明、唤醒,在第二、三部分是对绝对基地的发现,而后在最后一部分是对实证科学的本质构形的真正意义的澄清。”(书信VII,226)
[14] 这里可以留意一点:在《危机》这两个部分中包含的对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的评述后来还影响了胡塞尔的哥廷根学生、科学思想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其《伽利略研究》(Étudesgaliléennes, Paris 1939),而柯瓦雷的思想又影响了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说。
[15] 参见笔者:“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页42-49。上述四种历史研究对象和与之相应的方法分别为:“1)超越的、外在对象性的构造发生与历史,例如宇宙史、生物史、自然史、动物史,它们可以用‘科学史’的名义来概括;2)内在的、反思的对象性的构造发生与历史等等,例如心灵史、世界观史、宗教思想史、文化史,它们可以用维柯的‘新科学’的名义来概括。——这两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可以通过超越论还原的方法而得到区分;3)观念对象性的构造发生与历史,例如几何学的观念史、零的历史、廉耻观的历史、善的历史等等;4)实在对象性的构造发生与历史,例如物的历史、桌子的历史、吗啡的历史。——这两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可以通过本质还原的方法而得到区分。”(同上书,页44)
[16] 关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问题思考的历史与实质内容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参见耿宁(Iso Kern)写于1979年的文章:“生活世界:作为客观科学的基础以及作为普遍真理问题与存在问题”,倪梁康译,载于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2012年,页59-71,此处两段引文出自该书页59、页64。
[17] 黑尔德(Klaus Held):“导言”,倪梁康译,载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05年,页40、页45。
[18] 耿宁:“生活世界:作为客观科学的基础以及作为普遍真理问题与存在问题”,同上书,页71。
[19] Christoph Jamme, „Überrationalismusgegen Irrationalismus. Husserls Sicht der mythischen Lebenswelt“, in ChristophJamme/Otto Pöggeler (Hrsg.),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 Zum 50. TodestagEdmund Husserls,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 68.
[20]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n Wissenschaften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 Texte aus demNachlass 1934-1937, Hua XXIX,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en Haag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