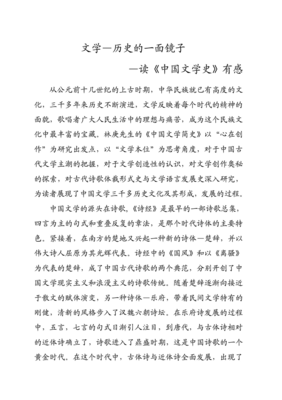
《中国文学1949—1989》是一本由洪子诚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0-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1949—1989》精选点评:
●洪子诚先生这本小书,寸铁杀人,点到即止。
●挺好看的书,克制却又通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语言感觉很浓的翻译腔。
●-_-意外的好看。有別於其他文學史整理,這本沒有把作家作品單獨拎出,而是從50年代(1949-1989)大陸文學整體印象切入,先提出觀點,然後再用同期的作者和作品來論證。主要描述的是某種文學現象出現和變遷的過程,追尋這種現象產生的背景,而非個別作家作品的深入剖析。
●正月十二,工作在迫近,还是要看书…签名本!
●此书为洪子诚老师《中国当代文学概说》2010年修订版的再版,非新书。
●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这本书可以当做一张地图一个一个的作家去打卡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一):一部朴素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和其他的一些宏大叙事的文学史比起来,这本小册子显得朴素的多,没有过多的理论阐述,没有过多的专业理论概念,娓娓道来,朴实无华。
这本书是根据作者在东京大学任教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原来的目的是让学生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的文学情况有一些比较完整地概括性地了解。后来讲稿变成了书稿,而书稿 也就成为作者洪子诚先生研究当代文学史的方法、观念和智慧的体现了。
在《前言:分期与方法》中,作者指出:“基于对2O世纪中国文学基本状况的这一理解,即对某种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性质及其演变的把握,我把 5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为‘当代文学’。”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选择了“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 的分期方法。当然分期的主要是时间,而文学的整体发展是无法分期的。正是从文学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文学的发展显得是有传承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那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文学?作者选择了后者,他在谈论一些文学思潮时,比较注意其产生的源流,以及产生时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已经这种思潮产生以后发生的一些流变。这样的论述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让读者不但了解这些文学现象,而且明了了这些文学现象是为什么产生的,是如何发展的。
作者在《前言:分期与方法》中指出:“在上编除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形态外,主要是了解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在下编,主要是考察控制削弱之后,在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作家心理素质和文化性格的状态,以及这种性格、心理状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作者是比较侧重从“文学——社会”的角度进行文学史处理。这是作者研究文学史的主要方法,也是对文学史感兴趣的读者的最大的方法论启示。
在这本书中,作者采用朴实的手法,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当代史,以历史整体意识和历史还原的方法,将这段长达三十年(1949——1989)的中国文学当代史的概貌比较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二):当代文学黄金四十年
中国近代,中国当代和中国现代的划分,曾经是一个必须细致搞清楚的问题。在历史书中有明确说明,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也是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点。所以,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而中国现代史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19年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这标志者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国当代史,则是1949年至今。
洪子诚的《中国文学1949-1989》很显然是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
除开这些文学之外的讨论,关于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其实,在我的眼里,是颇多经典好作品诞生的黄金时期。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各种思潮,各种改革创新,当代文学已没有这些年里创造出的那种朴素而沉浸到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学气质。——而这种文学精神,也正是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精神上最为缺乏的东西。
可以说,现代化初期的艰难困苦再一次以文学特有的姿态塑造出一代代人的精神,而这接地气的精神恰恰是传统的生命延续。因而让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更喜欢这当代文学初期三十年的文学。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三):在历史语境下不断摸索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1949——1989》是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修订版的再版,是由洪子诚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的讲稿整理而成。
由于原课程主要面向对这部分内容了解不多的学生,仅简略又较完整地介绍了1949到1989这四十年中国大陆文学的状况,尤其注意总结各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因此这本小书可以当作普及读本,很适合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这本小书虽然只回顾了四十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但这四十年恰恰是历史潮流波涛汹涌的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都随之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作家们面对着不断出现的时代冲突和超乎预料的思想挑战,因而中国当代文学也几经变革,不断摸索着创作道路。
洪子诚先生抓住了这四十年中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总结了不同历史阶段对文学潮流变革、作家及其作品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绘制出中国当代文学在这四十年中的发展脉络。
毋庸置疑,在50-70年代这段时期内,政治宣传需求主导了文学创作的方向和空间,大大限制了文学创作的范围,作品集中在特定领域内,以至于一些在思想艺术的其他方向探索的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反倒被当成了“非主流”文学。
不过,这些“非主流”文学仍然努力尝试去探讨现实生活问题,或借助历史题材、通过象征性的手法批判现实社会问题,反映作者们所经历的挫折、受到的思想冲击以及对社会和自身的思考,甚至包括对社会中已出现的“崩溃”征象的感知和对新出路的探索。
到了80年代,除了先前几十年主导文学创作的政治因素逐渐放宽之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于是,80年代成了作者们在文学逐渐解冻后全力尝试新方向的阶段,促使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现代派”、“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不同文学创作潮流的出现。随着“性别意识”的增强,女作家和关注女性的作品也有增多,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也变得多元化,女性的情感也得到了更多表达。
经历了50-70年代的束缚后,80年代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新的文学创作类型,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释放出新的活力,作家们逐渐恢复了创作热情,同时也急于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大展身手。
这些多元化的作品是作家们创作活力的体现,更反映了时代的痕迹。50-70年代改变了许多作家的人生轨迹,有些人搁笔多年最终沉寂,另一些人则在饱经沧桑后于中年之际重拾纸笔,记下自己对时代的感触、思索和对未来的展望,重新向文化土壤中寻根溯源、激发灵感、定位自我。这些影响都反馈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相应作品中。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创作有成功之处也必然有自身的局限性。在分析每一阶段、每个流派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时,除了简明扼要地点明作品特点之外,洪子诚也会直言其不足。洪子诚的点评,把握住了作者的个性思想和作品的精髓,诚恳、客观,对理解这些作者和作品很有指导作用。
要在15万字的篇幅内梳理建国后四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脉络实属不易,洪子诚的这本《中国文学1949——1989》确实提纲挈领,把握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和生存状态,展现了这四十年中文学创作被制度限制、打破限制后再重建的过程。
洪子诚曾在序言中说道:“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有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说很多的话”,这本篇幅紧凑的《中国文学1949——1989》言简意赅、抓住要害、点评得当,值得一读再读。
2020.12.20雾凇
《中国文学1949—1989》读后感(四):贴着当代历史进行零度抒写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文学史专著中的经典,这不需我来重复。它的好处,也自有学术角度的公正评说。然而,好归好,这样一部四百来页的教材,并不适合每个人阅读。它作为教材的面面俱到,论述的不动声色,是一种业内人士方能细细品咂出滋味的博雅贯通。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写给大学文科师生们研读的,那么《中国文学1949-1989》这本小书,则是每个读者都可一览的通识之作。虽然看上去讲的是文学,然而这四十年的社会文化事件,因为历史的特殊性,又有哪一件和文学没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呢。《中国文学1949-1989》不仅仅是一部“极简版”的当代文学史,仿佛看过那本大书之后,这本小书便无甚精义了。这本小书有着完全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是给大家划知识点,而是用朴实的语言,用每个人都可以听懂的方式,把四十年围绕文学发生的史、事,讲透彻,讲清楚。作者自己说:“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有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说很多的话;有时,说得越多就越糊涂,还会把点滴的‘意思’稀释得不见踪影。” 之所以能讲清楚,可能跟它的前身是针对外国受众的讲稿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洪子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他需要面向许多对20世纪中国的面貌缺乏整体印象或知识积累的日本学生讲述当代文学,许多中国读者心领神会、感同身受的前理解,于他们不起作用。这本书努力做到简而明:简有时容易流于浅,那就成了儿童读物,有时容易流于晦,那就成了抽象总结。在这本书里,简明是由博返约的举重若轻。 作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巨大转变过程之中,“现代化”是物质和精神领域的总题目,文学也由此形成某种统一的特征,所以应该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现代化中的“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如何经过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的“改造”,成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学规范,则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问题。左翼文学在30年代已占居重要地位,在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区域,它演变为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及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流通、阅读的规则等),在50年代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更凭借政治控制的力量,而成为中国大陆文学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到了80年代,这种一元的文学格局发生了变化,而展现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发展前景。 在作者这样的大局观视野下展开讲述,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辨。以往针对这段时间的文学历史,许多论述者要么全盘肯定,要么盲目否定,这些肯定和否定本身都不是历史的把握,而是个人价值观念的主观投射,是意识形态立场或个人审美阅读的观念表达并以论代史。很少有作者能贴着历史来讲述历史。贴着历史讲述,并非不知道什么是意识形态,也并非没有个人审美阅读,甚至他需要更深厚的审美阅读功力,才能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把历史的骨骼洗刷出来。赞美或批判或许是有压力的,但其得出赞美或批判本身,却是容易的。现在许多人都在为想尽办法找出新颖的赞美之词或竭尽全力发出晦藏支离的批评之词而努力,所以文学史著作越写越长越晦涩而且不尽如人意。这本小书,却以平淡的笔墨、零度写作的控制力,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冷静从容的抒写。 书的上编主要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左翼革命文学规范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作者努力追寻这故事里的种种情节产生的渊源与经历的变数。在这里文学思想甚至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因为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实紧迫问题,尤其是社会政治实践问题,所作出的回答。他有关文艺的论述,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政治含意,就是直接地为着某种政治目的。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讨论文艺问题要从分析“客观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他所列举的“现在的事实”中,包括当时的抗日战争、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文艺运动对战争和革命的配合。毛泽东是十分确定地从政治任务的要求上来看待文学的。这三十年,文学的就是政治的,政治的也是文学的。当作者把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政策这个核心理路抓住并梳理清楚后,那么随之而来的三十年的“规范与控制”,作家群体的嬗变、矛盾与冲突,主流作品的状况与总体风格,以及游离于这一主潮之外的非主流文学作品的面貌,也就势如破竹地获得了清晰的解释与呈现。许多文学史作者,要么不敢抓,要么抓不住。 书的下编揭示了这种支配地位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变化,以及中国作家“重建”多元的文学格局所作的艰苦努力。下编的切入点,又与上编有所不同,作者主要考察控制削弱之后,在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作家心理素质和文化性格的状态,以及这种性格、心理状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当中国当代作家开始获得比较“自由”的写作环境,来表达他们自身、他们对世界的体验时,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的潜在特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但他们这方面的弱点,也得到彰显。作者认为,这种情况,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既让人欣喜又叫人忧虑的现状和前景。有些人以为,这一时期的“自由”创作是摆脱了历史束缚的新篇章,急着与过去划清界限,但作者冷静地诊断出了这一释放背后历史无形的影响。因为,人本身越是抗拒,越是追求释放,就越是受到促使他追求释放的那一对境的反作用力,抗拒本身就是被对境赋予的形状。在这一点上,作者比那些吹嘘当代文学高度的人,更为清醒。 陈平原认为这本小书做到了禅宗所说的“寸铁杀人”,就是欣赏作者的“单刀直入”。观点的“棱角”,是作者真诚、认真、朴实的体现。洪子诚在贴着当代历史进行零度抒写的时候,真正做到了点到即止。许多人都仿佛懂得“即止”,但他们点不到,仿佛驾驶着概念的碰碰车在词语的游乐场碰来碰去,碰完一圈,文章结束,感觉什么都说了,就是抓不住痛点。点到,实在不易。
本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