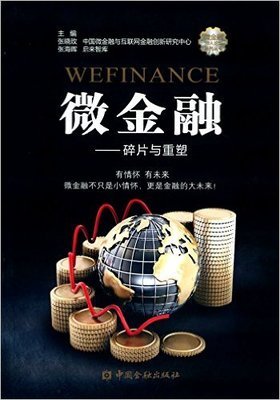
《人论》是一本由(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2.40,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论》精选点评:
●难以想象这本书当年的影响有多大
●没有理论框架,但适用于任何观念
●历史那一章是看得最通顺的。
●家藏80年代书籍
●高二读的,印象特深
●。。。
●文化哲学和人类学角度,“符号”串线。卡西尔也是个有野心的哲学家,或者说是,怀着一种宽容的心态、宏广的视角来研究,力图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包含在“符号”的统一与和谐里。
●两个字:符号!
●这种风格确实不喜欢。
●小学时似懂非懂的看过,起初只是被封面所吸引,现在连大抵内容也记不清了,只是怀念无忧无虑读书的日子。我还需要再翻出来重新看看一看。
《人论》读后感(一):人论
人是什么?这也算是人类的终极命题了,无数哲学家思想家下过定义,但总是偏于一方,无法完全概括,估计这也是个无解的问题。 作者认为人是符号化的生物,用本书的前五章进行定义,而后的七章则从历史、艺术等各方面进行进一步阐述。可是对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荒诞的,读者完全可以自己评价感悟,个人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
《人论》读后感(二):旧书偶购记
那日(2017/4/3)在古城消食兼闲逛,见路边小摊乱七八糟的铺了半地旧书,意外的见到几乎全新的查老译《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集)和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花二十元购下。《人论》这个版本我曾有三本,第一本自费购于北大校园,是我涉足符号学的入门教材。第二本是在武大时,在一朋友宿舍书架上看到,不由取下翻了几页,那朋友马上表示赠送之意。昨晚看到此书蒙着灰尘躺在地上无助的望我,想着并不深奥的内容和生动流畅的译笔,想起出版当年在我们这批学子间引发的轰动,心不由难受,还是把它领回家吧。
《人论》读后感(三):看看这本书吧!
我本科的时候,花了两年时间把《人论》这本书抄了一遍,笔记本还保存着。我那时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喜欢上语言学。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在生存斗争,将知识与经验以符号的方式留存下来,还不断以层累的方式加添进去。这一符号建构行为甚至反过来影响人之为人的属性。我今天大概是这样是这样认识这本书。师弟师妹们要是跟我唠叨哲学,我一般都不说话,宁愿装傻,那个时期已经过了。我从来不说自己看过卡西尔、弗洛伊德、荣格,只说自己抄写过。说实在话,卡西尔记得非常清,精神分析还是不太懂,但是那几个本子没舍得丢。
卡西尔很看得起语言,我后来选择了学习语言学,越走越偏,竟然去学民族语。哎,伤心人一声长叹,自以为满腹经纶还遭人鄙视,于是学会不说话。想起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的最后一句话。
稀里糊涂看了几本哲学书,谈了一个女朋友直到现在,无悔了。
除了甘阳译得太差,这本书就是极品。
《人论》读后感(四):卡西尔论神话与宗教
下篇才是《人论》的精华。卡西尔在下篇首章,即第六章《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中为整个下篇做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说明:
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 正是这种劳作(work),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个纽带不是一种实体的纽带,如在经院哲学中所想象和形容的那样,而是一种功能的纽带。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活动的无数形态和表现之后去寻找的,正是言语、神话、艺术、宗教的这种基本功能。而且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必须力图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源。
卡西尔试图用他的“文化现象学”方法来剖析人类文明的各个向度,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即是神话与宗教。神话和宗教似乎有别于通常的理性思维,它们究竟是另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还是区别于理性的思维方式?
寻求实在是神话和科学的共同出发点,原始人对于神话的相信,如同我们对于科学的相信。但经验思维关注的是感觉经验的不变特征,神话则感知观相学特征。根据前者,世界以自然为基底,后者则将秩序颠倒过来,用“人类经验的初级形式”——情绪,去涂抹自然。恰如涂尔干的洞见,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卡西尔认为这两种思维至少同样好,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用“关于知识和真理的理论范式观点”去评判神话感知和神话想象。
神话是“我”与世界浑然未分时期的产物,而对象思维则产生于主体性的建立之后。在物我不分的浑然状态中,原始人的生命观是“综合的”,而科学对实在的把握则依赖分离和系统化的方法。但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遵从理性——神话的情感基质仍然至少是“合理”的。在情感统一性和逻辑法则的二分(实践活动/理论活动)之下还有一个更低的“交感”(sympathetic)层次。
卡西尔反对柏格森,认为神话本就是潜在的宗教,二者的起源并非截然有别。
在作为“生命的社会”的自然中,人并没有显要的地位,死亡也没有自然法则所赋予的必然性。生命的不朽导致了“祖先崇拜”,斯宾塞认为“祖先崇拜”正是宗教的第一源泉和开端。原始人对死后生命的信仰建立在与死者精神的交往的普遍信仰之上。于是将对宗教来源的追溯止步于其对神灵的恐惧是不够的,毕竟原始人的生活总是受到未知危险的威胁。况且生命的坚固性、生命的不可征服这样的信念给予原始人的力量足以抵御这种心理倾向,原始人通过严格履行巫术仪式和宗教仪式来捍卫这些信念。
根据穆雷的观点,“奥林匹斯的征服”标志着人的个体性意识的觉醒,从此人看待自然及自身在自然中地位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弗雷泽采纳和发展了施莱尔马赫“宗教产生于对神的绝对依赖感”的观点,认为人在巫术仪式的参与中扭转了原始的观念:不再单纯地服从自然力量,而是通过成为自然场景中的活动者,开始相信自然活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行为,相信自己调节和控制自然的能力。
弗雷泽将巫术归结于理论活动或科学活动的产物,是人好奇心的结果。卡西尔则认为巫术的出现是由于的确好奇的原始人却没能破解事物真正的原因,转而迫使自己满足于虚构的原因。宗教没有理论目的,而是伦理理想的表达。弗雷泽区分了“模仿巫术”(imitative magic)与“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但在卡西尔看来,交感无疑是更为基础的根源:包含人在内的自然之中的一切事物之间有一个使之统一的纽带。
在人格神之前,神祇以功能神的形态出现(再之前则是瞬息神:原始人类每次将“超自然”力量临时归属于神祇以平复内心的不安)。功能神导源于劳动分工的事实,也因此受限于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当这些神祇不再因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特定的劳动分工而存在,而是因其本身而存在时,祂们就成了人格神,其名称也就具有了符号意义。人们在从事巫术的历程中所经历的对待自身态度的转变促成了人格神的诞生。
巫术在与宗教的共处中逐渐丧失了基础,宗教则从最原始的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之粗糙素材中提取新品质——对生活的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中变得成熟。“禁忌”概念的发展反映了宗教的转变。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这个词包括了宗教和道德的全部领域,杰文斯把禁忌说成是某种绝对命令(纯粹形式),先天地把某些事情说成是危险的,尽管事实常常并非如此。触犯禁忌的行为本身被禁止而不论其动机。凭借辨识和个体化的过程,神灵的领域与不洁或危险的领域得以区分开来,也使宗教进入一个成熟的形态提供了契机。禁忌有了理由,而不再是任意的划分。到了《旧约》,唯一具有宗教意义和尊严的纯洁是且仅是心灵的纯洁。
禁忌体系强加给人无数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它们完全是消极的,因为支配禁忌体系的是恐惧。然而禁忌体系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不可或缺,于是宗教从被动服从中发掘出激励和追求的力量,从而将禁忌体系的消极性转化为积极的人类自由和理想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