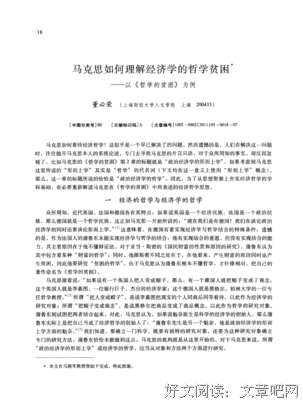
《哲学的贫困》是一本由马克思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0.54,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哲学的贫困》精选点评:
●正如凯恩斯通论的结尾,统治世界的不是物质,而是思想。蒲鲁东先生的原著没看过,但可以肯定内容是贫困的人的思想。而马克思此书名为哲学的贫困,内容是因为哲学的无用,统治思想的不正确,才导致社会的分裂,无产阶级数量的不断增多和生活上的不断水深火热,(明显的辩证唯物主义)明显体现出二人思想的差距。 一句话,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它。 读书人都在观察世界和了解自己,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和改造自己。
●人家蒲鲁东跟你不是一个阶级
●:无
●认真啃过的马哲经典
●语言犀利,有理有据
●妄图用绝对理性去构建经济、法律、社会制度进而建成理想社会的努力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所有的真理都要从从历史的哲学中获得,而不是依靠哲学的历史和理性的辩证法。
●前文艺青年马克思黑人的水平!
●打五星是因为最高只能打五星
●啥时候你能好好说话了我就给你五星
●政资研读书会18.10.27。不建议马克思主义初学者读这本,很容易晕(时而直接批评蒲鲁东,时而反讽,时而引用李嘉图……)读了《资本论》再来读应该会好很多,可作为补充。读完这本,准备暂时放下政治经济学,除非课程或社团必要。事实证明,我一直没有进入政经的语境,这不是适合我的路子,周荻说的对啊,重要的是现实问题,所以爱看什么看什么,能接受什么看什么。界限还是有,不过划界是为了越界,标签镣铐全走开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一):为什么我要给五星,一个富有爱心的马克思
刚开始看的时候,发现马克思的天才性在通篇都是显露出来的,当看到前面,我就觉得这本书可以给五星了,可是中间我在犹豫,是否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我毕竟没有看过蒲鲁东的作品,但是当我看见附录的几篇文章,尤其是关于自由贸易的那篇演讲说辞,我被马克思打动了,一个富有爱心,正义的马克思,而且论据也富有充分理由,举例鲜明和贴切,很棒的一部作品!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二):原来豆瓣也有五毛
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原来豆瓣也有五毛
看了《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原来豆瓣也有五毛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三):短評
5.4下完。馬克思與唯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決裂。馬克思這本書帶給了無產階級者一個科學並具有歷史實踐證明的新觀點,那就歷史唯物主義,而馬克思估計歷史唯物主義認定,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無產階級需要通過革命來取得勝利。這本書受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影響比較深,此時的馬克思還沒有誕生他的具有科學性歷史性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但是這本書給無產階級帶來了新的理論依據,他徹底的反駁了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和他的本質上還屬於唯心主義的自由主義精神,給無產階級革命帶來了新火種。
一讀哲學相關的書就頭疼,尤其是讀古典哲學,尤其是讀叔本華那套理論,句句都可以批判。
馬克思在為無產階級尋找方向的同時忍受著肉體與心靈的迫害,他沒有收入,孩子幾個是因為營養不良而死,陶淵明的獨子?就是營養不良而死,可是這是陶淵明害的,而馬克思的孩子餓死卻是無情的資本主義害死的。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四):一小塊馬克思
此書本來是為了批判蒲魯東的,正所謂不破不立,對於這一破之立,則是回到“德國人”身上,即馬克思的“初心”——黑格爾身上。
全書都是將蒲魯東的形而上的經濟學思想作為“主線”,蒲魯東本意是指出貧困相關的哲學,馬克思卻要“彎道超車”,也就是將商品變為精神——用辯證法來擊破蒲魯東的幻象。這首先是指出蒲魯東的含混不清,他只想保留好而剔除壞,把正反合之合題當作正反之外,卻從來沒有想過這不是相互隔離,而是互相包含的——壞就在善之中,正題就是上一正反之合題,無怪乎蒲魯東只曉得用平均分配來維持他的平等社會,但是他忽視了階級對抗,也忽視了這背後的“無”,而寧願倒退至行會。
從這一點看來,一小塊馬克思代表的並不是他所言的德國人,而正是法國人——德國古典哲學才是法國大革命的最寶貴成果,馬克思事實上是在社會主義(即當時由小資產階級主導的改良主義)中扮演了一小塊實在界——他是一個辯證法者,也不見得依賴於辯證法。與其說馬克思是一個哲學家,不如說是反哲學(形而上學)家,而後世的解讀或者“挖掘”始終將馬克思當成了目的論者,那恐怕也是有違初心乃至初心之初心——黑格爾左派(以馬克思為代表)本沒有把絕對精神當成歷史終結,而提出歷史終結者,必是沒有把黑格爾及其辯證法堅持到底——這種堅持就是逾越,要超越黑格爾的黑格爾,而不是像黑格爾右派(如弗朗西斯福山)那樣沉湎於“民主自由”的老舊秩序之中。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五):《哲学的贫困》中几个基本问题的简析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论战性的批判著作,他本人非常重视这部书,初稿于1847年写完后,时隔32年后他又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并指出“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虽然马克思本人对这一著作高度重视,但在我国理论界,这部著作的相关研究成果依然很少。初次学习本文我主要想简单地梳理几个基本问题:第一,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的批判对象是什么;第二,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蒲鲁东作为批判对象;第三,马克思是如何进行批判的。
《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副标题是《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很显然,马克思在本文中着重批判的就是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基本观点。这本书的全名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后来人们都习惯以副标题“贫困的哲学”作为其书名。先不谈该书的主要内容,仅从书名“贫困的哲学”本身,我们应当注意两点,一、这里的“贫困”指的是物质上的贫困,是个经济学范畴内的概念;二、“贫困的哲学”实质上就是要研究经济学的哲学。那么蒲鲁东本人及其研究成果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呢?其实在近代以来,英法德三国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都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特色,如果说英国是一个经济民族,法国是一个政治民族,那么德国就是一个哲学民族。作为法国人的蒲鲁东想要实现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这一愿望本是极好的,但是他自身却并没有实现结合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哪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蒲鲁东这种尴尬的四不像身份被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无情地揭露了出来,那么蒲鲁东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简单的来说,蒲鲁东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蒲鲁东的研究内容是脱离实际的纯粹抽象理论
从一开始蒲鲁东就偏离了正确的研究范畴,他说“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他所研究的内容是纯粹抽象的思想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自己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并且马克思在第五个说明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我们遵循蒲鲁东的假设,那么人类历史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原理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简单地说就是,蒲鲁东的“经济学”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畸形的经济逻辑学,他不考虑在真实的人类生活中各种经济概念是如何出现的,而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和所谓的“理性”将所有的历史事实都附会成符合他自己逻辑顺序的“经济理论的次序”,并将之称为自己值得夸耀的发现。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二,蒲鲁东的研究方法是拙劣的“伪辩证法”
蒲鲁东接触黑格尔哲学的时间不长,而且是1844年在巴黎同马克思的争论中,多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但由于“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他只能“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吓唬他们一下。”实际上,蒲鲁东将黑格尔哲学中精华的辩证法彻底歪曲甚至是阉割掉了,他丝毫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纯粹理性运动,只能用自己拙劣的模仿技能套用其术语,徒有其表,因而“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看起来有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实际上蒲鲁东却从未超越过最简单的“正题”和“反题”,也就是一种极其简单粗糙的二元论。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他这种低级的二元思维表现在方法论上,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把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第三,蒲鲁东的研究立场是唯心的神秘主义
内容的抽象和方法的拙劣已经决定了蒲鲁东学术理论的错误性,而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在讨论经济这么一个离不开实证与科学规律的严谨学术内容时,蒲鲁东竟然站在了唯心的神秘主义立场上,将“天命”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作为拖动他全部经济行囊前进的火车头。他甚至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天命,题目就叫“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问题的解答”。从他这个可笑的题目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学习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辩证法没学明白,倒是把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学了个十成十,并且还极富创意地制造出了叫做“社会天才”或是“普遍理性”的一种东西,使它扮演能够弥补自己逻辑上本末倒置的明显错误的修正液,因为有了“社会天才”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的万能驱动力,蒲鲁东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封建主的产生是为了达到把佃农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必要途径,这岂不荒谬至极。
从根本上来说,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名不见经传的蒲鲁东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论敌,是因为蒲鲁东的研究几乎集合了马克思所反对的一切学术错误:他脱离实际,不懂装懂,坚持唯心的神秘主义立场,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派相比,蒲鲁东简直毫无优长,因而对蒲鲁东的批判可以全面、深刻、系统地反映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概括来讲,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最主要的是使用了他的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他在第二个说明中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制造了相关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也就是说,是真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决定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则表现为经济范畴,这与蒲鲁东那种完全抽象、脱离实际的研究内容是彻底对立的。
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它使得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成为可能,而这种结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尚处于萌芽状态,它真正的成熟则体现在马克思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资本论》中,而《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大的价值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