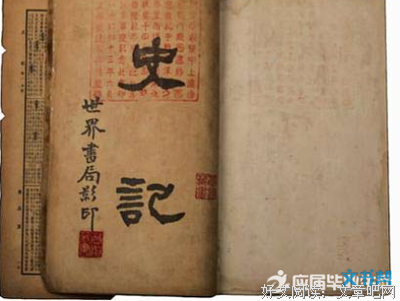
《语言的文化史》是一本由(英)伯克(Burke,P.)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言的文化史》精选点评:
●很好的书,讲的内容属于必要的知识
●当当
●a general history and some brilliant cases
●欧洲现代早期的语言革命,可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革命。
●翻译不好。网上有英文版PDF。
●共同体的语言,地方语言之间的竞争,标准化、混合、净化。引用布尔迪厄、《洁净与危险》。PNAS上也有度量语言影响力的论文...
●本書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語言與人類共同體之間的關係。地區、教派、職業、性別乃至民族,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共同體中,語言不僅是區分“他者”的工具,同樣也是確認“自我”身份的途徑。語言間的競爭同樣引人注目。曾經至高無上的拉丁語與逐漸勃興的地方語言之間、不同的地方語言之間爭奪統治地位的競爭構成了始終伴隨著近代民族國家興起過程的文化潛流,成為近代歷史進程中一條不可忽視的線索。
●这本神必得不行的书终于找到资源了! 题材很合胃口,写书的方式仍然非常得友好,然而囿于篇幅很多论点没来得及展开来讲,有些例子举的让我觉得并不是很能支持提出的观点,有点遗憾 看完了,总体感觉很好,最后也是我最关心的民族主义和语言问题也在跋里解释了,只是旧制度下不存在“语言政策”,语言未和民族挂钩之类的东西没来得及展开。。
●我们(中国人写的)这样的书太少了
●难得一见的好书,原作者与译者都非常棒
《语言的文化史》读后感(一):《语言的文化史》:中国的“学者”能这样写书就好了
这本书的名字看起来十分强悍,其实是一本通俗读物。作者没有掉书袋子,整一大堆专业术语,把大家弄得七荤八素的,然后再加入一大串的引言,草草了事。文章浅显易懂,即使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语言学了,读起来也丝毫不费力,不过总体感觉作者的考证多于见解,但有时思考问题的角度很独特,使人眼前一亮。
此书对于作者的母语着墨并不多,而是对于统治欧洲几个世纪的拉丁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的主线从拉丁语的一统天下,到诸多语种混战,再到今日欧洲语言格局的形成。
总结起来可以概括成这几句话:
1.语言的强盛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
2.语言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条件
3.语言是国家政权的统一的重要手段
4.所谓的语言政策都是统治阶级思想的反映
《语言的文化史》读后感(二):“只要你说话,我就能看清你”
在使用语言和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想到语言背后的整个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大学本科的语言学课程因为实在太过理性,被我学得一头雾水,只觉得真是没意思极了。但是这本书则展现了语言和文化乃至政治密切的关系,而且相当清楚易懂。
每一样事物都需要语言的指示,所以社会的发展就导致了语言的发展,这是最简单的词与物的关系。但是在此之上还有更多的因素被加入了进来。不同阶层提出不同的需要,底层民众开始反对拉丁语的教堂布道和法庭审判;共同体的自我发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都开始认为自己的语言才是最美和最富表现力的;而新的语言的发展又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反方向则引起了语言的纯化运动。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此书的主题——“向心力与离心力、趋同与散化、同化与抵抗、纪律与自由、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不断的冲突”。
在欧洲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却存在着如此多的语言,让中国人看起来实在是头疼至极的事情。但是其实仔细考虑,在书面语的系统之外,中国的方言的复杂和丰富也不遑多让。记得同学聚餐的时候桌上有三个浙江人,不过每个人的家乡话似乎都不能让别人完全听懂。当然,书面语上的统一则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从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学、思想价值考虑,而单单像伯克这样讲述语言的文化史——比如晚清的语体、民国的语体、地方方言、普通话的形成的影响、简化字和繁体字——这一定是相当有趣的论题。(——有没有类似的、适合非语言学专业阅读的著作?)
《语言的文化史》读后感(三):Burke的这本书也可以算作“语言共同体”
urke的这本书也可以算作“语言共同体”,翻译成汉语,需要扎实的欧洲语言、文化知识。
此次与此书一起购买的还有:
Dasha没有比对原文,而且,就是比对原文,原文里那铺天盖地各民族文字,Dasha也是看不懂的,所以别的就先不说了。感谢几位译者的翻译工作,尽管有些语句似乎是译者也没有读懂原文、也有“硬伤”:
比如第62页“如果向嫌疑犯出示书籍或刑具”,原文此页,Dasha目前在Google Books和Amazon.com上无权打开,但找到一种德语译本,德语是“Zeigte man dem Verdächtigten ein Buch oder die Folterinstrumente”;英语“book”作动词有“指控”,名词,与“刑具”并列,恐怕还是和“指控书”、“罪证”有关而与“书籍”无关。
但是,这个译本,至少能够帮助Dasha厘清欧洲语言文化的脉络。
《语言的文化史》读后感(四):语言的社会文化史
伯克此书铺陈各种语言之间的盛衰成败、同化排斥、混合纯化,似乎枯燥的理论融于丰富生动的素材,加上阅读者在祖国各地的些许成长经历,以及原有的一点儿社会语言学知识,使得这场阅读犹如轻舟过重山。笑点不需要很奇怪,也能不时捕捉到伯克的有趣和吐槽。
这是一场语言文化知识的盛宴,但犹如满汉全席,闻着香,吃不了,更兜不走。只有赞叹伯克有文化,感慨自己没文化。读的时候兴高采烈,眼花缭乱,读完了其实没剩多少,和《管锥编》、《谈艺录》之类的阅读体验一样。可你肯定觉得这书买得值了,不至于做完电子化摘抄觉得书可以扔了……
不过伯克此书原名是《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中译加了《语言的文化史》的主标题帽子,也就意味着对于这部作品的分析路数和对“communities”一词意蕴的某种取舍。我以为无论是本书的分析线索,还是“communities”的意涵,都是社会史和文化史并重的。叫做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比较妥当一些。就社会理论而言,伯克对巴赫金和埃利亚斯多有借鉴,但也颇有修正。略微提到一些布迪厄和玛丽•道格拉斯。
书里把De Certeau称为博学家,有趣。页114说德语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抽象能力偏低的语言,到18世纪莱布尼茨之后才逐渐被视为适合哲学思考,这更是长知识。
至于说校对,虽然我也懂N种方言,但不是伯克所说的欧洲各地方言,而是祖国各地方言(不过照页40、94等多处的描述,欧洲各地“方言”被调侃的方式是和我国相声一样的),所以,如果没有陈寅恪般的史语学养,没有豆瓣此书条目下dasha等资深网友的牛逼考证,还是保持小王子式的忧伤的谦卑为好,除非你具有《小王子》式的无边的自信。
以下只是随手记下自己阅读时发现的一些简单错误,是编辑就能避免的。就本书所涉知识之广博芜杂而言,中译算是不错了。
页47剑桥大学的马格德林学院(Magdalene),g不发音,应译作莫德林学院(牛津亦有),页76牛津的沃塞斯特学院(Worcester),c不发音,应译作伍斯特学院,而布拉塞诺斯学院(Brasenose)一般称作青铜鼻学院。
巴赫金的名字(Mikhail)有时是米哈伊尔,有时是米哈依拉。Justus Lipsius的名字一会儿是于斯特斯,一会儿是贾斯特斯。
页112的标靶语言(target language)一般称目标语言、对象语言或译入语。
页113的塞凡提斯通称塞万提斯,门多扎(Mendoza)通称门多萨(有中译《中华大帝国史》)。
页121的凯瑟琳•德•梅迪西,虽然对于这个家族的中译也不统一,比如美第奇、美第齐、梅迪奇等,但总得和本书后文及索引的译法保持统一才好。
页172的Giambullari,正文还是詹布拉里,同页下注却变成吉安姆布拉里。
页175介绍源自日语的“bonze”一词,说是“佛教和尚”,害我想了半天不是佛教的和尚。
页181弗兰德画家鲁本(Ruben),应该是鲁本斯(Rubens),就算原书漏了一个字母,或者真的不知道这位大师,前文和索引也都出现过鲁本斯啊。顺便说一句,全书荷兰、弗兰德、佛兰德比较混乱。
页227猛然出现彼埃尔•布尔迪,不过全书其他各处还都是比较正常的皮埃尔•布迪厄。
《语言的文化史》读后感(五):语言的共同体(修订版)
如果对方说“天王盖地虎”,你自然要答“宝塔镇河妖”。如果对方说“土豆土豆,我是萝卜”,你就要答“萝卜萝卜我是土豆”。如果对方说“雷到”,你就要答“我晕”。如果对方说“从话语权力和认同政治的角度看,这篇杰作探讨的是对待语言和语言形象的态度所构成的综合体或者系统”,你也要端着,回答说“不能不注意到作者从布拉格学派到社会历史语言学再到历史语用学,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养分。”如果对方说“顺颂夏祺”,本来你想说“此致敬礼”的,想起人家是老外,气不打一处来地改成“Yours Sincerely……”
语言不仅是用来交流信息的,语言也是用来构建共同体和实行社会区隔的。以方言来说,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大甩京片子,上海人遇到上海人不再理会身边的其他省份人说着说着就侬侬起来,都是在进行一种“认同”与“区隔”。水汪汪的文青语汇和干巴巴的学院风格彼此蔑视,上海那些海归俱乐部里,一大群中国人正八经地说着洋文,都是语言共同体的表现。
至于术语,更能体现专业群体对其他群体的隐形统治。大夫那龙飞凤舞的“医嘱”,是成心让你看不懂的,你以为那叫“感冒”,大夫写的可是“上呼吸道感染”。还记得那个笑话吧,一乡下病人急切地问大夫:“劳驾,13超怎么走?”大夫轻蔑地答:“什么13超,那是B超”。某个共同体使用的语言越是独特,它的凝聚力越强,而违反这种语言的代价也就越高。真事儿一则:某爱好诗歌的实习医生查房时在某患者病历上写:“肠音静如坟墓”,后来患者去世,家属凭这一条要告该实习医生“不专业”。
语言是势利的。西班牙人马丁•比西亚纳说:“每种语言都有三种说话的方式:学者的方式、贵族的方式和平民的方式”。还记得萧伯纳的窈窕淑女吧,卖花姑娘本来一口伦敦下层阶级的土腔,在经过语言学教授的密集培训后,上流语音外加上流衣服,那就是上流社会的入门证。我们社会的多面手经常使用“双语制”,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高级语言用于谈论高级问题,低级语言用来谈论低级问题。所以他白天在讲大词——amplification of deviance,cognitive dissonance,晚上讲小词——f--k, s--t, come on baby!
下面是言归正传: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思想的载体、认同的标识,也是民族的纽带、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彼得•伯克的这部书聚焦于“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探讨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语言的交融与竞争。基本脉络是从早期拉丁语势力的强盛,接续文艺复兴后各民族语言间的竞争,以及各民族语言的标准化和纯净化进程。伯克不愧是一流的文化史家,本书一如既往地简明有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果然大家风范。
语言的生死:且说拉丁文共同体在早期近代其实有三个相互独立的不同团体:外交共同体、文人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拉丁语是基督教世界的“世界语”,是上层贵族、文人学者、教会人士们使用的高级语言。而随着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崛起,拉丁文逐渐式微,成了濒死的语言。还记得哈代笔下的《无名的裘德》吧,一个上不了牛津的小石匠,自学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某天在酒馆里与大学生赌气,用拉丁文背了一段《尼西亚信经》。So What?从某种意义上说,裘德也是世俗观念的受害者,这个观念在说:拉丁文是高雅的、高高在上的,操拉丁文的人也该是高雅的、高高在上的——哪怕它是濒死的。
语言的霸权:一个强盛的民族,其语言也往往是强势的。无敌舰队覆灭前的西班牙,曾经使西班牙语成为欧洲各国外交官的必备语种,而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国,也使法语风头无两,在所有大使的房间里,法语的使用几乎和他们的母语一样频繁。此外,一个民族语言的兴起,也往往伴随着对另一个民族语言的屠杀,往好的方向理解是“归化”,向差的方向理解是“灭绝”。在中世纪,普罗旺斯语是一种重要文学语言,产生了骑士文学中抒情叙事诗的大量杰作,可是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在法语共同体和意大利语共同体的强势压迫下,操普罗旺斯语的人士为了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169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要“根除爱尔兰语”,也就是盖尔语,此后绵延不绝的爱尔兰独立运动,都将语言的复兴视为重要一步。我们耳熟能详的都德的《最后一课》,更把民族语言强调到痛彻刻骨的程度。
语言的规范:语言规范化往往是国策,起码是上流社会和文人们的愿望,暗含着文化权力的斗争。科学院的出现一开始并不是管理“科学”,而常常是制定语法规范,佛罗伦萨(1582)、巴黎(1635)、马德里(1713)、哥本哈根(1742)、里斯本(1779)、莫斯科(1783)、斯德哥尔摩(1786),科学院都要负责词典的编撰,西班牙科学院的座右铭迄今仍然是:“净化、稳定、辉煌”。规范化也是一门生意,印刷商、出版商、科学院院士、小学教员和教士们,借此谋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有趣的是,既然有“净化语言”的力量,也就有“杂化语言”的力量,文人的推陈出新、低层的俚语上侵、还有外来语汇的融入,都使语言处于不断的更新状态。
杂感又一则:中国的大学生受四六级考试的压迫已经很多年了。很少有人知道,英语曾经很弱势,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就说过:“在16世纪,除了英国人,没有人会期待别人说英语,即使是最完美的大使(大使应该掌握七门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土耳其语)。” 是19世纪英国的强大和20世纪美国的繁荣把英语推上世界通用语的宝座。期望在未来的“世界语言文化史”中,有中文崛起的一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