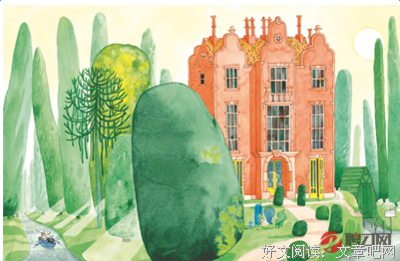
《论好客》是一本由雅克•德里达 / 安娜•杜弗勒芒特尔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好客》精选点评:
●如果我们不断地以分形的方式去追求意义,在词语的裂隙中我们必然会发现更多更大的世界。但如果一定有一个最后,那肯定是所有意义的矛盾与湮灭,或者是归于绝对的“一”。解构主义者,恐怖如斯。
●色情网站被谁禁止
●第一次接解构主义,很不适应德里达的新颖观观点和神奇视角,但字字珠玑,言之凿凿
●老实说现在的水平看这本书难免有些一知半解,可是可以多读一些此类哲学书,对其他事物的思考提供了别样的角度,哲学更多的是由点及面的思考方式。
●实话说,时常云里雾里
●讲康德和列维纳斯的部分还没想通。
●后期经典,译文勉强过关,建议读英译本。
●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o゚;哈哈哈哈
●看到评论区很多吐槽版式的我就放心了,这个书的排版虽然很好很好翻页,但是影响阅读体验... //唔...很多句子我都觉得挺造作的,各种定语堆砌在一块儿,我也不明白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大意能get到,从苏格拉底和俄狄浦斯切入外人问题也挺好玩的,我觉得不错~
●面对双重的不可能性:让人看到,并且让她失明和死去的父亲看到她的眼泪的不可能性,留给安提戈涅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杀。但是,她还想在父亲被埋葬的地方,在那个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因为忒修斯已经起誓)自杀。因为,这种不可测定性并不来自某种位相公式,它受誓言保护,是俄狄浦斯自己要求的,实际上是他制定和强加的。他律、欲望和他人法则,在其中这最后一个,他人,是的,最后一个,最先的俄狄浦斯(黑格尔)和最后的俄狄浦斯(尼采)一样,不仅仅求死,而且不想让亲人找到,逃避葬礼,自己飘逝,并且让哀悼他的本身的哀悼对亲人们成为神秘莫测的事情。钓雪按:德里达与康德和列维纳斯与苏格拉底和索福克勒斯,关于德与柏,参照德里达《柏拉图的药》、柏拉图《智者》、麦科米斯基《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Zuckert的《后现代柏拉图》等
《论好客》读后感(一):非書評
《论好客》读后感(二):我来到你的门前
德里达指出,好客具有两面性:
无条件的好客要求你对所有来到你的家门口的人,包括那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都敞开大门。但是,一旦他们侵入你的家,有可能你反而会受到排挤,被剥夺了在你的领地上的主宰权。当你不再是家的主人的时候,如何能够尽主人之道,表现好客之风?
因此,好客往往是有前提的:它要标定主人的权力,即对领地的所有权;同时也要标定客人的异者身份:他是你的国度的外国人、陌生人。只有遵守了你的领地原则的人,才能够成为你的客人。
人与人之间如此,社区与社区之间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
但这似乎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客”了:对客人进行甄别,是一种排斥性的行为,有些人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士。
quot;But pure or unconditioned hospitality does not consist in such an invitation (“I invite you, I welcome you into my home, on the condition that you adapt to the laws and norms of my territory, according to my language, tradition, memory, and so on”). Pure and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itself, opens or is in advance open to someone who is neither expected nor invited, to whomever arrives as an absolutely foreign visitor, as a new arrival, nonidentifiable and unforeseeable, in short, wholly other."
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从来不邀请小朋友来家里。理由是家里不该太嘈杂。小朋友却大多数有点吵。为了防止需要不断维护秩序的丑陋场景出现,干脆谁也不请。并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从来不让我到别的小朋友家做客。
没有读德里达之前,早已知道我的父母绝对不算好客的家长。读了,反而觉得他们和那些邀请小朋友来到家里玩,然后这里不让摸那里不让碰的爸爸妈妈相比,还不错呢。
而且,我也的确不是个好的客人。碰到熟人就反客为主,打蛇上棍,要求点菜看碟求娱乐等等,不被轰出去,只能感谢邀请我的主人好客慷慨善良又大度。
《论好客》读后感(三):随机摘录
外人的问题:外人的来到 德里达
战争内在于逻各斯。
(申辩中的苏格拉底)他要求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可以要求尊重的外人来对待。
差异,一种微妙有时又是在外人和绝对他人之间难以把握的差异。
绝对好客的规则要求与权利的好客,与作为权利的法律或公平决裂。公平的好客与法律的好客决裂,不是谴责它或对立于它,相反,把它置于不断进展的运动之中;但是,绝对好客的规则与法律的好客奇特的迥然不同,犹之乎公正相异于法律,不过,它们又如此接近而且在事实上不可分离。
好客是否在于向来者提问?
或者,好客始于没有问题的接待——问题和名字的双重消除?
苏格拉底于是以法律的面目如此说话,以法律的拟人声音。拟人法就是面容,面具,并且可以说首先是声音,是戴有面具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需要注视。
外人准备和外人说话。不认识,不知其来历和身份,不知他从何而来,又去何处。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在人与神之间。这难道不总是绝对来者的处境吗?
底比斯的无知造成俄狄浦斯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他不可宽恕的乱伦和杀父之罪。
如何去宽恕一个不可宽恕的人?宽恕他什么?
正是这座无知、无愿的城市的法律把俄狄浦斯推向罪恶,推向杀父和乱伦的境地,正是这种法律产生了凌驾法律之上的人。这实际上没有什么奇怪的。在有外人和好客的问题的地方,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杀父的场景。
在今天,关于好客的反思使我们假定,存在一种严格的划定界限的可能性,这种界限存在于家庭和非家庭之间,存在于外人和非外人之间,存在于市民和非市民之间,而首先特别存在于个人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于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之间呢。
正是这些技术能力威胁着传统的好客条件。
在传统意义上讲,没有自我对于“自家”的至高地位,就没有好客,但是因为没有有限性,也就不存在好客,这种至高地位只有通过过滤、选择,因此也就是通过排除和暴力实施才可能实现。不公平,某种不公平,甚至某种背信弃义,在好客权利一启动,就马上开始。
可见的和眼光下的祝福,这也是警察和政治所要求的。
对真实的追求是绝对无条件的。
确实,我总可以说谎(谁可以发誓和证明康德本人没有说过谎话?),但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不和他人说话,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在奠定法律和分析、揭示其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康德用欺骗的权利摧毁了任何保护自己、掩饰自己,对要求真话、招供或对公众透明进行抵抗的权利。这种要求不仅仅构建了法律和警察的本质,而且构建了国家的本质。
当纯粹道德成为法律时,警察以其名义被引到各个地方,以致被绝对内在化的警察处处都有自己的耳目。
这系于谈话的司法性,系于法律中有关好客原则的说明,好客的观念是无限的,它应该抵制法律自身——无论如何,它在要求法律之处超越法律。
(康德式的主人)把客人当做“人”。
不好客 德里达
好客的矛盾不可调和地以普通的个别性把法律和多样性对立起来。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是一种法规的简单分散,而是一种由划分和分化程序规定的被结构化了的多样性,或者说,一些以不同方式安排其历史和人文地理的法规规定的多样性。
悲剧,这是一种命运的悲剧,因为这个矛盾的对立双方并不对称。这里存在一种奇怪的等级。绝对的法规高于诸种法规。因此,绝对的法规是不合法的,是违规的,外在于具体法规,就像异样的法规,超越了诸种法规的法规,外在于法规的法规。
法规,而是一些书面法规。总之,它们在此只是为了统制和规定它们自己的堕落。漫长迂回的时间流逝,它们将等待我们。这些书面法规让我们想起安提戈涅为埋葬兄弟需要触犯的那些法律。
这是阿伦特那天的回答:除了语言之外,她不再感到自己是德国人。语言似乎成了归属的剩余,我们总是要回归于它。但是,事情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语言是归属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的话,那么,语言也是一种剥夺的经验,是不可缩减的前占有。
语言,因为与自我一起迁移,它抵抗一切不固定性。它是最少非流动性的东西,是保持稳固而又可携带条件,所有活动性中最活动的纯粹体。
(俄狄浦斯)就这样剥夺了她们的哀悼,强迫她们对哀悼进行哀悼。我们知道礼物的更加慷慨并更加有毒的形式吗?
如何为葬礼哭泣?如何为不能举行葬礼而哭泣?如何进行对哀悼的哀悼?而且一旦丧礼结束后又如何去面对别的事情?对丧礼的悲伤是无尽的吗?不可能旺季可能的丧礼吗?
这就是安提戈涅用眼泪为之哭泣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问题,因为问题是不哭的,但这或许是所有问题的起源。这是一个外人——女外人——的问题。谁不曾见过这样的眼泪?
在这两难之中我们不停地徘徊。一方面,无条件的好客超越了权利和义务限定。这二者总是相互败坏,而且不可避免,总是如此。
论邀请 杜弗勒芒特尔
这就是要接近话语围绕着它而被安排的沉默,这是诗歌有时候发现的并且在言谈或书写的活动中总是不被揭示的沉默。如果黑夜的某一部分铭记在语言中,那它也就是抹消语言的时刻。
言语的黑暗一面,我们可称之为纠缠。
尼采坚持认为:“哲学家需要双重的倾听——就像人们得到双重视觉的礼物——也就是说,最灵敏的耳朵。”尼采的事业所要求的正是这种对于语言“肉体”的关注:“啊,人,啊,超人,你们要注意,对你微妙的耳朵说话——那深沉的午夜在说什么?”我们应该学会感知几乎听不到的东西。因为,尼采补充道:“不能通过体验经验进入的东西,人们就没有听到它的耳朵。让我们设想这涉及一种第一次谈论新经验次序的新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非常单纯的现象:人们完全没有听到作者说什么,人们会产生错觉:认为在什么都听不到的地方,也就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惊恐?惊恐这个词,若仅仅要指使人惊奇,就显得太武断了。
话语于是可能偏离了它的进程,从而开启了一段空白的对话。我要向这种勇气致敬,当惊奇在某一时刻把理性变成客人时,这种勇气带来的哲学言语使我们脱离理性以主人自居其中的那些精神居所。
在对黑夜的共同归属中分辨光明,对我来说,也是由德里达的反思所开辟的道理之一。
索福克勒斯笔下的神话人物安提戈涅,她之所以吸引了我们,是因为她是质朴的人。“她是属于有爱而不是仇恨的人”,巴多卡说,但是,这种爱不是基督的爱,而是“重视作为诸神部分的黑夜部分的,与人类命运格格不入的爱”。
异在对立的不是临近,而是邻近的另外一种形象。
在传环游戏中,只有在歌声中传环的真理才成其为真理,这是发现真理的运动,是命名这种真理的印迹。关键不是规定、解释和理解,而是在这种对抗中发现标志着问题的领地,以根据所思对象进行衡量、确定。
无条件的好客威胁着一个已经通过分割责任获得公开使权力专制化的途径的社会。
在希伯来语中,“创造时间”等同于“邀请”。
“阿伦特似乎不能设想疯狂可以寓居于语言……阿伦特不那么坚定的回答似乎要保留对绝对恶进行救赎的可能性”<<<德里达
一旦走向边际的过程开始,德里达看到一块新土地在他面前展开,作为疯狂本身的场所的语言。
阿伦特护卫的语言的秘密、内在的现实,就是她所谓的“不可替代的”的母语,在自身中隐藏着非理性、创伤和仇恨。
德里达问:“那作为正义的纯粹好客法规是否要求我们打开超越家庭的好客?”但是拒绝家庭(以及它在其中延续的整个结构,市民社会、国家和民族),就是肯定纯粹好客的不可能性。因此,应该从这个悖论出发来思考好客。他最后总结说:“这是在欧洲进行的所有论战的空间。”
但是,从“大屠杀”以来,誓言还可能存在吗?
当人的存在被剥夺——不是从住所,也不是从他的家里,而是从把他和内在相连的东西那里——人的存在会变成什么?
“如果我们不能鼓励向动物实施好客,那我们排除的也是诸神。”
“在某些国家中,人们接待的外人就是将来的神。”德里达补充道,“但是,应该继续前进,并向着死亡思考好客。不存在没有记忆的好客。不过,那不回忆死者和要死者的记忆不是记忆。不准备侍奉死者和幽灵的好客是什么呢?”
“漂流的地方是没有幽灵的。幽灵出没于没有他的地方,他回到人们驱逐他的地方。”
我们在哀悼的固定模式中,或许已经忘记了这种作为好客、祭献的邀请运动,这种要求知道一点我们人性的运动。
《论好客》读后感(四):别样的思考
别样的思考
——读德里达:《论好客》
我读过什么,我没读过什么,这些都不重要,我的阅读与德里达研究专家相比显然不足,而与履行义务的被动读者相比又绰绰有余。我之所以在开头强调我阅读的业余爱好者态度,首先是因为不想预先设立种种法则,束缚自己的手脚;其次是为了不败坏自己的兴致,把写作当成任务。不存在所谓的读后,事实上,阅读,就是写作。
事实上规则一直存在。首要的第一条便在于思考的位置,“为了思考,你必须占据一个不可思考的位置。”我们知道,在收在《立场》中的一次通信中,德里达谈到了哲学的党派性。在一个如此的文本出现列宁的话语多少让人惊奇,我不愿做更多的分析,让我们保持这种惊奇和异质感,来开始“在别处”的思考。
[注]误读,确实是个可怕的问题,我一直怀疑自己论述的可靠性,而事实证明我最初的阅读中把绝对好客盲目地对应于解构之正义是错误的。因此,尽管我作出了自己不专业的说明,但这绝对不是为可能的错误进行预先的辩护,而不如说,正因为作为业余爱好者的态度,我更应该对可能的错误担负起责任,如果这一责任不是无限的话。
1.外人
德里达谈论好客,很容易让人设想到他的身份。好客问题的核心是外人,在起始处他便开始强调这一点。当我们在末尾处读到关于德里达所谓“自传性的”东西时(第137-145页),很容易联想到他的身份与境遇。作为生活在殖民地犹太人的经历,作为多次被高师“不好客”地拒绝的经历,这些能在德里达关于好客地思索中留下什么痕迹?我不愿把分析的中心倾向这个方向,让我们来回忆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外人的问题。
为什么要说外人本身是问题,外人的问题本身是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最初总是倾向于把外人当作某种异质之物?让我们回忆这种惊奇感,正是这种惊奇感,迫使我们思考(第36页)。外人首先是人,关于人的定义,德里达没有再进行叙述,但从他对希腊传统中对外人的界定来看,我们能发现一些端倪。
在柏拉图那里,外人对父系逻各斯提出了问题,因此而成为战争的策划者,成为革命者,在家中发动了明显、疯狂的斗争。让我们暂时停下来,仔细观察这一分析。外人并不是从绝对的外在发动进攻,而是从内部,内在于逻各斯地发起战争。外人也是人,他仍然在逻各斯体系之内,这就是我们回到关于人最古老也就最具有说服力的定义:人是说话的、有理性的动物。
反对逻各斯却仍然处在逻各斯之内,这样的事实只能唤起这样一个想法:逻各斯本身就带有疯狂。外人看起来的疯狂和斗争性,只是低于普遍逻各斯层面的疯狂。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到关于人的另一个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斗争只能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一旦涉及相遇和共同生活,政治就出现了。
然而,这种相遇并不是纯粹偶然的,两个相互异在的存在之间的相遇,而是语言中的相遇、普遍理性中的相遇。必须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也必须认识到母语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语言/理性作为法律、规范的含义。
外人首先与法律的语言不合。(第15页)我们看到规则、法律的名字,这既是实体的,也是抽象的。外人,是作为外人的儿子(他进入逻各斯),他也是杀父的外人(他制造混乱,反对逻各斯)。外人蕴涵着打破规则的可能性——如果“家人”是直接聆听逻各斯之父亲的话,那么外人显然不遵循这一口令,他进入法律,毋宁说进入法律的文本,却意图颠覆法律。外人是客人,因为他进入了“家门”,有望成为家人,因为他可以如进入自己母语般进入另一种语言,尽管这事实上不太容易,可是这么一来他还是外人么?外人同时也是敌人,因为他给现存的秩序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有可能反客为主,成为新的主人,可是这么一来,他还能是外人么?
因此我们看到外人这个词语给我们的纠缠,他既是客人又是敌人,或者两者都不是,他总是同时带有异质和同质的特性,这种模棱两可直接导致了好客的暧昧。因为好客的核心,恰恰是主体与外人的关系——没有无外人的好客。现在我们结束对外人的讨论,来分析好客,什么是好客。
2.好客
依据好客的对象以及规则,德里达把好客分为有条件的好客和无限的、绝对的好客,联系书中第二讲的标题,我们还要加上这一项:不好客。这个三项式的出现在我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戴顶帽子,甚至可以说这是后结构主义的精华所在。
让我们回忆结构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给出的四原则之一——对立原则。这既是结构主义方法的巨大贡献,也是结构主义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运动流产的根源所在。对立是意义的根本来源,然而在这里,差异必须被标记。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如何对好客做出标记,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好客涉及的核心问题:外人概念的含义的模棱两可?
现在让我们来看,康德和列维纳斯在这一问题上分别做出了怎样的处理。通过对和平问题的反思,我们不难推测在好客问题上(关于这部分,需要对杜小真老师的导读和方向红老师的《无限好客与永久和平》作一些不规范的引用)康德把和平的核心概念好客看作有限的权利,而相反,列维纳斯则把好客视作无限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限和无限这一对经过标记的对立。
在这两个对立项的每一个之下,也存在着其不同的意义生成模式。在康德那里,通过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的对比,好客获得了法权的地位,既然是在理性法前、法下的权利,好客自然就必须接受其约束,在自然合目的性面前,必须强调好客的有限约束性,也就是说,好客必须针对客人而不是敌人,必须强调法律、法规的条件性而不是无条件性,一句话,必须强制外人成为客人。联系到政治思想,也许共和主义的权利观会更加利于说明这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大强调道德改善的康德那里,好客与“恶”尖锐对立,好客必须首先处在和平的前提之下。好客必须有安全的保障,安全如何保障?权力。国家权力,家长权力,技术权力。我无意深入涉及技术问题和应用性伦理等的讨论,只想强调这样一点,把好客作为法权的做法,本身就蕴含着堕落的危险:因为法律不是正义,法律起源的暴力蕴涵着批判的可能性。康德眼中的好客,其实就预先默认了家长制及理性主体的自我中心地位,与其说向他者无条件地开放,不如说是对他者地某种驯化。另外,作为权利的好客要求履行法律义务高于道德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康德在《论说谎的权利》中的论述如此不近人情,也是为什么康德的好客有堕向不好客的危险。
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维纳斯。显然列维纳斯对好客问题的讨论本身就基于对康德的批判。他认为康德的好客无可避免地将陷入“计算,调停和政治学。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转变成交换和贸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同时,每个人又与一切人共同存在——像物质那样,转变成交互的限制和规定”。与此相反,通过前自然状态(这点我们可以转向德里达与之共有的犹太-圣经传统)与前自然状态之后的对立,列维纳斯把好客确立为一项无限的责任。这事实上是在试图把权利式的好客拉向道德一方。这个意义上,好客就必须无条件地开放,向一切人开放,毫无保留,朝向他者的面孔。好客不应该是主人对客人施展理性的暴力,而应该是他者向自我提出的权利;与其说和平保障了好客的可能性,不如说正是因为好客,和平才有可能。
这样的论述与康德相比,让人感觉要高尚得多。然而把并非全然是绝对他者的外人当作绝对他者对待,是否已经过于偏离外人这个模糊概念?既然外人不能单独与主人、敌人相对立异取得完整的意义,列维纳斯的二项对立是否也有其缺陷?
德里达在书中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把绝对的好客与不好客单独抽出来对立考察,固然能够实现意义分明的概念界定工作,可是同时也失去了好客的本义。好客具备非常的暧昧性,这里我们必须把好客还原为一个纯粹的活动来考察。
之所以强调好客作为活动,是为了跳出主客体分立并赋予主体过分权利的思维模式。我们发现,在此前的思索中,无论是列维纳斯还是康德,都无可避免地把好客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用主人、客人的绝对分立使得二者泾渭分明。而且,尽管列维纳斯已经认识到康德的主体式思维之缺陷,他在对康德的好客进行批判、强调他者时,仍然是通过这个二元对立的颠倒来实现的。无论在主体跟客体中选择哪一端,都落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都试图让其中的一项来统御和压制另一项。
德里达别样思考的可贵,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与他解构的众多对象一样,好客也有此不可能之可能性,由于其核心处的茫茫黑夜,我们无法简单地对好客作出界定(用理性之光照亮),而必须在实际地解构中来把握它。正是在好客权利的一面即法则,和义务的一面即好客之欲望和无条件性中,德里达发现了好客的规则:自我与他人、主人和客人、个人和公共等对立双方的转换。正如我们在外人进行剖析时发现的,作为人的定义的语言也好理性也好本来就蕴涵着暴力和疯狂,以此确定的主体之两面性也就不难理解了。列维纳斯思想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过分强调好客的“纯洁性”或者绝对无条件性,如同强调在政治生活中伦理的无限性一般,是极端危险的。绝对好客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现实政治生活的有限性和可计算性(如果世界上只存在我和你,那么伦理就是一切,然而世界上不只你我二人,在无限的绝对他者前我们都是有限的个体,计算不仅可能而且必须。马丁布伯式的“你和我”,只能作为一种良善的愿望存在,而远非事实),还因为这样一来就拆解了好客和侵犯的界限,使好客趋向于无限的败坏。
如果无限的好客不能达到,那么是否我们就应该后退以承认康德式的法律规定下的好客就是好客而且是可欲的好客?德里达认为并非如此。正如法律的规定一般,权利式的好客(走向极端就是不好客)正因为其有限性,因为其潜在的家长制权力结构,父权式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可解构的,而真正的好客,就是正义,是那不可解构之物,是对不好客的每一次批判和解构的依据,也是人类必须正视的根本处境,是二项对立不能简单概括的“真实”,是永远溢出人类有限性的真正无限——但同时也不是无根基的无限性。
3.死亡、幽灵及其他
必须注意,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德里达把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死亡问题,尤其是外人的死亡问题。正是外人的死亡(从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死亡是秘密的、外在的,没有留下可能的哀悼,同时也留下了无限的哀悼,通过不确定的死亡,把作为外人的死者转化成四处出没的幽灵,把对外人的容忍——好客变成了遗嘱,永远有待签名的遗嘱,召唤,永远有待回应或重复的召唤。由于时间关系和能力问题,关于德里达的幽灵谱系学以及更多的政治哲学思想本文不再探讨,我只想着重指出,这个讲座末关于死亡和传统的反复论述,敞开了通向《友爱政治学》的大门),把好客的无限性,对有限好客的无限改进放进了政治生活中。这个幽灵,也许就是乌托邦,总在建立的同时自我拆毁,总在自己不在之处出没。
如此,如正义等政治哲学的永恒话题一般,德里达把好客也看作解构运动本身。好客永远不是拘泥于过去既存法权形式的有限存在,也不是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无条件的绝对好客,好客是路标,无路之路,是画斜线的存在,我们无法具体描述它,它总是在我们说出它的同时逃逸到无限之处,在定名之外,永远变动,其有限形式永远接受无限的引导,吸收无限的能量。这样,我们发现,好客本身就是人类的存在状况,就是人类语言的处境,看似自足,却永远离不开无限的提升——这种无限,既是无限的欲望(对无限性),也是对他人死亡的无限责任。这是无限的十字路口,永远接受牵引,忍耐内部分离之苦,却永远不曾失去方向,接受分裂的事实。
因此,通过对好客的解构,德里达让我们通过踪迹(这一踪迹,便是无限责任在好客中的残留,应该说没有列维纳斯就没有对这种踪迹的发掘,但列维纳斯在发现它的时候又一次把它置入了意义系统)追踪到西方逻各斯意义传统建构之外的“存在”,即人的处境。通过对语言自身的解构,他更加激进地(尤其与阿伦特相比),在对政治、哲学进行意义分立的“科学”研究之外,给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现象学的可能性。指责这种直面现象而不进行道德提升的现象学分析是不必要的,因为如古典政治哲学一般,德里达也强调对无限欲望的控制,同时也强调这种无限欲望对有限性的牵引和提升。(当然,也别忘了列维纳斯的“死亡现象学”:现象学不应理解成对对象现象的沉闷描述,它还有先验的维度,如对他人之死的经验,对无限之他者的经验,一种无欲望对象的欲望……)我们所有的问题因此就在于,如何确证这种提升的存在?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到《马克思的幽灵们》和《友爱的现象学》中去寻找。而正是通过对好客的解构,德里达充分展示了语言尤其是解构语言的好客本性,“大门已经敞开,欢迎你,我的客人。”
王立秋
2008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