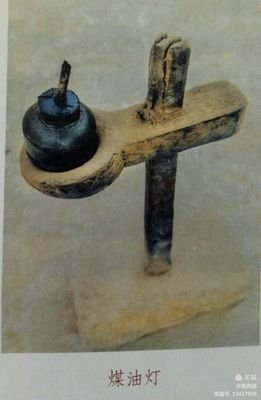
《灯下漫笔》是一本由鲁迅 周作人 胡适 许地山 林语堂等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404页图书,本书定价:16.50,页数:1995年,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灯下漫笔》精选点评:
●偶像的書一定是五星!/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 而且變了之後 還萬分喜歡
●大概率读的不是这一版,但对于一个两年没碰语文的工科生来说,这本书真难读!偶尔能看到熟悉的文字呦
●不知道如今算得上第三样时代吗?
●料,周作人浪击树人于我心。作人比树人,比是基础。存在的必要性,狭隘里说,我是不爱的,但我可服。
●有点读不进去啊 以后慢慢看
●老师要求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欢喜。
●只读了鲁迅部分……
●鲁迅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何为大师?他关心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针砭的已经不单单是时弊,而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中国人至多不过是奴隶”,看得人心头发凉。鲁迅是中国民主意识的拓荒者,他的大声疾呼“青年的使命”让人动容!
《灯下漫笔》读后感(一):一点想法
一点想法
——题记
讲起鲁迅,作为成长于社会主义光芒笼罩下的少年,很难从嘴里说出“不知道”的话。即使如此,身为反感意识形态的九零后,除了课文和被老师强制要求的几章篇目未曾品读过先生的其它作品。现在想起,有些相遇恨晚,但这之中亦有类似不幸之幸的感叹。不敢说现在自己已成熟到对先生作品可以洞幽察微,但对比过往依然过犹之而无不及。可以所谓是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好作品,难得!
改变我看法的板上之钉是先生文章的可读性,主要体现在即使时过境迁,这其中大部分音节依然适用这个社会。文中先生讲时代分为两个部分: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夸张,马上让我想起了当下,并联想到自己。文中还提出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老师说当下这时代就是所谓的“第三样时代”。老师半信半疑的语气,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感觉到了一丝对此的鄙夷,悲哀之余也窃喜,迅速引为同调。
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智慧型奴隶”的时代。因为前辈们有过不少针砭时弊的言谈,我们也接受说“这是好文章”,就以为自己亦有相差无几的思想深度。殊不知经过百年的起承转合,今时早已不同往日。
毕竟我在这世上存在时间不长,只能以“学生”这个拥有时间较长的称号来聊聊这个事。长达十二年的应试教育里老师们一边教育要独立思考一边“不允许”独立思考。哄骗我们“上了大学就好了”,可即使鲤鱼能跨过那道龙门,也会发现大学不过是我们自己虚构的乌托邦——一切如旧。不少人就这样认输了,勤勤恳恳地凑够学分,勉勉强强地拿个毕业证,然后再和大多数人一样……不鄙视认真努力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不过只想多问一句:”所以这就是你读十几年书然后期待的吗?”我不是,所以我也不太能容忍身边的大多数人甘于如此。嘿,你现在已经是暂时做稳的奴隶啊!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塑造好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像是一个弧形的陶瓷瓶 。有人告诉我们是非对错,慢慢帮我们建立世界观。一代一代的,的确,刚开始管用。因为人少,不敢二话,你如果特别,你就被孤立被指责,所以闭嘴。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然后麻痹。人们都安逸地待在陶瓷瓶最圆润的部分,即使黑暗,因为空间大,就自以为活得很自由。可是下一代人出生,层层叠加,来到了瓶子收颈的位置。后代的我们看到了瓶口射下的光,发现和瓶子圆润部分的颜色不一样。我已经看到不一样了,我还怎么能接受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黑色的。我只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在底下,你看不到光。
我有一个幻想:每一个人依旧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愿意表达(即使不表达,我希望在脑海中这个想法不要散去)。
其实我太清楚这个幻想有多么幻想,但我斗胆以我还年轻的理由做一次梦。
《灯下漫笔》读后感(二):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掀开烟波浩渺的史册,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习惯了逆来顺受,我们习惯了服从,我们习惯了用肤浅的眼光来审视周遭的一切,对待科学如此,我们从来不追究远离只是沉溺于习惯的总结,汉代的耕作技术到了清朝依旧没有较大改进,对待生活也如此,我们习惯了上位者的施令,却从不去追究上位者凭什么施令。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提出和认识是从鲁迅开始的,但是这奴性本身却是三千年文明中由来已久的。
任何存在都有其依据,国人的奴性也不例外,我们不妨准根溯源来探讨一下其由来。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古老的大河文明的发祥地。大河文明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农耕文明发达,而农耕文明的操作周期较长,强调稳定,于是便要求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管理;而另一方面,农耕文明的稳定性使得人民安土重迁,一个家族可能世代都聚居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以氏族为单位的村落,于是便必然出现了氏族内部的强调尊卑高下的等级关系。于是来自于国,来自于家的等级观念便形成了,我们也习惯了这种等级模式,在役人的同时,也役与人。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尊卑等级观念不断沉淀,不断强化,逐渐成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我认为在批判这种奴性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我们无可否认这种所谓奴性的处世哲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有学者批判到中国人只是活着,而不在意是以何种方式活着,尽管沦为牛马的境遇,也会乐意于活下去。但是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难道只有放弃生命,才是对生命的尊重?中国人一直有一套自己的哲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人很会在困境中自我安慰,把这个称为阿Q精神也罢,但正是这种精神让很多国人在困境中不抛弃从而又获得了人生的升华。
当然这种国民性也造就了我们的很多性格缺陷,比如冷漠自私。我觉得并不是我们很多人不善良,不是我们没有恻隐之心,只是我们性格上的软弱,我们习惯了被奴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都无法做到准确的把握,我们又怎敢妄图伸出一把手去帮助别人走出困窘。我们总想着等我有朝一日飞黄腾达,我一定广行善事,我觉得这种想法背后便暗含了那种我只有自己站在了食物链的顶层在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我认为,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总结是相当成熟的,但是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有些过于偏颇。诚然,中国存在贫富差距,也存在上位者的横征暴敛和下位者的麻木不仁。但是这种国民性有时也更我们带来了对待生活的随遇而安和对待理想的奋力拼搏。
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国民性正是我们华夏文明得以长期处于稳定结构的文化基础,也是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
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毕竟才是最近几百年的产物,与中华几千年文明相比,时间不过才十分之一,我们无法去判断其是否可以继续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到底是向自由而死,抑或,顺大势而生?见仁见智,我们无从去批判其选择的到道德高下。但暴动而死,负辱而生却不甚可取。
对于国民性,我们也要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国民性可以说是国人长期以来的处世哲学,在没有探索到一条新的可行的处世原则之前,不要一味去的批判逆来顺受,一味地去强调要反抗,要暴动。否则,只会导致人民迷失对于文化的认同,或变得越来越浮躁。近几年的各种社会上的暴力事件便和国民的浮躁有些许联系。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看得清的人是好的,认清自己的处境,才能去为了改变而努力;保留这份“喜欢”也
《灯下漫笔》读后感(三):文化衰落与主体性的沉沦——评析《灯下漫笔》
1、引言
爱夜的人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灯下漫笔》为我们展示一个深邃透彻的灵魂穿越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敏锐洞察力。鲁迅本着对于人生高度负责的态度与悲剧性的无畏精神,通过一层层抽丝剥茧的笔法,以及叙议结合的方式冷峻犀利的昭示了中国历史血淋淋的真相。
2、历史的证明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古人对于文章的定义,认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文以载道”——通过伦理性的教育传输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可见文学独立性与主体性的埋没,在文化中其终极定义是依附于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的附庸品。文章也是奴隶。“三千余年古国古”,被鲁迅拆穿了是一场骗人的把戏。
接下来进入对社会历史的剖析中。在对于一系列古国历史的文化解剖中,夹叙夹议,具体阐述种种杀伐屠戮、弱肉强食、兼并鲸吞、文辞粉饰的历史现实,颇有实证主义风采,并做出了如下价值判断:中国的历史只出现过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的新认知。
五四的时代是人的主体性觉醒的时代。从清朝一代热衷故纸堆的钱嘉学派到重义理轻才情流泻的桐城派古文,进而转变为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交汇、迸发生命火焰与自我个性高度标榜的狂飙五四,可以窥见人之主体性的被发掘。中国历史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被重新审视。在鲁迅的意识中,奴隶时代的原由在于统治者的杀伐血战与愚民政策。中国人骨髓当中浸润着的是集体无意识的随波逐流,在康乾盛世、文景贞观之治这样的朝代,文人学子大不用说,成日价探讨协商“和谐社会”的建立,百姓治希冀政府“给一口饭吃”,哈巴下人性的尊严摇尾乞怜,遂了停留在口腔阶段的心愿,便忙不迭的高声万岁,欢呼圣贤了;乱世之中则流离失所而辗转流窜于分崩离析之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便是离了主子后空虚惶恐的体现。“一治一乱”的历史呈周期性的历史循环。
3、人之主体性的丧失与沉沦
然而鲁迅终究没有给出文化根源的理性裁夺。奴性之根不仅最终不是简单的鲸吞杀伐,而是早在中国文化的发源之中就没有酝酿出人格的内容。作为世界级“酱缸文化”之首的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基本论述中窥探到奴性的本源。“仁者,爱人”,细细端详这个“仁”字,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不禁叹服中国的造字艺术,微妙的结集了文化的“精粹”。两个人,意味着在中国,个体的价值不是由自我来实现的,而自生命伊始就被当作一个非道德的主体,由他人(圣哲贤人一流)来对之进行后天性的改造。这就为儒家思想横行天下奠定了无坚不摧的文化功能。放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迅雷之势扎根于中国的广袤土壤,不是莫名无因的,而是早在有一人之心建立世间道德体系的孔孟时代就有了“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的论调,个体从没被当成是终极的目的,只是实现专制的、一元化“和谐”社会的手段。儒家思想与政治强权结合之后,个体的精神欲望以及正常的合乎人性的需求都可以在以“圣”为名义的指导下进行高贵的抹杀和摧残。
这种摧残放大到极限的结果是,人人毫无自尊,又不尊重他人,个体无法用尊严的有体面的形式追逐本应属于自己的生命幸福和价值权利,强权压制之下个体只能够依存社会提供的固有模式来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于是——奴隶着并享受着奴隶身份的顺民社会便形成。
有人说,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不是做一名合格的奴隶,而是成为奴隶主,恰有几分道理。但在《雷雨》的结局中,年轻一代的新生生命的一一飘逝,剩下了三位苟延残喘的人——周朴园,蘩漪与梅侍萍,呈现出一个暴君(专制黑暗的奴隶主)——疯子(妄图超越奴隶地位的疯魔人)——奴隶(顺天应命的卑微奴隶)的畸形结构,奴隶安于本分,颤颤巍巍苟活人世,疯子挑战奴隶规则,自然不免被抽筋剥骨,打入与奴隶并无二致的境地,就连奴隶主——饱受男权社会价值理念摧残而捆缚于辛酸孤苦的周朴园,实际上不也处在自由筋骨被挑断了的奴隶地位吗?可见,奴隶主的本质还是奴隶,同等的没有人性与自由。迅翁何其高明。
4、饮食文化与震慑西洋的魅力
鲁迅在文章后半段转入对“吃人”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用“吃”这个字来说明中国文化的本原自是再好不过的了。中国社会是一个漫长古老的农耕社会,与饮食文化有着同根生的联系。游牧民族长期忙于迁徙流动,无暇顾及“吃”之一字。商业社会的人民钻营为商之道,只有重农抑商的中国社会,在古老的与遍布荆棘作斗争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重实际,轻玄想”的民族特征,缺乏西方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想,“食色,性也”,缠绵于感官之上的满足,中国的一切审美文化活动也自饮食开端。于是乎“吃饭”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撮一顿”也是中国青年乐衷的习惯。耽溺于饮食,必然缺乏超越性主体精神,守着奴隶的本份度日,有一口饭吃,何苦发神经要求个性、尊严以及民主自由的精神。“吃”之一字,演化为民族的劣性,吃人的历史,记录下人性尊严沦丧的疮疤。
鲁迅提出,这“川流不息”的“山珍的海味”,这“人肉”的筵席,饮食“文明”使得本国人陶醉沉湎其中,更使得西洋人别有用心交口称赞,殊不知有的时候“文明”往往是腐朽的代名词。站在历史的枝头上,凝望旖旎繁华的江南朝廷,屡次被北方游牧所征服,便一目了然了。吃人的历史,食遍粗淡与腥膻的文化,潜台词意味着“人”不是“人”,被食之物而已,公主们可以用作苟安的城堡,宦官们可以献作慑人心魄的面首,人命可以充当瞬间即散的炮灰,然而最终还要震慑于文字的威力:如同张巡、许远般将妻女贱视为将士充饥的干粮,竟然美其名曰“男子汉大丈夫”,可见有的时候,要在中国和合“男人”、“女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必须泯灭作为“人”的代价。
5、艺术特色与总结全文
《灯下漫笔》一文思想容量丰厚,措词简约,达意传神,在犀利的理性中渗透着激切的情感:“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从个人感觉与理性判断来讲,这种口号式的宣言未必增添文章艺术价值,有些破坏文化观感,甚至未必反应作者的真实心态,仅具有特定时代的宣传价值。鲁迅说过自己的文章不是艺术,并非客套谦辞,真正的艺术是不会在迁就大众目标的心态下产生的,于是夏瑜的坟头出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小小花环。
鲁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倡艺术“为人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文化上的统治欲望。并非刻意不恭,既然严羽说过,“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是批评的真风骨,在下虽浅,却也对文化真理性有所仰望。直言以述,此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统治欲,与它提倡的“个体精神自由”相矛盾,导致了他由启蒙思想家变身“无产阶级斗士”,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的基本精神中囊括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内容,在后一时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垄断之下,消弭沉沦,国家主义大行其道,文艺沦为政治附庸的因由,便有所依循的脉络了。
第三样时代,毕竟还未开辟。
《灯下漫笔》读后感(四):《灯下漫笔》
《灯下漫笔 》鲁迅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⑺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