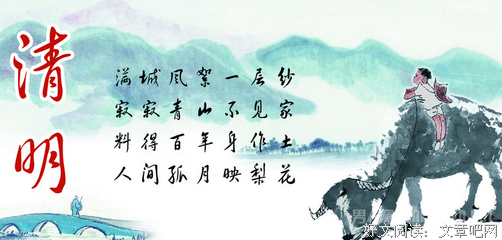
《科学史》是一本由(英) 丹皮尔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5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史》精选点评:
●图书馆√
●科学史就是一部哲学史。
●作者一方面怀有辉格史的纲领,将科学史描绘成现代科学取得合法性的过程,因此才会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而重其生物学。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科学只是人类为理解自然(或曰“实在”)的一套人造的知识体系,并不是自然或实在本身,照此推理现代科学并没有那么强的合法性。因此我认为作者对科学和科学史的态度是有互相抵牾之处的。
●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好些··
●按需。
●很多地方有非常明显的辉格史倾向,并且论述缺乏哲学上的深度。比起20世纪的其他科学史研究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当然和日常教科书相比还是可以了。最后安利一波张卜天老师翻译的各类科学史专著。
●要有一定的学识基础才能啃下它
●马哲课作业
●20世纪著名科学史家W.C.丹皮尔的著作,大致翻完了,兴趣不大。
●科学史最最经典的教材性读物,虽然有些观点未免看上去落伍了,对初学者而言,亦足矣。
《科学史》读后感(一):人类的对美的感受是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的
“由星体而来的一条光线,物理学可从它的遥远的发源地一直追寻到它对感光神经的效应,但是,当意识领悟到它的明亮、色彩和感受到它的美的时候,视觉的感觉及对美的认识肯定是存在着的,然而它们却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物理的。
“我们就会知道,物理科学按照它固有的本性和基本的定义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体系,不论它有多么伟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它永远不可能反映存在的整体。”“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我们需要领悟一个神圣的奥秘……”
这些话真的很触动人心
《科学史》读后感(二):读丹皮尔《科学史》
观察和实验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裁判者。
《科学史》让我从一种意义上的蒙昧无知,展开了眼界,对身处的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清醒客观的认识,和引起我对它的思考。
有许多大量科普性的客观知识的介绍,这一点本身首先就让我受益匪浅,广泛的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天体学、等许多具体的知识及其发展的脉络就让此书价值不菲。这些知识是破除愚昧、宗教中的利器;这些也是一个理性大厦的砖石基础。
我觉得对自己很大的一个影响或感化便是,自己以前看《西方哲学史》时,比较隔,既没有文学诗词上的美感,灵性享受,也难清明理性的信服它们;相比之下,《科学史》则是与我很贴的哲学。它的发展史其实也是逐渐摧毁一些虚妄或想当然哲学或“形而上学”哲学以及宗教愚昧的历史,它更让我信服,更亲近。它有很好的一致与逻辑性,而不是哲学中一些不入流的流派一旦遇到困难便用一种诡辩的伎俩使你陷入糊涂,抓不住问题,以为是自己太笨了。类似的是宗教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时,无法在其体系中解释的也可能使出一些先知或天启式的大招震慑住无知无助的我,使我怀疑自己而无条件屈服于它们。
而科学便打开了一道曙光,让自己把握自己与外在的科学、理性、实验、分析,这本书里提到的这些及这两年的科研让我比较深的信服它。
这本《科学史》太适合于现在的自己,或者说自己为何没有早点读它?
原来世界的科学及哲学在70年前就已经发展到这种广度和深度。广深到我自感自己是处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无知的人,虽然自己已经年快30,且是浙大工学博士了。读了这本书,就让自己觉得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与精神的大大不足,无论是为学还是为自己知识与理性都该狠狠的补充一番,我想捷径之一便是再精读本书一遍,之后找相关的书看一下,前两天在豆瓣上看上了两本书,虽然目前无闲暇读之,但可以留着名目,日后再读。《什么事数学》,这本书好似以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方式逐渐全面较深入地介绍着数学及其魅力,让我痛感国外可以将数学也可以写的如此迷人!然后便是费曼的《费曼物理学讲义》了,喜欢费曼是因为看他的书觉得他是很有趣而有学问的人,更兼他讲义目录里面许多条目都是在《科学史》中提到的,我倒很想一探究竟,同时也想对身处的这个世界有这种这方面的深刻认识,丹皮尔本身也是教授物理的。故《科学史》里面许多物理学的内容。
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化学、哲学、充斥于本书始末,自己这个文艺小青年就像投身于陌生的知识海洋,虽然这些年来一知半解的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难得一部科学史将他们重新给我简要的梳理了一遍,让我认知世界与自我。
对我软性上的影响,自然是科学的精神与实验精神。许多哲学于我总感觉很隔,然而科学却是逻辑明白,条理清晰地容易让人信服的。若相信哲学的话,我便是坚信科学实验的哲学。而这种理性的方式正是我东方文化急缺的一环,想想现在的我们还自得于四大发明的古代不前,西方的科学都已层出不穷的发展到光电,以太,介子,量子时代了,让人猛醒!
自我感觉最好的该是,兼具东方陶渊明的智慧自然人生,及西方的科学理性,方可成为凯恩斯般奥德赛式的人物。
而这两方面的兼修便是我人生之主路。
《科学史》读后感(三):科学是思想的浪漫-----丹皮尔《科学史》
在我看过的科学史著作中,往往充满了事实与发现的堆积,让人觉得科学的演进就像一个个待发现的任务,等着某个时候出来某一个留在历史上的人物来完成,这样的认识对于科学与其发展来说显然是浅薄与有失偏颇的,丹皮尔的《科学史》则完全不同,虽然受限于写作的年代和作者的知识,严格说来它只是一部欧洲科学史,但其中所弥漫的科学思想是其他著作中所难以见到的。
许多在今天被公认的定理,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都被我们写在了书本上,包括那些发现它们的伟大的名字。或许很多人会觉得人类花费了上千年才理解地球是宇宙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星球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时很多人或许也会认为与以往那些蒙昧年代的科学相比起来,与那个法拉第花费二十年才发现电磁感应的时代比起来,今天的科学技术无疑更加高端与有魅力的多,无疑对人类的发展会产生比以往大的多的影响,但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在我看来科学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那些被发现的定理,而是那些发现它们的探索与思想的精神。
总会有这样的时代,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已经够多了,当炼金术师和占星学家在中世纪游走,当教会宣布掌握了宇宙的真理,当牛顿时代物理学家们以为发现了所有关乎物理的规则,但事实往往给出更有力的反驳,这样的反驳告诉我们,科学所追求的真理永远不是绝对的,它总会需要存在于某种假设和条件之下才能被称作真理,即便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定律也需要设定宇宙空间是三维的,而科学精神,就是承认这个不存在绝对与永恒的事实,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的探索思考与发现,在观测与实验的基础上,给出合理的推论。
这大概也是科学与其他学说有着本质不同的地方,就像科学与神学的不同,并不在于其是否理性与具有逻辑,神学一样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与研究,并且神学上的这种努力也曾经一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神学总是会给你一个特定的不能去质疑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理性的研究也都会逃不出它的控制范围,一个神学体系是可以完全完美无缺没有丝毫破绽的,它用一个事实上人类尚且不能认识到的东西作为其根本,你接受了其后的任何一个理论也就要接受它全盘的体系。然而科学,总是会质疑一切,探究一切,抱着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与猜想,从不桎梏自身,从不给自己任何不可改变的限定,它看起来毫无信仰,其实它本身便从来是一种不弱于宗教信仰的伟大精神。
然而科学总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希腊的天文学家想要证明星星月亮的运行轨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没有大帆船的时代,地球是圆的永远只能是一个猜测,这时候就会有无数的谣言与谬误穿着神话的外衣前来,为了某些非单纯的企图或只是单纯的无知而去宣扬那些愚昧的思想,这时候又总会有那些智慧和执着的人们,即便他们逃脱不了时代的桎梏,也总会比时代走的更远一些,足以在一段时间内指引后人前进的脚步。科学真正的魅力便在于此,你需要置身于那个年代里去感受,在科学黯淡的年份里,再伟大的思想所创造的也比不上今天的一个零头,但那个零头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却是与所有留在历史上与正在发生着的伟大发现中所含的精神相一致的。
可以这么说,即便未来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人类的文明倒退了,就像希腊文明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基米德等等众多希腊学者的著作全都遗失,世界再度走进了蒙昧,即便在今天的某个时候人类世界又一次遭受这样的苦难,只要人类好奇与探索的本能长存,只要那些智慧的头脑不断绝,只要科学精神的光芒不熄灭,我们总会再度创造出非凡的文明来。
在丹皮尔的笔下,科学的发展就像一部浪漫史,那些先贤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思考与疑惑,付出无数艰辛和生命在时代中挣扎着只是努力想要看的更远一点。丹皮尔的《科学史》,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一切大师级的通史著作一样,其经典之处便在于抓住了隐藏在历史事实之后的思想与文化流动的脉络,而不仅仅是如现今依然流行的某些教科书一般把大部分眼光都聚焦在一小部分物质的变动上。人类历史由人类谱写,它的轨迹总是灵动与活泼的,那些历史事实背后的东西尤其充满魅力~
《科学史》读后感(四):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读书报告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我在接受基础和中等教育的过程中轻而易举获得的一个概念。它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什么是科学?”乍看之下是一个幼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科学不就是科学本身么”!科学就是科学,除此之外没有,也不需要更多的解释,科学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然而这样的回答不免显得武断。细究起来,“科学”这个概念是潜移默化地形成于我所经历的生活中的。从小开始学习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大学里开始学习的社会科学,无不在默默地在我的意识中建构起“科学”的概念。但是若要给科学下一个定义,我却不知从何说起。
任何的概念都不是从定义开始的,定义只是对于某一事物的不完全总结;同样,概念也不会被某一定义所终结,概念源于历史的积累和发展。而我们脑中的“科学”必然与我们的经历相联系,和其他人对于“科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那么作为人类共同分享的概念——“科学”,要弄清楚它的所指,就得梳理它的渊源。这就是我阅读W.C.丹皮尔的《科学史》的初衷。
起源——在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
若要说“科学起源于巫术”,对许多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Paradox”。科学与巫术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确确实实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概念。“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这样的标语或许仍留在许多中国人的院落里、墙壁上、脑海中。但是,像钻木取火这样的科学规律,对于数万年前的原始人来说更像是一种巫术。
“巫术要假定自然界中是有规律的,人通过适当的行为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去控制自然界,因此,从这个观点看来,巫术是一种冒牌的自然法则体系。……这样的巫术,有时由于巧合,好像也是灵验的,但是,失败的次数要更多一些;这是巫师在是失望的信徒面前,就有不可自保的危险。失望的信徒们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并且转而去讨好荒野中捉摸不定的精灵——神或魔鬼,希望这些精灵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过渡到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P16)
巫术的襁褓中裹着科学和宗教,科学与宗教同宗同源。从这一点,我嗅到了科学的气味——因果关系。在随后的历史中,科学靠不断修正的因果关系来将自己与巫术、宗教区分开来。
知识——实用科学的基础
我有一个即将上小学的表弟,每次电脑玩游戏被大人要求休息片刻时,都会被告知要过十分钟才能再玩。于是焦躁不安的他每过几十秒就会问我“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在他的意识里,时间的流逝缺少度量的标准。人类的最初也是如此,但他们可没有我的表弟那么有幸,有一个人会在分针走过两格后提醒他时间到了。在科学鸿蒙之始,生产生活的迫切需求让“常识性知识和工艺知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P18)成为实用科学的起源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纷纷划定了自己的度量衡、历法等,与生活相关的实用科学——几何学、天文学、医学、农学、数学等学科有了雏形。目前,这些学科的前沿研究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敬而远之,但对它们的初衷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划定统一的标准与规范,这些规范是人们在把握周遭万事万物时的凭藉。
到底什么是万物的基础?
约摸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对于泰勒斯的介绍是他提出“水是万物的本质”,从历史中单单抽出这一个拗口的名字和荒诞的论断不免让人难懂,其实对于万物本质的探索是人类从古至今不懈的追求,至今没有得到终极的答案。到底万物是由单一的元素构成,还是水、空气和火?抑或是像毕达哥拉斯所认为的那样“数就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可以说,就是存在由之构成的物质。”(P33)
古希腊的不同学派有着五花八门的解释,留下了许多对我而言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等。他们的理论如同今日我们在中学所学习的道尔顿的原子模型,还是高等物理中所阐释的质子、中子、夸克等构成物质的基础粒子,其实在都是在回答这同一个问题。书中下面一段话我认为很好地体现了人类科学的诉求,也许,科学就产生于人类想要通过理性来把握自然、宇宙与自身的这一种占有欲。
“自然界背后的实在究竟是一种在本质上同人类心灵所见的自然界相似的东西呢,还是一种对人和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巨大机器呢?一座山实际上是披着树木的绿袍、戴着永不融化的雪帽的一堆岩石呢,还是实质上是一批没有人的品质的小质点、一批不知何故能使人类心灵产生形式和色彩幻觉的小质点的集合体呢?”(P41)
既然对于有形的物质的分解至今都没有尽头,那么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探究万物的基础。柏拉图的“理式”学说中提出的涵盖世上形形色色物体的物体之普遍的类“universal class”存在于心灵当中,只有心灵才有把握住它们的本质,我认为用通俗的话讲出来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马,白的、黑的、的卢、汗血,而它们都只是我们心中“马”这一原型的映射。“自然界的一切对象都处在经常变化的状态,只有类型是实实在在的和一成不变的。”(P46)
这些讨论,看似不免有些脱离了我们心目中“科学”的范畴,但其实在古希腊“科学”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充分的建构,科学是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是在中世纪之后才逐步走向了现代的精确化和数学化。
不证自明的公理需不需要证明?
演绎和归纳这两种逻辑方法在科学中被广泛运用。尤其是在几何学范畴中,我们往往要通过某个公理或定理去推导一些结论。几何学最初是一种实用科学,从土地测量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在埃及的土地测量经验中,人们得到了某些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后来经过欧几里得的总结,将之定为公理。例如“任意一点到另一点都可以画直线”,“一条有限线段可以无限延长”,“凡直角都彼此相等”……
显然,上述公理是我们从身边周遭的世界中归纳出来的,同时也被我们无数次地演绎,并发现它们与我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验相符合。但是非欧几何却提供给我们另一个审视的角度,从这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些公理却也逃不出“所有渡鸦都是黑色”的渡鸦悖论。
“普通观察给人的暗示是有某种空间。心灵接受了这种暗示,给这种理想的空间下了定义。这种理想的空间其实完全是所观察到的空间在人们心目中的样子。”(P58)而现代我们所接触到的科学,已经不仅仅在研究“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一空间”,科学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来,却又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所谓的公理变成了仅在某种假设条件中存在的推论,尽管这一假设是那么的合乎我们感官所告诉我们的世界,但这些公理却变得不再那么不证自明,只是“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却盲目地接受了这种简单的直觉观念,把几何学的公理看做不证自明的事实”(P58)罢了。
让宗教归上帝,科学归理性
当我们回首望去,“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与我们这个世纪。”(P115)站在我们现代科学的山峰上看,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之间是一道绵延数百年的科学谷地,那就是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不可否认,在中世纪科学亦有发展,但是却极为缓慢,在某些观念上亦有倒退。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在那一时期,宗教思想统治了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留给科学的空间十分逼仄。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的经院哲学试图给予科学一个神学上的解释,尽管他做到了,但强扭的瓜不甜。
而科学的重新兴旺则在于文艺复兴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让人们的思维回归古希腊的理性,宗教改革将中世纪宗教的条条框框打破,使人们能够因信称义,使得宗教不再支配生活的全部,将信仰与世俗生活之间划了一条界限。
于是达•芬奇、哥白尼、哈维、开普勒、培根、伽利略、笛卡尔……这些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各个方面的建树终于为科学的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他们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数学分析的方法,将科学从哲学的分支中引领出来,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科学真正的起源。
上帝掷骰子吗?
现代科学似乎可以把握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的成因,这给我们一种错觉,似乎一切现象都可以用一种物理学上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这种机械自然观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即便对于一部分科学家来说这样的机械论也是他们简化工作的方式。毋庸置疑,这种简化是便捷的,但又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每当一个现象能用物理学的术语,如物质、力、能,或其他当时流行的概念表达的时候,生物学学家就往往认为他们找到了最后的解释,而物理学家却知道解释的困难至此方才开始。”(P492)
建立在这样“由A必然导出B”的基础上,科学不断地扩大我们对于自然界现象的知识和我们对于我们用来解释现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的了解,它替人类的心灵建立了宏伟的大厦,而且这些科学的大厦是如此的恢宏和精巧,以至于在上一代人看来,似乎它下方的基础是无比正确的实在。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座大厦当初的设计师牛顿就曾说过:“自然哲学(物理学)的任务,是从现象中求论证……从结果中求原因,知道我们求得其最初的原因为止。但这个最初的原因肯定不是机械的。”
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对牛顿这句结论加以说明:我们现在都知道,宇宙始于几百亿年前宇宙奇点的一次大爆炸,大爆炸之后的一切现象都可以由大爆炸所带来的能量和物质来进行解释。但是,大爆炸又是如何而来?我们现在的宇宙是大爆炸的结果,但是大爆炸本身作为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在现代科学对于电子、波群以及作用量子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肯定不是机械的概念,但是我们又不情愿抛弃这几百年来我们用来解释自然界结构卓有成效的机械论,因为在机械论的范围内,科学可以继续扩大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更深入地了解和洞察自然现象之间惊人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也许眼前的困难将被客服,物理学家将制定出一种新的原子模型,可以暂时满足我们的心灵。但明白易懂的机械论终将失败,而我们仍将面对着那个可怕的奥秘,就是所谓实在。”(P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