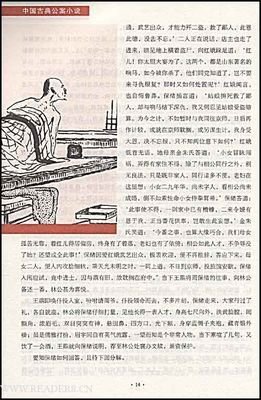
《从黄昏起飞》是一本由羽戈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黄昏起飞》精选点评:
●也许对于羽戈来说这本书凝结了太多青涩,但是对于我,这种真实的青春和痛感正是迫使我成长的动力。比起新作里的圆滑(非贬义),更喜欢这时候的羽戈。
●“枭声文丛”
●算不上佳作的杂文集,但“不可再版”之命运却与文章内涵意蕴相衬,令人哑然,还是多加一星吧。
●羽戈早期的文字。 大多数写作者都有掉书袋的毛病,羽戈痕迹比较明显。
●少年狂
●密涅瓦的猫头鹰从黄昏起飞
●图投入不oijoiuoiuj90
●后面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品读的金庸我不是很喜欢,另外,大爱那篇尼采《偶像的黄昏》的评注“从黄昏起飞”。相比于现在,当年羽戈前辈的文笔真的还欠些火候,不过,也还是极好的
●知道羽戈,是在无意中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关于萨特和加缪的文章,将爱和正义对立起来,灵魂的撕裂和拷问简直要把人逼疯。得空也会看看他的博文,对此人印象甚好。从黄昏起飞,这本书好像也是几经坎坷才得出版。
●不晦涩 很难得
《从黄昏起飞》读后感(一):文人论政
羽戈本质上是个文艺青年(虽然学的是法学),却偏偏要谈论历史、政治,真是个悲剧。
他的“论皮诺切特--正义之前”试图解决一个令自由派尴尬的话题——皮诺切特用暴力手段拯救了资本主义,并得到了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的大力支持。谴责?赞美?
【
“智利奇迹”之奇妙,或者说偶然,正在于构成了一道色彩鲜明的选择题:政治自由+经济专制,经济自由+政治专制——何者为优?何者更实用,有助于将一个一穷二白的传统国家送上高歌猛进的康庄大道?这里缺乏另外两个选项:政治与经济皆不自由,那是最坏的;政治与经济皆能自由,那是最好的。两头茫茫皆不见,既不能奔向天堂,亦不愿跌入地狱,在此利害交织的人间世,人们该如何权衡?
由此引出了我的一个论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建构,还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都不能一锅煮,最好将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它们乃是自由主义的任督二脉,或者比作一辆牌号为“自由主义”的马车的两个轮子,任何一方掉链子,都会影响车子的行进。只是在某些时候,你必须瘸一条腿,蜀道难,行路难,可终究得往前走,哪怕鹅行鸭步,缓慢如蜗牛。
我与友人讨论智利这一道选择题,将选项形象化为:
一、阿连德的方案:饿肚子,但可以骂娘,乃至骂总统的娘;
二、皮诺切特的方案:趋向丰衣足食,但不准骂娘,即便腹诽,亦不准;
我们依据自己的思想经验与人生阅历,一致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应以第二种方案为最佳,风险最小。毕竟,饿死事大,骂娘事小。肚皮开始闹革命,脑袋有气无力,哪里还有工夫骂娘呢?
皮诺切特的治理术,击中了人性最柔软的伤口,从而使自由主义内部的辩证法具有了普世性的意义:
经济自由未必是政治自由的充分条件,却一定是必要条件;
经济自由未必能直接导向政治自由,但缺乏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断然不能长治久安。
】
杰出的文人本应该有一颗对人民困苦敏感的心灵。
在皮诺切特和弗里德曼的治理下,“高达30%的失业率(1982年)”,工薪阶层“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1988年)“。
羽戈说这是趋向丰衣足食,是经济自由。可谓没有良心。
这只是财产的自由而已。所以它需要皮诺切特的暴力保护,它需要把”骂娘,即便腹诽“的人都装进麻袋扔进大海。
羽戈又说经济自由一定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可谓没有脑子。
既没良心,又没脑子。
.S ”猫眼看人“抗议羽戈污蔑皮诺切特大人。
《从黄昏起飞》读后感(二):(转一篇张培鸿大律师的书评)沉重与逍遥——兼谈羽戈《从黄昏起飞》
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思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一种半信半疑的生活,一种闪烁其辞的写作和一种心领神会的阅读,并将这样的状态当成了应然,甚至必然。慢慢地,我们甚至忘记了隐形的镣铐,不明白我们的喉咙,其实是一座敞开的坟墓。我们最多不过是在一种假想的空间里,体验自由的高潮。
这个尴尬的现实,即使八零后一代也不得幸免。
最初被网络文字震撼,是看到王怡的文章。王怡出生于1973年,那时候是关天茶舍的版主,他的时评、政论和电影笔记一起风行一时。后来开始看到羽戈,是在他接替王怡主持关天的时候。
想要准确地评论《从黄昏起飞》是不容易的,五辑内容分别围绕五个不同的主题:从学术到娱乐,从政治到哲学,从鲁迅到李敖,从电影到诗歌,从童话(武侠据说是成人的童话)到情色,羽戈在多个领域间游刃有余,在思想与生活的深处书写自由,或许还应该加上他的专业——法理与宪政。
总体来说,这些文章更偏向于学术体,即便在评论时事和描绘江湖,也有明显的论文痕迹,这使得文章读起来比较吃力,在鲜活的个案和事例中,夹杂着大量的术语,而句式也有着德语的特点,严谨、规范、多长句。
我斗胆断言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尽管不一定是他的自觉。透过互联网表达异见,赢得公众(网民)的认同,然后由虚拟的比特空间现身传统媒体寻求话语权,是当下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羽戈称为公共意见分子)不约而同的选择。然而,这个趋势不久就被精于舆论管制的力量捕捉到,从浩如烟海的信息管道中筛选出来予以围剿,以致于最终连网络都无法容身。比如王怡,只好使用儿子的名字发表文章。
羽戈没有儿子,所以他巧妙地将自己包裹在学术的辞藻和表达的圈套中,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扑腾。要想对他封而杀之,势必先要读懂文字背面的剑锋所指,这本身已属不易,到要禀报上司实施制裁,更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只得作罢。而他的读者,仿佛人手一把万能钥匙,不难窥见内里的玄机,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正是思考的代价,即便狡猾如李敖,不也说过我们要做战士不做烈士这样的话吗。
而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
2006年年底,王怡和朱学勤有过一段对话,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往往轻易地为某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背书,从而失掉自己批判的武器。
从近的来说,早年台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批判威权体制,把自己的立场锁定在国民党的对手一边,而当民进党取得政权,出现大量贪腐的时候,自由主义者遂失去对自身价值的把握和身份认同,四顾茫然。
在《从黄昏起飞》中,我最喜欢的两篇文章是《论德沃金和麦金农之争》和《哈维尔二题》,可以从中看出羽戈的犹豫和思考。在《哈维尔二题》中,羽戈借昆德拉(昆德拉借托马斯)之口,不无深意地发出“签名,还是不签名”的感叹。诚然,昆德拉的迷茫,是所有单纯以批判作武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其说这是托马斯的迷茫,不如说是昆德拉的迷茫;与其说是昆德拉的迷茫,不如说是羽戈的迷茫。当他们警惕一股裹挟着崇高道义而来的洪流,坦率地说出“不”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们勇敢,反而说这是懦夫;而当他们为一种纯粹的个体性的自由呐喊的时候,又有人说他们虚伪。几乎每一场网络事件,都是在验证表达常识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你我都还在挣扎,但是羽戈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羽戈以喜欢足球和美女自许,践行着竹林七贤的生活态度。在坚守自由和保守底线的民间知识分子和不自由写作者中,王怡抬头叩问上帝,羽戈俯身探询人间。显然,羽戈相信,在市井酒肆之间,同样有至高的真理。
《从黄昏起飞》读后感(三):狂欢年代的心魂书
2002年春天,时为西南政法大三学生的羽戈,因偶然的契机,读到一本名叫《拯救与逍遥》的书,顿时如遭电击:“书中提出的问题化作一柄柄解构的刀子,使我旧时辛苦累积的信念体系轰然崩塌。”从那刻起,他终止了“语言炼金术”的诗歌写作,义无反顾地迫近黄昏的思想之门。6年的过去了,求索跋涉存留的部分印记,结晶为青春菲薄的祭奠:《从黄昏起飞》。
羽戈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基于之前诗歌练习的馈赠,他的文字有着罕见的纯度、密度、精度、力度;同时大量的观察与阅读,使得他的书写也有着许多青年学人无法企及的广度和深度:社会问题、政治思想、文学批评、电影评论……但所有的思考又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现实。正是这一点,促成了我和他的相识。2005年,我在天涯社区不经意读到一篇名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网文,顿时被它那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所深深吸引。作者所指的故乡,是一座皖北小城——阜阳,如今它已被某些媒体形容为“新闻富矿”和“新闻重灾区”。当时我就注意到羽戈的行文,他并没有被无边的愤怒所左右,而是用一种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紧紧包裹住内心连绵翻涌的悲愤。在后来的交往我才得知:他是82年生人。
同样置身没有童谣的年代,当大多数同龄人宛如温水中的青蛙,在游戏和享乐的温柔乡里“沉醉不知归路”,羽戈却突然调转身来,反戈一击,向存在发问。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如此痛楚,它足以动摇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基石。在《焚烧的家园与寻找童谣的一代人》一文中,羽戈不无悲恸地写到:“这一代人,生在了一个不幸的年段。理想主义的沉沦,英雄路的荒芜,道德的覆灭,这些痕迹正是他们为了不再受骗而无奈遗留下的。由于一种对已逝去的那个政治嬉戏年代的恐惧,这一代人在拒绝了伟大的骗子的同时,也拒绝了某些真正的神灵。而拒绝到了极致,他们连现实也不再相信。”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缺失信仰就没有救赎的可能,否则我们的存在只能如一根在虚空中不断飘荡的鸿毛,无法坠地获取力量。怀疑正是信仰的开始,对自我境况的剖析类似于一次刮骨疗伤的自救,在战胜内心的惶惑与恐惧之后,“我们要相信,那幽暗中的眼睛依然是可以仰望天堂的,并且那里,已经为生于1980初的孩子留下了永恒的位置。”
自从尼采指认并宣判“上帝死了”之后,世界进入了真正的午夜,祭祀神灵的庙宇坍塌,广场挤满了狂欢的“空心人”。艾略特曾如是预言: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诗人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镜像:每天都有如此众多的嘘声此起彼伏的在我们耳畔想起,它们汹涌成河,试图淹埋每一个拒绝合唱的个体。羽戈命名当下的时代为“喜剧时代”,它的多元促使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恒久的坚守。它让那些习惯于一本正经“找寻意义”的人们失望,但就是在这样的年代,民主的朝曦才有杀破黑暗的可能。 “大一统”、只有一种声音是可怕的,人们需要荤素搭配的段子,“当政治符号化为娱乐符号,尽管政治的表层还涂抹着深厚的威严光泽,但它的触手无法抵达的地方,它的威慑力正在缓慢削减。” (《从1984到美丽的新世界》) “通过娱乐推进政治的透明化与公开化,让政治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娱乐与民主》)
在公共的言说之外,一种更为内在的书写流淌在羽戈的笔端。这种书写与功利和稻梁无关,它只是尝试制造火种,把内心幽暗的花园照亮。“在一个很特殊的壁架上,在危险与提升之间,他安顿下来,正是在这里,而非别处,他被允许写作”(卡内蒂)。为何写作,这一个难题,它像河流横亘在每一个写作者面前。在《书写的劫难》一文中,羽戈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写作之于我们,既是沉沦,又是救赎。虽然在没有经典的年代,“写下就是永恒”成了绝望的虚妄。但是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救赎是否真的存在?在《救赎与正义》中,羽戈试图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但却是如此牵强:个体的救赎高于一切,关于良知的安稳才至于正当。这不是羽戈的过错,在一艘将倾的沉船上,将自己抢救出来至关重要,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作业向我们索要答案,譬如爱与正义。圣经有云:惟愿公平如洪水滚滚,愿正义如江水滔滔。当爱与正义只是一道单选题,我们又该如何抉择?《爱与正义的辩难》是集中我最喜欢的文字,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它们像一根琴弦紧绷的两端,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合与分。
我承认,阅读羽戈的文字并不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情。这是一场有别于时尚与流行的心魂书写,作者时常把自己逼至孤绝的境地,也让有幸读到它的人坐立难安。没有人告知我们生活是有问题的,也没有人告知我们答案,羽戈的困惑也正是文本的价值所在。加缪说: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所认识的生活作伪证。作为生活某一阶段的见证,《从黄昏起飞》真实记录了“作者与分裂的灵魂进行肉搏战之时的剑拔弩张,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虽然作者自谦说“它充斥着矫情、偏激、武断、浅薄与大言不惭的自得”,但“时代列车的颠簸再过剧烈,终究难以消磨它们的价值。”
让我们期待密涅瓦的猫头鹰的下一次起飞。
而羽戈这只猫头鹰,正是用他近视的眼睛,在昏黄的夕阳下,看穿中西之争的薄暮,看到了古今之争这只老鼠。在同样被阉割出此书的《论吴经熊:超越东西方?》中,羽戈引用了吴经熊的文字说道:
《从黄昏起飞》读后感(五):写下便是永恒
密涅瓦的猫头鹰从黄昏起飞。
——黑格尔
斯人,斯书
从知道这本书的消息,到拿到这本书,我已经忘记过了多久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羽戈已经并非那时的羽戈,而这本书也并非是作者当初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不过“写下便是永恒”,作为羽戈的朋友欢喜总是多过遗憾的。
书中的文字大多曾经见诸报端或是网络,泰半我曾看过完整版甚至是初稿。从这些文字发生的变化中我清晰地看见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它展现了作者与分裂的灵魂进行肉搏战时的剑拔弩张,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
请原谅我对这本书的不甚满意,无论是对于羽戈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这些熟知他关心他的朋友而言,这本书的出版,其象征意义远大于思想意义。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文字,通过羽戈,我们知道在韩寒、郭敬明之外,还有着这样的一个同属于“八零后”的族群:他们阅读,他们思考,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世上的罪恶,他们用文字召唤被遗忘的公义……
羽戈是个有才气的人,他身体里的诗性远胜过他的理性(可能羽戈会极度反对我的这个判断)。从他那常常肆意昂扬,却又被理性紧锁着不至于失控的文字中,我们清晰地看见,在这个年轻的胸膛中活跃着一颗同样年轻的心。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如今一天天的被社会所俘获,在名利场中沉沦,为生计所迫而放弃理想,很欣喜地看到还有我们的同龄人,血仍未冷。而令我惭愧的是,羽戈在他的字里行间所展现的那种思考的冷静和平和的态度——不为外物所迷惑的内心,这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不论这些文章是为稻粮谋也好,还是个体化写作也罢,无法忽视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拥有着坚实的基础,每一个字都是出自作者对现实的思索。而唯有这样的思考,才会让我对作者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感同身受:在这个“夜半”的黑夜中,“诗人何为”?羽戈从诗歌的山峰步入思想的深渊,步履蹒跚而又坚定不移。无疑,作者思考的态度始终如一,虽然在这本书饱受煎熬的4年出版岁月里,作者思考的方向几经变化。与其说这是一本随笔集,不如说这是作者几年来的思想足迹。
不知是我们的幸运或是不幸,,生于这个激变的年代。外部环境、社会思潮的嬗变,既给我们带来了远胜于父辈们的丰富思想资源,又不可避免的冲击着我们并不稳固的心防。羽戈以他敏锐地眼光和独特的思考,为我们展示了这代人在时代中的尴尬处境和思想定位——我们是思想上“丧父”的一代,早在我们成年之前,巨变的社会环境已经把我们小时受到的那些“思想教育”扫进了历史的废纸篓。一直以来,我们就如同一群离家的孩子,无法获得精神上的独立。不断的向西方、向古典乃至向沉寂多年的马克思,寻求精神的支撑。只是那些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遇到这个古老国度中的年轻问题之后,纷纷折戟沉沙。而羽戈在灵魂流浪了多年以后,毅然的回归到现实,而唯有站在了这个坚实的土壤之上,他才真正的踏入了思想之国的门径。
当我们回到这部作品本身,虽然它拥有着诸多无法忽视的缺憾,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看到作者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社会问题、政治思想、文学批评、电影评论……羽戈思想的疆域可谓无所不包,但所有的思考又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现实。让我还是引用羽戈曾经写过的文字,作为对他思考的总结: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美好,但我们依然要拥抱生活
。虽然羽戈说他只相信前半句,但在文字里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他对于希望,毫不怀疑甚至有些倔强的相信着,坚持着,等待着并且找寻着……
喜剧?悲剧?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羽戈的判断和我大抵相同,可能他更乐观一些——他相信大厦终有倒塌的一天,而我不信。
曾经,羽戈提出过“喜剧政治学”这个概念,虽然近年来他不再使用这个词语,但其思想脉络并未发生根本转变。这本随笔集所选的文章,更多的也是侧重于反讽,而非他更擅长的正喻方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羽戈有着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喜剧只是悲剧的另一个表现方式,其精神实质上还是悲剧的。一旦失去了悲剧这个基本的支撑,喜剧就会迅速沦为闹剧、肥皂剧。而羽戈在文中反复提到的“喜剧的反抗方式”,面对着真正的恶的时候,所能起的作用十分值得怀疑。
而真正的喜剧,总是需要我们正是这个充满悲剧的现实世界,面对着淋漓的鲜血,不妥协、不放弃,不低头、不丧胆。而唯有诞生过伟大悲剧的国度,才能诞生同样伟大的喜剧,唯有能在悲剧中流泪的人才懂得在喜剧里放声大笑。喜剧不仅仅是解构,是反讽,过于重视这些技术手段,引来的只是些廉价的笑声。
很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中一向缺乏喜剧的遗传因子。我们无法发现喜剧,因为我们缺乏看到悲剧的眼睛,我们没有同情和悲悯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之上,羽戈想要建立的他的“喜剧政治学”,无疑是空中楼阁。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自己为什么不再思考”,于是我们在周围看到的永远只是闹剧:周老虎、艳照门、提款机事件、TW(汤唯或者台湾)……
不论喜剧或是悲剧,都会有个结果,会有个散场的时候,而这也正是我们期盼喜剧或者悲剧的理由——它们永不重复。而只有肥皂剧,才会毫无休止,不断重复,像跳帧的唱片,像每年一次的**大会。
期待用喜剧的方式消解恶,却又不能消解问题的严肃性,至少在目前我没有看到希望。
文字和现实的叛离
写下就是永恒。
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我来说就是永恒的谶言。
——费尔南多·佩索阿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野草·题辞》
每个人都在老去,尤其是对于还处在青春末端的我们来说。为了成熟,我们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青春而已。
把书中的文字和羽戈现在的书写相比,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时间,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羽戈的文字愈来愈纯熟圆润,而少了当年的那丝轻狂。不得不提出警惕的是,希望老辣的只是羽戈的文字,而不是灵魂。
当然,现实和理想的分裂的确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面临的困境。并且,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人,都败给了现实,放逐了理想,这当然更显得羽戈的卓尔不群。也更让我们期望羽戈能在这条孤独儿艰难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羽戈在后记中声称希望“遗忘”这些文字,我希望这样的“遗忘”只是针对文章内容和当时的思想。这些文字里所折射出的写作和思考的态度,是值得记住并保持的。在羽戈的文字日趋成熟的今天,我有理由产生这样的担心:希望羽戈不要沉溺于玩弄文字的技巧,而忽视那些比文本更加重要的,那些建立在文本之上的,真诚的精神。
当然,和担心相比,我对羽戈更多的是信心和期待。在思想的国度,羽戈依然只是个步履蹒跚的孩子,他依旧年轻,并且日趋成熟。我们拭目以待,“从黄昏起飞”的羽戈,到底会走出怎样一条“思想的荆棘路”?
最后,转引羽戈在后记中已经引用过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算不上评论的书评。
“不论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的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瓦尔特·本雅明
http://www.muouju.com/index.php/archives/xiexiabianshiyonghen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