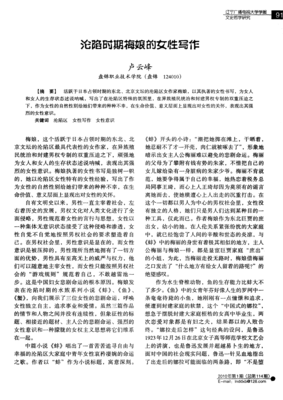原载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
山东大学 马兵
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金色笔记》而被称为“女权主义先锋”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她生命的暮年对自己当年亲身参与的女性运动充满了失望,并为这个“女权先锋”的头衔懊恼不已,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女权主义者希望从我身上找到一种其实我并不具备的东西,那种东西其实来自于宗教……他们希望我能说这样的话:‘嗨,姐妹们,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共同战斗,为了迎来一个再也没有男人的金色黎明。’”她甚至刻薄地宣称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因为过于“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浪费了女性的潜能”,使得其实质扭曲为“看我屁股的运动”。莱辛的说法尖刻,但未必不是有益的提醒。而且,莱辛的反水其实勾勒出了女性主义写作观念递变的一个大致轨迹——在埃莱娜·西苏和露丝·伊利格瑞等张扬女性身体之主体性的理论在全球显示其广泛影响的同时,在法国已经有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些质疑认为“女人本性”与“女性差异”的本质是乌托邦式的,诸如肖瓦尔特和斯皮瓦克等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对这一意义的女性写作表示了怀疑。
借由这个大背景观照自1990年代以来蔓延到新世纪的女性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者也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画出大致同样的路线,无论是林白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妇女闲聊录》的急遽转变,还是铁凝对“第三性”写作立场的强调,抑或是迟子建的“性别和谐论”的主张和严歌苓“超越女性视角”的表述,这些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浪潮中具有表率意义的作家都对冲出男权围城的叛逆写作姿态以及以身体为中心的写作策略表达了反省或拒绝,以为过于强调女性立场会落入新的画地自限。那么再由这个小背景来观照本文要讨论的“80后”女性写作的话题,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在的时代错位之感,女性前辈们虽然为“80后”这代人的登场作了足够的预热,但一来在理论支撑和观念纲领上,“80后”的女作家与前辈们基本上是资源共享的,她们常挂在嘴边的也不外乎是伍尔夫、波伏娃、阿伦特、西苏、米莉特、桑塔格、萨冈这些名字;二来因为前辈们相对地已经完成了从性别对抗到性别和解的路线图,且在对抗阶段集中实践了对男权冒犯、颠覆和瓦解的诸多可能,包括“私人写作”等对隐匿女性经验的呈现,其拓进与局限都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这使得“80后”最早的一批女作家,包括张悦然、春树、笛安、周嘉宁等尝试女性写作的起初显得颇不合时宜,她们勉强赶上一个潮流的尾声,热切地展现稚嫩又激进的女性意图,伴随着青春期特有的扮酷焦灼和不无矫情的叛逆,然而这种写作要么被视为是一种青春亚文学征候,要么被视为是对“70后”美女写作的一种新媒介环境下的复制,始终无法在新世纪文学的女性版图中真正获得一个落定的主体位置。一直等到十多年之后,作别青春、长大成人的她们这代人独特的女性经验和对女性主义走向的看法才显露其不可替代的自足性,她们与新世纪女性写作整体趋势的和而不同的关系也逐渐彰显出其意义所在。
本文的讨论拟从如下三个角度展开:其一,作为“独一代”的她们如何看待以父权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义;其二,在前辈已经过度祛魅的身体写作之后,她们如何看待女性的身体经验;其三,在《方舟》《无处告别》《弟兄们》《相聚梁山泊》等经典文本之后,她们如何书写姐妹情谊。
1因“父”之名
在张悦然的早期作品中,除了几部标志性的长篇之外,短篇《小染》是被提到较多的一篇,一个女孩手刃父亲后又用他的血装点自己苍白的嘴唇——弑父的故事并不新鲜,张悦然在这个小说里借由呓语式的叙述来表达忤逆人伦的凛冽快感,杀戮被唯美化,带着一种青春写作固有的媚俗趣味,但这个小说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将“父亲”的形象和“男人”的形象叠合为一,并确定了通过父女关系表达自己性别思考的写作架构。后来在散文《父亲》中,她说:“我的小说,至少在最初的一些,都是写给父亲的。……当我走向更广阔的实践,面对其他男人的时候,内心却依旧在进行着那场与父亲的战争。”几年后,在一篇访谈中,她又一次强调:“父亲的形象在我的成长中有一种缺席感,父亲当然一直都在,可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少。似乎还是生长在具有男权气氛的家庭里,父亲和女儿很难有亲密的感觉。我想得到父亲的爱,但是我们之间始终不能够达到令我满意的距离。在写作中,我似乎在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①小说中的弑父反而是现实中缩进与父亲情感距离的手段,这种微妙的父权意识为我们观照“80后”的性别意识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窗口。
即便她们本人不一定是独生女,但是作为代际属性的“独一代”还是深深地在“80后”女作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张悦然多次谈到过“80后”是“残缺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她们的孤独情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没有了与之争宠的弟兄姐妹,独生女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性别赋权,尤其在城市家庭中,独生女享受着父母的支持“来挑战对她们不利的性别规则,同时将这些潜规则变得有利于她们的发展。当女儿们没有被排斥在家庭资源之外时,和男孩子一样,曾经和父系制度相连的性别规范也能成为女孩们的工具”②。张悦然的因“父”之名的写作也有类似的意义,父亲那在场的“缺席感”不但成为其写作的起点,投射着自身的创伤体验和成长焦虑,同时也代表着她对女性意识的抒情化的自省,所以,在令人错愕的“弑父”之后,父亲一定会再度归来,并接受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再一次质询与和解。在她2016年出版的备受关注的长篇《茧》中,独生女儿变成了一个固执的“寻父者”,这让小说中的父亲李牧原颠倒性地成为女儿日后生活中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可见,张悦然笔下的“父亲”形象,其实有两层意涵:作为父权的肉身被惯性地批判和质疑,同时为独生女儿的平权提供庇护和照拂,两者之间既有悖谬也有统一。
在祁媛的《美丽的高楼》中,叙述者的丈夫得了肺癌,这让她想起因肝癌去世的父亲,在父亲去世后,“我感到处处是父亲,又觉得处处都在提醒我:父亲死了,不在了,永远的。这两种感觉都极其真实,同时并存,让我迷惑,我思忖这种迷惑恐怕要栩栩如生地蔓延到我自己的死为止”,所道出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满口四川俚语的豆瓣厂厂长薛胜强也是一位父亲,他出自颜歌的小说《我们家》。据颜歌说,这个小说本来确实是想写自己一家人热衷文艺的生活,但是因为不太喜欢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气息”和“教师家庭伦理感”,“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着把主角从语文老师变成了豆瓣厂土老板”。颜歌的父亲希望她能借此写“一个史诗性的故事,讲讲郫县豆瓣的历史”③,但是完成后的小说却戏谑地调侃了父亲的冀望,这不但不是一个史诗性的故事,而且恰恰是反史诗性的。小说的笔墨摆荡在薛胜强的粗鄙和善良之间,通过他在妻子和小三两边的鸡零狗碎,以及与母亲、哥哥和姐姐的亲情嫌隙,形神毕肖地勾勒出一个中年男性的颓败和狼狈。颜歌未必要刻意借这个小说来张扬女性意识,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在小说中基本是一个持续坠落的轨迹,而且段家真正的支撑者是对一切都看得通透的奶奶,这更衬托出父亲的颜面尽失,小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反讽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到其中对父权的拆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说中也有一个“缺席的在场者”,那就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而“我”的身份是薛胜强精神失常的独生女。“疯女人”的设定自然会让我们想到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里富有启发的论述,在《我们家》中,作为叙事者的疯女人虽并未成年,但是因为疯癫,她不但获得了超验的叙事自由度,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家族秩序的内部,荤腥不禁地暴露在平乐镇显赫一方的段家不足为外人道的污浊,她没有实质性地参与任何一个亲人的故事,却对所有的故事了如指掌并抱以嘲谑——这个被家族和父亲舍弃的女儿就这样以自曝家丑的书写完成了自己的报复。
在后起的“80后”女作家中,孙频是相当有辨识度的一位,她几乎没有经历过青春书写的历练,一下笔就深入女性经验的腹地,并以其阴郁和充满疼痛感的文风而被文坛关注。在题为《女人与女人,女作家与女作家》的创作谈中,她如此说道:“如果让我从一个‘80后’写作者的立场来说前辈作家对我的影响,我更愿意选择女性作家而且是‘50后’女作家这个角度。这当然不是说男作家对我没有影响,这仅仅是个角度,大约是因为我觉得女人与女人之间,女作家与女作家之间更容易有一种隐秘的通道在里面。”孙频在这里既解释了自己何以绕开青春期那些扮酷物语的缘由,也将自己接续到新时期女性写作的经典谱系中。她有篇小说,名字就叫《因父之名》,里面巧合地也有一位缺席了十年却以一种心理化的存在纠缠着独生女的父亲形象。田小会的父亲田叶军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了十年,这十年的空白不但让小会的心理有巨大的空窗,急需一种抚慰,她甚至把一棵大树当成父亲的肉身,而且因为失父,她先被六位老师强暴,后为求得保护认残疾人李段做了干爸,实则是沦为他的性奴。无论是亲生父亲莫名逃离又莫名地回返,还是干爸以保护之名的霸占,小会在家庭内外遭遇的双重暴力让她在小说中的自语和质问都成了一份指向父权的绝望诉状。在小说的结尾,田叶军杀死了干爸李段,想以此作为对女儿些微的赎罪。但显然这种赎罪是徒劳的,亲生父亲最后的暴力其实放大了性别场景中的权力意志,而在他与李段争夺女儿的过程中,这种宣示自己父亲位格的意志已经显现无疑。整体来看,因为用力过猛,《因父之名》在孙频一系列表达女性关怀的作品中并不是最出色的,但却是相当有隐喻力量的一篇。波伏娃认为父权的本质是忽视女性的主体性,父亲缺席才不至于让女性成为一个意识紊乱的客体。我们注意到,父亲的空位在孙频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情节设置。就这一点来看,孙频身上的确有着浓郁的“50后”、“60后”女性作家的气质。
同样是写“缺席的父亲”,周嘉宁在《你是浪子,别泊岸》中的处理稍微不同。就像霍桑的《韦克菲尔德》中那个莫名离家的丈夫,小元做地质工作的父亲在她童年时也不辞而别,父亲的消失没有给小元的成长带来过多的精神困扰,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弃儿,只是觉得,她与父亲“像是茫茫宇宙中两颗微不足道的星星,黯淡,但是确凿地知道彼此的存在”,而且在日后与父亲的几次相见中,她在血缘的亲近之外还分明感受到他那种散淡生活信条的影响。小元在小说中并非一个拷问者或质询者,她只是觉得自己和父亲越来越相像,而父亲仿佛成为她与外面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在长篇《密林中》,周嘉宁曾借主人公阳阳之口感慨,“男人才是天生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性别群体,而女人呢,多少都是通过男人才能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这让女性“单独地、直接地,以自己的名义”跟外界对话变得艰难。“80后”的女作家“因父之名”书写的意义也许正在这里,在青春期充满颠覆快感的弑父之后,她们终将发现,那个缺位的形象依然具有一种吸附力,并对长大成人的女儿发出召唤,提醒父女间那悬而未决的关系。
+(作家张悦然)
茧作者:张悦然